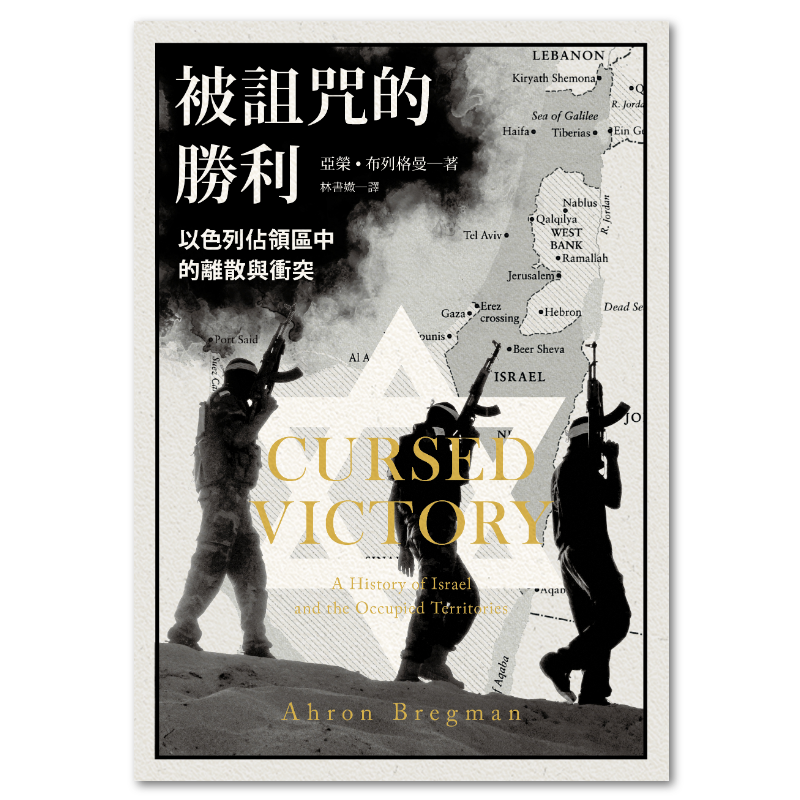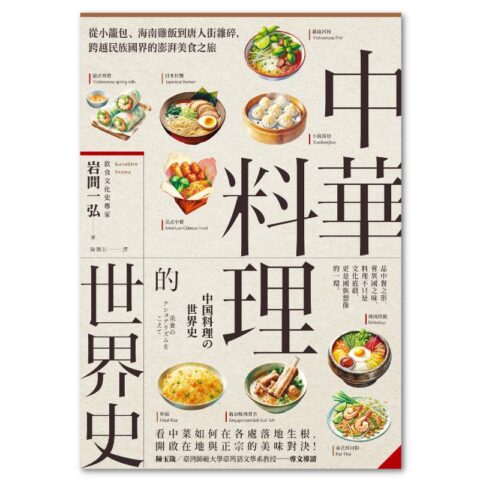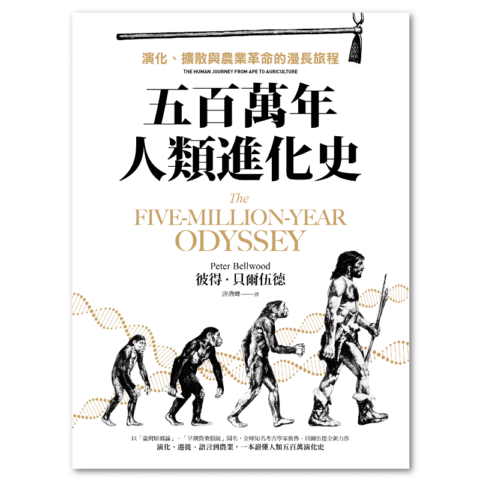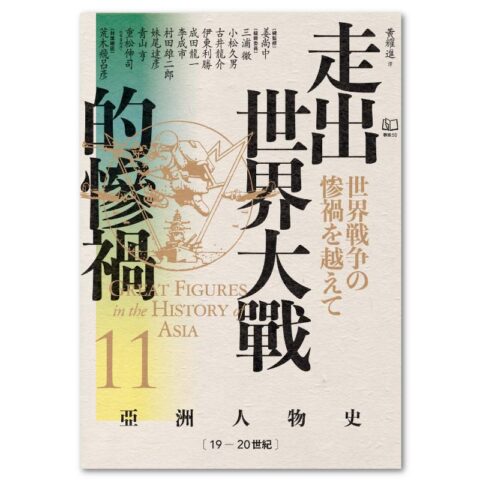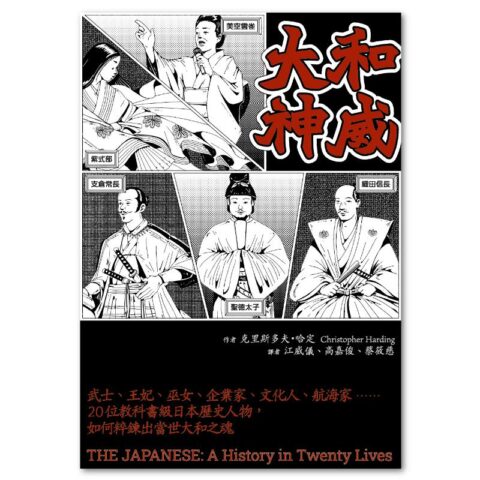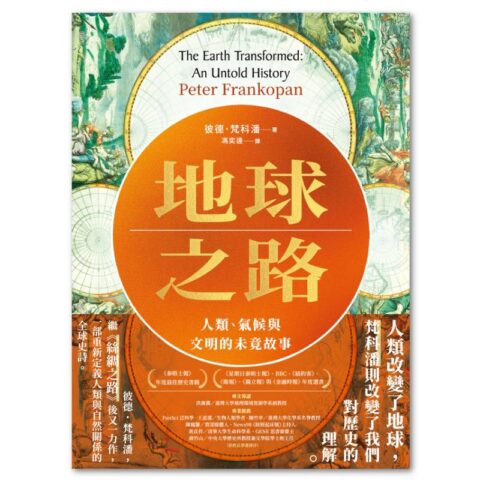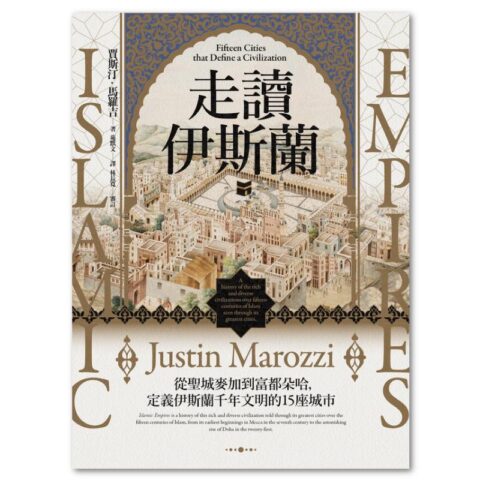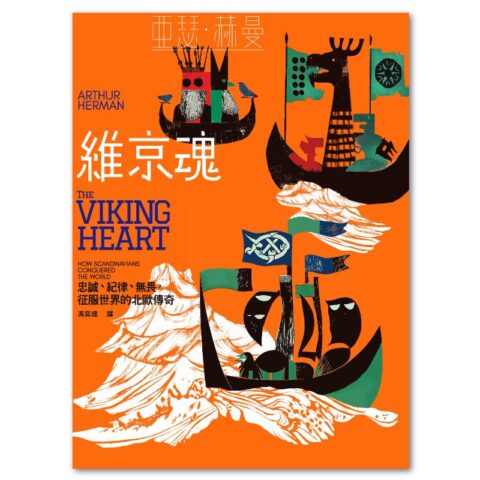被詛咒的勝利: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
原書名:Cursed Victory: 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出版日期:2015-11-13
作者:亞榮‧布列格曼
譯者:林書媺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44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6485
系列:歷史大講堂
已售完
加薩走廊硝煙再起,巴勒斯坦第三次大起義即將爆發?!
巴勒斯坦於聯合國首度升旗,奧斯陸協議岌岌可危。
曾親身經歷南黎巴嫩衝突及黎巴嫩戰爭的以色列前國防軍軍官
對以巴衝突與中東紛爭五十年始末之完整剖析
了解中東紛爭與以巴衝突的第一手完整情報
重回以色列佔領區、奧斯陸協議、屯墾區等新聞進行式的歷史起點
揭露以色列如何從離散的猶太民族成為強權的武裝國家
如何隱身在傷痕悲情下,成為加劇中東戰火、造成難民流離失所的武裝國家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決定對敘利亞、埃及、約旦等國開戰,並驚人地在六天內佔領加薩走廊、西奈半島、戈蘭高地、西岸與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自其於1948年建國以來,阿拉伯人認為以色列佔據了他們的家園,因此無論是南邊的埃及、東部的約旦,還是北部的敘利亞,都不斷地和以色列相互攻擊。在「六日戰爭」之前,鑑於猶太民族過去經歷大屠殺的歷史,以色列一直被西方國家視為悲情的受害者。但這場戰爭改變了一切,「受害者」搖身一變成為「佔領者」。以色列對佔領區人民的軍事鎮壓及對阿拉伯人的迫害,使這場勝利從被賜福的光榮時刻,逐漸成為「被詛咒的勝利」。
布列格曼曾服役於以色列國防軍,並親身參加1982年的黎巴嫩戰爭。他憑藉親身觀察與第一手情報,依循著以色列佔領地政策的曲折經歷鋪陳敘述。布列格曼帶領讀者認識以色列對西岸、耶路撒冷、加薩走廊、西奈半島、戈蘭高地的佔領,佔領區內巴勒斯坦人的動亂與起義,以及以巴走走停停的和平協商。四十多年來蜿蜒曲折的經歷,不但擺盪在兩股背道而馳的驅力之間,更決定了活在占領區中數百萬平民的命運。而阿拉伯─以色列衝突的真正悲劇所在,即在這四十多年間,雙方都犯下了些許錯誤,也造成了不必要的傷亡。衝突及錯誤的累積造成仇恨,也造成以巴兩國人民的悲劇,在「寧要土地,不要和平」的堅持下,這場中東衝突的主角該如何全身而退?
※ 全球媒體一致讚譽:
《經濟學人》:「身為一位曾參與黎巴嫩戰爭的前以色列軍人,布列格曼對他撰寫的主題有第一手資料。做為倫敦國王學院的學者,他已累積了豐富的文件,其中不少是加密且未被公開的。這是一本詳盡並經過深思熟慮而寫成的著作」
《出版人週刊》:「布列格曼極為熟悉他所運用的材料,而他清晰的寫作風格能吸引讀者全面客觀地看待阿以衝突。」
《Open Letters Monthly》:「亞榮‧布列格曼可能是世界上最有資格寫關於以色列自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占領巴勒斯坦一事的人。布列格曼帶領他的讀者穿過以色列占領區內豐富的故事。作者意圖避免在書中情緒激動地謾罵,而他成功地做到這一點。這本書嚴肅地記下瘋狂又邪惡的現實。」
《週日時報(倫敦)》:「布列格曼完美地講述了這個淒慘無望的故事,以及這是如何地悲痛。這是一份不利的判決。」
《Kirkus》:「一本直白又迫切的著作,深刻地批評以色列的政治。」
《獨立報》:「清楚易懂……即時……布列格曼讓這本書超越許多討論以巴衝突的著作。……這是本極易閱讀的研究,也是對那些想了解更多軍事勝利如何變成悲劇的人而言,一個絕佳的開始。」
馬丁•克里費德(Martin van Creveld,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系教授):「這是一本討論以色列占領區以及為何其占領必須盡快結束最好的書。只有深切熱愛他的祖國的人,可以寫出這樣深具豐富性及洞見的著作。」
作者:亞榮‧布列格曼
1958年生於以色列,曾服役於以色列國防軍,於1978年的利塔尼行動及1982年的黎巴嫩戰爭中,以砲兵軍官身分參戰,並被晉升為上尉。退役後,他於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就讀國際關係及政治學。1988年在以色列《國土報》的訪問中,布列格曼宣稱他將拒絕在以色列佔領區內擔任後備軍人,之後他即離開以色列並定居英國。布列格曼取得倫敦國王學院的軍事研究博士,並任教於此。著有《五十年戰爭:以色列和阿拉伯人》(The Fifty Years: Israel and the Arabs)、《以色列的戰爭:1947以來的歷史》(Israel’s War: A History since 1947)、《以色列的歷史》(A History of Israel)及《稍縱即逝的和平:聖地如何擊潰美國》(Elusive Peace: How the Holy Land Defeated America)。
譯者:林書媺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中央大學法文系碩士,現為康乃爾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候選人,譯有《被詛咒的勝利: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
圖片來源
地圖
資料來源紀要
作者誌
導論
關於占領
第一部 第一個十年(一九六七~一九七七)
一、西岸與耶路撒冷
二、加薩走廊
三、戈蘭高地
四、西奈
第二部 第二個十年(一九七七~一九八七)
五、利庫德年代
六、黑色十二月(一九八七)
第三部 戰爭與外交(一九八七~二○○七)
七、起義
八、波灣、馬德里、奧斯陸 (一九九一~一九九五)
九、錯失良機(一九九五~一九九九)
十、戈蘭優先(一九九九~二○○○)
十一、大衛營II (二○○○)
十二、阿克薩起義(二○○○~二○○一)
十三、夏隆與阿拉法特(二○○一~二○○四)
十四、阿猶分離計畫與其獎賞(二○○四~二○○七)
占領進入第五個十年
後記
注釋
參考書目
作者誌
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在驚人的六天內佔領加薩走廊(Gaza Strip)、西奈半島(Sinai)、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西岸(West Bank)與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Arab East Jerusalem)時,我年僅九歲。我還清楚記得,我們第一次的家庭旅遊是到剛被佔領的東耶路撒冷。我們家靠近特拉維夫(Tel Aviv),我們先從那裡搭火車到以色列屬西耶路撒冷(Jewish West Jerusalem),然後坐一段短短的計程車到雅法門(Jaffa Gate),在我們將以色列的里拉幣(lira)兌換成約旦的第納爾(dinar)之後,從那邊走進了舊城(Old City)。
顏色!這就是我首次造訪耶路撒冷的記憶。一切是如此色彩繽紛:廣場上有著形形色色的阿拉伯攤販,戴著他們的阿拉伯頭巾(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阿拉伯人);甜品店銀托盤中裝著滿滿的庫納法(Kunafa),一種用精緻麵條做成的甜點,裡頭塞滿白乳酪、浸潤著糖漿;木製的手推車上滿載著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卡克(cakh)是裹著芝麻粒狀似甜甜圈的麵包捲,它常與渣塔(za’atar)―一種用阿拉伯報紙包起來的混合香料一起賣;那宏麗的圓頂清真寺,它金色的圓頂閃爍照耀著聖殿山(Temple Mount)。脫下鞋子後,我們走入了神殿,我仍然記得那裡的涼爽與寧靜,記得腳下踩著的厚地毯、寫在牆上的阿拉伯文可蘭經,以及四處可見的虔誠信徒時而跪下、時而鞠躬、時而起身進行禱告。然後到了西牆(Kotel),好幾個世代的猶太人曾經在這裡禱告,而我也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下我的心願,將它塞入西牆石縫中。在牆的上方不可觸及之處,在古老的石頭上野草發芽茁長,鴿子也在上面築巢。在我們走過狹窄的鵝卵石巷弄和舊城的蹊徑時,我握緊父親的手,睜大眼睛環視周遭,爬上牆偷偷窺視隱蔽之處,圓頂、石穹頂、紅磚屋頂、尖頂、砲塔、教堂尖塔,植在舊錫罐中的茉莉、金盞花、天竺葵,和教堂的鐘聲。暮色降臨時,我們從一個高而平緩的屋頂上看著耶路撒冷變成金黃色。雖然城牆上滿是子彈刻出的傷痕,但它並沒有讓我們覺得這是佔領。就像是到了國外,到了異國土地,像活在夢裡一般。
十年或更久之後,我才開始面對佔領的現實。在我成為一名以軍的年輕軍官時,我被派遣去巡邏加薩的街道。那毫無掩蔽的穢物、未鋪設的泥地街道、腐敗與惡臭、齜牙咧嘴的狗在黑暗的巷弄間狂吠、(超大的)老鼠在垃圾中穿梭,以及,最重要的,當地人們所展現的赤裸裸敵意使我極度震驚。那是我第一次覺悟到,我實際上是一個佔領者,而他們是被佔領者,不論我喜歡與否,我軍靴底下踩著的,都是佔領地。
十多年後,我成為一個市民與後備軍官,我在尼泊爾的加德滿都放蜜月長假時,再度發現佔領地燃燒著熊熊戰火;這場戰爭很快地將會得到它響亮至今的名號:起義(intifada)。而在這遙遠浪漫的城市角落,一家小店中,我看到一張以色列軍人以來福槍柄毆打巴勒斯坦示威遊行者的照片,我的髮根豎直了起來。這張照片令人悲痛:巴勒斯坦人向上看著以色列人,而這位以色列軍人高舉他的來福槍往下看。我從加德滿都寄了一封信給以色列報紙《國土報》(Haaretz)的編輯,批評以色列人―我的同胞、我的朋友,控訴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犯下如此殘暴的罪行,這是世界上眾多其他族群曾經施加給猶太人的。我的岳父是拉特維夫大學的教授,他在不知道我寄了此信的情況下看到了報導,立即打電話向編輯抗議。他說他的新女婿,一個一九八二年黎巴嫩戰爭的老兵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並要求對方道歉。編輯回答:「﹁教授,那封信現在就在我面前,我可以告訴你,我什麼都沒改就送印了,頂多只改掉一個逗號。」
我在信中寫道,在殺戮結束之前,我不會返家。但是到最後,我無處可去了。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書店撞見了我的一位記者朋友,他抬了抬眉毛問:「是嗎?那你現在在這兒幹嘛?」我沒有回答。但我說,若被軍隊傳喚到佔領地去履行義務,我會明白拒絕。大約一週後,他將這席對話發表在《國土報》週末副刊中,標題為:「榮尼.布列格曼首次拒絕」(‘Ronnie Bregmanrefuses for the first time’)。我頓時感到,如同琳達.葛蘭(Linda Grant)筆下《猶在》(Still Here)的主人翁約瑟夫對越南所做的事情―戰爭是錯誤、不道德的,也是一個恥辱。我不能夠變成他的一部分,因此和約瑟夫一樣,我覺得在這瘋狂的事情結束之前,我必須找到另一個國度,到那裡生活。就我的案例而言,移民到國外可以把我從可預見的前途堪虞中解救出來,避免因拒絕服役―這種在起義前罕見的叛逆行為―而被送進監獄。因此不久後,我搬到了英國,現在我仍然住在那裡。
不論是多麼嚴謹的歷史學家,任何作者都無法將作品與自己的經驗、興趣、品味截然劃分開來,因而我確定本書必然背負著一道印記,亦即,無論是在近如以色列的第一手經歷,還是遠從英格蘭所報導的事件,作者既是當局者,也是旁觀者。如同讀者會看到的,我對於佔領的明確態度和犀利批評,相信會被我的以色列同胞視為賣國行為。寫這本書讓我得以重新省思我所經歷過的年代,並且質疑那些我一直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如同其他作者,我必須決定要含括什麼、刪除什麼:在這麼做的時候,我試圖剔除我的個人情感,盡量客觀忠實地專注於我認為是關鍵轉折點和重要事件的地方,我相信歷史會證明它們值得受到重視。
1 西岸與耶路撒冷
狀如腎形的「西岸」長約一百一十公里,寬五十公里,地如其名,壤接約旦河西岸,也是古巴勒斯坦的心臟地帶,一路延伸到西岸以北、以西和以南的地方。
西岸內部的地理風景並不均質:南部(聖經中的朱迪雅地區)氣候嚴苛、乾燥少雨,其北部(撒馬利亞)卻氣候溫和,土地豐饒。以人口和文化來看,西岸由三個不同的區域組成。南部以希伯崙(阿拉伯語Al Khalil)為中心,是穆斯林社群的發源地,密集而傳統。第二個區域位於中間,以耶路撒冷(阿拉伯語Al Quds)為重心,因為這個城市的獨特地位、國際名聲與絡繹不絕的遊客,使其相對具有國際性。北方以納布盧斯(Nablus)為首,是除了耶路撒冷以外西岸最大的城鎮,當地人較富政治意識與愛國主義,知識階層的文化底蘊深厚,還有勃興的商人與地主階級。
一五一七到一九一七年的四個世紀,這個地區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領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佔領了此處與其餘的巴勒斯坦土地。三十年後,英國撤出巴勒斯坦,那裡的猶太社群人口數不及非猶太巴勒斯坦人的一半,卻旋即在一次短暫的內戰中擊敗了後者,並進一步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宣布獨立。甫建國的以色列隨即與鄰國開戰,這些阿拉伯鄰國反對以色列的存在,希望能夠為戰敗的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重振士氣。戰爭期間,阿卜杜拉王(King Abdullah)的約旦軍隊跨過約旦河,拿下了西岸和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區,那裡有許多至為重要的伊斯蘭聖地。之後,阿卜杜拉王在一九五○年四月的議會中通過了《統一法案》(Act of Unification),將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納入了開國僅四年的約旦哈希姆王國(Hashemite Kin’dom of Jordan)。
國際間對於這我行我素的併吞行為普遍不以為然,其中包括了代表阿拉伯國家的阿拉伯國家聯盟(the Arab League),因為被併入哈希姆王國國土的巴勒斯坦土地,已經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被聯合國指定給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以建立一個與猶太國家比鄰的阿拉伯國家;只有英國和巴基斯坦認可這次的國土兼併。面對如此的反對聲浪,阿卜杜拉王直言西岸的兼併並非無法改變或不可撤銷,他會保管這塊土地直到「巴勒斯坦從以色列人的手中解放」。 雖然兩害相權取其輕:西岸人認為哈希姆王國較以色列政權可接受,但是整體而言,他們對這個新霸主的態度仍然曖昧模糊。他們懷疑這個國王密謀削弱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認同,況且長久以來西岸人都認為自己比新領主進步、高尚,教育程度也較高,因此往往戲稱這些新來者為「落後的沙漠遊牧民族」(backward Bedouins of the desert)。儘管如此,西岸人並不是不知道整合約旦河西岸與東岸具有重大意義,西岸人迄今都向西尋求與世界貿易和對外聯繫的管道,但是以色列國的建立於此築起一道藩籬,切斷西岸的傳統貿易路線,西岸人被迫必須向東找尋新的貿易機會與聯繫管道,也就是朝向約旦河以東。以此角度來說,雖然很少西岸人會將自己看作約旦人,但是與東岸合併、並且將其餘的古巴勒斯坦地區併入約旦,確有其重大意義。
許多西岸人漸漸接受了哈希姆政府,尤其因為一九六○年代的約旦經濟起飛,年成長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三,這樣的繁榮也無可避免地注入西岸。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阿卜杜拉王遭到暗殺,他的孫子胡笙.賓.塔拉勒(Hussein bin Talal)於一九五二年繼承王位後,非常重視西岸的需求,努力將這個區域整合進他的王國。然而,這相對的和平突然在兼併十七年後的一九六七年中止了,以色列先遣部隊佔領了阿拉伯屬東耶路撒冷和西岸,並且炸毀約旦河上的橋梁,象徵性地、同時也是實質上地,重新割裂了兩岸。
以軍步入西岸時,這個地區有大約六十七萬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東耶路撒冷的三萬五千人。在這塊傳統的土地上,生活步調緩慢,大家庭與社區扮演重要角色,一九六七年,隨處可見婦女從井中汲水,農人使用木犁驅牛犁地。但是隨著戰爭爆發,以軍摧毀了整個村落,土地和人民遭受了既快速又戲劇性的變化,萊特龍(Latrun)地區便是一例。
在一九四八年的戰爭中,介於特拉維夫與耶路撒冷中繼點的萊特龍經歷了激烈的戰鬥,以色列派了一波又一波的軍隊反覆嘗試欲攻陷這個約旦軍團的重要根據地,但屢試徒然。現在一九六七年,以軍終於成功地驅離了約旦駐兵,並控制了萊特龍與其鄰近地區,其中包括依姆瓦斯(Imwas)、貝特努巴(Beit Nuba)、雅魯(Yalu)等巴勒斯坦村落。
一九六七年以前,這些農村的生活簡單而平淡,就像雅魯村的八歲孩童艾希(Aishe)回憶道:「人們相處融洽。他們總是坐在一起……村裡有一個中央廣場,人們結束工作回家時都會到那裡去。他們會帶著咖啡和糖,在廣場一起歡樂。當外來訪客來到這個廣場,他會被邀請共進午餐與晚餐。請吃午餐的主人會宰殺一頭羊,分給廣場中的每一個人。」一九六七年發生在這些村落和其周遭地區的事情,我們可以從阿莫斯.肯南(Amos Kenan)―後來成為重要作家的一位以色列軍人口中窺知一二,他回憶道:「我這一團的指揮官說,上級決定要炸毀這些村莊,掃蕩這些謀殺者的巢穴,並且防範未來可能的任何基地滲透者。」他和他的同袍被指派去搜尋村莊中的武裝犯人,「沒有武裝的人都必須在時間內打包好自己的物品,然後離開。」
重型軍械於是被帶了進來,將整座村莊轟成礫石堆;在依姆瓦斯,三百七十五棟房子被摧毀,雅魯有五百三十五棟,而在貝特努巴則有五百五十棟;一萬名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並且從此不許再回到他們的土地上,這些土地有些被分給了以色列軍人,剩下的則變成了國家公園用地。然而,萊特龍事件並非特例,整個西岸的巴勒斯坦村莊摧毀事件廣泛發生於一九六七年戰爭與戰後期間,赫然違反國際戰爭法。然而,最戲劇性且重要的改變發生在耶路撒冷。
改變中的耶路撒冷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東耶路撒冷不只是聖地,也是重要的商業、行政、文化中心,是連結西岸南部和北部的天然交通樞紐。就像在萊特龍等地一樣,耶路撒冷的地方軍隊指揮官親自出馬主掌一切事務,以便在其軍事將領或政要的道德良知不受煎熬的情況下改變地上事實。因此耶路撒冷戰後第一任軍官、後來成為以色列總統的哈伊姆.赫爾佐克(Chaim Herzog)在首度造訪神聖的哭牆(Wailing Wall)時,下令移走一座正對著哭牆的小便斗。儘管這不過是個出於善意的小動作,但卻為日後其他重大改變埋下伏筆。赫爾佐克事後說道:「我們決定善用這個機會,把哭牆前的區域整塊清空。這是個歷史性的契機……」當時在哭牆前有二百多戶糞廠門區(Magharbeh Quarter,阿拉伯語Harat al-Magharibah,或稱摩洛哥區〔Moroccan Quarter〕,意思是摩爾人之門〔Gateof the Moors〕,因為十六世紀時,該地是北非摩爾穆斯林移民聚居之處)的房子,裡面的穆斯林住戶仍住在建於一一九三年的古伊斯蘭建築裡。但是由於糞廠門區位置離哭牆如此之近,因此沒有空間讓猶太人聚集禱告。從一九六七年以前的明信片上看來,哭牆前的建築是櫛比鱗次的。
六月十日,赫爾佐克將軍再度造訪此區時,和尤澤.納爾基斯(Uzi Narkiss)將軍一同命令軍隊拆毀整個糞廠門區,意圖在哭牆前建造一個可以容納數百人的廣場。赫爾佐克日後承認,他並沒有得到任何人授權,也壓根沒有想過要取得拆遷許可。他合理化這項決定的說法是:如果花太長時間等待政府批准,可能會錯失先機。納爾基斯的想法也類似,他提道:「某些情況下不需要牽扯到上級。」猶屬西耶路撒冷市市長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陪同將軍造訪耶路撒冷時,對拆遷的合法性有所疑慮,他諮詢法務部長,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什麼叫合法的情況。快點做,願以色列的上帝與你同在。」
緊接著,官員在糞廠門區挨家挨戶通知,住戶必須在兩小時內清空房子,一百三十五戶阿拉伯家庭(約六百五十人)被迫在推土機拆毀房舍前撤離。有些家庭拒絕離開,被活埋在殘骸之下。當時負責指揮拆除的以色列官員埃坦.本—摩西(Eitan Ben-Moshe)少校在一九九九年受訪時描述:「我們拆除完這一帶後,發現一些拒絕搬離的居民的屍體……」離開的人則來不及帶走太多東西;當年三十四歲,生長在此,於一九六七年新婚的馬赫穆德.馬斯路克希(Mahmoud Masloukhi)帶著家人逃離,「 身上只帶著衣服」 還有黑白相片。另一位居民穆罕默德. 阿布岱—哈克(Muhammad Abdel-Haq)描述,在拆除後數日,他的妻小回到故居遺址,清理善後的工程持續了數天之久,等以色列的推土機清除瓦礫,「我們才可以取回當時來不及帶走的衣服和其他財物」;這道儀式就這樣重複了整整一週。此區約半數的居民祖籍摩洛哥,在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HassenII)的援助下,許多人返回原鄉,其他人則到北耶路撒冷的舒法特(Shufat)難民營找尋棲身之所。
近來被佔領的東耶路撒冷地區中,最受人矚目的非聖殿山(Temple Mount,阿拉伯語Haram al-Sharif)莫屬。這裡原先是西元前十世紀所羅門王所建的猶太聖殿,四百年後重建,復又在西元七○年被羅馬人摧毀。約七個世紀後,穆斯林在同一地點建造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並在突出地表的岩石之上建立圓頂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根據伊斯蘭傳統,先知穆罕默德就是從這裡登上七重天,這裡被視為伊斯蘭第三大聖地。然而,約旦軍隊戰敗後,聖殿山落入以色列手中,人們愈來愈憂心宗教狂熱信徒(不論是哪個宗教)會聲稱此地屬於他們,因而激起流血事件。國防部長摩西.達揚(Moshe Dayan)意識到了這個危險,於是出手干預。
時年五十二歲的達揚,是以色列最偉大的戰爭英雄之一,他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獨立戰爭中,證明自己是個勇於衝鋒陷陣的陸軍元帥。八年後,達揚年方四十一,是當時以色列軍階最高的總參謀長,他與法軍、英軍聯手,成功領軍襲擊埃及。在戰爭中瞎了一隻眼睛的達揚,戴上黑色單眼眼罩,看起來活像現代版的海盜。他是以色列最色彩繽紛、也最備受爭議的人物:驍勇善戰,富領袖氣質,卻也剛愎自用,壯志凌雲,玩世不恭,高傲自負,還帶有些許享樂主義色彩。達揚在一九六七年的戰爭前夕被授命為國防部長,以軍在他的帶領之下大勝阿拉伯。
戰爭結束後幾天,達揚赴西耶路撒冷跟負責聖殿山的穆斯林委員會(Muslim Council)接洽。他明確表態希望所有宗教的信徒都可以自由進出聖殿山,且雖然以色列須負責整體的維安,但是國家並不會干涉其他方面,穆斯林仍然可以繼續如戰前那樣管理聖地。達揚也承認,讓猶太人在聖殿山祈禱可能會被看作挑釁,因此向穆斯林領袖保證禁止猶太人在聖殿山上禱告,猶太人只能在聖殿山下進入哭牆。達揚在回憶錄中記述,雖然穆斯林領袖對新規定「並不十分滿意」,但他們除了接受也別無選擇。
在六月二十三日,五千名穆斯林―其中有一千位來自以色列本土(及至此時,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都還不被允許進入這個聖地)―參加了星期五在聖殿山上的祈禱。以色列很快就顯現出對耶路撒冷野心勃勃的興趣。以色列的終極目標是完全改變此地的地理與人口結構:擴大市區的疆界,將阿拉伯屬東半部和猶太屬西半部合併,從而將過去被分割成兩部分的耶路撒冷統合為一個由以色列統治的城市。
早在一九四七年時,國際社群提議應該將耶路撒冷的特殊現況定為「獨立個體」(corpus separatum),並且維持統一。但是一九四八年戰爭後,卻由以色列和約旦兩方割據:西耶路撒冷,面積三十八平方公里,歸以色列統治;而東耶路撒冷,面積六平方公里,則由約旦統治。後來,兩方築起了一道藩籬,分隔雙方的城市領地,同時在邊境設置地雷帶,在這難越雷池的藩籬中,只有兩處在聯合國監視下得以進出,一者為曼德爾鮑姆門(Mandelbaum Gate),另一者則為錫安山(Mount Zion),但也只有外交官員或者朝聖者在宗教節日時可以進出。
然而,此時以國政府設置了一個特別的行政委員會,以謀建立一個統一的、由以色列控制的耶路撒冷。委員會的某些討論,甚至進一步建議將更廣大的、鄰近耶路撒冷的三分之二的西岸都擴大納入城市中。在這些討論中,達揚是較為中性的聲音,「這是什麼?」他評論一個提議:「這是一個城市計畫,還是國家計畫?」在其他場合他則說:「我知道猶太人的大胃口……但是我不贊成將……有兩萬名〔阿拉伯〕居民的村落〔併入耶路撒冷〕。」
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委員會帶著其最終提案向政府尋求批准。這個計畫將實質地兼併東耶路撒冷,以國的法律會被施行於此地,並且城市的面積將由一九六七年的四十四平方公里擴張到令人咋舌的一百零八點八平方公里。眾行政首長批准了這項計畫,並且進一步爭論應該如何將這次的兼併公諸於世。不若後來的幾年,在一九六○年代,以色列人對國際情勢與輿論都非常敏銳,知道他們擴張耶路撒冷的領土會違反國際法,觸怒國際社會。因此各行政首長無不試圖低調行事,面對以色列媒體時,只說是一連串小型行政事務,因而事態的全貌「不會受到太多宣傳和評論」。
委員會會長暨法務部長雅科夫.新雄.沙皮拉(Ya’acov Shimshon Shapira)向委員會彙報,在與幾位記者討論過後,他覺得「所有的記者都有同感〔並且願意低調處理〕,只有一名編輯認為讓他的讀者知道事情的發展比保守秘密還要重要」。為了確保國外媒體也低調處理,部長建議「進行審查,不得讓任何關於統一耶路撒冷的消息透過出版品或電報傳到國外……」;同時,外交部指示駐外代表避免使用「兼併」一詞,要將政府行動描述為「行政措施」,目的是供應水電,促進大眾運輸,提升教育及健康服務,是「市政整合」而非「兼併」。
許多人暱稱耶路撒冷的新邊界為「菸酒邊界」(the Arak and cigarette border),因為其制定的方式,彷彿讓巴勒斯坦的工廠只能在城市邊界之外生產菸酒,這些不受當時清教徒般的以色列國民所歡迎的產品。這些新邊界制定的方式,也是為了讓兼併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變少,讓耶路撒冷愈「猶太」愈好。
新的地圖繪製完畢,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以方發布命令解散由八名民選委員組成的阿屬東耶路撒冷議會,並補充道,所有市政單位各級機關的阿拉伯官員從此成為「〔以色列屬〕耶路撒冷市的臨時雇員,必須提出工作申請,並且由耶路撒冷市政府決定派任職務」。該命令最後「感謝儒希.哈提卜(Ruhi al-Khatib)先生(阿屬耶路撒冷一九五七年以來的市長)和市議員從以色列國防軍(Israel Defence Force,簡稱IDF)進駐〔阿屬東耶路撒冷〕迄今以來的服務」。就此,擴編的市區併入統一後的耶路撒冷,由首任猶太市長科勒克所管轄。兼併區內的巴勒斯坦人享有永久居留權,可以在以色列居住、工作,參與市政選舉投票,享有以色列提供的福利,在以色列和被佔領區內往來不受限制。想要取得以色列公民權的人,須宣誓效忠以色列,放棄其他國籍(通常他們有約旦國籍),且須通曉一點希伯來文。
達揚的一次舉措尤其大膽,他下令同時拆除所有一九五○年代起就分隔阿屬東耶路撒冷和猶屬西耶路撒冷的水泥藩籬、鐵絲網和地雷區,准許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互相往來。國防部長的這個決定起初引起警方和市長柯勒克的反對,他們害怕流血事件,但在達揚的堅持下,所有將耶路撒冷一分為二的藩籬都被拆除了,這即刻導致雙方人民的交叉遷徙。是夜,市長柯勒克拍電報給達揚:「你對了,」他說。「城市成了一個大型的嘉年華―所有阿拉伯人都在〔猶屬西耶路撒冷的〕錫安廣場,所有猶太人都在〔阿屬東耶路撒冷的〕雜貨市集。」沒有發生任何喋血事件。
儘管政府極力混淆視聽,耶路撒冷的改變仍逃不過外界的法眼: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聯合國大會採取第二二五三號決議(ES-V),要求以色列「廢止所有已採取之措施,就此停止採取任何將改變耶路撒冷現狀的行動」,而以方置若罔聞。以國外交部長埃班派送快遞信件給聯合國秘書長吳丹(U Thant),反覆強調以色列的論點:「兼併一詞是與現實不符的」,並且進一步說明以色列觀點,那些為了整合耶路撒冷所採取的措施都「在行政與市政的範圍內」。
住在現在業已被佔領的西岸與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一開始只是單純地被嚇傻了。誠然,一九六七年六月到七月是公認的「震驚月」(months of shock)―但是一從驚嚇中回過神來,他們立即揚起了抗議以色列兼併的旗幟,並且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發動遊行抗爭。在八月二十六日,被解職的前東耶路撒冷市長阿爾—哈提卜,率領八名阿拉伯貴族,在其巴勒斯坦同胞間分發一張信函,抗議以軍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為,這份信函後來也被寄送到聯合國。它詳細地描寫以軍如何使出渾身解數,欲使其兼併成為地上事實:「以色列佔領區當局……對國際輿論充耳不聞,違背阿拉伯居民的意願,一逕著手實踐兼併計畫,違背國際法中關於被佔領國家的最基本部分……他們……只在禱告的時間給予〔教堂和清真寺的〕通行許可。我們必須嚴正抗議男男女女的穿著和行為完全缺乏禮節,冒犯信徒的宗教情感……猶屬市政府摧毀了無數阿拉伯建築,而它持續採取相似的手法,目的在抹除最後一點〔耶路撒冷〕東西分隔線的蛛絲馬跡……原先在這座城市阿拉伯區所執行的所有約旦法律都被撤銷,被以色列方案和法律所取代,這違反國際法所說,必須尊重執行於被佔領區的法律……佔領區政府無法防止聖地被褻瀆,使世界上最大也最神聖的一間教堂遭受夜盜侵襲。髑髏地痛苦聖母像上鑲著鑽石的王冠被偷走了……佔領地軍隊摧毀了位於〔城〕牆內的大塑膠工廠,造成了兩百位技工與神職人員失業……建築本體被摧毀,而機械設備也被掠奪。」他們在信末聲明:耶路撒冷阿拉伯區與西岸居民堅決聲明,反對所有以色列佔領當局所採取的策略……這個藏在「行政措施」袍子內,試圖混淆視聽的兼併行動,與他們所謂「居民們」的意願相違。任何情況下,人們都不會屈服或接受。
在日益高漲的反對聲浪下,達揚告誡軍隊須在敏感地帶,例如耶路撒冷、納布盧斯、希伯崙等處,部署至少四到六台坦克車,以阻斷可能發生的暴亂。「我們必須處於備戰位置,以立即將他們撲滅。」他說。達揚所給的告誡出人意料,因為我們現在應該已經知道,他對於以色列佔領應該如何進行的哲學與此舉大相逕庭。
達揚的隱形佔領
達揚不僅是人們時常戲稱的「佔領地的蘇丹」(the Sultan of the Territories)―可謂一九六七年對以色列佔領地命運最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他也是唯一有與佔領地阿拉伯人群交涉經驗的行政首長。在一九五六年戰爭後,身為軍隊的參謀總長,他接管被佔領的加薩走廊,當時以色列才剛從埃及那裡得到這塊土地,並且將保管它長達一年。達揚在該地最重要的特色,或許就是他不願意擾加薩當地人民的日常生活。當地人民進行一場大規模抗議佔領的罷工運動―關閉學校和商店―時,達揚傳喚了加薩市(Gaza City)市長,並且告訴他:「如果你關閉商店,只有你的同胞會受苦。如果學校關閉了,是你們孩子的損失。我們不會干預……」
十年後,一九六六年,達揚學到了更深刻的一課。當時他以記者的身分跟隨美軍進入越南,並將切身經歷寫成一本名叫《越南日記》(Vietnam Diary)的書,這本書多為後人所忽略。在書中,他高度批評美國人強制將美式文化、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加諸於越南人身上的行為和企圖。他無法理解為什麼美國人認為越南小孩打棒球如此重要,他觀察到,與其干涉越南人的生活,不如讓他們自由發展、無為而治,美軍可能享有更大的成功。
這個經歷解釋了達揚對耶路撒冷軍事總督赫爾佐克下達的指示,在佔領舊城後,達揚立即敦促他,制止軍隊介入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不要試圖統治阿拉伯人,」他警告督軍,「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我想要的策略是阿拉伯人可以從出生到死亡都不會看見任何以色列官員。」以同樣的理念,戰爭結束後五天,達揚會見軍事指揮官時督促道:不要霸凌〔但阿拉伯人〕。由他們去吧。不要試圖教育他們,也不要對他們說教。若是安全考量……就去吧,用強硬的手腕。〔但是之後〕還他們平靜。讓他們自由活動,不管走路還是坐車,讓他們去種他們的田,做他們的生意……還有,為什麼有這麼多軍人在〔納布盧斯〕城裡?離開這座城。去城外部署。你們不需要被看見。這座城市必須看起來像是沒有被佔領一樣……讓他們覺得戰爭結束了,而且生活沒有任何改變。達揚還要他們撤下西岸司令部和軍事基地的以色列國旗,告訴他們,因為以色列國旗「對阿拉伯人而言是一個可恨的符號,我們不想因為一些不必要的挑釁,讓事態變得更糟」。
如同達揚自己常說的,他珍視阿拉伯文化;在戰爭之前,他時常與阿拉伯村莊的領袖在以色列會晤,並且親訪在以色列南部的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遊牧村落,與他們一同放牧,進入他們的帳篷,坐在地上與他們一同吃吃喝喝。因為這個原因,很多人都說他早期的佔領政策寬大懷柔。然而,我認為他的政策並非導因於寬大懷柔,而是馬基維利主義:他以為讓他的軍隊隱藏在「隱形的佔領」後方,拿掉像是以色列國旗這樣明顯的佔領標誌,就能夠使巴勒斯坦人對現況變得漠不關心,削弱他們對改變的渴望,藉此讓以色列得以永久地抓住這些佔領地。雖然並非信徒,但達揚確將西岸―朱迪雅和撒馬利亞―看作是猶太歷史的搖籃,並且希望以色列永遠保有這塊地。不過他也知道過於明顯的佔領形式只會招致更多反抗。若反抗確實發生,達揚希望是巴勒斯坦父母,而非他的軍隊去處理這件事。有一次,西岸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孩們,發動示威遊行,抗議佔領,達揚召集了當地的巴勒斯坦領導人,告訴他們:「我們不會與這些女孩衝突。這些女孩……他們有家有父母……我們之間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有件事情我們是一樣的―你有女兒,我也有女兒。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會無法控制我們的女兒,或者她們會做出我們不願見到的事情。
達揚的隱形佔領有著另一個面向,他對於約旦介入西岸事務視而不見,允許約旦的第納爾幣(dinar)持續通行。以色列不願意投資佔領地,並且就達揚所見,如果約旦資金可以持續支持西岸,何樂而不為?事實上,胡笙國王持續支薪給當地公務員―老師、醫療從業人員、法官和行政人員,希望透過持續的資金挹注,繼續保有他在此處的影響力,以期有朝一日這塊土地能夠回歸於他;而且在經濟上安定住被佔領的西岸,使當地居民願意留下來,他們就不會蜂擁跨越約旦河,到已經收容過多巴勒斯坦難民的約旦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