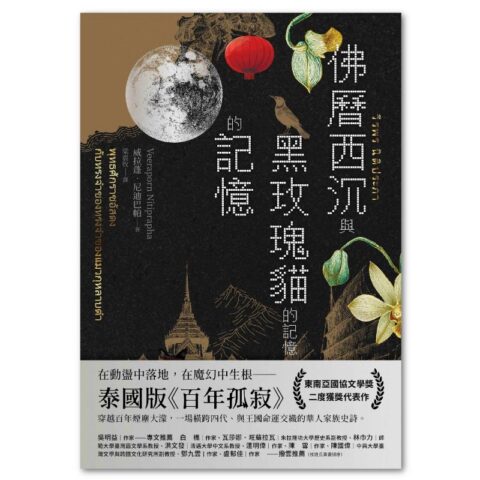樹屋
原書名:ツリーハウス
出版日期:2012-01-05
作者:角田光代
譯者:劉姿君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04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9418
系列:小說精選
已售完
最能直視人類生存極境的溫暖療癒小說
活著該面對?還是逃避?
推薦給總覺得自己人生哪裡不對勁,或者以為只要不是待在此岸,
而在遙遠的彼岸,就一定會有很精采的事情發生的所有讀者。
角田光代融合了時代、家族、生存、死亡的震撼人心最新長篇小說《樹屋》
呈現新舊時代底下「逃避」的各種面貌!
將撥動你生活中最細緻的感覺和記憶!
活著該隨波逐流?還是忠於自我?
希望在哪裡,我就朝著哪裡去?
一個跨越三世代的家庭故事,
一段牽繫中日兩地的戰時回憶。
透過對「逃避」、「面對」的揭露,
《樹屋》讓我們窺見「家」的真實樣貌。
★ 日本三大女作家角田光代文壇二十年的顛峰代表作!
★ 日本產經新聞大阪本社晚報連載一年,大獲好評!書店一致推薦!
★ 榮獲2011年伊藤整文學獎!
「翡翠飯店」這名字聽起來不錯呀!
「飯店」這個詞,在中文裡不是指餐館,而是旅社的意思。
而且,人們相信那綠色的石頭能給人不老不死的力量。
我們全家人,好像天生的DNA裡就有著有氣無力、毫不抵抗、隨波逐流的消極適應力。
祖父母和爸媽守著家裡那間又髒又舊的中菜館「翡翠飯店」,生意不上不下、越來越壞。沒有工作的叔叔要不就在店裡幫忙、要不就整天閒晃。離家多年的哥哥卻在祖父去世沒多久的某一天突然回家,還裝作一副自己從來沒離開過的樣子。久沒聯絡的姊姊這回不但挺了個大肚子回來,還說要把家裡中菜館一樓改裝成拉麵店。還有我,找了三年工作卻仍待業中。
這樣的家,就像簡易旅社。每個人都習慣各自行動,要回家也可以,不回家也沒關係,歡迎來的人,也不阻擋離開的人。唯一的規定就只有「自己的爛攤子自己收拾」,其餘的幾乎互不干涉;碰到事情時的萬能解決法是「那就到時候再說吧!」
我越來越覺得這樣的家,怪極了!可是卻說不上來哪裡奇怪。最怪的是,我竟然從來沒想過也沒問過這個家的來歷!我的疑問像打嗝般一一湧現,祖父的老家在哪裡?奶奶想回去哪裡?我以為爸爸是長子,沒想到戶籍上登記的卻是三男?除了家裡那個無業叔叔之外,似乎還有另一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小叔?再說,我們家的祖墳在哪裡啊?為什麼我們家從來不掃墓啊?
祖母跟我邁開步伐,走入既熟悉又陌生的街道巷弄中,看到了希望與失望,我慢慢了解我們藤代家究竟走過什麼樣的過去,才來到今天這一步……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就是不想死。(祖父泰造)
逃跑更需要勇氣,聽話輕鬆多了。(朋友保田)
我們一直逃一直逃,只想著讓日子好過一些。不是基於什麼崇高的理想,只是因為害怕才這麼做的。(祖母八重)
如果未來不是一直往未知的地方前進,是朝著已經知道的地方走,那該有多好。(小叔基三郎)
我是在摸索如何活下去,而不是做什麼活下去。(叔叔太二郎)
待在那裡熬不住的話,就逃吧。逃避不是壞事。如果心裡知道自己是在逃,就不是那麼糟糕的事。不是只有挺身對抗才了不起。(祖父泰造)
不要不反抗也不逃避,逆來順受地被時代吞沒。(祖母八重)
沒有「假如」。就算後悔,除了現有的以外,什麼都沒有。(祖母八重)
得獎紀錄
2011年第22屆伊藤整文學獎。
作者:角田光代
1967年出生於神奈川縣。小學一年級便立志未來要當小說家。就讀早稻田大學文學系藝文創作組。大一大二時,閱讀了同科系畢業、剛出道沒多久的村上春樹作品,第一次發現跟自己運用相同語言說故事的作家。
大學畢業隔年、23歲時以《幸福的遊戲》獲海燕新人文學獎,而正式步入文壇。四十多歲已出版了百部作品。
作品橫跨純文學與大眾文學,部部長踞暢銷榜,並屢見於各大文學獎之列。分別三度入圍芥川獎及直木獎,曾榮獲日本大眾文學最高獎項直木賞、川端康成文學獎、中央公論文藝獎、伊藤整文學獎等獎項。與吉本芭娜娜、江國香織並列為當今日本文壇三大重要女作家。
創作靈感多源於對大眾習以為常想法的不滿、質疑或憤怒。寫作時間跟上班族一樣,朝九晚五,有拳擊運動習慣。
1990年,以《幸福的遊戲》獲海燕新人文學獎;
1996年,以《朦朧夜的UFO》獲野間文藝新人獎;
1998年,以《我是你哥哥》獲坪田讓治文學獎;
2000年,以《綁架旅行》獲路傍之石文學獎;
2003年,以《空中庭園》獲婦人公論文藝獎;
2005年,以《對岸的她》獲直木獎;
2006年,以短篇小說〈禁錮的母親〉獲第32屆川端康成文學獎;
2007年,以《第八日的蟬》獲第2屆中央公論文藝獎,此作並改編為同名日劇和電影;
2011年,以《樹屋》獲第22屆伊藤整文學獎。
譯者:劉姿君
台大農經系畢業,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課程修畢。曾任職於日商及出版社,現為專職譯者。譯有《樹屋》、《府城的美味時光:台南安閑園的飯桌》、《路》等書。
推薦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小說家 甘耀明
《樹屋》非常適合整個家族一起閱讀與討論。書中每個人看起來有殘缺的記憶與性格,聚在同個屋簷下,無論彼此尖銳對待、忍讓、逃避、摩擦或衝撞,都像是一塊活生生、有稜有角的拼圖,湊在一起便拼成了《樹屋》生動的家族故事。
小說家 林宜澐
角田光代在這一本易讀的長篇小說中置放了好幾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從國族論述的虛假性到個人如何對抗命運等等不一而足,這使得讀者在輕鬆的閱讀過程中仍不免掩卷深思,東想西想地把那些問題連結到自己身上。也就是說,作者提出的大哉問並非遠在天邊,而是近在如小說中泰造與八重一家祖孫三代的平凡生活裡,也在你我讀者的日常生活之中。這是此類具有大眾體質的小說書寫所能達到的一種十分理想的狀態。一路讀下十幾萬字的文章,總該讓自己的靈魂發酵出一些騷動與反思,而覺得不虛此行吧?
喜歡音樂總經理 陳子鴻
樹屋,聽起來像是一個編織夢想的地方。在台灣長大的我們,家裡有後院可以蓋樹屋的不多,但我們總是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小角落編織屬於自己的、不切實際的夢想。小時候躲在棉被裡開手電筒畫漫畫;念書的時候買的日記本還要上鎖;當兵的時候在上下鋪的夾層藏照片;工作的時候在分機下面用便利貼寫滿座右銘卻從來不記得看;多年以後終於存到錢蓋了自己的錄音室,每天把自己關在裡頭創作出一首又一首的音樂。這些角落,都是屬於自己的「樹屋」。
作者從日本人的角度,看到與我們印象中歷史課本裡不同的滿洲國,時空的交錯帶到現代的日本與中國,從第一代爺爺奶奶帶著憧憬來到滿洲國,為了保命逃回日本,讀來引人入勝欲罷不能。
如同很多卓越的企業,一開始的目標,其實只是為了求生存。作者說:「有時候逃避也是一種追尋。」那麼我們應該省思,自己到底是在逃避還是在追尋呢?我想勇敢的活著,才是我們所該追尋的目標吧。
創作歌手 鄭宜農
這本書並非開頭就馬上揪緊心臟的類型,也沒有讓人著迷不已的人物,事實上,這個故事裡每一個角色都有他卑劣的一面,他們都是在不斷逃避的人生中,為了存活緊緊抓住了什麼不夢幻也不令人景仰的東西。但看到後面我好幾次忍不住哭了,明明是那麼直率的袒露人的醜陋,卻又可以在醜陋背後,織一張溫暖的網。那或許是所謂的羈絆,或許是在漂泊無根的歷史洪流中,在看不見未來的不安中,一個努力活下去的理由。這些基本的人性,讓我們在悲傷的故事裡仍可以看見希望,我想角田光代一定有一顆很用力的心吧。
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笹沼俊暁
當學生的時候,我送過報。每天很早起床,在昏暗的天空下帶著一疊疊厚厚的報紙騎機車繞來繞去。那時我的責任區是一個農村,可是那裡巷子很複雜,常常迷路,而且大部分的村民都有著相同的姓氏,所有的房子門口都掛著一樣的名牌。如果送錯的話公司會被罰款,所以我一個禮拜後就辭職了。幾年後,我在市立游泳池打工,發現一位同事就是那座村莊的人,當時他已是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他說他出生於滿洲,日本戰敗後穿著尿布上船「回國」。我問他有沒有當時的記憶,他說完全不記得。再幾年後,我從研究所畢業,離開日本,開始在花蓮教書。學校附近有個叫做「吉安鄉」的地方,以前日本開拓移民團住過那裡,當時叫做「吉野村」,可是六十年前所有的日本人都「回國」了。
之前我沒辦法想像那些移民者心裡的感覺,怎麼工作,怎麼交朋友,怎麼談戀愛,又是帶著什麼心情死去。在《樹屋》這本書中,角田光代詳細得描寫滿洲移民和他們家族的歷史。作者的想像力引領我們看到在「大東亞共榮圈」裡和戰後日本平凡的個人如何努力生活。
從小到大,良嗣都不會拿自己家和別人家比較。因此長久以來,他都把自己的家當作所有家庭的基準。
他以為每一戶人家都有祖父母和雙親,有無固定工作的親人同住。也以為店和家的界線模糊,一年到頭都熱鬧滾滾。
當然,只要到朋友家去玩,就會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大多數的人家父親都不在家,大多數的人家都靜悄悄的,也沒有父母和祖父母之外的親戚無所事事地住在家裡。但在良嗣心中,他認為這些人家才奇怪。良嗣在進入青春期前,甚至還同情別人家,認為他們「反常」。例如他會覺得:他們家好可憐,白天爸爸不在家;他們家好可憐,沒有爺爺奶奶,也沒有親戚;他們家好可憐,每天都這麼安靜。
他開始覺得不對勁,是長男基樹大學休學、到國外流浪,而且同一時期姊姊早苗化起當時流行的怪妝、不斷外宿的時候。這時良嗣即將從國中畢業,班上有好幾個人已對將來有所展望,因此早已決定好志願的高中。良嗣心想,我們家和別人家好像不太一樣。可是,究竟哪裡、如何不同,這時候他還說不上來。
啊!我們家就像簡易旅舍──他能夠順利以語言形容自己家裡與眾不同的氣氛,是高二必須認真思考畢業後的方向時。每個人都各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要回家也可以,不回家也沒關係,唯一的規定就只有「自己的爛攤子自己收拾」,其餘的幾乎都不干涉也不關心。自己不管說要上大學,還是說要離開東京去工作,或是說要直接留在家裡,恐怕祖父母和父母一樣都只會說聲:「噢,是嗎。」
然而,良嗣並未因此感到不滿。雖然和別人家不同,但他本來就不知道別人家是什麼樣子,而且不關心不干涉,說輕鬆倒也是很輕鬆。只不過,的確是有種沒有根基的不踏實感。那種不踏實,就好像相信自己站在地面上,卻發現自己其實是站在薄冰上;以為根已牢牢向下扎,根卻早已腐爛。但實際上,輕鬆往往勝過不踏實。當良嗣報考的學校一一落榜,決定要上一般人口中的三流大學時,雙親也只說了一句:「學費要自己付」。即使如此,考慮到自己家住新宿,和要租房子的學生比起來,良嗣仍不得不承認自己占了地利之便。三年前,以「就是覺得不太對勁」為由而辭掉食品進口公司的工作時,父母也只說:「要補貼伙食費」,沒有責備他,而他找工作一拖就是三年,但父母至今也沒對他囉嗦過。一想起有朋友被要求繼承家業而不情不願地回老家,還有朋友找不到工作、至今仍住在沒有浴室的破公寓,良嗣便會老實承認自己運氣很好。
然而現在,良嗣懷著至今未曾有過的心情,開始認為家裡怪怪的。他所感覺到的奇怪,不是和別人家相比的結果,換句話說,不是相對的「奇怪」,而是絕對的「奇怪」。而且這個「奇怪」,比他以前思考過的還要負面得多。
此刻,藤代一家人都坐在拉上鐵門的「翡翠飯店」店內。太過明亮的日光燈照著店裡所有的一切──油煙燻透的天花板,牆上寫著菜名的發黃木條,三合板的餐桌,紅色吧台,裝免洗筷的銀色筷盒,沾滿油垢、黑袜袜的抽風機,掛在牆上的中式炒菜鍋和深湯鍋。今日子和母親坐在吧台,父親和太二郎坐在靠牆的桌子,祖母坐在放在廚房裡的圓凳上,良嗣在最靠裡的那張桌子,和昨天回來的早苗面對面坐著。吧台上放著裝有骨灰的盒子和祖父的遺照。昨晚守靈,今天下午舉辦了告別式。
姊姊早苗是在昨天午後,家人忙著準備守靈時突然回來的。也不知她是哪裡弄來的,身上穿著一件非常合身的喪服。而全家人一看到早苗,就不能不去看她的肚子。因為她的肚子不自然地隆起,一眼就看得出她不是變胖,而是懷孕了。「妳是怎麼了?」母親這麼說,但早苗理所當然般回答:「什麼怎麼了,不是要辦葬禮嗎?有什麼我能幫忙的?幾點要出門?地點是在哪裡?」像是要迴避話題般連續發問,結果由於接踵而來的紛亂,母親「怎麼了」這個真正的問題沒再被重提,早苗也就樂得不回答。
「啊啊,好累。來喝個啤酒吧!」
今日子這麼一說,太二郎便走進廚房,開始發店裡使用的玻璃杯。今日子站起來,從冰箱裡拿出瓶裝啤酒,為每個人斟酒。
「啊,妳不能喝吧?」今日子停住為早苗斟啤酒的手。
「只喝一點點應該沒關係,一口就好。」早苗這麼說,今日子便幫她倒了半杯啤酒。
「那麼,敬爺爺。」
父親以莊重得可笑的聲音說。大家低下頭,高舉玻璃杯。儘管突兀與厭惡在內心交雜,但良嗣還是跟著大家這麼做。
「晚飯怎麼辦?」
「我不餓。中午的便當份量好大。」
「我把剩的拿回來了,所以要吃便當的話還有。」
「不會吧,妳帶回來了?怎麼好意思?」
「不帶可惜呀!那些都是要收錢的。」
「那,我來吃好了。」
「你要吃?要不要熱一熱?」
「不用、不用,冷的就好。」
「倒是店裡,怎麼辦?什麼時候要開店?」
「上週進的食材八成已經不能用了。星期三開吧?」
「星期三?不會太早嗎?乾脆休到頭七吧?」
良嗣啜飲著啤酒,一面聽著彷彿祖父沒死般的對話。心想這些人果然很怪。而且覺得剛才好像有點理解他們「怪」的理由了。
會不會應變得太快了?家裡有個人忽然不見了,就接受事實。有人回來了,也不問理由就讓他回來。這麼做不是因為寬容,而是怕麻煩。現在良嗣這麼認為。不應該在那裡的誰出現了,就習慣他的存在;應該在那裡的誰不見了,也立刻習慣。心中存疑、試圖恢復原狀、加以訂正這種事,一概不做。對於祖父不在這件事,看樣子這些人也已經習慣了。還沒傷心就先習慣了。假如早苗就這樣在家裡住下來生孩子,大家應該也不會產生疑問,就這麼習慣吧。這顯然很奇怪。良嗣正思考著這個問題,只聽一直保持沉默的早苗冒失地興致勃勃地說:
「要不要把店裡改裝一下?」
「咦?妳在說什麼?」母親彷彿聽到笑話般笑了。
「我們這家店,從很久以前客人就數得出來了吧!維持反而更花錢吧?不如乾脆重新改裝?我想過了,把這裡改建成三層樓。一樓開現在流行的排隊拉麵店,然後二樓賣正統中菜。我覺得會比現在好。」
「哪來的錢?」父親從廚房後面取出一公升瓶裝的清酒,往內緣沾有啤酒泡的玻璃杯裡倒,一口氣喝光。
「拿土地去擔保借錢就好啦。生意好起來就能還錢。我覺得至少會比現在好。」
「先別說這個,妳的孩子什麼時候出生?父親是誰?怎麼沒來?」
良嗣鼓起勇氣問。每個人都轉頭看良嗣而不是早苗。
「孩子當然有父親啊,這不是廢話嗎。我們還沒有登記,所以我想沒有必要叫他來。然後,我想過了,叫這孩子的父親去學一學,讓他開一樓的拉麵店應該不錯。爸媽就照現在這樣,在二樓賣中菜,這樣不是很好嗎?」
「別傻了。要做出有人排隊的味道,哪有那麼容易。」
「那,孩子到底什麼時候會出生?」母親問。
「十二月。」簡短回答之後,早苗又看似機伶地說:「再這樣開著又舊又髒的店,也不會有未來呀。我認為正好趁這個時候好好想一想。」
「的確,這也許是個好機會,反正再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撐不下去的。」太二郎不經大腦就開口的語氣,就和前天在咖啡店時一樣。
瞬間,大家都閉上了嘴,店內靜悄悄的。良嗣往坐在廚房祖母看了一眼。隔著吧台的祖母,正默默地望著雙手握住的玻璃杯。不知是不是心灰意冷,自祖父去世的那一天起,祖母就幾乎沒有開口,看起來只是在發呆,倒不像是很傷心,因為祖母沒哭(家裡也沒有人哭就是了)。大家自顧自地談起改裝,祖母不知作何感想,從她的表情完全看不出來。父親彷彿要逃避這陣沉默般,打開了店裡的電視。架在靠近天花板位置的膠框電視,傳出廣告熱鬧的聲響。
「奇怪?」母親突然站起來,「剛才玄關是不是開了?」
「咦,什麼聲音都沒有啊。」
「沒有嗎?你去看一下啦,我覺得門好像開了。」
父親在母親的催促下站起來時,走廊的確傳來大踏步的腳步聲,一名男子從分隔住家與店面的布簾中探出頭來。是哥哥基樹。所有人都傻楞楞地看著基樹。
「咦?怎麼了?大家都穿得好像去參加葬禮。」多半是沒料到所有人都在吧,不知是害臊,還是純粹只是吃驚,基樹說這句話的聲音高了好幾度。
「就是有葬禮啊。」看似吃驚又無力的父親說。
「咦!喪禮?啊!」基樹的視線停留在吧台上的遺照,張著嘴看得出神,「爺爺!」
「就是辦你爺爺的葬禮啊。」父親重複。
「這樣啊,這就叫作心電感應吧。我總覺得有人叫我。啊,得上個香。欸,沒有香可以上啊。好吧,那就算了。不過,能趕上真是太好了。爺爺,是你在叫我吧。」基樹劈哩啪啦說個不停,同時做出良嗣眼裡十分做作的動作站在遺像前,雙手合十,深深低頭,就這樣定住不動。基樹不是個多話的人,良嗣認為他會這樣連珠炮發,多半是出於內疚。眾人瞪大了眼看著基樹躬身禮拜的背影,但等他一抬頭,便又轉移視線。
「你都在做什麼呀你,真是的。」母親嘆息著說。
「阿樹,你肚子餓了吧?有剩的便當。」生性從容的姑姑平靜地對基樹說。
「那我就不客氣了。我也可以來點啤酒嗎?哎,不過,真沒想到爺爺會去世。雖然也可以算是壽滿天年,可是就是不會想到家人會死啊,總以為是不死之身。不過,對喔,爺爺走了,以後就冷清了。咦,早苗,妳肚子好大啊!結婚了?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哎,葬禮也是,沒幫上忙,真的很不好意思。」
基樹低頭行了一禮,便擅自從廚房拿來玻璃杯,在良嗣身旁坐下,自己倒起啤酒來。今日子在一口氣喝光啤酒的基樹前面放下便當。基樹一開始大口吃便當,眾人似乎便對睽違許久的長男失去興趣,紛紛看起電視或倒起啤酒。沒人說話,只聽到電視聲和基樹咀嚼便當的聲音。良嗣半蹲朝著櫃檯伸手拿搖控器。搖控器包了保鮮膜防污,但因為從來不換,保鮮膜反而黏黏的。良嗣無意義地轉換頻道,停在新聞節目。因為新聞正在特寫客運劫持犯的照片。
小說家 林宜澐
過去的不會消失──談角田光代小說《樹屋》
角田光代在這一本易讀的長篇小說中置放了好幾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從國族論述的虛假性到個人如何對抗命運等等不一而足,這使得讀者在輕鬆的閱讀過程中仍不免掩卷深思,東想西想地把那些問題連結到自己身上。也就是說,作者提出的大哉問並非遠在天邊,而是近在如小說中泰造與八重一家祖孫三代的平凡生活裡,也在你我讀者的日常生活之中。這是此類具有大眾體質的小說書寫所能達到的一種十分理想的狀態。一路讀下十幾萬字的文章,總該讓自己的靈魂發酵出一些騷動與反思,而覺得不虛此行吧?
小說的故事涉及三代,祖父母泰造與八重當年各自因為不同的原因遠赴中國東北的滿州國。泰造是在聽了一場移民滿州的政策說明會後,「體內開始感到一股蠢蠢欲動的興奮感」,「腦中滿滿都是那從未見過、從未想像過的光景,凝目眺望遠方的地平線,那無窮無盡的開闊世界,慢慢與自己的未來重疊。」結果事與願違,到了環境惡劣得可怕的移民屯墾區後不久,他開始逃亡生涯,但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他雖逃出屯墾區到了繁華的新京(長春),卻還是得面對日本在二戰末期窮途末路的命運,他必須繼續逃出國家機器所撒出的徵兵大網,才有最大的機會活下來。泰造便這樣用迥異於當時主流價值觀的茍活哲學,一路從長春活(逃)回了東京,還與八重建立了一個家庭。這樣的存活之道,要如何對得起為「東亞共榮」的崇高理想而戰死的皇軍呢?
為此,作者透過泰造的腦袋瓜發出一連串樸素的問題,「對於五族共和與國家毫無概念的自己,為何要每天餓著肚子抱著槍?為何要心驚膽顫就怕槍聲響起?為何要莫名其妙地挨打?」更荒謬的是,隨著日本的敗戰,他們曾經所屬的「滿州國」消失了,經過艱難的撤僑過程(死了一個幼兒)回日本後,這批來自滿州的日本人因為物換星移人事全非而成了無根之人。原來一切都是謊言,國家、聖戰云云無非是自欺欺人的虛幻口號。祖母八重在一甲子後重回新京,發現許多當年的建築在現今中國的旅遊文字說明中充滿著「偽」字,偽滿州國、偽長春……,也因此更形諷刺地印證了當年那異鄉之國原是建立在虛幻流沙之上的事實。其實不只那個東北之國,當年太陽旗底下所發動的每一場戰爭也都同樣地虛幻,而且罪惡。
泰造的逃,至此便理直氣壯了起來。平民百姓的所愛所憎畢竟才是歷史的主體。角田光代在這裡所顯露出來的觀點又左又低,完全承認並接納小老百卑微慾望的正當性,這對終戰迄今依然存在的諸多右派軍國主義者來說,難免是刺耳難聞的呼喊吧。
因此,祖母八重六十年後重返新京之旅的意義就在於,她用極度溫情(甚至浪漫)的尋夢心情,回到一個她跟泰造曾經休戚與共,但與龐大的國家論述不必然相關的歲月,那段歲月裡邊有血有肉,深刻地影響了她與泰造的一生。「時間會過去,但過去不會消失。」人比戰爭更強韌,戰爭會過去,戰爭底下的人性卻永遠存在。八重浪漫地懷念那段歲月裡的人與事與物,她孫子良嗣陪她到了長春街頭,「跟著祖母下了計程車。祖母筆直地走在人行道上。不像剛才那樣四處張望,簡直就像要去見什麼人,而且她已經看到那個人似的,腳步堅定確實。」那個人是誰?那個人就是無暇理會軍國主義大纛,而認真生活的每一個小老百姓。「時間會過去,但過去不會消失。」祖母八重用一生的辛苦體會到這個秘密,而在死前渾然天成地實踐了其內在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