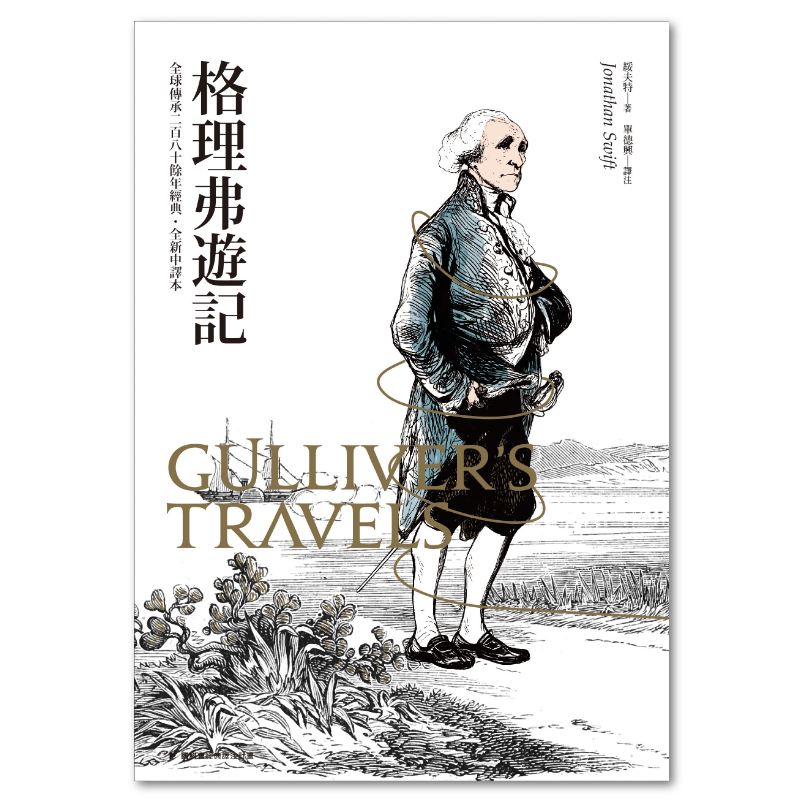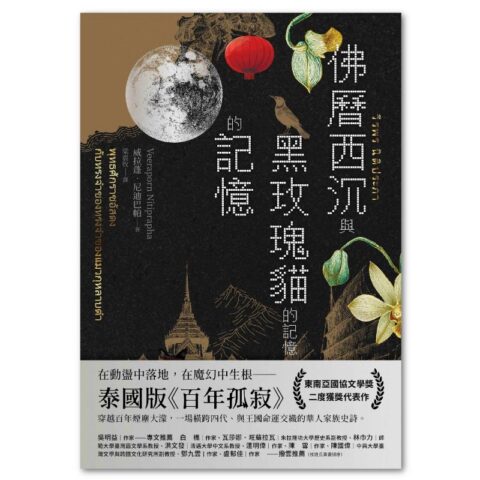格理弗遊記(普及版)
原書名:Gulliver’s Travels
出版日期:2013-05-02
作者:綏夫特
譯注者:單德興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76
開數:25開(21×14.8cm)
EAN:9789570841619
系列:聯經經典
已售完
《知識分子論》作者薩依德:《格理弗遊記》作者綏夫特是最偉大的英文文體家。
《一九八四》作者歐威爾:如果要毀掉世上所有的書,只保存六本的話,我一定會把《格理弗遊記》列入其中。
‧英國《觀察家報》及挪威讀書俱樂部評選為「史上最偉大的一百本小說」之一
‧全球傳承二百八十餘年經典之全新中譯本
‧與同時代《魯濱遜漂流記》並列翻印最多次的暢銷著作
中央研究院學者單德興精心譯注
《巨流河》作者、台大外文系名譽教授齊邦媛傾心推薦
遭逢海難的格理弗,流落他鄉,展開一連串異國之旅。在小人國的格理弗食量超大,身為巨人的他看盡人類的渺小;他為小人國建立奇功,深受皇帝的倚重,卻遭受其它大臣誣陷,不得不離去。在大人國,國王處理政事的態度令格理弗相當好奇:只要有人能使原先長出一枝稻穗的地方長出兩枝稻穗,他的貢獻就比任何政治人物來得大。漂浮在天空的「飛行島」對人民實行高壓統治;附近諸島上有人可以長生不死,卻活得很不快樂;有人可用魔法召喚死者,詢問歷史真相。慧駰國把人類當作低等動物「犽猢」(Yahoo)看待,暴露出人類的劣根性……
風行全世界將近三世紀的《格理弗遊記》結合文學與人道關懷,以異域遊記透視人性本質,藉由小人、大人、慧駰、犽猢對照人類的罪惡與貪婪;作者張望世界,為的是在瑰麗的想像中追求人類的美與善。本書是奇幻文學的先驅,更是挑戰人性的試煉之旅。
作者:綏夫特
綏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父母親為英國人。他往返於都柏林與倫敦之間,出入於文壇、政界與宗教界,為新古典主義代表作家,擅長諷刺文體,後因文賈禍,得罪當道,未能如願在倫敦獲得任命,於一七一三年擔任都柏林聖帕提克大教堂總鐸,直到一七四五年去世。
文學史家公認綏夫特是最傑出的英文諷刺作家,善於運用犀利的文筆,為民喉舌,伸張正義。〈野人芻議〉(“A Modest Proposal”)為最著名的英文諷刺文,流傳最廣、影響最深遠的則為《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自一七二六年問世以來風行全球,老少咸宜,已成為家喻戶曉的世界文學經典。
譯注者:單德興
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美國加州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訪問學人,曾獲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三次),第五十四屆教育部學術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著有《銘刻與再現》、《反動與重演》、《越界與創新》、《翻譯與脈絡》、《薩依德在台灣》等,譯有《文學心路》、《知識分子論》、《禪的智慧》、《權力、政治與文化》等,並出版訪談集《對話與交流》及《與智者為伍》。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文學、亞美文學、翻譯研究、文化研究。
航越小人國─齊邦媛推薦序
《格理弗遊記》普及版序
啟事
格理弗船長致辛普森表兄弟函
編者致讀者函
第一部 小人國遊記
第二部 大人國遊記
第三部 諸島國遊記
第四部 慧駰國遊記
注釋
人物與地名表
綏夫特年表
有關此譯本的幾點說明
前言(節錄):中外翻譯史上罕見的誤譯/單德興
在中外翻譯史上,像《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舊譯《格列佛遊記》、《格利佛遊記》或《大小人國遊記》)這般普受歡迎、卻又遭到誤譯與誤解的作品甚為罕見。誇張地說,《格理弗遊記》的中譯史本身便是一部誤譯史,因為這部英文經典之作在易「文」改裝後,改頭換面程度之大不僅是「一新耳目」,甚至可說是「面目全非」。於是便出現了弔詭的現象:一方面《格理弗遊記》在中文世界裡幾乎是人盡皆知的兒童文學、奇幻文學之作,另一方面這種盛名反倒掩蓋了它原先在英文世界的經典地位,以及作者綏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身為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諷刺作家的評價。
綏夫特的生平簡介
綏夫特於1667年11月30日出生在愛爾蘭的都柏林,父母親都是英國人。他於1682年就讀當地最高學府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1686年獲得學士學位,1688年前往英格蘭,擔任田波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的秘書,1692年獲得牛津大學碩士學位,1702年獲得三一學院神學博士學位。
倫敦是當時政治、經濟、宗教、文學的中心。綏夫特穿梭於倫敦與都柏林之間,一方面希望在英國文壇謀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有意往政界發展,涉入惠格黨(the Whigs)與托利黨(the Tories)之爭,以致得罪當道,未能如願在倫敦獲得任命,只得於1713年6月接受都柏林聖帕提克大教堂總鐸(Dean of St. Patrick’s Cathedral)一職,直到1745年去世,前後長達32年。
愛爾蘭在政治、經濟上長期遭受英格蘭剝削,綏夫特心中甚為不平,提起如椽巨筆,充當被壓迫者的喉舌。時值新古典主義時期,諷刺文體(satire)盛行,他便以此文體撰詩為文,諷刺時事與人性。〈野人芻議〉(“A Modest Proposal” [1729])藉由「野人獻曝」的手法,建議愛爾蘭窮人將嬰兒賣到英格蘭充當佳餚,既能減輕人口壓力,又可賺取收入,為英國文學史上最有名的諷刺文。
在他的眾多著作中,流傳最廣的就是1726年10月28日於倫敦出版的《格理弗遊記》,不但頗受英國人矚目,廣為流傳,不少人針對書中影射的人、事對號入座,以此為樂,而且得到外國青睞,譯本紛紛出現。由於有些諷刺過於露骨,倫敦書商莫特(Benjamin Motte)於初版時唯恐因文賈禍,於是增刪、改寫。綏夫特甚為不滿,九年後在都柏林書商福克納(George Faulkner)出版的作品集中,納入親自修訂的《格理弗遊記》作為第三冊,書前特以主角格理弗的名義撰寫一函,批評遭到竄改的版本。
綏夫特四十歲左右罹患梅尼爾症,導致暈眩、重聽。七十歲之後,痼疾益發嚴重,逐漸喪失記憶與心智能力,於1745年10月19日逝世。綏夫特終生未娶,身後與紅粉知己瓊森(Esther Johnson)同葬於聖帕提克大教堂的地板下,遺產的三分之一(一萬一千英鎊)在都柏林設立聖帕提克醫院,至今依然是愛爾蘭著名醫院,以治療精神病聞名。他除了為愛爾蘭伸張正義,發揚人道精神之外,最大的遺產便是他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格理弗遊記》。
必也正名乎?
Gulliver’s Travels原名“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寰宇異國遊記」),在中文世界裡最為人知的譯名是《大小人國遊記》。其實全書共有四部,依序是主角到小人國、大人國、飛行島等國與慧駰國的冒險記聞。《大小人國遊記》一名簡單明瞭,響亮易記,文字對稱,其實不僅在內容上腰斬了全書,而且在名稱上以音害義,掉反了原書的順序。
《格列佛遊記》或《格利佛遊記》之名較忠於原作,也往往保留第三、四部,但此譯名仍有商榷之處。如“Gulliver”一名很容易就讓原文讀者聯想到“gullible”(「容易受騙」)。「格列佛」或「格利佛」雖稱得上是忠實的音譯,卻未能傳達原文幽微、諷刺之處。故本書採變通之計,將“Gulliver”譯為「格理弗」,除音譯之外,力求維持原文意涵,暗示主角勇於冒險、敏於學習、「格」物窮「理」,卻屢遭拂逆,到頭來落得自以為是、窒礙難行、違背常理、格格不入、落落寡歡(「弗」)。
早期中譯
《談瀛小錄》
此書第一個「中譯」《談瀛小錄》實為改寫,清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至十八日(1872年5月21至24日)連載於上海《申報》。此版並未署名,然而根據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考證,譯者可能是《申報》編輯蔣其章。
為了加強「真實」的印象,《談瀛小錄》以頭上安頭的方式加了一段前言,指稱有人發現數百年前遺稿,提供報社披露。此版依該報體例以文言撰寫,沒有任何標點,甚至把主角轉化為中國東南沿海人士(「某家籍隸甬東」)。然而,此篇連載僅四日即戛然而止。總之,《談瀛小錄》為此經典之作的中譯開啟先河,並為「譯寫」(transwrite)、翻譯就是「改寫」(translation as rewriting)以及譯文的「馴化」(domestication)、「歸化」(naturaliz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提供了具體例證。
《僬僥國》/《汗漫游》
第二個中譯以章回小說形式連載於《繡像小說》,由光緒二十九年(1903)七月至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配以中國風插圖,未著譯者。此版起初使用「僬僥國」一名(「僬僥」為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矮人),非但未掩飾其為翻譯,甚至刻意標舉異國風味。後來易名「汗漫游」,兼具「不著邊際的漫遊」及「漫漶難以稽考」之意,而其「水勢浩瀚洶湧」之意涵又與主角多次海上冒險吻合,比原譯名更為適切。此譯本各章標題採取中國章回小說的對仗回目,內文卻以白話翻譯,長期連載,並配上「既中又西」、「不中不西」的插圖,生動展現了圖文互涉的況味。
《汗漫游》將四部全譯,提供了更完整的面貌,但不乏歧出之處:如第三部僅譯出飛行島之遊,割捨其他奇國異域;第四部在主角離開慧駰國後,另增遭巨鯨吞入腹中一節。前者為省略之過(sin of omission),後者為增添之過(sin of commission),顯示《汗漫游》依然難逃改寫的命運。
《海外軒渠錄》
林紓與魏易(一說曾宗鞏)合譯的《海外軒渠錄》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第一個以專書形式出版的該書中譯,而且托桐城名家林紓盛名,成為流傳最廣的譯本達數十年之久,在此書中譯史上佔有獨特地位。
《海外軒渠錄》意指「以海外奇聞異事博君一粲」,並藉以諷刺時事及人性,與《鏡花緣》有異曲同工之妙。林紓不曉外文,只得與人合譯,畢生竟完成一百八十部左右的文學翻譯,誠為世界翻譯史上的異數。林紓在諸多譯序中表達感時憂國的強烈情懷,可見他從事翻譯除了為稻粱謀之外,實有更深的懷抱。林譯古雅生動,甚受歡迎,影響遠較前二版本深廣。然而由於腰斬全書,以致國人誤殘為全,以訛傳訛,形成中文世界裡「大小人國遊記」的傳統。
《小人島》/《小人島誌》
台灣最早的漢文譯本很可能是刊於《臺灣教育會雜誌》的《小人島》(第二期起改稱《小人島誌》),自明治四十二年(1909)10月25日至次年1月25日,連載四期,譯者為蔡啟華,序言以駢文撰寫,對仗工整,譯文也出之以文言,標點主要為圓圈,如傳統之句讀,偶爾出現引號,並以日文譯出兩處地名,在此書中譯史上難得一見。由使用文體與刊登場合推測,讀者多為教育界人士及社會菁英。
蔡「試於公退無聊之候。偶檢逸史。為述一絕奇絕巧之事。」英文原著第一部共八章,蔡自稱「抄譯」,意即摘譯,序言與譯文分刊四期,篇幅短小,內容簡略,著重原書奇巧之處,志在娛悅讀者,而非諷喻,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擾。然而在大力鼓吹日化的時代,蔡譯以典雅漢文發表,此舉本身便可能隱含愉悅/逾越之動機與效應,值得深思。
《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
台灣另一早期譯本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小人國記》刊於昭和五年(1930)3月3日至5月18日,《大人國記》刊於7月6日至12月6日──也是節譯/腰斬,譯者不詳。然而兩篇〈緒言〉的文言典雅,旁徵博引,用於翻譯的白話相當流利,足證譯者對古今文體之駕馭能力,譯文中也呈現對人性與政治的諷喻。
此版特色在於透過譯文暗示當時台灣殖民情境以及譯者的反殖民態度。譯者有意經由新聞媒體,讓讀者得以接觸西方文學與社會,達到啟蒙作用,更透過翻譯(運用漢語,而不是殖民政府大力提倡的日語),暗示對當權者及其政策之不滿,既達到諷喻的目的,也避免牢獄之災。
綜而觀之,此書雖可概稱為奇幻文學,但中譯傳統大致有二,一為諷刺文學,一為兒童文學,後者對該書的普及作用甚大,大都以改寫的腰斬形式出現,直到晚近才漸有納入全本的趨勢。此外尚有一旁支:由於故事具想像力,內容生動有趣,半個多世紀來便有英漢對照本或註解本,晚近更搭配有聲書CD、MP3、電子書等,作為學習英文之用。
文學理念與效應
筆者參觀都柏林作家博物館(Dublin Writers Museum)及翻閱愛爾蘭文學史相關論述時,發現許多以綏夫特為愛爾蘭文學的鼻祖,然而詢問當地民眾,卻發現不少人似乎對他有著矛盾的情感,或許與其認同與諷刺有關。
然而,諷刺文學為何大受歡迎?綏夫特在為諷刺下定義時,順帶諷刺人性:「諷刺這面鏡子,觀者在鏡中通常只見他人的面孔,而不見自己。它之所以那麼受世人歡迎,很少人反感,主要原因在此。」綏夫特對自己諷刺的手法與心態則有如下說法:
但他的目的從不在於惡意;
嚴厲斥責罪惡卻饒過姓名;
沒有一個人能夠憎惡他,
因為成千的人都是對象;
他的諷刺所指向的缺點,
無非所有凡人都可改正……
綏夫特對於寫作目的也有獨特體認,宣稱自己「殫精竭慮的主要目的是攪擾世界,而不是娛樂世界。」弔詭的是,他不但以寫作去攪擾世界,更因為諷刺手法獨特,反而化攪擾為娛樂。他對《格理弗遊記》的說法是:「這些遊記精采,大益於世道人心。」由此可見,他所謂的攪擾或娛樂都只是手段,目的是回歸到當時盛行的文學觀:「寓教於樂」、「文以載道」。只是此處「寓」、「載」的方式不是單純的「說教」或乏味的「傳道」,而是透過「攪擾」與「娛樂」的高超手法,讓人印象深刻,即使哭笑不得,卻仍舊「受教」、「明道」。因此,《一九八四》的作者歐威爾(George Orwell)對此書推崇備至:「如果要毀掉世上所有的書,只保存六本的話,我一定會把《格理弗遊記》列入其中。」
江森(Samuel Johnson)曾盛讚莎士比亞的戲劇宛如「人生的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性。綏夫特以超凡的想像創造出小人、大人、慧駰、犽猢(“Yahoo”)……來對照人類,提供的是一面哈哈鏡,透過文字的折射,人性某些方面被放大,某些方面被縮小,看似扭曲,卻是顯微,然而其攪擾與娛樂正在於此,其寓教於樂也在於此,有請讀者親自領會。
第一部 小人國遊記
第一章
作者略述生平家世;早年即性好旅行;遭遇海難,泅泳逃生;安抵小人國海岸;淪為階下囚,解送京城。
我父親在諾丁漢郡有份小家產,生了五個兒子,我排行第三。十四歲時,父親送我上劍橋的艾曼紐學院,在那裡待了三年,一心向學。雖然我有些許的津貼,但因財力短絀,而維持生計的費用過於龐大,就隨著倫敦的良醫詹敏思‧貝慈先生為徒,前後四年。父親偶爾送筆小錢來,我都花在學習航海和其他數學方面的知識,這些技能對有意於旅行的人是有用的,因為我一直相信,總有一天命運會帶我踏上旅行之途。離開貝慈先生之後,我投靠父親;在父親、約翰伯伯和其他一些親戚的幫助下,我拿到了四十鎊,他們也答應每年提供三十鎊,維持我在萊登的費用。我在萊登學醫兩年七個月,知道那在長途航行中派得上用場。
從萊登回來之後不久,承蒙恩師貝慈先生把我推薦給燕子號的亞伯拉罕‧潘諾爾船長當隨船醫生,跟了他三年半,去了一兩趟地中海東岸和其他地方。回來之後,我決心定居倫敦,恩師貝慈先生也這麼鼓勵我,而且把我推薦給幾個病人。我在舊猶太街分租一間小屋,聽了別人的勸,為了改善處境,娶了住在新門街的襪商艾德蒙‧伯頓先生的次女瑪麗‧伯頓女士,得了四百鎊的嫁妝。
但是,兩年後貝慈恩師去世,我的朋友很少,又無法昧著良心模仿許多同行那種心黑手辣的作法,於是生意開始沒落。因此,我和妻子及一些友人商量之後,決心再度出海。六年間我連續在兩艘船上擔任醫生,幾次出航到東西印度群島,財產略有增加。閒暇時我就閱讀古今最好的作家,因為我總是隨身帶著許多書;上岸時就觀察風土人情,學習當地的語言,因為我長於記憶,所以很有語言才華。
由於最後一次出航收入不多,我逐漸厭倦了海上生活,有心在家陪伴妻子和家人。我從舊猶太街搬到費特巷,再搬到瓦平,希望能在水手之間接點生意,但沒什麼幫助。盼了三年,情況未見好轉,於是我接受羚羊號威廉‧普利查船長的優渥條件,當時他正準備出航南海。我們於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自布里斯托啟航,起初很順利。
為了某些原因,不宜用我們在海上冒險的細節來煩擾讀者。總之,在前往東印度群島途中,我們被暴風雨吹趕到范‧狄門之地的西北,觀測後發現位於南緯三十度二分。船員中有十二人因為勞累過度和食物惡劣而一命嗚呼,其他人的身體狀況則很虛弱。十一月五日,當地正是初夏,大霧瀰漫,水手們瞧見一塊礁石,距離船身不到三百呎,但強風把我們直吹過去,登時船身斷裂。連我在內的六個船員把小艇放入海中,好不容易擺脫了大船和礁石。依我估算,我們大概划了三里格,就再也划不動了,因為在大船上就已經耗了許多氣力。於是我們只得任憑海浪擺佈,經過大約半個小時,北方突如其來一陣颶風打翻了我們的小艇。小艇上的同伴,還有逃到礁石上和留在大船上的夥伴,他們的下場如何,我不得而知,只能推斷他們全完了。至於我自己,則在命運的指引下游泳,由風浪推著向前。我時時垂下雙腿,卻總搆不到底,就在幾乎筋疲力竭、無法繼續掙扎之際,發現自己的腳踩到底了,這時暴風也減弱了許多。此處的坡度很小,所以我走了將近一哩才上岸,我猜測那時大約是晚上八點。又前進了大約半哩,但不見任何人煙──至少是因為身體很虛弱,所以沒看到。我疲倦極了,加上天熱,離開大船時又喝了大約半品脫的白蘭地,所以睡意甚濃。我躺了下來,在很短小又柔軟的草地上沉沉入睡。記憶中這輩子還沒睡得這麼沉過,我推斷睡了超過九個小時,因為醒來時一片天光。我試著要起身,卻動彈不得。由於恰好是仰臥,我發現自己的手腳被牢牢綁在地上,又長又密的頭髮一樣被綁在地上,也感覺身體從腋下到大腿被幾條細繩套住,所以只能朝上看。太陽開始熱了起來,光芒刺眼。我聽到周遭的嘈雜聲,但以我躺著的姿勢,只能看到天空。不多時,我感覺有個活生生的東西在左腿上移動,輕輕移過胸部,幾乎來到下巴。我把眼睛盡量往下看,映入眼簾的是一個人形,不到六吋高,手持弓箭,背上揹著箭袋。同時,我感覺到至少還有四十個同類(我這麼猜想)跟在他後面。我吃驚極了,發出巨吼,把他們嚇得全都往回跑,後來有人告訴我,有些人從我兩側跳落地面時摔傷了。然而,不久他們又回來了,其中一個放膽前進到可以看到我整張臉的地方,驚訝地舉起雙手仰望,以尖細而分明的聲音叫著「何奇那 得古」,其他人也重複相同的字眼好幾回,但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的意思。讀者可想而知,我躺著的這段時間很不舒服,努力想要掙脫,終於幸運地扯斷了綁住我左臂的繩索,拔起釘在地上的木樁──我是把左臂抬到面前時,才發現原來他們是這樣綁我的。同時我猛力一拉,頓時覺得痛入心扉,卻稍稍掙鬆了綁住我左側頭髮的繩索,所以頭堪堪能轉個兩吋左右。但我還來不及抓住這些人,他們就又跑開了。這時只聽得一聲高亢的尖叫,聲音甫落,又聽得其中一人大叫「托哥 風那克」,頓時覺得上百隻箭射上我的左手,有如百針齊扎。接著又是一陣箭射入空中,就像我們在歐洲發射砲彈一般。我猜想有許多箭落在我身上(雖然我感覺不到),有些落在臉上,我立刻用左手擋住。這陣箭雨過後,我發出傷痛的哀嚎,再次試著掙脫,卻引來一陣比前番更猛烈的狂射,他們之中有些還試著用矛來刺我的兩側,幸好我身上穿著緊身皮衣,他們才沒法刺透。我心想,最穩妥的方法就是躺著不動,心中盤算就這樣待到夜晚,既然我左手已經鬆綁,輕易就能脫身。至於這些居民,我自信抵擋得了他們的大軍──如果他們全都像我見到的那個人一般大小的話。但命運之神對我另有安排。這些人見我安靜不動,就不再射箭。但從愈來愈大的嘈雜聲,我知道他們人數愈來愈多。距我右耳大約四碼的地方傳來敲擊聲,持續了一個多鐘頭,好像有人在做工。我就木樁和繩索允許的範圍,把頭轉往那個方向,只見地上搭起一座一呎半高左右的台子,台上容得下四個人,旁邊架了兩三個梯子供人攀爬;台子上站著一個看似頗有地位的人,衝著我講了一長串話,但我一個字也聽不懂。應該一提的是,那個大人物在開始演說前,大喊了三次「蘭哥羅 德呼 三」(後來有人把這些字眼和先前那些一併重複,並且向我解釋)。語音才落下,就有大約五十個居民走上前來,斬斷綁住我頭部左側的繩索,讓我能轉向右側,看著這個正要說話的人和他的姿勢。這個人看似中等年紀,比隨侍的三個人都要高些;這三個人中,一人是侍從,持著他的衣擺,身高看來比我的中指稍長,其餘二人分立兩側,扶持著他。此人渾身上下十足像個演說者,我聽得出其中有許多威脅的話語,其他則是一些承諾、憐憫、慈悲的話。我回答了幾個字,卻以最屈從的模樣舉起左手,雙眼注視太陽,彷彿請他見證。在離開大船之前幾個小時,我就沒吃過一口東西,這時饑腸轆轆,忍不住表現出自己的不耐(也許有違嚴格的禮儀),頻頻把手指向嘴巴,表示我要食物。「豪哥」(後來我得知他們是這麼稱呼上卿)很明白我的意思,從台上走下來,命人在我兩側架上幾個梯子,有百來人扛著裝滿肉的大桶登上梯子,走向我嘴邊──原來國王一接到有關我的通報,就派人備妥這些肉送來。我留意到有幾種不同動物的肉,口味上卻分辨不出。這些肩肉、腿肉、腰肉加上了許多佐料,形狀像是羊肉,卻比雲雀的翅膀還小,我一口就吃了兩三塊。他們的長條麵包大小有如毛瑟槍的子彈,我一次就是三條。他們儘快餵我,對我巨大的身軀和胃口表露出上千種驚異的神情。我又作手勢要喝東西。他們從我的吃相發現戔戔小量無法滿足我。手法異常靈巧的他們,很巧妙地吊起最大的桶子,滾向我手邊,打開桶蓋,我一飲而盡,毫無困難,因為大桶的容量幾乎不到半品脫。喝到嘴裡,只覺得像是勃艮地的淡酒,卻美味得多。他們給我第二桶,我照樣喝下,並作手勢還要,但已經沒有了。我表現過這些令人驚異的動作後,他們歡呼,並在我胸膛上跳起舞來,像最先一樣重複喊了幾次「何奇那 得古」。他們向我作手勢,要我把兩個大桶拋下去,但先警告底下的人退到一旁,口中還大聲喊著「波拉奇 米弗位」,看到桶子拋到空中時,大聲齊呼「何奇那 得古」。我承認,他們在我身上來來去去時,我常想抓起最靠近的四五十個,把他們摜到地上。但想到先前受到的很可能還不是他們最惡毒的手段,而且我把自己順從的行為解釋為向他們的榮譽保證,所以立刻就把剛才那些想法拋到腦後。此外,這些人這麼慷慨大度款待我,使我覺得自己也該表現出為客之道。然而,那些小人竟敢冒險登上我的身體,而不被眼中如此龐然巨物嚇得發抖,還在上面走動,渾然不顧我有一隻手是自由的,想來著實讓我對他們的大膽驚訝不已。過了一段時間,他們看我不再要肉吃了,這時皇上派來的高官出現在我身前。這位高官登上我右腿的小腿彎,朝上走來,一直到我面前,背後跟著十幾個隨從。他取出蓋了御璽的信物,緊貼著我的雙眼出示,接著說了大約十分鐘的話,話中沒有任何憤怒的表示,只是透露出堅決的語氣。他頻頻指著前方,後來我才發現那是京城的方向,原來御前會議決定把我帶到大約半哩之外的京城。我回答了幾個字,但不得要領,我還把鬆了綁的手放在另一隻手上(但越過高官的頭,唯恐傷到他或隨從),然後放到頭上、身上,表示我想得到自由。他似乎很明白我的意思,因為他搖搖頭表示不答應,並以手勢表示必須把我當成俘虜解送。然而,他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手勢讓我了解,我會有足夠的肉食、飲料和很好的待遇。那時我再度想要掙脫,但再度感覺到他們的箭射上我的臉孔、雙手,十分刺痛,起了許多水泡,而且很多還插在上面,同時又留意到敵人為數更多了,於是以手勢示意任憑他們處置。「豪哥」和隨從見狀,再三致意,滿臉歡喜地退下。不久就聽到眾人齊聲高喊,並不時重複著「丕普隆 西蘭」等字,接著感覺到左側許多人鬆開了繩索,讓我能轉身向右,解決內急。他們從我的動作猜出我要做什麼,當下閃立左右,避開從我身上奔流而出、又猛烈又嘈雜的急流,尿量之多令他們大為吃驚。在這之前,他們在我臉上、手上塗了一種很好聞的膏藥,幾分鐘內便消除了所有箭傷的刺痛。頗為滋養的飲食讓我恢復了不少體力,再加上這些待遇,使我舒服入睡。後來他們告訴我,我睡了大約八個小時;這也難怪,因為醫生奉皇帝之令,在那兩大桶酒裡摻了安眠藥。
似乎在我登陸睡倒之後,有人一發現就派了專差向皇帝報信,在御前會議中決定趁我睡著的夜晚用上述方式把我綑綁起來,送給我很多的肉食、飲料,並準備工具把我載運到京城。
這個決議也許看來很大膽、危險,而且我相信任何歐洲君王在類似情況下都不會仿效這種決議,但依我之見,卻是極為審慎而慷慨的作法。因為,設想這些人如果要在我睡夢中用矛、箭殺死我,我一感覺到疼痛必然會醒來,這些疼痛激起我的憤怒與力量,我就會扯斷綁在身上的繩索,到時,他們就無法抵抗,也不能指望我會手下留情了。
這些人是最傑出的數學家,皇帝更以支持學術聞名,在他的贊助和鼓勵下,他們在數學上達到最完美的境界。這位君王曾命人把幾項器械固定在輪子上,好載運樹木和其他重物。他經常在巨木成長的森林中建造最巨大的軍艦,有些九呎長,然後用這些車輛把它們運到三四百碼外的大海。五百個木匠和工程師立即奉命準備他們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車輛。這是一座離地面三吋高的木架子,大約七呎長,四呎寬,底下有二十二個輪子。這部車子似乎在我登陸後四小時內就出發,現在聽到的叫喊聲是車子到了。他們把車子拖來,和躺著的我平行,但最大的困難是把我抬起,放到車上。因此,他們豎起了八十根柱子,每根柱子一呎高,並且把綑紮繩般大小、很堅固的繩索用鉤子固定到許多布條上,而布條早已由工匠纏繞在我的脖子、雙手、身體、雙腿上。他們召來九百名最強健的壯丁,把許多滑輪固定在柱子上,由壯丁們拉這些繩索,因此不到三個小時就把我抬起,吊入車內,緊緊綁住。這些都是我事後聽說的,由於在整個行動過程中,我因為酒裡的安眠藥睡得很沉。他們用上了皇帝一千五百匹最高大的駿馬,每匹大約四吋半高,把我拖往先前提過的半哩外的京城。
我們啟程大約四小時之後,發生了一件很荒謬的事,把我弄醒。車子因為有東西故障,需要修理,暫停了一陣子。這時有兩三個年輕的當地人好奇,想看看我睡覺的模樣,於是爬上車來,躡手躡腳地走向我的臉,其中一名御林軍軍官把短矛的矛尖深深探入我的左鼻孔,就像稻草般搔弄我的鼻子,使我猛打噴嚏,他們隨即悄悄溜走,直到三個星期後,我才知道自己當時突然醒來的原因。接下來的時間,我們走了很長一段路,夜晚休息時,我的兩側各有五百名守衛,一半舉著火把,一半持著弓箭,只要我稍稍一動就準備放箭。次晨日出時,我們繼續上路,大約中午時分來到距離城門不到兩百碼的地方。皇帝和滿朝文武都出來會見我們,但大臣們絕不讓皇上冒險登上我的身體。
停車的地方矗立著一座古廟,被奉為全國最大的廟宇。幾年前發生了一起傷天害理的謀殺案,玷污了這個地方,以致在善男信女心目中褻瀆了神明,因而改作一般用途,所有的裝飾、器物都已搬走。他們決定要我住在這座建築裡。朝北的大門大約四呎高,將近兩呎寬,所以我能輕易爬進爬出。大門兩邊各有一扇小窗,離地不到六吋。國王的鐵匠由左側窗口運來九十一條鐵鍊,形狀如同歐洲仕女錶上懸掛的鍊子,小大也相仿,並且用三十六個掛鎖鎖在我左腿上。二十呎外,有座塔樓隔著一條大道與這座廟相對,樓高至少五呎。皇帝在眾多朝廷大臣陪伴下登上塔樓,好有機會看看我──有人是這麼告訴我的,因為我並看不見他們。據估計,超過十萬名的居民也同樣為了看我而出城。儘管周遭有守衛,但我相信隨時有不下一萬人借助梯子爬上我的身體。但官府不久就發出禁令,違者處死。工匠們確定我不可能掙脫之後,便把綁著我的所有繩索斬斷。我站起身時,覺得自己這輩子的處境從沒有比這更悲慘的了。看到我起身,走動,人群發出的喧嘩和驚奇之聲,實在難以用言語形容。鎖住我左腿的鍊子大約兩碼長,不僅讓我能在半圓的範圍內自由前後走動,而且因為固定在距離大門四吋之內,所以我可以爬進大廟,伸直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