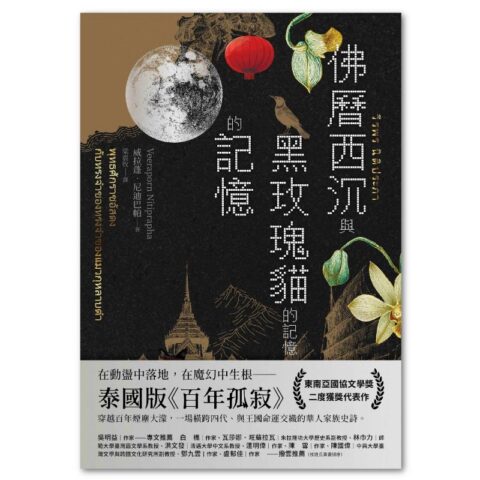過度纖細的身體
原書名:Corpus Delicti: Ein Prozess
出版日期:2015-01-08
作者:尤麗‧策
譯者:唐薇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48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5105
系列:小說精選
已售完
沒有反叛者的世界,永遠不會是真正的天堂!
當體制審查一切,請問國家約束人權的極限在哪?
21世紀版《1984》,媲美《美麗新世界》的動人之作
德國著名暢銷作家尤麗‧策,繼《物理屬於相愛的人》後,驚豔讀者的最新小說
◎諾貝爾文學大師鈞特.葛拉斯心目中唯一的接班人
◎歐洲最令人振奮的小說界巨星,讀者、媒體高度評價之作!
◎全球英、美、法、義、荷、韓等15國出版!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追求的天堂。但每個天堂都有反叛者。……每個時代都有反烏托邦的故事,而主題莫不是: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鴻鴻(詩人、導演)專文推薦
王聰威、夏曼‧藍波安、陳思宏、蔡素芬 共同強力推薦!(姓氏排列按筆畫順序)
當「感冒」等於中古時代的黑死病……
在健康第一的烏托邦世界裡,不准虛弱、不准生病,「打噴嚏」能造成恐慌,抽菸就是犯罪……。
在過度強調健康的大法世界裡,當社會政策推向理想的極端,將是什麼景象?你能想像不健康就等著坐牢的一天嗎?
年輕美麗、獨立自主的女主角,也是社會菁英的米亞‧霍爾被檢察官告上法庭。是過度的愛(愛護弟弟)、過度的理智(思考邏輯太科學)、過度獨立的思想,讓她痛苦沉淪。在以健康為依歸的社會體制底下,恐怖和危險自有其定義。米亞‧霍爾想替自己被判強暴致死罪的弟弟洗刷冤情,不料陷入體制的黑洞,因為她對弟弟的愛而危及性命。在這個被號稱「理想國」的國度裡,如果沒有好好維護自己的健康,不會被送進醫院,而是被送進法庭。小說所描寫的,正是一個震撼人心的新興恐怖世界。
德國著名暢銷作家尤麗‧策的這部新作,是描寫發生在未來世界的科幻小說,以一幕一幕的生動情節逼視著人性。在這個世界裡,體制審查一切,高唱健康極權。健康乃國家最高指導原則。「大法」要求每位公民提供睡眠數據、營養報告和每一天的運動步數。這樣的「健康新世界」談論的議題是:國家約束人權的極限在哪?
如此一部值得讀者省思的小說,尤麗‧策用精巧獨特的語言鋪陳了一個超乎想像的未來世界,更在情節推演中,隱喻我們生存在此時此刻的當下。
本書曾拍成舞台劇上演,轟動德國文壇!故事由一場審判開始,小說女主人翁米亞‧霍爾被指控違反大法,因為未遞交睡眠報告與營養報告,沒有進行對自身健康的通報義務而被法庭審理,而克拉馬是位知名記者,也是大法擁護者,扮演與米亞相反的角色。在這個刻板體制下,米亞的弟弟莫利斯是不受拘束的生活者,有著不同的理念,卻因為一場冤案而枉死,米亞為弟弟的枉死而難過不已,同時米亞又得思索著生活面對的難題。到底莫利斯是怎麼死的,米亞與克拉馬之間又會有怎樣的攻防,在這個標榜「健康」的未來世界到底怎樣運作,都在小說中一步步揭露!
※ 國際媒體推薦
「《過度纖細的身體》讓尤麗‧策成為當代女性歐威爾。」──德國廣播公司Deutschlandradio
「反烏托邦裡的法庭戲,寫成一部政治驚悚小說──既恐怖震撼又掐人心弦。」──《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
「是監控還是保安?是健康還是極權?作者帶領讀者打一場益智的思想乒乓。」──德國《時報》Die Zeit
「冷凍庫裡的巫婆──尤麗‧策的科幻小說《過度纖細的身體》,描述女生物學家挺身而出,對健康至上的瘋狂理念的一場宣戰。
尤麗‧策警示著我們,未來就發生此地此時……《過度纖細的身體》相較於歐威爾的《1984》,更接近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藉著這本作品,作者從過去敘說著未來,也從未來敘說著過去,教導著人們恐懼。」──《鏡報》Der Spiegel
作者:尤麗‧策
1974年生於德國波昂,擁有法學、文學雙學位及國家律師、法官資格,曾服務於紐約、薩拉耶佛等地的聯合國機構。積極關懷公眾議題及深入國際法研究之外,更活躍於文學創作領域。她曾表示,法學論述及研究是興趣,文學才是她的職志。2001年第一部小說《老鷹與天使》(Adler und Engel)出版即獲巨大成功,翻譯授權近35種語言。暢銷冠軍書《遊戲本能》(Spieltrieb)亦引起讀者、評論家廣大迴響。小說《物理屬於相愛的人》(Schilf)改編自劇作,曾於德國「激進青春」戲劇節演出,榮獲「觀眾票選獎」。《過度纖細的身體》曾為舞台劇上演,後改編成小說,描述的未來世界引起廣泛話題與關注。
作品備受肯定,獲頒德國圖書獎、不來梅文學獎、Rauris文學獎、Ernst Toller文學獎、瑞典Per Olov Enquist小說獎、法國Prix Cevennes歐洲最佳小說獎,Carl-Amery文學獎(2009),Gerty-Spies獎(2009),Solothurner文學獎(2009),湯瑪斯曼文學獎(2013),Hoffmann-von-Fallersleben批判文學獎(2014)。
譯者:唐薇
1972年生於台北,輔仁大學德國語文學碩士,往返於柏林、台北和上海三城之間。曾因譯作受邀至柏林文學學會駐村創作、出席德國慕爾海姆戲劇節翻譯研討會、瑞士洛克巴德文學節、德國博世基金會文學翻譯研討會等。譯有(尤麗.策)《物理屬於相愛的人》、《雪國奇遇》、(夏洛特.羅奇)《潮溼地帶》、(朵特.席珀)《讓日子多一點生命》等。現任「譯動國界論壇https://zh-tw.facebook.com/TAFF.TW」總召集及策展人,推動文學和翻譯交流。
推薦序/歡迎光臨無菸天堂/鴻鴻(詩人、導演)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追求的天堂。但每個天堂都有反叛者。原因不是因為天堂不夠完美,而是因為太完美,完美到不容許有人拒絕這種完美。反叛者追求的不是地獄,而是自由。所以,每個時代都有反烏托邦的故事,而主題莫不是: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
德國中生代作家尤麗‧策(Juli Zeh)曾以平行世界的推理小說《物理屬於相愛的人》讓台灣讀者驚艷,她的新作《過度纖細的身體》則猶如歐威爾《一九八四》的當代版。隨著時代不同,現在我們對極權主義已有所警覺(不管是法西斯極權還是共產極權),但是一種全新的極權卻悄悄誕生。那就是「健康」的極權。
當時代已經警覺到,殺雞取卵式的剝削環境來換取經濟利益,會造成多大的災害,環保、綠能、有機、再生、永續發展……便逐漸成為共識。同樣的,我們也在追求一個無毒的環境,反核、反基因改造、反農藥、反化學食品、素食救地球,都是為了確保我們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健康。但是這種潔癖般的追求也有其盲點,那就是,為了整體人類的幸福,我們是不是犧牲了個人的自由?
在台灣,「反菸」和「反反菸」的對抗,就是明證。癮君子逐漸發現自己成了社會的過街老鼠,不但所有室內的公共場合不能抽菸,甚至走廊、公園也不行,最後連許多露天的人行道也不行了。問題是,為什麼每家便利商店都可以買到菸,卻沒有地方可抽?抽菸會危害他人健康,那麼,人有權利危害自己的健康嗎?還可舉出一個更簡單的例子:騎機車為什麼一定要戴安全帽?如果個人的生命安全,個人可以負責,那麼為什麼要動用國家權力,來制訂不可違反的鐵則呢?
我們最常聽見的理由是,這樣會損及公共醫療資源。「公共」的概念無限擴張,個人的自由選擇只有靠邊站。
尤麗‧策的《過度纖細的身體》從這裡出發,推演出一個以「健康」為宗旨的美麗新世界:「透過追求全方位的個人健康,將能提升整體社會使其臻至完美。」而反過來定義個人:「不致力追求健康之人,不僅將要罹病,而是已經患病。」於是,所有人都失去隱私權,必須在體內植入晶片,定量運動,菸酒咖啡都得進行管制。如果沒有好好維護自己的健康,不是被送進醫院,而是被送進法庭。
故事的主角米亞,她弟弟捲入一樁強暴殺人案,遭到錯判後自殺。米亞從此陷入身心雙重的自暴自棄當中,而成為被法庭列管的對象。米亞會跟弟弟留下的想像人物「理想戀人」對話,荒廢運動,還因吸菸被鄰居的三個「正義魔人」叫來消防隊。律師為了幫米亞辯護,意外昭雪了弟弟的冤情,想不到讓米亞陷入更大的危機。因為冤案證實了「大法」的漏洞,檢察官不惜給米亞羅織罪名,把她打成恐怖組織首腦,必須處以極刑。
尤麗‧策不甘只是說一個峰迴路轉的故事,她在小說中不斷透過米亞和不同人物(包括死去的弟弟、理想戀人、法官、律師和檢察官)的辯證,指出「正常」的概念是多麼變態。例如檢察官用尖刻的方式嘲諷人類的歷史和宗教,聲稱「人類愛上疾病」,只會用各種疾病爭取別人的關注:「幾百年來人們推崇虛弱,甚至還將它升格為世界宗教核心。人們跪在瘦削的大鬍子受虐狂面前,他頭戴鐵刺冠,臉上血流如注。這就是病人之傲,病人之神聖,病人之自戀。」米亞則從更廣闊的視角來審視所有的體制:「起初我們管它叫基督教,後來改名為民主,今天我們則稱它為大法。」但事實上,「一切都是宗教。」
米亞傳道,米亞受審,米亞受難,米亞復活,這整個過程簡直像極了耶穌的翻版。這提醒了我們,所有的救世主,事實上都是世俗的反叛者。當然,如果我們已經身處天堂,為何還需要拯救?但是尤麗‧策不只鼓動我們對抗主流意識型態,更長驅直入個人情感難以言宣的部分。米亞和她的律師,以及陷害她的檢察官,居然都發展出曖昧的情感關係;甚至和想像中的理想戀人,也有許多親密的互動。《過度纖細的身體》不但用米亞的理念反抗當權,更用她複雜的感情世界,作為個人無法被體制或理念規範的強大例證。個人和權力、個人和想像之間的依存、戀慕,成為這個抗爭故事底層最耐人尋味的部分。
如果沒有塵世天堂的企望,我們可能沒有前進的動力。但是,沒有反叛者的世界,永遠不會是真正的天堂。
理想戀人
「正因為人生那麼沒有意義,」米亞說,「而人偏偏得囫圇承受,所以我偶爾才會有想焊接銅管的念頭,也許用它來形塑一隻鶴;又或者只是簡單地纏繞它,築一個蟲窩,接著我再把成品固定在底座上,然後給它取個名字叫做『浮動載體』,或者管它叫『理想戀人』。」
米亞面朝書桌背對房間,三不五時在紙片上做著筆記。落坐沙發的理想戀人,披著一件以午後陽光和一襲長髮做成的外衣。這位美人不動聲色,誰也不曉得她是否理解米亞所說的話。我們甚至不確定她是否在觀察米亞。說不定她更屬於另一向度的空間,在那兒的她望向虛無,而米亞,只有在不經意的時候、在世界與世界交錯的所在,落入她的眼底。彷彿未長眼皮的水生動物一般,理想戀人的眼神冰冷而凝重。
「只是想留下點什麼,」米亞說,「做一些沒有用途的東西。任何有用之物某天一旦被使用了,也就消耗殆盡了。就連上帝不也有個用途,是用來安慰世人嗎?你看:儘管祂再怎麼不朽,也不過僅此而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屋子裡一片狼藉,看上去好像幾個禮拜沒有整理、沒有打掃,也不曾通風過。
「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這些都是莫利斯說過的話呀。他說:追求不朽的人,不該汲汲求生。」
由於理想戀人遲遲沒有反應,坐在旋轉椅上的米亞開始轉圈圈。
「以前只要他想惹惱我,就會說:你啊其實應該去當藝術家才對。他認為科學思維徹底教壞了我。他問我:當自己和自己觀察的對象都來自萬物本源、也就是原子漩渦時,該如何去觀察事物或觀察自己所喜愛的人呢?腦子是掌管視覺和理解的唯一工具,當它和我們所看見、所理解的一切的組成元素相同時,叫人怎麼接受這個事實?『搞什麼嘛,』莫利斯一定會這樣大叫,『難道是物質與物質在對望嗎?』」
理想戀人與物質之間其實沒什麼共同點。或許米亞跟她談這些,只是為了讓自己心裡好過些。
「科學知識先是摧毀了以神為主的世界觀,接著又把人變成世界的主人。它讓人杵在那兒卻不給答案,這麼做豈不是萬分可笑?!這是莫利斯常掛在嘴邊的,這一點我倒是很能認同。看來我們兩人的想法並非南轅北轍,只不過結論不盡相同。」
米亞的筆頭指向理想戀人,彷彿自己有理由控告她。
「他總想為愛而活,可是如果你仔細聽他說話的內容,就會發現『愛』這個字對他而言,其實泛指他喜愛的一切事物。『愛』是大自然,是自由,是女人,是釣魚,是胡作非為,是與眾不同,是進一步大規模地胡作非為。總之,一切對他而言都叫做『愛』。」
米亞再度轉身面向書桌,一面說話一面寫下筆記。
「這個我要寫下來。我要把『他』寫下來。人腦的記憶庫每隔幾天就會刪除百分之九十六的訊息。百分之四的莫利斯不夠,百分之四的莫利斯不足以支撐我接下來的人生。」
她先是頑強地寫了一陣子,然後抬起頭來。
「只要我們一談到愛,他就感到委屈。你啊,他說,是個科學家,你觀察自己的朋友和敵人時只透過電子顯微鏡。當你開口說『Liebe,愛』這個字時,要用心去感受它,就好像嘴裡含著東西。這樣你說這個字的聲音聽起來才會不一樣。『愛』,高四度音。憋緊喉嚨呀,米亞,這個音很尖銳的,你小時候跑到鏡子前面練習過的。『愛』。當時你望著鏡子裡的自己,想找到自己說不出這個字的原因──『愛』。其實啊,米亞,你就是無法正確表達這個字的涵意。對你而言,它屬於一種陌生的語言,只適合在非常態的口腔構造裡發生。你說說看,米亞,說我『愛』你!說『人生在世,首要是愛』。『我親愛的』,『我最親愛的』,『你愛我嗎?』──你又逃開了,米亞!你在打退堂鼓!」
坐在旋轉椅上的她再度轉了一圈,這一回轉速極快。
「那他所說的最後一句話又是什麼?──『人生,是個大可回絕的提議。』那麼,他的所愛又在何方?有些話就像是鋼印一樣烙在腦海深處,唯有循著這個軌跡才能繼續思考。我該怎麼忘掉這一切?該怎麼做,才能不把這一切忘掉?你是認識他的,或許你比我跟他更熟。我真不知道,他曉不曉得我有多愛他?我甚至不知道,」米亞大喊,「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以最恰當的方式來想念他!」
「別再胡說下去了。」理想戀人終於開口。「我看,我們就照著老辦法來做。朝思暮也想,就這麼想念著他,來,我們一起。你過來嘛!」
當米亞起身,張開雙臂朝著理想戀人邁去時,門鈴響起。
優雅姿態
總有幾個片刻能讓時間停下腳步。當兩人四目交接──就等於物質凝視著眼前的自己──在視線穿過腦袋無限延展的此刻,整個世界會有好幾秒鐘的時間,圍繞這條視線軸旋轉。為了避免誤會,在此要澄清的是──我們談論的重點並非一見鍾情。米亞跟克拉馬之間發生的一切,姑且可以稱之為「故事初啟時的暗潮洶湧」。
米亞替他打開門,好一陣子誰也沒說半句話。克拉馬心裡在思忖什麼無法測知,大概他是在等米亞意識到自己是這屋子的主人。他是個有耐性的男人。或許他如此體貼入微,禮貌地在門前等候,把時間交給對方,是因為他明白她眼下的處境有多麼詭異。畢竟這不是每天都遇得到的場景,一個被你在心裡用盡千方百計千刀萬剮的男人,居然活生生地出現在你的面前。
「奇怪,」米亞總算恢復了語言能力,「我又沒開電視,怎麼還是可以看到您?」
克拉馬以迷人開朗的笑容回應她的話,對於只在媒體上見過他的人來說,一定會感到難以置信。這是一個私底下的微笑,一個盛名之下,卻仍然能忠於自我的微笑。
「健康萬歲。」他一邊說話,一邊將右手的手套褪下,將自己赤裸的手掌交給米亞。米亞打量他的手,彷彿在觀察稀有昆蟲,之後才猶豫地將手指放上他的掌心。
「這麼優雅的姿態,像老電影裡的畫面一樣,」她說,「但好像跟您不太搭。您不害怕我的傳染潛力?」
「人生在世,風格第一,米亞•霍爾。歇斯底里可是完美風格的頭號殺手。」
「您的臉孔,」米亞一面說話一面思忖,「就像一種標籤,可以拿來貼在各式各樣的觀點上。」
「容許我進門嗎?」
「您是在要求我,要我開口邀請謀殺我弟的凶手進門喝東西?」
「完全不是。以這種拙劣的判斷而言,您顯得太有智慧了。不過我倒真的挺想喝點東西的。比如來杯熱開水。」
克拉馬當著米亞的面走進屋內,朝沙發走去,坐在沙發上的理想戀人立刻咻地滑到沙發另一側。克拉馬還沒坐下,整座沙發卻霎時變得是為他一個人專門設置的模樣。理想戀人怨恨的眼神他看不見,絕對不是源於他的自信,而是基於一個事實──他看不見理想戀人。
「若要追根究柢,其實不是我謀殺您弟弟的。或許我們該問的是,他人在牢裡,從哪裡能弄來一條釣魚線上吊自殺?」
米亞站在屋子的中央,以雙臂抱住自己,指甲掐進上臂的肉裡,像是要緊緊抓牢自己的身體──或許她是想阻止自己撲向克拉馬、把他掐死。
「您……」米亞激動無比,「您這不是在努力加深我的仇恨嗎?」
克拉馬也擅長阿諛奉承式的微笑,還順手拂了拂頭髮。
「您儘管恨吧。」他回答。「我來這裡,只是想跟您談談。您不必嫁給我。」
「希望我們的免疫系統不合。」
「有趣的是……」克拉馬伸出手指輕點鼻尖,「我們的免疫系統應該滿吻合的。」
「有趣的是……」理想戀人說話時也伸出手指輕點鼻尖,「您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混帳。」
「我們用邏輯來釐清一下,」米亞的聲音恢復冷靜,「要不是您和您那幫狐群狗黨聯手發動輿論攻擊莫利斯,他也就不會被判刑,沒被判刑他怎麼會自殺。」
「這下我是更欣賞您了。」克拉馬右手手臂攤開放到沙發椅背,彷彿想將理想戀人擁入懷抱。「邏輯思考,您會我也會。所以您一定能輕而易舉地認知自己思維上的謬誤。因果本身絕不等於罪過,否則您該去譴責宇宙大爆炸,要它為您弟弟的死負責。」
「或許我會這麼做。」地球忽然在此時脫離了軌道墜向深淵,米亞搖搖欲墜,想撐住書桌卻整個撲了空。「我譴責宇宙大爆炸,我譴責宇宙,我譴責父母,誰讓他們把莫利斯和我帶到這個世界。我譴責一切,譴責每一個促成他死亡的人。」
「來吧,讓我扶您一把。」
克拉馬站起來,把跪倒在地的米亞扶起,一起走向沙發,他體貼地將她額前的亂髮撥到一旁。
「不准碰她!」理想戀人怒叱。
「我去煮點熱水。」克拉馬的身影消失在廚房裡。
基因指紋
我們在此談論的案件其實發生沒多久。只消看一眼細節就知道這是個簡單到出奇的案件。莫利斯,二十七歲,是一名溫柔又固執的男子,他父母喚他作「追夢人」,朋友稱他為「思想自由派」,姐姐米亞則大多時候叫他「狂人」。在某個尋常的週六夜晚,他因為一樁可怕的發現到警局報案。一名叫做西貝兒的年輕女子,本來跟他約好在南方橋下盲目約會,可是當他抵達橋下時,卻已無法判斷女子可愛還是不可愛了,原因是她已經沒有脈搏。警方替驚慌失措的莫利斯做完筆錄後便送他回家。兩天後莫利斯被羈押。警方在被強暴的女子體內,採集到他的精液。
DNA鑑定報告終結了調查程序。每個正常人都知道,基因是獨一無二的。即使是雙胞胎,也不見得擁有同樣的遺傳因子。莫利斯只有一個胞,身為科學家的她必然最清楚基因序列獨一無二的特性。以這種證據定罪乃法界慣例。遇到這種情況凶手會認罪,或遲或早,但他們終究都會認罪。或許認罪能減輕良心的譴責,又或許是能藉此取得社會大眾的饒恕。但莫利斯卻偏偏不顧事實。他堅稱自己並未強暴西貝兒,更遑論殺害她。當觀眾聚集在螢光幕前觀看下午電視節目時,期待的是一場緊湊明快的審判,然而莫利斯卻瞪大了碧眼宣稱自己無罪,無血色的臉因堅持立場而倍顯蒼白。只要逮住一個機會,他就不斷複誦那句猶如繞梁金曲的名言:「你們是在把我推上祭壇,成為瘋狂信仰的犧牲品。」
近代司法史上從來沒有一名凶手有過這種表現。一個運作良好的國家的公民,早已習慣視公共和個人利益為一體兩面,特別是在人性最陰暗的角落。莫利斯在法庭上的表現成為媒體醜聞。輿論聲浪掀高,一是同情他的處境,二是提出延後審判的要求,而其他人則是開始加倍地唾棄他──不只因為他的暴行,更甚者,是他的負嵎頑抗。
在蜚語流言滿天飛的情況下,米亞與莫利斯的血緣忽然成為不能說的祕密,而她,自然也成為司法當局的保護對象。白天她照常上班、完成健身義務,晚上則偷偷跑到監獄探監。無法入睡的她在夜裡抱著一只碗嘔吐,還得悄悄地溜出門把嘔吐物倒在馬路邊的水溝槽裡,以免廁所裡的感應器在廢水裡偵測到過高的胃酸值。克拉馬的新聞採集系統不僅能夠造就重要的媒體討論,也能剷除媒體討論最重要的部分。他筆下所寫,口中所談,不外乎以冷靜的實證主義者和「大法」最忠誠的擁護者為立場──此時此刻正在廚房裡忙碌的他,對米亞重申的也是相同的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