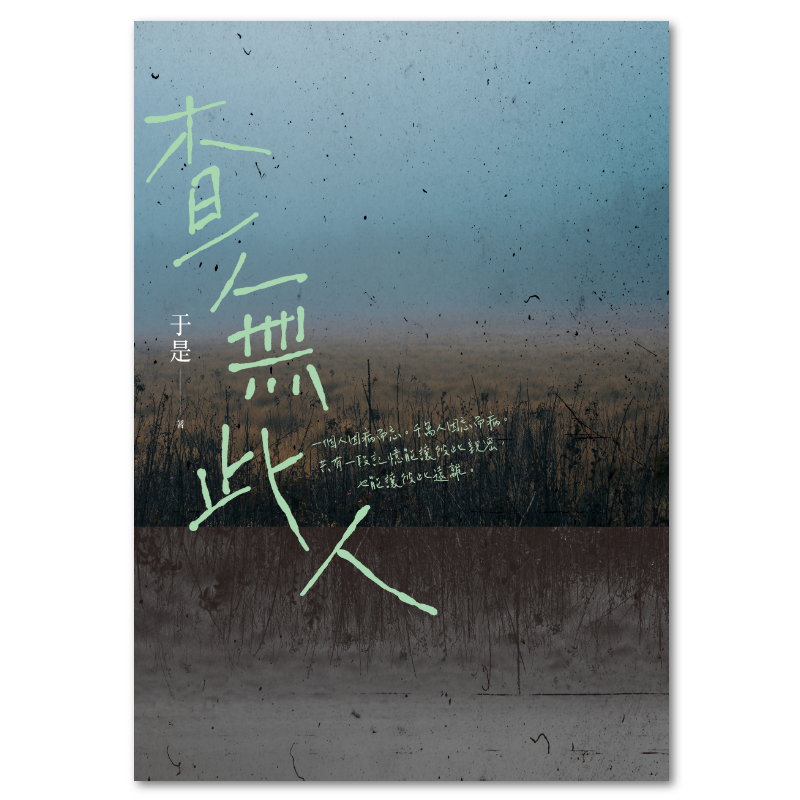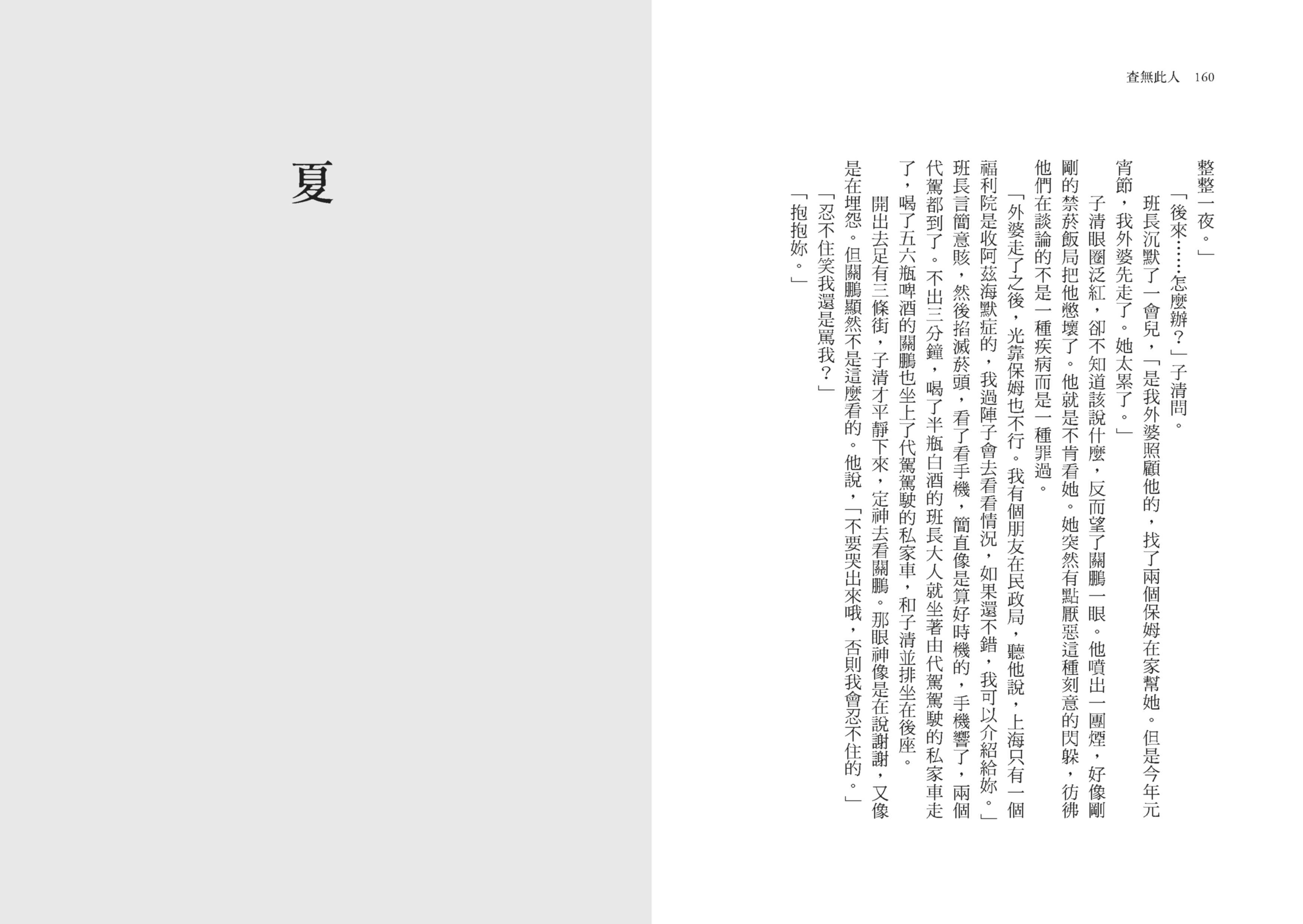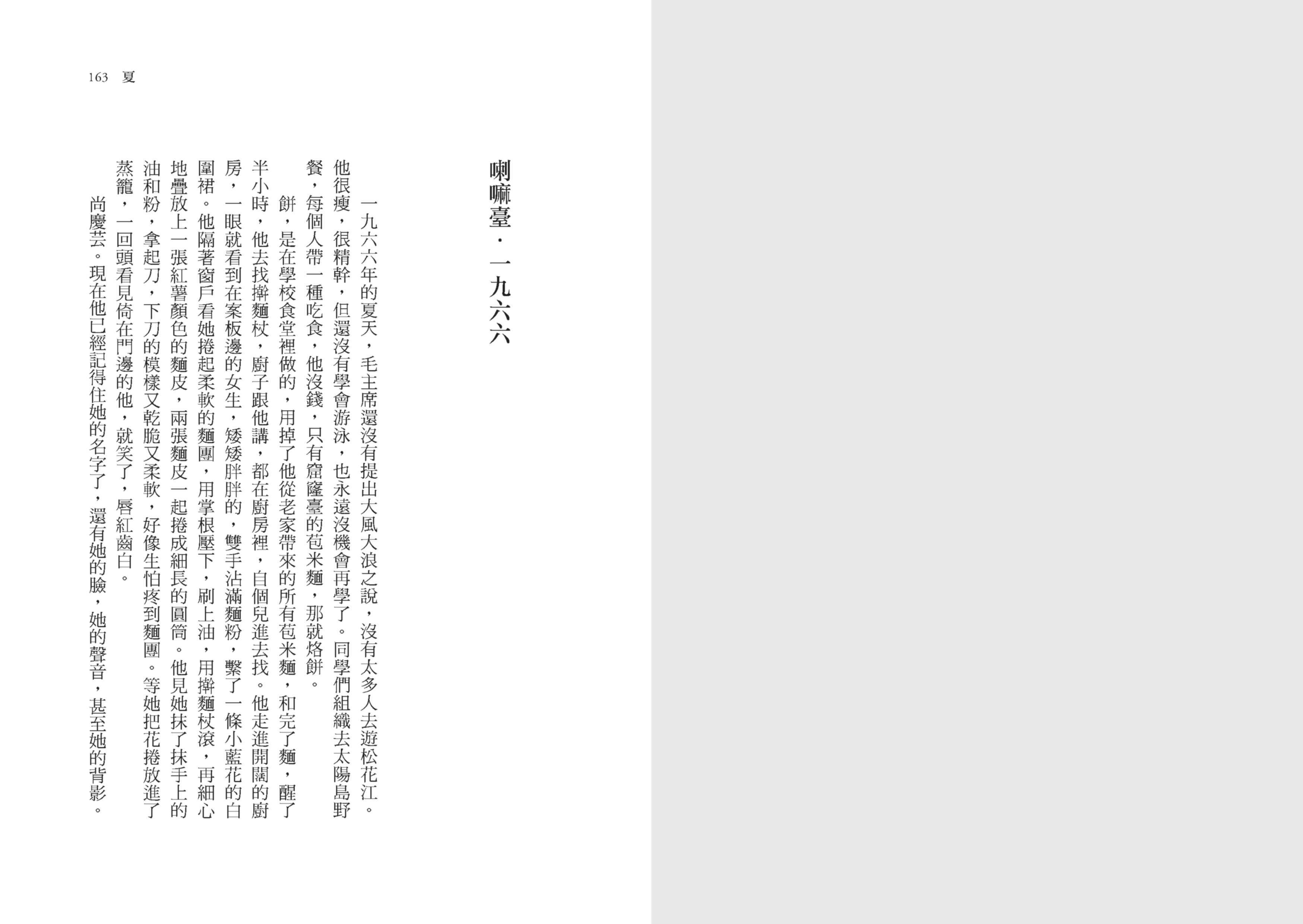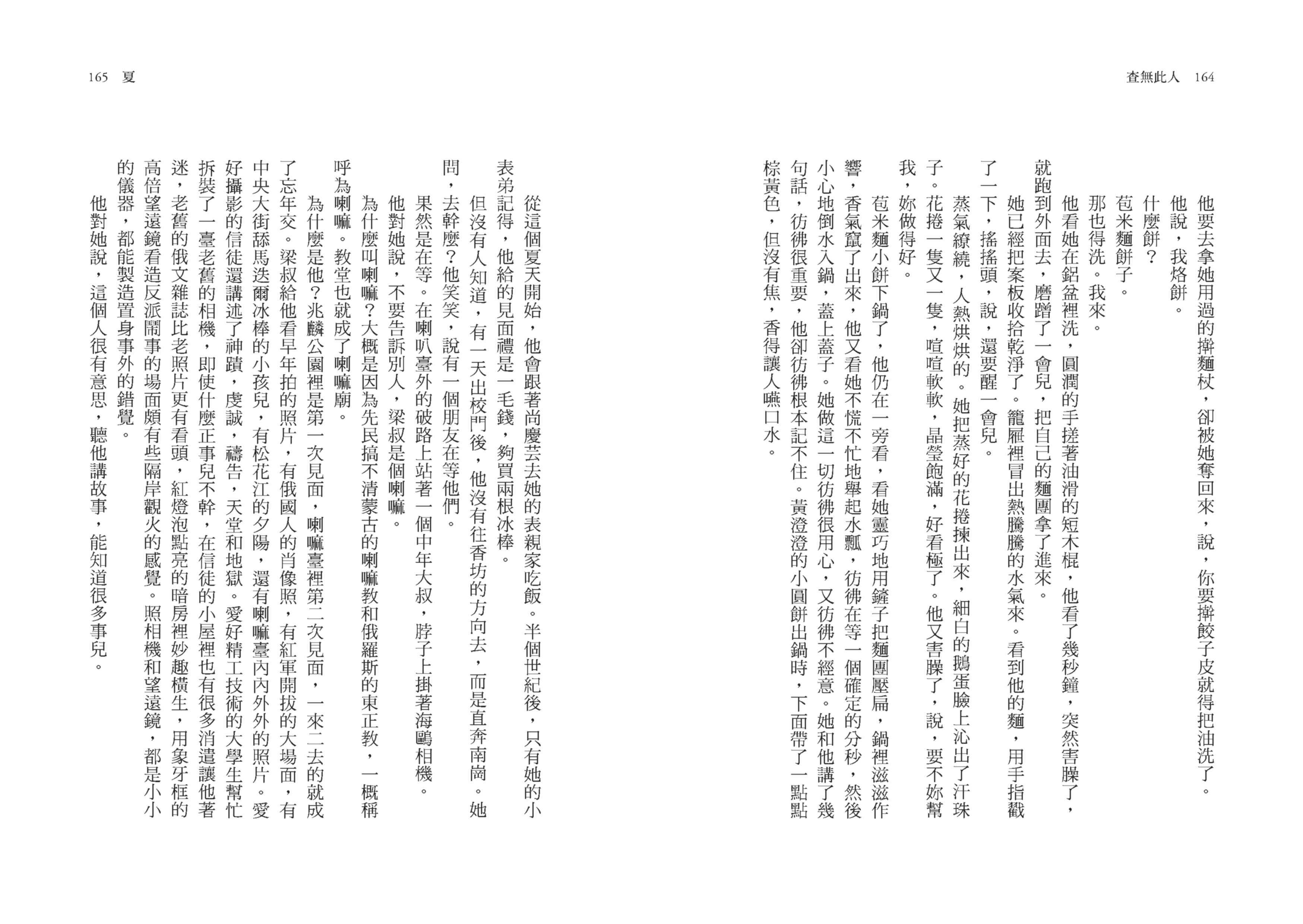查無此人
出版日期:2020-07-17
作者:于是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52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2.2cm
EAN:9789570855623
系列:當代名家
尚有庫存
遺忘是太容易了。
一代人離去,下一代人還沒辦法收攏那些記憶,
又要汲汲營營地去創建自己的生活。
上海七○世代小說家于是的抵抗忘卻之作
一個女兒,伴著一個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父親,
寫遺忘為表象的病徵,寫病的隱喻。
【Podcast】當面對失智與失憶-用文學叩問生命的意義
查無此人,令人感傷的,並非尋回原址而人已離去,從來都是景物近在眼前,但記憶破損,讓所有存在的證明失卻了依據。
上海小說家于是的《查無此人》,書寫屬於女子子清的兩代故事,當年邁的父親罹患阿茲海默症而漸失記憶,她回到父親身邊,在日常陪伴之間,逐漸貼近陌生的至親,走進他出身的東北,一個亂世中的商人家族與歷史往昔。小說往來於分隔的時空,彷彿舊事零散等待著拼湊,從四○年代以至二○一○年代,不同代的人們,同樣磕磕絆絆地走來。
于是說:「我想寫:在以遺忘為表象的疾病背後,還有一場又一場龐大的遺忘事件:集體的、自發的、被迫的、歷史性的大遺忘。」老年的疾病,在小說中,擴展為一個家族、幾代人遷離與尋根的故事,年輕時的父親從鄉村到城市,如女兒從一國放逐至異國,而她們所牽引的親情、愛情、歷史、病疾,且存放著屬於眾人這漫漫半世紀的共同命運。
文壇好評
專文引讀
彤雅立
張怡微
共同推薦
吳妮民
李欣倫
凌明玉
徐禎苓
張郅忻
(按姓氏筆畫排序)
作者:于是
小說家、譯者,現居上海。
著有《你我好時光》、《慌城孤讀》、《事後》、《一隻黑貓的自閉症》、《六翼天使》等小說和散文。譯過珍妮特.溫特森、保羅.奧斯特、史蒂芬.金等作家數十部作品。
推薦序/父親記憶的殘瓦 彤雅立
推薦序/煙火債.很少的事.枯榮之心 張怡微
冬
春
夏
秋
後記
煙火債.很少的事.枯榮之心/張怡微
許多年來,于是的主要職業更像是一個文學翻譯。儘管她曾以暢銷小說名世,主打都市言情,在文學與網路相遇伊始,許多人都讀過她的作品。
于是從事過許多工作,寫過很長時間的專欄、評論。與都會生活中許多獨立女性一樣,她擁抱自我、熱愛旅行。但歷經時光砥礪,終於又回到小說寫作中,契機卻是源於父親的一場病。
在父親被確診為「阿茲海默症」之後,于是的生活慣性被打破了。和父親單獨相處的時光,孕育了《查無此人》這部小說,而直至這本書真正完稿、出版,又經歷了漫長的時間。疾病突然創造了負擔與責任,但換一種方式來想,也許是父親又將于是拉回到更純粹的文學世界中。《查無此人》令她仔細爬梳了父親的來歷、其實也就是自己的來歷;找尋到遙望祖輩的鄉愁、其實正是檢閱現世的哀愁。也令她從一個都會女性,還原為一個普通的女兒。
「我不再是我」。她藉由小說人物「子清」在故事中自陳。「她甚至懷疑,命運要她把前十年欠下的煙火債一次性還清。」
《查無此人》被分割成不同時空,一是父親的身世,出身於東北,一個亂世商人家族;另一個則是女兒子清的內心生活。身世越來越完整,離別就越來越切近。從子清的獨白,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孤獨的女生舉重若輕地介紹著自己的前半生:「我有一個安分的童年,姐姐遠嫁加拿大,大學時母親亡故,兩年後父親再娶,畢業後我獨自生活,沒有固定單位。父親和母親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上海,再也沒有離開,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到退休,無波無瀾。續弦後他和女方一家住在一起,每年我大概會過去看幾次。父親三年前中風跌倒,同時被宣判得了阿茲海默症。大約一年前就叫不出我的名字了。就這樣。」
顯然,「就這樣」不足以生成一部創作的根基。所謂「煙火債」,更像是子清對於複雜的身世、離散的陰影及撿回一個沒有記憶的父親時的無奈、惶恐、不習慣的淺淺應答。子清的善良、樂觀包裹著敏感脆弱的內心,殘酷的命運橫陳眼前,在審美和批判之間,她選擇了吞下難以細表的苦衷,一頭栽入對新的日常生活鉅細靡遺的描述和接受,以期緩解內心的種種喪氣與哀涼。
女作家書寫「父女關係」是一個經典的母題。如吳爾芙的《燈塔行》、鍾芭•拉希莉的《陌生的土地》、又或者李翊雲的《千年祈願》……父親象徵著權威、尊嚴、品德,女兒對父親的愛看似簡單卻又深厚,看似隔閡卻又溫柔。父女之間,既是男女,又是長幼。如戴錦華所說,在「父親情結」之中,潛藏著的不僅是潛意識、欲望的詭計,而且是女性現實困境與生存困境。
在父親喪失的記憶之後,子清反而奪下了父女生活的話語權。那個被繼母還回來的父親,在她的引導下一點一滴完成日常生活。這本身很反諷,全部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但溫馨居然是真切的,悲傷也是。子清心裡明明白白,她的付出不會有人真正懂得,也不會有人認真記得。父親的疾病與離開,照耀她的孤獨,這種孤獨令他生前的出走、破壞都可以顯得是打發時間的小事。對於子清而言,病魔險惡過任何一個陌生女人,與子清拉扯、搏鬥。子清的孤獨、驕傲,只能令她假裝虛與委蛇,「她挽著他,像一個嫉妒心極強的小老婆,決不允許他離開自己半步,決不信賴外面的花花世界。她挽著他,也像一個耐心的早教老師循循善誘……只有她永遠是父親的女兒,這一點無可改變。」所有人都離開了父親,但是子清不能。子清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人走失了,卻沒有人去尋找他們」,但她做不到。那是一位女兒童年以後、一位父親晚年以前,被生生挖去一大塊的殘破生命史。
小說開篇,子清說起父親的一生,「和我們一樣,做了很多事,但不一定很重要。」小說末尾,「她們每天都好像去很遠的地方,但只做很少的事,很累地回家。」洋洋灑灑一輩子,可以說出來的事卻顯得那麼蒼白。父親零碎的一生在原鄉親眷們口中,像碎片一樣降落。只有子清知道,唯有內心的野獸是父親交給她的血脈、遺產,誰也奪不走,因為他生養了她。
「查無此人」這個題目很嚴酷。閨閣之間,昭曠之原,都不再有父親這個人。世界、世間都像患上阿茲海默症一樣,將普通人的歡喜哀愁一併忘卻。像于是自己說的,「一代人離去,下一代人還沒辦法收攏那些記憶,又要汲汲營營地去創建自己的生活。」
有情的人,情何以堪。
世全•2013
昨晚翻譯到三點半,夢做得太逼真,醒來很累,已過中午。但她決定還是去一趟遙遠的城郊,看望父親。每週總有那麼一兩天心神不寧,她分不清多少是因為擔憂,多少是因為愧疚。匆忙地刷牙洗臉,換上黑色外套和牛仔褲,穿板鞋,喝下一罐咖啡,塞下一只紅豆麵包,把耳機戴好,再挑一本不太厚且無需太動腦的書,出門。
父親的病,擴大了她的版圖。十號線轉乘三號線到終點站,最快也要一個半小時。只有兩次,關鵬有空,開車送她去,但沒有陪她上樓。關鵬用他的方式將版圖又擴大了一點:從福利院出來,不直接上高架,而是左拐進入一條小路。子清這輩子都沒有去過、甚至沒有聽說過那條路,事實上,她對這片區域的認知僅僅在於福利院本身、地鐵站本身,以及兩者之間的步行路線。要不是關鵬,子清永遠不會知道,父親所在的福利院和濕地公園那麼近。公園內的花草蟲魚和潮汐對她來說也是全然陌生的。最陌生的感覺則來自於這種組合:看望父親的短途旅行+無憂無慮的公園觀光。未知可以迅速變成已知,只需依靠注釋完整的圖文指示牌。木棧道兩旁的妃柳漸漸合攏,河口的風景依稀可見,彷彿走在綠色岩洞裡,走到盡頭就見到水草瑩瑩的灘塗,枯黃的蘆葦朝著一個方向拜倒,再遠處有長船悠然駛過,吳淞港的高腳吊車聳立出堅硬線條——那是兩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第一次看到的上海河口景色。
10:10分的潮位紀錄:0.7米。
14:15分的潮位紀錄:3.5米。
子清第一次想到:記錄潮汐,也許是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和潮汐相比,地鐵裡的人潮雖然也有潮位規律,但太不具美感了。如果人不多,她會看書,地鐵很能考驗情節的抓地性。她會低眉順眼在書頁三十釐米的上方,但書頁翻動的速度很可能是自欺欺人的表演。她會看到無數褲腿、鞋子和肉鼓鼓的手指,觀察氣味和指甲的狀態,默默判定身邊乘客的來處和歸處,動用不必要的、過剩的警覺,不可避免地走神。有一次,她看到一個人在地鐵裡認真地研讀樂譜,便在心裡給他布置了艱苦的亭子間童年,輝煌的未來則設置在維也納的歌劇院。還有好多次,車廂裡的氣味和嘈雜讓她無法安心看書,便假想追看的美劇主人公在這節車廂裡會怎樣:福爾摩斯會一敗塗地,Dexter無法替天行道並安然撤離,豪斯醫生會死於腦力衰竭和諷刺過勞,Nikita也會黯然失色,瞬間回到難民孤兒的初態……有時她會想到,父親在上海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卻從沒有搭乘過這條地鐵線。
如果人太多,沒有座位,她只能站在人群裡聽音樂,調大音量。聽了十多年的歌手們的聲音才值得依賴,起承轉合帶領她正常呼吸。她的iPod裡大都是老歌,Chara肆無忌憚的野貓般的唱腔,小室哲哉破產前的創作,椎名林檎撒野般的高音……每當隨機播放到Suede的Everything Will Flow,她都會在心裡說,來了來了,這才是看望父親之旅的主題曲。
今天的地鐵裡,她把書看到157頁,凶手幾乎已要落網。走出地鐵站的時候,她看了看手機上的時鐘,剛好三點,距離福利院的晚餐時間還有一小時,她決定不打車,步行二十分鐘,剛好過去陪父親吃飯。
父親最終住進這家福利院,是幾個月前的事情。父親和她都有點不適應。他也許有極其短暫的清醒時刻,也許會抓緊時間咒駡沒良心的女兒和後妻,也許會害怕地發現自己被一群陌生的老頭圍繞,每一個都不像是正常人,而等短暫的清醒過去,他又和他們渾然一體。泥牛入海。而對子清來說,唯一不適應的就是負罪感,即便斜跨整個城市去看望父親,實際上不過是消耗體能和時間,換來一點點心安理得的錯覺,根本無法改變她對病情無可奈何的事實,卻又處處提醒著她:她把他交出去了,再也沒有努力陪他,沒有照料他,而是徹頭徹尾地放棄了。
走進福利院,在門口簽了出入證,她便看到那些貓。大都是三花和黑貓,懶洋洋的徘徊在花園的草地上、樹下,等待著晚餐時段會出現的剩飯剩菜。一個老人坐在輪椅上,和一隻肥胖的花狸貓四目相視。另一個老太太抓著貓糧袋,不停地趕跑別的貓,又對一隻懷孕的黑貓說,快點吃呀,多吃點,別讓牠們搶走了。他們都是老人公寓裡的住客,生活可以自理,所以可以自由進出。走過兩棟老人公寓,再走到小徑的盡頭,便是父親所在的那棟樓,電子門鎖意味著裡面住著喪失自理能力的失智患者,他們不可以隨意外出。
二樓三樓住著老太們,四樓住著老頭們。電梯和居住區之間也隔著玻璃門,從內部出來時需用門卡開門,就連樓梯間通向外部的那道門也需要門卡。這些封閉策略都是針對失智者的,讓他們幾無可能獨自走出去,從而杜絕走失和迷路的機會。有一次她不想麻煩護工來為她開門,以為走樓梯也能出去,卻發現自己被困在樓梯間裡,上下左右都是死路。
大多數時候,這座內裝修規格達到三星賓館的福利院裡都很安靜,公共活動區的一大半空間被一張大桌占據了,老人們大多圍坐在桌邊,什麼也不做。只要有人弄髒了地板,保潔員就會在幾分鐘內收拾乾淨。每一條走廊都被拖洗得鋥亮,反襯著某種骯髒的必然性。她還見過幾次洗地機工作的場面,肥皂水和消毒水轉出一圈圈的白色泡沫,像一幅緩緩鋪張的抽象畫,那是她在這個空間裡見過最有生機的圖案。
她常覺得這裡的潔淨維持得太好,讓人放心,卻也偽飾太平。都市養老機構裡有寬敞好用的大洗浴室,走廊、窗邊、床邊和衛生間裡都有扶手,瓷磚地,塗料牆,木製原色吊頂,吸頂燈,中央空調,統一的潔具……沒有任何個性,也沒有缺點。她在心裡稱之為:老年幼稚園、時空結界、生靈墓園……
今天,一出電梯,她就覺得四樓的氣氛有點怪異。大廳裡,人影寥寥無幾,擺在電視機牆對面的藍色沙發上竟也空無一人。通常,護工們會在這個鐘點把老人們聚集起來,讓他們各就各位,圍坐大桌,準備開飯,她會在那一群老人的剪影中迅速找出父親,因為他的座位幾乎是固定的,整個白天,他都默默地坐在那裡。今天桌邊沒有人。但她還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她看到,父親雙手抱著一臺微波爐,繞著長方形的大桌走成背影,插頭線在桌腳絆了一下,又被拖著走,不情不願的跟在一雙白生生的赤腳後頭,隨著蹣跚的腳步一頓一頓。肩胛骨彷彿要刺穿汗衫聳出來,和懷裡沉重的分量艱難對峙著。現在,他又拐彎了,微波爐有一扇鏡面門,搖晃在他身前,映現出一個年輕女子的身影,左右顛動中,反倒是她更像被招進魔鏡的魂,而他是巫。她強忍著,把視線從過分清晰的鏡面中的自身拉出來,去看他的臉,他凸起的膝蓋,他幾乎瘦到隱形的胯部,他裸露在外的顫抖的小腿和大腿,皮肉像裹屍布垂掛下來。他繼續繞行,又走成了背影。她不知道他這樣捧著一臺微波爐繞著桌子走了多少圈。她想像不出一個耄耋老人有多大的氣力能完成一件荒唐透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