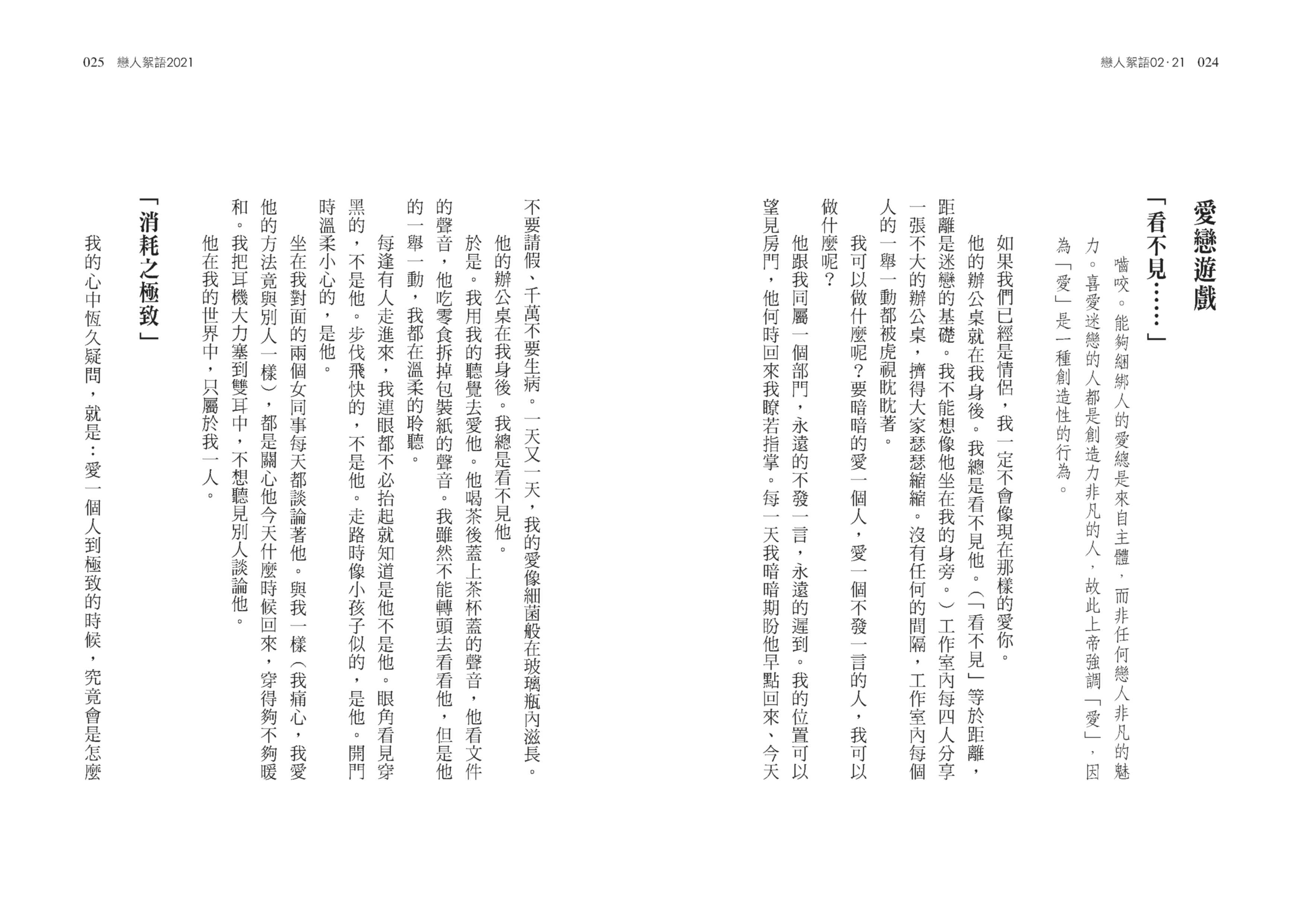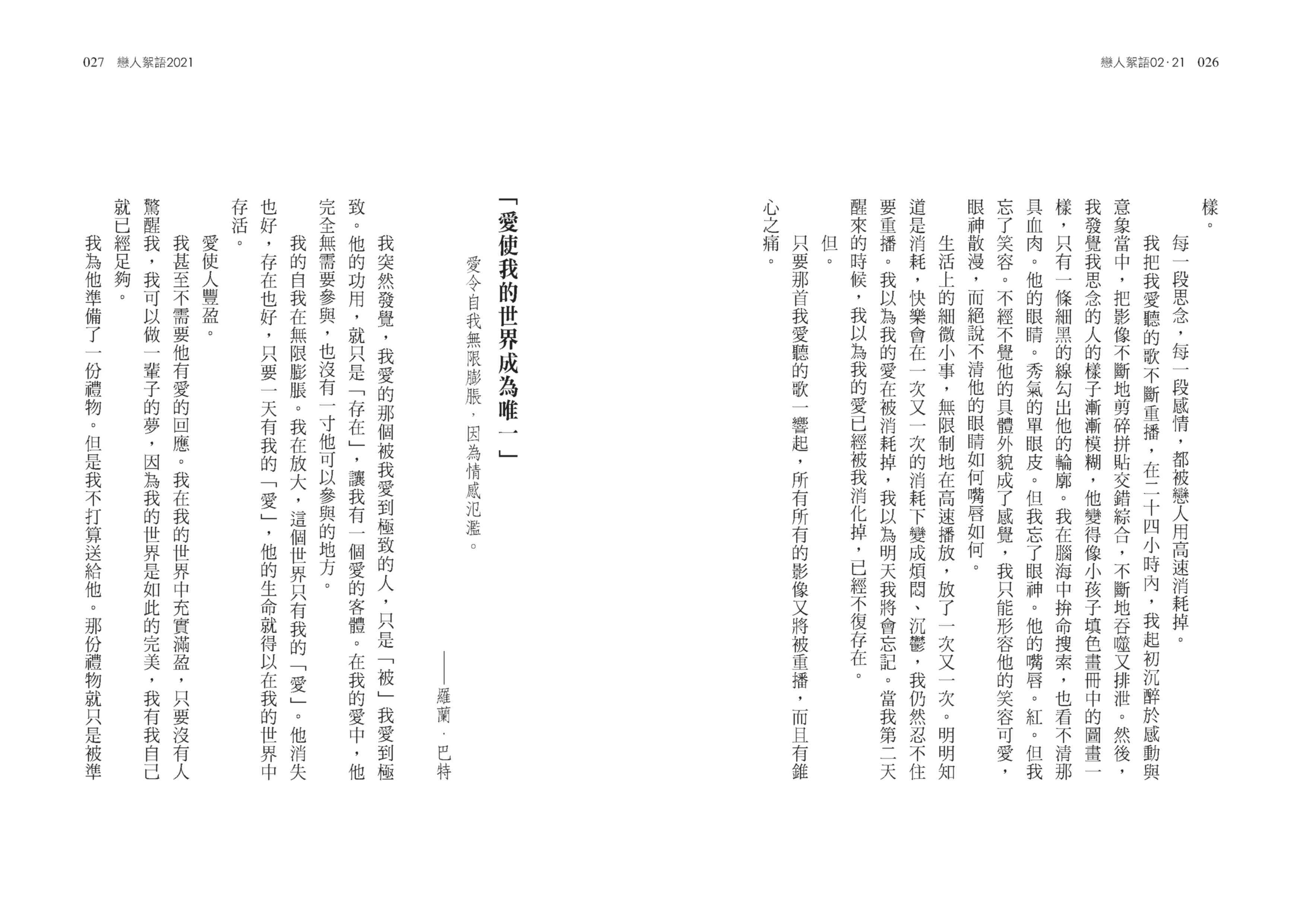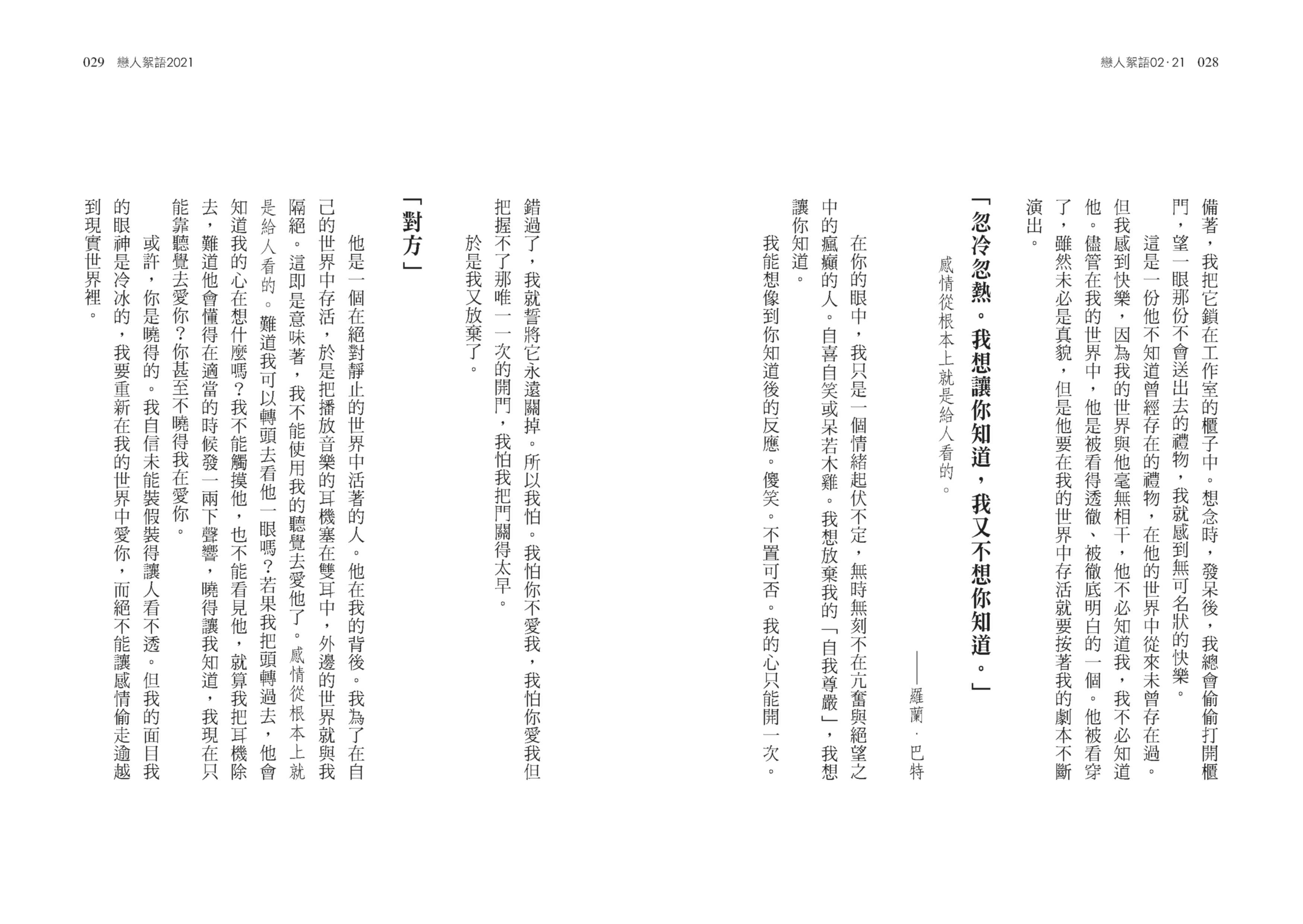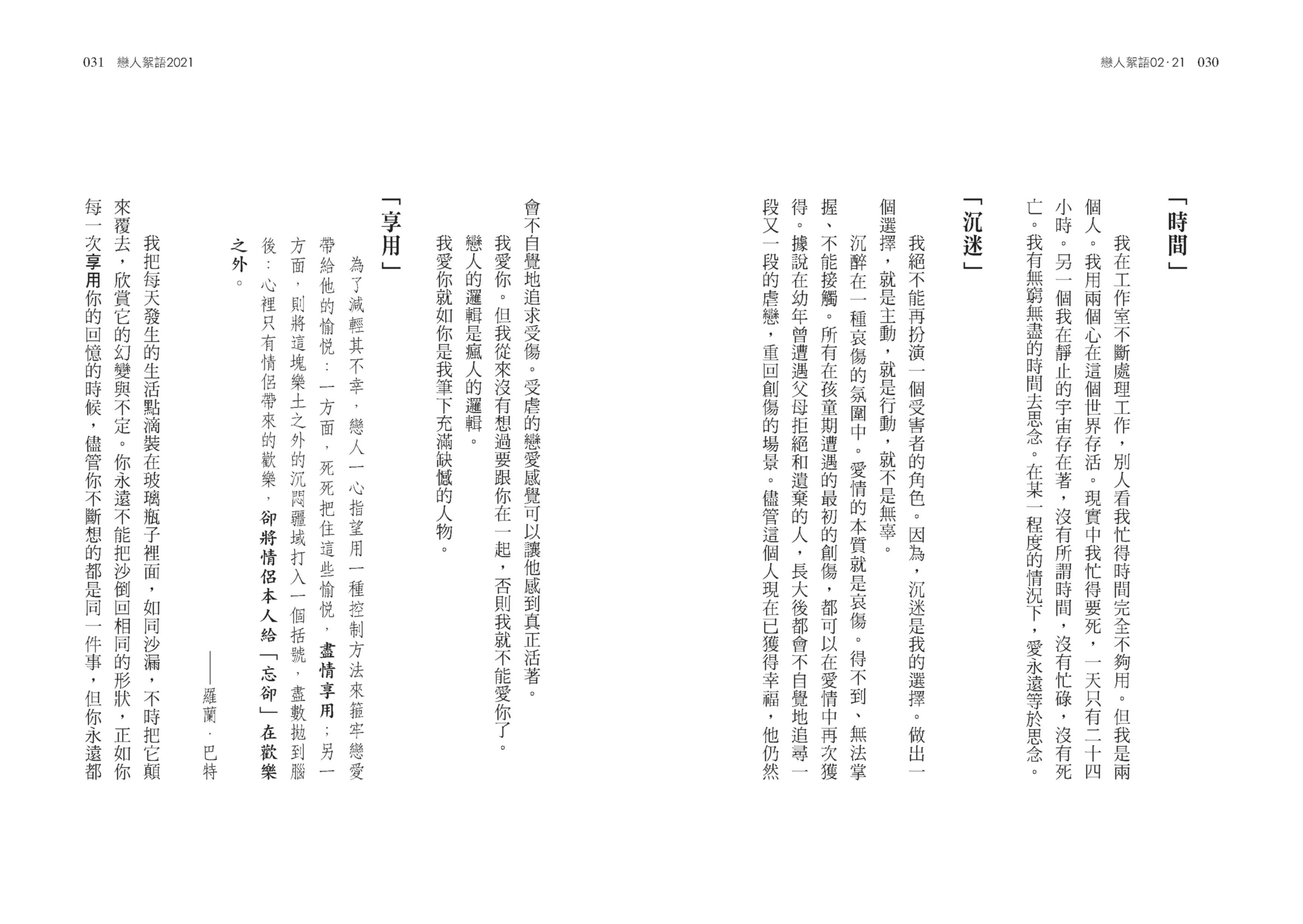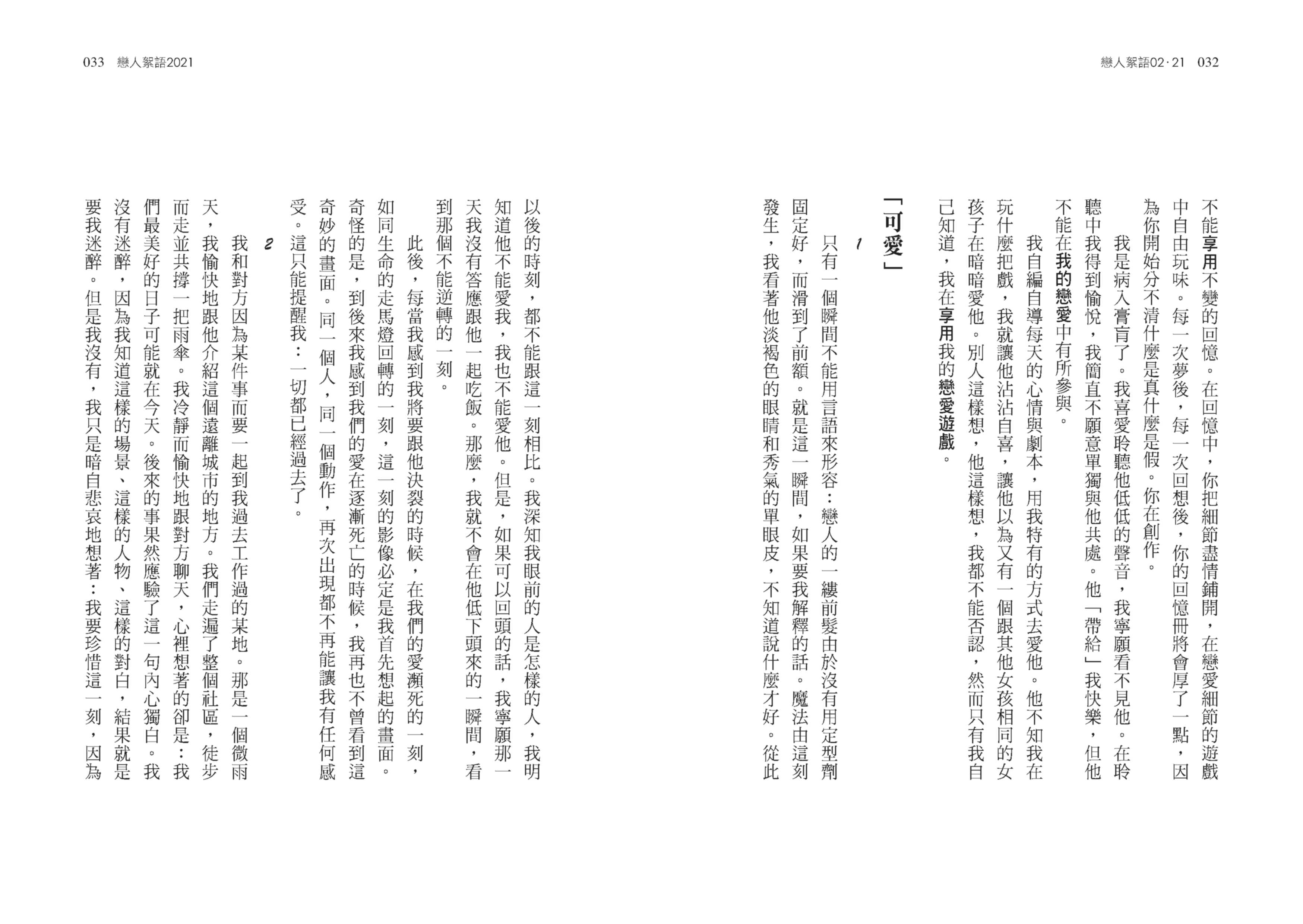戀人絮語02.21
出版日期:2021-03-18
作者:梁慕靈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88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1.8cm
EAN:9789570857252
系列:聯經文庫
尚有庫存
我愛你。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你在一起,
否則我就不能愛你了。
從前的戀人,未來的愛情,終將走向不可避免的結局。
每一段文字都是戀人的後設,
而每一句書寫都是對愛情的消費。
梁慕靈:
羅蘭.巴特以戀愛去思考後設和語言,我則以後設和語言去思考戀愛。
這是一個值得記念的狀態:每一次的戀愛。如果你在閱讀這部小說時感到莫名的感動,那麼恭喜你,你一定曾經經歷過真正的戀愛之感;而我常常懷疑,在這個城市生活的人,是否每個人都曾經經歷過愛情。
離去和失去是這麼的不同:是我要離開你,所以我已經不再在意是否失去你。
Instagram上的「限時動態」才是我們該採取的愛情模式。
在有限的時間內,把狀態在眾人的眼前公開,然後期限過去,
訊息自然銷毁,一切都煙消雲散,連把短訊刪除的過程都可以省略……
1977年,羅蘭.巴特出版最著名的愛情論述《戀人絮語》,以愛情為題探究戀人的娓娓傾吐和叨叨話語;2021年,梁慕靈則借其語絲和形式,以女性的角度重新思考,建構新的、屬於當代的愛情觀。
走進小說情節中的戀人模式,感受屬於這世代的日常短訊、內心呢喃,在戀人的愛與不愛間,在文字的曖昧計較間,在訊息的真假虛實間,試著捕捉這時代的愛情想像與戀人意義。五篇或長或短、值得細心品讀的絮語碎片,是零碎閱讀中的靈光,是愛戀思索中的片羽,也宛若三稜鏡透析那些屬於愛情的各種揣想與臆度,將幽微最不可言說的感覺和關係,化作異常清晰的──愛的質粹。
那些心動暗想
▍如果我們已經是情侶,我一定不會像現在那樣的愛你。
▍我的自我在無限膨脹。只要一天有我的「愛」,他的生命就得以在我的世界中存活。
▍我愛你就如你是我筆下充滿缺憾的人物。
▍我愛你。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你在一起,否則我就不能愛你了。
患得患失的起伏
▍我的心只能開一次。錯過了,我就誓將它永遠關掉。所以我怕。我怕你不愛我,我怕你愛我但把握不了那唯一一次的開門,我怕我把門關得太早。
▍沉溺,是一種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狀態。我認輸了,全面投降,不作任何反抗。
▍愛情其實是一個人的事,對方永遠都不可能體會到你自己的感受。從來沒有兩情相悅。
關於曖昧迷戀
▍慣於迷戀的,都是具有高度想像力的人。
▍我自編自導每天的心情與劇本,用我特有的方式去愛他。他不知我在玩什麼把戲……然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享用我的戀愛遊戲。
▍瞹眛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狀態……你們早已戀上了。其後的一切都只是在反覆驗證戀人的自我欺騙。
耽溺掙扎的理性
▍所謂的失戀,就是失去想像的空間及對象。戀人不能再有任何藉口去想念,沒有人名正言順的讓自己去掛念。
▍愛情的美好以維持時間越長為目標,卻不知自身的本質是相反的。
▍戲劇裡的對白每一句都具有意義,而日常生活的說話並不具備這種被舞台燈光照射過的存在感。是的,是存在感,真正的存在感。心靈上的愛情、身體上的痛感以及藝術上的創造,是世上唯一可能證明存在感的事。
劫後餘燼
▍漸漸地,對方在我面前只能演出默劇,因為他在一個不屑當觀眾的人面前,再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念誦他的對白。
▍比起揭穿對方,我更希望看清自己的醜態:你曾經沉醉的是如此容易不攻自破。
▍離去和失去是這麼的不同:是我要離開你,所以我已經不再在意是否失去你。
名家好評
專文推薦
何杏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共同推薦 (按姓氏筆畫排序)
李豪|詩人
吳俞萱|詩人
張嘉真|作家
董啟章|作家
溫如生|作家
蔡傑曦|攝影作家
潘國靈|作家
蘇乙笙|作家
戀人的語言往往是最難捉摸的詮釋學,唯有投入愛情之中方得一些靈光。本書書名脫胎自解構大師羅蘭•巴特的名著,作者梁慕靈揮灑著新世代的語境,令讀者更貼近愛的真相。
──李豪|詩人
她將愛情看成一幢抗衡她的書寫系統的複雜幻象。我們作嘔閃躲的一團血肉,她用手指慢慢剝開,找出裡頭的神明。
──吳俞萱|詩人
一個人的時候總在等待一個更加瘋魔的人出聲,來擺脫瘋魔與驗證瘋魔,作為指南與熱燙的傷疤,這本書非常有效。
──張嘉真|作家
梁慕靈的小說揉合了溫柔的剖析與冷峻的抒情,猶如一支理性與感性的雙人舞。
──董啟章|作家
人世間最難理解的愛,慕靈提出了當代的困惑和洞見,讓我們能在字句扉頁間,釐清並找到自己的解答。
──蔡傑曦|攝影作家
作者:梁慕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2002年以〈故事的碎片〉獲臺灣《聯合文學》第十六屆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並入選臺灣九歌出版社《九十一年小說選》,並於《聯合文學》、《香港作家》及《明報》等發表小說創作。
現為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創意藝術學系系主任及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主任,曾出版學術著作《視覺、性別與權力: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數碼時代的中國人文學科研究》及《博物館的變與不變:香港和其他地區的經驗》等。
推薦序:從碎片掇拾到絮語編織
在2019年與夏目漱石對話──是為序
戀人絮語
故事的碎片
紅莓記
胸圍
仁愛街市
後記
推薦序文(節選)/從碎片掇拾到絮語編織
何杏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所長)
一
最初讀到慕靈的〈故事的碎片〉,是在2002年一個季夏夜發出的電郵裡。慕靈說她寫了一篇小說,請我有空看看,給她一些評語。那一年,慕靈已完成大學課程,畢業論文的題目是〈從古典好萊塢電影看張愛玲的劇作〉。她在畢業後攻讀教育文憑,兼任「抗戰前中國現代劇本」研究計劃的助理,並協助香港中文大學「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特刊的編務。因為感激她的幫忙,很想在其小說創作的路上予以鼓勵,於是立刻打開文檔,當時讀到的是〈故事的碎片〉。
這篇小說寫得非常細密,極富生活質感,讀來充滿驚喜,足以令人忘卻那種帶著責任的閱讀動機。2002年,有關「地誌書寫」(topographical writing)和「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的討論方興未艾,有關「聲景」(soundscape) 的研究,更未進入華語評論界的視野。當時我只可以說,這篇小說寫香港非常地道,細節很豐富,既有西西浮城寓言的意趣,亦有張愛玲那種沉到底的悲哀,這是何等奇異的組合。
小說文檔的最後一頁,附了慕靈的個人資料,她正打算把小說投到第十六屆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故事的碎片〉獲得了短篇小說首獎,先發表於《聯合文學》,後收錄於九歌出版的《九十一年小說選》,同屆得獎的作者還有甘耀明和聞人悅閱。
獲獎之後,慕靈發表了兩個小說,按時序排列,〈胸圍〉在2003年1月發表於〈明報‧世紀〉、〈紅莓記〉同年12月發表於《聯合文學》,2005年收錄於《台港文學選刊》。兩個小說寫的分別是中文大學學生的情事和貨櫃車司機一家的鬧劇,從選材到發表和入集,可見台港兩地的文學因緣。
集裡的長篇小說〈戀人絮語2021〉於2003年開筆,從香港的故事轉到關於愛情本質的思考,以絮語的方式探索小說的界限。這個長篇的完成歷時十八春,期間慕靈於2004年考上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研究院,從哲學碩士到哲學博士,一直醉心於張愛玲和新感覺派的研究,成績斐然。
小說集裡最後一篇〈仁愛街市〉寫於2000年,之前未有發表。仁愛街市位於香港屯門區,故事寫的是中學生阿欣在仁愛街市賣菜。阿欣最擔心的是雪白的校服裙子遭街市的髒水濺污。她的願望是考上大學,因為大學代表了自由快樂,街坊都說她勤力,但她考了兩次會考都只三科合格。她從未到過港島區,屯門便是她的整個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阿欣的形象,跟〈胸圍〉裡的洪小美和〈紅莓記〉裡的趙小怡以至張揚,皆可或顯或隱地連繫起來。平凡瘦削的洪小美,是家庭鬧劇裡的冷眼旁觀者,一直如常活下去。充滿傳奇色彩的趙小怡,則是考上了大學的阿欣——若早生一個年代,趙小怡或阿欣甚或可以成為〈故事的碎片〉裡的外婆,一個「時代的傳奇女子」,替政府的洋官管家,一口香港式的流利英語。只可惜阿欣厭惡屯門,反覆想到要死,其後真的目睹自己那條千方百計要保護的白色校服裙被輕鐵輾過稀爛。敘述者在小說的結尾加了這一句:「本來,那死的念頭只是隨口說說,輕輕略過」,甚有張愛玲那種畫外音說話人的風範。
二
在這個集子裡的作品,可以分為兩部分來閱讀。第一部分是四個以屯門、秀茂坪和赤泥坪等香港地景為主軸的短篇,第二部分是開首的長篇小說〈戀人絮語2021〉。這四個短篇和一個長篇,可以視為作者一個成長的歷程。在那崎嶇的成長期,漫漫長途,看不見盡頭。在一片荒涼和滿目瘡痍中,或許只有冷靜的觀察和傳奇的投射,可以撫平青春的激越。
如果你對成長故事有興趣,又或是喜歡研究地誌和市聲,我會建議你先讀集裡的四個短篇。這四個短篇裡面,有一種青葱的真誠和坦率,那股氣場與力量,是走過長路以後,無法重回也難以複製的。我很慶幸慕靈在求學的歲月,可以用如此豐盈飽滿的筆觸,把當下的感應以小說的形式表達出來。慕靈在這些短篇裡所選擇的書寫方式,需要兼顧人物和對話、故事和情節、意象和象徵、並要帶出寓意與觀照,是小說的本色寫法,難度非常高。她近年任教於香港公開大學的創意藝術系,亦會教授寫作課,這一系列的短篇小說,絕對是精彩的演示。
作者自序
「在2021年與夏目漱石對話」──是為序
發揮才智,則鋒芒畢露;憑借感情,則流於世俗;堅持己見,則多方掣肘。
總之,人世難居。
──夏目漱石
要有痛苦,才有寫作。不一定是自身的痛苦,卻是感受到他人之痛苦而轉化為自身的痛苦,是為寫作。
世上有太多沒有痛苦的寫作,在我看來都是庸俗與欺世盜名之作。痛苦不分大小,痛苦是一個寫作人的存在之證明。我在重踏寫作之途的這幾年,卻是在想,比起世上千千萬萬追尋自由和幸福之人,寫作人的痛苦又有什麼值得書寫呢?靈魂的痛苦比起肉體的痛苦就更高尚了嗎?
有一天在異地,夜快將盡,在半明半昩的時刻,在睡夢中的我驀然醒來,然後在這段時間以來一直分裂地生活的自己,竟然不由自主地流起淚來。我看著自己在床上躺著,明明是在睡覺,淚就是控制不住的流下來,流下來。就是這樣無聲地流下來,壓抑不住。
我珍惜自己還有感覺的這個時刻,因為,這個狀態就是一個可以寫作的狀態。但是,寫作人儘管把這些都寫下來,但在千千萬萬死去了或將死的人之中,這樣的寫作究竟有什麼用?
把自身和別人的痛苦記錄下來,使它不至於煙沒、遺失,我以為是寫作的意義。然而夏目漱石卻說:
孤村溫泉,春宵花影,月下低吟,朧夜清姿,──這些無不是藝術家的好題目。這些好題目,一起浮現在我的眼前,而我卻做了不得要領的詮釋,進行多餘的探求,在難得的雅境裡建立起理論的系統,用惡俗的情味踐踏了求之不得的風流。這樣一來,非人情也就失掉了標榜的價值。
十多年前,我去寫起學術論文來。那是一個非人情的世界,我學會了以冷靜和理智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一過就過了這麼些年,然後,我又重回了這個充滿血肉和醜陋的人情之世。是我的選擇,我自己的選擇,我選擇了長久凝望深淵。它的回望終於來了。
這篇執筆於2003年的〈戀人絮語2021〉得以完成,是在這些年來一直縈繞在我心中一種「來不及了、來不及了」的催促和預感下完成的。我並不知道命運還安排了怎樣的未來給我,但是,就讓我還可以寫作的時候,盡情地寫吧;就讓我還可以不顧一切地工作的時候,盡情地做吧。因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我們身後推波助瀾,我們除了順應命運,還有什麼可以做呢?今日的一切勞苦,可能只為成就將來的某一瞬間的某一個決定。然後,祝願我在未來能夠有一天隱匿於大市,在一切的歷練以後,靜靜地寫作其他作品吧。
2020年1月30日
寫在瘟疫蔓延之時
「看不見……」
嚙咬。能夠綑綁人的愛總是來自主體,而非任何戀人非凡的魅力。喜愛迷戀的人都是創造力非凡的人,故此上帝強調「愛」,因為「愛」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
如果我們已經是情侶,我一定不會像現在那樣的愛你。
他的辦公桌就在我身後。我總是看不見他。(「看不見」等於距離,距離是迷戀的基礎。我不能想像他坐在我的身旁。)工作室內每四人分享一張不大的辦公桌,擠得大家瑟瑟縮縮。沒有任何的間隔,工作室內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被虎視眈眈著。
我可以做什麼呢?要暗暗的愛一個人,愛一個不發一言的人,我可以做什麼呢?
他跟我同屬一個部門,永遠的不發一言,永遠的遲到。我的位置可以望見房門,他何時回來我瞭若指掌。每一天我暗暗期盼他早點回來、今天不要請假、千萬不要生病。一天又一天,我的愛像細菌般在玻璃瓶內滋長。
他的辦公桌在我身後。我總是看不見他。
於是。我用我的聽覺去愛他。他喝茶後蓋上茶杯蓋的聲音,他看文件的聲音,他吃零食拆掉包裝紙的聲音。我雖然不能轉頭去看看他,但是他的一舉一動,我都在溫柔的聆聽。
每逢有人走進來,我連眼都不必抬起就知道是他不是他。眼角看見穿黑的,不是他。步伐飛快的,不是他。走路時像小孩子似的,是他。開門時溫柔小心的,是他。
坐在我對面的兩個女同事每天都談論著他。與我一樣(我痛心,我愛他的方法竟與別人一樣),都是關心他今天什麼時候回來,穿得夠不夠暖和。我把耳機大力塞到雙耳中,不想聽見別人談論他。
他在我的世界中,只屬於我一人。
「消耗之極致」
我的心中恆久疑問,就是:愛一個人到極致的時候,究竟會是怎麼樣。
每一段思念,每一段感情,都被戀人用高速消耗掉。
我把我愛聽的歌不斷重播,在二十四小時內,我起初沉醉於感動與意象當中,把影像不斷地剪碎拼貼交錯綜合,不斷地吞噬又排泄。然後,我發覺我思念的人的樣子漸漸模糊,他變得像小孩子填色畫冊中的圖畫一樣,只有一條細黑的線勾出他的輪廓。我在腦海中拼命搜索,也看不清那具血肉。他的眼睛。秀氣的單眼皮。但我忘了眼神。他的嘴唇。紅。但我忘了笑容。不經不覺他的具體外貌成了感覺,我只能形容他的笑容可愛,眼神散漫,而決說不清他的眼睛如何嘴唇如何。
生活上的細微小事,無限制地在高速播放,放了一次又一次。明明知道是消耗,快樂會在一次又一次的消耗下變成煩悶、沉鬱,我仍然忍不住要重播。我以為我的愛在被消耗掉,我以為明天我將會忘記。當我第二天醒來的時候,我以為我的愛已經被我消化掉,已經不復存在。
但。
只要那首我愛聽的歌一響起,所有所有的影像又將被重播,而且有錐心之痛。
「愛使我的世界成為唯一」
羅蘭‧巴特:愛令自我無限膨脹,因為情感氾濫。
我突然發覺,我愛的那個被我愛到極致的人,只是「被」我愛到極致。他的功用,就只是「存在」,讓我有一個愛的客體。在我的愛中,他完全無需要參與,也沒有一寸他可以參與的地方。
我的自我在無限膨脹。我在放大,這個世界只有我的「愛」。他消失也好,存在也好,只要一天有我的「愛」,他的生命就得以在我的世界中存活。
愛使人豐盈。
我甚至不需要他有愛的回應。我在我的世界中充實滿盈,只要沒有人驚醒我,我可以做一輩子的夢,因為我的世界是如此的完美,我有我自己就已經足夠。
我為他準備了一份禮物。但是我不打算送給他。那份禮物就只是被準備著,我把它鎖在工作室的櫃子中。想念時,發呆後,我總會偷偷打開櫃門,望一眼那份不會送出去的禮物,我就感到無可名狀的快樂。
這是一份他不知道曾經存在的禮物,在他的世界中從來未曾存在過。但我感到快樂,因為我的世界與他毫無相干,他不必知道我,我不必知道他。儘管在我的世界中,他是被看得透徹、被徹底明白的一個。他被看穿了,雖然未必是真貌,但是他要在我的世界中存活就要按著我的劇本不斷演出。
「忽冷忽熱。我想讓你知道,我又不想你知道。」
感情從根本上就是給人看的。
在你的眼中,我只是一個情緒起伏不定,無時無刻不在亢奮與絕望之中的瘋癲的人。自喜自笑或呆若木雞。我想放棄我的「自我尊嚴」,我想讓你知道。
我能想像到你知道後的反應。傻笑。不置可否。我的心只能開一次。錯過了,我就誓將它永遠關掉。所以我怕。我怕你不愛我,我怕你愛我但把握不了那唯一一次的開門,我怕我把門關得太早。
於是我又放棄了。
「對方」
他是一個在絕對靜止的世界中活著的人。他在我的背後。我為了在自己的世界中存活,於是把播放音樂的耳筒塞在雙耳中,外邊的世界就與我隔絕。這即是意味著,我不能使用我的聽覺去愛他了。感情從根本上就是給人看的。難道我可以轉頭去看他一眼嗎?若果我把頭轉過去,他會知道我的心在想什麼嗎?我不能觸摸他,也不能看見他,就算我把耳筒除去,難道他會懂得在適當的時候發一兩下聲響,曉得讓我知道,我現在只能靠聽覺去愛你?你甚至不曉得我在愛你。
或許,你是曉得的。我自信未能裝假裝得讓人看不透。但我的面目我的眼神是冷冰的,我要重新在我的世界中愛你,而決不能讓感情偷走逾越到現實世界裡。
「時間」
我在工作室不斷處理工作,別人看我忙得時間完全不夠用。但我是兩個人。我用兩個心在這個世界存活。現實中我忙得要死,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另一個我在靜止的宇宙存在著,沒有所謂時間,沒有忙碌,沒有死亡。我有無窮無盡的時間去思念。在某一程度的情況下,愛永遠等於思念。
「沉迷」
我決不能再扮演一個受害者的角色。因為,沉迷是我的選擇。作出一個選擇,就是主動,就是行動,就不是無辜。
沉醉在一種哀傷的氛圍中。愛情的本質就是哀傷。得不到、無法掌握、不能接觸。所有在孩童期遭遇的最初的創傷,都可以在愛情中再次獲得。據說在幼年曾遭遇父母拒絕和遺棄的人,長大後都會不自覺地追尋一段又一段的虐戀,重回創傷的場景。儘管這個人現在已獲得幸福,他仍然會不自覺地追求受傷。受虐的戀愛感覺可以讓他感到真正活著。
我愛你。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你在一起,否則我就不能愛你了。
戀人的邏輯是瘋人的邏輯。
我愛你就如你是我筆下充滿缺憾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