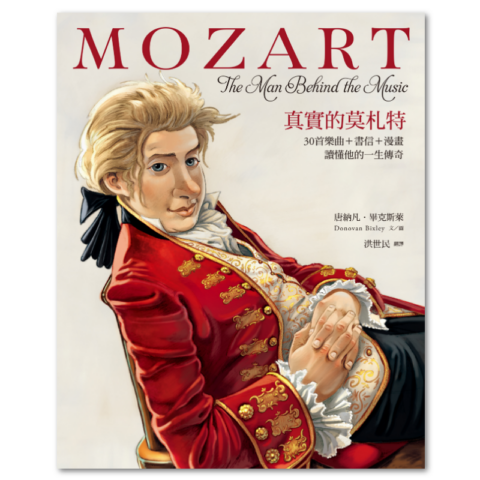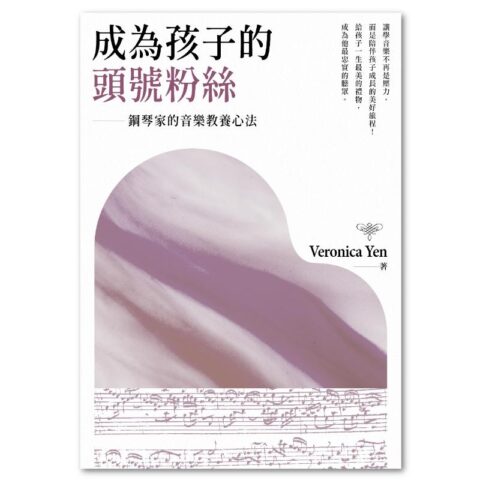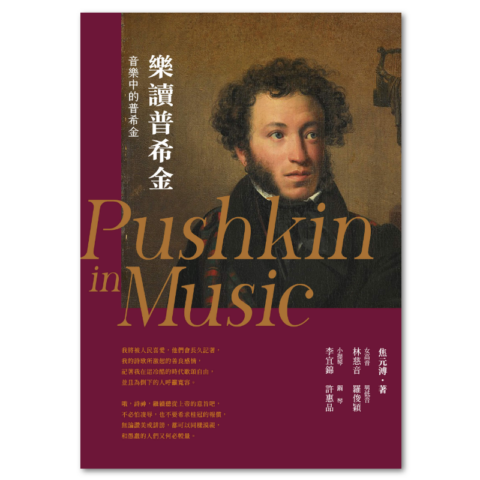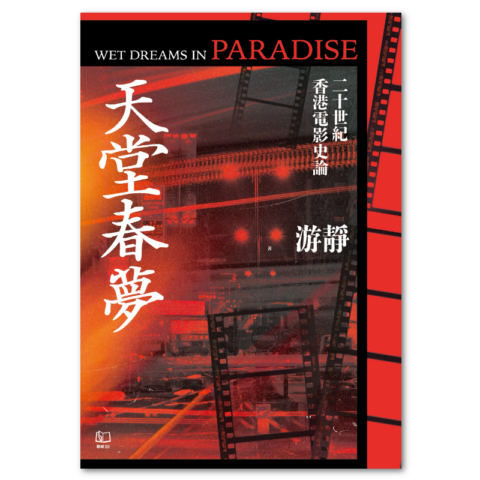百變千幻不思議:台語片的混血與轉化
出版日期:2017-10-11
作者:施如芳等
譯者:何曉芙、王念英、卓庭伍、張玄竺
編者:王君琦
翻譯校訂:蔡巧寧、柯昀青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04
開數:18開,高23×寬17cm
EAN:9789570850239
已售完
台語片如何崛起、何以衰敗?
台語片紛雜又深具開創性的美學風格從何而來?
台語片在全球電影史的語境座標何在?
台語片與台灣早期整體社會如何互為文本
台語片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是195、60年代重要的民間活動、是國家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是電影跨國╱境交流的產物,也在於它為台灣電影整體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對當代電影產生了具體的影響。但是,在威權時代,由於主政者的意識形態影響,台語片的歷史長期被忽視,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早已忘記這段豐富而重要的史蹟。
1989年,井迎瑞教授擔任國家電影資料館(國家電影中心前身)館長時,成立了「台語片小組」,眾人以幾乎是拓荒的方式從一片歷史廢墟中清理出台語片的輪廓,將我們從被迫的遺忘中喚醒。不過,台語片小組至今已將近二十年,相關研究雖然是按轡徐行,卻仍顯稀薄。《百變千幻不思議:台語片的混血與轉化》將近年來散見於國內外各處的研究論文集結成冊,冀望此書成為開創「台語片研究」這個新學門的第一步。
《百變千幻不思議:台語片的混血與轉化》所收錄的文章雖然沒有共同的理論框架或研究方法,但都回應了研究台語片的幾個共同關注,包括:台語片如何崛起、如何衰敗?台語片紛雜但深具開創性的美學風格從何而來、又是如何座落於全球電影史的語境?台語片與當時台灣整體社會如何互為文本?本書各章雖是各自針對不同的主題書寫,但彼此之間有著互為補充,或互為辯證的對話關係。透過這些書寫,原本形貌模糊的台語片得以被以不同的角度進行批判性地重構。期待這本書提供答案也帶出問題,以吸引更多後起研究者一起同行。
《百變千幻不思議:台語片的混血與轉化》企圖兼具歷時性及共時性,一方面串連跨時二十餘年來的著作,另一方面也橫通不同學界的研究,盼能在描繪出研究方向拓進的輪廓之餘,更收拋磚引玉之效,激發更多具有開創性的台語片研究。本書分為五大部,第一部的論文分別從社會史、文藝史、科技史的脈絡探討台語片的發展歷程並對興衰提出解釋。第二部的論文則是聚焦於台語片的類型發展與美學風格。在台語片的眾多類型當中,產量最豐、也最為後人所知的類型,便是帶有悲情色彩、並在當時多被以「家庭倫理文藝」等關鍵字進行宣傳的通俗劇類型。是故,本書在第三部收錄了三篇與台語片的悲情特色有關的論文。台語片一直以來在電影實踐上試圖與全球電影接軌之餘,又加以在地轉化的主要趨勢,在第四部的幾篇論文裡被充分展現。要理解台語片,除了在文本及史料上進行分析之外,更需要回到歷史現場。本書的最後一部重新收錄了石婉舜早期所發表有關玉峰影業與湖山製片廠的文稿以及林摶秋導演生前的訪問稿,以及陳幸祺以第一手訪談資料所梳理出有關台語片經營模式及演員制度的文章,這兩篇文章可與前面幾篇有關台語片產業發展的文章遙相呼應。此外,第五部也納入三澤真美惠與曾在台拍攝台語片的日本導演小林悟的訪談,在訪談中小林悟提及自己當年向台語片取經學習,他的見證更是推翻台語片拍攝技術欠佳的第一手資料。
作者:施如芳等
施如芳
1968年生於彰化,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現為劇場編劇,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助理教授級專技教師,作品有京劇《快雪時晴》、歌仔戲《燕歌行》《桂郎君》、崑曲《亂紅》、豫劇《花嫁巫娘》、音樂劇《大國民進行曲》、舞台劇《孽子》等二十餘部,曾出版劇本書《黃虎印》、《願結無情遊》、《孽子》。
鍾秀梅
現任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副教授,澳洲雪梨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博士。研究領域為第三世界女性主義、族裔研究、另類全球化研究等。專書有《發展主義批判》、《台灣客家族群史專題:美濃中、宋兩屋家族婦女生命史為例》、《西螺大橋推手:李應鏜與他的年代》。編審《孔邁隆教授:美濃與客家研究論集:客家的法人經濟、宗教、語言與認同》。
蘇致亨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國家電影中心助理研究員。碩士論文《重寫台語電影史:黑白底片、彩色技術轉型和黨國文化治理》曾獲頒若干論文獎,台語片研究專著將在2018年由衛城出版社出版。
洪國鈞
出身台灣花蓮玉里鎮。2004年取得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辭學博士,現為美國杜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副教授,以及動態藝術研究中心主任。著作與研究範圍包括台灣與華語電影,電影理論與電影史學,音影文化,類型電影以及紀錄片。
陳龍廷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法國國立高等實踐研究院(E. P. H. E.)宗教科學與文化人類學博士候選人。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史、台灣戲劇史、台灣歌謠與文化研究、台灣口頭文學研究、文化人類學等。主要著作:《台灣布袋戲的口頭文學研究(上)(下)》、《台灣布袋戲創作論:敘事‧即興‧角色》、《聽布袋戲尪仔唱歌:1960-70年代台灣布袋戲的角色主題歌》、《庶民生活與歌謠—台灣北海岸的褒歌考察》、《發現布袋戲:文化生態‧表演文本‧方法論》、《聽布袋戲:一個台灣口頭文學研究》、《台灣布袋戲發展史》。
施茗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東亞語言文化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台灣與韓國的文化研究,比較文學,電影與媒體研究,冷戰與後殖民研究,華語圈文化流,喜劇美學。
蔡玫姿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2004年獲國科會千里馬計畫補助,赴美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研習文學理論。曾獲府城、竹塹、南瀛、教育部文藝獎,著有小說集《指染女身》(2001)。為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中心副研究員,2013頂尖大學聯盟選赴美國柏克萊大學訪問學人,專著《從性別觀點閱讀類型文學》(2009)、《親臨陌異地—五四作家跨國經驗形構的文學現象》(2010)、《不安於室:成功大學的人文景觀》(2012),主編《反思身體:跨領域教學實踐與研究誌要》(2013)、《跨國─1930─女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
沈曉茵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西洋戲劇、電影研究。合編有《戲戀人生:侯孝賢電影研究》及《戲夢時光:侯孝賢電影的城市、歷史、美學》。近期論文發表於《藝術學研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等期刊及其他中英文專書。
張英進
美國聖地亞哥加州大學文學系系主任,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傑出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訪問講席教授。英文書籍包括《中國比較文學論文集》《華語電影百科全書》《民國時期的上海電影與城市文化》《華語電影史》《當代中國的另類電影文化》《全球化中國的電影,空間與多地性》《華語電影明星研究》《世界華語電影指南》《民國時期的上海視覺文化與都市現代性》《華語新紀錄片》《中國現代文學指南》等十三部。中文書籍包括《審視中國》《電影的世紀末懷舊》《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影像中國》《多元中國》等十部。
蔡明燁
高雄市人,英國里茲大學傳播學博士,現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台灣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以及歐洲台灣研究協會祕書長。研究領域以華語電影、媒體、科學與文化傳播為主,中文著作包括《媒體世界》、《危機與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與台灣電視》、《界定跨科際》、《看見,台灣電影之光》等;最新英文作品有《勞特里區華語傳媒研究手冊》(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Media)以及《台灣電影:國際評價與社會變遷》(Taiwan Cinema: International Reception and Social Change)。
王君琦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美國南加大電影電視批判理論研究博士。研究領域為媒體文化研究、性/別研究、華語電影及台灣電影研究。相關論文發表於《藝術學研究》、《文化研究》、《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等期刊及其他中英文專書。
林奎章
1979年生,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戲劇學研究所碩士,現任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約聘規畫師。致力於文化行政工作,曾服務於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統一蘭陽藝文股份有限公司等,承辦第49屆金馬在宜蘭、第35屆金穗獎暨短輔成果展宜蘭巡迴、電影《大稻埕》傳藝中心行銷活動等。碩論:《尋找台語片的類型與作者:從產業到文本》(2008)。
林芳玫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專長領域為媒體社會學、通俗文化、女性與媒體 、性別與國族 、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1992年至2000年任教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同時參與婦女運動,創辦「女學會」、擔任「婦女新知」監事。2000年至2006年任職於政府單位,推動婦女創業、青年志工、非營利組織與公民社會發展等議題。2006年迄今任教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著有專書《解讀瓊瑤愛情王國》(1994),獲聯合報年度十大好書獎;《跨界之旅》(2005),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最佳專欄寫作獎。近期將出版施叔青研究專書。
王俐茹
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研究領域為台灣古典文學與通俗文學。目前於華夏科技大學擔任通識兼任講師。發表論文包括:〈「忠義」的重製與翻譯:黃得時水滸傳(1939~1943)的多重意義〉、〈彌合歷史的艱難―以作家龍瑛宗、楊雲萍戰後初期(1945~1949)的「中國」歷史敘事為例的探討〉等研究論文。
梁碧茹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文化研究博士候選人。
陳幸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班畢業。因父親陳義為台語片製片,曾在台灣影人協會協助行政庶務,並嘗試進行台語片研究。2005年起從事公職,先後服務於臺東縣政府文化局;臺北縣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桃園縣政府文化局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桃園縣政府文化局。2014年辭職。嘗試轉業中。
林慧羚
現任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專技助理教授,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專長領域電影文本分析、影視企劃與編劇、跨媒體整合企畫。2016年文化部指導、世新大學《2016廣播電視電影經典人物口述歷史》專書及網站計畫協同主持人。2014年國立故宮博物院《送不出去的國書》專案顧問,該專案獲第49屆休士頓國際影展新媒體網頁類銀牌獎。2014年以「文化與創意產業」獲「教育部103年度甄選全國技專校院通識課程」績優通識「跨領域課程」獎項。2011年以《皮尺》企劃採訪台灣電影攝影師獲文化部高畫質紀錄片補助。著有專書《2016廣播電視電影經典人物口述歷史》(合著)、〈尋找何基明:台灣第一部正宗35釐米台語片導演〉(2017)、〈乾隆潮,潮什麼?:從媒介化觀點試論新媒體體感互動〉(2014)等單篇論文。
石婉舜
1966年生,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專長領域為劇場史學、現代戲劇、台灣戲劇與劇場。2010年以〈搬演「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獲博士學位。著有專書《資深戲劇家:林摶秋》(2003)與〈展演民俗、重塑主體與新劇本土化——1943年《閹雞》舞台演出分析〉(2016)、〈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戲院、歌仔戲與殖民地的觀眾〉(2014)、〈高松豐次郎與台灣現代劇場的揭幕〉(2012)等單篇論文。曾獲K氏台灣青年獎(2005)、行政院優良電影劇本獎(2005)。
三澤真美惠
1999年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2004年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後期課程學分修畢,2006年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術)學位。曾任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二十一世紀COE事業客座研究助理,現為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教授。著作包括《殖民地下的「銀幕」―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年)》(2002)、《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日治時期台灣電影人的交涉與跨境》(2012)。
譯者:何曉芙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文學組碩士,曾為自由譯者,現從事電影相關工作,翻譯仍是最美好的興趣與調劑。
譯者:王念英
中興大學外文系學士,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研究所碩士,甫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所博士班。
譯者:卓庭伍
紐約大學電影研究博士候選人。自由撰稿、翻譯。研究主題包括跨國電影、亞洲電影與類型片發展史。
譯者:張玄竺
英國愛丁堡大學英國文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視翻譯為一輩子的志業及身心靈的形而上搖滾。
⬛ 編者:王君琦
⬛ 翻譯校訂:蔡巧寧
⬛ 翻譯校訂:柯昀青
回探與展望:台語片六十年來的出土、口述與研究出版
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陳斌全
批判性的重構:台語片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主編王君琦
第一部 數載春秋不是夢:台語片的起落與產業變遷
第一章 歌仔戲電影所產生的社會歷史
施如芳
第二章 1960年代台語片與大眾文化的流變
鍾秀梅
第三章 重訪台語片的興衰起落:黑白底片進口與彩色技術轉型
蘇致亨
第二部 國族、類型、美學:混雜身分的在地認同
第四章 類型與國族的糾葛:台語電影二十年(1955~1970)
洪國鈞著、何曉芙譯、蔡巧寧審訂
第五章 台語電影所呈現的台灣意象與認同
陳龍廷
第六章 「串」住最後一笑:晚期台語片的戲曲傳承、喜劇與敢曝的魅力
施茗懷著、王念英譯、柯昀青審訂
第三部 悲情、性別、現代性:台語片戀愛敘事
第七章 「運河殉情記」:台南安平的羅曼史敘事與影像(1926-1956)
蔡玫姿
第八章 錯戀台北青春:從1960年代三部台語片的無能男談起
沈曉茵
第九章 悲情表述與性別空間:1960年代台語片的政治與詩學
張英進著、卓庭伍譯
第四部 不只是地方:台語片的跨國性
第十章 台語電影:國家vs.市場、國家文化vs.跨國文化
蔡明燁著、張玄竺譯
第十一章 台語電影與日本電影的親密與殊異:以電影通俗劇的比較分析為例
王君琦
第十二章 1960年代中後期的台語片混種現象:以台語西部片為例
林奎章
第十三章 從英文羅曼史到台語電影:《地獄新娘》的歌德類型及其文化翻譯
林芳玫、王俐茹
第十四章 辛奇電影中的地理參考與次帝國意識
梁碧茹
第五部 重返歷史現場
第十五章 1960年代台語片演員與影業之關係
陳幸祺
第十六章 尋找何基明:台灣第一部正宗35釐米台語片導演
林慧羚
第十七章 玉峯精神:林摶秋的電影志業與湖山製片廠(附林摶秋訪談錄)
石婉舜
第十八章 日本人拍攝台語片的視角:訪日籍導演小林悟
三澤真美惠
台灣電影史裡的遺珠:台語片的出土、修復和研究
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 陳斌全
1956年是台灣電影史上重要的一年,從前一年《六才子西廂記》問世到這一年《薛平貴與王寶釧》廣受歡迎,台語發音的電影,也就是人們習稱的「台語片」,正式進入廣大群眾的視線之中。此後,一直到台語片產業在1970年代因多種原委而衰落前,台語片的總產量高達一千餘部,其全盛時期的年產量高達百餘部,使台語片無疑地成為台灣電影史上重要的文化現象。
這千餘部台語電影,歷經1990年代起,在時任「國家電影資料館(現國家電影中心)」館長的井迎瑞教授搶救與保存後,目前僅蒐藏有170餘部在國家電影中心的片庫裡。這些影像文化資產如何被活化使用?是否還有更多台語片膠捲遺落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以上這些提問,有賴更多電影與文化工作者、研究者的投入,而國家電影中心亦責無旁貸。
從第一部台語片問世到現在,已經過一甲子,隨著時光推移,曾經參與過台語片全盛時期的觀眾和電影工作者,對這些電影的記憶,因為年歲增長而逐漸淡去;然而,新一輩的電影學者與文史工作者對此時期的研究,卻是逐年展開,有不同程度與面向的挖掘和探討。
電影學者湯普森和鮑威爾(Thompson and Bordwell)在其論著《電影百年發展史》中指出,建構電影史的方法之一,即是仰賴「電影作品」本身做為媒介,提供電影史學家由不同角度切入,建立史觀,詮釋電影本體的歷史。在經歷1990年代台語片的出土與保存後,2014年起,國家電影中心藉由電影數位修復技術的應用,開始持續地修復台語片。1數位修復過後的經典台語片,能呈現更多電影原初的細節,為建構電影史提供更多的佐證素材,也讓新世代的電影愛好者,於今得以重新認識險些佚失的台灣電影文化瑰寶。
《百變千幻不思議:台語片的混血與轉化》的出版,是配合電影數位修復過程,建構整體台灣電影史與台灣電影文化論述下的一項計畫。本書承繼早先台語片史料訪查與整理者的心血,也納入最新的台語片研究方向,期待在更多台語片被數位修復後,提出台語片研究的其他可能性;更進一步地,可以涉入與充實華語電影研究的廣大範圍。
我們相信《百變千幻不思議:台語片的混血與轉化》在深度與廣度上,可以補過去台語片論述之不足,在電影和文化研究領域亦能展現其重要性。感謝本書主編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王君琦教授的參與,以及書中惠賜大作的19位學者專家。本書分別就五個不同面向,進行邀稿、編集與整理,本書的出版,將是台語片研究方興未艾、開拓其他領域的領頭羊。
期待未來有更多電影愛好者投入台語片研究與推廣的領域,讓台語片為不同世代的觀眾所熟悉,也讓這個台灣電影發展史裡重要但險被遺忘的文化現象,能發散出宛如珍珠般溫潤的光澤,回饋到台灣電影史、乃至於華語電影論述的整體光譜。
主編序(節錄)
批判性的重構:台語片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王君琦
在戰後蓬勃發展產量高達千餘部的台語片,無疑是台灣電影史及文化史的重要資產,然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台語片因為受到黨國意識形態影響導致檔案保存闕如,無論是膠捲底片本身的保存或是相關的文字論述都寥寥無幾,這樣的狀況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開始出現轉變。國家電影資料館(現改制為國家電影中心)前館長井迎瑞教授於擔任館長任內開始對台語片進行系統性地蒐集、整理,並舉辦台語影展、進行台語片影人口述歷史。同時,國家電影資料館機關刊物《電影欣賞》於第47期刊出電影學者李泳泉所策劃的「台語片整理」專題,隔年第53期則將之後數期與台語片研究計畫相關的文章及工作紀錄集結為「台語片特輯」(即為專書《台語片時代(一)》)。此後,有關台語片史料的專書相繼出版,包括資深影評人黃仁的《悲情台語片:台語片研究》和電影史學者葉龍彥的《春花夢露:正宗台語電影興衰錄》等。有關台語片歷史資料的回顧和書寫讓我們得以從宏觀的角度走過台語片從興發到沒落的二十年,以更多的歷史細節構築出台語片的樣貌。
台語片的學術論述也是自1990年代開始起步。如果說國家電影資料館的台語片小組為台語片研究打下了基礎,那麼電影學者廖金鳳於2001年所出版的《消逝的影像:台語片的電影再現與文化認同》一書,無疑是銜接檔案史料與電影研究的重要樞紐。該書以電影符號學為方法探討台語片美學發展與文化意識形態,其最大貢獻在於將研究視野從台灣本土脈絡拉升至全球電影並與之接軌,並提供了後續台語片研究可以推進的方向。《消逝的影像》一書所提及好萊塢類型挪用、台語片與台語流行歌曲的互文性等等,皆在國家電影資料館於台語片五十週年時所舉辦的「春花夢露五十年:台語片學術研討會」中有了更深化的討論,該次研討會也提出了以後現代惡搞文化思考台語片美學、探討台語片如何運用東方電影類型如武俠片等嶄新的分析角度。從五十週年的研討會到本書出版之際又經過了十年,這期間隨著台灣文學與文化論述的日漸豐沛,與台語片相關的人物傳記、報導與研究論文也陸續問世,雖稱不上是雨後春筍的盛況,但持續拓邊的能量不墜,新的問題意識不斷被提出,將既有的歷史或研究論述進一步多邊化與複雜化,展現出巴赫汀式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也突破過去意識型態先行所產生的侷限。本書除了收錄國內出版的文章之外,亦有多篇翻譯自英文期刊的研究論文。美國電影學界對於台語片的關注,與對「中國(/華)電影」(Chinese cinemas)一詞的反思有關。電影學者葉月瑜在1998年刊登於《跳接》(Jump Cut)的一篇書評中指出,1990年代末期的美國電影學界仍傾向將中港台兩岸三地電影視為單一國族電影,但台灣和香港的本地學界卻已經開始以「華語電影」(Chinese-language cinemas)來強調歷史所造成無法被均質化的差異。英語電影研究學界對包括台語片在內的所謂「方言電影」(dialectic cinema)的關注,即是在反思國族電影侷限性的批判意識中展開。例如在魯曉鵬與葉月瑜在共同主編的《華語電影:編史、詩學、政治(暫譯)》(Chinese-Language Film: Historiography, Poetics, Politics)一書中,台語片便被認為是示範了以方言鞏固區域主義、並表述與國族論述之間矛盾關係的一種型態。此後,史書美提出「華語語系」(Sinophone)概念,旨在將視野置於中國以外使用各式華語的社群、以及中國境內被迫使用漢語的少數民族,在大中國中心主義以外另闢蹊徑。台語電影在包括北美學界在內的電影研究領域愈來愈受到重視,也與這個視野轉向多少有關。
第十五章 1960年代台語片演員與影業之關係
陳幸祺
臺語片最興盛的時期,電影公司多不勝數,但可持續經營者並不多,多數是所謂的一片公司。論者在此僅討論能夠持續經營者的產業規模,就其預算結構中片酬支出比例,看見演員在產業中的地位。
可以持續經營產製臺語片的電影公司,製片預算通常在三十萬元上下,重要的電影公司中,以永新電影公司製片戴傳李,願意投資三十五萬元拍攝時裝片最高。在1962年到1965年間,由於臺語片票房好,製作費節節上升,從1962年約二十五萬,上升到三十萬,最高可達三十五萬。票房最好的台語片約可分得一百萬至一百二十萬的票房,在票房外尚有賣斷拷貝影片所得收入。
在三十萬元上下預算的正規製作外,尚有較低成本的製作模式,這類製作在1962年到1965年間,也有製作費上漲的情況,約從十二萬漲到十五萬之間,最高到二十萬。這種製作通常從小鄉鎮開始上映,配合隨片登台,有時候會巡迴到較小的城市放映。與規模大的電影公司,通常從臺北、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等五大城市開始排片上映 大異其趣。這個規模的製作頗多一片公司,難以長久經營,他們多半不被製作規模較大臺語片人認同,不被認同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製作規模較小,而是因為他們不了解行情,無法長期經營 ,在《春花夢露─正宗臺語片興衰史》的口述收集中,有一人提及三環影業公司 ,恰好是「每部電影只花十幾萬」的案例,這間公司僅拍七、八部電影,就因無法獲利解散。在他們的製作中,演員的片酬每部只有五百到一千元,至多兩千元。
臺語片並無共通的製片預算模式,臺語片的製片都沒有受過專業教育,他們依靠經驗摸索,找到一套可以運作的方法,持續複製相同模式。因此成本相當的製作,在同一間電影公司,不同製片人,規劃預算的方式都不盡相同,不同的電影公司之間自然也會有所不同。無論是三十萬元上下的製作或十幾萬元的陽春製作,可能都各有好幾種不同的估算方式,不過本文研究對象不在製片結構而在於演員和產業的關聯,由於演員行情固定,且明星的號召力可以明顯表現在票房上,於是片酬支出在相同成本的不同製作中,所佔比例相近,而片酬外尚有演員在外住宿、飲食、交通等各種延伸費用,可見與演員相關的支出,在臺語片的製片預算中佔有重要位置。
結構較為完善的電影公司,至少同時有兩個製片人,每個製片人至少負責兩條線的生產,製片人隸屬於營業部門,但他們實際的工作卻多在製片部門,製片部門負責電影的製作本身,送審、宣傳、發行、上映則由電影公司的營業部門負責,另外僱有專職行政人員。而專職行政人員,有時也會輪替外派到製片現場工作,或是輪替到電影院負責押片與監票等工作,押片與監票,牽涉到票房分帳,對電影公司而言相當重要。押片者負責保管拷貝,在放映時必須看著放映師,結束後也要把拷貝帶回,一方面為拷貝進行例行的保養、清理,另外一方面防杜地方戲院跑片 ,監票人員有兩位,一位看守票口的撕票人員,是否確實撕下每張票的票根,另外一位在電影院內點數觀眾數量,查看觀眾數量是否與票數相同,避免電影院經營業者「吃票」,隱匿票根,將票房以多報少,造成電影公司損失,監票只能減少損失,無論如何監控,電影院都會「吃」掉部分票房 ,若有隨片登台的計劃,押片與監票人員也要負責相關工作。
一部製作費三十萬元的台語片,不計臨時演員,光是主要演員,即佔據了支出項目達三分之一左右。在此列出演員片酬預算細目,以一個雙生雙旦的文藝片類型推估,主要演員大約如何分割這九萬元的片酬。
第九章 悲情表述與性別空間:1960年代台語片的政治與詩學
張英進
近年不乏關於於台灣新電影的論述(Berry/Lu 2005; Davis/Chen 2007; Yeh/Davis 2005),尤其是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1989),被視為大膽使用「台語」(台灣方言) 的電影代表作,其語言選擇出其不意的挑戰了威權政體,表述了台灣本土文化中長期被壓抑的情感──悲情。(P. Liao 1993; Yip 1997; Reynaude 2002)的確,一直到1988年 ,國民黨政策對台語持強硬態度,當年陳坤厚(b. 1939)欲以台語配音的《桂花巷》(1987)參加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競賽,卻被台灣新聞局以台語非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國語」為理由拒絕。相較之下,一年後的侯孝賢則幸運許多,他得以由東京的電影沖印公司直接將悲情城市的拷貝送至威尼斯影展參展,同時將另一份拷貝送回台北審查。新聞局的破例有了讓人驚喜的結果:侯孝賢的作品得到了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也是首部得到此榮耀的華語電影。接著在1989年,侯孝賢在保守勢力的質疑聲浪中榮獲金馬獎最佳導演,因為片中使用大量的台語,不符合當時台語對白不得超過全片的三分之一(Huang Ren,1994a: 23-24)的規定。
悲情城市的成功讓台灣電影得以重掌台語的使用權,也因此,接下來兩個世代的新導演得以在台灣的「鄉土」與「本土」經驗上培植創作。據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1998:105)觀察,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電影「導演通常會使用非專業演員,並以對話中的方言來反映出角色特定的生長地域和階級。」對於如凱爾納這樣的評論者來說,「方言」使用的政治性為台灣新電影顯著的特點。然而嚴格來說,台灣新電影中的語言特徵及其強調本土文化的復興、城市的迷人與疏離、在苦難中仍保有純真的小人物、一貫的悲情基調,這些在台灣電影史中皆非創新。早在五〇年代中期至七〇年代初盛行的「台語片」已經觸及這些主題,並呈現出冷戰時期台灣在劇烈的社會變遷與時代動盪中獨特的悲情基調。台語片在台灣存在多年,證明國民政府沒有徹底執行電影中限制台語的政策,且直到七〇年代,在嚴峻的政治氛圍下,台語片以其文化形式成功的在嚴峻的政治氛圍中存活了下來。
不意外的,如悲情城市,台語片也與「悲情」相連,甚至林福地導演也曾拍攝過故事不同,但與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同名的台語電影。1994年黃仁所著《悲情台語片》一書,特意強調了台語片的「悲情」特性──在1960年代受到歡迎的台語片,到了1970年代中期之後熱潮遽減,甚至被完全遺忘。直到2001年,廖金鳳坦言在他高中之前沒聽過「二二八事件」──1947年國民黨對台灣反抗勢力進行的大規模軍事鎮壓(M. Berry 2008: 179-249; Lin 2007)── 在1989年之前也不知道台語片的存在。諸如此類,「悲情」,是集體記憶受壓的迫下的產物。
當然,自1987年七月國民黨解除戒嚴之後,情況已經不同。在1991年,國家電影資料館開始在《電影欣賞》期刊中刊載一系列的台語片目錄與過去台語片導演的訪談,以先鋒之姿促成了一本關於台語片的著作誕生(國家電影資料館,1994)。從此之後,在台灣,雖然電影研究尚未晉升為一門備受尊崇的學科,亦已逐漸發展為正規專業。即使台灣新電影依然是英文的電影研究著作中最受矚目的主題,許多學者已經(Lu 1998: 69-124; Ye 1999; Liao Jinfeng 2001; Huang/Wang 2004: 1: 174-249, 339-405)出版了研究台語片不同面向的中文著作。
本文旨在重探台語片──在台灣電影研究中被視為(Guo-Juin Hong 2010:6)「看不見的年代」中(1980年代以前),一項幾乎被遺忘的早期傳統。自1950年代後期,台語片為一種非官方的、或與其「平行」(Yeh/Davis 2005: 15-52)、「競爭」的電影,以社區為基礎,有意識的發展出其跨地方的娛樂形式,產量很快的超越了所謂的「國語電影」(Jiao 1993),還有國民黨片廠拍攝的「政治片」(Huang Ren,1994)。從1955年至1959年,台語片的產量共達178部,遠多於國語片的41部。至1969年,台語片製作共有1052部,國語片則只有373部。在最高峰的時候,台語片的年產量曾達120部(1962)、114部(1965)、112部(1968)。(見表1)
與其提供、縱觀台語片歷史上的興衰,我所關切的,首要是台語片中的悲情表述,與其作為一種情感結構、敘事手法,還有觀察1960年代地緣政治的視野。首先,作為一種情感結構,悲情取自也同時供養了當年台灣從農業社會過渡至現代、都會型社會結構時最為氾濫的情感(Huang Jianye 2000: 359-600)。的確,據洪國鈞(2011: 54)觀察,「台灣方言的通俗劇將現代性電影化,成為空間與時間的問題。」我則想在此也加入「性別」的問題(如:被閹割的男人、女性欲望),由於這些在現代化之下無可避免的衝突,像是銀幕上常見的城鄉移民問題,造成了預料之外的社會、文化效應,也使得悲情成為了當時情感表現的主流。隨著時間流逝,台語片中訴說的「悲情」也逐漸改變,1960年代初期多為一連串「充滿哀怨命運、破碎家庭、分離情侶、流浪孤兒和困苦生活的意象」,而在1960年代晚期則逐漸展現出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所揭示,狂歡(carnivalesque)氣氛下的生機勃勃、眾聲喧嘩(Liao Jinfeng 2001: 162)。然而,根據我對兩部1969年的影片分析,至少在都會通俗劇的範疇,依然可以見到悲情作為情感結構的延續。
第二,作為敘事手法(策略),「悲情」可以追溯至許多特定的地方、跨地的台灣文化傳統,如歌仔戲、歌謠、流行樂曲,皆以台語演出。最早的兩部台語片──《六才子西廂記》(1955)、《薛平貴與王寶釧》(1956)──都是改編自歌仔戲 ,可見其對於台語片的影響力。歌仔戲源於福建省南部的錦歌,從1910年代(Liu 1999)開始在日據台灣發展茁壯,至1950年代已十分流行,單於1958年,歌仔戲班的數目從160劇增至235,佔了當年台灣所有登記的演出劇團的百分之47.1(Chen 1988: 94-97)。全台有367個戲院一度專演歌仔戲,在鄉間野台戲的演出更是多不勝數( Lu 1998: 60)。歌仔戲累積了家喻戶曉的敘事、經驗豐富的演員、現成的服裝道具,還有當地忠實的觀眾,宛如台語片的寶庫,而其「苦情」的情感特色也迅速的被台語片吸收。台語片中另一個流行元素是台灣歌謠,是在日據時期發展出的一種敘事形式,故事多圍繞著怨嘆命運多舛,懷念故鄉、思念情人的角色展開(Liao Jinfeng 2001: 92-93)。台語片的拍攝人員繼承了民俗歌謠中一貫的悲哀敘事而受到喜愛,同時也將悲嘆命運的流行歌曲融入通俗劇之中,而片中的苦情歌曲更帶來「另一個與影像平行的敘事」(Guo-Juin Hong 2011: 58)。這證明了台語片充分的活用了豐富的資源,從本土文化媒體、習俗中獲取了題材、靈感。
第三,以地緣政治的視角而言,台語片以「悲情」為其主要特色,是建立在台灣特地的空間、時間、語言之上。歷史上,台語的廣泛使用對國民黨推行國語為官方語言的政策是一大威脅。早在1950年,國民黨便嘗試禁歌仔戲,但是由於它的廣泛流行,只好將政策改為管制與改革其類型(Lu 1998: 61)。由台語片在1950年中期的竄起來看,這些方案皆效果不彰。這些電影中,跟歌仔戲一樣,藉著台語的使用,自然流瀉出悲情,觀眾亦對中國古代帝王使用台語而非國語感到自豪。在日本殖民時代與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人大多無法掌握政治權力亦無法象徵性的代表族群發聲,而台語片中悲情氛圍的重要性,與其作為一種抒發被壓抑情感的管道,也表達本土認同的另一條路──至少是與國語片中英雄式、愛國式的敘事截然不同的另一條路。
第十一章 台語電影與日本電影的親密與殊異:以電影通俗劇的比較分析為例
王君琦
在討論從1955年開始到六、七〇年代,以台灣所拍攝、使用閩南方言為主的台語電影之形塑與發展時,無論是當時的影評或是當代的論點,皆普遍認為台語電影的發展受到日本電影極大影響,反映出過去日本殖民的遺緒。六〇年代知名影劇記者姚鳳磐就認為,台語電影走向衰亡的因素之一就是毫無節制地模仿日本電影、缺乏獨創性導致僵化。當代文化評論人Ko Tsì-jîn也指出,台語片因為主要工作人員受日本教育的背景、大量運用日本題材、邀請日本影人參與等因素,因此有相當鮮明的「日本化風情」(Ko 2014)。當代台語電影史學家亦多同意六〇年代評論者的觀點,台語電影研究先驅黃仁在《日本電影在台灣》一書中指出,台語片仿拍日片乃因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讓「台灣文化早已溶入日本文化」,因此日片故事可以很輕易地搬到台灣被本土化(黃仁 2008: 243)。台灣電影史學者葉龍彥也提到,台灣與日本在地理、語文生活的相近,使得日本電影成為台灣電影學界、尤其是台語電影主要的學習對象(葉龍彥 2006: 159)。上述觀點所共同暗示地即是,台語電影對日本電影的模仿乃是殖民影響下的後殖民現象。
儘管台語電影與日本電影確實有著可辨識的相似性,而此一相似性也的確與殖民歷史高度相關,但上述論點都顯得過於簡化,欠缺從被殖民者的角度與脈絡提出詮釋。對西方歐美帝國時期殖民主義提出批判的後殖民研究,除了關注殖民歷史與狀態如何影響前殖民國與前殖民地之間的互動外,也強調對抗殖民者知識生產與傳播霸權的政治意義,以開拓、尋求另類表達的空間與可能性,甚至做為抵抗(Ashcroft, Griffiths & Tiffin 1995: 85-86)。本文便是從這個角度重新思考台語電影所蘊含的殖民遺緒,不將台語電影視為前殖民地人民對日本電影拙劣的複製品,以跳脫表面上的文化相似性被等於殖民情結的觀點,並試圖打開研究台語電影發展與變遷的問題意識。日本電影對台語電影的影響不可諱言,但這個影響絕非壓倒性的,也不必然就具有定義台語電影的關鍵性。本文除了重新思考對台語電影與日本電影之間親近性的原因與意義之外,也將透過對台語電影通俗劇所進行的系統性分析,進一步了解台語電影通俗劇如何居中媒介了六〇年代戰後台灣的現代性經驗。
台灣的電影工業從一開始就在政治、文化、經濟等層面與日本電影有著密切的關係。當電影這個新型態的傳播與娛樂型式在日治時期被帶入殖民地台灣時,即引發了不少關注, 並在1925年左右成為島上最受歡迎的娛樂型式之一(三澤真美惠 2001: 290)。 在殖民地政策下,電影是以做為教育與教化的手段被引進,島內最早的電影放映活動是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委託高松豐次郎(又譯,高松豐治郎)而展開的。高松不只建立了台灣初期的電影發行系統,更在之後的幾年迅速擴展旗下的戲院映演管道 (葉龍彥 1998: 67-72)。在電影製作方面,日本於二〇年代初開始在台拍攝劇情片及紀錄片, 台灣人 (時稱本島人) 也因此得以透過加入日本人的製作團隊而涉足電影拍攝,但相關研究指出,當時台灣人能獲得的電影知識和資源極為有限 (三澤真美惠 2001: 367;Chiu 2011: 83),即使是台灣人出資的拍攝計畫也不例外。
也是在日治時期,偏菁英階級的台灣人開始前往日本學習電影相關的專業知識,有的是進入專門學校,有的則是進入如松竹或東寶等片廠工作。如前面的例子所透露的,戰後台語電影被認為承繼了日本電影的其中一個原因,即是台語電影工作人員與日本電影工業及日本電影教育的淵源。開啟台語片拍攝濫觴的兩位導演邵羅輝與何基明,正分別代表這兩種赴日取經的途徑。第一部台語片是由邵羅輝所執導的十六釐米歌仔戲電影《六才子西廂記》(邵羅輝導,1955),儘管這部片票房失利,但卻證明了拍電影的可行性。隔年,何基明所執導的歌仔戲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1955)解決了《六才子西廂記》裡所出現的媒材轉換的問題,獲得票房佳績,也進一步鼓勵了更多人投入台語片的製作與拍攝。邵羅輝曾在東京帝國影劇學校就讀,並在日後加入松竹片廠 (葉龍彥2000: 133-141);何基明從東京攝影學校畢業後,加入十字屋文化電影部(李展平 2000: 101),亦曾擔任日本導演的攝影助理。除此之外,台語電影亦相當借重日本電影工作者的專業長才協助發展,岩澤庸德、宮西四郎、千葉樹泰、湯淺浪男、小林悟等皆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台語電影的拍攝,不少台語電影更是直接翻拍日本電影,諸如《金色夜叉》、《湯島白梅記》、《請問芳名》等等。六〇年代的評論者咸認為,台語電影所使用的語言會吸引到曾被殖民而偏好日本電影的「本省觀眾」,這個因素驅使台語電影在主題與形式風格上追求與日本電影的高度相似性 (余聞 1965: 6)。這類看法又因為台語電影票房的波動總是相應於日本電影在台放映數量的多寡 (即日本電影放映數量多,台語電影票房差),而被更進一步強化。
儘管日本電影對台語電影的影響確實存在,但本文將論證,過度強調殖民遺緒,會忽略當時也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美國帝國文化主義、冷戰結構、國民政府國族打造計畫等其他因素。從國際電影發展的觀點來看,影響台語電影的除了日本電影之外,亦包括好萊塢全球勢力,以及鄰近的香港電影、尤其是廈語片。內戰遷台後,國民政府為了攏絡華僑,對包括了各種不同方言的香港電影採取了許多優惠措施,這也解釋了為何國民政府不允許拍攝方言電影,口音與台語相近的香港廈語片卻可以進口台灣 (Taylor 2011: 95)。本文將指出,台語電影應該被視為傅科在《知識考古學》所提到「做為網絡中一個節點的物件」(Foucault 1972: 23),處於一個共構的參照系統之內,其意義是連結到與其有關的更大、更全面性的知識和概念網絡,而對台語電影而言,日本電影正是參照系統內的一部份知識和概念,但不是全部,也不具有絕對主導性的影響。不具有文化正當性的台語電影因為同時必須與國族電影以及國際電影競爭,因此其所採取的策略便是吸納來自四面八方的電影慣例以設法保持自身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其所吸納挪用的對象包括了、但不限於日本電影,此一生存法則類似於巴西新電影(Cinema Novo)的食人主義美學。巴西新電影的食人主義美學有著巴赫汀概念下的文化食人主義的精神,意指吞食來自內外包括地方的、國族的、殖民的、全球的各種影響,以達到一種不純粹但獨樹一格的表達形式,巴西新電影正是以食人主義做為文化國族主義的形式,透過彰顯已成為自身一部份的帝國痕跡,批判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並讓反抗成為可能 (King 2000: 23)。雖然台語電影並沒有像巴西新電影一樣策略性地轉化歐洲殖民論述以建立帶有後殖民批判意識的主體認同,但台語電影揉雜本地文化特殊性和各式外來元素的事實卻是不可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