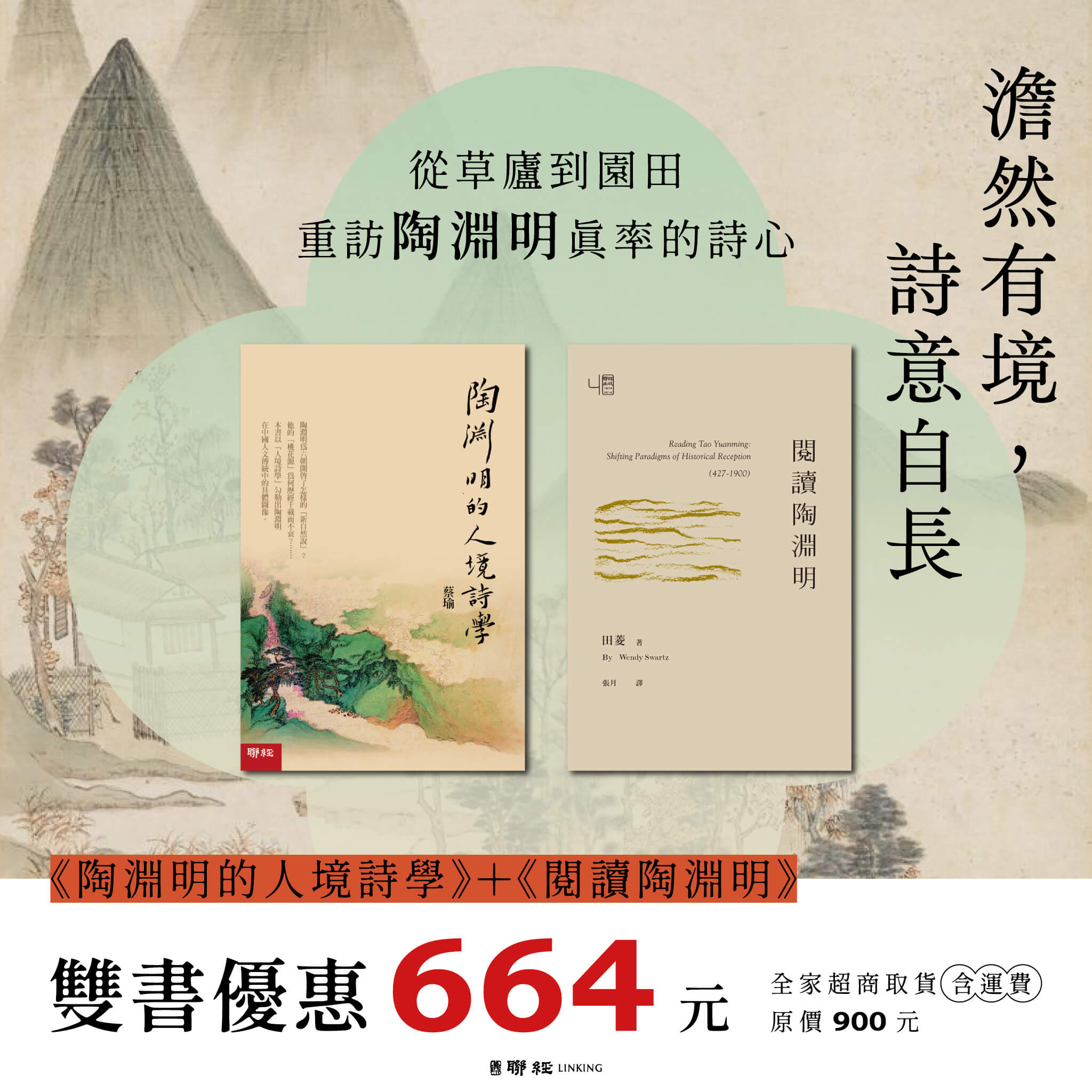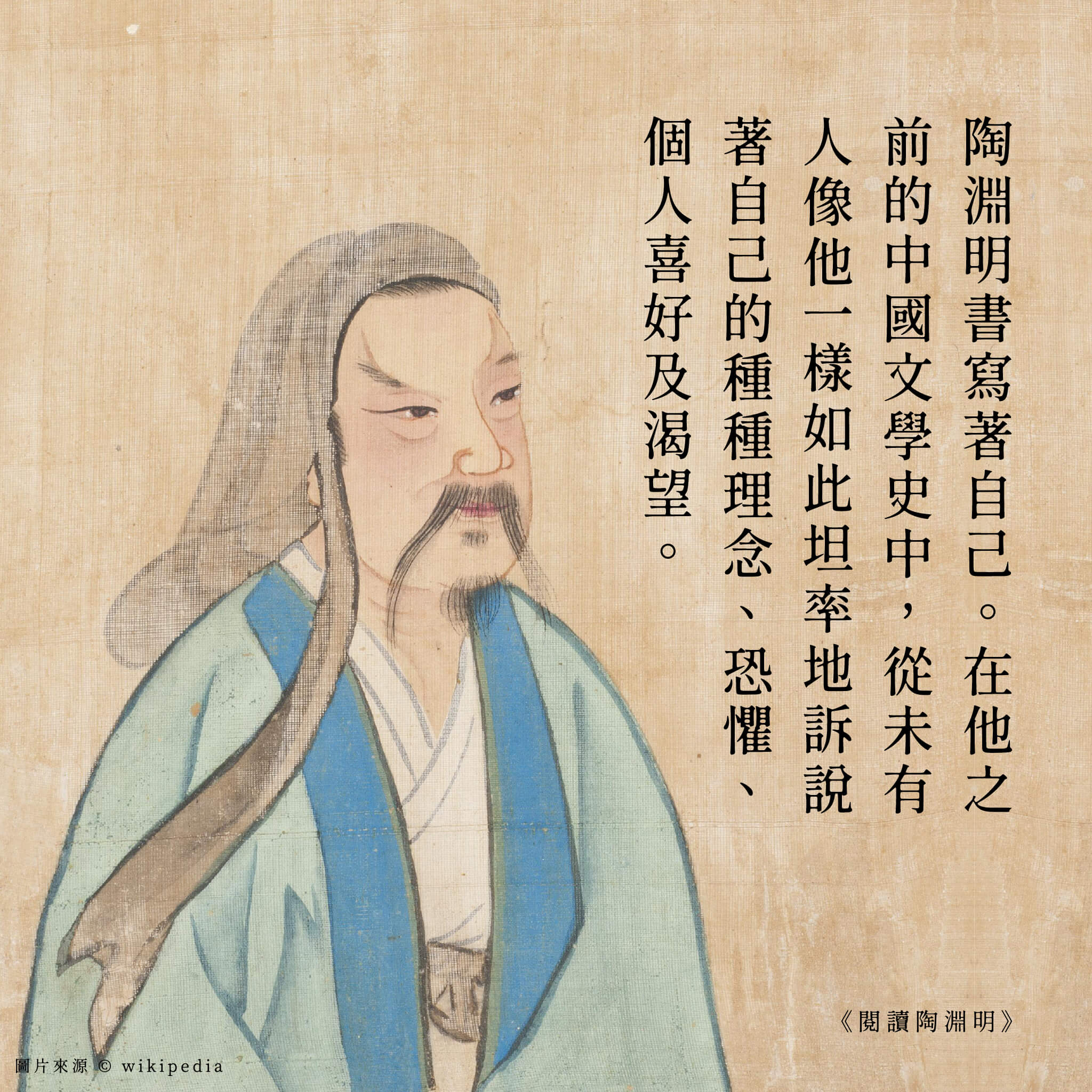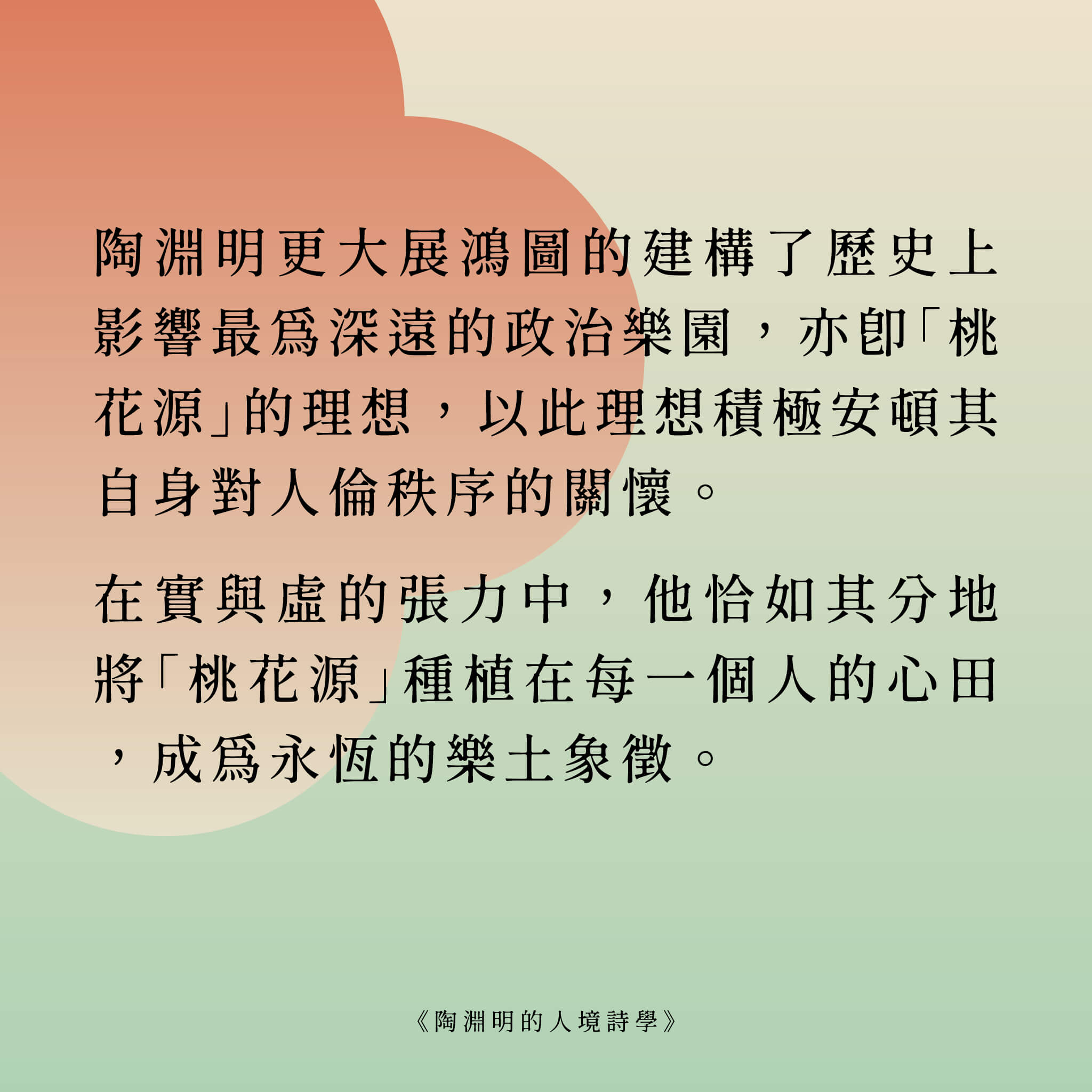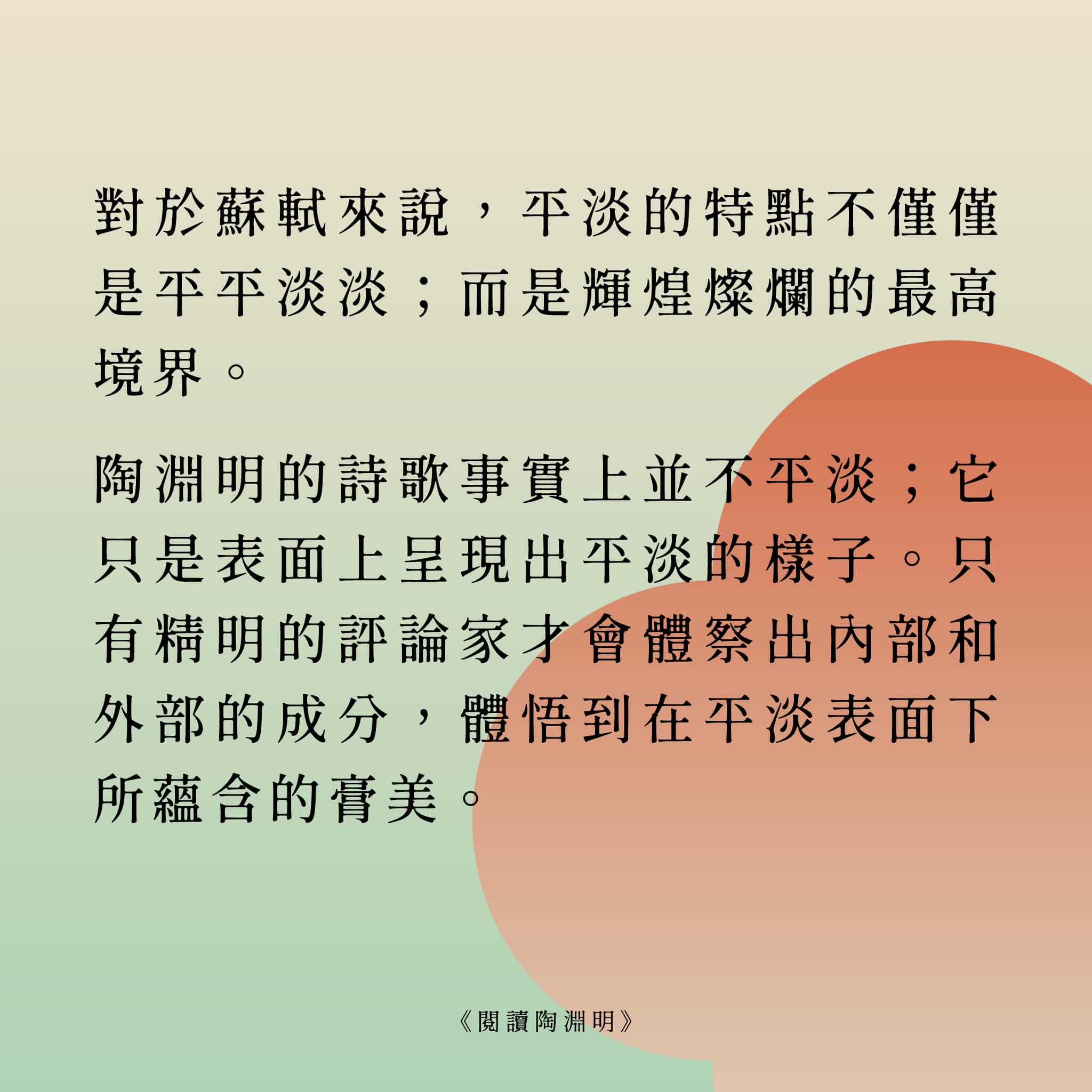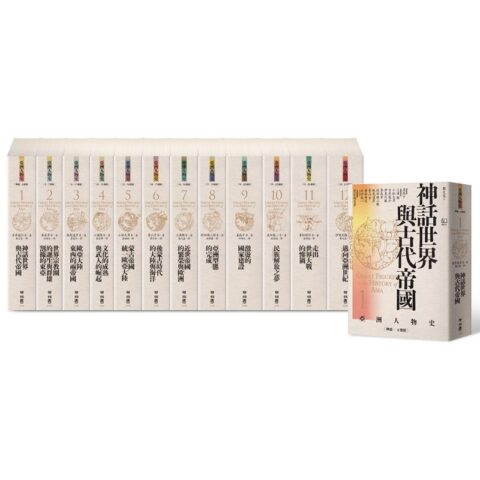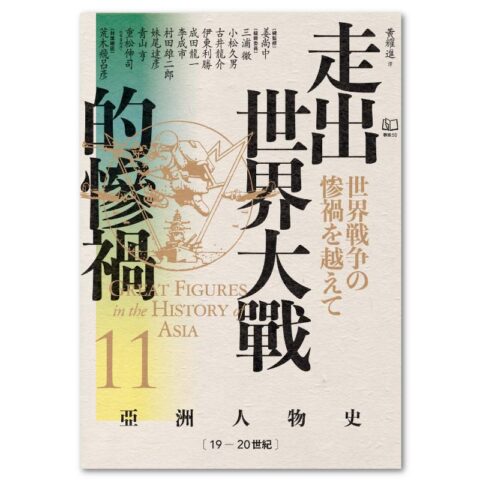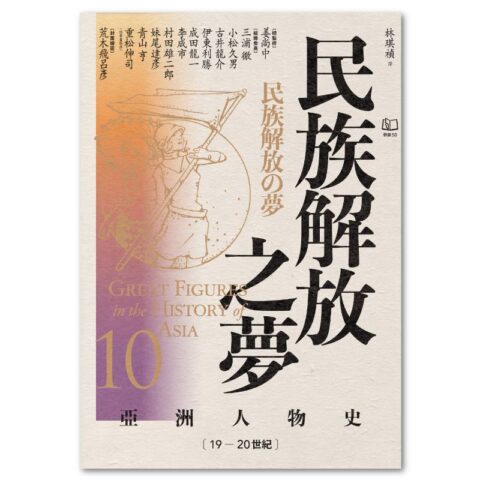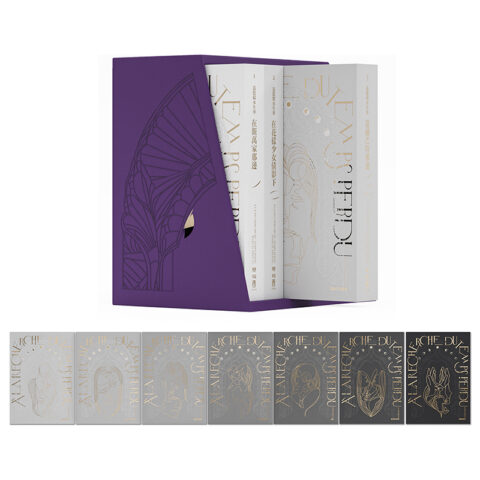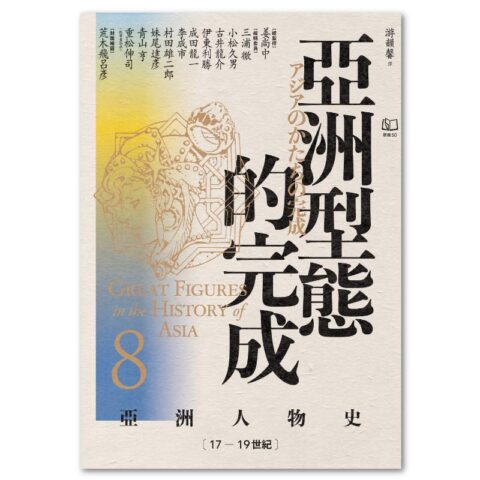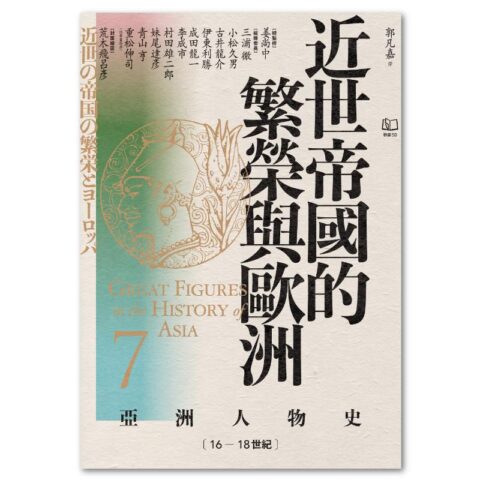【優惠套組】《陶淵明的人境詩學》+《閱讀陶淵明》
澹然有境,詩意自長:從草廬到園田,重訪陶淵明真率的詩心
《陶淵明的人境詩學》+《閱讀陶淵明》雙書優惠 664 元(全家超商取貨「含」運費,原價 900 元)
※ 恕無法使用折價券
尚有庫存
陶淵明之名一出現在中國典籍中,即具有鮮明的個性,他隱居於廬山腳下的草廬,成為一種令人無法忽視的文化象徵。他被認為與俗寡諧,具有抗議精神,是一位異議分子;也被認為與當時最大的宗教勢力保持友善,卻不為所動,是一位另類士人。但在他身後數個世紀裡,陶淵明作為隱士,而不是因其詩名,廣為人知,儘管在李唐時代逐漸引人注目,但是只有到宋代他的作品才開始被奉為詩歌經典。
⠀
蔡瑜的《陶淵明的人境詩學》用「人境詩學」勾勒出陶淵明在中國人文傳統中的具體圖像。試圖以中國人文傳統為座標,從當代共具的關懷為切入點,依「人境的自然」、「園田」、「隱逸」、「生死」、「飲酒」、「懷古」等主題切入,揭示出人必須在具有倫理關係的共同體中安身立命。最後則以「對話」回應首章,說明陶淵明為何是一位最善於以藝術形式呈現思想深度的哲學家詩人,並由此開展出與後世之人永恆的對話關係。
⠀
田菱的《閱讀陶淵明》則著眼於陶淵明「身後聲名」的「建構」和在他作品的接受過程中所涉及的「機制」問題,全面探討了從甫問世直到晚清,其作品是怎樣被解讀和評價的。研究材料由六朝晚期直至民初史料,審慎地將他放回歷史脈絡中探討,考察當初是在何種社會與學術條件下派生出這些言論。這個過程通過數世紀的交流和對話來實現,而居於對話核心的是中國士大夫文化的三個要項:隱逸、個性和詩歌。在這一對話中,對陶淵明生活和作品的眾多解讀,源於變化的審美和道德需求,以及新的詮釋實踐和批評語彙的發展。
⠀
蘇東坡曾喟然長嘆:「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 如其為人,實有感焉!」陶淵明不僅僅被看作為一位僵化定型的「傳說人物」,他更像是一面珍貴的鏡子,反映出歷代讀者自身的焦慮與理想。
《陶淵明的人境詩學》
◆ 作者:蔡瑜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主治魏晉南北朝及唐宋時代的詩歌與理論,並究心於女性文學及性別研究。著有《高棅詩學研究》、《宋代唐詩學》、《唐詩學探索》、《中國抒情詩的世界》等書。作者長期致力於開拓中國詩學的深度與廣度,近年隨著己身「性好山水」的發現之旅,乃將詩學研究的視野擴展於「身體」與「自然」的雙向詮釋,「詩」與「思」的聯結交響,本書即具現了此一關懷。
黑白印刷 | 精裝 | 384 頁 | 25 開,21 × 14.8 cm
《閱讀陶淵明》
◆ 作者:田菱(Wendy Swartz)
羅格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主要側重六朝時期的詩歌和詩學。在美國主流學術期刊發表過關於陶淵明和謝靈運研究的相關文章,如〈哈佛亞洲研究〉和〈中國文學:隨筆、論文和書評〉》。亦主編《六朝原始資料選編》,於2014年1月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閱讀陶淵明:歷史接受中的範式轉變(427-1900)》(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出版,2008)曾被美國圖書館聯合會《精選》雜誌評為該年度優異學術著作獎。
◆ 作者:譯者:張月
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博士,現執教於美國伍斯特大學(College of Wooster)。教學和研究的主要領域為中國語言、文學和文化。
黑白印刷 | 平裝 | 392 頁 | 25開(高21×14.8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