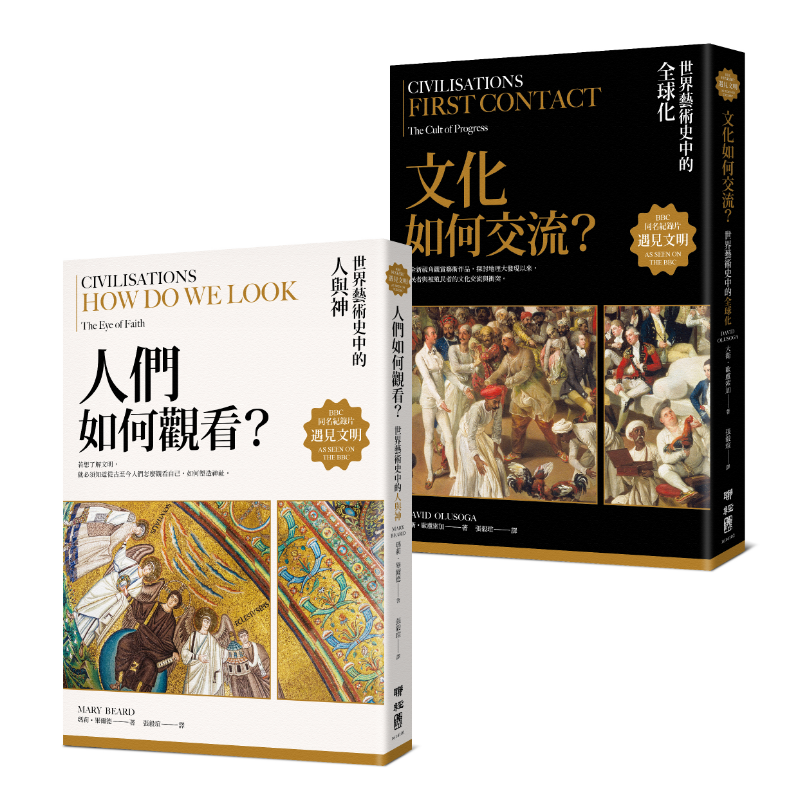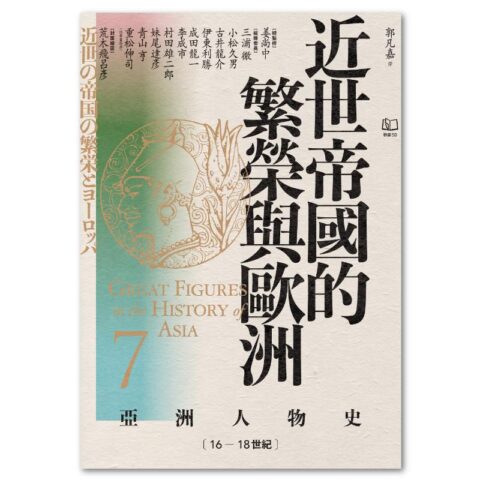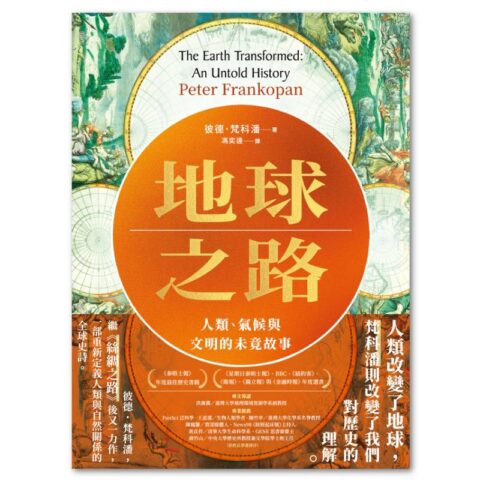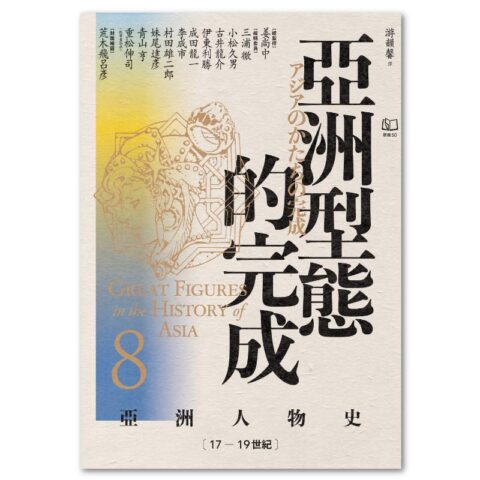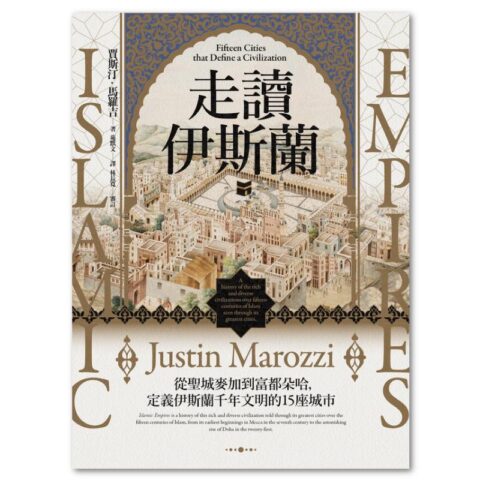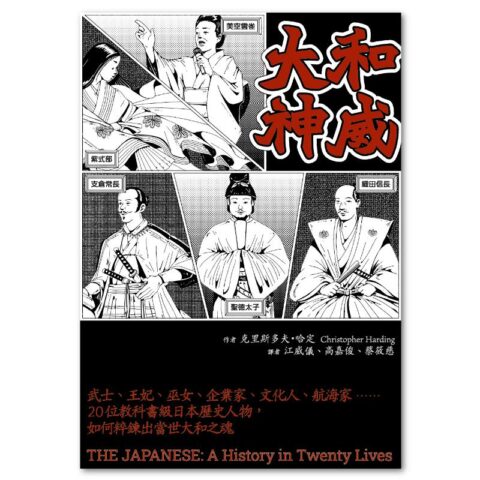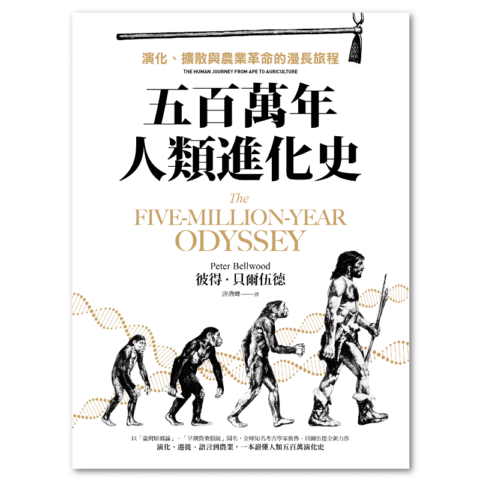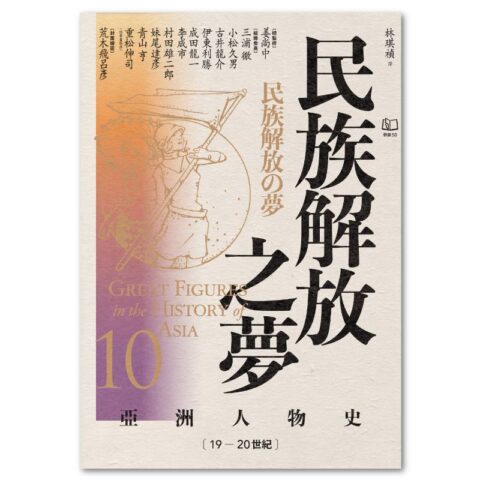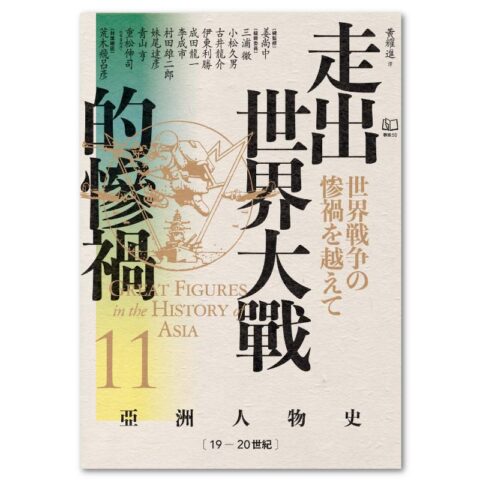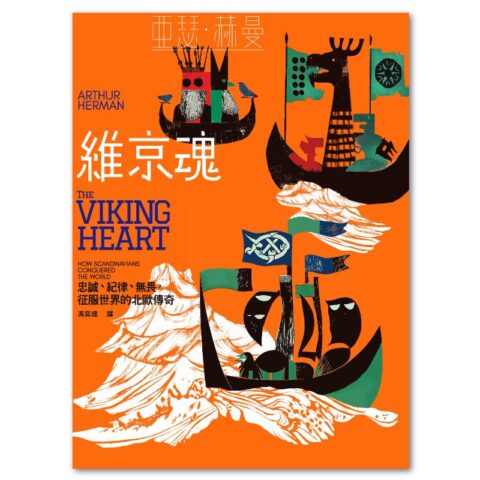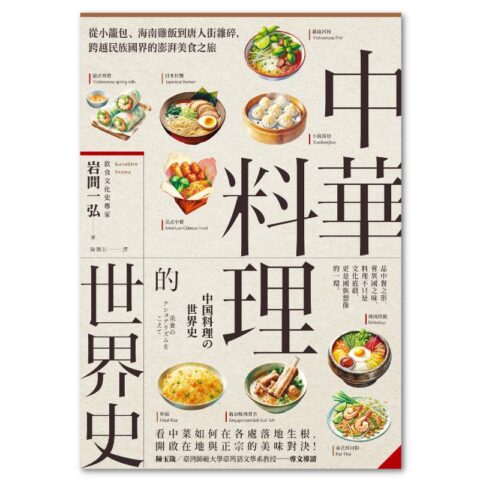【遇見文明典藏套書】人們如何觀看?+文化如何交流?
原書名:Civilisations: How do We Look / The Eye of Faith、Civilisations: First Contact / The Cult of Progress
出版日期:2022-03-31
作者:瑪莉.畢爾德、大衛.歐盧索加
譯者:張毅瑄
印刷:全彩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44
開數:25開,寬14.8×長21×高3.4cm
EAN:4711132389357
系列:遇見文明
已售完
BBC同名紀錄片《遇見文明》集結成書。
這部2018年由BBC製作的藝術歷史系列電視紀錄片,由瑪麗.畢爾德、西蒙.夏瑪、大衛.歐盧索加共同主持,涵蓋六個大陸,三十一個國家,超過五百件藝術品。
若想了解文明,就必須知道從古至今人們怎麼觀看自己,如何塑造神祉。
用全新視角觀賞藝術作品,探討地理大發現以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文化交流與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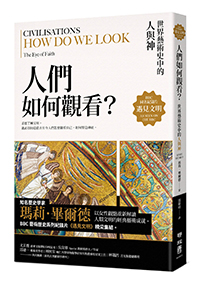
▍《人們如何觀看?:世界藝術史中的人與神》
「文明」這個概念在歷史上始終備受爭論,甚至為此引發戰爭。在這些爭議的核心存在著一個大問題,那就是人們──從史前到今天──怎樣描繪自己與他者(包括人與神)。著名歷史學家瑪莉.畢爾德在此探索創作者怎樣塑造藝術,而藝術又是怎樣塑造創作者。我們怎樣觀看這些圖像?為什麼它們有時如此充滿爭議?
第一章〈我們如何觀看〉
歷史上某些最早的藝術作品如何呈現人體?而過去某種呈現人體的特殊方式,又是如何在今天依舊影響西方人看待自己文化與其他文化的態度?除了製作圖像的藝術家,那些使用這些圖像、觀看並詮釋這些圖像的人們,他們是如何觀看?
古老奧梅克的石人頭、古希臘的人體雕像、埃及木乃伊棺木畫像、秦始皇的兵馬俑大軍、巨型法老王坐像、禁忌的裸體阿芙洛蒂雕像、《美景宮的阿波羅》、《垂死的高盧人》銅像……
第二章〈信仰之眼〉
宗教一直是藝術創作的題材來源,但要讓天國在人間現形絕非易事。所有的宗教都必須處理偶像崇拜和破除偶像的問題,既製作藝術又摧毀藝術,透過〈信仰之眼〉,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切?
阿旃陀洞窟壁畫、聖維塔教堂馬賽克、亭托雷多的《耶穌被釘十字架》、塞維亞的流淚聖母像、藍色清真寺中的書法、「破除偶像」後的伊利主教座堂、帕德嫩神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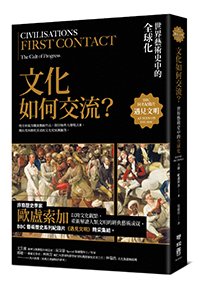
▍《文化如何交流?:世界藝術史中的全球化》
過去人們曾普遍相信文明是單一的,是從唯一一個來源傳播到世界某些地方的現象,這個信念如今也一樣問題百出。為了替歐洲發展海外帝國時進行的殖民冒險背書,各國都聲稱自己投身於一場偉大的「文明教化」事業,以此合理化自己對其他民族的統治。或許「文明」這個概念裡面唯一可肯定的,就是「文明」的對立面「野蠻」是有害的。
藝術傑作──無論是掠奪所得或是創作成果──都是我們理解歷史的關鍵。
第一章〈最早的接觸〉,帶我們探索大航海時代,當文明初次相遇,當時的藝術會受到什麼影響。毫無疑問這是一段征服與摧毀的時代,也是一段彼此好奇、全球貿易與思想交流的時代。
西非的「貝南青銅」、日本畫家狩野內膳的「南蠻屏風」、維梅爾的《窗邊讀信少女》、佐法尼的《鬥雞賽》、阿茲特克畫家的《佛羅倫丁手抄本》……
第二章〈進步觀信仰〉,讓我們看到工業革命改變了世界,它影響了全球每一片土地、每一個文明。從英國密德蘭地區的棉織廠開始,我們看到拿破崙征服埃及,也看到美洲原住民與紐西蘭毛利人的悲慘境遇。
德拉克洛瓦的《阿爾及利亞女人》、透納的「黑鄉」伍斯特郡風景畫、描繪美洲大陸的敘事畫《帝國之路》、凱特林的「印地安畫廊」、攝影發明後的巴黎街景、世博會的「活人展品」、畢卡索的《亞維儂的女人》……
大衛.歐盧索加帶領讀者走過千山萬水,將那些連接各個文化的共享的歷史串連起來。
本書特色
BBC同名紀錄片《遇見文明》是2018年由BBC製作的藝術歷史系列電視紀錄片,由瑪麗.畢爾德、西蒙.夏瑪、大衛.歐盧索加共同主持,涵蓋六個大陸,三十一個國家,超過五百件藝術品。
專家力薦
尤芷薇 前華文媒體駐印度記者
吳宜蓉 Special教師獎得主/作家
邱建一 藝術史學者
林秋芳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教授兼校史室主任
林瑞昌 吉光旅遊總經理
各界讚譽
「讀者會很高興由這位聰明、睿智的畢爾德帶領……她的每一本作品都精采有趣而發人深省。」——《舊金山紀事報》
「一本內容紮實的小書……畢爾德將焦點從西方歐洲往外推展,詳實地調查探討從埃及到中國、猶太教到基督教、古代到現代的藝術,強調觀者的角色勝過創作者的動機……推薦給所有想用全新觀點探討宗教、藝術與歷史的讀者。」——《Booklist》書評
「這位聲名卓著的作者瑪莉.畢爾德再次出手,這一次是關於藝術,以及人們的反應,跨越千百年的時間與千萬里的空間。」——《科克斯評論》
「歐盧索加是位機智又富創意的敘事者,對歷史充滿熱情,具有獨特的優雅魅力。」——《衛報》
「字句流暢易懂又簡單清楚……是一本可讀性很高又引人入勝的書。」——《星期日泰晤士報》
「沒有任何一本書,可以把這一段長期被忽略或否定的英國歷史,解釋得如此清楚、全面,讓讀者融會貫通。歐盧索加絕對是一位優秀的導覽員。」——亞當.霍奇希爾德(Adam Hochschild),著有《利奧波德二世的鬼魂》
作者:瑪莉.畢爾德
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古典學教授,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LS)古典部編輯,擁有世界級的學術成就。她的著作包括獲得沃爾夫森獎(Wolfson Prize)的暢銷書《龐貝城》(Pompeii)、《帕德嫩神廟》(The Parthenon)、《面對古典學》(Confronting the Classics)、《SPQR》和《女力告白》(聯經出版)。
她活躍於媒體,參與多部享譽國際的BBC紀錄片,包括《相約古羅馬》(Meet the Romans)、《卡利古拉》(Caligula)、《瑪莉.畢爾德的終極羅馬》(Mary Beard’s Ultimate Rome)和2018年的《遇見文明》。
作者:大衛.歐盧索加
奈及利亞裔英國歷史學家、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BAFTA)獲獎廣播主持人、電影製作人。他的三本著作包括《德皇大屠殺》(The Kaiser’s Holocaust)、《世界戰爭》(The World’s War)以及最近期的《黑人與英國:一段被遺忘的歷史》(Black and British: A Forgotten History),後者入選為水石書店2016年度歷史書籍(Waterstone’s History Book of the Year),入圍2017年奧威爾獎(Orwell Prize)初選名單,並贏得赫賽爾.蒂爾特曼獎(PEN Hessell-Tiltman)與朗門歷史董事會獎(Longman History Today Trustees award)。
他製作的電視影集包括《一棟房屋的今昔》、《黑人與英國: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世界戰爭》、《被遺忘的英國奴隸主》和《遇見文明》。
譯者:張毅瑄
臺灣大學化學系、歷史研究所畢業,譯有《哺乳動物們》、《地球毀滅記》、《古典洋裝全圖解》、《遇見文明.人們如何觀看?》、《遇見文明.文化如何交流?》等書,最喜歡的一句話是「若以求知的觀點看待一切,所有的事都是好事」。
▍《人們如何觀看?:世界藝術史中的人與神》
我們如何觀看
頭與身體
會唱歌的雕像
希臘人像
觀看「失落」:從希臘到羅馬
中國皇帝與人像的力量
把法老變大
希臘藝術革命
大腿上的污跡
革命遺澤
奧梅克摔角選手
信仰之眼
吳哥窟的日出
阿旃陀「洞窟藝術」:誰在看?
耶穌是誰?耶穌是什麼?
虛榮這個問題
活雕像?
伊斯蘭教的藝術性
聖經故事
戰爭的傷痕
印度形象,伊斯蘭風格
文明中的信仰
▍《文化如何交流?:世界藝術史中的全球化》
最早的接觸
維多利亞時代:懷疑
航海者的國度
入侵者與掠奪
為征服辯護
對文化的關注
擁抱新事物
帝國作風
進步觀信仰
法老的誘惑
中土革命
都市與貧民窟
美洲大自然
帝國之路
竊取身分
傳家畫像
相機的發展
藝術對進步的回應
逃脫到異國
轉變
歐洲墜落
後記/《文化如何交流?:世界藝術史中的全球化》
在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我母親會在夏天帶我和兄弟姊妹到大英博物館。那裡雖有各門各類的文化珍寶可供探索,但我們一家人一定會特地去看貝南青銅,當時是陳列在主階梯一個大平臺上。我母親之所以這麼做,是想要確保她擁有一半奈及利亞血統的混血兒女能接觸到來自父母雙方背景的藝術與文化。在那裡,在十六與十七世紀貝南的藝術傑作之前,我們感覺到與非洲的先祖血脈相連;這些飾板曾妝點歐巴皇宮,而我們與製作飾板的匠人有如同族般親密。貝南藝術的裱框照片掛在我們福利住宅的牆上,我們的非洲祖先與歐洲祖先都一樣曾創造出偉大藝術、形成有深度的文明,這是我從有記憶以來就知道的事。
我對歐洲藝術與文化的的欣賞與喜愛主要不是來自參訪博物館與畫廊,而是從另一個媒介灌注給我:電視。我個人頓悟的一刻是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日,那天我母親要我看BBC二臺一部紀錄片《畫家與模特兒》(Artists and Models),我在六十分鐘內飽覽法國新古典主義大師雅各─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藝術作品與精采人生,令我沉迷不已,讓我從此帶著新入教者的狂熱情懷開始去附近圖書館借書。因為《畫家與模特兒》內容與歷史和藝術都有關,兩者都使我燃起熱情,我對二次大戰那年少無知的著迷也就因此消退。
兩年後,我靠著週末與學校假日在商店打工存夠錢,踏上環遊歐洲的旅途。一路上除了在沙灘上曬太陽和拜訪朋友以外,我每到一座城市就去參觀當地大型美術館。十八歲的我來到羅浮宮,BBC節目裡出現過的畫作此時就在我眼前。一位當代作家在《畫家與模特兒》裡說雅各─路易.大衛的畫中氣氛非常冷峻,你幾乎能感覺到寒風從他的畫布裡吹來;我還記得當時站在大衛的《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前面,想要去體會那種森嚴冷氣迎面襲來的感受。對我來說,讓藝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這是何等新而令人興奮的想法;因為我母親苦心讓我接受啟發,因此我才能獲得這般美好的禮物。我先去巴黎,然後去阿姆斯特丹,去了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在那裡我頭一回看到林布蘭(Rembrandt)、維梅爾(Vermeer)、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和其他荷蘭大師的作品。接下來我到馬德里,去看普拉多博物館(Museo del Prado),我在那裡接觸到提香(Titian )、艾爾.葛雷科(El Greco)、畢卡索(Picasso)、迪亞哥.維拉斯貴茲(Diego Velázquez)和耶羅尼米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我在普拉多博物館的紀念品販賣部買了波希《人間樂園》(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複製畫,這是當時的我幾乎買不起的東西,也是我珍藏多年的寶物,我每換一個宿舍房間都要把它掛在牆上。
三十幾年前,一點星星之火通過我家那臺租來的四方形電視機厚螢幕觸及我,我的人生自此不同,雖然當時我並不知情。在我出生前一年,有一個電視節目立下傳統,賦予這傳統形狀與動能,而我小時所看的紀錄片節目就是這傳統的一部分。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的《文明的軌跡》(Civilisation)系列共有十三集,這節目在英國與美國都是電視史傳奇。它擁有數百萬觀眾,其中許多人因為這節目而改變一生,就像後來《畫家與模特兒》對我的影響一樣。在這系列開始播出的兩年前,彩色電視才剛進入英國市場,而色彩規格足以呈現這節目畫面之美的彩色電視就更少見。買得起這種電視的家庭會舉辦「《文明的軌跡》派對」,邀請原本只能用黑白兩色來欣賞歐洲藝術奇觀的親朋好友共聚同樂。連續十三週,在肯尼斯.克拉克的導覽之下,觀眾被帶往一百一十七個不同地點。節目播出的三個月內,畫廊與博物館的負責人都表示訪客數量有所增加。後來,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成千上萬的人前往法國、義大利與其它地方的畫廊參觀,親眼見識肯尼斯.克拉克帶進他們客廳的那些藝術與建築經典,有報導說那一季的旅客人數因此大增。
本書是一部電視節目的姊妹作,該節目是從《文明的軌跡》獲得靈感。現在距離肯尼斯.克拉克這個系列播出時間已經將近五十年,但它依舊家喻戶曉,且理當如此。不過,《文明的軌跡》出名之處不只是因為它對觀眾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而且還因為它的觀點十分狹隘。它所說的故事只包括歐洲藝術與文化,其中又以義大利和法國為主,節目拍攝地點僅涵蓋十一個國家,日耳曼地區在敘事中扮演配角,英國則只有客串演出。這系列裡完全看不到西班牙藝術,此事在馬德里還引起公眾不滿。我們當然不應只憑這部電視節目就給肯尼斯.克拉克下定論,他在其他擴充著作中所展現的世界觀比節目裡要廣闊許多,比方說他終生都對日本藝術情有獨鍾。然而,就算在書裡,克拉克眼中的藝術依然是個男性主宰的天下,現代觀眾很快就能發現《文明的軌跡》系列缺乏對女性藝術家的介紹。
克拉克曾應邀參與一場BBC會議,會中用了「文明」這個詞,他就是在當時出現參與節目製作的想法。文明一詞激起克拉克的想像力、啟發他決定成為這項計劃的主持人與作者,這詞本身的作用超越其他所有動機。就在節目第一集第一景,克拉克有段著名的臺詞是以「文明」的定義做文章,他站在巴黎聖母院前面打趣的問說「什麼是文明?我不知道……不過如果我看到它,我就會認出這是文明。」
對於世界其他各種文明,或這些文明的鑄造者所具的文化想像,克拉克毫不遲疑加以批判。在與節目成套的書中,他寫了一段話,這段話並未出現在節目播出時的臺詞裡;克拉克這段話是將一面屬於布倫斯柏里(Bloomsbury)藝術家與藝評家羅傑.弗萊(Roger Fry)所有的非洲面具以及《觀景殿的阿波羅》(Apollo Belvedere)雕像頭部相比較,他寫道:
無論它身為藝術品的價值是什麼,我認為它(觀景殿的阿波羅)比起面具所蘊含的是更高的文明發展程度,此事毫無疑義。這兩樣東西都象徵著「靈」,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信使,也就是來自一個我們想像中的世界。在尼格羅人的想像裡,那是一個充滿恐懼的黑暗世界,人們隨時都會因為觸犯微不足道的禁忌而遭那個世界施以嚴懲。在希臘人的想像裡,那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光明世界,裡面的神都像人一樣,只是比人更加美麗,祂們下凡來教導人們理性與和諧的法則。
我們可以說,克拉克「尼格羅人的想像」這種用詞是一個生於愛德華時代的人會隨口說出的話,事情或許確是如此。然而,許多年前的夏天,我母親之所以帶她擁有一半非洲血統的孩子們來與貝南青銅面對面,正是因為她知道「文明」一詞是如何被用來貶抑她孩子父親的先祖。正是因為我出生長大時,「尼格羅人的想像」這種概念在英國仍被大部分人認為是原始且缺乏內涵(相較於「歐洲人的想像」),因此我們從孩提時代就被帶去參觀大英博物館、被要求接觸非洲作家的著作,讓我們穿戴上抵抗這種思想的盔甲。
我認為文化的接觸、互動與衝突是過去五百年歷史的關鍵特質;在這本小書以及成套的兩集影片裡,我試圖探索藝術在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我這樣做並非是要反駁肯尼斯.克拉克的觀點,這位極具重要性的文化人物是我尊崇的對象;我的目的是要提醒我自己與那些可能有興趣的人,全人類的想像都是一致的,而一切藝術都是這想像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