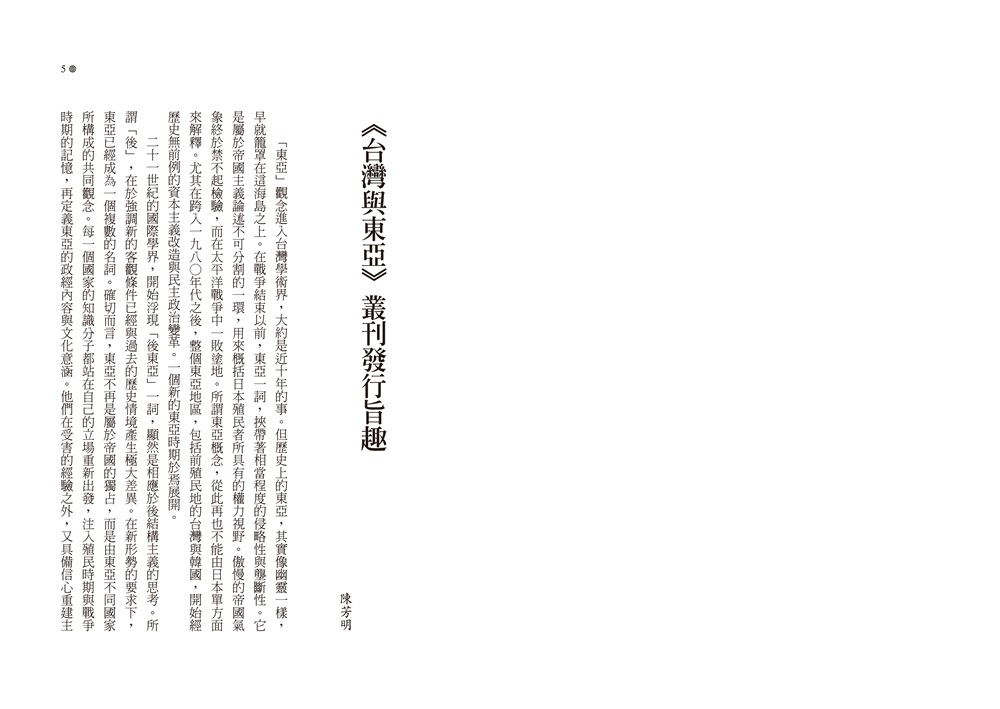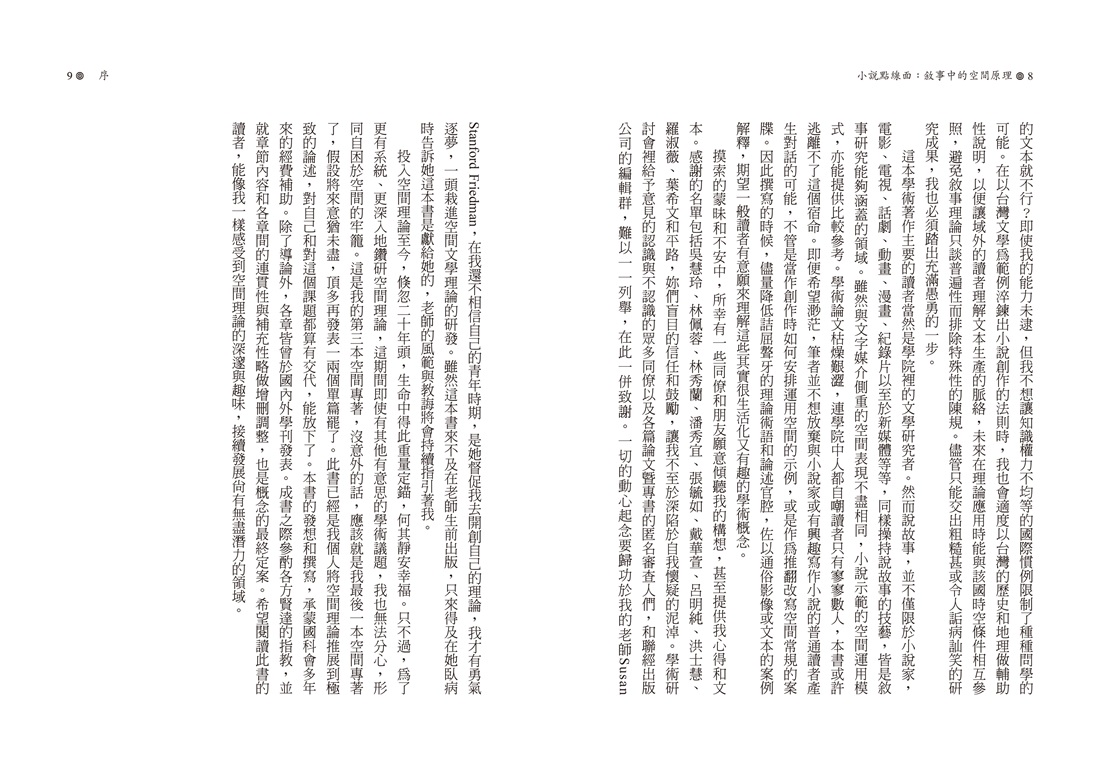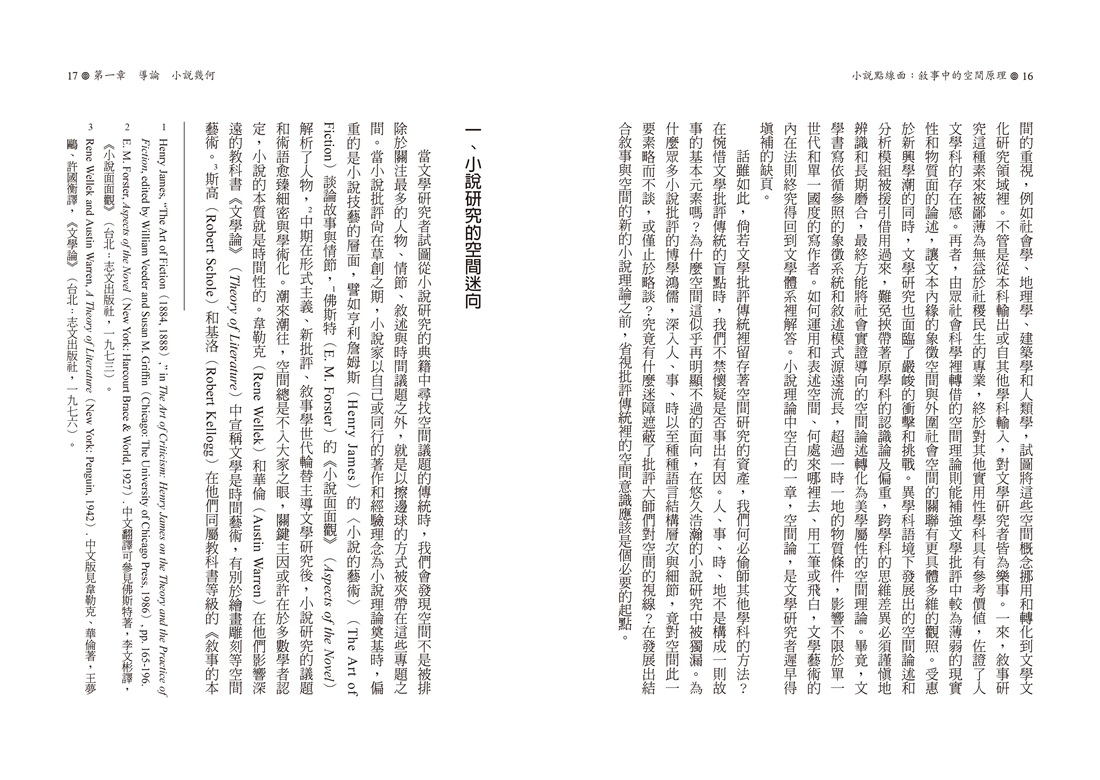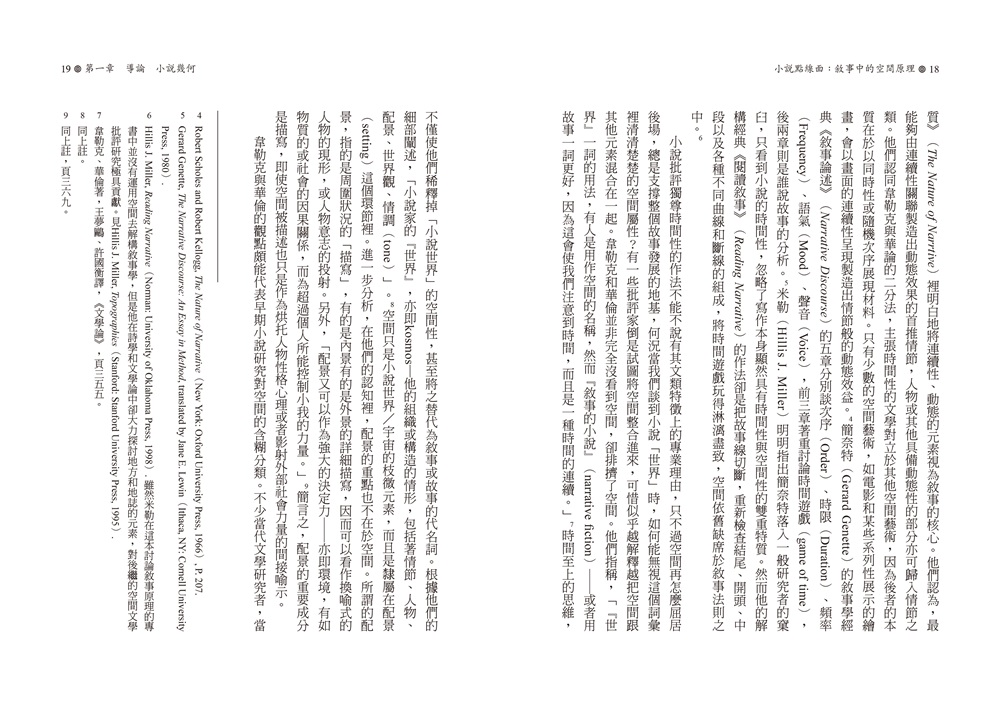小說點線面:敘事中的空間原理
出版日期:2024-08-22
作者:范銘如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56
開數:25 開,長 213 × 寬 14.8 × 高 1.4 cm
EAN:9789570874631
系列:台灣與東亞
尚有庫存
小說裡的空間有那些類型?
空間的配置和結構如何影響對故事的推進?
不同類型的空間上在小說的敘述上發揮何種功能?
小說家與小說研究者向來關注人物、情節、敘述與時間等議題,《小說點線面》一書則另闢蹊徑,挑戰傳統的文學批評方法,將空間元素置於小說分析的核心。
范銘如提出了獨特的空間分類理論,以「點、線、面」三個基本類型,再加上複合空間和邊界等變異形式,涵蓋從微觀到宏觀的各類空間形態,也深入探討了這些空間在文本中的多重功能。
點,包含小面積的居室、單一功能建築體和特定園區,偏向個人的日常活動領域;線,是路徑,是具有聯結、憩止、衝突、逃逸、抉擇性質的中途性空間;面,則是較大範圍的空間,是由許多定點與路徑組織而成偏向集體的公共活動領域,側重於呈現集合性的特徵。
透過細緻梳理百年來的台灣文學,《小說點線面》試圖建構一個既具普遍性、又涵納特定歷史地理彈性的理論模型,不僅揭示空間在文學創作與閱讀中的重要性,為文學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也為跨學科的敘事研究開闢出嶄新視野。
作者:范銘如
台灣嘉義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東亞文學系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現當代小說、台灣女性文學、女性主義理論、文學批評理論、空間理論等。著有《空間╱文本╱政治》、《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書評職人:失憶時代的點書》、《像一盒巧克力:當代文學文化評論》,主編多本文學和評論選集,合編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21th Century 和 The Columbia Sourcebook of Literary Taiwan。
《台灣與東亞》叢刊發行旨趣/陳芳明
序
第一章 導論 小說幾何
原型空間
第二章 小說中的定點
一、定義與功能
二、主輔空間的常見組合
三、變數
四、句點
第三章 小說中的線
一、線的基本作用
二、行路難
三、人生路
四、沿路風景
五、文脈與迴路
六、結論
第四章 小說「面」面觀
一、小說的基本面
二、如何造鎮
三、結論
變異空間
第五章 複合空間
一、家庭空間的複合使用
二、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相互挪用
三、公共空間的屬性轉變
四、畸零地
第六章 邊界
一、地/心理的轉喻點
二、出界
三、入界
四、結論
第七章 結論 延展空間
參考書目
論文出處
索引
導論:小說幾何(節錄)
閱讀一篇小說,可不可能從文本中的空間型態和配置,看出故事的重點或某些情節的走向?上個世紀的理論家顯然不作如是想。從二十世紀伊始,一代代的小說家與批評家,從人物、情節、敘述和時間等等重要的敘事機制,闡述小說藝術的特徵,屢屢翻新表義和表現模式的想像框架,再再讓讀者驚異於這個文類的涵納能量。唯獨空間,始終在敘事研究中乏人問津。所幸空間與敘事這兩個學術議題在二十一世紀的重要性遽增並逐漸合流,只不過轉變的契機既非源自於小說批評領域裡的驅動,至今也尚未結合成系統性的小說理論。精準地說,敘事轉向(narrative turn)與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是兩股主客場不同的跨學科應用趨勢。敘事轉向主要是文學研究之外的學科認識到敘事的重要性,借重人文領域的敘事模式作為呈現或治療的手段,法律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屬性相近的學科固不待言,甚至連認知科學都開始積極探索人的心智如何運用敘事構築完整的認知世界。空間轉向則是文學批評注意到其他學科對於空間的重視,例如社會學、地理學、建築學和人類學,試圖將這些空間概念挪用和轉化到文學文化研究領域裡。不管是從本科輸出或自其他學科輸入,對文學研究者皆為樂事。一來,敘事研究這種素來被鄙薄為無益於社稷民生的專業,終於對其他實用性學科具有參考價值,佐證了人文學科的存在感。再者,由眾社會科學裡轉借的空間理論則能補強文學批評中較為薄弱的現實性和物質面的論述,讓文本內緣的象徵空間與外圍社會空間的關聯有更具體多維的觀照。受惠於新興學潮的同時,文學研究也面臨了嚴峻的衝擊和挑戰。異學科語境下發展出的空間論述和分析模組被援引借用過來,難免挾帶著原學科的認識論及偏重,跨學科的思維差異必須謹慎地辨識和長期磨合,最終方能將社會實證導向的空間論述轉化為美學屬性的空間理論。畢竟,文學書寫依循參照的象徵系統和敘述模式源遠流長,超過一時一地的物質條件,影響不限於單一世代和單一國度的寫作者。如何運用和表述空間、何處來哪裡去、用工筆或飛白,文學藝術的內在法則終究得回到文學體系裡解答。小說理論中空白的一章,空間論,是文學研究者遲早得填補的缺頁。
話雖如此,倘若文學批評傳統裡留存著空間研究的資產,我們何必偷師其他學科的方法?在惋惜文學批評傳統的盲點時,我們不禁懷疑是否事出有因。人、事、時、地不是構成一則故事的基本元素嗎?為什麼空間這似乎再明顯不過的面向,在悠久浩瀚的小說研究中被獨漏。為什麼眾多小說批評的博學鴻儒,深入人、事、時以至種種語言結構層次與細節,竟對空間此一要素略而不談,或僅止於略談?究竟有什麼迷障遮蔽了批評大師們對空間的視線?在發展出結合敘事與空間的新的小說理論之前,省視批評傳統裡的空間意識應該是個必要的起點。
一、小說研究的空間迷向
當文學研究者試圖從小說研究的典籍中尋找空間議題的傳統時,我們會發現空間不是被排除於關注最多的人物、情節、敘述與時間議題之外,就是以擦邊球的方式被夾帶在這些專題之間。當小說批評尚在草創之期,小說家以自己或同行的著作和經驗理念為小說理論奠基時,偏重的是小說技藝的層面,譬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談論故事與情節,佛斯特(E. M. Forster)的《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解析了人物,中期在形式主義、新批評、敘事學世代輪替主導文學研究後,小說研究的議題和術語愈臻細密與學術化。潮來潮往,空間總是不入大家之眼,關鍵主因或許在於多數學者認定,小說的本質就是時間性的。韋勒克(Rene Wellek)和華倫(Austin Warren)在他們影響深遠的教科書《文學論》(Theory of Literature)中宣稱文學是時間藝術,有別於繪畫雕刻等空間藝術。斯高(Robert Schole)和基洛(Robert Kellogg)在他們同屬教科書等級的《敘事的本質》(The Nature of Narrtive)裡明白地將連續性、動態的元素視為敘事的核心。他們認為,最能夠由連續性關聯製造出動態效果的首推情節,人物或其他具備動態性的部分亦可歸入情節之類。他們認同韋勒克與華論的二分法,主張時間性的文學對立於其他空間藝術,因為後者的本質在於以同時性或隨機次序展現材料。只有少數的空間藝術,如電影和某些系列性展示的繪畫,會以畫面的連續性呈現製造出情節般的動態效益。簡奈特(Gerard Genette)的敘事學經典《敘事論述》(Narrative Discourse)的五章分別談次序(Order)、時限(Duration)、頻率(Frequency)、語氣(Mood)、聲音(Voice),前三章著重討論時間遊戲(game of time),後兩章則是誰說故事的分析。米勒(Hillis J. Miller)明明指出簡奈特落入一般研究者的窠臼,只看到小說的時間性,忽略了寫作本身顯然具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雙重特質。然而他的解構經典《閱讀敘事》(Reading Narrative)的作法卻是把故事線切斷,重新檢查結尾、開頭、中段以及各種不同曲線和斷線的組成,將時間遊戲玩得淋漓盡致,空間依舊缺席於敘事法則之中。
小說批評獨尊時間性的作法不能不說有其文類特徵上的專業理由,只不過空間再怎麼屈居後場,總是支撐整個故事發展的地基,何況當我們談到小說「世界」時,如何能無視這個詞彙裡清清楚楚的空間屬性?有一些批評家倒是試圖將空間整合進來,可惜似乎越解釋越把空間跟其他元素混合在一起。韋勒克和華倫並非完全沒看到空間,卻排擠了空間。他們指稱,「『世界』一詞的用法,有人是用作空間的名稱,然而『敘事的小說』(narrative fiction)─或者用故事一詞更好,因為這會使我們注意到時間,而且是一種時間的連續。」時間至上的思維,不僅使他們稀釋掉「小說世界」的空間性,甚至將之替代為敘事或故事的代名詞。根據他們的細部闡述,「小說家的『世界』,亦即kosmos─他的組織或構造的情形,包括著情節、人物、配景、世界觀、情調(tone)」。空間只是小說世界/宇宙的枝微元素,而且是隸屬在配景(setting)這個環節裡。進一步分析,在他們的認知裡,配景的重點也不在於空間。所謂的配景,指的是周圍狀況的「描寫」,有的是內景有的是外景的詳細描寫,因而可以看作換喻式的人物的現形,或人物意志的投射。另外,「配景又可以作為強大的決定力─亦即環境,有如物質的或社會的因果關係,而為超過個人所能控制小我的力量。」簡言之,配景的重要成分是描寫,即使空間被描述也只是作為烘托人物性格心理或者影射外部社會力量的間接喻示。
第三章 小說中的定點
儘管某些小說會將空間處理為模糊的背景或場景甚或完全略過,大多數文本裡的空間是烘托人物、情節和主旨不可或缺的整體性要素。不管是運用何種寫作技巧與流派,小說作為虛構的世界,不論從故事的發展、角色的外貌、行為、對話、心理、關係、思想,以至時間、文化和美學上的邏輯,總須營造出某種可能性,空間亦是製造讀者感覺合理的幻術之一。其間的關鍵處即是帕維(Thomas G. Pavel)特別點明的,虛構世界無關文本是否寫實或邏輯上可不可能,需要的是作者和讀者之間有共識。小說人物或事件應該出現在哪些地點,哪些地點出現的時候連帶暗示著何種情節或心情的發生,在作者和讀者間隱隱形成某種不行文的默契。沒有對的地點,即使安排了對的人在對的時間發生了對的事,虛構世界的認識會跟讀者的感受有所出入導致對主旨的傳達打了折扣。場景的基礎功能雖然是讓故事可能和真實,不見得必須要非常寫實的描寫,可以是模糊的這裡與那裡,可以是複雜紀實的地誌,也可以是突出的前景或是不鮮明的背景,只要能產生某種區隔和對比或是凸顯了故事的主題即可。
小說空間是個體居住、勞動、休憩和移動組織起來的範圍,定點尤其是重中之重。所謂的定點(spot or Point),指的是小面積的居室和單一功能建築體,包括房間、家庭、學校、工作和娛樂場所等,偏向個人的日常活動領域。以現代生活中對空間的運用簡單計算——一天之中八小時在工作場所或是學校學習,再加八小時在家裡睡覺休息,定點無疑是所有空間形態中人類居憩停留和人際互動時間最長的地點。文本空間以現實空間為本,人物駐留場所的時間越長、事件發生的比例越高,因此點線面三種小說空間形態中定點的使用率最多、重要性最大。對空間的使用長短不代表小說中該空間被敘述的比重,因為小說空間的使用不僅是搭配事件的發生,還是對故事重點的強調。某些場所可以在文本中反覆出現描述,有些地點出現一兩次,抑或潦草掠過。依據其占比篇幅多和篇幅少,小說裡出現的空間又可區別為主要空間和輔助空間。點線面三者雖然皆可作為主要空間,最常被設置為主要空間的還是在定點,而在定點之間同樣亦有主輔空間之分。因此,本章首先討論最基礎的定點、也是點線面三種基本型及其無窮組織的起始原點。下文依序將歸納文本中空間定點的設計,由主要空間和輔助空間這兩種概念分析其定義、功能和常見的組合模式,然後再討論幾個影響這些定點組織的變異參數,包括不同時代演進的小說形式、主旨與流派。
一、定義與功能
為了具體解釋小說中的各種空間形式及其如何串聯起人物的活動與移動,我想先以台灣新文學史上最早期的小說〈她要往何處去〉(一九二二)為例,並將其空間轉換作為敘事分鏡的說明。小說共有五小節。第一節開場,放學返家的女主角桂花進入臥房休息,當她思念起在日本念書的未婚夫清風時,母親拿著同在日本留學的表哥電報進來,報知兩人即將返台的訊息。數天後母女倆前去基隆港迎接清風和表哥。第二節的場景在水源地,樹蔭下有對私語的情侶─清風和他在日本秘戀兩年的女友,商議著如何將戀情告知不知情下擅自為他訂下婚約的家人、以及正和表哥一邊划船一邊不安地望向兩人的桂花。第三節是表哥來家中告訴母親原委、然後進桂花的臥房勸慰表妹;與此同時,母親收到清風寄來的悔婚道歉信,進房一起安慰桂花。第四節場景一樣在桂花的閨房,退婚後傷心消沉的她臥病在床數天,最後決定振作起來,到日本留學。第五節時空進行很快。桂花從基隆港離台,在船上偶然與一名女學生攀談,兩人遭遇不同,卻一樣是媒妁婚姻的受害者。了悟封建婚姻對青年,尤其是女性的束縛後,桂花終於走出被毀婚的傷痛。最後桂花在東京展開自信又開朗的女留學生新生活。
從五場簡單的分鏡可知,這篇小說的空間是由點和線構成,定點尤其是情節發生的真正舞台。就上述的故事分鏡中,桂花的家(尤其臥室)是最常出現的場景,五節中占了三節,其他地點包括港口(兩次)、水源地、船上、東京,然而篇幅不多。顯然桂花的家是故事中最重要的定點,其他定點皆顯次要。為了更清楚的區分這些定點的性質,我將把前者稱之為主要空間,後者稱為輔助空間。由於線的部分(去基隆港接人和去基隆港搭船赴日的路程)皆是浮掠帶過,同樣視為輔助空間。〈她要往何處去〉的空間結構就是以一個定點(家)作為主要空間,其他幾個定點和路線的輔助空間組合而成。
一般而言,短篇小說的篇幅有限,空間的類型相對比較簡單,大致包含幾個定點:一個主要空間搭配兩三個左右的輔助空間。長篇小說能容納的空間類型較多,情節通常還是會聚焦在一個或以上的主要空間搭配多個輔助空間,但是地理幅員涵蓋的範圍較廣,有時會以一系列的定點配置組合成面。不過字數與章節的多寡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不同創作流派和主旨的小說亦會相應產生不同程度的變化。絕大比例的小說是將某個定點當作主要空間去展演或推動情節,少部分會設計在路徑(線)、更少部分則是以面作為主要空間,後兩者將次第專論。
主要空間通常被設置來配合人物身分和個性或彰顯情節主旨,是整個故事的發動、危機或轉機之處。角色的空間活動有其合理性,這種合理性部分是源自社會空間的實踐,部分則源自美學實踐的傳統,形成了作者與讀者雙方認知上的基礎與共識。以〈她要往何處去〉為例,跟二○年代台灣和中國的主流論述與文學一樣,藉由一個少女的覺醒,由遵循盲目的媒妁婚姻到追求自我的提升(與自由戀愛),呼籲以啟蒙、個性解放的現代性想像來推翻封建傳統的封閉落後。在傳統的修辭裡,未婚少女通常形容為待字閨中、養在深閨,和閨閣、閨秀這種內室空間意象連結。小說主旨既是鼓勵從私領域走向公領域,因此桂花臥房是主要空間、而她最終必須從家中出走,是敘述女性解放母題時常見的空間隱喻。類似的空間走向從十九世紀易卜生的娜拉以迄袁瓊瓊八○年代女性小說〈自己的天空〉屢見不鮮。家門出入可說是二十世紀婦女解放書寫中普遍的空間想像。
當小說主角的身分是某類職場的上班族、而且此身分與故事主旨有關時,主要空間多會是與之相應的工作場所,農夫在田庄、工人在工廠、白領在辦公室及其業務相關場所、老師在學校、舞女在舞廳。當小說側重的是主角的家庭倫理身分時,不管是夫或妻、是兒女、公婆、兄弟、姊妹、妯娌等,主要空間通常會設置在家庭或家族有關的場地;當主要空間安排在跟職場或倫理身分有關之處,故事的主旨通常傾向探討角色們在工作或家庭場所內遭遇到的問題、衝突與解決方式。舉例來說,黃春明的〈兩個油漆匠〉描寫兩個從東部鄉鎮來到西部大都市謀生青年的困境,整篇小說最主要的空間就是鎖定在他們進行油漆工作的高樓頂端上的工作架和未完工的鋼條和照明鐵架間,顯示他們看似「往上爬」實則孤懸無靠的社會位置。王禎和的〈小林來台北〉描述鄉下青年小林在台北航空公司當工友的故事。小說篇名既是來台北,照理說主要空間應該反映出大都會的熱鬧繁榮,然而通篇故事只見小林在任職航空公司所在的大樓間被呼來喝去,凸顯其低微狼狽的處境。台北的時尚風光完全與他無涉、航空連結的國際網絡更與他無關,這棟密閉空間才是主宰他的世界。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顧名思義是舞女領班的退休倒數,主要空間當然是在舞廳,在這個五光十色的聲色場所回顧女性青春戀夢的繁華與虛妄。
比較特別的是,以農夫為主要角色的小說,活動空間雖然是在農村,主要空間卻鮮少設置在田地上,反而多在一些村庄裡公共聚集的場所。可能的原因是田畝的耕種比較屬於個體的勞作行為,若主要空間需要承載小說人物們互動對話間帶動起的情節變化,農地這種私有場地的功能自不若農會、會堂、港口、市集、廟埕、某棵村眾聚集的大樹下、甚或是主角的住家。因此,宋澤萊講述的〈笙仔與貴仔的傳奇〉,明明主角都是瓜農,小說中瓜田出現的比例遠遠不如廟場和瓜果市場,在這種小農作物的集散地才更能夠彰顯盤商與通銷制度對個別農家的絕對優勢與剝削。
角色的空間活動既然是理解上的某種默契,小說家同樣可以利用這種讀者的預設認知,故意讓角色不得其所(displaced),出現在跟角色身分不符合的地點。一來可以來用反差凸顯這個角色身分面對到的矛盾,二來也可以製造閱讀上的緊張感或戲劇性效果。例如星期二早上十點,幾個穿制服的學生在西門町遊逛,或者一名穿西裝拿公事包的男子踏進了公園,又或一群拿著鋤頭的農夫走上街頭,在應該上班上課的時間出現在不應該出現的地點,讀者立刻能夠感受到其中必有緣故而期待情節的交代。失去了與身分相應的空間更是書寫身分政治時常見的策略,不管是五○年代遷台的外省移民小說、六○年代留學生小說、到當代探討流落都市討生活的原住民文學,身分空間的錯置都是文本中必然重複申訴的愁思。
主角的身分雖然是影響主要空間設置的因素,小說意圖表達或探討的主旨才是最關鍵的要素。一樣是軍人,朱西甯的軍官多在營區或山野裡生聚備戰,白先勇的將軍多賦閒家中撫今追昔。一樣是教師,鍾肇政《魯冰花》的正常版美術老師不是在教室或戶外教畫就是進行家庭訪問,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妳》的老師卻斯文掃地在「得恩堂」的宗教祭壇上開授英語速成班儲備接待美國大兵的高級妓女。神聖的教堂淪落為歡場職訓教室,空間認知與身分錯置的衝突,以及一干「師生」時地不宜的惡行穢語,是這本社會諷刺小說最成功的設計之一。
輔助空間則是主要空間的延伸或者對照,輔助空間提供是角色活動以及各情節發展需要的場合,蜻蜓點水式的跳接即可,不必然描述一個明確的空間或清楚的範圍。不像主要空間與小說主旨的緊密連結、相對設限輔助空間的選擇比較自由、不需要必然的邏輯,只要作者覺得情節上需要就可順帶一提。上文舉例的〈她往何處去〉除了女主角的家,其他出現的地點都是所謂的輔助空間;同理,楊逵的〈送報伕〉顧名思義,主要空間必然是報社,其他輔助空間就可以隨著主角的移動而出現宿舍、租處、路上、飯館、公園、故鄉的家與媽祖廟埕等等。袁哲生的〈時計鬼〉,主要角色是兩個學齡頑童,他們的活動場所,除了教室是不得不出現的主要空間,當然無法拘束在幾個定點。小說中的輔助空間包括家庭、校內外空地、村莊中任何這裡那裡他們覺得好玩的地點都是出沒之處。這些輔助空間符合角色身分與故事進行的合理範圍,但嚴格說來這些地點可增可減可替代。越往當代,八○年代以後益發明顯,台灣小說裡空間的跳接就像時間的切換一樣,不要求仔細的邏輯交代,俐落而突兀的替換加速敘事節奏已是常見凸顯小說風格的方式,輔助空間的數量和頻率、連續性及其選擇性更趨向多元甚至零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