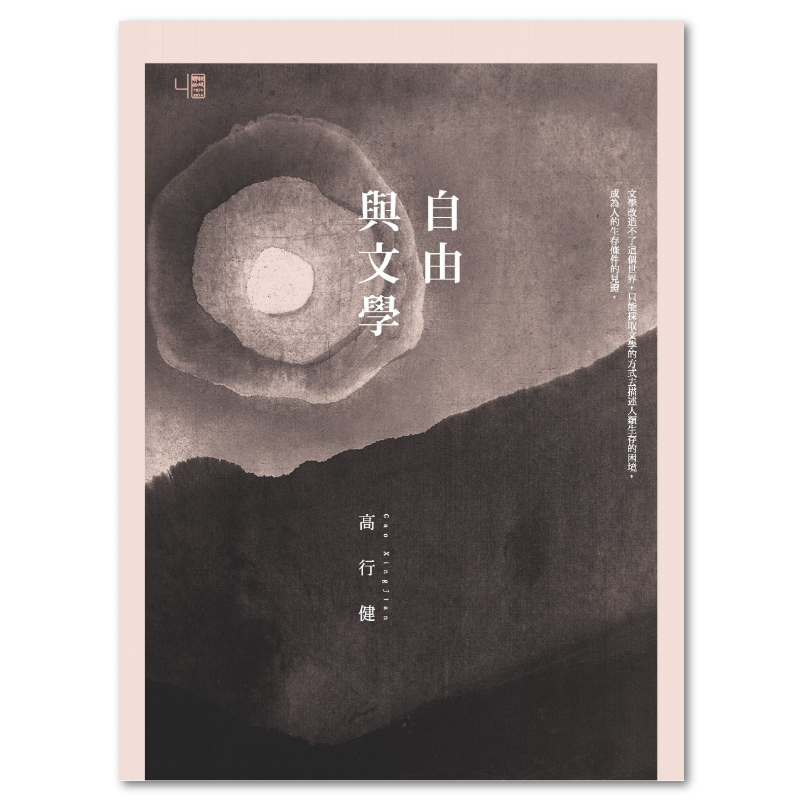自由與文學
出版日期:2014-03-28
作者:高行健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16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3620
系列:當代名家
尚有庫存
《自由與文學》結集自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演講
包括在世界各地的精彩演講紀錄
全面呈現高行健文學藝術上的思想成就
「作家從他的精神視野來說,乃是天生的世界公民,不受政治權力乃至國家的約束,天馬行空,來去自由,這也是文學本身具有的品格。」
「文學改造不了這個世界,只能採取文學的方式去描述人類生存的困境,成為人的生存條件的見證。」
──高行健
高行健對於寫作自由高度重視,認為「寫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賜的,也買不來,而首先來自作家自己內心的需要。」更提出「文學改造不了這個世界,只能採取文學的方式去描述人類生存的困境,成為人的生存條件的見證。」成為本書最好的註解。
他的一生,孜孜不倦在小說、戲劇、繪畫乃至電影等文學藝術領域不斷創新,而且不屈不撓地追尋文學的真理。他最後找到的文學真理就是真實、真誠、獨立不移和對於「自由」的覺悟。
──劉再復
作者:高行健
國際著名的全方位藝術家,集小說家、劇作家、詩人、戲劇和電影導演、畫家和思想家於一身。一九四○年生於中國江西贛州,一九八八年起定居巴黎,一九九七年取得法國籍,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小說和戲劇關注人類的生存困境,瑞典學院在諾貝爾獎授獎詞中以「普世的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加以表彰。
他的小說已譯成四十種文字,全世界廣為發行。他劇作在歐洲、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亞頻頻演出,多達一百三十多個製作。他的畫作也在歐洲、亞洲和美國的許多美術館、藝術博覽會和畫廊不斷展出,已有上百次展覽,其中多達九十次個展,出版了五十多本畫冊。近十年來,他又拍攝了三部電影詩,融合詩、畫、戲劇、舞蹈和音樂,將電影作成一種完全的藝術。
他亦榮獲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法國文藝復興金質獎章、義大利費羅尼亞文學獎、義大利米蘭藝術節特別致敬獎、義大利羅馬獎、美國終身成就學院金盤獎、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雄獅獎、盧森堡歐洲貢獻金獎。香港中文大學、法國馬賽—普羅旺斯大學、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臺灣大學、臺灣的中央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和國立師範大學皆授予他榮譽博士。
此外,二○○三年,法國馬賽市為他舉辦大型藝術創作活動「高行健年」。二○○五年,法國愛克斯—普羅旺斯大學舉辦「高行健作品國際學術研討會」。二○○八年,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和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高行健藝術節」。二○一○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辦「高行健的創作思想研討會」。二○一一年,德國紐倫堡—埃爾朗根大學舉辦「高行健:自由、命運與預測」大型國際研討會;同年,韓國首爾高麗大學舉辦「高行健:韓國與海外視角的交叉與溝通」,韓國國立劇場則舉辦「高行健戲劇藝術節」。二○一四年,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舉辦「高行健作品國際研討會」。二○一七年,臺灣國立師範大學舉辦「高行健文學藝術節」。二○一八年,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圖書館設立「高行健研究與資料中心」。二○二○年,臺灣國立師範大學圖書館設立「高行健資料中心」。現任臺灣國立師範大學講座教授。
序言 世界困局與文學出路的清醒認知/劉再復
輯一
環境與文學──我們今天寫什麼?
──國際筆會東京大會文學論壇開幕式演講
意識形態與文學
──韓國首爾國際文學論壇演講
自由與文學
──德國紐倫堡─埃爾朗根大學國際人文研究中心舉辦「高行健:自由、命運與預測」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
認同─文學的病痛
──臺灣《新地》雜誌舉辦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在臺灣大學演講
走出二十世紀的陰影
──臺灣《新地》雜誌舉辦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在台中的演講提綱
意識形態時代的終結
──韓國首爾檀國大學演講提綱
非功利的文學藝術
──韓國首爾漢陽大學演講提綱
呼喚文藝復興
──新加坡作家節演講
輯二
洪荒之後
關於《美的葬禮》──兼論電影詩
《山海經傳》──臺灣國家戲劇院演出感言
輯三
創作美學──香港中文大學演講
杜特萊與高行健對談/蘇珊譯
輯四
林兆華的導演藝術
馬森的《夜遊》
後記
附錄:高行健年表/劉再復整理
序 世界困局與文學出路的清醒認知/劉再復
高行健這部新書的主要部分是他的演講。我直接傾聽過他在法國普羅旺斯大學、德國埃爾朗根大學、韓國漢陽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華文盛會(新地雜誌主辦)等處的演講,還和他在香港共同進行過一場題為「走出二十世紀」的對話。八○年代在中國大陸時,我喜歡聽他說話,那時,我和劉心武可能是他的最好聽者。心武說,聽行健說話,如聞天樂。我也有此感覺。出國後,山高水遠,各居一方,還是喜歡聽到他的聲音,除了在電話中交談之外,我還特別留心他的演講,並蒐集和閱讀他的每一篇演講稿。我喜歡聽他說話、演講,原因極為簡單,因為他的談論很有思想,而且思想又是那麼新鮮,那麼獨到。在當下缺少思想的世界裡,他的每次演講,都如空谷足音,給了我振聾發聵的啟迪。他醉心於文學,認定文學才是自由的天地,一再勸告作家不要從政,不要誤入政治歧途,但他自己作為一個具有普世關懷的作家,卻從不避世,而且總是直面人間的困境發表意見。而這些意見既「充分文學」又不僅僅是文學,他觸及到的是時代的根本弊病,是世界面臨的巨大問題,是人類生存的種種困局。我曾說,有膽有識,二者兼備方能構成境界。而高行健正是這種兼備者。他身處海外,早已走出精神囚牢,得大自在,也早已無所畏懼,絕不俯就任何政治集團和利益集團。既不迎合泛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胃口,也不迎合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胃口(包括不迎合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的胃口),只發出個人真實而自由的聲音。其言論的膽魄眾所周知。「膽」之外是不同凡響的「識」。我把「識」分為五個層面,即常識、知識、見識、睿識、天識。他的演講不僅處處有「見識」,而且蘊含著許多睿識與天識。我本身是個寫作者又是個思想者,對「思想」和對「語言」都有感覺,二三十年來,我被高行健所打動的正是他的思想與他的語言。但能進入我心靈深處的,還是他那些抵達當下世界精神制高點的新鮮思想。
如果說「冷觀」是高行健的文學特點(這一特點使他創造了「冷文學」),那麼,可以說,「清醒」則是高行健的思想特點。我本想用「深刻」二字來形容他的思想,最後卻選擇「清醒」這一關鍵字,是覺得無論是他的「冷觀」,他的寫作,還是他的演說,都有對世界、對人性、對文學的極為清醒、極為透徹的認知。這種認知,就像犀利的寶劍,一下子穿透事理的核心,事物的本質。我常為之而震撼。記得剛出國時,我還在為遠離故國而徬徨的時候,他就斬釘截鐵告訴我:「逃亡正是自由的前提。」由此,我才產生「美學逃亡」而非「政治逃亡」的思想,更是贏得告別政治牢籠的大快樂。這之後,他又寫出劇本《逃亡》,劇中的哲學主題是:人可以從專制的陰影中逃亡,但最困難的是如何從「自我地獄」中逃亡。這種地獄,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它都緊跟著你。這是何等清醒的思想?人貴自知之明,但自知之明絕非易事。如果不是讀柏拉圖,那我就會身處「洞穴」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讀魯迅,那我就會身處「鐵屋」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讀高行健,那就會身在「自我地獄」之中而不自知。現在有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其問題恰恰是缺少「自我地獄」的清醒意識。不知自身燃燒人性的欲望,內心一片渾濁,卻要充當「救世主」並把自己打扮成「社會正義」的化身。高行健的清醒,則是訴諸個人的良知,正視自身「惡」的無限可能,不以標準化權威化的「社會良心」自居。他一再批評尼采,拒絕「超人」和「權力意志」等理念,認定這是歐洲十九世紀最後的浪漫。他拒絕尼采而推崇卡夫卡與慧能,其背後乃是他對「人」與「人性」的清醒把握,他認定,「超人」、「大寫的人」並不真實;倒是回歸「脆弱人」、「平常人」,正視人性的脆弱、荒誕、黑暗,才是人類「自救」的起點。
高行健不僅對「人性」具有清醒的認識,而且對世界、對人類生存環境、對文化走向等,也有極為清醒的認識。只要讀一讀本書中這些演講以及相關的談話與文章,我們就會明白,他給當今世界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睿識。這些睿識,可概括為下述三個基本點。
第一,「世界難以改造」(但可以理解)。高行健提出「世界難以改造」的觀點,挑戰的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世界範圍內的烏托邦思潮與革命思潮,而首先打破的是中國大陸流行的習慣思維和一貫性思維。高行健和我這一代大陸知識人,從小就接受「改造世界」的宏大理念,也可以說是「抱負」與「使命」。這一理念付諸實踐,產生的是烏托邦狂熱與暴力革命崇拜,以為革命可以改變一切,甚至以為文學藝術也應該革命,而革命文藝也可以改造世界。與此相應,便在各領域中「推翻舊世界」、將前人一概打倒,將文化遺產統統掃蕩。高行健是我認識的同一代人中,第一個清醒地放下「改造世界」的重負,從而也放下文學可以成為改造世界之奢望的思想家。高行健一再強調,文學只能見證歷史,見證人性,見證人類生存條件,而不能改造世界,改變歷史,所以文學不應當以「社會批判」為創作的出發點。倘若以此為出發點,只會使文學降低為譴責文學、黑幕文學、黨派文學、傾向性文學,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形象注腳或形象轉述。正是因為放下「改造世界」的妄念,所以高行健既反對政治干預文學,也反對文學干預政治。總之,認定放下「改造世界」的理念重負,才有自由。
第二,「時代可以超越」。認識到世界難以改造的高行健並不避世,也不悲觀。他明確表示,文學應當關注社會,乃至關注種種社會問題。儘管我們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時代的條件與社會環境,但可以喚醒人的覺悟,可以超越時代的制約,也即時代所形成的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的制約。政治當然免不了權力的角逐,經濟當然逃不脫利潤的法則,人類社會離不開這些功利的活動,但文學卻可以超越這些功利,而且可以置身於功利活動的局外,退入邊緣而成為潮流外人。這就是作家詩人能做出的選擇,在時代潮流中獨立不移,自鳴天籟。既不從政,也不進入市場;既不接受任何主義,也不製造新的主義與新的幻象。文學可以為時代所不容,但它恰恰可以超越時代去贏得後世的無數知音,這便是文學的價值所在。
功利可以懸擱,時代可以超越,那麼,超越之後作家要到哪裡去?高行健又清醒告訴我們:文學應回到它的初衷,它的「原本」。文學的初衷是什麼?文學的初衷是文學產生於人類內心的需要,有感而發,不得不發。文學初衷本無功利,即無政治、經濟、功名之求。文學本來就不是政治學、經濟學、市場學、新聞學,因此返回文學初衷才是文學的出路。他說得好:
文學不預設前提,既不企圖建構烏托邦,也不以社會批判為使命。文學當然關注社會,乃至種種社會問題,然而,文學並非社會學,關注的是社會中的人,回到人性,回到人性的複雜,回到人的真實處境,才是文學的宗旨。
──在國際筆會東京文學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
第三,「文藝可以復興」。儘管世界充滿困境,市場無孔不入,俗氣與時髦到處蔓延,但高行健確信,文學藝術仍然可以有所創造,有所復興,大有作為。因為文學藝術本來就是充分個人化的活動,一切取決於個人的心靈狀態。天才都是個案,並非時代的產物。文學藝術都是由個人去創造的,所謂「復興」,也應由個人去實現去完成。儘管世界亂糟糟,但有心人還是可以找到有意義的事情默默去做。米開朗基羅、達文西等文藝復興的巨人們,他們正是在宗教的大黑暗中,借著上帝的外殼而注入人性的內涵。也正是在雍正、乾隆文字獄最猖獗的清王朝,曹雪芹卻創造出中國文學的經典《紅樓夢》。高行健一再說明,文學是自由的領域,但這自由不是上帝的賜予,不是他人的賜予,而是自己的「覺悟」。唯有自身意識到自由,才有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詩人在惡劣的環境中也還可以贏得內心的自由,寫自己要寫的作品,只要能耐得住寂寞。
高行健的這些演講和論述,如果一篇一篇認真讀下來,就會明白,他關注的是文學與文化的根本,是世界大局與未來。我出國後二十多年,一直留心西方學界與思想界,覺得西方學人確實提供了許多專業的新知識與新見解,也常對某個歷史事件和某段歷史行程做出了理性而精彩的評說,但少有對當下世界困局與人類前景的清醒認知與宏觀把握,也就是說,還很難見到類似高行健這樣清醒、透徹的思想者。我讀高行健常為自己的同胞兄弟而自豪,因為他讓我看到,終於有一個華人作家藝術家,走上歷史舞臺,超越「中國視野」,真正用全球的眼光與普世的情懷觀察與討論當今世界的困局,而且在那麼多的領域中提出那麼多新鮮的思想。高行健耗費了前半生,經歷了多次逃亡,一再被批判、圍剿、查禁,卻仍然擁有強大的靈魂活力,又如此獨立不移。二〇〇五年,我到巴黎訪問他時,見到他寓所中滿牆的水墨畫(已在十幾個國家舉辦過七十多場畫展)和書架上幾百多本各種文字的高行健作品集與畫集,真是感慨不已。一個質樸低調、一起從東方黃土地走出來的同齡朋友,就這樣走向世界精神價值創造的高峰,提供了如此豐富的思考與作品。
高行健是一個作家、藝術家全才,他的一生,孜孜不倦在小說、戲劇、繪畫乃至電影等文學藝術領域不斷創新,而且不屈不撓地追尋文學的真理。他最後找到的文學真理就是真實、真誠、獨立不移和對於「自由」的覺悟。難怪此書要以「文學與自由」為題,既是總題又是主題。
環境與文學 ── 我們今天寫什麼?
我首先感謝日本筆會會長阿刀田高先生對我的信任,邀請我在東京舉行的世界各國作家雲集的這一盛會上,以「環境與文學──今天我們寫什麽」爲題作這番演講,提出一些問題和看法,供大家討論。
文學面臨的環境大抵無非是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這兩重關係,如今都困境重重。自然環境污染日趨嚴重,而地球大氣暖化也已經成了全人類普遍的焦慮,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雖然早已成了政治和媒體日常的公衆話題,卻絲毫不見什麽有效的政策和實施,哪怕稍許延緩人類賴以生存這唯一的環境的惡化,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卻相反正在加速進行。
另一方面,人類生存的社會環境也同樣免除不了政治的干擾和市場經濟的侵淫,政治和廣告通過鋪天蓋地的媒體侵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現今這偌大的地球恐怕再也找不到一片不受污染的淨土,這便是現今文學面臨的環境,可以說是十足的困境。
面對這樣的困境,作家能做些什麽?或者說文學能否改變人類面臨的這種困境?這就是我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現今的作家面對這無邊無際的困境,應該說,確實無奈,而文學也無非是作家個人的聲音,這如此脆弱的個人如果不訴諸神話和科幻又能做些什麽?文學改造不了這個世界,只能採取文學的方式,去描述人類生存的這種困境,成爲人的生存條件的見證。而如何描述現時代人的真實處境,換言之,首先是如何認識這種處境,這才是作家的工作。
作家在現今社會並不具有獨特的社會地位,既無權力又無特權,如果不投入政黨政治的話,孑然一身,倘若沒有別的職業或自家經濟來源的支撐,僅僅以寫作謀生,又能否抵制市場的壓力,保持精神上的獨立不移,把他的觀察與思考寫到書中去?對現時代的作家來說,這才是既真實又嚴峻的現實處境。
這裡說的文學,是這種面對人的真實處境的文學,而非書市的排行榜上的暢銷書,這種文學所面臨的困境,也正是當今文學的處境。現時代的作家如果不肯捲入政黨政治,爲選戰捧場或充當政治權力的鼓吹手,又不追隨市場炮製的時尚,不得不面對這無需爭辯的現實。現時代人類的生存困境同作家和文學的困境就這樣緊密聯繫在一起。
在現今的社會條件下,且不說作家如何去改變困境,在這種困境中如何堅持這種超越功利的寫作,抵抗各種各樣的壓力和誘惑,維護精神的獨立,都是非常艱難的,這就是我們進而要討論的。
作家並非聖人,而聖人安在?作家也非超人,既非造物主又非救世主,也不必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言人、時代的喉舌或社會正義的化身,再說這樣的角色不如留給政客,而且也已經太多了,像走馬燈一樣,媒體上天天在表演,卻並沒有拯救這個世界。
文學改造不了世界,把文學作爲工具或武器,乃是出於政治的需要。文學介入政治,絲毫改變不了政治乃是權力的較量和現實利益的交易所達到暫時的平衡,這也是政治言詞背後掩蓋不了的真相。所謂政治正確則隨著這短暫的平衡的打破而時過境遷,再立新的標準。文學介入政治的結果只能是文學爲政治效勞。再說,這現實的政治無非是政黨的政治,何曾見到能由作家來掌控的政治?作家從政,不成爲政治的點綴便成爲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這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西方和東方、歐洲和亞洲,都屢見不鮮,就不用細說了。
在極權政治的統治下,這種敢於面對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學從來受到打壓、查禁和封殺。即使前共産黨集權的國家如今也對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開放,這樣的文學並沒有就此解脫政治的審查,而且還落入市場的機制,可說是更加艱難。在民主政治下,政治權力雖然不直接監控文學,但所謂政治正確卻通過意識形態牽制文學。作家倒是可聽可不聽,然而,自由卻從來不是免費賜予的,是選擇自由還是選擇市場, 對作家仍然是嚴峻的考驗。一個作家要是既非左派,又非右派,獨立不移的表述,也得耐得住寂寞。
文學要超越政治,又不屈從市場而獨立,在當今社會可說是相當艱難。文學也不可避免從社會生活中日益邊緣化。文學不僅從新聞媒體中退出,且已不再受到大衆的關注。然而,我們要討論的正是這種不爲政治服務,又不屈從市場消費,面對人的生存困境獨立自主的文學。
這種文學超越政治的功利,卻並不迴避政治,不介入政治權力的爭鬥而抽身靜觀,不做簡單的是非和倫理的判斷。再說,現今這時代是非善惡的判斷早已由種種政治正確所取代。各個黨派都設立一番以維護自身的現實利益爲標準的政治正確,並且隨時調整,各說各有理,而且總也有理。作家當然不必跟隨這種政治風向,而這種政黨政治的晴雨表隨權力鬥爭演變,今是而昨非,這種短淺的價值觀往往等不到一部長篇大作寫完便已時過境遷。作家並非記者,新聞有新聞的價值,又當別論,而這種不進入媒體的文學自然得由作家去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
對作家而言,真實與否才是文學固有的價值判斷。作品是否揭示了人生的真相,即使人物是虛構的,而人物的境遇與感受是否令讀者信服,真實與否的這種價值判斷因而又並非是作家任意確立的,而是不言而喻,建立在人性上人人相通的共識,自然也超越現實功利,同樣也超越時代,由人類長期形成而且可以世代相傳的良知所確認。
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注入的這種真情實感首先來自作家對人世的認識,是否洞察人生百態和人世的艱難。這裡首先還不取決於才能,關鍵在於作家是否真誠面對他的創作,恰恰要排除現實功利的考慮,切實寫出作家真實的感受和認知,因而真誠與真實便成了文學所要求的獨特的倫理與價值觀。
作家倘若確認文學的這種倫理與價值觀,也就百無禁忌,贏得精神上的獨立和充分的自由,既超越政治,也超越爲政治提供理由充足律的意識形態。
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是一個意識形態氾濫的時代,意識形態取代了以往的宗教,製造了一個又一個革命的現代神話,從共産主義到民族主義,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革命,也包括革命文學和文學的革命,以各種各樣的模式來打造文學,把文學變成意識形態的解說,以革命的宣傳來代替道德的說教。隨著這些革命一個個的蛻變,這種烏托邦和新人、新社會的神話如今已紛紛破滅,這種宣揚群衆暴力,鼓吹革命戰爭,歌頌革命領袖,爲革命黨高唱贊歌的作品如今都成了廢紙,也無人再翻閱。然而,以批判資本主義爲前提的這種意識形態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到毛主義,陰影卻並未消散,仍然時不時左右人們的思想,影響人對世界做出清醒的認識。
文學要認知這真實的世界,不僅要超越政治功利,還需要從意識形態的思想模式中解脫出來。以一個預設的烏托邦來裁決現存的社會,由此進行的社會批判並沒有隨同共産主義革命而終結,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卻通行無阻,前共産國家如今較之西方老資本主義國家對金錢的追逐還更爲狂熱。世界未必日益走向進步,這種社會進化論與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提供的是否就是真理,也大可懷疑。
人類究竟向何處去?這樣的問題意識形態解答不了,而哲學的思辨恐怕也同樣無能爲力。文學並不企圖給世界做出一個完備的解說,這也正是作家同哲學家的區別。當哲學家努力建構一個盡可能周全的對世界的解說,作家卻只描述永遠也不完備的世界。哲學家精心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作家卻面對活生生的人世,努力給予一個審美的呈現。
如果說真實是文學作品最基本的價值判斷,而審美便是作家賦予作品的主觀的情感的判斷,以取代政治是非或倫理的善惡判斷。作家不裁決人生,也不企圖改造世界,且不說無能爲力,改造不了。然而,作家對他筆下的人物給予某種審美的判斷,悲劇或喜劇,或亦悲亦喜,或滑稽,或怪誕,或荒謬。作家對他的人物的感情盡在其中,這種判斷如此有力,而且永遠伴隨人物,世世代代如此,只要這作品日後還值得再讀的話,並不隨政治是非和社會習俗的變遷而有所改變。
文學超越政治,也超越意識形態,自有文學固有的價值和獨特的審美判斷。這也是文學自主而獨立存在的理由,而且從來如此。文學介入政治並依附政治,乃至於從屬政治,不過是二十世紀流行的一種時代病,從革命文學鬧到文學革命,再弄成黨派的文學,也是二十世紀那種特定的意識形態的産物。從歐洲的列寧主義所謂文學的黨性原則,演變成亞洲的毛澤東的文藝爲工農兵服務,把文學弄成無産階級專政機器上的螺絲釘,而作家則弄成黨的宣傳員。
這種意識形態的根據也來自馬克思主義,一旦把人的本質歸結爲社會關係的總和,而階級關係便決定人的社會地位。人在現代社會也即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也就成了政治生物。而政治又是社會關係的集中表現。革命被認爲是推動歷史的火車頭,文學介入政治,呼喚革命也就理所當然。批判資本主義則是建構這種意識形態的前提,文學納入意識形態,也就成了批判的武器。
經過幾代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精心建構的這種意識形態,隨同共産主義革命的終結,如今只剩下一個空洞的邏輯構架,並不提供對現實社會和人的認知。其後繼者的不斷革命,也即所謂顛覆,不僅絲毫動搖不了現今的社會結構,相反得化解到文化消費的市場中去。顛覆只是一種修辭的策略,用語義的解析來消解意義。這種智能的遊戲有時乾脆變成作秀,在當代藝術和後現代主義的言說中也一再重複,到令人生厭的地步。
文學不預設前提,既不企圖建構烏托邦,也不以社會批判爲使命。文學當然關注社會,乃至於種種社會問題,然而,文學並非社會學,關注的是社會中的人,回到人,回到人性,回到人性的複雜,回到人的真實處境,才是文學的宗旨。
帶有革命和顛覆標記的二十世紀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是否也該結束了?這種時代性的標記如果納入賴以建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自然不可能永存,較之人性也只是膚淺的標籤。相對不變的倒還是人性,既不可能改造,也異化不了。這也正是文學不變的主題,人性的複雜與幽深同樣也難以窮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