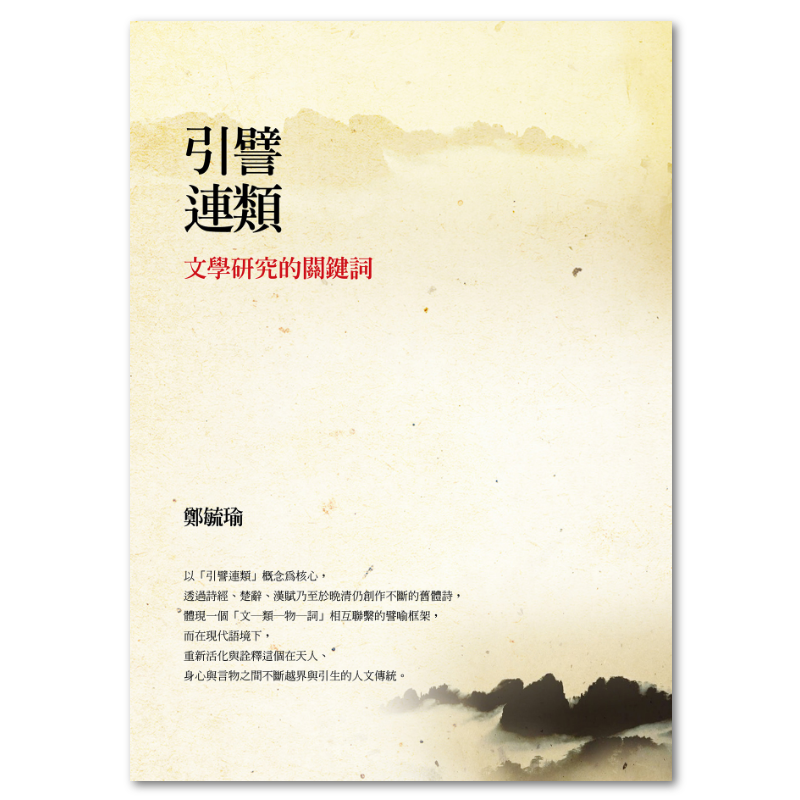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
出版日期:2012-09-06
作者:鄭毓瑜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344
開數:25開(21×14.8cm)
EAN:9789570840476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本書以上古以來極為重要的「引譬連類」這個概念為核心,
透過詩經、楚辭、漢賦乃至於晚清仍創作不斷的舊體詩,
體現一個「文─類─物─詞」相互聯繫的譬喻框架,而在現代語境下,
重新活化與詮釋這個在天人、身心與言物之間不斷越界與引生的人文傳統。
鄭毓瑜教授的《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探討傳統抒情詩學「引譬連類」的特徵和在文學、文化史中深遠的影響,藉著「引譬連類」的研究,再次提醒中國「文」學渾厚綿延的體系:記號──樣式──文飾──文化──學問──著作──文學。她尤其強調「情」與「物」兩者之間的交錯關係,從體氣到感通,從興發到格物,千絲萬縷,相互融成。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以「文」「明」發端,為「譬類」世界追溯其建構的最根源;繼而詳細論述中國上古書寫中包含身/心、言(文)/物的跨類連繫,以及言詞、句式與段落組塊的重複圖示式,以說明兩個甚或多元類域間,如何跨越或相互貫通的蹤跡;再者,透過「替代」與「類推」,來呈現上古文學傳統如何在「比興對應」以及「類聚輻輳」上交互編織,從而被認定、評述,而為後代所謂「文學(史)」、「文類」以及「文學評論」等建構出關鍵性的第一步;最後,以「類物(或類應)」體系作為古典詩文最具交集性而得以超越時間的「物」背景,並選取晚清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為例,由其中反覆牽引與融合的傳統神話、月令物候與政治象徵,說明傳統並不專屬於「古代」,而往往具有對應處境的「現代」意義;同時,正是由於典故成詞所在的認知或思考框架也進行了「重複」之外的「重設」,基於古典類應體系的舊體詩因此竟也可以被挪借翻轉而為新世界代言。
本書以六章專論作為六種探討的門徑。第一章討論「體氣」與「抒情」,指出抒情的修辭功能會意形聲,與身體鬱悶或舒緩、充盈或匱乏形成微妙的震蕩。其他各章更討論諷誦的愉悅、勸誡、乃至醫療功能;《詩經》以降的「重複短語」所投射的風土地理經驗與延伸譬喻;「替代」與「類推」所置換排比、堆疊輻輳而成的歷史、倫理關係網絡;「類」與「物」構造的知識論。本書的第六章則以黃遵憲詩歌為例,討論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援用、變化「舊詩語」以為理解甚至掌握「新世界」的方法。從抒情傳統的兩端──遠古與近代,本書勾勒千百年來「引譬連類」如何在身體、文化、知識等層次,不斷重塑也延伸讀者感時觀物的現象。
作者:鄭毓瑜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並擔任國科會中文學門召集人。曾任美國傅爾布萊特計畫訪問學人、哈佛大學訪問學人、日本京都大學訪問學人、捷克查理大學客座教授等,並曾獲國科會研究傑出獎、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畫補助以及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獎。著有《六朝文氣論探究》、《六朝情境美學》、《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等專書,及相關期刊論文數十種。
序/詩與物──《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王德威
前言
導論 「文」與「明」──從「天文」與「人文」的類比談起
第一章 「體氣」與「抒情」說
第二章 諷誦與嗜欲體驗的傳譯
第三章 重複短語與風土譬喻
第四章 替代與類推
第五章 類與物
第六章 舊詩語與新世界
參考書目
序(節錄) 詩與物──《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王德威
「抒情傳統」是台灣漢學界對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的重要貢獻。1958年,任教美國的陳世驤教授在台灣大學講授詩歌,重新介紹抒情觀念,以後十餘年更繼之以重要論文多篇。到了1971年,陳教授總論研究所成,指出中國早期文學「詩意創造衝動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從本源、性格、和含蘊上看來都是抒情的」。中國文學精髓無他,就是「抒情傳統。」
陳世驤教授的觀點日後有同在美國的高友工教授回應。兩人方法雖有不同,但對抒情信念都是一往情深。70年代末高教授來台講學,啟發一輩青年學者;1985年更提出「抒情美典」觀念,視野擴及文學以外,包括音樂、書法、文人繪畫等等。抒情與中國人文藝術精神的互動,因此更見豐富魅力。
由陳、高兩位教授所引領的「抒情傳統」研究從80年代起在台灣開花結果。柯慶明、呂正惠、顏崑陽等教授梳理抒情源流,蔡英俊、張淑香、廖棟樑、龔鵬程等教授思考,甚至辨難抒情理念,僅是其中佼佼者。香港的陳國球教授、新加坡的蕭馳教授也相與呼應,形成龐大脈絡,影響至今更及於現代文學研究。
鄭毓瑜教授的治學成就必須置於以這樣的抒情傳統脈絡裡,才能顯出意義。她早期的六朝「文氣論」、「情境美學」探究,到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等作,已經展現端正大方的研究氣度。而在《文本風景》(2005)裡,鄭教授的眼界陡然開放,屢屢給予讀者驚喜。這本論文集以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切入抒情傳統研究,無論是對中古城市作為一種興亡的景觀現場,地方風土與詩情史識的互動,身體與自然所滋生的情感、知識體系,都有與眾不同的看法。鄭教授認為抒情之為「物」,不必局限在一般感時傷逝的窠臼裡,而是蘊含綿密的感官、地理、思想的編碼體系,由此展演的詩歌形式,曲折幽深,才能真正體現「抒情傳統」的博大。
鄭教授的新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即是據此加以延伸的系統化研究。這本專著探討傳統抒情詩學「引譬連類」的特徵和在文學、文化史中深遠的影響。顧名思義,「引譬連類」指向古典詩歌中所表達的關聯式思考的傾向和實踐。「引譬」借此喻彼,「連類」連鎖引類,都是啟動詩歌想像的修辭方式。鄭教授指出「引譬連類」的淵源來自中國詩學的「比興」正宗:西漢孔安國即將「興」釋為「引譬連類」;邢昺疏曰:
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
而最為我們所熟悉的解釋出自《文心雕龍》:
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劉勰認為詩與物相互感動,不僅帶來心身體氣的交流匯聚,更與萬象形成婉轉應和的關聯。而詩人出入感物連類的體系,發情采為辭章,自然占有關鍵位置。
識者或認為這樣的觀點不外傳統詩學由物色而情動、由情動而辭發的演繹。但這正是鄭教授思辨的起點。在她看來,情與詩與物的關係在中國的語境裡如此繁複綿密,我們的討論因此毋須局限於感物/感悟的詮釋模式。「情」在語源學的流變裡不僅指的是七情六欲的情,也是情實和情理的情,更是「道出於情」(《郭店楚簡》)的情。如此,抒情傳統的格局豁然開朗。
本書的關鍵詞「引譬連類」一般多以修辭法則視之,鄭教授則別有所見。她強調修辭作為物象的一部分,由引譬連類所接引、衍生、創造、應用的過程也可以及於其他生命層面,包括感官體氣的調和、地文氣候的判別、政治外交的辭令、醫療診治的方法、國族意識的表彰、哲學思考的模式等。究其極,「引譬連類」形成知識體系,也同時由這樣的知識體系所帶動。由感知到經驗,由常識到玄思,鄭教授認為「引譬連類」不妨可以作為中國傳統認識論的一種起源。
這是視野相當龐大的界說,所引發的豐富問題有待我們持續思考。就此書所及,鄭教授以六章專論作為六種探討的門徑。第一章討論「體氣」與「抒情」,承襲《文本風景》已經提出的身體與詩學討論,指出抒情的修辭功能會意形聲,與身體鬱悶或舒緩、充盈或匱乏形成微妙的震盪。所謂「發憤而抒情」(《九章‧惜誦》),此之謂也。據此,鄭教授其他各章更討論諷誦的愉悅、勸誡、乃至醫療功能;《詩經》以降的「重複短語」所投射的風土地理經驗與延伸譬喻;「替代」與「類推」所置換排比、堆疊輻輳而成的歷史、倫理關係網絡;「類」與「物」構造的知識論。本書的第六章則以黃遵憲詩歌為例,討論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援用、變化「舊詩語」以為理解甚至掌握「新世界」的方法。如此,從抒情傳統的兩端──遠古與近代,本書勾勒千百年來「引譬連類」如何在身體、文化、知識等層次,不斷重塑也延伸我們感時觀物的現象。
由於所學有限,我其實不足以評點鄭教授的新著。但既然「抒情傳統」出自現代對古典的發現甚至發明,我們或許得以從比較文學角度,再思「引譬連類」的詩學意義。最明顯的例子是俄國形式主義大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對詩歌語義學的研究。雅氏認為語言表意過程中,選擇軸(selection)和組合軸(combination)──或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y)──的對立,組合為人類語言兩種基本運作方式。詩歌是對這樣的對立軸線精密的創造,不僅在隱喻的選擇軸顯示對等原則,而且在轉喻的組合軸上如語音、節奏、句法等也要顯示對等原則,從而在隱喻和轉喻雙軸上形成相似、對稱、平行等關係。雅氏因有名言:「詩學功能把對等原則從選擇軸上投射到組和軸上。對等被提升為句段的構成方法。」
雅各布森的影響深遠;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結構人類學,巴特(Roland Barthes)的批判符號學都有脈絡可尋,七○年代高友工、梅祖麟教授對唐詩的意象研究也曾點明師承。乍看之下,雅各布森的隱喻/選擇與轉喻/組合軸系統與「引譬連類」有相似之處,都著重符號類比下的意義衍伸。但雅各布森一脈學說堅持科學式抽象結構,以之作為放諸四海的規則,而鄭教授藉「引譬連類」則強調在不同的歷史語境裡,語言修辭的套數如何與生存體現相與為用,迴旋輻輳,「聯類不窮」。雅各布森最知名的語言基型(parole)和言說表現(langue)的二分法因此不存在抒情語境裡,因為他設想的結構萬變不離其宗,而中國詩學裡的「興」所啟動的綿延脈絡首先就不能存在。
前言
李約瑟由先秦兩漢陰陽五行的思想,認為中國古人有一種「關聯式的思考」(correlative thinking),並認為在關聯式思考中,事物是藉感應而相互影響,並非由於外在的因果推求;而透過類應所形成的系統,萬物密切結合在一起而構成自然有機的和諧世界。雖然李約瑟認為古代中國透過「關聯式的思考」所形成的有機整合世界,類似原始科學的論述,但是,如馮耀明也已經提出辯駁,認為李約瑟由漢代思想所歸納出的天人之間的「神祕的共鳴」(mysterious resonance),其實是由「自然主義的事實陳述」與「基於人文觀點而作的規範性描述」所混合的宇宙論,既不是經驗層面、也不是在邏輯層面上進行,更不是基於某種成熟的科學觀念。換言之,這種「關聯式的思考」並不是專為邏輯推理而設,當然也不能片面要求這種思考模式會促進某種科學或哲學化的論述模式的產生。仔細檢閱上古相關文獻,會發現所謂「引譬連類」(或「引譬援類」)可以說是總括自先秦逐步發展而來的跨越個別物種、由內質到外形可以拓展無數連類可能性的說解宇宙、建構世界的方式;它隱然是一套生活知識或者說是已成共識的框架,時時牽引著個我的種種身心行動。「引譬援類」像是四通八達的通導脈絡,迅速地串連起透過經驗、文獻所累積的各種時物事件;前代的傳抄被視為知識性的前提,理所當然地接受並作為據點,繼續進行各種或顯或隱的關係延伸。換言之,這個「連類」模式因此不是邏輯論辯的程式,而是理解活動進行的基本框架,憑藉這個框架,觸動或開啟我們的視野,導引深遠的連結,同時讓傳譯的語言文字如織錦般煥發顯現,並且引領身體行動。透過這個反覆的理解框架,我們累積知識,同時也累積身體實踐的體驗,進而開發洞見;我們愈來愈純熟地進行「想成」、「視如」的概念理解活動,透過會聚與親附,我們跨越表象差異所形成的類別界線,在不斷越界中去鑽探共存共感的底層。
換言之,這些關於「引譬連類」的論述,最根本的關鍵顯然就在於「越界」或「跨類」(cross categorical boundary),單就文學研究來說,如果置放回「引譬連類」的思考(理解)背景中,像是物/我、身/心、言/意、文/情等議題,是否可以獲得比較好的詮釋?比如:在文學經典中這些「物類」、「事類」系統究竟如何形成,而這些分類系統又是如何連繫彼此而成為有意義的關係體?其次,這些連類關係的形成與個我的身體實踐如何相關,尤其在什麼樣的感知或行動狀態下,這完整的連類意義會被「體現」?再者,這些透過分類、連類所形成的關於事、物並與人情感知相應的共識體系,如何被傳移摹寫,尤其是透過什麼樣的表現技法或體類規模,可以保證這個共識體系的在場?而這些問題最根本的關鍵其實是如何成類與連類。提到「類」,很容易讓人想到類書,但其實在中國第一部類書《皇覽》出現之前,就已經有對於種種知識的分類,比如《爾雅》對於語詞的訓解分為十九篇,「釋詁」、「釋言」之外,還包括像是「釋宮」、「釋器」、「釋天」、「釋地」等,可以說是針對當時語詞使用對象的分類,如同生活世界的「百科名詞」,又如班固(在劉歆《七略》的基礎上)《漢書》〈藝文志〉中將書籍分為「六藝」、「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同時將單篇詩、賦輯為「詩賦」略,關於「賦」又區分出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及雜賦四類,似乎與曹魏以後文體論的出現有不可忽視的關聯。這透過語詞訓解或書篇輯錄所進行的分類,說明了分類可以不僅限於史家、小學家或目錄學者的專業目的,分類所發揮的作用更根本是在於建立知識體系,甚至成為生活實踐之必要準則,也因此,關於文學的研究同樣不可能脫離這分類系統所建構的關係世界。
方師鐸的《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一書就是當代討論文學與類書關係的重要著作,其中最著力的兩點是:其一,將總集也納入類書領域,讓「類文」的《文選》、《文苑英華》等也成為類書的一部分,其二:由辭彙學的角度來看辭賦,將辭賦視為類書的前身,這兩點凸顯了「類事(物)」或「類文」不只是單純的有助於隸事或論述文體,文學領域中的類別區分,也都應歸屬於認知世界的方式之一,換言之,類分事物、詞語或文體,同時也可以說是架構某種看待世界的模式。不過,如果要藉助類書資料來詮釋文學作品,其實還有更大的困難,因為類書著重在類分,對於如何「連類」並不是考量重點,除了很明顯地自唐代以後大抵建立了「天──地──人──事──物」的次序,對於類與類之間或每一類所包含的子目之間究竟具有何種關聯性,似乎並無法從類書已有的輯錄狀況得到具體說明。除了可以翻查已有的名物注釋,面對文本中往往是多樣事物的組合,研究者更重要的工作可能還在於探索事(物)類之間的關聯性與組合後的意趣引生。換言之,當焦點放在文本,而不只是個別事物的孤立分判,事(物)類如何被應用、詮釋與取捨、再製,以及這名物連類的效果究竟如何開發文學詮釋的新視域,成為更迫切需要探索的焦點。
以《詩經》為例,針對詩經名物的詮釋其實早已成就詩經研究中「博物學」的一支,三國時人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早的代表作,到了清代甚至出現如日人岡元鳳的《毛詩品物圖考》,圖文並置,而現代學者利用植物學、動物學等新知識,也仍有如《詩經中的經濟植物》等著作不斷出現。對於名物的古今命名、物理特性或相關記載加以疏理,這當然是理解詩經本文的必要基礎,然而也有不少學者指出,這種詩經博物學的研究,往往只在「多識」這方面著力,卻忽略了「詩意」的推求,也就是「詩」與「物」仍無法相交融。這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如果回到作為解詩要則的「比興」來說,顏崑陽認為「比興本是一種非常複雜的觀念,……(而)是古代諸多文士,對宇宙、作者、讀者、作品諸因素互涉的人文活動經驗,所產生的體物與言說」,亦即,「比興」本來就不僅止於名物訓解,而可能是「人文活動」的全面圖式。西漢孔安國直接釋「興」為「引譬連類」,而邢昺疏曰:
詩可以興者也,……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
「引譬連類」,其實就是比類、比譬,邢昺直接將「比興」連言,正解釋了孔安國所謂「引譬連類」也是視「興」如「比」。而孔穎達釋〈詩大序〉「六義」之「興」,就融合了孔安國的說法:
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
由反覆出現的所謂「連類」、「引類」,說明了比喻或譬喻其實是兩種「類」別之間的連繫,並非兩個孤立事物的比擬,換言之,「比興」或者稱為「譬類」,其實是關於「成套的」譬喻,任何「比興」的說解其實是由整個系統去決定它的含意。現有的關於名物譬比的說解往往太近似字書或辭書的本義解釋,或僅針對單篇詩的語境進行說解,因此難以明瞭當時的文本環境中究竟如何理解與交互應用這些語詞所指涉的概念結構。
既然由「譬類」──也就是「成套的」譬喻出發,這顯然就不是個別「物與我」或「情(事)與景(象)」的對應問題,而是在一個「概念系統」之中如何被認定,或是兩個「概念系統」之間,如何相互理解的問題。而西方晚近由雷可夫(George Lakoff)和詹森(Mark Johnson)提出的「概念譬喻」(conceptual metaphor)的說法,也許可以有助於我們對於所謂「成套譬喻」的解析。雷可夫和詹森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這本書裡曾以空間譬喻為例,說明每一個空間譬喻都有一個內部系統(internal systematicity),如「我情緒高昂」、「精神大振」都源出於「快樂是上(up)」這個概念系統,而且這譬喻概念界定一個整體相合的系統(defines a coherent system);而人的完整理解活動其實常常透過兩個以上的概念譬喻來完成(如來源域與目標域),換言之,人不但必須掌握各個譬喻系統內部的相合性,還必須掌握兩個以上的譬喻系統的相合性。比如,「在這點上,我們的爭辯並無多少內容」,其實就結合了「爭辯是旅行」與「爭辯是容器」兩個譬喻,而對於所爭辯的範圍與內容進行檢討。雷可夫和詹森的「概念譬喻」雖然主要是以日常用語為討論焦點,與文學文本之間顯然有距離,但是,文學中的「譬類」如果可以由兩個以上的譬喻系統來理解,並嘗試由來源域(如旅行、容器、食物)去追索目標域(如愛情、爭辯、思想)的譬喻意含,不但可以避免孤立化、受限於單篇語境的意象解釋,也可以得出更根本、具體的單一或多重譬喻體系的實際經驗與運用原則。
在雷可夫和詹森的理論中,認為譬喻的使用常常是透過一個比較熟悉的類別(categorization)去理解一個較難理解的類別,最明顯的如擬人法,而人的身體經驗又成為許多譬喻理解的基礎。這也許可以進一步解決許多抽象感知的詮釋問題,比如透過身體行動的進出、上下所牽引的空間感知,來應照季節的來去(如春天的腳步近了)或心情的哀樂起伏。個人過去針對節氣感的研究也曾經注意到,許多「感物」的悲秋詩作,所欲傳達的也許就是時氣與體氣交響的話語,以身體為核心的情緒震顫,同樣被漣漪一般的傳響反過來層層環繞與籠罩。「這讓情感成為身體可以展現,同時也是可以具體感受到的空間性的力量。這也許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漢末以來的『秋』詩有那麼多的動作姿態,除了強調外在景物的影響力,進一步來說,……這當中充滿著無距離、方位與寬窄限制的相互牽引,正是這牽引關係構成了無限擴散的情緒張力網,起坐、俯仰、出還的姿態是內在的發動,同時也是風物外力侵進、圍裹的承受與抵拒」,換言之,像是「徘徊」、「徬徨」、「躑躅」等語詞在情緒表達上其實明顯奠基於身體行動。如此,藉助概念譬喻所源出的身體經驗,對於某種情感的詮釋也許就可以由融合實體與抽象的譬喻體系來說明,比如在《詩經》裡,形容憂傷的重言(疊字)多達二十種,《爾雅》〈釋訓〉曾經條列其中十個而只是總說為「憂也」,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其中如何透過度量(多、滿)、定位(不定、搖盪)等有關於容器與身體行動的經驗,來應照「憂心(程度)如容量升降」或「憂心(狀態)如行動不定」,那麼面對這一系列相關於憂心的詞語,將可以透過相應的實體經驗來理解。
內文選摘(節錄)
導論 「文」與「明」──從「天文」與「人文」的類比談起
「人文」與「天文」的類比
《周易》〈賁〉卦下〈彖〉傳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概是「人文」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劉若愚認為這是「文學顯示自然之道」的概念之起源,而這個句子將「天文」與「人文」作為「類比」,這一個類比,後來被用於自然現象與文學之間,「認為是道的兩種平行顯示」。從《易傳》中,劉若愚因此整理出包括一系列光譜的「文」的意義:
記號──樣式──文飾──文化──學問──著作──文學
並且徵引摯虞〈文章流別志論〉、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以及蕭統〈文選序〉等,或是將文學的淵源追溯到宇宙開端,或者認為文學就是宇宙原理之顯示,魏晉南朝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理論中「形上」概念的「全盛時期」。不過,以劉勰〈原道〉篇為例,劉若愚認為劉勰是利用了與「其他形式或文飾間的類比」來談「文學」,換言之,劉若愚以許慎所謂「錯畫」為「文」──圖樣、表象或修飾,作為現在我們所理解的「文學」、「文章」的原始意義。但是問題也就在這裡,表象的圖案或文飾也許是起點,卻很難以完整說明是如何發展到所謂的「文學」,「文學」與「圖案」是形成了類比,卻沒有說明如何在兩個意指間順利越界。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引用劉若愚的說法來解釋《文心雕龍》〈原道〉篇,不過,針對〈原道〉篇並列天地到動、植物乃至於人的各種「文」,宇文教授認為這是一系列潛在秩序的外顯,每一種自然物象都有其合宜的「文」。但是,人並不是直接展現在物質形體上,而是透過人最重要的本質──也就是「心」來展現成為「文學」(書寫)的形式。宇文所安強調,這「心」其實是在「宇宙的身體」中運作(man serves the function of mind in the cosmic body),不同於西方的模仿說,人心的活動不是為了再現外在世界,反而就是完成各種「文」(從天地、動植到人)的圓滿顯現的最後一步。針對完成「文」的終極顯現,宇文教授因此說到:
書寫的「文(字)」不是符號,而是將一切圖式化,這因此沒有主宰權的競爭關係。每一個層次的「文」,既屬於宇宙、也屬於詩,並且妥適地存在於相關的類域中,而「詩」是最後的外顯形式,也是完足的階段。
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將「文學」書寫視為「圖式化」過程(schematization),可以連結各種不同類域(correlative realm)的物象,而發動連類作用;這個「類」(natural category),並非出自有意的比喻或比附,而是因為彼此的組成元素基本上屬於同一類(of the same kind)。宇文所安也引用〈物色〉篇的段落,而談到中國文學中的「連類」作用(categorical association),並說明連類作用使每件事物都是整體的一部分,比如〈物色〉篇提及的四時感物,讓人與自然都處在一個共感的循環中。宇文教授是藉助劉勰的看法,來處理中西比較文學的問題,尤其透過對於杜甫與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詩作的分析,說明東西雙方讀詩態度的差異。對西方讀者而言,詩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封閉符號系統,是虛構的;但是對於杜詩的讀者而言,詩不是虛構的,而是如其所述的真實,是在一個歷史時刻的遭遇、經驗,以及對世界的回應,亦即中國詩歌的讀者,很自動地將許多甚至是相反的事物,都視作在一個相互關聯的架構中彼此應和(they echo in correlative frames of referrence)。
顯然,透過「天地之心」(在宇宙之中)來談「圖式化」或「連類」作用,一方面可以落實所謂「形上」概念,使之不成為虛化的話頭,另一方面,似乎也揭示出一個中國文學的龐大背景,那同時也是中國「人文」學研究必須正視的連類的整體。關於連類,宇文教授簡單提及是「同類」關係,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在中國人文學中最基本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類推」,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是這種類推的模式賦予世界萬象以意義,同時建構宇宙合諧的秩序;如果依照宇文教授的說法,「文」既屬於宇宙、也屬於詩,那麼,詩與宇宙同樣都在類推所建構的意義世界裡。這基本上會觸及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其一,在後代被認為具有「個別性」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個體「心」、「志」,如何說是參與一種集體的類推運作,宇文教授所謂在「宇宙身體中」的「人心」是否可以有進一步的解釋?其二,這樣一種文學中的類推運作,如何就是「成為世界」的最後一步(the last phase of the world’s coming-to-be),「心之文」或「言之文」又如何就是「物」與「意」的在場,而能參與宇宙大化,並與天文相比並?很明顯這都牽涉「跨類」(cross category)「越界」(cross boundary)的問題,在「宇宙之身」與「個體心志」間的聯結是什麼?而在「心(志、情、意)」與「言」、「物」之間又是什麼樣的通道?
「宇宙──身體」之「文」:氣感與連類
最先引發我們注意的是劉勰在〈物色〉篇所說的: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劉勰總是同時提舉兩個面向,其一,「隨物宛轉」與「與心徘徊」,這牽涉心與物;其二,「寫氣圖貌、屬采附聲」與「隨物宛轉、與心徘徊」,則關涉言與意、詞與物的層次。而所謂「宛轉」、「徘徊」則描述了兩兩界域之間相互往來、彼此周旋的情狀,當然不是直接、明確的對應指涉。更值得注意當然是「感物」與「連類」,既稱「感」,則「感物」當屬心的活動(「沉吟視聽之區」),但這活動的作用又是在「連類」──連繫相關物類(「流連萬象之際」),換言之,「感物」引發「連類」,而「連類」就是「感物」的內容與體現。而「人」在這個類推體系中是唯一能「感知」同時又「應顯」的樞紐;人身能夠接收來自天地萬物的訊息(包括陰陽慘舒、四時動物、日影短長),同時又將這訊息反應給原本發出訊息的世界(寒暖、舒躁、淒遲)。就「文」的共同成效──「顯示」(manifestation)作用而言,宇文教授談到這連類作用最後一環,也就是語文的書寫,然而其實我們不能不先注意到這當中最關鍵的一環,正是作為宇宙類推中心的「人」。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詞與物》(The Order of Things)這本書中,討論到四種表現相似性的模式(similitude),其中一種就是「類推」(analogy),傅柯認為「類推」的力量巨大,只要細微關聯性,就可以從一個單點連結出無限的關係,而成為人與宇宙萬物相互靠近的場所,他也提到「人」是這個類推世界特別幸運的焦點:
(它)充滿了類推(所有類推都可由其中尋得必要觀點),而且所有類推通過這個點的時候,即便是有所轉折,也不會失去本身的力量。……這個點就是人,……他還是所有類推關係的支撐點,所以我們又在一系列關於人類、動物、所居住的地球之類推中發現這些絲毫無損的相似性:他的肌肉是土塊,他的骨頭是岩石,他的血管是大河,……人的身體總有可能是一半的世界全圖。
這說法中的人身與宇宙的關係已經不是模仿或複製,兩者之間沒有因為類別差異所產生的隔閡,也就是沒有以誰為主所分別出的「客體」或「外在」,人感應出世界,也身處世界之中;更重要的是,世界的整體於是在人的個體上顯現,而出自個體身心的文學就是整體世界的舞臺。這是彼此相互包含與顯現的「個人──整體」,「人身」不只是如傅柯所說可能占有「一半的世界全圖」,當他們相互成為對方,嚴格說來,根本沒有「另一半」。
在這樣的「連類」角度下,我們也許可以想像,在「宇宙──身體」中其實沒有以物質形軀出現或者僅僅以封閉在內的心志所呈現的「人」,反而是瀰漫擴張、彼此穿通而無所窒礙的「氣態」存在,亦即如果我們要談到屬於宇宙也屬於人之身心的「文」,我們首先就不能忽略這樣一種「(體)氣」的顯示。在先秦到漢代的文獻裡,比如《左傳》、《禮記》〈樂記〉、《黃帝內經》以及辭賦作品中,其實很容易發現關於如何療救、養護「體氣」的種種說法,出現在對於君王、太子的勸諫上,也出現在自我抒懷上,這麼普遍應用的現象說明了「體氣」是一個思想家、醫家或君侯身邊各家道術的進言者所共同關注的話題,而針對這話題的種種說法或評論同時也不停地累積成更大的共識集合。換言之,任何有關「體氣」的論述,都不應該被縮小解釋為只是出乎個別心志或才智的修辭策略或說服技巧;而是自先秦以來,已經存在或被認同的一種熟悉的「『體』驗」,就像學者栗山茂久(Kuriyama Shigehisa)這個比喻:人身表面如同具有個別「通氣孔」(orifices),而成為宇宙的、地域的以及個人的風氣的匯聚之處。
這個彷如「通氣孔」的身體經驗,可以促進我們對於相關文學書寫提出更有效地詮釋,最明顯的例子是辭賦作品。宋玉的〈風賦〉、枚乘的〈七發〉明顯承繼《左傳》所謂「節宣其(體)氣」或者《素問》所說「此皆陰陽表裡上下雌雄相輸應也」的看法,諫止或是不免於勸往往就是一體之兩面,個體因此彷彿是個氣流出入的安全閥,因應體外大氣的入侵,從而形成個體內兩股氣流迎應消長所產生的紓放或緊縮的狀態,而正是這些狀態,直接「書寫」了「宇宙──身體」的處境。至於《楚辭》作品中糾結纏繞的悲秋氣息,其實說話者在編織「情緒」的同時,彷彿也被「氣息」所編織;是這些「飄風」、「邪氣」的侵襲所形成的憔悴、於邑、衰老的「病體」之上,愁苦以一種不可遏抑、不容自已的震顫狀態顯示出來。所謂「心踊躍其若湯」、「心沸熱其若湯」或是「氣涫沸其若波」,不但是「心」與「氣」相互詮釋、彼此包含,這「踊躍」、「沸熱」傳導了人與宇宙(物/我)、物質與精神(心/物、身/心)相互感通所形成的內、外在一體的動盪視野。這樣巨幅的詮釋視野,很難在「抒情自我」中完全開展,反而是在「體氣」、「氣感」的主題所形成的集體共識中,可以讓外在於我的宇宙,成為內在於我的一部分,而在如波沸動的體氣中,顯現完整的「宇宙──身體」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