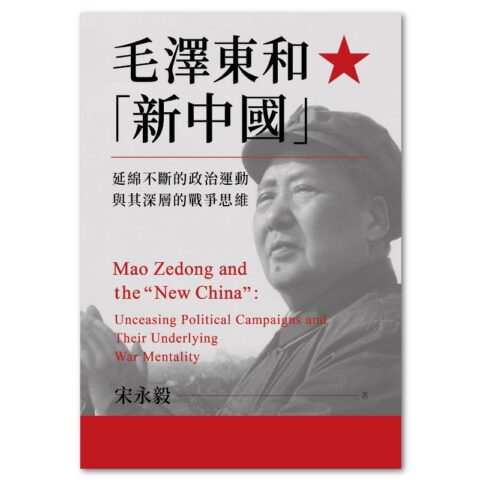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
出版日期:2008-01-28
作者:蕭啟慶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464
開數:18開
EAN:9789570832280
尚有庫存
元代是中國史上最以其世界性及族群文化多元性融合的時代。本書正稿收錄論文九篇,頗能彰顯這個時代的特色和重要性。書中各文主要以宏觀視角,考察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之影響,以及各族群之間的社會文化互動。或對個別蒙古、色目家族的「士人化」現象作深入研究,以修正當今學界所習用的「漢化」概念。按,元代科舉與其他各朝不同,頗能反映當時各族群間政治、社會、文化之互動關係,因而亦是本書的一個重點。
此外附錄論文兩篇︰一篇探討燕京五大漢人家族在遼朝的重要及金元時代的延續,顯示征服王朝與漢人世家的共生關係。另篇論文,則考述元史研究先驅陳垣先生對元史及現代中國史學研究的貢獻。總之,這兩篇論文雖不屬元史研究的範圍,卻對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蕭啟慶
江蘇泰興人。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哈佛大學博士,以蒙元史研究馳譽海內外,著有《西域人與元初政治》、《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元朝史新論》、《內北國而外中國》、《元代族群文化與科舉》、《元代進士輯考》及英文《元代軍事制度》、《蒙元前期名臣傳論》、《劍橋中國史》第六卷(聯合編著)。
序論
第一章 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
第二章 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
第三章 論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漢化與士人化
第四章 元季色目士人的社會網絡:以偰百遼遜青年時代為中心
第五章 元朝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
第六章 元代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
第七章 元朝南人進士分佈與近世區域人才升沉
第八章 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
第九章 元朝的區域軍事分權與政軍合一
附錄一 漢人世家與邊族政權:遼朝燕京地區漢人五大家族
附錄二 推陳出新的史學家陳垣
序論
自大學時代學習遼金元史以來,從事元史研習已四十餘年。在這漫長的過程中,始終被蒙元的時代特色所吸引,因而對這一冷門的學問,鍥而不捨,遂也累積了不少成果。《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是我的第四本論文集。書中各文是過去七年來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
元朝是中國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元史也是一個特殊的研究範疇。元朝是中國近世幾個由北方遊牧民族或半遊牧民族所肇建的征服王朝之一,而且是第一個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元朝又是一個包擁歐亞世界帝國的一部分,當時中外關係之密切、活躍族群之繁多,語言文化之複雜,以及少數民族語文史料及域外記載之豐富,在中國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元代因而可說是中國史上最具世界性及族群文化多元性的時代。本書所收各文應能反映元代的時代特色。
征服王朝的統治對中國近世歷史發展的影響一直是史學界關心而有爭議的問題。本書中〈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及〈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都是探討這一問題的論文。〈歧異與統合〉係以唐宋變革為背景,探討金元等征服王朝是否延宕了中國近世化的進程。此文顯示:「唐宋變革」與「明清變革」之間缺乏聯續性及南方與北方發展的巨大差距的產生確與征服王朝有關。雖然征服王朝統治在文化方面長遠影響較小,但對經濟、社會產生甚大負面後果。金、元統治導致北方經濟、人口的逆退及南北不平衡。在社會方面,金、元統治不僅造成北方中古質素與近世質素並陳的現象,也擴大了南、北區域社會的差異。
中國文化在蒙元統治下確實經歷空前嚴峻的挑戰,卻能克服這些挑戰,浴火重生。〈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自兩方面探討蒙元統治對中國文化的衝擊與影響:一為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衝擊,另一為中原本土文化在在蒙元時代的發展,希望這兩種不同方向的探討能夠顯示元朝在中國文化發展上的地位。本文指出:一方面,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僅有短程的衝擊,而無長遠的影響。草原文化與西方文化(主要是伊斯蘭文化)皆是如此。外來文化不能產生更廣泛影響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征服情勢妨礙漢族人士與外來文化的接觸。第二、宋代以來中原文化本身的「內向」造成士大夫對外來文化的抗拒。本土文化在蒙元統治下的新發展,如道學確立為官學、文人畫的成立與俗文學之提昇,皆與外來文化及蒙元朝廷政策沒有直接關聯,而是宋金時代早已存在的一些趨勢在蒙元特殊政治社會環境中發酵的結果。總之,蒙元統治並未影響中國文化發展的主要方向,元朝滅亡後中國文化大體仍按照原有的軌轍向前發展。
蒙元時代大量的蒙古、色目人徙入中原、江南,與漢人、南人共存共榮,相互涵化。族群間-尤其是征服族群蒙古、準征服族群色目與被征服的漢族(包括漢人與南人)間-的社會文化互動因而構成中國史上有趣的一章,也是元史研究的重要焦點。〈論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漢化與士人化〉、〈元季色目士人的社會網絡:以偰百遼遜青年時代為中心〉皆是探討與族群文化相關的課題。
過去學者往往以「漢化」(sinicization)一辭描述當時蒙古、色目人的大量接受漢文化。〈論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漢化與士人化〉提議以新概念「士人化」(literatization)來探討這一現象。「士人化」與「漢化」的主要差異在於:「漢化」者必須放棄原有族群認同,而與漢族融為一體,而「士人化」的蒙古、色目人雖接受士人文化,卻未必放棄原有的族群認同,甚至選擇性的保留其固有文化。元代中後期不少蒙古、色目人皆是如此。本文選用木華黎、高昌偰氏及唐兀崇喜等三個家族的歷史具體說明當時蒙古、色目人雖已士人化,但未真正漢化。這些家族的成員熟諳士人文化,接受儒家禮教與行為規範,並且與漢族士人在文化與社會兩方面密切互動,但是這些家族既未改採漢姓,而其婚姻亦是以族群差異與政治社會地位為主要考量。上述三家族放棄固有認同而與漢族融為一體是在元亡明興之後。本文「士人化」的概念或亦可應用於中國史上其他征服王朝時代的類似問題之研究。
士人化的概念在〈元季色目士人的社會網絡:以偰百遼遜青年時代為中心〉一文中得到更具体的証實。本文主要根據在韓國新發現的一本詩集—《近思齋逸稿》—,對元季色目士人—偰百遼遜(1319-1360)—青年時代的社會網絡作一較為詳盡的考索。百遼遜出身高昌偰氏。本文顯示:百遼遜所承繼與營造的是一個青年科第士人的社會網絡,與漢族士人差別不大。但是,由於偰氏家族持續與本族聯姻,而且仍然保持畏兀兒式的名字,反映偰氏仍未完全放棄原有之族群認同,若說此一家族在當時已經完全「漢化」,或不盡適合,但稱之為「士人化」,應屬允當。因其交往皆以士人為對象,並且以士人文化為互動基礎。這一篇文章應與我的另一篇論文〈蒙元時代高昌偰氏之仕宦與漢化〉(收入《元朝史新論》,【台北:允晨文化事業公司,1999】,頁243-298)合觀,〈仕宦與漢化〉對偰氏家族的歷史有廣泛的探討。
科舉制度是近世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政治、社會與文化機制,影響極大。元代科舉實行時間短、規模小,但對當時各方面仍然不無影響。我研究元代科舉已逾二十年,一方面重構元代科舉進士錄,另一方面則根據重構的進士錄撰寫論文。進士錄的重構已經完成,各科〈進士輯錄〉已陸續在各學報發表,希望年內結集成書。而本書所收〈元朝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等四篇論文便是進士錄重構的副產品。但是這些論文不是研究科舉制度的本身,而是從進士的家族背景、地域分佈、及在鼎革之際生死與出處的重大扶擇去探討元代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問題。
元朝的科舉制度是當時特殊政治社會結構的忠實反映。 在中國科舉史上,元朝是第一個兼採族群與區域兩種配額以選取進士的朝代。一方面。元朝由於族群等級的考量而制定科舉中的族群配額。蒙古、色目雖然人口甚少,在科舉中卻享有與漢人、南人相等的配額,反映蒙古、色目為備受優遇的兩個族群。另一方面,科舉中的地域配額制度原是為維持考試之公平競爭而又兼顧偏遠落後地區考生而設計,真正開始實行的是元朝。元朝區域配額制厚待北方漢人而壓抑人口眾多、文化發達的南人。因而科舉對各族群之影響大小不一,本組的前三篇論文皆與蒙古、色目、南人進士相關。
〈元朝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係探討蒙古、色目進士的社會流動及其與漢族間的社會、文化互動。本文顯示;多達八成的蒙古、色目進士出身於官宦家族,而來自布衣之家者不過二成。可見科舉制度的主要作用在於為官宦子弟增加一條入仕的途徑,但亦為原來甚為閉鎖的蒙古、色目統治菁英階層注入數量不大,卻甚重要的新血。自族群分佈言之,蒙古各族原有文化水平頗為近似,科舉所產進士的數目亦甚平均。而色目各族所產生進士人數的多寡則與其本族原有文化水平的高低具有密切的關聯。自婚姻關係言之,甚多蒙古、色目進士的家族早己與漢族通婚,而嫁入蒙古、色目家庭的漢族婦女對其子孫的文化取向及登科應舉的動向具有重要影響。總之,從社會觀點來說,大多數進士是蒙古、色目族群中傳統菁英家族的延伸。從文化觀點來說,蒙古、色目進士則是其族群中漢化最深的一群。
〈元代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是以南人(「南人」,乃指南宋舊境居民,包括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及河南行省南部)進士家族為基點,探討元朝在近世士大夫家族發展史上的地位。過去由於對元代士大夫的情況所知不多,論者往往認為元朝是士大夫階層發展史中的斷層,也是此一階層研究史上的「失落聯鎖」。本文以統計及實例証明元朝南人進士出身仕宧家庭者多於布衣家庭,而其祖先具有宋朝仕歷者遠多於曾經出仕元朝者。顯然,元代科舉之採行使甚多南宋士大夫家族得以在政治上復甦。本文又由元亡後改仕明朝的進士及元進士後裔在明朝登第、仕宦兩方面來展示明朝科第仕宦階層與元朝乃至宋朝士大夫階層之連續性。因而元朝的科第之家實為宋、明二代士大夫階層的橋樑。江南士大夫階層顯然具有頗大的穩定性,未因征服王朝的介入而中斷。
〈元朝南人進士分佈與近世區域人才升沉〉係自空間與時間兩個角度考述元朝進士的區域分佈及其歷史意義。本文首先自行政區劃中的省、道、路三級研析元代進士的分佈。自省的層次言之,江浙成績最優,江西次次,湖廣又次之,河南殿後。自道的層次言之,江浙四道表現普遍優異,江西、湖廣各道表現頗有軒輊。自路的層次的分析,更證明江浙各路之優越,江西、湖廣各路之不均衡及河南各路之落後。其次,本文借用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區域經濟社會體系」並兼顧文化、教育因素,希望能為各區域之進士分佈尋求合理的解釋。最後則討論了宋、元與元、明之間的進士分佈的延續與變化,藉以顯示在近世中國人才分佈的趨勢及元朝在其中之地位。從宋、元進士分佈看來,兩代之間領先地區與落後地區大體相同。但在元朝領先地區中,卻呈現出贛昇閩降、浙東穩定發展及吉安、紹興等路在科舉中領先全國的局面。明朝的進士分佈一方面延續元朝的趨勢,另一方面則有浙西、廣東之興起的新發展。總之,在中國科舉人才分佈史上,元朝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宋、元與元、明之間,皆有延續,亦有變化。延續固然是由於各該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所決定,而變化則是由於這些因素的改變所形成,與蒙元統治並無密切的關聯。僅就南方人才分佈言之,蒙元統治的影響顯然不大。
推翻元朝的明朝則為一漢族王朝,元明易代因而具有華夏光復的重大意義。〈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即是以各族進士為中心,探討士人對元明鼎革的各種反應。本文共臚列易代之際的進士共一四四人次,據其抉擇差異分為三型:一、「忠元」型:包括殉國忠義、北歸外奔及守節遺民。比率高達60.4.4%。二、「背元」型:出仕群雄與明朝,比率為31.3%。三、「隱遁」型,乃指前述在元亡之前即已退為「逸民」者,佔8.3%。可見多數進士選擇忠於元朝。這一結果與宋元之際南宋進士對易代的反應相差不大。 自族群差異言之,「忠元」型進士中,四大族群皆各占一定比率。可見殉國或守節是一超越族群藩籬的現象。一方面,不僅不少蒙古、色目進士作出「忠元」的抉擇,甚多漢人,尤其是最受歧視的南人,也為元朝殺身或守節。而在「背元」及「隱遁」型的進士中極少蒙古、色目人,反映這兩族群對元廷具有強烈同舟一命的認同感。以上論述足以顯示:元明易代雖然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由夷入夏」,但真正影響士人對生死與仕隱抉擇的因素是「君臣大義」,而不是「夷夏之辨」。
〈元朝的區域軍事分權與政軍合一:以行院與行省為中心〉的性質與上述各文不同,是一篇探討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的文章。元朝首創行省制度。過去學者對元朝行省之性質及其與中央之權力關係看法頗多歧異。或認為行省是元朝推行中央集權的工具,或主張行省享有甚大權力並且具有甚高主性,是一種地方分權的政治體制。本文自軍權的角度檢視元朝行省的權力問題,指出:元朝的征服情勢及廣大幅員對軍力與軍權的分配有甚大影響。在軍力分佈上,元廷巧妙利用各軍的族群差異來達致內外制衡的效果而未完全襲用漢族王朝時代「內重外輕」的政策。而在軍權分配方面,各行省兼擁政軍二權,表面上看來,元朝政體屬於區域(地方)分權體制,但是行省的軍隊提調權只能在中央的監督下執行中央委付之任務,並不擁有甚大裁量權與自主性。而且由于掌握兵權的行省長官多由出身皇室家臣的蒙古人充任,區域分權所可能造成的威脅更減少。與宋、明等朝相較,元朝行省享有較大權力,可說是區域分權,亦可說是政軍合一。從軍權分配看來,元朝政府實際是透過區域分權來達到控制地方之目的,亦即是看似分權,實則集權。這篇論文固然是我研究元代軍事制度的延伸,但也受了李治安教授《元代行省制度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不少啟發。
元史研究有兩條主軸,一為探討元朝在中國史上的獨特性,一為考察其在中國史上的延續性。前者著重橫向的探討草原傳統及外來文化衝擊所造成的元朝制度與文化上的特色。後者則著重縱向的研析元朝與前後各代之異同及其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地位。過去蒙元史專家往往偏重前者而忽視後者,而一般歷史學者則多跳越元朝,對此一朝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未能深入探討。早年我較為著重上述的第一條主軸,如探討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原因,蒙元軍事制度,西域人的政治角色之類,都是想探究草原傳統對中原歷史的衝擊。近年來我較為重視第二條主軸,本書中多數論文都是如此,而以〈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一文最為典型。當然我也體認到這兩條主軸不可偏廢,因而也想結合兩條主軸而勾勒出蒙元時代在中國歷史及北亞歷史長河中的地位。〈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可說屬於此類。
附錄中兩篇論文雖不屬於蒙元史範疇,卻與蒙元史研究具有關聯。遼朝(907-1125)是中國近世的第一個征服王朝,元朝的先驅。遼、金、元在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皆有甚大連續性。〈漢人世家與邊族政權—以遼朝燕京五大家族為中心—〉以遼朝(907-1125)燕京地區五大漢人家族-玉田韓氏(韓知古家族)、安次韓氏(韓延徽家族)、昌平劉氏、醫閭馬氏及盧龍趙氏-之仕宦與婚姻為研究對象,並兼及此五家族在金朝(1115-1234)之延續,藉以顯示征服王朝與漢人世家間之共生關係。本文指出:這些漢人世家原為唐季、五代官宦家族,對遼之建國及統治皆有卓著功勳而備受遼廷倚重,得以維持累世官宦之地位於不墮。其子孫仕宦之延續性及普遍性皆甚強。漢人世家與契丹統治家族及其他重要漢人官僚家庭密切聯姻,形成一個包擁胡漢的內婚集團。故自仕宦及婚姻二點言之,若干漢人世家已深入遼朝統治階層之核心。遼朝滅亡後,五大家族中之四家在金朝仍維持仕宦地位。其中玉田韓氏及昌平劉氏更是金朝最顯赫之漢人家族。可見統治民族之改變對漢人世家地位之影響不大。這一情形與南方宋朝社會形成強烈的對照。宋朝社會中之統治菁英階層係以多元性及流動性高著稱。但在征服王朝統治地區,少數漢人世家仍享有崇高之政治社會地位,累世不變。
陳垣(1880-1971 )是民國前期的史學大師,也是元史研究的先驅。我對其史學成就甚為欽慕,因而撰寫了〈推陳出新的史學家陳垣〉。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於探討陳氏史學的前後變化及其對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從兩方面言之,陳垣可稱之為「推陳出新」的史學家。一方面,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重要史學家中,他繼承傳統史學最為直接,卻對乾嘉考證史學方法的現代化作出重要貢獻。另一方面,陳垣的史學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與政治環境變化之間的關聯尤為密切。陳垣史學的發展經歷三個主要階段:第一,考證史學:抗戰以前陳垣致力於中國傳統史學的現代化,並運用現代化的考證史學方法開闢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及元史等研究範疇。貢獻甚大。第二,抗戰史學:在對日抗戰期間,身處日軍侵佔之下北平的陳垣由考證史學轉治經世史學,寫出幾部發揚愛國精神,伸張民族氣節的專著。此一階段之著作雖仍以堅實的考證爲基礎,但過分強調民族大義,不免在擇題與論斷上有所偏失。第三,馬克思主義史學:一九四九年中共進入北京後,陳垣公開揚棄考證史學,擁抱馬克思主義史學,並且欲以史學研究作為「改造社會」、服務人民的工具。但是陳垣史學之馬列化僅止於公開表態之層次,並未付諸實踐。總之,陳垣對中國史學發展的主要貢獻在於促進傳統考證史學的現代化。近年來,由於意識型態的淡化,考證史學重新成為大陸史學研究的主流,陳垣等早期考證史學大師將繼續具有影響。
七年前我在一篇學術自傳中寫下面這段話:
回顧我的學術生涯,研究數量不算龐大,內容也未必精彩。畢竟人文與自然科學性質不同,很難說什麼才是突破性的研究。重要的是,每項研究都必須具有意義,一點一滴的累積,聚沙成塔。我的研究也是如此,談不上什麼驚人發現,不過是在元代政治、軍事、社會、族群、人物等方面,將研究前沿略微向前推進。如果有任何成就可言,主要由於我對一門冷門學問的執著與堅持,抱著「千山我獨行,何必相送」的襟懷,多幾分傻勁,少幾分功利(〈千山獨行:我的習史歷程〉,原刊於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3:3(2000.10),頁4-15)。
時至今日,這段話仍然代表我對自己學術歷程的看法,也適用於本書各篇文章。
回首前塵,四十餘年來,我先後受到不少師友的啟迪與砥礪。姚從吾、札奇斯欽、柯立夫(F. W. Cleaves)等先生都是引我入門的導師,師恩浩蕩,對他們無限感念。很多前輩先進及同輩友人的愛護與啟發,也使我感激不已。因為人數眾多,在此不擬一一提及。
歲暮途遠,仍有不少工作尚待完成,今後將繼續努力,但會放慢腳步,從容前進。
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
-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
一、引言:两大變革與征服王朝
中國近世史上有两大變革期,一次是「唐宋變革」,另一次是「明清變革」。這两大變革又與漢族王朝、征服王朝的更替相互重疊,關係錯綜複雜。
「唐宋變革論」是由日本京都史學前輩內藤虎次郎於八九十年前提出,主張唐宋之際,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皆發生巨大的變革,遂將「中古社會」轉化為以宋為首的「近世社會」。這一理論後經內藤氏的弟子宮崎市定等人的補充,更臻完備,成為中國近世史研究的重要典範,影響很大。近年來海峽兩岸更掀起一波探討唐宋變革的新熱潮。相關會議不斷召開,論著頻頻湧現。最近柳立言撰有〈何謂「唐宋變革」?〉一文,強調:唐宋變革所指不是一般的改變,而是根本或革命性的轉變。同時指出:「唐宋變革期」是專指上述重大變革發生和漸趨固定的時期,即中唐(八世紀)至北宋初年(十世紀)。雖然「變革期」的終點仍不乏爭議,有的學者主張北宋中葉(十一世紀),有的則主張南宋初年(十二世紀),但「唐宋變革期」不應與「唐宋時期」一詞相混淆。
「明清變革」開始於1500年左右。在第二變革期中,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經歷了與「唐宋變革期」相類似的重大變化。包括白銀的貨幣化、農業商品化、鄉村及都市生產的擴張、農村社會身分的變化、區域都會體系的成熟、政府對經濟控制的放鬆、學校的擴張及社會風氣的競尚奢糜等。
這兩次變革間的關係如何?大陸學者曾以「資本主義萌芽」一辭來概括這兩次變革,顯示兩者的同質性。美國學者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從「大區域」(macroregion)的觀點討論商業都會發展,認為第二次變革是第一次變革的量變與質變。明清變革時代的都會發展不再侷限於長江三角洲及國都附近,而是擴及全國多數區域,而且都會體系更臻成熟。最近大陸學者葛兆光從思想文化史的觀點解析兩次變革間的關係,他認為第一次變革期間發展的是菁英的「創造性思想」,第二次變革期間的主要發展則是這些思想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識化。可見第二次變革是第一次變革的廣化與深化。
但在兩個變革期中間的四百年的情形究竟如何,學界爭議頗多。過去大陸學者蔡美彪說過:中國近世歷史發展的圖像呈馬蹄形,首尾是兩個高峰,中間是一個低谷。施堅雅認為唐宋變革與帝國晚期之間隔有一個逆退與蕭條的黑暗時期,而伊懋可(Mark Elvin)則主張十三、四世紀為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轉捩點。對這一階段發展趨勢的評估都是負面的。
近年出版的論文集《中國史上的宋元明過渡》對這一時期的歷史重加探討。此書將南宋初至明代中葉四百年(1127-1500)稱之為「宋元明過渡」。書中各位作者達致的共識顯然不多。編者之一的Richard von Glahn僅能指出下列幾點: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發展所造成的災害不大,明初種種造成更大斷裂;江南興起而成為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道學政治社會觀的制度化。就整體發展而言,編者只能說:這一時期不是唐宋變革與晚期帝國之間的一道裂縫,而是一個過渡以及具有長程連接性動力的顯著階段。這本論文集雖然盛義頗多,但對這四百年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的地位仍未明言,而且對征服王朝及北方社會注意不足,可以探討的空間仍多。
中國近世前期史研究有一個嚴重的缺憾,即是南北兩方現存史料與相關研究之多寡非常不平衡。有關遼、金兩代及元代北方的史籍、文集、方志遠少於南方,以致研究北方區域歷史者往往因資料欠缺而裹足不前。梁庚堯曾指出:「學界對於宋代南方經濟的研究要多於北方,對南方經濟的了解也超過北方」,經濟研究如此,政治、社會、文化研究莫不如此。
南、北兩方研究的不平衡導致學者認為南方的發展是中國近世歷史發展的代表。劉子健先生說:「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心」,近八百年的文化甚至可以用南宋東南型作代表。
日本竺沙雅章教授談到宋金元歷史研究的一個基本缺失:即是學者說到宋代,往往僅論述北宋與南宋,對於金朝統治下的華北則不包括在內。他又說:
一般也有用宋元時代這種區分,但嚴密的說,這也有北宋-金-元與北宋-南宋-元的兩個潮流,也就是說有北流與南流,對于各演變的不同,以及王朝交替導致的流向之變化,也因金元治下的社會不明之故,而不能貫通。
由於學界偏重南流,忽略北流,而對近世前期的歷史得不到全面而正確的認識。
近世中國是胡、漢民族輪流做莊的時代。征服王朝的地位很重要。這些征服王朝皆是由北亞遊牧與半遊牧民族所創建。其原有的文化背景與中原漢族相差甚大,在其征服中原後,所採用的種種制度與政策,與漢族王朝時代也大有出入,對中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應該產生不小的影響。內藤教授在京都大學的後輩田村實造〈遊牧民族と農耕民族との歷史的關係〉一文中便認為:宋明之間經濟社會發展缺乏聯續性是由於金元等征服王朝的介入。可惜田村教授未加申論。而德國傅海波(Herbert Franke)則提出這樣的問題:
各征服王朝是否真的代表中國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自然發展」的主要挫敗?如果沒有征服王朝,宋朝在十一世紀的那種迅速成長與理性模式能否繼續?征服王朝是否促使學者所謂在宋朝已經出現的「近世」(modern age)半途夭折?或是由於各種侷限,如國家的效率、疆土的遼闊與複雜以及菁英未能注重實際和實用,宋朝的種種發展原本便是一條死巷?
傅教授所謂征服王朝乃指遼金元三代,他的問題事關征服王朝與中國近世發展,意義頗為重大,值得我們不斷努力尋求解答。這篇講演便是這項努力的一部分。
這篇講演擬以唐宋變革為背景,探討金元等征服王朝對中國近世化歷程所造成的影響。首先以十二、三世紀宋金對峙時代為範圍,比較金代統治下的北方與宋朝統治下的南方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異同。其次,再探討蒙元混一南北後,那些方面統合成功?那些方面失敗?而統合的結果,在那些方面比北宋進步?那些方面則是退步?希望這一努力能部分解答傅教授提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