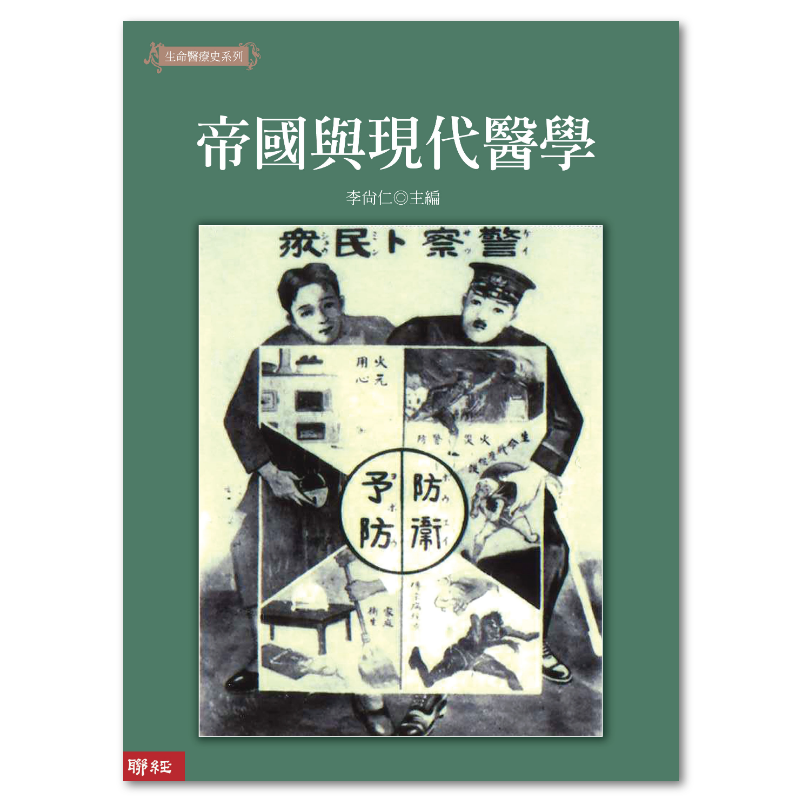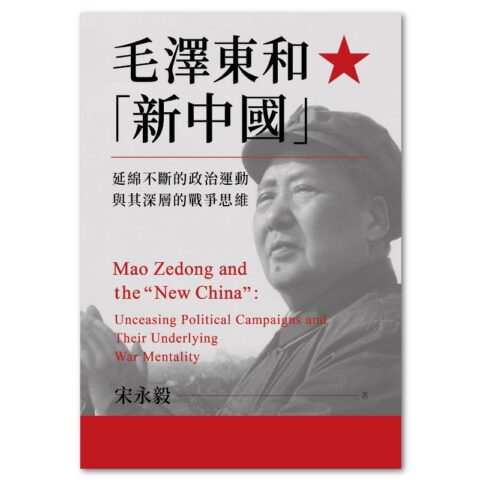帝國與現代醫學
出版日期:2008-10-22
作者:李尚仁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512
開數:18開西式橫排
EAN:9789570833256
尚有庫存
醫學在近代帝國的擴張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是建構殖民現代性與塑造被殖民者身分認同的關鍵力量。研究東亞的現代醫學史,必然會觸及到殖民與後殖民研究的課題。要理解現代醫學擴張的歷史,國家疆界與國族主義的分類範疇並無法提供適切的分析架構。本書企圖超克國族主義史學的局限,透過跨帝國的研究視野和新的史學想像,來探討帝國與現代醫學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
作者:李尚仁
李尚仁,台北市人,倫敦大學帝國學院醫學史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台大醫學院社會醫學科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為十九世紀以降的現代西方醫學史、科學史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STS)。
李尚仁 <導言>
一、醫學與殖民統治
1.新醫學在臺灣的實踐(1898-1906) ——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范燕秋)
2.氣候、體質與鄉愁——殖民晚期在台日人的熱帶神經衰弱(巫毓荃、鄧惠文)
3.從阿片君子到矯正樣本:阿片吸食者、更生院與杜聰明(許宏彬)
4.嬰兒死亡率與近代香港的嬰兒健康服務(1903-1941年) (楊祥銀)
二、中心邊緣的互動與知識生產
5.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戴麗娟)
6.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李尚仁)
7.「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劉士永)
8.美援下的衛生政策:1960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郭文華)
三、 疾病、空間與身份建構
9.「地方感」與西方醫療空間在中國的確立(楊念群)
10.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和疾病(雷祥麟)
11.「當下為人之大任」:戴秉衡的俗人精神分析(王文基)
導言
李尚仁
醫學史近年來在台灣已經成為一個活力旺盛的研究領域,回顧這十餘年來的發展,成果最豐碩的還是中國傳統醫學史研究,不過對現代醫學史(history of modern medicine)的探討也出現令人振奮的發展,並且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本書收錄的文章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同仁的著作,以及學界朋友在生命醫療研究室主辦的會議中發表過的論文。以較為整體的風貌呈現台灣醫學史學界的現代醫學史研究成果,是編輯本書的目的之一。此外,書中也各收錄了一篇大陸和香港學者的著作。雖然數量有限,但我們希望能有助讀者注意到這兩地優秀的研究成果。
近年台灣醫史學界的研究經常涉及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研究的課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學術研究潮流,一方面是一九八○年代以來英美殖民醫學史研究的蓬勃發展,帶給台灣歷史研究者許多刺激和啟發。 但更重要的是,現代西方醫學進入東亞的歷史和帝國擴張過程與殖民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研究東亞地區的現代醫學史,必然會觸及到帝國與殖民的歷史。不過和南亞、非洲、澳洲及美洲等地的殖民醫學相較,西方醫學和帝國擴張在東亞的歷史又有其獨特的風貌。例如,日本是東亞推展現代西方醫學的重要帝國力量,但是它有系統地學習現代西方醫學的時間其實並不長。中國並沒有成為殖民地,但在英法帝國強權壓力下產生了通商港埠、租界區、治外法權、英國人管理的中國海關(包括其醫療勤務)等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的制度和機構,也是英、美基督教傳教運動在海外投入最多醫療傳教士的國家。因此西方醫學進入中國的過程和風貌,既具有某些殖民醫學的重要特徵也有重要的差異,包括缺乏殖民統治的力量來推動公共衛生措施、法規和正式的醫療教育機構。相較於殖民地,來華西方醫師必須在更大程度上和中國官方與地方各種民間力量協商與妥協,他們在探討中國的醫療衛生狀況時,觀察性質的研究也遠多於更直接的干預介入。 這些歷史狀態都構成值得深入探索也深具挑戰性的研究議題。
現代醫學與帝國的殖民擴張
西方醫學傳播的歷史和歐洲的擴張有著密切的關係。近現代時期(early modern period)前往海外的航海家、商人、旅行家和墾民(settlers)是傳播西方醫學的先鋒。在美洲與大洋洲等地,這些歐洲人帶去的舊世界疾病,帶給當地原住民大量的疾病與死亡,削弱其抵抗能力而間接促成了歐洲的殖民征服事業。不過此一時期歐洲的帝國主義活動,西方醫學扮演的角色和對當地社會的影響都相當有限。這是因為西方醫學的用途大都侷限於維護海外的歐洲人的健康,而較少觸及到當地的社會與環境。另一方面,當時西方傳統醫學和印度、東亞以及伊斯蘭醫療傳統的相似程度遠大於差異,也不自認療效一定比當地的民俗療法優異。事實上,十八世紀還有很多殖民地的歐洲醫師主張要從當地的醫療傳統、藥材以及飲食起居習慣,汲取有用的醫療保健知識。因此這段時期的西方醫學在殖民地並沒有很強的介入傾向和強制性格。到了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擴張更加積極而深化。此外,十九世紀興起的現代西方醫學的優越感和侵略性大為增強,此一知識性格使其和帝國擴張與殖民活動有了更密切的結合。殖民醫學最初也最重要的任務是維護帝國的軍隊、官員、商人、農場主等殖民者的健康。等到殖民過程進一步深化,為了有效利用當地資源,被殖民者的勞動力開始被視為是有價值的資源,殖民醫學隨之介入被殖民者的醫療保健和環境衛生,更深刻地成為殖民統治機制的一部分。
本專題中范燕秋、許宏彬、楊祥銀、巫毓荃與鄧惠文的四篇論文都處理了現代醫療與帝國殖民統治的密切關係。關於日治時代台灣的現代醫學與公共衛生和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關係,台灣學界已有出色的研究成果。 這些研究勾勒出日治時代台灣人的疾病與健康,豐富了我們對這段時期台灣人生活狀況的歷史理解。它們深入分析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人身體細膩的介入與監控,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權力運作、意識形態和種族主義提出重要的洞見。此外,這些研究進而探討日本殖民醫學和歐美殖民醫學的關係,不只將台灣醫學史放進一個比較研究的架構中,也從世界史的眼光與脈絡中來進行台灣史的研究。前面所述西方殖民醫學的歷史變化,類似過程也出現在日治時期台灣的殖民醫學。然而,歐洲殖民醫學百餘年的轉變過程,在日治台灣卻是壓縮在數十年間發生,而且日本殖民當局和醫學界更是主動積極地選擇吸收西方殖民醫學的經驗與知識,並根據其殖民需求調整運用晚近習得之西方醫學知識。范燕秋的<新醫學在台灣的實踐>探討日本如何利用十九世紀晚期歐洲的醫學與生物學理論來建構一套殖民統治思想,並運用於台灣殖民醫學政策的擘劃。本文扼要地討論了殖民地台灣的醫療制度、衛生建設、防疫措施、醫學教育與研究,進而宏觀地勾勒出日本殖民醫學在台灣的許多重要面向。許宏彬的<從阿片君子到矯正樣本>一文則指出,殖民醫學研究往往植基於殖民統治所帶來極不對稱的醫病權力關係,也突顯出杜聰明這類接受日本醫學教育的台籍菁英在殖民醫學研究和政策執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日本吸收修正西方醫學理論的過程,或許最鮮明地表現在日本殖民醫學關於「風土馴化」的探討。歐洲醫學的風土馴化研究原本處理的是白種歐洲人如何適應熱帶環境、如何將殖民地具有經濟價值的動植物移植到氣候不同的歐洲、以及如何在殖民地養殖歐洲的農作物和家畜。這類研究往往強調白種人和其他人種的體質差異,而為科學種族主義提供學理的支持。 日本如何吸收這套醫學與生物學理論並應用在與日本人人種差異並不顯著的亞洲殖民地,是個饒富深意的比較研究課題。范燕秋對這段歷史已有深入的開創性研究,並且指出日本醫學界一方面吸收歐美熱帶殖民醫學關於熱帶地區的種族較為低等、熱帶氣候會讓高等民族的人種體質變質退化的看法,而對於在台日人的健康問題與面臨的體質退化威脅極為憂慮。另一方面殖民當局和醫學界也發展出四種做法來因應此一狀況:一、在學校實施有系統的身體檢查,觀察在台生長的日本學童有無任何退化跡象,以及早預防與補救。同時也透過比較日本學童與台灣學童的身體檢查資料來證明日人的人種優越性。二、透過個人衛生實作來預防日人體質的退化,其中即包括鼓吹洗冷水澡、加強體育和鼓勵運動風氣。三、加強熱帶醫學研究與公共衛生設施來防治瘧疾等與環境因素有關之傳染性疾病。最後,日本醫學界也從環境與氣候適應能力之角度,發展出一套日本種族優越論以回應歐美的種族醫學學說,宣稱日人的體質更能適應熱帶氣候也更有能力從事熱帶殖民事業,並且選擇被認為最能適應台灣氣候的九州人來台拓殖。 巫毓荃和鄧惠文對此一課題的探討則擴及到日本的殖民精神醫學。這篇論文細膩地分析現代醫學如何將「鄉愁」、「不適應異地生活」等情緒與感受「醫療化」(medicalized),將殖民者身處異鄉的焦慮建構成為「神經衰弱」的症狀。
在大英帝國各殖民地當中,香港殖民醫學的社會史與文化史研究相對而言算是很少。這點令人感到困惑與可惜,因為香港是少數經歷二次大戰後歐洲殖民地紛紛獨立的去殖民化潮流,而持續到二十世紀末的英國正式殖民地,而且擁有完整的殖民政府機構設施,其豐富的檔案紀錄和文書史料,提供難得的機會來研究西方殖民醫學在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中的百餘年長程變化。楊祥銀的香港醫學史研究,是填補這個史學闕漏的重要一步。<嬰兒死亡率與近代香港的嬰兒健康服務>一文記錄了香港殖民政府試圖減少幼兒死亡率所推動的一系列醫療政策與措施,並指出這段期間香港的嬰兒死亡率確實顯著地降低。雖然這篇研究尚無法區辨出這樣的改善有多大程度該歸功於西方醫學與殖民醫療政策,又有多大程度是經濟發展的附帶結果,不過楊祥銀認為殖民政府引進西式婦幼衛生的過程,港人並無強力的抗拒反而相當樂意使用這些設施。這樣的觀察提出了相當重要的史學問題:這樣的現象是殖民意識形態灌輸成功的成果?還是被殖民者主動利用殖民醫學的表現?除了抗拒之外,被殖民者在面對殖民醫學時還有那些方式來展現其主體性和能動性(agency)?被殖民者接受某些殖民醫療措施卻抗拒另外一些措施的原因和脈絡是什麼?畢竟港人也曾抗拒英國當局引進抽水馬桶的衛生政策。殖民者使用殖民醫學的方式和態度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醫學史課題。
帝國的網絡和醫學知識的建構
在研究現代醫學史時,目前的國家疆界與國族主義的分類範疇,經常無法提供適切的分析架構讓我們有效地理解歷史過去。當英美的醫療傳教士將西方醫學帶到「異教的國度時」,他們的組織、計劃與行動並不受國家疆界所拘限,中國、非洲、印度都含括在他們以全球為範圍的計劃當中。 當天津條約要求清朝政府將海關交由英籍人員主掌之後,海關的醫療勤務以英文出版的《海關醫報》(The Half-Yearly Medical Report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其內容不只涵蓋中國的通商港埠,也出版了日本、韓國等地的西方醫師的研究報告。英國醫師在觀察探討中國的衛生狀況時,其分析架構和醫學觀念則深受英國殖民印度所發展醫學學說的影響。在一篇回顧近年英語世界殖民醫學史研究狀況的文章,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批評道:「我們似乎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沒有言明的國族主義史學家的封閉領地。我們很會追問西方醫學在某個特定殖民場所或後殖民場所有什麼特殊性,而非探討西方醫學的殖民性」。 安德森批評的對象,是那些依照殖民地獨立後的民族國家範圍,來畫訂研究範圍與設定歷史分析架構的殖民醫學史著作。
所幸的是近年台灣的醫學史研究已經試著要突破這樣的侷限,而不致淪入以政權或國家的疆界來畫地自限的困境。由本文所收錄的文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點。例如,劉士永與范燕秋對日本殖民醫學史的研究,都非常注意日本醫學與歐美醫學之間的知識交流,如何影響日本在台灣所實施的醫療政策、衛生措施和醫學研究。李尚仁的〈健康的道德經濟〉則探討來華傳教醫師的醫學觀察、英國醫學界關於公共衛生學說的辯論以及蘇格蘭的社會經濟矛盾,如何形塑了德貞(John H. Dudgeon)對於中國衛生狀況的看法。戴麗娟的<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則透過「黑色維納斯」的悲慘命運,分析被殖民者的身體如何成為「展示品」、「學術研究材料」、「博物館收藏品」,而流傳於英、法兩大帝國的秀場、解剖室、博物館等場合。從十八到二十世紀,博物館是帝國的全球資訊蒐集類網路中重要的集中分類整理研究的中心,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體質人類學,正是帝國認識殖民地環境、替不同種族劃定位階的「博物館科學」(museological sciences)的重要一環。過去對種族科學的歷史研究大多以種族形象再現(representation)為討論的焦點,戴麗娟的研究則另闢蹊徑,分析研究材料、資訊與觀念的流通、交換和展示,進而探討殖民醫學與科學的物質基礎。若要研究日治到戰後台灣的體質人類學史,或是民國以來中國大陸少數民族調查研究的歷史,像戴麗娟這樣從物質文化入手的研究取徑應可帶來許多洞見。這篇文章還提醒我們注意知識、材料和實作(practice)的流通不只是跨國的、而且還是跨帝國的。正由於同一帝國不同殖民地之間以及不同帝國之間存在複雜交錯的流通關係,使得有些學者認為過去的歷史研究所經常運用的「中心與邊陲」研究架構有所不足,應該代之以「多重權威與多重互動」的「多中心流通網路」。
對歐洲帝國擴張和西方科學與醫學的歷史關係進行批判性歷史研究的先驅麥克勞德(Roy MacLeod),在「科學史學會」年刊Osiris的專題「自然與帝國:科學與殖民事業」的主編序言中,對於未能收錄到討論美國的文章深表遺憾,因為「美國科學、技術與醫學在古巴和菲律賓,更不用說在後殖民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地重大。的確,相較於英國和法國,目前的殖民醫學史研究似乎常忽略掉美國這個新興帝國。 幸好本書沒有這樣的缺憾。 郭文華的論文指出,家庭計畫並不能等同於「節育」,其整體目標應該是「營造家庭幸福」,因此還應包含「家庭經濟、計畫生育、老年保險、幼兒照顧、子女教育、婦女健康」等領域。然而,一九六○年代台灣大力推動的家庭計畫幾乎完全以節育為唯一目標,政策設計與執行都導向減少生育,而忽略了家庭計劃的其他面向。促成此一取向的重要因素則是來自美國的建議與壓力。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防堵共產主義而對台灣等開發中國家進行財經援助,卻又擔憂這些國家快速增加的人口會吃掉經濟成長而導致對美援的長期依賴,引此主張這些國家必須推動節育以減緩人口成長。甚至台灣衛生當局推廣樂普作為主要的避孕方法,也是源自相當偶然的美國因素。郭文華的個案研究讓我們清楚看到後殖民時期不進行直接統治的帝國,是如何對其扈從國進行指導、施加壓力進而深刻影響其衛生政策。
帝國、現代醫學與身份建構
現代西方醫學擴張的動力並不只來自歐洲中心。許多遭到帝國主義侵略殖民的社會,隨後認為現代科學、技術與醫學是國家強大的關鍵。追求現代科學、醫學與技術成為十九世紀國族主義運動的重要成分。 殖民當局教育培養的當地醫療人才,往往成為殖民地新興的資產階級精英,並且在國族建構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前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在政治上取得獨立之後,現代醫學更成為「現代化」運動的重要一環,也是本土精英掌握實質利益與文化霸權的有效手段。阿諾指出在印度:「到了一九一四年,印度菁英已經無法忽視西方醫學的文化修辭和政治權威。它所代表的不只是直接的健康領域,還是領域更廣的政治與文化霸權。從醫學和疾病的殖民語言中擷取的名詞和意象,滲透到印度自我表達的語彙中,成為新國族主義秩序之意識型態表述的一部份。」 類似的過程也可見諸日治與戰後的台灣。
過去的史學著作經常把這個過程描繪成現代科學「傳播與吸收」的過程。這樣的看法嚴重簡化了西方醫學進入非西方社會的複雜歷史過程,因為它忽略了當地社會往往對西方醫學抱持著分歧、矛盾以及選擇性利用的多樣態度,也未能釐清糾葛其中的複雜動機與利益糾葛,更沒有看到當地人常是透過既有的文化資源和認識框架來理解現代西方醫學。楊念群的<「地方感」與西方醫療空間在中國的確立>就指出,西方醫學進入中國時,不論診斷與醫療的進行方式或是空間安排和醫院管理,都必須因應當地文化習俗而折衷變通,如此才能贏得當地人的接納。澳洲學者Michelle Renshaw最近分析美國傳教士博駕(Peter Parker)的外科手術紀錄,發現他的中國病人術後感染與死亡率遠低於當時美國或英國的醫院。Renshaw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博駕的醫院的運作方式配合了中國習俗:醫師在對病人遺體進行病理解剖後沒有消毒洗手就接著檢查與治療病人,是十九世紀歐美醫院院內感染的重要因素。中國人不肯接受屍體解剖反而減少了院內感染。同樣地,在各病床之間走來走去又沒有適當感染預防概念的護士,也是十九世紀歐美醫院造成感染的重要因素。然而,中國人住院通常都有家屬陪伴,不需要護士照料日常起居,結果也就減少了感染的機會。
西方現代醫學進入中國之後促使中國社會重新界定身體、疾病與衛生的複雜歷史,目前已成為學者探討的焦點。例如,Rowgaski就認為中文裡「衛生」一詞在知識上所指涉的範圍,和英文的hygiene或sanitation等詞彙不盡相同,因此在她的書中一律使用“weisheng”這個拼音字來加以指稱。 雷祥麟是近年對此一課題投注心力最多、成果也最豐碩的學者之一。他的研究指出在這個歷史過程中,透過一系列的論述和實作(practice),醫生和病人的身分重新受到界定,過去傳統醫家擇病而醫、病人擇醫治療的醫病關係,被一套以「責任、權力與信仰」為核心的契約關係所取代,並建構出「負責任的醫師與有信仰的病人」的新醫病身分。 傳統中藥「常山」在進現代技術科學網絡(techno-scientific network)之後,即使它治療瘧疾的用途不變,此一藥物的身分和科學地位卻發生重大的轉換,而原本長期使用此一藥物的中醫卻被排除到網絡之外。 甚至中國傳統醫學的知識性格也被重新界定,原本在中醫傳統中不具重要地位的「經驗」,被建構成為中醫的知識論基礎。 在本書收錄的<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一文,雷祥麟探討民國時期大量引介西方衛生學說與概念之後出現的各種另類衛生觀。他認為這些中國的衛生之道,並非只是對現代衛生概念的誤解或是落伍過時的舊學說在負嵎頑抗,而是自有其「物質、情感與認同」之基礎。一方面肺結核(tuberculosis)這個細菌學界定下的「疾病身分」(disease identity),並無法取代「肺癆」這個傳統疾病範疇,反而在中國衍生出一個混雜的(hybrid)疾病身分;另一方面,雷祥麟認為對中國人而言:「擁有一個仍具活力的中國式衛生,便為另一種主體性保留了一份切身的可能」。西方醫療衛生所帶來觀念轉化,對人、事、物的身分的重新建構,及隨之而來的「混雜」產物 ,也透過不同歷程以不同樣貌出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劉士永的<「清潔」、「衛生」與「保健」>一文指出,日治時期「健康」、「衛生」與「傳染病」等西方衛生概念,雖然取代了台灣傳統的「勇健」、「養生」與「瘴毒」等觀念,卻又參雜了後者的內容。王文基的〈「當下為人之大任」〉則指出,戴秉衡早年在中國反抗帝國強權的國族主義潮流下參與禁絕鴉片運動的經驗,聯繫到他日後在芝加哥進行的社會心理研究以及他的精神分析理論。中國抗日戰爭的時代背景也深刻地織入戴秉衡對中國人人格的精神分析探討。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論在遷徙到中國的過程中,隨著當地的社會文化情境和政治情勢而為之調整修訂。
帝國、現代性與史學的視域
現代西方醫學之所以有強大的意識形態正當化作用和形塑身分認同的力量,並不僅在於其預防與治療的能力,也在於它在帝國擴張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它在後殖民時期所具有的現代性光環。學者有時把現代西方醫學稱為「普世醫學」( cosmopolitan medicine )。 然而,由於現代醫學擴張的過程中表現出知識的排他特質和對於醫療市場的壟斷主張,使得一九七○年代之後有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認為現代西方醫學本身就具有「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性質。麥克勞德指出:「醫學…今天越來越是個典型的西方文化體制。今天『醫學帝國主義』(medical imperialism)這個語彙所涵蓋的不只是征服新的疾病,也包括將『生物醫學』(bio-medicine)的模式擴張到非醫療的領域。它也意味著將西方文化價值延伸到非西方世界。」 大衛‧阿諾則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所有的現代醫學都在進行一種殖民的過程」,其所追求的是「對身體的壟斷權力」。現代生物醫學在歐美透過與國家的「共生」(symbiotic)關係,排除民俗醫學而取得壟斷地位,也是一種殖民的過程。 安德森更認為:「我們必須知道西方醫學的基本語言,它對普世主義與現代性的宣示,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帝國的語彙。」 若把「帝國」納入考慮,我們就不會陷入以現代醫學為標竿卻忽略帝國殖民擴張的歷史脈絡,淪入史學界早已揚棄的進步史觀而做出偏狹的論證和評斷。
近年來科技史、醫學史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STS)指出,「標準化」是現代醫學與科學這種「帝國擴張」過程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標準化的對象則包括度量衡、器械與儀器、作業流程與檢測基準,乃至人員的訓練與檢定。標準化又很容易成為國家以「現代化」之名進行監控規訓的技術。實驗室在現代西方醫學標準化診斷、治療乃至疾病身份(disease identity)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 雷祥麟等人的研究卻指出,帝國、國家機器與專業菁英往往無法順利達成將單一壟斷的標準加諸人民身上的企圖,進行規訓的權力網絡總有無法觸及與遭遇頑強反抗之處。在中國、印度以及許多其他地區,現代西方醫學的進入並沒有導致傳統醫學的消亡,後者反而在西方醫學挑戰下經歷種種變革調適而展現出嶄新的風貌與強大的活力。此外,現代醫學的概念與實作在不同的社會與文化有時甚至會發生轉化、雜交與變形。實驗室更不是唯一能界定疾病身份、衛生概念與實作內容的「計算中心」。 當地社會往往根據自身的需求、文化資源與認識方式,建構出對現代醫學多樣的想像與願景。歷史學研究應該分析這些願景的生產脈絡與建構過程,它們和帝國主義與西方現代醫學糾纏拮抗的複雜關係,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利益與權力。
帝國、殖民主義與現代醫學在東亞的歷史還有太多有待探索的領域與課題。我們希望日後華文世界醫學史研究的眼界還能更進一步拓展。就研究課題而言,專研南非史的英國學者Shula Marks十年前(1997)回顧英語學界的殖民醫學史研究時,認為此一領域對於種族主義、身分認同、性別、權力等課題的探討已有豐碩的成果,但是對於政治經濟課題的分析相對而言卻較為缺乏。 同樣的觀察與批評似乎也可以適用於目前台灣學界的殖民醫學史研究。 這本書的主題是帝國和現代醫學的關係,然而,醫學和帝國擴張的歷史淵源遠早於十九世紀。歐洲十九世紀之前的傳統醫學也占有殖民事業的一席之地,雖然當時西方醫學在知識性格上較不壟斷排他,對身體的監控介入也遠不如現代醫學那般深入細密,然而,這個時期的西方醫學仍深刻參與了殖民知識與種族概念的建構生產。 此外,中國也是個殖民擴張歷史悠久的帝國。種族思想在中國有相當長遠的歷史,而中國統醫學也對人群差異進行解釋與分類的工作。 近年來學者已經開始探討地圖學(cartography)這類的知識和技術在大清帝國的殖民擴張事業中所扮演的角色。 或許現在我們也該開始探討中國醫學和中華帝國的關係了。除了延展時間的歷史縱深之外,我們也有必要擴展空間的視域。當日本帝國殖民台灣並引進現西方代醫學協助其統治之時,現代西方醫學在日本亦不過發展僅二十年左右,因此必須掌握日本醫學與德國、英國、美國等其他帝國強權的醫學傳統的傳承和互動,才能釐清某些日本殖民醫學中的預設和概念。只有了解日本帝國在滿洲、中國及韓國的醫療活動,我們才能更深入了解台灣的殖民醫學史。另一方面,台灣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正好可以是個試金石,可以檢視擴大後的日本帝國,是否存在著一個與西方不盡相同的東亞殖民醫學型態。 同樣地,也只有了解到英美的傳教醫療活動、英國人掌握的中國海關醫療勤務、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中國醫療教育與公共衛生的介入參與,以及日本在中國引介現代西方醫學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我們才能對清末到民國的中國醫學史有深刻的了解。帝國的視域是全球性的,它不以國家的疆界為限,更遠超過國族主義史學的視野與想像力。正如安德森所說:「對於隱喻、預設和實作的全球流通,我們需要凝神傾聽…我們必須學著讓歷史學家成為能夠同時理解遷徙(migrancy)與在地(situatedness)的游牧者(nomads),而不是文本的帝國主義者或國族主義者。」 要研究帝國醫學及其歷史遺產,史學家的視域不只必須和帝國的視域一樣遼闊,還需要在歷史縱深上加以超越。
「清潔」、「衛生」與「保健」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修訂稿)*
劉士永**
一、前言
清廷因甲午戰爭失敗而於一八九五年割讓臺灣給日本。從主權歸屬來說,割讓臺灣的行為代表了治權的移轉;此一治權移轉的過程,即便同年五月至九月有臺灣民主國的存在,仍然可以清楚的界定中日兩國何時對臺灣開始行使主權。然而,從公共衛生觀念的轉變來說,這樣涇渭分明的區隔卻並不存在。觀念的轉變本就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方能見其端倪,何況在日治前期臺地動盪的情況下,更是需要時間來催化殖民政府所帶來的衛生觀念和相關學說。更重要的是,日本國內對所謂「衛生學」的定義與相關的應用,直到一八九○年代醫學界才勉強有比較一致的看法,而且這個看法還不斷地因西方新學說的興起而修正。大致上來說,西方新興的公共衛生學說約莫興起於一八二○年代,然而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基本上仍處於因應傳染病(contagious diseases)和新病因學(etiologies)的範疇,從傳統的隔離主義(quarantinist aspects)到強制性國家衛生制度(compulsory state hygienic system)的過渡階段。 至於今日所謂的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觀念,雖有部分要素,如隔離(quarantine and isolation)、乾淨(cleanliness)、消毒清潔(sanitization)、管制(control)等,曾散見於早期的各種學說之中,卻要等到細菌學革命(bacteriological revolution)昌盛之後,以及公衛理論中之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再次抬頭,並配合近代國家機制與財政資本化的展開,才在一九三○年代以後的西方國家有快速發展的機會。
就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衛生概念的轉變看來,日本國內流行的衛生學(hygiene)思潮當然是影響最大者,但在一九三○年代,一則是日本衛生學界逐漸引進西方新興學說,再則臺灣醫界也主動向外尋求新知,近代公共衛生思想遂陸續被引進臺灣社會,到一九四○年代也出現了一些相應的設施與制度。 簡言之,日本殖民政府自一八九五年開始以其國內流行的衛生學為基礎,陸續在臺灣推動一些相關的政策與衛生工程,但因為日本國內對「衛生」的定義未臻一致,加上新學說不斷的出現,致使殖民政府的政策中,曾經出現不同的理論依據及其相應的措施。從政策的延續與連貫性來看,衛生觀的改變似乎並不明顯;但細究其內容,卻可見殖民政府的衛生改造工程,實際上呼應了日本國內的發展、衛生官員的偏好與國際間公共衛生學說的演進。本文的主旨即在於點出前述的特點,並藉此呈現日治時期臺灣地區公共衛生觀念遞嬗的經過。
二、一八九五年以前日本的近代衛生觀
「健康」與「衛生」,這兩個名詞的形成與定義,始於幕末到明治初年間,日本衛生學者有意識的「製造」。這一套製造新知識的過程及其結果,日後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殖民政府的衛生政策與各種衛生標準。因新的學說不斷出現而使新的判定標準不斷地被應用於殖民地。為求論述的完整性,有必要先簡要地交代一下日本近代衛生觀形成的過程。
根據現行中央研究院電子文獻索引的結果,並未在中國舊籍中檢索出「健康」一詞。進一步檢索相關的詞彙後發現,中國傳統上對於描述身體機能與狀態完好的名詞,比較常見的是「健壯」、「健美」、或「勇健」等詞句。如《元史》兵制︰
雖所管軍不及五百,其家富強弟子健壯者,亦出禿魯花一名,……。
《福建通志》亦云︰
使節臨戎,守令禦寇,武夫健壯,拱聽指揮,……。
又記載:
泉兵丁,素稱勇健,每多桀驁不馴,該提督訓練有方,善於駕馭。
大致說來,在這些中國舊籍裡,「健壯」一詞出現的頻率普遍高於「勇健」和「健美」,而「健康」一詞則似乎並未於十九世紀末以前出現。 再者,一九一三年由臺灣教會出版,牧師甘為霖(Rev. W. Campbell)所編之《廈門音新字典》,也僅有「勇健」與「康健」的詞彙,既無「健康」一詞也沒有後來使用廣泛的「衛生」。該字典主要是根據當時泉州、漳州和臺灣流通的白話詞彙所編製之羅馬拼音字典,以利宣教師能運用通行於三地之閩南語推展教務,因此編寫之口音與詞彙皆以三地通用者為主。 據此推論,日本醫學家自幕末時期以來所慣用的「健康」一詞,其來源極可能既不是中國舊籍,也不是泉、彰、臺三地既有的日用詞彙。
既然「健康」一詞並不源起於中國,則日本如何創造及定義之,當有其他的依據。從時間上來看,緒方洪庵(1810-1863)的《病學通論》是第一個使用「健康」一詞的正式著作。《病學通論》刊行於一八四九年(嘉永二年)四月。據該書卷二之〈疾病總論〉所述︰
凡人身諸器不缺、氣血循環不滯、運營如常者,謂之「健康(ゲソンドヘイド)」,有變其常者謂之「疾病(シーキテ)」。
引文中所謂ゲソンドヘイド,實為荷蘭文gezondheid之音譯。就其出處而言,緒方洪庵所言健康的影響因素,顯然受到當時蘭學的影響,採用了荷蘭醫學的觀點。依據荷蘭醫學的衛生學基礎,緒方洪庵進一步分類健康的表徵,說道:
氣血諸器完備、運營毫無過或不及者,固可謂為「十全健康(フォルコーメネ ゲソンドヘイド)」。……世所謂健康者,運營常欠調和,但無較顯著的患害,得免病者之稱呼,是謂「帶患健康(ベトレツケレイケ ゲソンドヘイド)」。
依杉浦守邦的看法,緒方洪庵之所以要分別「十全健康」與「帶患健康」,其目的在於強調生理安定的恆定性。杉浦守邦並推論,緒方洪庵以「健」字表示強力維持恆定性的意味,用「康」字代表生理上的安定狀態。 《病學通論》初稿於一八四四年(天保十五年)送交坪井信道刪修定稿,完稿再於當時蘭學重心之適塾廣為流傳。 從幕末到明治初年,適塾出身的洋學家在日本思想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醫學與衛生學方面亦是如此。福澤諭吉及長與專齋即是最佳的例證。
福澤諭吉(1835-1901)於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間在適塾學習。他於一八六六年(慶應二年)出版《西洋事情(初編)》時,對西洋學校有如下的描述︰
學校之旁必設遊園,……又園中有立柱、架梯、張網等設施,學童或攀柱梯、或習網渡之藝、或為五禽之戲,以運動四肢、以散苦學之鬱閉、以保身體的健康。
在撰寫《西洋事情外編》(1867)及《西洋事情二編》(1870)時,福澤諭吉對健康的定義明顯傾向於英國公共衛生學(public health)的用法。在《西洋事情外編》中,他強調經濟上必須建立相互扶持的制度,才能以健康無事之人幫助患病之人,共謀社會之健康進化。在具體的衛生事業方面,淨水的供給構成了人體健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條件。 至於《西洋事情二編》,則強調人民有追求健康的權利,政府應當立法保障這種權利。 上述福澤諭吉的言論,顯然受到當時英國衛生學者John Snow等人的理論所影響。一方面,由於Snow發現霍亂傳染具有「水媒(waterborne)」的特性,遂力主污水為萬病之源,強調淨水對健康的必要性。Snow 的理論對當時盛行的「瘴氣論(miasma theory)」而言,無疑是一項重大的發現。 另一方面,Chadwick在一八四二年的衛生報告書中,即提出公共衛生立法管制與建立社會福利體系的觀點, 這也許就是《西洋事情二編》中衛生福利事項立論之主要依據。
長與專齋(1838-1902)是另一位對日本近代健康論及衛生學有重大貢獻的人。他在一八五四至一八六○年間就學於適塾。在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他受政府任命,赴歐美考察各國醫事衛生制度。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原幕末舊制之「醫務局」改制為「衛生局」,長與專齋就任為首屆衛生局長。在其自傳《松香私志》裡,長與專齋清楚地記錄他對英、美、德諸國衛生制度差異的理解,以及為何要由《莊子》中擷採「衛生」一詞,取代自緒方洪庵以來對「健康」的用法。
在英美調查醫師制度的過程中,常見到サニター(sanitary)或ヘルス(health)等詞彙,……到柏林後,幾度聽到ゲズンドハイツプレーゲ (Gesundheitspflege) ……起初僅從一般的字義去了解,並未特別留心。但隨著調查步伐的進展,感到(按:Gesundheitspflege)並不是單純的指健康保護而已。等到疑問漸增、了解漸深,才發現指的是負責國民一般健康保護之特種行政組織。
後為起草《醫制》、推展西方類似之觀念,長與遂以為,
……這樣的健康保護事業,東洋尚無以名之,而且是一全新的事業,……醫制起草時,原詞本欲直譯為健康與保健等文字,但為求更直接有趣,我考慮了其他更適當的語詞。後憶及《莊子》「庚桑楚編」有衛生這樣的說法,和原意差異不大,字面又高雅,……適用於表達這種健康保健的事業。
長與專齋的敘述顯示出三個特點。(一)長與所謂的健康與衛生,源起於德文Gesundheitspflege。(二)早期傳入日本之荷蘭醫學,本為德奧醫學系統之旁枝; 因此,長與所代表的官方對「健康」事業欲重新定位時,就採用了傾向德國醫學的角度,而另以「衛生」名之,這恰好回歸了緒方洪庵翻譯健康一詞時的情景因素,足見德國醫學對日本醫界和官方如何定義「健康」及「衛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三)從緒方洪庵的「健康」到長與專齋之「衛生」,健康問題顯然已從個人生理機能的良窳,轉而成為政府施政的要務。衛生健康不僅僅屬於個人自利的範疇,而且是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因此國家介入衛生事業的必要性增加。
以明治初年日本醫學界的認知而言,德國醫學以社會進化論(social Darwinism)或生物學原則(biologicalism)定義生理上的「健康」,即所謂健康者必須要能在「優勝劣敗」的競爭過程中存活與延續,而政府亦要以醫學或政治的手段,協助其人民在此一競爭中生存下來,此即「衛生」的本質。 大體上說來,日本醫界所接受的德國衛生觀有三個特質。(一)公部門必須介入社會中的衛生活動,以維持個人與社會全體的健康。(二)健康論所規範的是生理的完整(integrity)和生命的延續(continuity),而衛生學所指涉的是一套以行政手段促進健康的作法。(三)政府必須由上而下的進行衛生改革,因此有必要明訂健康及衛生的判定標準,並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分配醫療資源。易言之,醫療資源的配置不取決於市場因素,而是交由國家從增進社會整體健康水準的角度,由國家安排醫師專業分科的比例與執業的地理分佈。
大學東校(東京帝大前身)於一八七○年發表〈保護健全意見書〉,一時成為明治健康觀的代表性宣言。該文分「道」、「護健使」、和「學」三大部份,其中論及「健康之學」的部分,作者主張︰
……悟造化之效,究物理之博,然後遠可以校日月星辰之運行及感應,近可以詳山川風土及氣候之變更。對水火金石草木及蟲魚禽獸之性質變化消長,識其原、推其用。由此得以掌握人生之所宜者。所以其本在於論人身百體之功用,詳其生成活動思慮及五感之妙機,講明所以成萬物之靈及生死疾病之道理。然講明此理需有二端︰一是人在未病時須有防護禁戒之預防,以除厄保健康,此乃斯道之根本。一是人既患疾,自始即變通藥術以施之,以復健全、以全天命,此理需以前理為本,否則將止於斯道之餘技耳。
從上文可見,預防和治療已是明治時期健康觀的兩大重心,甚至還更強調預防的重要性。再者,「健康之學」的內容不限於人體,尚及於全體自然界。這樣的態度似乎呼應了十八世紀末以來,西歐醫學家以博物學為基礎所推論出來的一套醫學理論。 這樣的健康觀無疑地呈現出相當多的西方影響。根據〈保護健全意見書〉的論點,長與專齋於一八八三年在《大日本私立衛生會雜誌》上發表〈衛生ト自治ノ關係〉一文,他主張︰
人事愈複雜,僅一人一己之力不能達自愛自衛之目的,遂至一致團結,相互共謀扞外護中,……是則有集合體自治之興起。
此一集合體自治之衛生要務如下︰
衛生之目的在謀人生之無病長命,在此目的下,第一要務即供給清淨的空氣和飲水。又此事業之內包含上水的引用、下水之排除,所謂衛生兩大工事﹔以及家屋之改良、塵芥不潔物之掃除、道路之修繕等。加以傳染病流行之際,行消毒檢疫隔離之法,以控制病毒之蔓延,或預防於未發之時。以上等等都是今日所稱衛生上的重大事業。
從上述的討論不難發覺,一八九五年以前日本的健康論與衛生學,均受到西方醫學很深的影響,其中尤以英國醫學和德國醫學的影響最大。因此,當時日本醫學界吸收了不少正在西方流行之各種病因論。這些病因學說比較重要的有︰瘴氣論 (the miasma theory)、霍亂菌之水媒論 (the waterborne theory of cholera)、和一八九○年代新興之細菌論( the germ theory)等。由於日本衛生學具有集體主義和中央集權之特色,在接受西方病因學說之際,每因學說之更替而使日本衛生官僚忙於重訂健康與衛生的判定基準。對於日本國內為了因應西方新學說,引發了種種討論與更動,日本學界已有許多討論,但此非本文重心,故在此暫不論列。不過,儘管健康與衛生的判定基準會因學說更替而改變,在英系與德系醫學的影響下,日本健康論中「預防重於治療」和衛生學裡國家干預的特質,則是兩項不變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