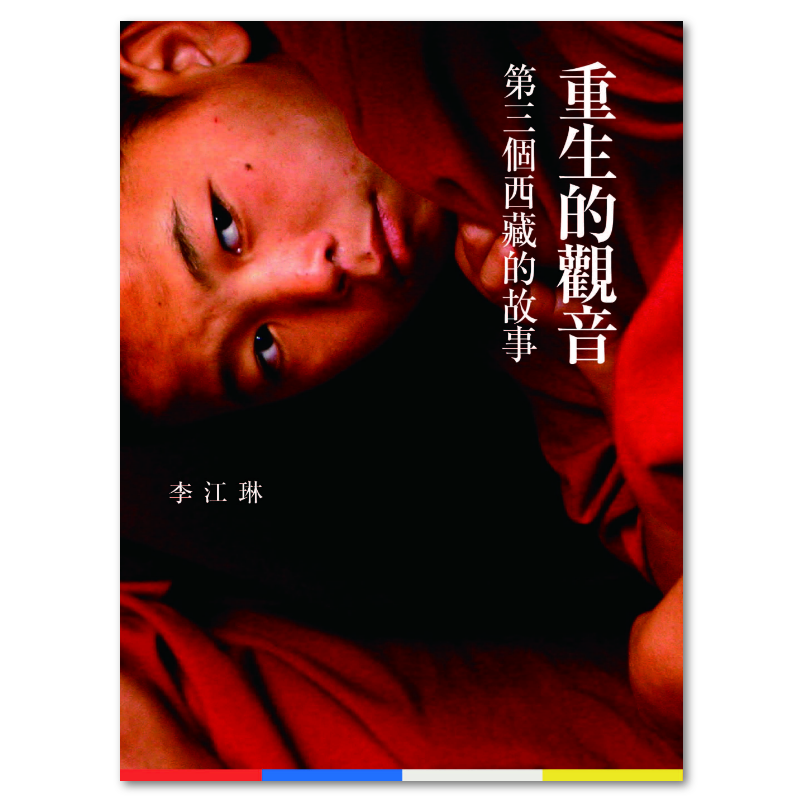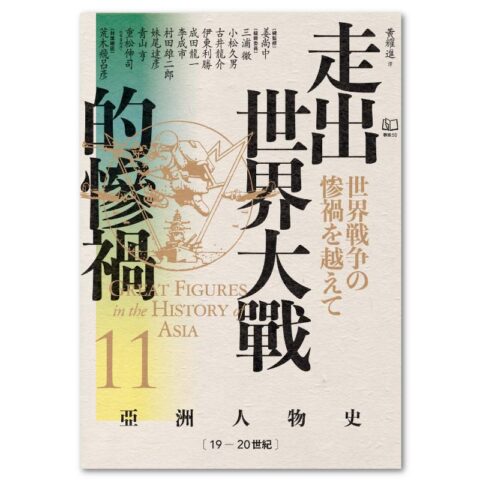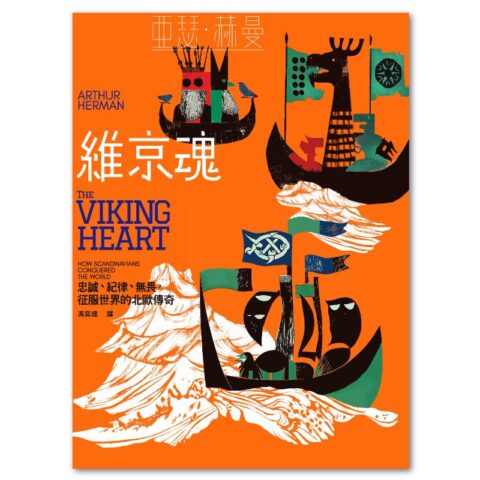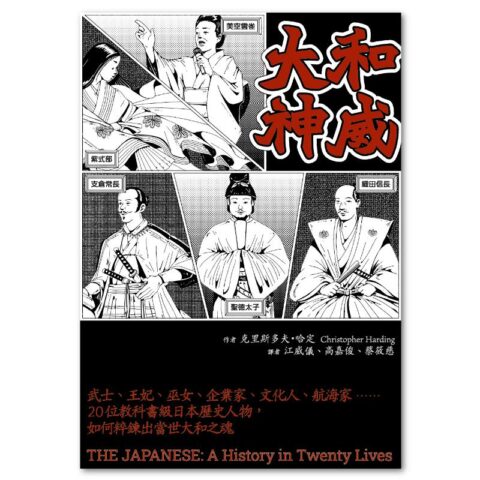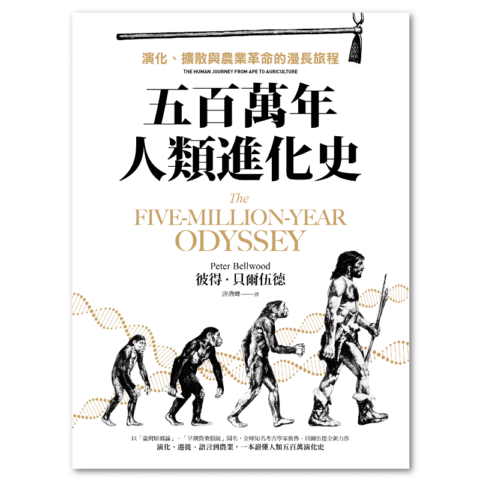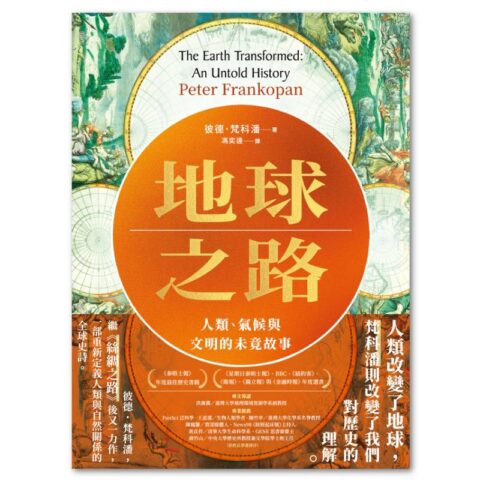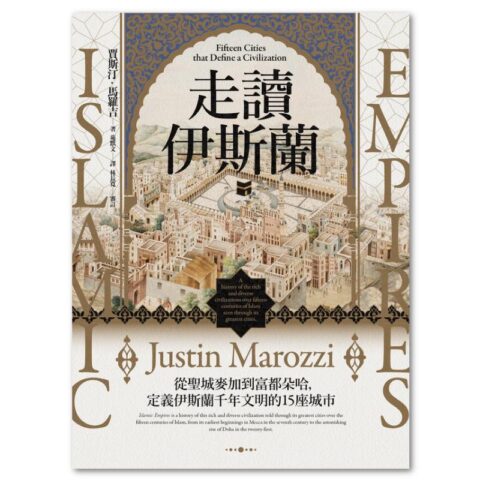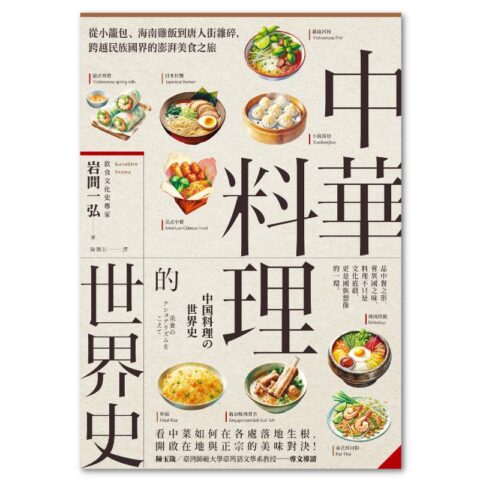重生的觀音:第三個西藏的故事
出版日期:2017-02-08
作者:李江琳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88
開數:18開,高23×寬17cm
EAN:9789570848793
系列:歷史大講堂
尚有庫存
達蘭薩拉,一座世界知名的小鎮。
她是藏傳佛教的新聖地,也是一座難民營。
在被妖魔化的「舊西藏」與被革命窒息的「新西藏」之外,
千里跋涉、翻越雪山、通過達蘭薩拉走向全世界的
「第三個西藏」在此重生。
「西藏三部曲」作者李江琳
繼《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藏區祕行》後,
新作《重生的觀音:第三個西藏的故事》書寫藏人流亡半個多世以來罕人知曉的故事。
對許多藏人來說,「香格里拉」不在喜馬拉雅山之北,
而是在喜馬拉雅山之南,一個叫作達蘭薩拉的地方。
從文化而非地理的意義上來看,以達蘭薩拉為中心的西藏流亡社會,可以說,那就是第三個西藏。
達蘭薩拉(Dharamshala)是個太複雜的地方,那裡是西藏文化的濃縮之地,也是流亡藏人「暫時」的歸屬。在那裡,每一個藏人都有一則屬於自己的流亡故事,不只是肉體的流亡,更深刻的是心靈的流亡。走出極權主義控制下的藏區,走進未知的印度領土,等待著他們的是從未想像過的新世界。李江琳親自走訪達蘭薩拉,聽取一個又一個流亡藏人訴說,關於勇氣、困頓、疑惑、重生的故事。
李江琳在《重生的觀音:第三個西藏的故事》敘述,筋疲力竭的難民們好不容易逃過戰爭和饑荒,到達印度,卻立刻面臨新的危險。生活在高寒地區的藏人,對許多疾病,天生沒有免疫力。他們已經很衰弱的身體與各種病毒接觸時,完全無法抵抗。肺結核、寄生蟲、流行感冒之類的疾病,奪去了大量難民的生命,據說死亡率高達十分之一。
古老的西藏文明顯然需要走向現代,可是達賴喇嘛並不認為西藏走向現代化意味著必須完全拋棄傳統。古老的西藏文明如何在當代世界爭取到一席之地?虔信佛教的藏人怎樣在現代社會裡生存,同時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西藏的宗教文化與現代科技文明怎樣才能有效地結合?如今仰賴流亡在外、卻有機會接觸到現代西方文明的民族先覺者如何教育他們的下一代。
在藏人幾近走投無路的時候,印度人民收留了他們,盡最大努力幫助他們重建生活。近半個世紀來,達蘭薩拉的印度社區和流亡藏人社區比鄰而居,共同把昔日的荒山建設成一個熱鬧的小鎮。如果沒有流亡藏人,很可能不會有今天的達蘭薩拉。如果沒有心胸寬廣,慷慨智慧的印度人民,也不會有藏文化的異地保存。
1967年的一天,邊巴奉召前往法王府,達賴喇嘛請他為達蘭薩拉大昭寺塑造三尊造像,其中一尊是千手觀音像。達賴喇嘛同時交給他一袋銀圓,和來自拉薩大昭寺的八個觀音殘面。這八個殘面是一位西藏和尼泊爾混血的人,從拉薩收集來,帶到印度的。達賴喇嘛說:「這座觀音像是用中國的銀幣和西藏的觀音面鑄造的,將來我們要帶回西藏。」
作者:李江琳
江西南昌人。1982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1987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先後獲得波士頓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從2004年開始研究西藏問題。2007年以來持續研究西藏流亡史,在印度和尼泊爾訪問了17個西藏難民定居點、近300名來自西藏三區的難民。先後在《明報月刊》、《開放》、《人與人權》、《中國人權雙周刊》等雜志發表了多篇有關西藏問題和西藏流亡社會的文章。曾著有《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是重建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史實的重要作品。
出版序
前言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給友人的信
第一部 走向達蘭薩拉
褲子街
飄落的袈裟
阿尼諾宗
寺廟街上的小販
雪山隔斷的童年
牧羊少年的故事
巴塘來的朝聖者
第二部 朵拉達山脈下的小鎮
「無名街」上的芳鄰
傍晚,達蘭科特
喜馬拉雅水晶
彼得和伊凡娜
圓祥法師
第三部 聖地,在喜馬拉雅山南
乃穹寺
重生的觀音
喇嘛嘉瓦
藍哈達
智慧之海
出版序
2007年10月,我第一次去達蘭薩拉。那是我深入研究西藏當代史的開端。旅行期間,每天採訪、參觀之後,我會盡可能詳細地記錄見聞。這本書就是那次達蘭薩拉之行後寫的,初稿完成於2008年。寫完之後未及修改,我又束裝出發,第二次去達蘭薩拉,就這樣與達蘭薩拉結下了不解之緣。
此後的幾年中,我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來研究1950年之後的西藏歷史。《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這兩本書出版後,我才有了一個寫作「空檔期」。2012年,我在中國大陸和印度旅行期間,抽空對這本書作了一些修改。
幾年來,達蘭薩拉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英國人留下的舊房已經不多,新建了不少樓房,手機、Wifi 都已相當普及。來訪的人也愈來愈多。隨著研究和採訪的逐漸深入,我曾想對這本書作較大修改,加入更多的採訪故事。然而,這本書裡的很多內容,是發生在特定時間中的片段,它已經成為歷史,保留這一點歷史紀錄,並非毫無意義。因此,我對文字作了一些潤色,插圖還是採用2007年拍攝的照片。
2007年在達蘭薩拉,很多人為我提供了種種幫助。在此,感謝那次為我翻譯的達瓦才仁先生和茨仁紮西先生,感謝喇嘛嘉瓦、阿尼諾宗、頓珠諾布、塔丁才旦、措姆、多傑紮西以及「甲喇嘛」圓祥法師接受我的採訪。他們有的還在達蘭薩拉,有的移民去了西方國家,有的返回西藏,有的已經去世。他們的經歷是藏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我希望,有更多的漢人來傾聽藏人的故事。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給友人的信
達蘭薩拉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西藏文化的濃縮版和精華版。假如沒有西藏,就不會有達蘭薩拉。
說起西藏,作為同時代人,你知道,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西藏只是個傳說。在我有限的知識版圖裡,「西藏」不過是個地名,「達蘭薩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則根本不存在。那時候,我對西藏的全部了解,來自於一部電影和幾首歌。電影是你我這代人可能都看過的《農奴》,歌是〈逛新城〉、〈在北京的金山上〉,還有文革期間廣為流傳的〈洗衣歌〉。
官方話語中有兩個西藏,一個「舊西藏」,一個「新西藏」。幾十年的宣傳中,「舊西藏」的一切都被妖魔化,「新西藏」的一切都被浪漫化。可是,「舊西藏」和「新西藏」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其實並不了解。小時候,我被老師們帶領著去看《農奴》的時候,我不知道那裡曾經發生過什麼;當我們看著一群女紅衛兵穿著藏服、唱著〈洗衣歌〉,在舞台上跳舞的時候,也不知道那裡正在發生著什麼。如果說,那時候的中國是個藏在鐵幕後面的國家,西藏則被掩藏在雙重鐵幕之後。那時,我對那片土地和那個民族,以及在那裡發生的一切,均一無所知。
現在,去拉薩的火車一票難求,坐在供氧車廂裡欣賞高原風光的人們,同樣也未必知道,有些人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另一個方向,前去朝拜他們心中的觀音菩薩。對許多藏人來說,「香格里拉」不在喜馬拉雅山之北,而是在喜馬拉雅山之南,一個叫作達蘭薩拉的地方。從文化而非地理的意義上來看,以達蘭薩拉為中心的西藏流亡社會,可以說是第三個西藏。
我是到了美國之後才開始接觸西藏文化的。我所了解的一切顛覆了官方話語中的「新、舊」兩個西藏。然而在美國,有關西藏的一切又被推到另一個極端。對於物質過於充足,生活過度優裕的美國人而言,這個被封閉在雙重鐵幕之後的民族,幾乎成了一個當代神話。
很長時間裡,我對宗教相當困惑。我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社會裡長大,成長過程中,所有宗教都被妖魔化。如果說五四運動為古老的中國帶來現代的曙光;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卻有鮮明的反宗教傾向。他們認為,中國需要的只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宗教屬於一個落後的時代,中國不需要宗教。
1949年以來,宗教信仰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活動中,宗教遭到毀滅性打擊。在那場對文化本身的「革命」之後,我們民族所剩無幾的傳統,包括傳統的信仰,以及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道德觀、倫理觀和風俗習慣幾乎被摧殘殆盡。我對文革最初的記憶,就是一堆被砸爛的佛像。
以佛教信仰為文化底蘊的西藏,宗教文化所受到的打擊可想而知。就在歡快的〈洗衣歌〉唱遍大江南北的同時,西藏有無數的寺院被摧毀,佛像被砸爛,價值連城的宗教文物被破壞。然而,當破壞者在聖殿的廢墟中歡呼的時候,他們不知道,當聖地成為廢墟之後,他們自己也將失去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一切。如今我們的民族正是如此:物質的豐裕並不能帶來精神的充實,除了錢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有了高樓大廈,卻丟失了靈魂。
「革命」是一場集體狂歡,但也是一場假面舞會。但假面被拆下後,我們還得面對自己,並且面對一個可怕的事實:在集體狂歡的過程中,人生中最寶貴的一切不是被粉碎,就是被抽離。革命是集體的,革命後的心靈重建卻是個人的。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獨自去尋找通往精神家園的路。
我想我還是相當幸運的。命運把我從中國帶到耶路撒冷,又從耶路撒冷帶到達蘭薩拉,讓我有機會在神聖與世俗、出世與入世的兩極之間,尋找自己的中道。說到底,有關彼岸的追求本是為了此岸,有關去處的追問原是為了當下。頭頂的星空和腳下的草地,都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風景。
心靈重建是一種漫長而且艱苦的過程。那是條孤獨寂寞的路,你只能千山獨行。出發的時候,你不知道有沒有終點,也不知道終點在哪裡。你得擺脫理性的傲慢與偏見,學會聆聽來自自己內心的聲音,讓冥冥中的神祕力量帶領你,走向自己的精神家園。沿途你得一次次俯身,拾起破碎的靈魂,一點一點地重新拼接。很多固定的觀念將被顛覆,很多習慣的行為將會改變。路的盡頭就是你的聖殿,它可能是一片森林、一條河流、一朵沾著晨露的花;也許是羅馬、耶路撒冷,或者達蘭薩拉。
我該怎樣形容達蘭薩拉呢?藏民族的政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駐錫的小鎮,官方地名叫馬克利奧德甘吉。這個小鎮很特別,不是我能「一言以蔽之」的地方。
馬克利奧德甘吉雖在印度,我卻不能用「一座印度小鎮」來形容它。鎮很小,一座小廣場,幾條窄街,兩邊擠滿了高高低低的房子,有低矮的破舊木板房,也有三、四層樓高的磚石建築,靜靜訴說著這座小鎮的獨特歷史。房子以實用為主,用途不是餐館旅社就是禮品店。各種簡陋的小攤子,賣藏式披肩、廉價首飾、蒸的或者煎的「饃饃」(包子或餃子)、甜茶、藏式面餅、糌粑。
不管從世界哪個地方出發,去達蘭薩拉都不大容易。你得先飛到新德里,在德里乘一整夜火車,再坐幾小時汽車。從德里的西藏難民定居點「桑耶林」乘長途汽車也行,這是最簡單、最便宜、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不過,那得在印度北方的公路上顛簸一夜,約十三小時,其中一半是在山中夜行。夜間上山至少有一個好處:印度司機開著大客車飛馳,在不合規範的狹窄公路上翻山越嶺,你呢,眼不見,心不顫。
藏在深山裡的達蘭薩拉是座名滿天下的小鎮。在中國之外的世界裡,她的名聲不亞於西藏本土。這些年來,她已變成了一個旅遊勝地,反而讓人忘記,這座小鎮實質上是座難民營。我在馬克利奧德甘吉的小街上漫步時,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各國遊客,常常覺得不可思議:這是座難民營啊!她怎麼變成「旅遊點」了呢?也許,宗教、政治、流亡、「神祕雪域」等等「當代神話」的因素,在激起人們同情的同時,也引發人們的好奇?
達蘭薩拉也是海外藏傳佛教的中心。由於達賴喇嘛和17世噶瑪巴的緣故,對於虔信佛教的藏漢洋各色信徒來說,她已經成為一個新興的佛教聖地。每年都有大量佛教信徒和準信徒從世界各地前來,參拜達賴喇嘛,聽經、參加法會和其他重要佛事活動。在達蘭薩拉街頭,常常看到裹著絳紅袈裟的洋喇嘛和洋尼姑。他們神色安詳,步履從容,走過身穿藏袍,手握轉經筒的西藏老人。還有些人乾脆就是來「避世」的,哪怕是短暫的避世,以獲得片刻的寧靜。
表面上,這座小鎮也像其他國家的小鎮一樣寧靜安詳。可是,它平靜祥和的外表下暗流洶湧。街邊商店的牆上貼著下落不明的小班禪照片,到處可見雪山獅子旗,一家小商店的玻璃窗上貼著告示:「本店不售中國貨」,奧運倒數計時牌問每一個路過的人:「2008年,你將在哪裡?」這一切都提醒外來的人們,這座小鎮與藏民族的現狀與未來密切相關。小鎮的平靜中因此有一種不確定感。如果說絡繹往來的過客是「流水的兵」,小鎮本身也未必是「鐵打的營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裡的每個人都是過客,只是逗留的時間有長有短。
達蘭薩拉有很多層面,每個層面都有故事。那個地方有故事,那裡的人也有故事,不管是定居的西藏難民,還是絡繹不絕的各國來客,都有獨特的故事。藏人基本上都是失去了一切的人,他們翻山越嶺,一路漂泊到這裡,在遠離故土的深山小鎮裡安家,重建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他們故事裡的關鍵字通常是「逃離」和「捨棄」。這裡的每個藏人都有一個關於逃離和捨棄的故事,當這些故事被普通人用平淡的口吻敘述時,令人倍感驚心動魄。
許多難民生活困頓,光是國際兒童緊急救助會(SOS-Kinderdorf International)之下的西藏兒童村裡,就有一千多名孩子,必須通過外界的援助在那裡生活學習。有些孩子已經得到了資助,有的還在等待善心人士慷慨解囊。年輕人前途渺茫,很多人靠小本經營勉強維生。他們一日一日地面對貧困,面對失望,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然而,達蘭薩拉的平靜並非麻木,也不是逆來順受。達蘭薩拉的平靜源於外人難以理解的精神底蘊。因此,這種平靜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它體現著生命的尊嚴和風度。
我在達蘭薩拉記錄了不少故事。這些故事都是私人講述,是一個個普通人的生命歷程,是一些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和兒童,身不由主,在政治、民族、宗教和歷史的漩渦中浮沉的故事。這些故事集中起來,就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不可否認,藏民族的集體記憶帶著深重的悲情。然而,藏民族的集體記憶並非僅限於悲情。
藏民族還有另一部分集體記憶:當聖殿成灰,家園盡毀之後,流亡境外的難民在他們精神領袖的感召和領導下,以非凡的勇氣和毅力,在異國他鄉重建物質與精神的家園。達蘭薩拉不僅記錄了苦難,更重要的是,達蘭薩拉還記錄了超越苦難的力量、決心和勇氣。
如果我講述的達蘭薩拉顯得支離破碎,那是因為每個人的故事,以及達蘭薩拉本身的故事,都還在進行之中。這些故事早已開頭,尚無結尾。因此,我所記錄的故事,以及我所看到、聽到和經歷的一切都是不完整的。我只能把一些碎片交給你,由你自己去拼接這個尚在進行中的故事。
褲子街
回到紐約後,我常常想起那兩條小街。不知道有沒有街名,我在兩頭的街口都找過,沒看到街名牌。我的朋友達瓦管它們叫「褲子街」。廣場是「褲腰」,他說,從廣場一邊延伸出去的兩條老街是「褲腿」。從地圖上看,兩條平行的老街還真挺像條褲子的。
達蘭薩拉不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城鎮。她的歷史軌跡清清楚楚,而且都與「外國人」有關。往遠裡說,達蘭薩拉的歷史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跟幾個英國人有關;要是往近裡說呢,那就得從1960年4月30日,一位西藏人算起。
1960年4月底的那天傍晚,當達賴喇嘛的車隊到達馬克利奧德甘吉的時候,前來歡迎的人群除了當地印度居民,只有二百多名西藏難民,他們比達賴喇嘛早來一個禮拜,是專程從築路營前來歡迎他的。
達賴喇嘛遷居達蘭薩拉之後,分散在各地的西藏難民紛紛追隨而來。馬克利奧德甘吉所在的山頂,是一道山梁的最高處。朵拉達山脈山峰陡峭,山坡上松林茂密,只有山頂的公園還算平整。難民們用木板和石塊作為建築材料,在公園裡蓋了幾排小房子,房子之間的狹長空地,就形成了最早的兩條街道。山梁狹長彎曲,兩條最早的街道順著山勢彎曲,從山梁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將近五十年後,馬克利奧德甘吉可不止兩條街了。好幾代西藏難民在這裡安身立命,重建人生,
昔日的荒山野嶺如今已是名滿天下的小鎮。環繞廣場有好幾條街口,通往不同的方向,上山,或者下山。山上山下處處可見飄揚的五彩經幡。
不過「褲子街」 還是最熱鬧的街,或許也可以說,是最亂的街。
「亂」好像是印度的常態,馬克利奧德甘吉也是這樣,熱熱鬧鬧,生氣勃勃地亂著。房子之間橫七豎八地掛著違章電線,猴子把電線當作棧橋,從街那邊的屋頂跳上電線,順著四通八達的電線網竄來竄去,野狗追著電線上的猴子狂叫。有一天,我站在廣場邊的新旅館門口,跟一個澳大利亞人聊天,幾條躺在街邊的流浪狗突然跳起來,竄到小街中間,仰頭狂吠。猛然間,一個黃乎乎的東西從天而降,落到我面前,嚇了我一大跳。原來是隻猴子從屋頂上掉下來,落在街中間。狗狂叫著追,路人東倒西歪地閃避,猴子竄過馬路,攀上電線杆,後腿一蹬躍上屋頂。
牛在街上東遊西逛。有幾頭牛以小鎮為家,每天都看到牠們在「褲子街」裡慢悠悠地走。有頭大黑牛常常獨個兒在街上逛,邊走邊低頭覓食。牠體型龐大,性情卻很溫和。有時候,牠從我身邊走過,我拍拍牠的大腦門兒,黑牛抬頭看看我,目光小鹿般溫柔。
鋪著水泥的老街很窄,兩邊的屋簷下各有一道深深的排水溝。達蘭薩拉是印度降雨量最高的地區。雨季裡,街上的雨水淌進排水溝,形成兩條小溪,流過家家門前。街邊沒有人行道,汽車開進小街,行人閃到路邊,汽車一路按著喇叭,貼著行人開過。
從馬克利奧德甘吉往上走,山愈來愈高,路愈來愈險。公路只通到海拔約2500公尺的嘎魯廟,再往上就只有在密林中彎曲的小路了。現代交通工具無法進入高山裡的村莊,貨運就得靠馬幫來往。在馬克利奧德甘吉,時常會看到趕馬人趕著一隊馬或者毛驢,沿街走來,牲口背上馱著各種各樣的貨物,慢條斯理地走著。汽車猛按喇叭,摩托車在馬幫中竄來竄去,驢馬早已習慣了人的喧鬧,牠們氣定神閒,不緊不慢,頸下的銅鈴一路叮叮噹噹,清脆地響過小鎮。
向晚時分,霧氣從樹林裡嫋嫋升起,縹縹緲緲,漸漸填滿山谷。落日蒼蒼,霧海茫茫,遊牧的嘎第人披一身晚霞,趕著羊群下山,浩浩蕩蕩走進鎮裡,滿街的人、車、牛、狗紛紛為羊讓道。牧羊人身穿長袍,頭戴繡花小帽,皮膚被陽光曬成古銅色,又被風刻出深深的皺紋。他一臉見慣風雲變幻的淡然,不理睬汽車的喇叭,不在意拍照的遊客,走過網吧,走過金頂佛塔,走過賣「安多餅」的女子,穿過小街,走過廣場,下山,回到山腰的村莊。
達蘭薩拉如今相當國際化。「褲子街」上有取款機,用各國的銀行卡可以隨時取款。街上的行人來自世界各地,有背著大背包的登山者,有遠道而來的朝聖者,也有髮型怪異的「龐客」。印度中學的學生成群結隊到這裡參觀,各國的出家人前來參訪。在「褲子街」的商店和小攤上,可以買到藏式披肩、喀什米爾繡花長袍、開司米圍巾、拉達克的佛教藝術品、漢地的茶磚、藏地的首飾,還有喜馬拉雅山區特產的各種寶石。
清早,我到嘎其素餐館去吃早飯,常常看到打扮得半印半藏的西方女人,穿著「旁遮普套裝」、印度式拖鞋,裹著藏式披肩,從街上走過。有些西方人已經在達蘭薩拉居住多年,還有些裹著袈裟的洋喇嘛和洋尼姑,在達蘭薩拉的各寺院裡學經修行。牆上貼的告示,不僅有藏語和印地語,還有希伯來語、英語、法語。
比鄰而居多年,藏人學會了一些印地語,印度人也學會了一些藏語。在「褲子街」裡遇到的印度乞丐,一見我就伸出手:「Madam,Good Morning!紮西德勒!拿瑪斯特!」
夜晚,「褲子街」滿街燈火,晚上跟白天一樣熱鬧。路邊小攤裡掛著燈泡,暈黃的燈光下,神色疲倦的老人把一條條披肩折好,準備收攤回家。初次上山那天,我曾在他的攤子上買了一條僧人用的絳紅披肩。
賣明信片的小攤旁,幾個外國遊人停下腳步,在燈下挑選達賴喇嘛和十七世噶瑪巴的照片。廣場邊那座新旅館的外牆上,垂下一條條彩色燈飾,家家餐館燈火通明,裡面坐著各國來客。
將近五十年了,難民營成了繁華的城鎮。建造城鎮的第一代難民在異鄉老去,日漸凋零,「褲子街」也有了很多變化。街上的老房子很多已經消失,被新建的樓房取代。一座樓房的底層正在裝修,雖未完工,牆上已經掛滿了唐卡,地上放著幾尊大銅佛。佛像旁邊,一公尺多高的濕婆神在火圈中舞蹈。在濕婆神優雅的舞姿中,世界輪迴往返,生生滅滅。佛祖在蓮花寶座上跏趺而坐,雙目低垂,注視著來往不息的芸芸眾生,嘴角一絲淡淡微笑。
「褲子街」上,還剩下為數不多的木板房。這些小木房有的已經傾斜,看上去搖搖欲墜。它們在喜馬拉雅山南的小鎮裡,經歷了將近五十個雨季,木板已然褪色,年輪依舊清晰。
達蘭薩拉的故事,就從這裡開
飄落的袈裟
那年,頓珠諾布32歲,出家已經整整21年了。
在這21年裡,西藏之外的世界天翻地覆。不過,對頓珠諾布來說,雪山之外的世界並不存在。他與他那個時代的藏人一樣,對世界的全部認識,沒有超過南方的鄰居印度、尼泊爾和東方的鄰居中國。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天旋地轉,西藏很安穩。眾生雖不富裕,倒也自給自足。西藏深藏在大雪山中,像依偎在母親懷抱裡的孩子,對外面的世界不聞不問,簡單、懵懂地活著。
頓珠諾布壓根兒不知道,當酥油燈在佛前閃爍的時候,世界陷入了戰爭的血海。且不說遠的了,雪域的東方鄰居正在跟一個叫作日本的國家打仗,日本人戰敗後,鄰居自己人之間,「紅漢人」和「白漢人」又打起來了。
可是,就算聽到了一句半句的,頓珠諾布也不會特別關心那些事兒。他何必要操那份心?漢人兩虎相爭,逐鹿中原,那全都是漢人之間的事兒,鹿死誰手,跟日喀則紮什倫布寺的頓珠諾布有何相干?他當然更不會關心南方鄰居的事兒。印度獨立?獨立是什麼意思?印度,對藏人來說,只是佛法之源,是聖地,是若有福報此生必去朝聖的地方。頓珠諾布沒想到,日後他倒是去了印度,也去朝過聖,卻是以他做夢也想不到的方式去的。
就在頓珠諾布念經拜佛的日子裡,東方塵埃落定。「紅漢人」大勝,並且揮師西進。頓珠諾布對這些事情毫不知情。他不知道,1949年,東方的鄰居已經改朝換代,還發出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的誓言。兩萬大軍已在四川集結,血紅的旗幟正步步逼近雪山,佛國上空戰雲密布,殺劫將臨。
當時的西藏內外交困,風雨飄搖。駐錫拉薩的達賴喇嘛和臨時駐錫青海塔爾寺的班禪喇嘛,是兩個稚齡少年,一個14歲,一個11歲。這兩個少年將要面對的中共領袖,一個叫毛澤東,一個叫周恩來。而且,當時的十世班禪喇嘛尚未獲得拉薩噶廈政府的承認,要等到漢藏兩方在《十七條協議》上簽字之後,他才獲得承認。
頓珠諾布日日念經修練,在佛像前磕長頭。
「紅漢人」兵分四路,包圍昌都。數萬身經百戰的將士兵臨城下。面對他們的,是約八千名裝備落後,從未見過現代戰爭的藏兵。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甚至是勝之不武的戰爭。
頓珠諾布每日往酥油燈裡添油。一勺勺酥油傾入銅燈盞,一顆顆溫暖的火苗在佛像前跳動。昏暗的燈光裡,釋迦牟尼佛低垂雙目,悲憫地注視著匍匐在地的僧俗民眾。
昌都戰役,八千多藏兵不敵幾萬漢兵,一敗塗地,占整個西藏正規軍實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軍被全殲,包括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一批軍官及大批士兵被俘,西藏門戶大開,「紅漢人」勢如破竹,長驅直入。一年後,「紅漢人」抬著頓珠諾布從未聽說過的大幅畫像進入拉薩。有人告訴頓珠諾布說,畫像上的兩個人,一個叫「毛澤東」,一個叫「朱德」,他這才知道,他的家鄉已經被「和平解放」。
不過,歷代班禪喇嘛一向跟漢人友好往來,歷屆漢人政府對班禪大師也相當禮遇,因此,即使鄰居已經改朝換代,家鄉也天翻地覆,紮什倫布寺的日子還是過得下去的。頓珠諾布一如既往,念經、打坐、磕長頭。今生今世,頓珠諾布別無所求,今生虔誠修練,來生脫離苦海,這就夠了。北京簽約,漢兵入藏,康巴戰事,雪域早就不再太平,但這些事都沒有讓頓珠諾布放下經書。
1959年3月的一天,頓珠諾布終於放下了經書。
拉薩出事了。
1959年5月14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條發自印度腳山的消息。消息報導說,第一批西藏難民於5月13日到達印度,進入印度政府在阿薩姆邦腳山的難民營,並告訴記者中共軍隊用機槍射殺民眾的殘暴行為。這批難民共91人,全部是男性,他們衣衫襤褸,在崎嶇的喜馬拉雅山路上步行了五週。報導還說,印度政府宣布,已經有一萬一千五百名西藏難民越過印度國境,進入中印邊境的阿薩姆邦,正在前往臨時難民營的途中。
這條消息僅167字,而且刊登在第30頁上。對於美國民眾來說,有關西藏的故事至此就結束了,他們的注意力早就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然而,對於逃離故土的藏人來說,他們流亡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難民們成群結隊,有些騎著馬,大多數人步行,從各地匯集到米蘇瑪日。一望無際的叢林中有片空地,一道清澈的河水流過樹林。河邊的沙灘上,印度政府用竹子和篾片為材料,派人在兩週內趕建了三百座大棚屋,作為西藏難民的臨時棲身地。到了這裡,難民們已是人困馬乏,再也走不動一步路了。他們在棚屋邊的草地上停下,或坐或臥,等待印度政府的人員前來登記。
在臨時難民營裡,逃亡藏人的死亡率相當高。精疲力竭的難民們好不容易逃過戰爭和饑荒,到達印度,卻立刻面臨新的危險。他們遇到的第一個殺手是印度的濕熱氣候。從西藏到印度,海拔一下子降低了二千多公尺,同時溫度提高了幾十度,難民們到達印度時,大多數還穿著皮袍皮靴,戴著厚帽。到了難民營後,他們脫下皮袍,到河裡去洗澡,換上印度政府發給他們的印度式白布長袍。為了防止傳染病,難民們帶來的皮靴和皮袍被收集起來,堆在一起,放火燒掉。每個難民領到一個鋁製飯盒,醫生為他們檢查身體,為路上受傷的人包紮傷口,然後,大家待在難民營裡,等待下一步的安排。
疾病是難民們遇到的第二個殺手。逃亡的過程中,來自各地的西藏難民常常食不果腹,加上長時間的步行,有時還要躲避追兵。到達印度後,由於緊張、疲乏、勞累和饑餓,他們的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大量難民在短時間內到達難民營,設計容納幾千人的營地很快人滿為患,每座棚屋裡住著30到50名難民,有時候甚至不得不擠進一百名難民,傳染病流行難以避免。戰爭的最大受害者常常是老人和兒童,西藏難民也是如此。許多老人兒童逃離了戰爭,卻無法適應印度的氣候和水土,每天都有人死去,焚骨異鄉。短短幾週內,就有167名兒童死亡。
那時候,印度獨立還不到15年,國家百廢待興。印度本身也是個窮國,大量難民突然湧進來,印度人民雖然同情他們的遭遇,經濟上卻幫不了太大的忙。為了解決西藏難民的生存問題,印度政府提供了一個方案。印度北部山區人煙稀少,政府正計畫在北部山區修建公路。北方喜馬拉雅地區山高天寒,氣候潮濕,印度南方居民不適應氣候,何不讓印度政府雇用西藏難民來修路?這樣既可以給西藏難民工作機會,又解決了印度政府的問題。
走投無路的難民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這個方案。1959年9月,第一批難民從臨時難民營出發,到錫金去修路。以後的幾年裡,難民們一批批被送到各地的築路營,在山區修築公路。
20世紀60年代,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南側的森林裡,到處是流亡藏人的築路營。這段時間是流亡藏人最困難的時期。生活在高寒地區的藏人,對許多疾病,包括肺結核,天生沒有免疫力。
他們已經很衰弱的身體與各種病毒接觸時,完全無法抵抗。肺結核、寄生蟲、流行感冒之類的疾病,奪去了大量難民的生命,據說死亡率高達十分之一。具體的死亡數字人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了,正像人們永遠無法知道,在「平叛」、「大饑荒」和「文革」這三場席捲了整個藏區的人禍中,有多少藏人死於非命。
牧羊少年的故事
牧羊少年塔丁才旦坐在山坡上,望著白雲在空中悠悠飄過。天很藍,草很綠,羊群在牧場上低頭吃草,偶爾有隻羊抬起頭,咩咩地叫幾聲。那一刻,如果有內地來的遊客路過,一定會舉起相機,對著牧羊少年和他的羊群猛拍一氣,然後把照片放在網上,感歎藏區風光如畫,羡慕牧羊人生活悠閒。
他們當然不會知道,牧羊少年心事重重,覺得自己生活單調,前途無望。他想,難道就這樣,一輩子放羊?可是,除了放羊,他又能做什麼呢?他是個孤兒,又是文盲,既沒有家庭背景,又沒有文化知識,前途在哪裡?怎樣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塔丁出生在青海玉樹一個貧窮的牧人家庭。四歲時父母離異,他和雙胞胎兄弟由母親撫養長大。兄弟很小的時候就因病雙腿癱瘓,家裡一貧如洗。塔丁11歲那年,母親去世了。兄弟倆只好跟著舅舅生活。舅舅是木雕匠人,一手技藝得自家傳,可是木雕手藝養不了一大家子,舅舅家的日子也過得緊巴巴的,沒錢交學費,塔丁和表兄弟們都上不了學。母親在世的時候,盡力想讓兒子上學,塔丁讀了一年書,母親實在無力讓他繼續上學。塔丁只好離開學校,此後再未進過校門。
17歲那年,塔丁做出他一生中第一個重要決定。他要到拉薩去闖蕩一番,看看有沒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塔丁當時並不知道,拉薩還是前往印度的出發點。許多西藏流亡者的流亡之路,就是從拉薩開始的。
牧羊少年帶了一點點錢,告別舅舅一家,獨自從青海玉樹出發,前往拉薩。到了拉薩,他只剩下八元錢。塔丁在拉薩人生地不熟,無親無故,投靠無門,真正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塔丁走進一家小餐館,拿出最後一點錢,買了點吃的。吃完,他懇求老闆給他一份活兒幹。老闆見他身體不錯,能幹活兒,吃得了苦,就收留了他,讓他在餐館裡打雜,工錢雖然不多,但吃飯總算有著落了。牧羊少年絕處逢生。
在那家小餐館裡,塔丁什麼活兒都幹。他一邊打雜,一邊偷師,有空就看廚師怎樣做菜。一來二去的,他學會了大廚手藝。一年後,來自青海的牧羊少年成了拉薩的餐館廚師。
在拉薩,塔丁開始聽說一些有關達蘭薩拉的事兒。有些從印度回來的人私下裡給他看達蘭薩拉的照片,告訴他達賴喇嘛就在達蘭薩拉。人家還告訴他,在達蘭薩拉,他不僅可以學佛法,還可以免費讀書,學藏文和英文。
從青海牧區到拉薩,對塔丁來說,是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祖父輩的時代,拉薩還是一個封閉的城市,是藏人心目中的聖城。現在,拉薩已經不再是聖城了,她已經變成一個世俗城市,一個世界性的旅遊熱點,城裡到處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不過,對塔丁來說,拉薩是一扇窗子,透過這扇窗子,塔丁窺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要與那個世界接觸,他必須學會使用那個世界的語言。
在拉薩,塔丁做出了他一生中的第二個重要決定:他要去達蘭薩拉。他不知道達蘭薩拉是什麼樣子,在那裡怎樣謀生,能不能找到出路,他只知道,他要去拜見達賴喇嘛,然後留下來,學英語和藏語。
去達蘭薩拉除了危險,還得花錢。從拉薩到尼泊爾,路上吃喝開銷以外,還得花三千左右人民幣僱嚮導。由於沒有護照,進入尼泊爾屬於非法偷渡,到了邊境,一旦被尼泊爾警察抓住,得拿錢打點警察,算是「買路錢」吧。西藏方面的嚮導只帶到中尼邊境,過了邊境,還得再花幾百人民幣僱尼泊爾方面的嚮導,這些人熟知當地的情況,能夠避開各種危險,把逃亡者帶到邊境城鎮,從那裡搭車去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不過,決定出走印度時,塔丁並不知道這些具體細節。他只知道要花不少錢。
廚師塔丁省吃儉用,拼命攢錢。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估計錢差不多夠了,20歲的塔丁辭掉工作,背上一袋糌粑,帶著簡單的行裝,朝喜馬拉雅山南走去。
那是西元2001年11月,西藏高原最冷的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