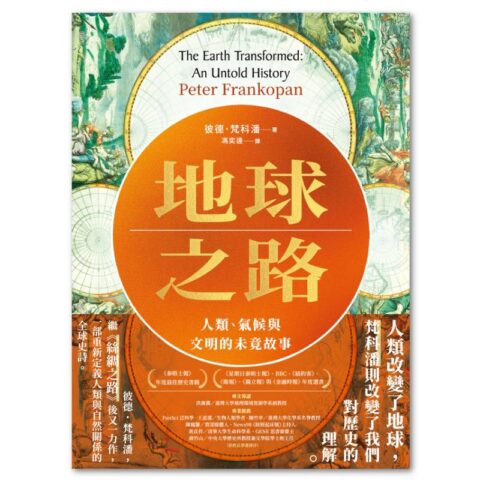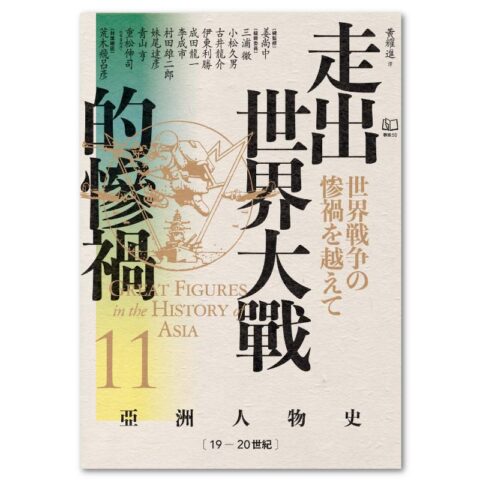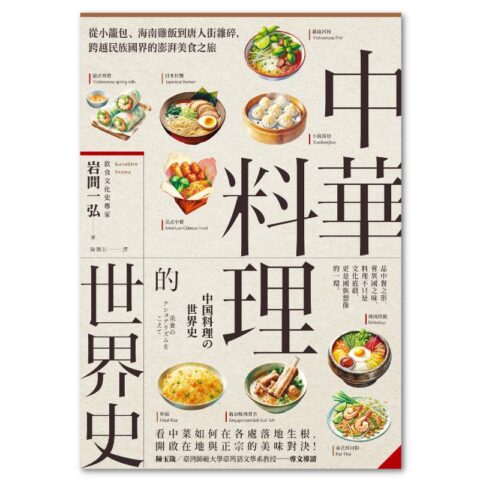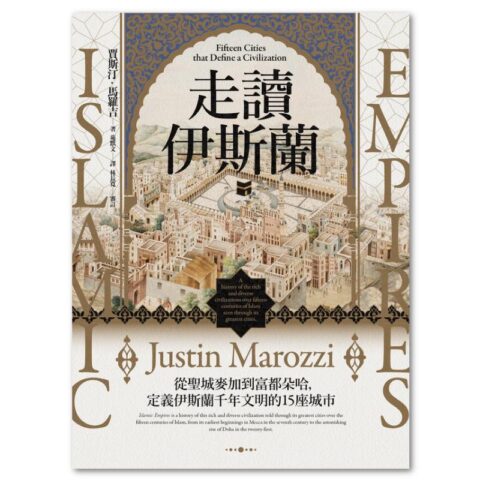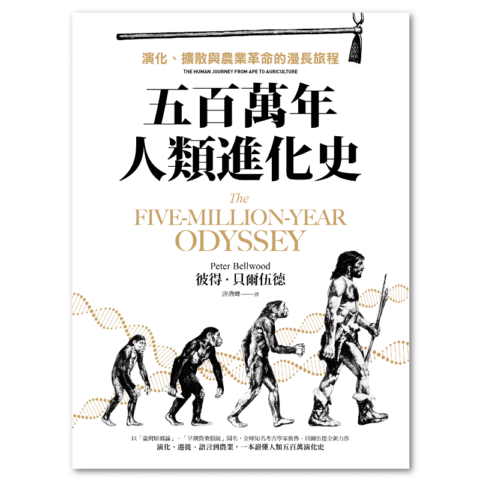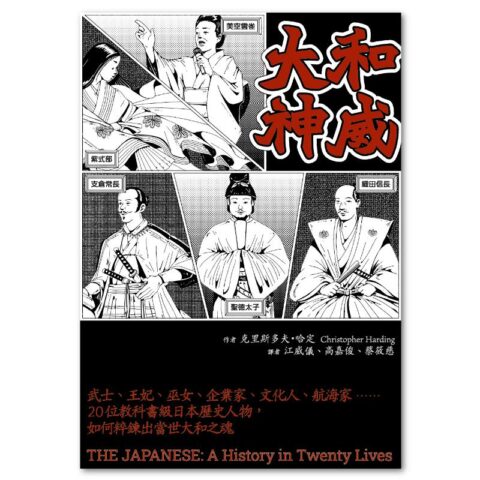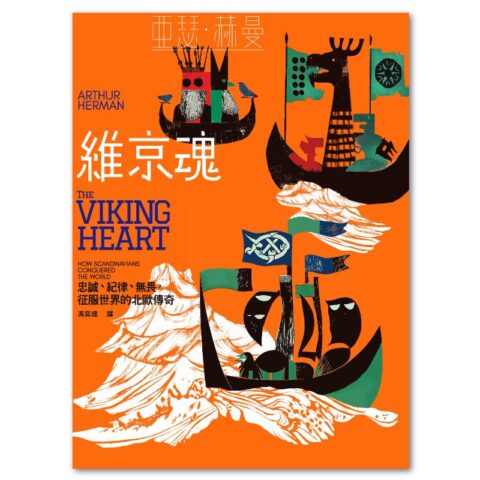暗渡文明:大搶救還是大疑案?改寫非洲歷史的廷巴克圖伊斯蘭手抄本事件
原書名:The Book Smugglers of Timbuktu
出版日期:2019-04-10
作者:查理‧英格利許
譯者:蔡耀緯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52
開數:18開,長23×寬17×高2.1cm
EAN:9789570852899
系列:歷史大講堂
已售完
要守護一個文明,首先要做的竟然是盜走它?
來自遙遠國度的傳奇,一座傳頌百年的鍍金城市
賭上《衛報》記者職涯寫就的巨作,曲折離奇的伊斯蘭手抄本竊盜案!
廷巴克圖是傳說的發源之地,自古到今,這個城市自身即是傳奇。
在歐洲探險家尚未涉足非洲大陸的漫長年歲中,廷巴克圖是口耳相傳的桃源鄉,相傳那裡的房舍牆壁鍍了金,居民以小塊純金作貨幣,且他們的帝王坐擁金山,能毫無顧忌的隨意揮霍黃金。這個西非城市的歷史面貌始終籠罩在訛傳與誇大的描述之中,面目模糊,但它的確掌握了一個文明的核心。
廷巴克圖之所以被傳說打磨、閃著金光,原因不在物質,而在文化。歷經紛亂而漫長,充滿佔領與衝突的時光,這個古城裡埋藏著巨大瑰寶,是一頁又一頁十五、十六世紀的書寫史料,一疊又一疊令伊斯蘭研究者興奮顫抖的手抄本,數量之多,據說只要稍加鑽研,便足以全面翻轉現行非洲歷史敘事。
2012年,北非基地組織攻陷廷巴克圖。隔年,市長宣布城中所有古老史料盡毀,但這卻是這座城市傳說又興的起點。一群圖書館員竟冒著烽火搶救了大量手抄本!然而就在眾人歡欣慶賀之時,作者查理‧英格利許深入挖掘真相,赫然發現這次國際矚目的搶救文明行動,竟可能是場聯合當地知名藏書家,組織精良的騙局。
世上有兩個廷巴克圖,一個真實存在於尼日河畔,一個則完全虛幻,坐落於你我心靈之中。當心靈的力量與渴望被激情煽動,真實與虛偽便能輕易變造真相,而一個文明的份量,也許就立基在人們是否相信它的存在上。
當裝著文明質量的木箱始終緊閉,擁有鑰匙的所有人不願開誠布公時,我們能做的僅有觀看,並選擇是否要相信這則鍍金的傳說。
※ 國際媒體一致推薦
這部兼具報導、歷史敘事與浪漫情懷的作品全然扣人心弦!
──《星期日電訊報》
讀來有如搶救中古非洲手抄本的《辛德勒名單》故事,既是調查報導寫作的典範,也是一部極其多采多姿的歷史與旅行著作。
──威廉‧達爾林普(William Dalrymple),2017年《衛報》年度選書推薦詞
這是本迷人的書。廷巴克圖驚心動魄的當下和過去,由查理‧英格利許匠心獨具地交織起來;他同時擁有作家令人愉悅的文筆、記者追查真相的嗅覺,以及小說家建構敘事的聽覺。英格利許的著作充滿了令人難忘的英雄與反派,核心則是一次名留青史的救援行動,是一個把故事說好的榜樣。」
──瓊‧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切‧格瓦拉:革命生涯》(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巴格達陷落》(The Fall of Baghdad)作者
作者:查理‧英格利許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研究員、《衛報》前國際新聞組組長。十九歲時首次前往非洲旅遊,做了既深而廣的探索,之後遊歷世界各國,經驗豐富。文章常見於各大報。
為了撰寫廷巴克圖的故事,他在得知手抄本並未被毀的消息後,辭去了《衛報》的工作。
譯者:蔡耀緯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現為自由譯者。譯有《叛國英雄:雙面諜O.A.G.》、《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等。
推薦序 占領、毀壞、解放:廷巴克圖神話的誕生 李易安
地 圖
序 章 雄心與天賦兼具之人
第一部 占領
第一章 尋找手抄本的人(二○一二年三月)
第二章 廣袤無垠的空白(一七八八年六月─十一月)
第三章 地獄就在不遠處(二○一二年三月)
第四章 第四位旅人(一七九五─一八二○年)
第五章 基地組織伸出援手(二○一二年四月)
第六章 傳說之城應當屬於我(一八二四─一八三○年)
第七章 伊斯梅爾的名單(二○一二年四月)
第二部 毀壞
第八章 紙上談兵的探險家(一八三○─一八四九年)
第九章 無頭騎士(二○一二年四月─五月)
第十章 廷巴克圖的教宗(一八五○─一八五四年)
第十一章 祕密工作者(二○一二年六月─九月)
第三部 解放
第十二章 學者人生(一八五四─一八六五年)
第十三章 糟糕二人組(二○一二年九月─二○一三年一月)
第十四章 利奧波德國王的紙鎮(一八六五─一九○五年)
第十五章 火刑(二○一三年一月)
第十六章 研究者的編年史(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
第十七章 真實上演的印地安納‧瓊斯時刻!(二○一三年一月─二月)
第十八章 手抄本熱(一九六七─二○○三年)
第十九章 神話工廠(二○一三─二○一五年)
終章
補充說明
致謝
考書目
序(節錄)
一八二五年夏天,萊恩從的黎波里出發,走進撒哈拉沙漠華氏一百二十度的酷熱之中。土地在一年中的那個時候是如此乾旱,連他的駱駝都瘦成了皮包骨。他的嚮導在沿海地帶表現得溫和親切,愈往南走卻變得愈貪婪,當他們走到大小相當於加州,一片熾熱的塔奈茲魯夫特平原(Tanezrouft)時,他顯然是把萊恩出賣給了一群圖瓦雷克人(Tuareg)。全副武裝的男人在深夜包圍了這位探險家的帳篷,開槍射擊並拔刀砍殺,然後把他拋下等死。萊恩對自己在這次襲擊中傷勢的敘述,是殖民地部檔案卷宗裡最不同凡響的創作之一。那是一八二六年五月十日在廷巴克圖北方兩百英里處的一個沙漠營地寫下的,直到此時為止,他送來的信件都以一種華麗而前傾的銅版印刷體寫成,而這封如今已霉斑點點、摺線被撒哈拉塵土染黑了的信,字跡卻是忽上忽下、凌亂潦草,據他解釋,這是用左手寫下的。
「親愛的領事:」他寫道:「我寫這封信,交給不確定能否送達的信差,只是為了告知:我正從嚴重創傷中復元……遠遠超過最樂觀的預期所能估計的。」事件的詳情是令人驚異的「卑劣背叛與戰鬥」故事,但只能容後詳述;眼下他要告知領事的,是在攻擊中遭受的創傷數量及性質:
從頭開始,我的頭頂被軍刀割傷五處,左太陽穴三處,每一道傷口都深可見骨,另一刀砍在左臉頰,造成頷骨骨折,耳朵也被砍裂,留下很不雅觀的傷痕;另一刀砍在右太陽穴,頸背也有一處可怕的切口,稍稍劃傷了氣管。
他的臀部上也留著一枚火繩槍彈,這發彈丸一路穿透他的身體,擦傷了脊椎骨;右臂和右手掌也有五處軍刀刀傷,「橫切過手臂四分之三」,兩手腕骨也被穿透了;左臂也有三處刀傷並且骨折,右腿輕傷一處,左腿兩處,包括一處「可怕的切口」,更不用說他用來寫字的左手手指受到的打擊。
細看這份創傷清單,一如焦急的領事六個月後在的黎波里收到信件時那樣,讀者們想必也在尋找撤退的跡象。萊恩必定打算一等身體狀況許可,就盡可能從最快的路徑撤退,並籌畫一套在歸途中防範盜匪的辦法吧?恰好相反。地平線彼端不曾被歐洲人視線驚擾的廷巴克圖吸引力實在太強,他絕不願在此時放棄而自取其辱。他告訴領事,即使有傷在身,仍然「進展順利」。他還不想帶著「許多重要的地理資訊」返回英格蘭。他已經發現許多必須在非洲地圖上更正之處,如今只求上帝假以時日,讓他完成任務。
將近兩個月後,萊恩再次來信。他的狀況惡化了。營地遭受類似黃熱病的「可怕疾病」侵襲,使團半數成員喪生,包括他最後僅剩的僕人。「如今我是使團裡唯一還活著的成員,」他痛苦地告知領事:「我的狀況一點都不好。」但他對自身命運的預感是這麼強烈,他決心繼續前進:
我非常明白,要是我不去探訪,全世界將永遠(對廷巴克圖)一無所知……因為我所說的「在我之後絕不會再有基督徒造訪它」,絕非妄作論斷。
六星期後,萊恩終於實現了他偉大的抱負,在一八二六年八月十三日踏進了廷巴克圖。接著發生一件有些詭異的事:他沉默了。
整整五個星期,他完全沒有寄給領事隻字片語。直到九月二十一日他才再度寫信,而這封信只有短短五百字。他仍然用左手握筆寫字,此時的筆跡變得逼仄而僵硬。他告訴領事,他的性命受到威脅,急著動身離開:
我沒有時間詳述我在廷巴克圖(Tinbuctu)的見聞,但我應當簡短聲明:除了規模大小之外(周長不大於四英里),它在每一方面都完全符合我的預期……我在此停留期間十分忙碌,在城中到處搜尋記載,資料量龐大,取得各式各樣情報;而我說自己的不屈不撓充分得到了報償,如此的滿足也絕非常情所能測度。
寫下這封信的次日,萊恩離開廷巴克圖,從此也走出歷史之外。領事將最後一封信轉呈倫敦,並附上一段近乎宣布勝利的案語─這是「基督徒從該地寫來的第一封信」;但在傳達這個歐洲地理重大目標的資訊上,萊恩的遠征卻是一敗塗地。倘若廷巴克圖「完全」符合了他崇高的期望,詳情究竟是什麼?最令人困惑的是,萊恩斷言城中有著豐富的記載,而他從其中取得了「各式各樣的情報」。究竟是怎樣的情報足以引起一位軍人的注意?對於英國政府又有什麼用處?
將近兩百年後,人們清楚知道了所謂「城中的記載」,是多半以阿拉伯文寫下的大量文本的其中一部分,它們如今被合稱為「廷巴克圖手抄本」(the manuscripts of Timbuktu)。這座城市的文獻數量多到幾乎沒人知道確切數字,而萊恩似乎是第一個看到它們的歐洲人,儘管一般認為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它們包含了十五和十六世紀的廷巴克圖,乃至這個城市所屬的偉大桑海帝國(Songhay Empire)所謂黃金時代中一些最珍貴的書寫史料,並被專家們譽為相當於《死海古卷》、《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的非洲重要文物,見證了這片大陸鮮活的書寫歷史。
二○一二年,這段歷史似乎遭受威脅。在馬利南部一場政變之後,廷巴克圖被伊斯蘭北非基地組織(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的戰士攻陷。聖戰士隨即開始有系統地摧毀聳立於城內數百年之久的蘇菲派聖者陵墓。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廷巴克圖市長向全世界宣布,城內所有的古代手抄本也已付之一炬。
我清楚記得那個早晨。那時我是《衛報》的國際新聞主編,而馬利對我而言更有特殊意義。好多年前,在我十八歲時興起了駕車跨越撒哈拉沙漠的想法。我存錢買了一臺舊的路華(Land:Rover)汽車,和一位朋友一起從約克郡(Yorkshire)出發,經由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前往馬利,在一九八七年春天抵達。阿蓋洛克(Aguelhok)這座沙漠城鎮是跨越沙漠之行的終點,也是我們旅程的顛峰,我們一到那兒就有了新的想法:要是我們用這臺破車交換三四隻駱駝,一路騎到廷巴克圖去呢?我們能說的故事會有多麼精采!我們找到一位商人,交涉了一星期,但他只能找來一隻瘦小的駱駝,我們只好放棄這個計畫,繼續南下。我在古代桑海帝國的首都加奧(Gao)賣了車,繼續旅行到布吉納法索和象牙海岸,然後回家。我沒去成廷巴克圖,但我愛上了沙漠旅行這個想法。我在一九八九年開著另一輛車來到撒哈拉,但它太不可靠,無法冒險開到馬利。那座三百三十三位聖者的城市又一次可望而不可及。
二○一二年七月,我悲憤地看著聖戰士搗毀廷巴克圖紀念物的影片。隔年一月,當我們的特派員得知叛軍縱火焚燒這座城市的歷史文獻,我們在《衛報》線上版以頭條刊登這則新聞。幾天過去,情況逐漸明朗,手抄本其實並未被毀,實際上,他們都被城裡的圖書館員偷運到了安全地方。我開始深深著迷於這次行動的詳情深深著迷。在我看來,這次行動和羅伯‧克萊頓(Robert Crichton)的滑稽小說《祕密大戰爭》(The Secret of Santa Vittoria)遙相呼應,在那個故事裡,一個托斯卡尼小鎮的鎮民從納粹劫掠中搶救了一百萬瓶酒;唯一的差別在於,這次行動遠勝於小說:廷巴克圖的寶藏意義重大不知多少倍,更重要的是,這次撤運乃真有其事。於是我辭去工作,決心將這個故事寫成一本書。
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曾經留意到,世上有兩個廷巴克圖。一個是真實存在,坐落在尼日河(the Niger)轉彎進入撒哈拉沙漠之處的那個有氣無力的商隊城鎮;另一個則是完全虛幻、位在烏有之地的傳奇城市,它是心靈中的廷巴克圖。我打算沿著兩條交錯的軸線,敘述這兩個廷巴克圖:其一是西方長達數百年之久尋找、征服和理解這座城市的奮鬥,其二則是當代拯救它的手抄本與歷史免遭毀滅的努力。第一個敘述要探討傳說在形塑我們對廷巴克圖的看法時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個則要講述占領與撤運的故事。
而我那時還不明白,這些故事竟是多麼密切地映照著彼此。
廷─巴克─圖(Tim-buk-too)。這三個短音節的地名由來一直眾說紛紜。它們是指住在尼日河灣最北端五英里之外這片留名青史之地的女奴巴克圖(Buktu)的「牆」或「井」嗎?或者它們是桑海語,意指「一個大肚臍女人的營地」?或者,它們純粹是指一片藏身於沙丘之中的低窪地帶?這個字的由來有多種理論,其發音和拼法也有很多種,布魯斯‧查特文稱之為一套「禮儀慣例,聽過就記住不忘」。明確的事實似乎是,此地在西元一一○○年前後就建立了聚落,由於地處世界最大的熱帶沙漠和西非最長河流的交會點,得以成為重要的市鎮。
撒哈拉沙漠綿延三百六十萬平方英里烈日曝曬的土地,從大西洋伸展到紅海,又從地中海延伸到薩赫爾地帶(Sahel)。它涵蓋的地表面積比起美國和中國本土,或是澳洲大陸都更加廣闊。它在大眾的想像裡是由一望無際的沙丘構成,但這片沙海儘管存在,面積卻不及整個撒哈拉沙漠的六分之一。圖瓦雷克人稱撒哈拉沙漠為「提那瑞文」(tinariwen),意思是複數的「沙漠」,以此反映它的多種不同性質。那裡有高達一萬一千英尺,直入雲霄的山嶺,也有面積一如安大略湖的鹽灘,流沙足以吞噬一部汽車。但絕大部分還是數十萬平方英里平坦而裸露的岩石。
六千年前的撒哈拉是一片綠地,大象、長頸鹿和犀牛漫步其間,飲水於湖泊並啃食植被。如今撒哈拉的大部分地區可以好幾年不下一滴雨,一旦真正降雨,就會有滾滾洪流在地表上沖刷出深溝,隨後即消失無蹤。相當程度上,這裡也是地球最熱的地方,遮蔭處的溫度可達華氏一百四十度;但在冬夜裡,沒有厚厚的雲層遮蓋,也沒有土壤和植物,沙漠也可以凍成一片銀白。而在這片不毛的大地上空,熱空氣層和冷空氣層的碰撞產生了暴風,可連續吹上五十天,捲起令人窒息的沙塵遮蔽太陽,更掀起沙龍捲殺害動物、拔起樹木。
倘若沙漠憎恨生命,那麼在它的西南角,沙漠則和西非的生命力相遇;這是一片當地人稱為「焦利巴」(Joliba)的水體,意思是「大河」或「河中之河」,世界其他地方則稱之為尼日河。尼日河發源於幾內亞富塔賈隆(Futa Gallon)高原一處兩千八百英尺高的峽谷,這片高原也是全世界最潮濕的地區之一。富塔賈隆高原是非洲三條大河的發源地,另外兩條河分別是甘比亞河和塞內加爾河。這兩條大河分別成為一個國家的名字,但偉大的尼日河同時成為兩個國家的國名(尼日和奈及利亞)。要是這條河流循著最短路徑注入大西洋,將會是一條一百五十英里長的陡急激流,但它卻信心滿滿地往反方向出發,向東北方游曳,不可思議地在尼日河灣的巨大回轉裡滑進了沙丘中間,直到注入距離發源地兩千六百英里的貝南灣(Bight of Benin)為止。
史詩般的旅程走了大約三分之一時,尼日河迷失在一片三百英里長的平坦內陸三角洲裡。自空中鳥瞰,就像一條小河在流過沙灘時逐漸耗盡,水流分成了數十條淺淺的水道和溪流。尼日河三分之二的水流在此消散,乾季結束之前,大片河床都枯乾了。到了七月,當雨水再度落下,浩大水勢滾滾向下流,乾涸的水道和湖泊再次滿盈,生命也再次綻放。水草和菰米(wild rice)怒放,魚類與昆蟲繁衍,白鷺和琵鷺前來加入河馬、鱷魚和海牛的行列。牧牛人駕著他們的牛來到沿河生長的草地,農人則收成稻米、高粱和小米。
廷巴克圖位於這片三角洲的下游末端,也在河灣的最北端。它位於河上貿易與沙漠商隊路線的交叉路口,古老的格言是這麼說它的:「每一個乘坐駱駝或獨木舟旅行的人」會合之處。
如同尼羅河每年一度的氾濫孕育了古埃及王國,尼日河肥沃的內陸三角洲也滋養了自己的文明。即使在古典時代,這些地方的消息也輾轉傳回了歐洲。希羅多德(Herodotus)在西元前五世紀提到,沙漠的遠處有一條充滿鱷魚的河流,河岸上則有一座黑人巫師居住的城市。五百年後,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則描述了生活在那裡的駭人部族,包括「半人半獸」的羊人(Aegipani)、不會說話,只能發出蝙蝠般吱吱聲的穴居人(Troglodytes)、以及「沒有頭,嘴巴和眼睛都長在胸前」的無頭人(Blemmyes)。這些畸形人類的傳說一直流傳到了中古時期:大約一三○○年前後繪製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圖(Hereford Mappa Mundi)將無頭人和穴居人描繪在非洲,日後的歷史學家則將普林尼描述的非洲人誇大成一隻眼睛長在額頭中間,或是舉起一隻巨足就能夠遮蔽太陽的人。
公元七世紀時,基督教歐洲通往非洲的道路,被西進橫掃地中海南岸直抵大西洋的穆斯林大軍阻斷,此後一千兩百年內,撒哈拉之外的消息就只剩下經由往返於沙漠的商人輾轉傳來的回聲。這些消息通常是捕風捉影,有好幾篇傳回中古歐洲的報導,都提及巨大的螞蟻在非洲河床上獲取黃金,但對這個地區財富的傳聞卻是有所本的。在西班牙人殖民美洲之前,地中海世界流通的全部黃金有三分之二來自蘇丹。穆斯林地理學家伊德里西(Muhammad al-Idrisi)在十二世紀時講述,古代迦納的國王十分富有,他有「一整塊三十磅重的黃金,並非其他任何器具加工或鑄造,只能由真主旨意完美塑造」,而在十四世紀,一位人類歷史上旅行經驗最豐富的旅人─伊本‧巴圖塔(Ibn Batutta),則記錄了馬利皇帝穆薩一世(Musa I)的事蹟。有時被稱為曼薩‧穆薩(Mansa Musa,即穆薩王)的穆薩一世,據說在一三二四年前往麥加朝覲,隨行人員包括六千名士兵和五百名奴隸,還有一噸黃金供沿途消費之用;他隨心所欲地揮霍財富,導致開羅的黃金價格貶值了一個世代之久。
又過了五十年,廷巴克圖第一次出現在歐洲地理上,那是一三七五年由馬約卡島的製圖師柯雷斯克(Abraham Cresques)呈獻給西班牙國王的已知世界全圖《加泰隆尼亞地圖集》(Catalan Atlas)。這座城市的名稱被拼為「登布赫」(Tenbuch),從一開始就和財富連結在一起,因為柯雷斯克將穆薩畫在城市旁邊,穆薩手中握有巨大的黃金權杖和一塊大金磚,頭戴沉重的金皇冠。日後的報導似乎證實了柯雷斯克的資訊:一四五四年,一位接受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親王(Princen Henry the Navigator)資助的威尼斯船長,到達的黎波里南方的貿易綠洲瓦當(Waddan),帶回一段關於駱駝商隊攜帶岩鹽到「坦布圖」(Tanbutu),再到「黑人帝國梅利」(Melli)換取大量黃金的記載。可是一直到了十六世紀,才有一部廷巴克圖的第一手記載在歐洲問世,最終確認了這個由黃金打造的傳說。
這位旅行者名為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瓦贊‧札亞迪(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 al-Zayyati)。他的生平資料相當簡略,一般認為他出生於格拉納達(Granada),少年時代遷居費茲(Fez)並受到良好教育。大約在一五○六至一五一○年之間,據說十七歲的他和一位叔叔加入派往蘇丹的外交使團,造訪了廷巴克圖。十年後他被基督徒海盜俘虜,送往羅馬,由教宗利奧十世(Leo X)釋放並改信基督,改名為約翰尼斯‧利奧‧梅迪奇(Johannis Leo de Medicis),隨後成為利奧‧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利奧在義大利定居,寫了幾本著作,但最為轟動一時的仍是他在《非洲記述》(Description of Africa)之中描述的蘇丹生活:據說,他為歐洲人發現了一個新世界,程度不亞於哥倫布找到美洲。
廷巴克圖在利奧的敘述中,是一座富裕而迷人的城市。儘管房屋多半由泥磚和茅草築成,市鎮中心卻有「一座寺院,由一位(西班牙南部)貝堤卡(Béticos)的建築師由砌石和灰泥築成……以及由同一位建築大師興建的宮殿,這是國王的住所」。城內有幾處水井湧出甘泉,還有豐富的糧食、牛、牛奶和牛油,鹽卻十分昂貴,因為要從五百英里外沙漠中的鹽礦運來。他提到這個城市的居民都「非常富有」,他們不用錢幣,而是以小塊純金消費。廷巴克圖的國王除了指揮一支由三千名騎兵和大量發射毒箭的步兵組成的常備軍,也擁有「錢幣和金錠的龐大財寶」,其中一塊金錠重達三百磅,宮廷也很「壯麗」:
國王和朝臣在各個城鎮之間巡行時,他都騎著駱駝,馬隊則由馬伕引導。倘若必須作戰,馬伕就將駱駝的雙腿綑綁,士兵則全體上馬。有人要向國王陳情的話,就在國王面前跪下,手捧一把沙土,灑遍自己的頭和肩膀。
城市裡的居民天性無憂無慮。「他們習慣在深夜十點到凌晨一點之間於城中遊盪,演奏樂器和舞蹈,」利奧寫道。城市裡還有很多有教養的人,這座城市十分愛好手抄本,手抄本在市集中的價值高於其他商品:
廷巴克圖有眾多法官、學者和教士,他們被十分敬重讀書人的國王重金禮聘。還有許多來自巴巴利海岸(Barbary)的手抄本在此販售。這門生意比其他商品獲利更多。
利奧的著作廣受譯介,其在一六○○年發行的英文版,激起一波人們對非洲的興趣;它是莎士比亞劇作《奧賽羅》(Othello)的可能改編來源之一,而它對撒哈拉以南地區財富的記載,則激勵英國探險家追趕著葡萄牙人,沿著幾內亞海岸更往南方深入。一六二○年,英國紳士理查‧約布森(Richard Jobson)率領探險隊抵達甘比亞海岸的騰達(Tenda),該地的一位非洲商人告訴他,上游遠處有一座名為通博康達(Tomboconda)的城鎮,「房屋鋪滿黃金」。約布森的遠征紀錄,在一六二五年由文集編纂者薩繆爾‧珀切斯(Samuel Purchas)重新發行,編者力勸同胞進一步探勘非洲大陸。「世上最富饒的金礦就在非洲,」珀切斯寫道:「我不得不疑惑為何這麼多人、派了這麼多人,花了這麼多時間前往東方與西方更遙遠之處,卻忽略了兩者之間的非洲。」
到了十八世紀晚期,黃金廷巴克圖的傳說已經確立於歐洲人的想像之中。它是吸引著歐洲人深入西非心臟地帶的冒煙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