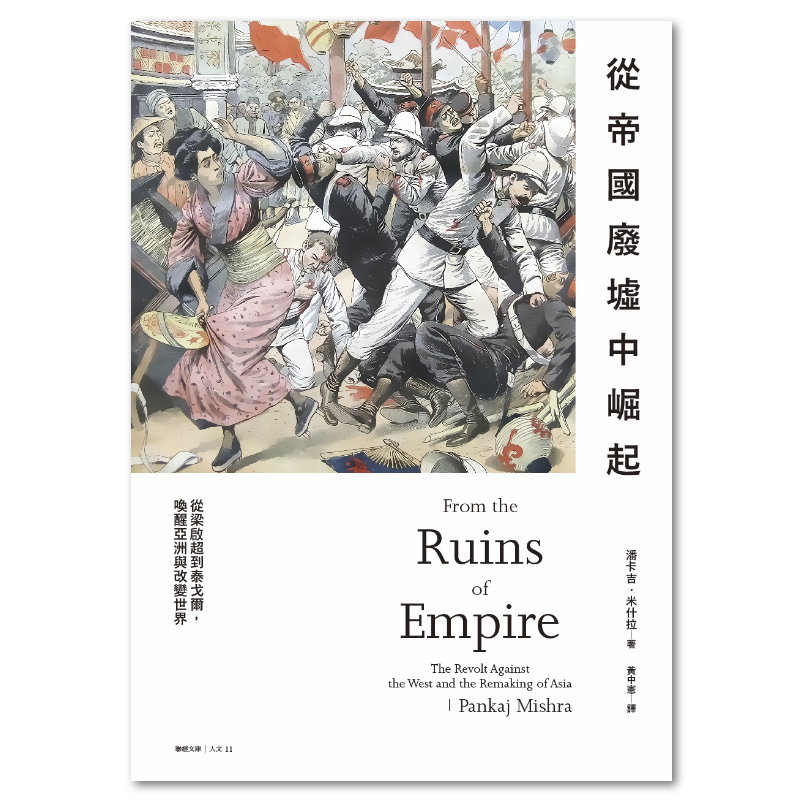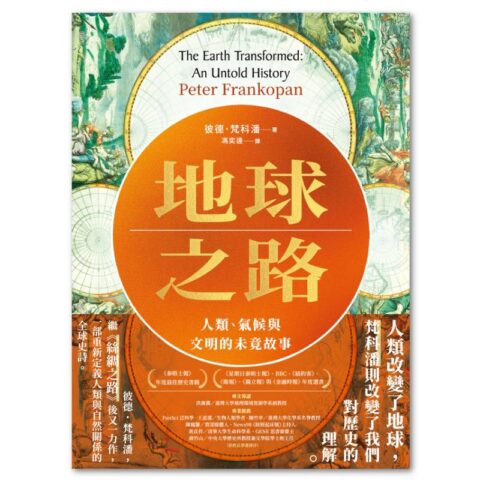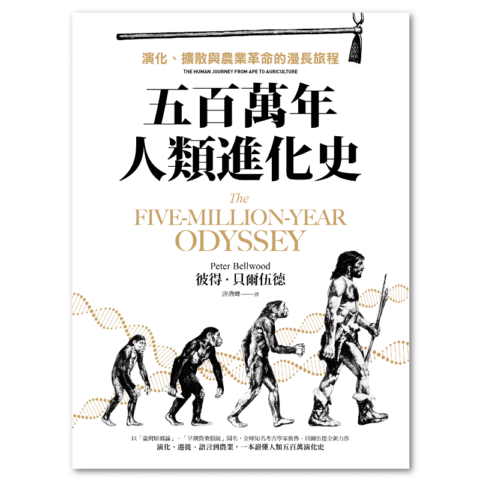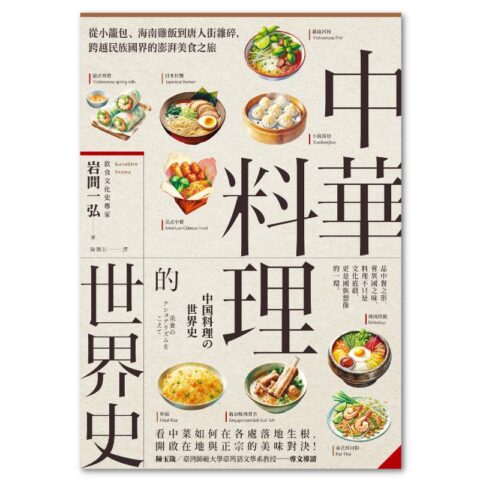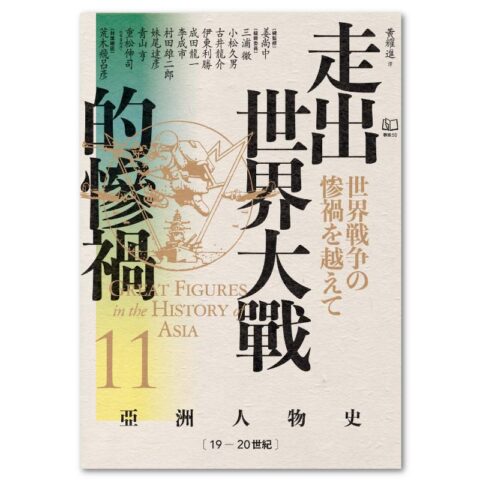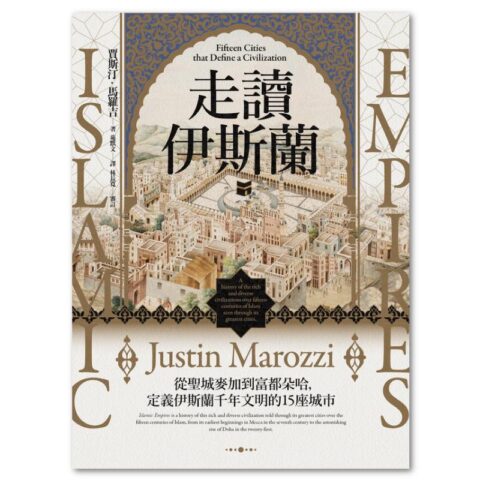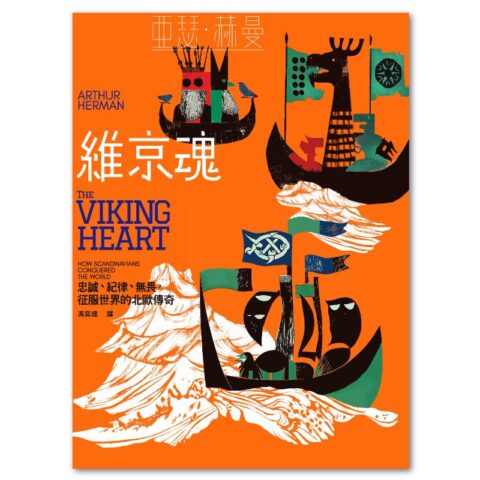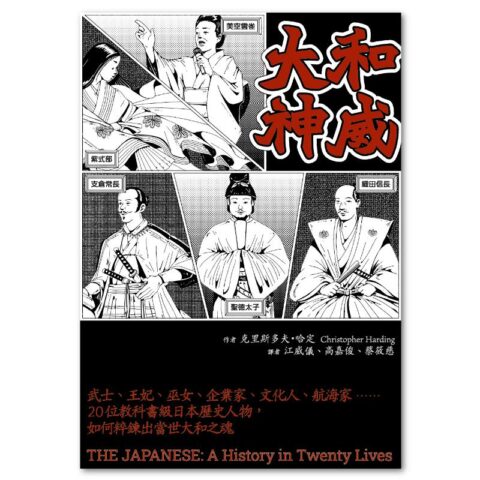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
原書名: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出版日期:2013-08-23
作者:潘卡吉‧米什拉
譯者:黃中憲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16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2371
系列:聯經文庫
已售完
《經濟學人》譽為「薩依德的繼承者」
《外交政策》評為「全球百大思想家」
2012年獲選《經濟學人》年度最佳圖書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大力推薦
何謂亞洲的價值?
亞洲各國如何從西方帝國的廢墟中重生?
亞洲各地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知識份子,試圖擺脫傳統的框架,尋求抑制西方國家對亞洲大陸日漸增長的支配欲望、尋找亞洲重生的道路,進而重塑亞洲。
潘卡吉‧米什拉的《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從世紀初的日俄戰爭開始談起,述及日本將霸權一舉伸向韓國及太平洋部份地區,因其打敗強大的俄羅斯帝國,由此次的空前勝利對亞洲國家各地的知識份子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中國的梁啟超、孫中山,印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伊斯蘭之父賈邁勒丁‧阿富汗尼,他們都想像當時的日本一樣,開始東方國家政治與經濟的改革。然而本書作者潘卡吉‧米什拉卻以不同的角度,呈現給讀者亞洲歷史文化的另一面向:這些思想家的見聞,建構了亞洲現代哲學的思想理論,並向大眾展現他們共同嚮往亞洲擁有更為宏遠的目標,但其實現在的亞洲國家卻是盲目採用西方的模式,盲目跟隨西方政治、經濟思想,導致亞洲喪失本身的文化,同時更承襲西方國家的惡習。
《從帝國廢墟中崛起》結合了東方的政治思想,集結印度、中國及阿拉伯的精神,是一本不容忽視的預言式作品。
在西方人眼中,昂揚大步向外擴張的維多利亞時期,在亞洲人眼中卻是場浩劫。外國軍人和商人瓦解原是文明核心的大帝國。隨著英國人以船堅炮利拉下蒙兀兒帝國的末代皇帝、燒掉北京圓明園、羞辱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破產統治者,因此,探索救亡圖存之道是亞洲國家的當務之急。
潘卡吉‧米什拉以引人入勝、趣味橫生的筆觸,講述亞洲大陸上一群有智之士如何迎接西方挑戰。他們不斷地質問、掙扎、深感痛苦,既痛恨西方,又體認到得與敵人正面交鋒及向敵人學習,亞洲才有復興可言。經過許多挫敗和誤入歧途,一連串強有力、彼此矛盾且最終勢不可擋的觀念誕生,成為如今從中國共產黨到凱達組織,從印度民族主義到穆斯林兄弟會的種種勢力背後之動力根源。
米什拉透過遊歷歐亞各地的記者、詩人、激進份子、克里斯瑪型領袖的眼睛,引領讀者重新審視過去兩百年的歷史。這些思想家坐在當時似乎注定會被列強永久瓜分的舊帝國的廢墟之中,構思出反過來將使新帝國注定走向滅亡的觀念,且這些觀念還成為支撐二十一世紀亞洲大國的支柱。
※ 名家推薦
米什拉以敏銳、博學又有趣的態度呈現亞洲思想家如何回應西方逐漸衰頹的霸權,這位著名的當代印度知識份子是「薩伊德的繼承者」。
──《經濟學人》
米什拉反轉了長期由西方角度看東方的視角,呈現了世界上大多數民眾──從土耳其到中國──所感受認同的現代歷史。
──罕・帕慕克(Orhan Pamuk,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文學大師)
一本非常棒且突破創新的著作。這不只是一部卓越的亞洲史,更是一部為亞洲人所寫的生動歷史。
──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美國小說家,貝蒂特拉斯克獎得主)
《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以極具說服力的言辭,描繪一群亞洲最有教養、最有洞見的知識份子令人好奇且複雜之思想歷程。
──茱莉亞・洛弗爾(Julia Lovell,英國歷史學家,《鴉片戰爭》作者)
富有深入的研究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創性……任何想了解今日我們處在怎麼樣的環境的人,都應該將這本具洞察力又令人不安的書放在必讀書單上。
──約翰・格雷(John Gray,《獨立報》專欄作家)
繼薩依德的經典著作《東方主義》後,《從帝國廢墟中崛起》提供另一種令人振奮的現代歷史觀點。米什拉相當博學……是善於抓住讀者目光的敘事者。
──汪暉(北京清華大學思想史教授)
米什拉機敏且幽默地結合被忽略的歷史材料,傳達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展乃是亞洲的知識覺醒和政治覺醒」的重要主張。
──哈里‧昆茲魯(Hari Kunzru,《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作者:潘卡吉‧米什拉
1969年生於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英美文學碩士,長期為《紐約書評》、《紐約時報》、《衛報》撰寫評論,是小說家、散文家,也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提名的「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在第一本著作Butter Chicken in Ludhiana(1995)這本關於印度的社會學研究報告即嶄露頭角,之後更寫出許多重要作品:Temptations of the West: How to Be Modern in India, Pakistan, Tibet, and Beyond(2006)、《從帝國廢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2012)、A Great Clamour: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2013)等書。2008年被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會員,2012年,《經濟學人》則稱之為「薩依德的繼承者」,將《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列為「年度好書」。新作《憤怒年代》被《紐約時報》選為當年度最值得注目的書籍,獲Slate、NPR選為年度最佳書籍,並入圍「歐威爾獎」。
譯者:黃中憲
1964年生,政大外交系畢業,現專職翻譯。譯作包括《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帖木兒之後:1405~2000年全球帝國史》、《太平天國之秋》等。
前言
第一章:亞洲臣服
埃及:「一連串大災難的開始」
印度、中國的緩慢受創
新全球階層體系
第二章:哲馬魯丁‧阿富汗尼的奇異旅程
一個穿粗布衣的小人物
印度與阿富汗的覺醒
歐洲「病夫」和其危險的自我療法
埃及:辯論家出現
自強之外:泛伊斯蘭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起源
歐洲插曲
在波斯:最得意的時刻
金籠子:阿富汗尼在伊斯坦堡度過的晚年
餘波久久未消
第三章:梁啟超的中國和亞洲的命運
令人欣羨但舉世無雙的日本興起
頭幾波改革衝動
日本與流亡之險
拳亂:又一些得自挫敗的教訓
泛亞洲主義:世界主義之樂
梁啟超與美國的民主
獨裁與革命的誘惑
第四章:一九一九年,「改變世界史」
美國與其自決承諾
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
使世界有害於民主制度
西方的沒落?
第五章:泰戈爾,亡國之民,在東亞
第六章:亞洲再造
出人意表的結局:泛亞洲主義與軍事去殖民化
知識去殖民化:新傳統派的興起
伊斯蘭世界的反現代
民族國家的勝利:病夫土耳其重振雄風
「中國人站起來了」
「他者」的興起
結語:含糊不明的報復
參考書目淺談
中英對照
註釋
前言(節錄)
一九○五年五月的某兩日,在對馬海峽的狹窄水域,今日世界的格局開始定型。在這裡,當今世上最繁忙的航運路線之一,由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統率的一支日本小艦隊,對上繞過半個地球來到遠東的俄羅斯海軍艦隊,把後者打得幾乎全軍覆沒。對馬海戰,德國皇帝口中自百年前特拉法爾加海戰以來最重要的海戰,美國羅斯福總統口中「世界史上最重大的現象」,實質上結束了自一九○四年二月即開打,主要在決定朝鮮半島、滿洲由俄羅斯或日本掌控的一場戰爭。自中世紀以來,首度有歐洲以外的國家在重要戰爭中擊潰歐洲強國;這項消息傳遍了已被西方帝國主義者──和電報的問世──緊密結合在一塊的世界。
在加爾各答,守衛大英帝國最重視之領土的印度總督柯曾勛爵(Lord Curzon),擔心「那場勝利的回聲已像雷鳴一般傳遍東方竊竊私語的觀眾。」漠不愛與人交往且常出大紕漏的柯曾,難得一次探問當地民意,而把民意表達得最清楚者,乃是人在南非而當時仍沒沒無聞的律師甘地(Mohandas Gandhi,一八六九~一九四八)。他預測「日本戰勝的根已蔓生得太遠太廣,因而它會長出哪些果實,如今已無法完全預見。」
在大馬士革,後來人稱阿塔圖克(Atatürk)的年輕奧圖曼軍人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一八八一~一九三八)欣喜若狂。急欲改革、強化奧圖曼帝國以抵抗西方威脅的凱末爾,和許多土耳其人一樣早把日本視為榜樣,日本打敗俄國使他深信果然沒看錯。當時十六歲,後來會出任印度第一任總理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在家鄉看報,興奮追蹤日俄戰爭的早期進展,幻想自己為「印度與亞洲擺脫歐洲枷鎖」貢獻心力。得知對馬海戰的消息時,他正在火車上,從多佛前往他就讀的英格蘭哈羅公學途中;那使他立即「心情大好。」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聽到這消息時,人也在倫敦,同樣的雀躍。一九○五年晚期搭船返華途中,蘇伊士運河的阿拉伯搬運工以為他是日本人,向他道賀。
土耳其、埃及、越南、波斯、中國的報紙上,充斥著對日本戰勝之可能影響的興奮猜測。印度村莊裡有新生兒以日本艦隊司令之名命名。在美國,黑人領袖杜博伊茲(W. E. B. Dubois)提到全球各地迸發「有色人種的自豪。」反戰詩人(和後來諾貝爾獎得主)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一~一九四一),顯然也有類似的感受,在得悉對馬海戰的消息後,在孟加拉鄉間帶著他的學生,在小校園裡即興展開勝利遊行。
那和他們屬於哪個階級或哪個種族沒什麼關係;世上遭宰制的人民強烈體會到日本戰勝的更深層意涵——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意涵。這些人出身的差異之大令人吃驚。尼赫魯出身親英的富裕婆羅門家庭;他父親是英國統治印度的受惠者,甚至據傳將襯衫送到歐洲乾洗。孫中山是貧農之子,當時不少中國苦力赴加州淘金,他有個兄弟就死於加州淘金熱時。當時最傑出的泛伊斯蘭主義知識分子,一九○九年前往日本以結交日本政治人物和行動主義者的阿卜杜雷希德‧易卜拉欣(Abdurreshid Ibrahim,一八五七~一九四四),出生於西伯利亞西部。凱末爾來自薩洛尼卡(今屬希臘),雙親分屬阿爾巴尼亞裔和馬其頓裔。他後來的同志,以日本艦隊司令的姓──東鄉──替自己新生兒取名的土耳其女小說家哈莉德‧艾迪普(Halide Edip,一八八四~一九六四),是個不受宗教約束的女權主義者。緬甸的民族主義象徵烏‧奧塔瑪(U Ottama,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受日本戰勝俄國的鼓舞,一九○七年搬到東京,而他是個和尚。
為俄國戰敗而歡欣鼓舞的諸多阿拉伯、土耳其、波斯、越南、印尼民族主義分子中,有一些人的背景更為分歧。但他們都有一共同的經驗:遭他們長久以來視之為暴發戶、甚至野蠻人的西方人宰制。他們都從日本的戰勝得到一個教訓:征服世界的白種人不再是所向無敵。遭歐洲人控制國土而敢怒不敢言的有志有識之士,如今心裡綻放出無數幻想,民族自由、種族尊嚴或純粹只是報復洩恨的幻想。
鑑於十九世紀遭西方列強欺凌,且凜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粗暴對待,日本從一八六八年起展開浩大的內部現代化工程:廢除半封建的幕府將軍體制,代之以立憲君主制和統一的民族國家,創立高生產、高消費的西式經濟體。在一八八六年暢銷書《將來之日本》中,日本最著名記者德富蘇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詳述了日本若漠然無視西方所立下的「普世」潮流,可能會有什麼負面影響:「那些藍眼紅鬍種族將像巨浪般入侵我們國家,把我們的人民趕到海中孤島。」
一八九○年代,日本日益壯大的工業、軍事力量,已激起歐美「黃禍」降臨的想像,亞洲人席捲白種西方的可怕情景。俄羅斯戰敗正證明日本迎頭趕上西方的計畫已取得驚人成果。「我們要戳破非白種人劣等的迷思,」德富蘇峰嚴正宣告。「我們要以自己的力量躋身世界強權之林。」
對許多非白種人來說,俄羅斯的慘敗似乎正打破了西方的種族階層觀,大大嘲弄了歐洲人欲將據認「落後」的亞洲國家「文明開化」的傲慢。印度的社會學先驅貝諾伊‧庫瑪爾‧薩卡爾(Benoy Kumar Sarkar,一八八七~一九四九)嚴正表示,「白人的負擔」一說「已和時代脫節,如今只有最盲目的狂熱分子不這麼認為。」8日本已證明亞洲國家能找到自己通往現代文明之路和自己的特殊活力。青年土耳其黨(Young Turks)的行動主義者,後來出任部長的艾哈邁德‧里札(Ahmed Riza,一八五九~一九三○),扼要說明了這一迴蕩於眾人心中的欽敬之情:
遠東的情勢已證明,歐洲頻頻但有害的介入,無益於改造一民族。相反的,一個民族愈是和歐洲入侵者、掠奪者少接觸,愈是不和他們接觸,就愈可能走上理性革新之路。
甘地在白人所統治的南非與形諸體制的種族歧視抗爭時,從日本的戰勝得到類似的道德教訓:「當日本境內的每個人,不管是富是窮,都開始相信該自尊自重,這個國家就得到自由。她能甩俄羅斯一巴掌……同樣的,我們也必須有自尊心。」
中國哲學家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回憶起從鴉片戰爭到燒毀北京圓明園,西「夷」所加諸中國的百年羞辱,推斷「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
日本已證明可如何富國強兵。對許多受苦於昏庸專制君主和掠奪成性之歐洲商人的亞洲人來說,日本的憲法是其躋身強國之林的秘鑰。在日本改革有成的鼓舞下,亞洲各地的政治行動主義者協助推動一連串人民立憲革命,以對抗食古不化的獨裁政體(戰敗的俄國本身於一九○五年突然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奧圖曼統治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一八四二~一九一八)蘇丹,已緊緊追隨日本的現代化腳步,特別是在歐洲列強日益升高的需索使伊斯坦堡的主權地位如同虛設之時。但在穆斯林世界,許多景仰日本者是極世俗化、甚至反宗教的民族主義者,例如流亡國外的青年土耳其黨黨員暨作家阿卜杜拉‧傑夫戴特(Adbullah Cevdet)。在他筆下,日本是「對抗壓迫者,對抗傲慢入侵者的利劍;指引受壓迫者,指引有意看清自己的火炬。」在日本戰勝的鼓舞下,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青年土耳其黨,一九○八年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蘇丹重新施行一八七六年起就遭擱置的憲法。波斯人受立憲日本擊敗獨裁俄國的鼓舞,一九○六年創立全國代表大會。
同年,埃及出現第一次反英國占領的大規模群眾示威。在埃及的民族主義穆斯林眼中,日本是「旭日」:日俄戰爭爆發前不久,埃及的民族主義領袖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一八七四~一九○八)寫了以此為書名的一部著作。穆斯林國家的學生,這時前往東京學習日本進步的秘訣。連在最近才被荷蘭殖民主義者統一的印尼群島,都感受到日本戰勝的骨牌效應,該地的上層爪哇人於一九○八年創立了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
最深遠的改變出現於中國,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一九○五年後數千中國人前往日本取經,造就出當時最大的集體留學潮。推翻帝制後的中國第一代領袖,有許多將出自這群留學生。一九一○年,湖南一小鎮上的學童毛澤東(一八九三~一九七六),學會曾留學日本的音樂老師教他的一首日本歌:
麻雀唱歌,夜鶯跳舞,
春天裡綠色的田野多可愛。
石榴花紅,楊柳葉綠,
展現一幅新圖畫。
幾十年後日本威脅中國時,毛澤東仍完全記得其歌詞,說「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日本的美,我又從這歌曲中感覺到它對於戰勝俄國的光榮和武功的發揚。」
在其他地方,日本戰勝俄國一事也激發愛國情操,甚至將這份情操推向極端。西化的本土菁英分子所心嚮往之但未能實現的自由民族主義,乃是在這一新情操下沒頂的東西之一。暴動和恐怖攻擊,證實了印度國大黨所一直以來只敢委婉表露的反殖民情緒,自一九○五年起日益強硬。在加爾各答和達卡,激進分子開始支持孟加拉學生前赴東京,以歐美為大本營的反殖民鼓動者,與愛爾蘭、俄國革命分子和中、日領袖搭上線,以將武器偷偷運到孟加拉。
法屬印度支那的文人也開始追求革命暴力。越南民族主義先驅潘佩珠(一八六七~一九四○),一九○五至一九○九年落腳日本,教導許多在其東遊運動號召下來日的法屬印度支那學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戰爭觀和生存鬥爭觀,開始污染儒家中國、伊斯蘭埃及和佛教錫蘭境內的政治論述。在開羅,拉希德‧里達(Rashid Rida,一八六五~一九三五)興奮寫到使日本皈依伊斯蘭,把歐洲人腦海裡的「黃禍」轉化為擺脫異教徒宰制的泛亞洲運動的可能性。後來,他的著作成為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誕生的推手之一。
對馬海戰十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殺戮,將使歐洲在亞洲人眼中僅剩的道德威望喪失大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征服亞洲之舉雖然落敗收場,卻將有助於使亞洲大陸許多地方擺脫國困民疲的歐洲帝國日益薄弱的掌控。但長遠來看,為西方的退場讚美詩奏出退場樂者似乎是對馬海戰。
對馬海戰所未能立即扭轉者,乃是在十九世紀大半歲月令亞洲、非洲無力招架的西方武器、商業優勢。德國出兵教訓反西方的中國義和團,美國鎮壓菲律賓境內的一場叛亂,英國在印度士兵協助下攻打在非洲南部的荷蘭殖民者,為二十世紀揭開序幕。到了一九○五年,這些戰爭都已結束,中國、菲律賓臣服,南非被納入英國統治。西方要再過許多年才會放掉其所占有的東方領土。但日本戰勝俄國使一個無可逆轉的過程加快──那即使還談不上是政治去殖民化的過程,但至少是知識去殖民化的過程。
孫中山於一九二四年赴日演講時,回憶起十九世紀死氣沉沉的最後十年,說那時候「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於現今),以為歐洲的文化是那樣進 步,科學是那樣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為亞洲一定不能抵抗,一定不能脫離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
孫中山說,日本擊敗俄國給了亞洲人民「大希望」:「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他還說,不到二十年,埃及、土耳其、波斯、印度、阿富汗、中國境內的獨立運動也已壯大。一如甘地於一九○五年所預測的,「東方人民」終於要「從昏睡中醒來。」柯曾勛爵所憂心的東方人的竊竊私語,將在不久後升高為敞開喉嚨喊出的主張和要求。一盤散沙的眾人將集合起來組成群眾運動和造反。他們將以驚人迅猛之勢激起革命,扭轉現狀。
歐洲對亞洲的控制,將從二十世紀初的最盛期急劇衰退;到了一九五○年,印度、中國都已成為主權國家,歐洲在亞洲將淪為無足輕重的勢力,完全靠最新的西方強權美國支撐,且日益倚賴由軍事基地、經濟壓力、政變構成的非正式帝國。歐洲人、美國人將先後發覺他們低估了亞洲人消化現代思想、技術、建制(institution)──西方稱雄的三個「秘鑰」──然後用它來對西方本身的能力。他們未能注意到,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到穆勒的歐洲大部分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眼中不適於自治的那些人,追求平等與尊嚴的強烈念頭。諷刺的是那些思想家的思想將對這些「受支配民族」產生意想不到的強烈影響。
如今,從土耳其到中國的諸多亞洲社會,似乎生氣勃勃且自信。但十九世紀把奧圖曼帝國、清帝國斥為「生病」、「垂死」的那些人,對亞洲社會的觀感並非如此。經濟支配權從西方轉到東方這個備受期待的轉變是否真會發生,還說不準,但世人觀看世界史時無疑有了新的視角。對歐美大部分人來說,二十世紀史大體上仍以兩次世界大戰和其與蘇聯共產主義的長期核僵局為主軸。但如今的情勢愈來愈清楚表明,對世上過半數人口來說,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展,乃是亞洲的知識覺醒和政治覺醒,以及亞洲從亞洲帝國、歐洲帝國兩者的廢墟中站起來。承認這點,就表示不只從世界的現狀來理解世界,還理解到世界正如何以配合過去受支配民族之抱負與渴望的方式,而非按照西方的模式,繼續被改造。
在這場漫長的現代亞洲改造過程中,誰是主要的思想家和改造者?他們眼中我們所置身的世界和後代子孫所將置身的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本書致力於解答這兩個疑問,而方法是從亞洲的幾個不同角度檢視現代世界史(本書所謂的亞洲大陸,根據希臘語對此詞的原始定義來界定,以愛琴海為歐、亞分界,以尼羅河為亞、非交界──這一地理觀與今日的地理劃分並無不同)。
西方人透過其自身戰略利益、經濟利益的狹窄視角來看亞洲,而未檢視──且沒有想到過──亞洲諸民族的集體經驗和主觀想法。繼續用這一來自他者的視角來看亞洲,可能會感到茫然,而本書無疑會用到許多西方讀者所不熟悉的人名和事件。但本書無意以同樣站不住腳的亞洲中心視角來取代歐洲中心或西方中心視角,反倒欲以多種視角看過去和現在,因為深信西方稱雄觀──愈來愈站不住腳的觀念──不再是可靠的觀點,甚至可能帶來危險的誤導。
從西方觀點看,西方的影響可能既是不可避免且是必要的,不需要徹底的歷史審核。歐美人習慣將他們的國家和文化視為現代性的來源,且以他們文化擴散全球的特殊現象來證實他們這一看法:如今,除開婆羅洲或亞馬遜雨林裡某些與世隔絕的部落,每個社會幾乎都至少局部西化,或渴求躋身西方的現代境界。但曾有一段時期,西方只意味著一個地理區,且其他民族潛意識裡以自己的價值觀為中心構想世界秩序。晚至十九世紀,以伊斯蘭教或儒家學說之類信仰體系為核心的社會──占已知世界的大半──其人民仍可以認定,人間仍與由他們的祖先或神所界定的更大的神定秩序或宇宙秩序不可分割合為一體。
本書欲以宏大視野呈現東方某些最聰穎、最敏感者如何回應西方對他們社會的侵逼(有形的侵門踏戶和對知識領域的無形入侵)。本書描述這些亞洲人如何理解他們的歷史和社會存在(social existence),如何回應一連串特殊的事件和運動──印軍譁變、英國—阿富汗戰爭、奧圖曼現代化、土耳其與阿拉伯的民族主義、日俄戰爭、中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日本軍國主義、去殖民化、後殖民時代的民族主義、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興起──它們共同決定了今日亞洲的格局。
第二章:哲馬魯丁‧阿富汗尼的奇異旅程
這一時代何由而生?其他人對我們完全視而不見,同時改造、發展他們的機器,擬出並落實計畫,在我們之間進進出出,然後我們一朝醒來,突然發現一根根鑽油井架像尖釘插在土地上,怎麼會這樣?
我們為何落到遭西方毒化的境地?
且往歷史追本溯源。
賈拉勒‧艾哈邁德(Jalal Al-e Ahmad),《迷醉西方》(Gharbzadegi),一九六二
一個穿粗布衣的小人物
一九六○年代初期,有群流亡巴黎的伊朗人常在聖日耳曼區名叫「起初」(Au Départ)的咖啡館碰面。他們大部分是來自伊朗的政治難民。民選的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sadegh)政府將伊朗石油業國有化之後,美國中情局和英國軍情六處於一九五三年協助推翻了該政府。後來成為伊朗伊斯蘭革命之龍頭理論家的阿里‧沙里亞蒂(Ali Shariati,一九三三~一九七七),就是這些流亡巴黎、滿腔怒火的難民之一。他在這場英美政變十八週年那天哀嘆道,「被判定犯了對劫掠的西方打出第一鞭之罪的民族,仍未脫離被囚之境。」一如他的流亡同志,他在巴黎除了提升自己的政治、知識素養,然後告知、教育他的同胞,別無什麼目的。他將沙特的《何謂文學》和法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譯成波斯文。他在伊朗流亡人士經營的期刊上──期刊常偷偷運回伊朗──撰文談論孫中山、阿爾及利亞的反法叛亂、甘地與尼赫魯(此二人在他眼中是印度的摩薩台)。他參加抗議帕特里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剛果民主共和國首任總理)在剛果遭殘酷殺害的示威活動。他也密切注意一九六三年六月反伊朗親西方政權的流血暴動。伊斯蘭神職人員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就因這場暴動成為政界風雲人物。他和他的友人,在他們於聖日耳曼區的常去之處,討論一位十九世紀四處巡遊的行動主義者和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一八九二年初期,在寫給奧圖曼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信中,阿富汗尼已表達了他一直揮之不去且後來也縈繞沙里亞蒂心頭的憂心,憂心西方列強只有一個居心,即把我們的土地完全奪走。從這一點看,俄羅斯、英格蘭、德國或法國是一丘之貉,特別是如果他們看出我們的衰弱、無力反抗他們的意圖的話。相反的,如果我們團結起來,如果穆斯林萬眾一心,我們就能傷人,有出息,我們的心聲會得到傾聽。
一九五五年還在馬什哈德(Mashhad)求學時,沙里亞蒂就已撰文談這位相對來講較無人知的人物。在鑽研與宗教無關的西方解放理論,在求知之路上繞了一大圈子之後,一九六○年代,在巴黎,他再度回到阿富汗尼身上。而誠如沙里亞蒂於一九七○年所寫的,他深信「了解他,就等於認識伊斯蘭和穆斯林,還有我們的現在與未來。」
在伊朗,哲馬魯丁‧阿富汗尼被譽為伊斯蘭革命的理論教父。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於一九七九年走訪德黑蘭時,稱那場革命是對抗西方「全球體系」的「第一場大起義。」更值得注意的,從埃及、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到馬來西亞,可看出穆斯林國家彼此差異極大,但在如此紛然雜陳的穆斯林世界,不只伊斯蘭主義者、泛阿拉伯主義者、泛伊斯蘭主義者,還有左派的世俗主義者,都把阿富汗尼視為開時代之先的反帝國主義領袖和思想家。阿富汗尼被拿來和十九世紀另兩位偉大的政治、哲學流亡人物馬克思、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相提並論,如今在西方卻少有人知,儘管其影響勝過赫爾岑,且至少從其影響之長久來看,幾乎和馬克思不相上下。
這至少有一部分得歸因於他的生平有很大的空白。他遊歷穆斯林世界期間的言行,有許多已湮沒於歷史。要重現他的求知軌跡,如後文所嘗試做的,就要探討他所走過那些國家的社會、政治騷動──彰顯他世界觀之內涵與特性的那些經驗。無論如何,要探明他一生思想的演變,絕不可如對待許多西方思想家那般,倚賴那些闡述明確概念且已公諸於世的文本和詳細交待參考資料的傳記。就阿富汗尼來說,他的思想史就是他觀點的歷史,而他的觀點,本質上與他所處的世界不一致,也不可能一致。
在穆斯林地區,的確幾乎沒有哪個社會趨勢或政治趨勢──現代主義、民族主義、泛伊斯蘭主義──非阿富汗尼開明、充沛的感受力所點燃,或未受到其推波助瀾。也沒有哪種政治活動──反帝陰謀、教育、新聞報導、憲政改革──未受到他思想的影響。阿里‧沙里亞蒂宣稱阿富汗尼是「在蟄伏的亞洲發出覺悟之聲的第一人」,幾非誇張之語。
阿富汗尼自承是個「地位不高且未當上高官的小人物。」但誠如他所提醒的,「豐功偉業」是像他這樣的人所立下,這樣的人「四處流浪,一身粗布衣,嚐過冷熱、苦甜,跋涉過許多高山、沙漠,經歷過人世。」事後來看,他的成就更大,尤其是與他之前那些穆斯林思想家相比的話。
拿破崙入侵埃及,讓許多穆斯林首度體會到西方有些人已找到經濟力、軍力的新來源,而且能將此力量投射到數千哩外。但許久之後,伊斯蘭國家的統治階層和知識界,仍有許多人大力主張採行西方生活方式,主張適應而非反抗西方的稱雄。他們還未擔心歐洲會造成伊斯蘭文明的嚴重頓挫,會挑戰穆斯林對自身世界地位最堅信的觀點。埃及編年史家賈巴爾蒂雖不安於拿破崙的入侵,卻大剌剌嘲笑法國人的上廁所習慣。他未深究法國人來埃及的動機,對於使歐洲陡然陷入混亂的法國大革命思想──共和政體、社會平等與流動、公正、不偏不倚的國家──幾乎完全不懂。後來關注西方之創新的人士,好奇之情甚於焦慮,特別是在埃及、奧圖曼帝國著手仿效西方建造現代國家和軍隊時。
埃及大學者里法‧巴達維‧拉斐‧塔哈塔維(Rifa’a Badawi Rafi al-Tahtawi,一八○一~一八七三),一八二六至一八三一年在巴黎待了五年,在他眼中,歐洲倒似乎是個無害的榜樣。他闡述法國大革命和法國憲法,為阿拉伯語讀者首度全面介紹西方某國的政治制度。他以欽佩口吻寫道,「法國人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因聲望、地位、名譽、財富上的差異而有異。」7同樣的,突尼西亞人海爾丁‧突尼西(Khayr al-Din Tunisi)於一八五○至一八六五年間多次赴歐期間,成為伏爾泰、孔狄亞克(Condillac)、盧梭、孟德斯鳩的衷心仰慕者,只對這些哲學家的痛批宗教感到遺憾。他指出歐洲人的志願性社團和組織長才:「如果人結合在一塊以達成某個共同目的,就連最難的事,都能達成。」英國的統治印度,就是這類「不可思議例子」之一。「英國政府透過印度公司這個由本國商人組成的社團,得到約三億五百平方公尺的地和其上超過一億八千萬的人口。」
塔哈塔維、海爾丁、敘利亞教育家布特魯斯‧布斯塔尼(Butrus al-Bustani,一八一九~一八八三),都屬於穆斯林世界裡最早認同必須改革以遏制內部衰敗的官員、老師、軍人。布斯塔尼編的字典、大百科、期刊,協助創造了現代阿拉伯語和文學。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初期,伊斯坦堡奧圖曼朝廷也有許多知識分子得出同樣的結論:本國的社會—政治秩序已衰老不堪,需要用外部知識來翻新。這些知識分子未如阿富汗尼不久後那樣,將他們的國內情況與國際關係上令人心驚的轉變扯上關係。他們眼中的改革,大體上就是採用歐洲知識和實用技術,軍隊現代化。許多歐洲菁英已開始將基督教和白人視為較優越且獨一無二。但景仰孟德斯鳩、基佐(Guizot)的土耳其人、埃及人,一八三○年代在西方人指導下開始推動現代化,卻尚未完全意識到歐洲的新種族階層體系;他們希望本國的穆斯林社會最終會進步到和歐洲平起平坐。奧圖曼作家納米克‧凱末爾(Namik Kemal)於一八六○年代深信:歐洲花了兩百年才達到這樣的狀況,而他們在進步之路上費心發明,我們則有各種現成的方法可用……即使要花上兩百年,我們也能躋身最文明國家之列,不是毋庸置疑的事?
值得注意的,一八六○年代歐洲在亞洲的勢力仍大體上侷限於印度之時,阿富汗尼已留意到穆斯林將面臨的危險。他理解到歷史正以不受可蘭經之真主左右的方式在運行,主動權已被西方那些躁動、衝勁十足的民族拿在手上。那些民族衝出存在已久的文化、政治死水,正發掘、探索新的世界,以此前的帝國擴張中從未用過的工具,征服穆斯林和其他非西方民族。
印度與阿富汗的覺醒
阿富汗尼的早期生平,相關資料極缺,且因其在數個國家一再聲稱自己是來自阿富汗的遜尼派穆斯林而引人誤解。但如今很清楚的,他於一八三八年生於波斯西北部哈馬丹(Hamadan)附近的阿薩達巴德(Asadabad)村,先後在德黑蘭、幾個什葉派大城──主要是納傑夫──的伊斯蘭經學院、印度受過教育。他在波斯的早年歲月,正逢巴布教派(Babism)興起。巴布教派主張揚棄舊制度、舊律法,施行由新先知制定的新制度、新律法。該派於波斯遭鎮壓後,許多信徒逃到奧圖曼人統治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什葉派城市;阿富汗尼對伊斯蘭的大膽、有時近乎離經叛道的觀點,還有他徹底變革舊制度的革命主張,有可能曾受了他們的影響。但他早年也得到波斯伊斯蘭哲學傳統方面的基礎訓練,而該傳統比遜尼派阿拉伯的伊斯蘭哲學傳統更願意接受新事物,因而對阿富汗尼的修正主義伊斯蘭的產生,顯然有推波助瀾之功。
什葉派伊斯蘭在波斯有著較異端的傳統,而晚至十九世紀,這一傳統仍產生重要的伊斯蘭哲學家毛拉哈迪(Mullah Hadi)。什葉派波斯保留了在阿拉伯語地區老早就式微的哲學傳統,例如調和理性主義思想與啟示宗教。阿富汗尼在異端傳統裡受教育,因而能比其遜尼派同儕更早談到革新和改變。但身為什葉派教徒,他的想法在遜尼派地區將難以廣為傳播,而為了讓自己在他所欲改革的國家被當作遜尼派穆斯林,他似乎認為自稱生於阿富汗是明智之舉。他在埃及也是共濟會一員,儘管為時不久。阿富汗尼既非盲目的西化者,也非死硬的傳統派,最關心的似乎是如何制訂反帝國主義策略。他於一八五○年代晚期前往印度進修,接下來十年裡有相當多時間待在那裡,包括待在孟買(有許多波斯僑民之地)和加爾各答。就在這個印度人激烈攻擊英國人和英國人殘酷反制的時期,他思想中傳承自巴布教派的反叛傳統,開始從地方性的反抗意識形態轉變為全球性的反抗意識形態。
不久後,就在阿富汗,阿富汗尼進入信史,角色雖小但令人想一探究竟。當時的阿富汗,一如不久前的阿富汗,乃是諸多地緣政治野心欲染指的詭譎之地。一八六八年來自坎達哈、喀布爾的英國政府秘密報告,稱阿富汗尼於一八六六年從印度來到阿富汗,是個極危險的反英鼓動家且很可能是俄羅斯特務,身材修長,膚白,額頭寬闊,天藍色眼睛非常銳利,蓄著山羊鬍,愛喝茶,精通地理學和歷史,通阿拉伯語、土耳其語、波斯語(類似波斯本地人所操語言),外表上看無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偏歐洲而非穆斯林。
抵喀布爾後不久,阿富汗尼成為阿富汗埃米爾的顧問。當時,該埃米爾正與同父異母弟打內戰,且被其強鄰,印度的英國人,懷疑與俄羅斯勾結。在這之前,阿富汗人已讓英國人見識到他們的厲害。一八三九年,印度的英國人想在喀布爾扶植親英的統治者。阿富汗游擊戰士按兵不動,等時機成熟,才攻擊遠征喀布爾的英國大軍。英國大軍經受一連串攻擊,最後被打到只剩一人:垂頭彎腰騎在馬上的一名英國軍醫,呈現在維多利亞時代名叫《殘兵餘勇》(Remnants of An Army)的畫作中,最後成為十九世紀英國最慘重軍事挫敗的象徵。
一八六○年代,英國人再度侵逼阿富汗,阿富汗尼似乎看到了機會。他深信阿富汗仇恨外族入主者,並在寫於一八七八年的阿富汗史中申明這一信念:「靈魂的高貴使他們寧可光榮而死,也不願在異族統治下卑躬屈膝的過活。」阿富汗尼看到鼓動高傲強悍的阿富汗人對抗英國人的機會,於是勸埃米爾考慮和這時已在從奧圖曼帝國到西藏的廣大地區裡成為英國死對頭的俄羅斯人合作。阿富汗尼對一位向英國人提供情報的阿富汗人,說明了為何該與俄羅斯而非與英國合作的數個理由,其中一個理由是「英格蘭人是偷偷摸摸搜刮的小偷,最近才現身,他們所取得的東西,全是靠陰謀詭計得來。俄羅斯國自亞歷山大大帝時就已存在於世。」
無論如何,阿富汗尼過度高估了自己的本事。一八六八年,埃米爾遭同父異母弟謝爾‧阿里(Sher Ali)擊敗,失去其埃米爾之位。謝爾‧阿里與英國人達成協議,迅即將阿富汗尼逐出喀布爾,迫使他尋找別的穆斯林統治者,以宣說英國帝國主義的危險。阿富汗尼離開阿富汗時,對阿富汗領袖印象特別差,覺得他們不可靠,動不動就和歐洲列強合作(後來,一八七八年謝爾‧阿里與其英國主子反目,引發第二次英國、阿富汗戰爭時,他的觀感改變)。
關在喀布爾的巴拉堡(Bala Hisar),等著驅逐出境時,他以押韻散文體抒發他在阿富汗所激起(和不久後在其他許多國家也會激起)的誤解,字句中充滿諷刺意味:
英格蘭人認為我是俄羅斯人
穆斯林以為我是祅教徒
遜尼派以為我屬於什葉派
什葉派當我是阿里的敵人
四聖伴的部分友人認為我屬於瓦哈比派
有些伊瑪目派教徒以為我屬於巴布教派
有神論者認為我是唯物主義者
虔信者當我是不虔誠的罪人
有學問者當我是無知之輩
信士認為我是不信的罪人
非信士不召喚我
穆斯林也不認為我與他們同道
遭逐出清真寺,遭廟宇拒於門外
我心中茫然,不知該靠誰,該打誰
拒絕某人使朋友變成死敵
我逃不了某群人的掌控
沒有固定的居所來打另一方
坐在喀布爾的巴拉堡,雙手被縛,雙腿斷掉
我想知道「神秘者的簾幕」會屈尊向我揭示什麼,這一惡意蒼穹的旋轉會帶給我什麼樣的人生際遇。
爾後幾十年,阿富汗尼將頻頻落入失敗的一方。但他仍會以當時任何穆斯林所不能及的說服力和急切之情,進一步闡發西方對伊斯蘭文明的多重威脅,而且他將永遠不會停止強調他早期的印度經驗。印度是惟一擁有龐大穆斯林人口且被英國人占領、局部治理的國家。一八五七年,《德里烏爾都語消息報》主編大毛拉巴卡爾,已在抒發初萌的宗教性反殖民主義,運用可蘭經中寓言和土耳其歷史、印度教史詩和神話,描寫與英國人全然不同、全然相反的印度民族。一八七八年,阿富汗尼寫到印軍譁變時,也宣稱受到普見於印度各社會階層、各宗教派系的反英心態影響。他寫道,「他們(對英國人)的怨恨、敵意甚深,因而沒有印度人不期盼俄羅斯人陳兵印度邊境。」
阿富汗尼從印軍譁變和該事件後的悲慘情勢所得到的政治啟發,令他此後人生受用良多。多年後他與某阿富汗人交談時,仍哀嘆於譁變印軍的不堪一擊和英國人吞併奧德的輕易。他將把英國人比擬為「已吞掉兩千萬人,喝光恆河、印度河水,仍不滿足,仍隨時要吞噬世界其他人,喝光尼羅河、烏滸河水的一條龍。」
阿富汗尼用語的暴烈,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在譁變後的印度親眼目睹整個穆斯林社會、文化遭毀所激出。在德里,英國人夷平該城大片地區,殺害或驅逐該城大部分穆斯林居民。蒙兀兒末代皇廷的最偉大詩人哈利卜(Khalib),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發怒的獅子進入該城,殺害任人宰割者,燒掉房子。一群群男女、平民、貴族,從三個城門湧出,避難於城外的小村落和墳墓。」哈利卜哀嘆道,「這城市已成為荒漠。」英國人直到一八五九年才准穆斯林回德里。「穆斯林的房子空了這麼久……牆壁簡直像是用草建的,」哈利卜寫道。
一八五七年英國人在德里大肆報復時,有些印度人逃出該城,包括原在蒙兀兒皇廷當官的尼赫魯先祖。但尼赫魯家族,來自喀什米爾的高階種姓印度教徒,遭遇不像上層穆斯林那麼慘。例如該家族的秘書(munshi),屬於上層穆斯林,而尼赫魯在自傳中寫道,該秘書看著自家家產成空,部分家人遭英軍殺害。損失不只如此。對於長久以來在印度屬於統治階層的印度穆斯林來說,印軍譁變遭殘酷鎮壓,無異於精神上徹底且全面的挫敗。
印度穆斯林心中的羞辱和被迫流落異鄉之感慨,在詩人筆下得到最生動有力的抒發。目睹印軍譁變的阿克巴‧伊拉哈巴迪(Akbar Illahabadi),在詩中道出穆斯林共有的悲苦:「你若走那條路,會看到我受蹂躪的村子/一座英國兵營矗立在殘破的清真寺旁。」在另一首詩中,伊拉哈巴迪描述了適應全新世界的痛苦:
吟遊歌手、音樂、旋律都變了。我們的睡眠變了;過去常聽的故事,不再有人講。春天跟著新裝飾一起降臨;園中夜鶯唱起別的歌。大自然的作為有了革命性改變。天上降下另一種雨;田裡長出別種穀子。
地方詩人阿爾塔夫‧侯賽因‧哈利(Altaf Hussein Hali),也在其家喻戶曉的《穆賽德斯:伊斯蘭的起落》(Musaddas: The Flow and Ebb of Islam,一八七九)一詩中,描寫穆斯林的失勢:
如有人看出我們的衰落普見於全境,
看出伊斯蘭一倒下就未再起,
將不會再相信每次退潮後都會漲潮,
一旦那人看出我們的大海已消失無蹤。
二十世紀初期,哈利的輓歌將成為反殖民統治的穆斯林政治集會時固定誦讀的詩篇,而其中許多穆斯林後來將積極鼓吹讓印度穆斯林有自己的家園,巴基斯坦。
秋意已籠罩花園時,
為何談花開的春季?
敵意的影子籠罩現在時,
為何念叨往日的輝煌與榮光?
沒錯,這些是該遺忘的東西;但如何用
黎明忘掉前夜的情景?
大會剛散;
蠟燭仍在冒煙;
印度沙地上的足印仍在訴說
有支優雅的旅行隊走過這條路。
英國人常把印軍譁變怪罪於穆斯林而非印度教徒,因而經此事件後,比以往更積極阻止穆斯林從政。與一八八五年任英國印度事務大臣的蘭道夫‧邱吉爾(Randolph Churchill)會晤時,阿富汗尼當面說明了印度穆斯林恨英國人的原因:「你們消滅了德里帝國;第二,因為你們未付薪水給伊瑪目和清真寺的宣禮員、住持。而且你們放棄瓦合甫(譯按:穆斯林為宗教或公益目的而捐獻的建築物或土地),未修復神聖建築。」但阿富汗尼於一八五○年代晚期初次來到一受辱的國家時,似乎更感興趣於從帝國主義受害者那兒得到更大的教訓。
印度穆斯林,例如印軍譁變期間任職於東印度公司的賽義德‧艾哈邁德汗(Sayyid Ahmed Khan)爵士,已開始主張穆斯林受西式教育,深信掌握科學是在現代世界成功的基礎。一八五七年譁變士兵要賽義德爵士離開英國人加入叛亂大業時,他賭對了邊。他答道,「印度不能沒有英國人統治。」(後來他為一英籍的地區收稅員和其家人弄到安全通行證,使他們免遭譁變士兵殺害。)此後,賽義德爵士致力於創立教育機構,尤以在北印度阿里格爾(Aligarh)鎮所創立的機構最為有名,並在這方面得到英國人協助。他勸穆斯林同胞利用「英格蘭人的風格與藝術」造福自己。他的座右銘變成「教育,教育,教育」,而且他得到許多印度穆斯林支持。傑出的烏爾都語小說家、散文家納吉爾‧艾哈邁德(Nazir Ahmed)聲稱
我們全忙於無益的爭論時
歐洲人躍進真主所造世界的虛空中。
過去他們的日子過得比我們慘
但如今全世界的財富如大雨般落在他們身上。
如今真主已著手和這些國家分享他的秘密
因為他們已認識大自然運作的模式。
接下來幾十年,阿富汗尼將對其穆斯林同胞發出類似的勸誡。他在一八七九年寫道,「噢,東方的子民,你們不知道西方人的強盛和他們的支配你們,源於他們在學問、教育上的進步,不知道你們在那些領域衰落了。」在這同時,他對英國的仇恨與不信任,將永遠不會止息──他這心態於他在印度時發展出來,且在諷刺詩人阿克巴‧伊拉哈巴迪筆下得到最扼要貼切的闡發:
英格蘭人想中傷誰就能中傷誰
想往你腦袋裡塞什麼就能塞什麼。
他揮舞鋒利的武器,阿克巴。最好離他遠遠的!
他把上帝切成三塊。
一八七八年,埃及有人質疑阿富汗尼筆下英國對印度人民的壓迫時,他把批評者斥為不值一顧,認為他們受了英國人所寫歷史書影響因而有此反應。他說那些書「以英國人自戀的手和自負的鋼筆、欺騙的鉛筆寫下,必然未講述真相,未報告事實。」阿富汗尼深信英國人對印度的陳述,為其讀者「撒下了含糊不清的羅網和表裡不一的陷阱」,因而對於帝國宣傳家宣稱英國人是為了印度人好而來到印度,英國為此建造城市、鐵路、學校,罷黜奧德國王之類暴君的說法,他也從來未相信。他說這說法很可笑。即使印度的統治者腐敗、壓迫人民,他們能傷害的範圍很有限,而且他們把他們的不義之財在印度花掉。英國人恐嚇、剝削所有印度人,把掠奪來的東西運到英國。至於他們所帶來的電報、鐵路,阿富汗尼斷言,凡是印度人都會說,建造它們只為了吸光我們的財富,方便不列顛群島居民貿易,擴大他們的賺錢領域:除此之外,還有什麼造成我們陷入貧困,財富耗竭,富饒消失,許多人餓死?
阿富汗尼聲稱為印度人發聲,讓人覺得太托大。但數十年後尼赫魯寫自傳時,同樣強調鐵路、電報、無線電報這些「工業主義先驅」「來我們這兒,主要是為了強化英國人的統治」,尼赫魯甚至寫道,「鐵路這個帶來生機的東西,始終讓我覺得像是將印度困住、關住的鐵箍。」
阿富汗尼於一八六○年代初期在英國統治的印度完成教育後,似乎──在這點上欠缺可靠史料──去了伊朗,且很可能還去了麥加、巴格達、伊斯坦堡。他在阿富汗的英、俄「大博奕」(Great Game)舞台上短暫而精彩的現身,只是他所捲入的諸多國際陰謀的第一場。但它立下了一個模式:他對西方勢力(特別是英國勢力)和使西方勢力得以在穆斯林國家裡呼風喚雨的本土人士的擔憂與不信任,將貫穿此後他的所有活動。
沒錯,印度已臣服於英國腳下,阿富汗是個落後的小公國,阿國的統治者,相較於阿富汗尼於一八六九年會前去的奧圖曼帝國的統治者、知識分子,只是無足輕重的藩臣。但在奧圖曼帝國,他將親眼見到就連當時最強大的穆斯林帝國,雖未在軍事上受到西方威脅,仍漸漸倚賴西方;見到奧圖曼人試圖藉由創立新行政結構、現代軍隊、有效率課稅措施來自我革新,卻引發國內大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