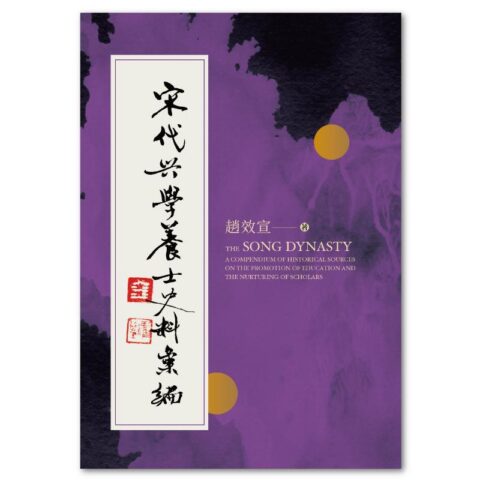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
出版日期:2005-03-18
作者:趙岡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248
開數:25開
EAN:9789570827743
系列:中國制度史論叢書
尚有庫存
本書蒐集明清官方地籍資料及民國期間的農村調查資料,利用正規統計方法,對明清以來之農村地權分配作了明確之計量研究,並對地權分配之長期趨勢及短期週期變動有具體之分析。
作者:趙岡
趙岡,1929年出生於哈爾賓市,1951年畢業於台灣大學經濟系,1962年獲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先後在密西根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威斯康辛大學任教38年,著作甚多,僅經濟史學科就出版了英文著作8本,中文著作12本,及中英文期刊論文80餘篇。趙岡和陳鍾毅夫婦編著的《中國土地制度史》獲得1982年行政院金鼎獎,另外一本著作《中國棉業史》(聯經出版)、獲得1978年教育部學術獎。
目 次
自 序 i
第一章 緒 論 1
一、經濟史研究上的一個誤區 1
二、租稅制度的影響 9
三、商業資金流向農村 22
四、人口增加 27
五、我們需要實證分析 28
第二章 土地丈量、登記與統計 31
一、沿 革 31
二、從地籍到戶籍 40
三、面積單位 43
四、墾田面積的可信度 48
第三章 分析工具 55
第四章 綜合分析 67
一、從吉尼係數看 67
二、地區性的差異不顯著 74
三、地權分配的變動 90
第五章 農村分化 93
一、墾荒運動之後續發展 94
二、朱學源戶分家析產 98
三、包產到戶 102
四、地主的置產簿 105
五、是福音還是罪惡 117
第六章 地權分散的機制 121
一、繼承制度的歷史演變 122
二、貧戶與富戶生育行為之差異 126
三、養子與嗣子 128
四、兩種相反的力量決定地權分配之變動 131
五、土地分配的周期 135
第七章 地權分配的長期趨勢 141
附 錄 167
A、北宋主客戶統計 167
B、明清土地分配 177
C、國民政府內政部之調查統計 213
D、滿鐵調查統計 223
E、其他調查統計 225
自 序
我二十多年前就立意要寫一本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市場與土地分配的書,結果拖到今天才實現,成為我的封筆之作。這一段時間內,我出版了二十幾本專書,發表了八十幾篇論文,其中我著重討論的是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制度。這本封筆之作,可以說是我個人在這方面的結論。在書中我要強調提出兩個看法。
第一,秦漢以後出現的地主,不是皇帝所「封」或政府所「建」,被稱為「封建地主制」是很不恰當的名稱。絕大多數的地主是由土地市場定位的。在農業生產部門有大農戶,也有小農場;在商業部門有大商號,也有小商店,它們都是由市場定位的。主流派的學者一向認為地權的轉移都是不同方式的土地兼併,地權是越來越集中,即所謂的「不斷集中論」或「無限集中論」,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的第二個要著重提出之點是,中國明清兩代殘存下來的地籍冊檔,其價值不應完全被否定。有人說中國歷史上的政府「不懂得數字管理」,又有人說明清繪製的魚鱗圖冊「根本不是史實而是傳奇」,我們真正翻閱過並研究過明清的魚鱗冊、編審冊、實徵冊、推收冊的人是不會說這種話的。這些地籍冊檔自然不夠齊備完善,有其缺點,但絕不是「傳奇」,若加適當運用,再配合私家存留的置產簿及收租冊,還是很有價值的實證史料。
1979年夏,我是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成立後第一批選派的美籍人員前往中國大陸從事研究的學者之一。我在南京大學、北京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歷史研究所等處翻閱很多屯溪檔案,並抄錄了很多有用資料,臨回美以前,應李文治老先生之請,為經濟所研究人員作了一次報告,說明這些地籍檔案的價值,並提示若干可進行研究的途徑。會後,章有義先生單獨與我會晤,討論如何進行研究。我回美後即利用所抄錄的屯溪檔案地籍資料寫成我「中國土地制度史」中的一部份內容,在1982年出版。章有義先生也於1984-1988年間,利用此類資料,寫了不少有價值的論文。
當然,大陸上也有些學者,對於這些檔案資料抱持「敵視」的態度,1984年出版的某期「經濟研究」刊登了一篇讀者的書評,認為它是在歌頌地主鼓勵剝削,是反動學者放毒之作。八十年代對外開放以後,這類基本教義派的文章就少見了,大陸學者開始很認真辛勤地整理這些地籍資料,有可觀的成果。我現在這本書就大量利用了他們整理出的資料,作些實證研究。到現在為止,還是有相當數量的地籍資料,仍不許民間學者查閱。例如浙江蘭溪縣檔案館所存的七百四十冊魚鱗冊就不對外開放,是一大遺憾之事。
第一章
緒 論
一、經濟史研究上的一個誤區
中國歷史上有一段封建時期,即西周時期(1066-771BC)。周天子分封諸侯,「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受封者有確定的釆邑,封君封臣有層級性的從屬關係,互有固定的權利與義務。統治權是分散的,受封者享有一定的行政權及司法權。這個封建制度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敗壞,至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時,已正式結束。但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史學家覺得封建時期在中國結束得太早,為了意識型態的要求,硬把中國的封建時期向後延長了兩千多年。王毓瑚教授認為這種主張是由於中國學者之「歐洲中心論」及自卑感在作祟 :經典的社會發展公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西歐有的中國也應該有,而且西歐是發展最先進的地區,發展階段一定比中國早,中國總要落後一大段。傅筑夫教授也反對這種「歐洲中心論」,他認為從秦漢開始 :
中國歷史便完全沿著與歐洲歷史不同的發展道路前進,並為自己獨有的經濟規律所支配,因而對社會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和所造成的結果,遂與歐洲完全不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
不幸,很少中國學者肯接受這個說法。「歐洲中心論」一直是中國史學界的主流思想。他們創立了「封建地主經濟制」的理論,把周代稱為「領主封建制」,春秋戰國以後為「地主封建制」,兩者都屬於封建時期,一直延續到廿世紀。這樣既沒有完全乖離歐洲中心模式,封建時期的終止點也遠遠落於歐洲之後,可說是面面俱到。
學者又為中國的封建地主制推衍出許多「特性」:封建地主制之社會是自然經濟;中國及整個東方都沒有私有土地的制度,所有土地都歸皇帝所有,皇帝與地主就是封君封臣的關係,皇帝有最高最後的土地所有權,地主只有一小部分所有權;在中國歷史上,土地沒有進入流通過程,土地不是完全「自由運動」的,只能單向運動,也就是兼併式的運動,所以農村中的土地是「不斷地集中」,「無限地集中」 。
「封建地主制」的理論已把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帶入了嚴重的誤區。這個理論本身漏洞百出,與實際史料也不符。為了彌補破綻,學者提出許多補充理論。不幸,這些後續的補充理論也自相矛盾,不但無法彌補破綻,反而引起一波又一波的爭議。
「封建地主制」理論的第一個大破綻是「地主」一詞沒有明確而統一的定義。大體說來,學者共提出兩套不同的定義,而每一套卻又內部分歧,莫衷一是。第一套定義著眼於地主占有田產之多寡,也就是為地主的田產規模定出一個下限,超過此限者有資格當地主,而且一定會被列為地主。譬如說,有人將此下限定為100畝,田產超過此限者便是(當然是)地主。在這一派中,又分為兩支,100畝為限者稱為庶民地主,150畝為限者稱為紳衿地主。有人將此下限定在50畝上,也有人定在30畝上 。30畝是很小的耕地面積,只有4.9英畝(acres),全世界絕大多數的農戶,其規模都在此限之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設限的武斷性。占田29畝者是自耕農,占田30畝便是地主,這只是文字遊戲而已。最奇特的是胡如雷為地主所設的活動下限 他說:
起碼擁有多少土地才能取得地主的資格呢?這取決於畝產量。如果地主全家的最低消費量是五十石,畝產量是二石,剝削率是100%,即對分制,則地主土地最低必要限量就是五十畝。如果畝產量增加為三石,剝削率不變,則地主土地最低必要限量就會降低為33又1/3畝。反之,如果畝產量降低為一石,則地主土地最低必要限量就會上升為一百畝。
胡如雷否定了一切農業發展的理論與措施。按照他的說法,每當平均畝產量上升一點,農村便要增加一批新地主,一切促使農業發展的措施都會提升農田的畝產量,也就製造了更多的地主,所以一切發展農業的措施都應打倒。
第二套地主的定義,可以避免為地主占地設限的武斷性,那就是著眼於土地是否出租給佃戶,將田地出租給他人耕種,坐收地租,便是地主,這樣就不必武斷地為地主占田規模設定下限。然而,正因為沒有下限,被列為地主之農戶可能占田很少。例如有周世彥者,研究廿世紀三十年代湖北咸寧的土地分配 ,他調查了三十八家地主,這些地主共占地533畝,平均每家地主只有14畝田地。應注意的是,14畝只是一個平均數,小的地主有田不足10畝,但是因為田租給了佃戶,便身入地主之列。最極端的例子是曹幸穗書中引用三十年代末滿鐵在蘇南地區的農村調查 ,其中無錫榮巷三個自然村中共有36戶地主,平均每戶地主出租1.63畝土地。這36戶被稱為地主,實在是太恭維了。
更重要的是,第二套地主定義中,有一個很大的邏輯問題。很多有大量土地的農戶並不出租他們的田地,而是雇工耕種。既然以是否出租土地為標準來劃分地主身份,這些雇工經營的農戶就應該排除在外。然而學者仍將這些農戶列入地主一類,於是地主又分為兩類──租佃地主及經營地主,同屬封建地主。這裡便又發生了一個概念上的矛盾:經營農場與經營商店或手工業工場,在性質上有何不同?為什麼經營農場之人是封建人物?而商店主人或工場主人便不是封建人物?如果一戶人家今天經營農場,明天改業經營商店,他又將如何歸類?更有甚者,許多田產之業主常常是將其一部份土地租給佃戶耕種,留下一些土地,自己雇工經營。對於這些地主之歸類便由研究者隨心所欲地劃分。你要著重土地租佃,便稱這些地主為租佃地主;如果你要強調經營地主的進步性,便將之歸類為經營地主。譬如,「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性質」一書中(附錄表二)列出泰安北石溝武錫賢有地1,000畝,雇人耕種30畝,出租970畝,及棲霞馬陵塚李緒田有地3,000畝,雇人耕種80畝,出租2920畝,但二人都被列為經營地主。
封建地主制理論,不但缺乏一個明確而統一的定義,而且理論上也有很大破綻。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不論根據那一套定義,地主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出現,絕不是一種定制,他們沒有層級性的從屬關係,他們的田產不是固定的采邑,而是隨時在增減變化,甚至可以隨時消失,他們的田產不但多寡隨時可變,田產的所在地點也隨時可變,他們除了產權外,並未享有行政權及司法權。地主這個圈子是一個free set,人們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退出,不是一群固定的農戶,更不成其為一種制度。中國傳統農村社會有變動性(不一定是地域上的流動性),很多貧窮的農民處於上升狀態,很多的富裕農戶則正處於下降狀態,家道中落。在任何時點上,總可以找出若干占田100畝的農戶,就如像在任何時點上進行人口調查,總可以找出一批年滿40歲的人口。但是這不是「定制」,中國傳統農村的土地市場相當自由,土地不但在運動,而且是多向運動,地權分配的變動性很大,既非采地式的定制,也非「無限集中」,「永遠兼併」的單向運動。
以前不久,史學界曾經發生過一段爭論。1954年尚銊與鄭昌淦編寫的《中國歷史綱要》一書,提出莊園是一種經濟制度盛行於唐宋兩代的說法,許多學者也隨之附和。後來,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莊園只是當時農村中的一種現象,而不是一種經濟制度 。鄭昌淦在1980年的「綱要」修訂本中,就把「莊園制」中的「制」刪掉,改為「莊園經濟」。我們現在討論的「封建地主制」,也是同樣情形,它不是西歐中世紀那樣的一種經濟「制度」,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下是在專制政體下的編戶齊民,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行為造成的後果。地主之出現,不是什麼人設立的,也不是什麼政府指定的,而是土地私有產權在市場上交換自然形成的,整個過程是一個自然過程。
從秦開始,編戶齊民就能合法擁有私人財貨的產權,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後果。市場就是人民交換產權的交易場所。財貨分產品與生產要素兩大類,所以市場也分為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產權最主要的內容是所有權與使用權,所以市場交易的形態也分為兩大類,即所有權之交換與使用權之交換。在產品市場上主要的型態是所有權之交換,買者以其對金錢的產權向賣者交換實物的產權。要素市場則兼有兩種交換型態。最基本的型態是使用權之交換,買方付出某種代價來換取生產要素的使用權。要交換使用權,雙方必先言明使用期限,所以使用要素的代價都有時間單位。譬如說,使用勞動力要付工資,工資是以小時計,以日計,以月計,或以年計。使用他人的資金要付利息,以日計,以季計、或以年計。依同理,使用別人的土地要付租金,租金也有時間單位,以月計或年計。如果使用期限無限延長,就變成買斷式的所有權交易,也就是買方付一筆代價取得要素的所有權,然後無限期的使用。土地買斷時所付之代價就是地價,沒有時間單位。資金買斷時則不再是借貸,而是入股,變成equity capital,也沒有以時間單位計算的利息。勞動力買斷時所付之代價便不是工資,而是「奴價」,按人頭計算,被購買的奴婢人身便永遠屬於買主所有,永遠供其役使。要素市場最完整的時候都有這兩種交易型態。不過在現代國家中,政府以法令禁止奴婢買賣,買斷勞動力的交易便被禁掉了。在中國歷史上,秦漢以來雇佣市場與奴婢市場都是合法存在的,人們可以從勞工市場上取得勞動力的短期使用權,也可以付出身價購買奴婢的人身所有權,無限期地使用其勞動力。這兩種勞動力市場是平行的,互相置代,供人選擇,工資太高則買奴,奴價太高則雇工,工資水平與奴婢價格長期維持均衡,從工資可以推算出奴價,從奴價可以推算出工資 。美國在1860年內戰以前,勞動力也是有這樣兩個平行市場。至於土地做為生產要素,只要進入市場交易,也是兩個市場平行,古今中外皆然。中國歷史上也是如此,兩個市場平行,人們在一個市場上進行土地所有權的交換,在另一個市場中進行土地使用權的交易,後者即租佃市場。我們不能只承認其一,而不承認其二。既然有兩個平行的土地市場出現,就有人願意在土地上投資,在一個市場上買進土地所有權,而在另一個市場上賣出使用權。這些人就是我們所謂的地主。他們之出現與存在是自然過程,是在市場上進行土地產權交易的結果。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這種活動,任何人也可以自由放棄地主的身分。我們沒有理由把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市場,租佃市場,土地交易,及其當事人,視為與其他國家者不同,以異類目之。我們也沒有理由把這些市場活動的自然結果,視為一種制度,而將領主封建制與所謂的「地主封建制」相提並論。
一旦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除非政府強力干涉,地權是不會平均分配的,實際分配的情況是由市場交易所決定,這種過程是自然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產權隨時隨地在流動,而且多方向流動,有的農戶在上升,他們的田產逐漸增加,有的農戶在下降,其田產逐漸減少,也有人先升後降,也有人先降後升,各種情況都可能出現,唯一不能出現的就是單向運動的「永遠兼併」。
如果再進一步考察,我們會發現,這個自然過程是受到許多不同的因素所影響,有的會使地權分配趨於集中,有的會使地權分散。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以互相抵消一部份,留下一些淨的影響。下面我們將從理論上簡述幾個影響地權分配的重要因素。(一)租稅結構:累退結構會使地權趨於集中,累退的結構改善,租稅的影響便趨於中立。(二)商業利潤向農村轉移,會使地權分散。(三)人口增加,會使地權分散。現分述之。
二、租稅制度的影響
在中國,私有土地制度一開始就產生了一個十分矛盾的現象。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 ,不久就引起某些人的非議,認為新制度導致土地分配之極端不均,「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另一方面國內又有大量可供使用的荒地,無人開墾耕種。漢末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也說: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
可是在同一文中他又說:
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
從居延漢簡所顯示的漢時物價也可以看出,與其他生產要素相比,土地的價值很低 。例如:
小奴二人直三萬
用馬五匹直二萬
大婢一人二萬
田五頃五萬
軺車一乘直萬
田五十畝直五千
大婢一人的價值相當於二百畝田地。這也許是反映邊區地帶地多人少的現象。「中州內郡」的農田據說最昂貴,大多畝值一金(合萬錢),「號為土膏」 。國內普通地價則在千錢至三千錢之間。建寧二年(西元169年)河內王末卿買田鉛券載所買田每畝價值三千一百錢。光和元年(西元178年)平陰曹仲成買地,每畝一千五百錢。光和七年(西元184年)平陰樊利家買地鉛券載每畝地價三千錢 這些都是河南境內的田地價格,時間相差也不遠,看來每畝三千是常價。曹仲成所買是冢地也許便宜點。
更值得注意的是地價與其他物品價格之比,即相對價格。居延漢簡所載當地糧價是「粟一旦,直一百一十」,比一畝田地的價值還要高百分之十。據晁錯說,當時普通土地的年產量大約每畝一石 。即令河西邊區土地的生產力沒有這麼高,農地價值也不過是略高於一年產量的價值。《漢書》卷七十二〈貢禹傳〉中也說:
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微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百三十畝田地價值不滿萬錢,與居延漢簡所記很接近。賣田百畝去置備一輛車馬,與漢簡中的軺車一乘值田百畝的比價完全符合。可見當時田地價值相對低廉確是事實。
於是我們不免要問:如果勞動力不足,豪富兼併了那麼些土地有何益處?如何利用?其次,從無地之民的角度來看,既稱「中地」,顯然不是低劣不堪使用的土地,無地之人為何不去開墾耕種?土地價值這樣便宜,勞動力這樣昂貴,購置田產應非難事。在這種條件下,土地為何會高度集中,而同時又留下大量閒置的可用之地?
據我看,對於這些矛盾現象的答案在於租稅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租稅結構是促成土地高度集中的主因。基於自古以來的重農經濟理論,執政者認為農業生產才是真正的生產工作,才能創造財貨。也因此,他們認為農業生產者才是真正有能力負擔租稅的人。於是農業生產者的稅負一向偏重,而工商業者只負擔一些雜稅而已。
農業生產者歷朝所繳納的主要租稅,大體可以歸納為兩大系統。第一個系統是田賦,也就是對農業生產活動的課稅。兩漢的田賦是採農業收益稅的型式,按每戶納稅人的農業總收穫量課徵一定比例的稅。要確實地徵收這種稅,地方政府一定要能有效地監督農民收割,並度量其實際產量。依當時的政府行政效率及技術水平,這是難以實現的理想。所以到了東晉,才「度田而稅」,改為土地稅,不論實際生產量,每畝課徵定額之稅。這樣便簡便易行,以後歷朝大體也沿襲此制。
另外一個系統是人頭稅,或是按勞動力單位,即所謂「丁」者課徵,或是按法定的標準戶(例如一夫一婦謂之一床)來課徵。這一系統又分為兩種方式徵收,一種是由政府直接徵調勞動力,人民每年定期為國家服勞役若干日。一種是繳納定量的布帛、絹綾,甚至現金,稱為「算賦」、「調」、「丁捐」,或「丁賦」。
在西晉限田以前,這兩個系統的租稅表面上是獨立的,但在實際徵收時卻是互相關連的。應服徭役的人從二十三歲起便須向政府掌管土地登記的「疇官」處登記,算是「著於名籍」、「給公家徭役」,到五十六歲方得免除徭役 。疇官同時掌管兩個系統的課稅,而其共同基礎便是田產之有無。有了田產的人,便有正式而固定的戶籍,於是田賦與徭役的義務便同時發生。沒有田產登記的人,流動性較大,即使有法令規定他們要納稅服役,以當時的行政效率,也難以實際課徵。
這兩種租稅中的田賦,不論是按總收穫量課徵或是按田畝數課徵,在理論上總算是比例稅。但是人頭稅系統,不論是按勞動力單位課徵或是按標準戶課徵,都是定額稅(lump-sum/taxes),其稅負與納稅人的生產量或所得沒有任何比例關係。現在這兩種稅都因為土地所有權之存在而發生,它們的總稅負便變成了急驟累退的稅率。每單位產量或收入所負擔之總稅額因土地擁有量之上昇而遞減。
這兩種稅制比較之下,田賦的負擔遠較人頭稅為輕。其法定稅率,各朝代都能維持在總收穫量的百分之十以下。在漢朝某個時期,政府的減稅政策甚至將此法定稅率降低至百分之三左右。此外,田賦的隱逃較易,難以全額稽徵,故實際稅率往往遠低於法定稅率。但是人頭稅部份則情形反是。漢初力役之征,「正卒」以每丁每年一月為期,另外每丁每年戍邊三日。無法親自服役之人,可以每月二千錢的代價請人代役,是謂踐更 。這個代價,與居延漢簡中所記載的土地每畝百錢,粟每石百十錢相比,可說是相當高了。到了唐朝,「正役」之外另有「加役」。兩者合計,可高達五十日 。每逢戰亂多事之秋,實際征調的力役往往大為超過法定日數,占用了每一勞動力每年的大部分時間。在這種稅負重而又高度累退的租稅結構下,農民如果在很小一塊田地上進行生產,其每年的淨所得將不足以繳納租稅。土地已不是資產(asset)而是一種負債(liability)。許多小土地所有者在無法擴大其土地擁有量的情形下,只好放棄土地,全家逃亡,以避免納稅。可耕的田地便這樣被荒蕪了。不過,逃亡並非長久之計,於是更多的小農將他們的田地獻給富豪,以求蔭庇,是為「帶產投靠」。
從富豪巨室的立場來看,田產愈大,繳稅後的報償率也愈高。不過,在他們擴充田產的同時,必須設法獲得必要的勞動力,「帶產投靠」正好為他們同時解決了這兩項問題。在很多朝代,許多富豪因為政治地位或官職而享有合法收納「蔭戶」「附戶」的特權,及免除賦役的特權 。許多巨室雖然不能合法取得這些特權,卻也非法地這樣做。帶產投靠的農民因此得以脫離政府課稅的編戶。勞動力與土地同時向大戶集中。
人民因避役而棄產逃亡,或帶產投靠巨室,史不絕書,《鹽鐵論》的〈未通篇〉及〈徭役篇〉都指陳此一事實。《後漢書》更不斷記載「流人」現象。東漢時編戶人口之急驟減少,也與此不無關係。國家編戶人口之減少,一部份是反映富豪蔭戶人口之增加。於是累退租稅結構的後果,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人民棄產逃亡,或帶產依託豪強,政府課稅的基礎便日形縮小,因而不得不提高稅率,結果迫使更多農民棄產投靠,殘留在編戶內的納稅人人數便更少,最後不免全面崩潰。
針對這種趨勢,政府早晚要謀求改制。西晉倡行的限田制,便含有租稅改革的意味,企圖以對每戶私有土地數量的限制,來避免租稅負擔的累退現象。如果每一農家都按照「標準戶」所限定的田畝數置產,每一家又按標準戶所規定的稅額納稅,租稅力役之負擔自然平均。這種理想後來更進一步發展成北朝的均田制。不過在南朝各代,土地私有制絲毫未受限制,而士族之免徭役更加制度化 。士族私屬的佃客、典計及衣食客「皆無課役」,也是有明文規定的 。於是南朝士族隱丁匿口兼併土地益盛。
即使是在均田制實施區內,土地的分配也不是完全平均的。北魏北齊都允許人民畜養奴婢,而奴婢也可以分得若干「露田」。不過每名奴婢負擔的稅賦則遠較一般良丁為低 。其結果自然是鼓勵人民在法令範圍內多畜奴婢,從事耕作。唐初的均田制,原則上仍是依法令受田還田,但是法令也允許在例外情形下的土地合法買賣。在法令規定以外,私自違法買賣田地者,應受處罰。可是到了均田制的後期,戰亂頻仍,法令廢弛,兼併之風再起。
唐之稅法,據新唐書記載,租庸調皆「以人丁為本」,即以人丁為計稅單位,也就是租庸調三者合併為一項人口稅。在均田法有效執行時,各戶地與丁有固定比例,不論是以田畝為計稅單位或是以丁為計稅單位,其結果一樣。但至唐中葉,均田法已不能嚴格執行,土地分配不均,尤其是在地少人多所謂的「狹鄉」中,土地不敷分配,很多人都不能足額受田。這時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就造成嚴重偏差,地多丁少者稅輕,地少丁多者稅重,對於後者,田畝已非資產,反變成負擔,於是有人企圖棄產逃稅,或是變賣手中現有的口分田,或是根本放棄受田的權利,避至他鄉,不入本地戶籍以避稅。政府更以法定免稅特權來鼓勵人民遷至他鄉。《通典》說;「諸人居狹鄉者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於是有大量人民逃鄉避稅,他們在新居地沒有戶籍,稱為「客戶」。《文苑英華》卷七四七說:「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州縣收其名,謂之客戶」。在這同時,另有一批人享有免稅特權,可以廉價收購逃亡農戶所棄之田。唐制允許某些人不納租庸調,如部曲客女奴婢,他們無權受田,自然無義務納稅。另有一批人,他們可以占有田產但卻有不納稅之特權,包括九品以上之品官、太學生員、四門學生員,稱「不課戶」或「形勢戶」。這些戶趁機大量廉價收購逃鄉農戶的棄田。官戶之創設唐室開其端,此後一直延續未廢,為中國稅制史上的大漏洞。史載唐天寶十三年總戶口數9,619,254,其中「不課戶口數」為3,886,504。這其中一部分是部曲客女奴婢,其餘的就是這些不納稅的形勢戶。天寶十一年的詔書已明白指出形勢戶兼併土地之氾濫:
如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咨行吞併,莫懼章程。……爰及口分永業,違法買賣,或改籍書,或云典貼,致令百姓無處安置,乃別停客戶,供其佃食。
唐德宗建中年間,楊炎為相,明令廢止租庸調制,改行兩稅法,這是一項大改革,也是中國賦稅史的轉捩點。秦漢以來,地畝與人丁均為課稅對象,但以丁為主,漢時地稅輕丁稅重,唐時「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實際上是三者合併為丁稅。兩稅法實行以後,或是以田畝為計算單位,變成綜合財產稅,或是地與丁並重,但地重丁輕。從邏輯上看,這種轉變是合理的。從多種稅源徵課,可能減少稅制上的嚴重偏差,但執行起來困難較多,集中於一兩項稅源,行政上易行,所以歷朝均有簡化稅制的構想。但如何才能捕捉到最主要的稅源?漢代地多人少,勞動力是制約性的生產要素,有勞動力者便能從事生產,賺取所得,只有土地而無人力便無法從事生產。故以勞動力做為所得的標誌,訂為課稅對象,原則是不錯的。但至唐時,情況已經變了,很多地方都是地少人多,土地才是制約性的生產要素,應該以土地為課稅對象。唐的租庸調制以丁為本,形成重大偏差,很多小農戶丁多田少,沒有足夠的所得來付稅。唐中葉,小農戶棄產逃鄉之高潮,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德宗楊炎不得不改弦更張,扭轉這種偏差。
楊炎的兩稅法是將「租」的部分,從按丁徵收改為按畝徵收,「十畝收其一」,於是變成真正的田賦,分夏秋兩季徵收不同的穀物。原來的「庸」與「調」併入戶稅,改按丁或按戶收,以錢幣繳納。稅率按戶等而分高低。不是務農人民,其邸店行鋪及爐冶皆列為稅產而納戶稅。任官的免稅特權亦被取消,任官一品為上上戶,稅四千文,九品為下下戶,稅五百文。田賦加戶稅可以說是綜合財產稅,田賦是百分之十的比例稅率,戶稅則是累進稅率。更重要的規定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課稅對象擴大,包括客戶。至此,小農戶棄產逃鄉的誘因大為減弱。陸贄〈均節賦稅恤百姓〉一文中說;
「先王之制賦人也,必以丁夫為先……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
我們可以說,由於租稅制度不良,兼併之風至唐中葉達於高潮,耕地分配不均也以此時為最。兩稅法實行以後,未見進一步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