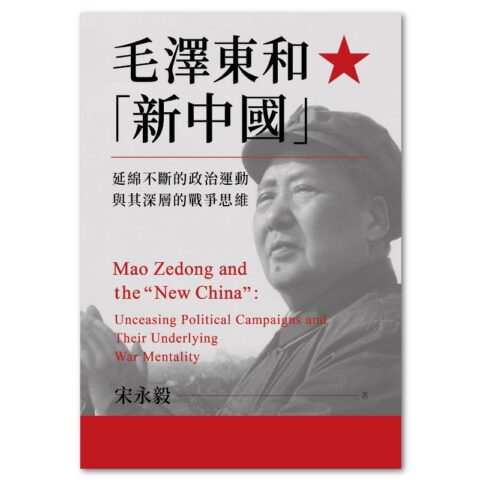中國的城市生活
出版日期:2005-10-25
作者:李孝悌等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596
開數:25開
EAN:9789570828696
系列:中國制度史論叢書
已售完
本書收集的十三篇論文,原發表於2001年12月19日至21日在埔里暨南大學所舉辦的「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研討會,是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的成果之一。這些文章探討的課題包括:逸樂作為一種價值、宗教與士人生活、士庶文化的再檢討、城市生活的再現、商人的文化與生活、微觀/微物的歷史以及傳統與現代等。是台灣文化史研究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作者:李孝悌等
編者簡介
李孝悌,台大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與生活》等書。
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課題(李孝悌)
過眼繁華:晚明城市圖、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王正華)
明清以來漢口的徽商與徽州人社區(王振忠)
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與尚俠風氣(王鴻泰)
明清江南東嶽神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以蘇州民變為討論中心(巫仁恕)
在城市中徬徨-鄭板橋的盛世浮生(李孝悌)
水窩子:北京的供水業者與民生用水(1368-1937)(邱仲麟)
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文人的彈詞創作初探(胡曉真)
發現生活: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重慶城市社會變遷(張 瑾)
黃鶴樓:人去樓坍水自流──一個樓的文化史(陳熙遠)
城鄉的過客──檔案中所見的清代商販(劉錚雲)
完美圖像:晚清小說中的攝影、慾望與都市現代性(曾佩琳Paola Zamperini)
民國時期的摩登玩意、文化拼湊與日常生活(馮 客)
「荒涼景象」:晚清蘇州現代街道的出現與西式都市計劃的挪用(Frank Dikötter柯必德Peter Carroll)
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課題
李 孝 悌
(一)
在美國歷史學界,「新文化史」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發展成一個新的次學門。1984年,以Victoria Bonnell和Lynn Hunt為首的一批史學家,應加州大學出版社的邀請,出版一系列以「社會與文化史研究」為名的叢書。在這套叢書的序言中,編者為研究主題作了大概的界定,指出這套書的研究範圍將包括「心態、意識型態、象徵、儀式、上層文化及通俗文化的研究,並且要結合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作跨領域的研究」 這套叢書以「社會與文化」為名,其中的一個原因是這些後來以文化史研究成名的學者,原來受的多半是社會史或歷史社會學的訓練—這個傾向也反映了到1970年代為止,社會史研究在美國史學界所佔有的重要地位。
但在1970年代中,隨著Clifford Geertz、Pierre Bourdieu及Michel Foucault等人的著作的問世,一個對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與文學批評等領域都有深遠影響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逐漸蘊釀成型,文化史研究從1980年代開始,成為美國史學研究的顯學。
從1980年代開始打著鮮明旗幟出現的「新文化史」,就和它所承續的社會史一樣,有著極強的理論預設。從1950年代開始興盛的社會史,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和年鑑學派的影響下,對傳統偏重少數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的政治史研究提出批判,將研究重點移向下層群眾和所謂的整體歷史及長期結構,認為惟有如此才能掌握到社會的真實。 但新一代的文化史家卻不相信有這樣一個先驗的、客觀的真實,他們也反對過去社會史、經濟史和人口史學家以建立科學的解釋(explanation)為最終目的的基本立場。在傅柯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文化史家主張所謂的真實,其實是深深受到每個時代所共有的論述(話語)的影響。而在Geertz的影響下,對意義的追尋和詮釋,就成了文化史家的首要工作。
由於不相信有一個客觀的、先驗的實存被動的停留在那裡等待我們去發現,論述(discourse)、敘述、再現等觀念,都成為新的文化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論上的問題。此外,由於不相信我們可以經由科學的律則和普遍性的範疇來發現歷史的真理,文化史家轉而對文化、族群、人物、時空的差異性或獨特性付出更多的關注。不少知名的史學家放棄了過去對長期趨勢或宏大的歷史圖像的研究,而開始對個別的區域、小的村落或獨特的個人歷史進行細微的描述,Emmanuel Le Roy Ladurie 和Natalie Davis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文化史家雖然對科學的規則或普遍的範疇感到不滿,並對一些後現代主義和文學批評所啟發的理論有細緻深刻的思辨,但在從事實證研究時,卻常常在課題的選擇上招致批評。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權威學者Francois Furet就曾指責年鑑學派的心態史研究缺乏明晰的焦點,而由於沒有清楚的定義,研究者只能跟隨流行,不斷地尋找新課題。即使像Robert Darnton這麼知名的文化史家,也批評法國的文化史家無法為心態史這個研究領域建立一套首尾一貫的觀念。 不管這樣的批評是否公允,文化史研究的目的何在,似乎成了各地的學者都要面臨的問題。
(二)
台灣的文化史研究,大約是從1990年代開始萌芽。其中雖然可以看到年鑑學派、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但在最初的階段,對再現、敘述等觀念的理論意涵,並不像前述西方史學家那樣有深刻的省思,和歷史社會學的關係也不緊密。此外,由於台灣的文化史家不像西方的同行那樣,對社會史的理論預設,因為有清楚的掌握從而產生強烈的批判,所以從來不曾把社會史研究作為一個對立的領域,並進而推衍、建立新文化史的理論框架和課題。我們甚至可以說,台灣的新文化史研究其實是從社會史的研究延伸而出。
這個新的文化史研究方向,最早是從研究通俗/大眾文化出發,然後有專門的團隊以「物質文化」為題進行研究。最近三年由中研院支持的主題計畫「明清的社會與生活」,聚集了一批海內外的歷史學者、藝術史家和文學史研究者,以中國近世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明清江南為題,持續地進行團隊研究,累積了相當的成果。文化史的研究至此可以說是蔚為風氣,一個新的研究次領域也大體成形。
在通俗文化的研究中,民間宗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社會史研究的影響在此清晰可見。葬禮和三姑六婆等不入流的下階層人物,也因此躋身為學院研究的對象。接著學者開始從戲曲、畫報、廣告等資料去探討城市民眾的生活、心態和娛樂等課題,文化史的色彩日益突顯。我自己和其他幾位學者又進一步利用戲曲、流行歌曲、文學作品、通俗讀物、色情小說等資料,對士大夫、一般民眾以及婦女的感情、情欲、情色等感官的領域,作了一些踰越過去研究尺度的探索。與此同時,和通俗讀物有密切關係的明清出版市場,以及圖像在通俗讀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等課題,也吸引了藝術史學者和歷史學者的重視。
物質文化的研究,是一個已經被提上議程,卻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在這一方面,對中古時期的椅子、茶/湯,以及明清時期的流行服飾、轎子等細微之物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這其中關於服飾和交通工具的研究,其實和海峽兩岸學者對十六世紀初葉之後,商品經濟的勃興所造成的社會風氣及物質生活的改變所作的大量研究,有極密切的關係。
「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的主題計畫在提出時,有一部份受到Braudel對日常生活的研究及所謂的 “total history” 的觀念的影響,覺得我們過去對明清社會的研究,還有不少需要補白的地方。但我們對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其他理論背景並沒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完全不知道Lynn Hunt等人也以「社會與文化史研究」為名,進行了十幾年的集體研究,並出版了一系列的叢書。
雖然在計畫提出時,我們都希望針對一些過去不會被拿來當作嚴肅學術研究對象的課題進行研究,但卻不曾對探討的課題作太多的限制或給予一個非常緊密、集中的理論框架。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必須尊重研究團隊各個成員自己的專長和興趣,一方面也因為我們覺得生活或城市的歷史自身就非常豐富、歧異,在對細節有更多的了解前,似乎不必用過份聚焦、狹隘的視野限制了可能的發展。
在這樣的認識下,我們在過去三年中,對食、衣、住、行、娛樂、旅遊、節慶、欲望、品味、文物、街道、建築等課題進行廣泛的探索,這些實證性的研究,除了提供許多新鮮有趣的視野,使我們對明清文化的了解有更豐富、多元的理解,也讓我們建立了一些解釋框架,再轉過來協助我們去重新看待史料。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對這些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課題,作進一步的介紹和分析。
這些課題包括:逸樂作為一種價值、宗教與士人生活、士庶文化的再檢討、城市生活的再現、商人的文化與生活、微觀/微物的歷史以及傳統與現代等。
(三)
1.逸樂作為一種價值
我在<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禎在揚州>一文中,曾經對以逸樂作為學術研究的課題有下述的論辨:
在習慣了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的角度,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後,我們似乎忽略了這些人生活中的細微末節,在型塑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結果是我們看到的常常是一個嚴肅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層文化。缺少了城市、園林、山水,缺少了狂亂的宗教想像和詩酒流連,我們對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構,勢必喪失了原有的血脈精髓和聲音色彩。
這樣的看法,並不是我一個人偶發的異見,而是我們長期浸淫在台灣的史學研究環境後,必然會產生的一種省思和反映。事實上,我們這個計畫團隊的成員,紛紛從不同的課題切入,指出在官方的政治社會秩序或儒家的價值規範之外,中國社會其實還存在著許多異質的元素,可以大大豐富我們對這個文化傳統的理解。
陳熙遠在<中國夜未眠-明清時期的元宵、夜禁與狂歡>一文中, 利用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狂歡節的觀念,對中國元宵節的歷史與意涵作了深入的剖析。官方對這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節慶日,雖然原有一套規範的理念與準則,但在實踐過程中,民眾卻踰越了種種規範,使得元宵節不僅是明清時期重要的娛樂節慶,更成為顛覆日常秩序的狂歡盛會。
百姓在「不夜城」裡以「點燈」為名,或在「觀燈」之餘,逾越各種「禮典」與「法度」,並顛覆日常生活所預設規律的、慣性的時空秩序-從日夜之差、城鄉之隔,男女之防到貴賤之別。對禮教規範與法律秩序挑釁與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類活動遊戲規則的主軸。……而在明清時期發展成型的「走百病」論述,婦女因而得以進城入鄉,遊街狂廟,甚至群集文廟、造訪官署,從而突破時間的、空間的,以及性別的界域,成為元宵狂歡慶典中最顯眼的主角。
元宵節固然為民眾-特別是婦女-帶來了歡愉和解放,卻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廟會、節慶同樣也能讓民眾從日常的作息和勞役中得到暫時的解脫。巫仁恕對江南東嶽神信仰的研究,顯示在明清之際,江南各地不論是城市還是市鎮,都會隆重的慶祝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東嶽神誕會」:「金陵城市春則有東嶽、都天諸會」「諸皆遨遊四城,早出夜歸,旗傘鮮明,簫鼓雜遝。」「無錫鄉村男女多賚瓣香走東嶽廟,名曰『坐夜』。江陰迎神賽會,舉國若狂。」「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為東嶽天齊聖帝生辰,邑中行宮,凡八處,而在震澤鎮者最盛。清明前後十餘日,士女捻香,闐塞塘路,樓船野舫,充滿溪河,又有買賣趕趁茶果梨,……以誘悅童曹,所在成市。」
這樣的廟會節慶,和元宵節一樣,發揮了重要的娛樂功能,但另一方面也同樣潛在著顛覆既存秩序的危險。一旦遇到政治、社會狀況不穩定時,節慶的儀式活動很可能為民眾的叛亂與抗爭活動,提供象徵性的資源。
除了這些定期的節日和廟會慶典,明中葉以後流傳的民眾旅遊,也提供了更多娛樂的機會。這些旅遊活動很多是和民間信仰中的廟會、進香有關,也有一部分是受到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和晚明士大夫旅遊風氣的盛行的影響。根據巫仁恕的研究,晚明以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許多大城市附近的風景區都變成民眾聚集旅遊的勝地,北京、蘇州、杭州、南京等地附近的名勝都有「都人士女」聚遊與「舉國若狂」的景象。在歲時節慶時,旅遊活動的規模更加擴大。 逸樂已經很明顯的成為士大夫以及民眾生活中的一環。
王鴻泰對游俠的討論,更精闢地指出不事生產、縱情逸樂的游俠之風,如何在明清之際的士人文化中,成為「經世濟民」「內聖外王」和科舉考試等主流的儒家價值觀之外,另一種重要的人生選項和價值標準。這些士人由於在舉業上受到挫折,逐漸放棄了儒家基本的價值觀-齊家、治國、治世-,並發展出一套全新的人生哲學和生活實踐。任俠、不事生產、不理家、輕財好客,縱情游樂,詩酒活動成為這些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而城市則提供了實踐這種游俠生活最好的舞台。
在經濟、宗教因素之外,價值觀的改變,則為俠游或廣義的逸樂活動帶來了更正面的意義:
俠游活動,對個人而言,是一種新的人生觀、生命意義的建構工作,而對整體社會文化而言,則可以說是種新的社會價值、生活意義的創造過程。或者,更精確地講:俠游活動是個人透過特定的社會活動,以及相應的意義詮釋,而在社會文化層面上,進行意義與價值創造的工作。
我在這裡以「逸樂作為一種價值」為標題,有兩層意義:一是用來呈現作為我們研究對象的明清文化的一種重要面相;一是要提醒研究者自身正視「逸樂」作為一種價值觀、一種分析工具、一種視野以及一個研究課題的重要性。而這兩者又相互為用。前面介紹的幾項研究,都顯示在明清士大夫、民眾及婦女的生活中,逸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甚至演生成一種新的人生觀和價值體系。研究者如果囿於傳統學術的成見或自身的信念,不願意在內聖外王、經世濟民或感時憂國等大論述之外,正視逸樂作為一種文化、社會現象及切入史料的分析概念的重要性,那麼我們對整個明清歷史或傳統中國文化的理解勢必是殘缺不全的。
知名的思想史家Stuart Hughes在1958年出版的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一書中,一開頭就提到:「自來歷史學家便在不知所以然的情況下,一直在撰述『高層次』的事物。他們的性質氣質投合於過去的偉大行為與崇高的思想。社會科學的新自覺,並沒有改變他們的這種傾向。」 這句幾乎是半個世紀前有感而發的議論,即使在今天看來,仍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特別是當我們要為逸樂這個軟性、輕浮的,具有負面道德意涵的觀念在學術史上爭取一席之地時,作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型態,明清的儒家思想和歐洲中古的基督教、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或十九世紀末的實證主義,在各個文明的實際進程和研究者的論述中所佔有的主導性地位,是不需要有什麼懷疑的。但在主流之外,如何發掘出非主流、暗流、潛流、逆流乃至重建更多的主流論述,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在這樣的脈絡下,Bakhtin對森嚴的中古基督教世界內的嘉年華會研究; Peter Gay對啟蒙運動中,哲學家對「激情與理性」等議題的辨析; 以及Stuart Hughes對十九、二十世紀初,實證主義之外的無意識作用和「世紀末」的思想風氣的論述,無疑地都對我們在理學之外,彰顯逸樂的價值,有極大的啟發性。
2.宗教與士人生活
在我們從2001年到2003年所執行的三年主題計畫中,宗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課題。西方漢學界過去二、三十年內,對民間宗教以及宗教與民眾叛亂間的關係,已經作過大量的研究,有不少也成為典範性的作品。巫仁恕對江南東嶽神信仰的研究,除了指出廟會節慶活動幽默、滑稽與競賽的娛樂功能外,並就民間信仰與城市群眾的抗議活動之間的關係,作了相當細微的闡述。過去的研究,多半將焦點集中在農村,對城市改變的研究,則側重在經濟社會面,而忽視了宗教所扮演的功能。就此而言,巫仁恕對東嶽神信仰和城隍信仰的研究,無疑是有許多新意。
相對於巫仁恕從城市群眾與暴力的觀點切入,我則特別想理解宗教在明清士大夫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之所以選擇士大夫作為研究的重點,有一部份的理由和前述的逸樂觀類似。我的基本前題是:作為意識型態的儒家思想或理學,雖然是形塑明清士大夫價值觀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但卻絕不是唯一的因素。過去的研究太側重在作為主流意識型態的儒家思想在道德及理性層面所發揮的制約、規範力量。在這樣的一個道德的、理性的儒學論述之後,那些被視為不道德的、非理性的、神秘的面相──如逸樂、宗教──,在我們討論明清士大夫文化、思想時,往往隱而不彰,甚至被刻意消解掉。
在我所處理的幾個個案中,王士禎對風水、算命等宗教活動和各種奇怪可異議之論,表現出極高的興趣。袁枚對宗教信仰的態度,雖然不像王士禎那麼清晰明確,但《子不語》和《續子不語》中,數十卷虛實相間的神怪故事,卻構築出一個豐富、駁雜的魔幻寫實世界。在十八世紀南京城的一隅,從儒家仕宦生活中退隱的袁枚,在自己的後花園中,發揮了無比的想像力,營造出一片神秘的宗教樂園。
比袁枚早一個世紀的冒襄(1611-1693),雖然因為不同的原因中斷了儒生的志業,卻和袁枚一樣,精心營造出一片園林,並在園林中充分享受了明清士大夫文化中的各種美好事物。和袁枚一樣,冒襄也在幽曠的園林中,留下了鬼魅魍魎的記敘。但不同於袁枚各項記述的虛實相間,冒襄卻以驚人的細節,描繪了自己和親人在死生之際的種種神秘歷程。更重要的是,冒襄因為賑濟疾厲、災荒而致病瀕危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忠實地履踐儒生經世濟民的志業和地方士紳周濟鄉黨的職責。而他之所以能死而復生,則是因為在執行這些儒生的志業時,所累積的功德。另一方面,冒辟疆幾次傾其所有的賑濟災民,背後的一個重大驅力,則是出於至孝之忱,希望以此累積功德,為母親陰騭延壽。
Cynthia Brokaw的研究,指出功過格在明末清初士大夫階層中普遍流傳,有極大的影響力。 冒襄的夫子自道,為這項研究提供了極佳的例證。但我特別感到有趣的是,在這個例子中,儒生的價值觀和神秘的宗教信仰是如何緊密的糾結在一起。 我們在研究明清士大夫的生活與文化時,如果只從一個特定的範疇-如儒生/文人,或學術的專門領域-如經學/理學/文學-著手,勢必無法窺其全豹。這些既有的學術傳承常常讓我們忽略了研究的對象並非都是「扁平型」的人物,而往往有著複雜、豐潤的面貌。文化史和生活史的研究,在此可以扮演極大的補白功能。
3.士庶文化的再檢討
我在1989年,首次對大/小傳統或上/下層文化這套觀念的由來,及其在中國史研究上的應用,作了簡要的介紹。 接著,我又在1993年,從「對民間文化的禁抑與壓制」、「士紳與教化」、「上下文化的互動」三個角度出發,對十七世紀以後中國的士大夫與民間文化的關係,作了一次研究回顧。 在此期間,台灣學界對民間文化的研究日益增長,但對上/下層文化這個觀念作為分析工具的效力的質疑,也不斷出現。
但儘管有各種質疑,從我們這個團隊的成員所作的研究中,卻可以發現士庶文化這個課題仍有極大的探索空間。王鴻泰、巫仁恕等人的研究,也讓我們對明清的雅/俗、士/庶文化,有了耳目一新的看法。
根據巫仁恕的研究,一直到明代中葉,旅遊還不被當成正經的活動,知名的理學家湛若水就對士大夫的山水旅遊抱持輕蔑的態度。不過就像許多其他現象一樣,士大夫對旅遊的觀念也從明中葉以後漸漸有所改變。旅遊不僅被視為一種「名高」的活動,更成為士大夫中普遍流行的風氣。在士大夫篤好旅遊之風的影響下,遊記大量出現,旅館日趨普及,甚至還有了為遊客提供各項服務的代理人(牙家)。士大夫出外旅遊,除了呼朋引伴、奴僕相隨外,也不時勞動僧道作為導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旅遊並不是士紳官僚的專利,在大城市附近的風景區往往也成為一般民眾聚集旅遊的勝地。士大夫優越的身分意識,在這種情境中毫不遮掩的顯露出來。對他們來說,嘈雜的民眾總是將美景名勝變成庸俗之地:「使丘壑化為酒場,穢雜可恨」。所以在遊旅的地點和時間上,士大夫往往作刻意的區分,不是選擇一般民眾不常聚集的郊外山水,就是選擇人蹤稀少的季節或時辰。同時,為了彰顯自己獨特的品味,他們也常常發展出獨特的旅遊觀──所謂的「遊道」。對遊具、畫舫的講求,就是士大夫展示其精緻品味的具體表徵。
巫仁恕的研究,不但豐富了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內容,也為雅俗之辨找到了一個有趣的切入點,但事實上,隨著經濟的發展、民眾消費能力的提昇和市場的流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模仿、複製士大夫文化,在晚明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這些庸俗化的模仿、複製,不但讓自命風雅的文人名士感到不屑、厭憎,也往往引發他們對身分認同的自覺和危機感。所以,區分雅俗,經營出特有的生活品味和風格,就成為明清文人士大夫的重要課題。王鴻泰在<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與雅俗的辯證>一文中,就對文人文化的特色作了全面而具有理論意涵的分析。
在王鴻泰看來,明清文人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建基於一套將世俗價值掃落於後的「閒隱理念」。但重要的是,要實踐這一套閑隱的理念,文人士大夫不但不能無為地坐任文化自動開展,反而要孜孜矻矻的努力建構。王鴻泰在此提出生活經營的概念,可說是切中問題的核心。我對袁枚隨園和冒辟疆水繪園的研究,可以作為「經營」這一概念的註腳。
雅文化之所以能夠建立,除了一定的物質、經濟基礎外,閑情雅緻也是必需具備的條件。王鴻泰從時間、空間兩個向度展開論證:
所謂閒雅的生活,其經營的起點,可以說從時間和空間的重新架構而展開的。首先,所謂的閒雅,必要的基本條件是「閒」,即要有時間上的餘裕,至少在感受上,必須要有一種不為時間所役的「閒情」;再者,必需要有個「雅」的空間來承載、投注、寄托、體現他們的閒情。所以,士人的生活經營,除了基本生存條件的經營等世俗層面外,他要在概念與形式上,重新建構新的時間、空間。
巫仁恕提到士大夫在旅遊地點和季節、時辰的選擇上的講求,與王鴻泰此處所說的雅俗之辯,可以前後互應。
除了山川旅遊、詩酒酬唱、歌舞笙簫外,對玩物的耽溺,也是士大夫雅文化的要素:
明清士人「閒隱」理念的具體落實乃開展出一套「雅」的生活,而所謂雅的生活可以說是在重新架構起來的時間、空間中,放置新的生活內容,這些生活內容如上所言:無非「若評書、品畫、瀹茗、焚香、彈琴、選石等事」,也就是說將諸如書畫、茶香、琴石等各種無關生產的「長物」(或玩物)納入生活範圍中,同時在主觀態度上耽溺其中,對之愛戀成癖,以致使之成為生活重心,進而以此來營造生活情境,作為個人生命的寄託,如此構成一套文人式的閒賞文化。
這種對雅文化的追求,自明中葉以後逐漸形成,在不斷的充實與渲染之後,漸漸成為士人/文人特有的文化類型,這個文人文化一旦發展成優勢的文化類型,就引起社會上不同階層,特別是商人階層的倣效。文人為了劃清與這種附庸風雅的複製、膺品間的界限,乃格外重視雅俗之間的辯證。
4.城市生活的再現
在我們這個研究團隊中,邱仲麟是真正從一般民眾切身的生活瑣事著手,討論明清北京日常生活的「真實」面貌。他在這幾年內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內,分別討論了民眾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燃料、用水,以及如何用冰來維持食物的新鮮,並緩解酷熱的氣候所造成的不適。
媒炭、用水與冰,看起來和閒雅的士大夫所沈溺其中的書、畫、茗、香、琴、石一樣,都是瑣細之物,但所具有的意義自然是不同。由於邱仲麟能將這些瑣細之物,放在更廣大的生態史和制度史下的脈絡來考察,不但使原來看似乾澀的典章制度和單調、沒有生命的結構、物質,因為和生活緊密相聯,而立刻產生新的意涵;也同時讓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細瑣之物,能承載更嚴肅的使命。
北京居民原來是靠附近森林所提供的木柴,作為主要的燃料。但隨著人口的增長,飲食炊爨、居室建材等需求加大,山林濫伐的問題日益嚴重,柴薪的供應也日趨枯竭,從十五世紀後半葉開始,媒炭的使用日益普遍,漸漸取代柴薪,成為主要的燃料。煤炭固然解決了燃目之急,卻也對北京的生活環境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煤屑堆積及空氣污染等問題,在明代後期愈加嚴重。
煤屑、污染使得北京原來就不是很好的居住環境變得更加糟糕,從許多士大夫的記敘和回憶中,我們知道北京在「宏偉的城牆、壯麗的宮殿、堂皇的衙署、繁華的市街與眾多的人口」之外,其實還有著陰暗難以忍受的一面。沒有了北方森林的屏障,塵土和風沙的侵襲益形嚴重,雨後泥濘不堪、臭氣薰天的街道,更成為許多人生活中的夢魘,再加上狹窄的居住空間,四處飛舞的蚊蠅和不時出現的瘟疫,都讓北京的日常生活變得狼狽而猥瑣。
根據邱仲麟的解釋,明清士人對北京的回憶之所以如此惡劣不堪,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南北的差異。記敘者多半來自氣候溫和、山水秀緻、街道整齊、空氣清新的南方,用他們對南方的懷念和記憶來對比北京的嚴峻和污穢,印象就格外惡劣。
南北城市生活的差異,自然讓回憶者的記敘呈現不同的面貌,但我自己對揚州和鄭板橋的研究,則顯示記敘者的身分和心境,無疑也影響了他觀看城市的方式和視角。對前半生落魄不第的鄭板橋而言,揚州城的繁華,反而更襯托出自己的落寞和悲傷。這種文人感懷身世的回憶,當然是城市經驗的一部分,但必需和其他不同性質的記載合而觀之,才能讓我們對十八世紀揚州的城市生活有更全面的掌握:
十八世紀的揚州留給後人最強烈的印象,當然是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板橋的一些詩作,也明確無誤地反映出他所身處的這個城市的光影溫熱。但更多時候,他是用一種落魄的、文人的眼光,冷冷地看待這些不屬於他的塵世的繁華。像是一個疏離的旁觀者一樣,鄭板橋讓我們在商人營造的迷離幻境外,看到不第文人的困頓和文化歷史的傷感。不論是對困扼生活的寫實性描述,或對城市景物的歷史想像,鄭板橋的文人觀點,都讓我們在李斗全景式的生活圖像,和鹽商炫人耳目的消費文化之外,找到另外一種想像城市的方式。加在一起,這些不同的視角呈現出更繁盛和誘人的城市風貌。
不僅南北的差異,記敘者的身份、心境會影響到城市呈現的風貌,記憶呈現的媒介也會大大影響到我們對城市的印象。文學、圖畫和攝影,不同的媒介,常常帶給閱讀者/觀賞者迥然不同的體驗。王正華對城市圖的研究,就是一個絕佳的例證。透過藝術家再現出來的城市圖像,色彩明朗鮮艷,街道整潔熱鬧,人物或是衣冠華美,或是表情愉悅,充分展現出城市生活的富庶和誘惑。在此,我們看不到城市生活的陰濕卑陋,更聞不到令人掩鼻的腐臭氣味,藝術史和社會史的差別,在此明顯可見。
當然,這並不是要否定城市圖像的寫實功能,這一點王正華說得很清楚:
據說張擇端本《清明上河圖》中船隻的描繪十分寫實,今日可據以重構,而畫中拉縴方式即使今日縴夫見之也點頭稱是。再如《皇都積勝圖》中正陽門、棋盤街及大明門附近市集的描寫,確實在某種程度上符合同時代《帝京景物略》的記載。或者一如《上元燈彩圖》所繪,晚明南京的古物市場如此蓬勃興盛,而且「碎器」及「水田衣」隨處可見,著實流行於世。
但是從十六世紀晚期開始大量出現的城市圖,其主要的意義並不在於對不同時期的不同城市,作寫實性的描繪。和當時流行的城市讀物一樣,晚明城市圖因為價格低廉,完成後就成為一種文化商品,提供另一種消費的選項和城市想像的憑藉:「畫作完成後,成為文化商品,為時人文化消費的對象,在不同的人群中流通展閱。書寫記錄與口耳相傳,提供一種模寫城市的模式,並進而形塑當時的城市觀。」
在城市中徬徨-鄭板橋的盛世浮生
李孝悌
(一)緒言
在近年來研究取向的影響下,我們一提到明末的社會,馬上就聯想到經濟的發展,和文化思想的多元與解放。但課題一轉到十八世紀,我們的焦點卻都集中在帝王的專制統治、學術思想的閉鎖和文化道德的保守壓迫。明清文化似乎在此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斷層。我在<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欲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 一文中,從下層文化的角度,證明十八世紀的文化,並不像我們一般所假想的那般冷酷森嚴。在另外一篇討論袁枚的文章中 ,我進一步指出,即使在士大夫階層中,十八世紀的面貌,也和我們從文字獄、乾嘉禮學中所得到的印象截然有別。
袁枚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十八世紀社會的視野。我們當然可以輕易的假定袁枚的頹廢放縱,只是一個偶發的例外,缺乏更廣泛的文化史或思想史意涵。但在沒有對更多的士大夫生活史作更深入的分析之前,這樣的假設,其實和我們過份突出乾嘉禮學的社會影響力一樣,都缺乏堅實的基礎。無法讓我們對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有更全面的掌握。
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於透過個案研究,進一步累積我們對十八世紀士大夫的知識。將對象集中在揚州和鄭燮有幾個原因:一是鹽商的聚集,帶來了繁庶的經濟生活。根據研究,在明萬曆年間,數百家的鹽商已經造就了揚州「富甲天下」的榮景,清康、雍年間,揚州經濟在劫亂之後,再度穩定的成長。康熙、乾隆多次南巡揚州,更對城市的風貌帶來深刻的改變。 袁枚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追憶揚州的歷史時,曾提到他在四十年前游歷城西北的平山堂,一路水道狹隘,「旁少亭台」。但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南巡之後,山水、樹木、苑落都有了戲劇性的轉變:
水則洋洋然回淵九折矣,山則峨峨然 約橫斜矣,樹則焚槎發等,桃梅舖紛矣。苑落則鱗羅布列,閛然陰閉而霅然陽開矣。猗歟休矣!其壯觀異彩,顧、陸所不能畫。班、揚所不能賦也。
第二,鹽商的大量進駐,不僅改變了揚州城的外貌,也大大豐富了當地的文化內涵。從戲曲、園林、聲色、飲食到繪畫、出版、經學,集中地反映了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的複雜面貌。對以經學、禮學著稱的揚州來說,多重面貌的同時存在,尤足以顯示從乾嘉考據或禮學復興來概括十八世紀文化風貌之不足。
第三,鄭板橋的多重身份(儒生/文人/藝術家/官員)和生命歷程的各種矛盾、糾結(儒/釋,田園/仕宦,城/鄉,科名/叛道,對商品經濟的依賴和批評),正如同他所身處的盛世揚州一樣,提供了一個重新觀察十八世紀的新鮮視野。
(二)生平梗概
自號板橋的鄭燮,康熙三十二年(1693)生在揚州府興化縣的書香世家。曾祖父作過庠生,祖父是儒官,父親則是品學兼優的廩生,以授徒為生。 三世儒生的背景,固足以說明板橋的出生純正,卻不能保證他衣食無憂。事實上,貧窮可以說是板橋前半生最刻骨銘心的經驗。康熙六十一年(1722),板橋的父親立庵公過世。年已三十,並育有二女一子的鄭板橋,在一組回憶平生的詩作中,就不斷提到自己的貧寒和落魄:「鄭生三十無一營,學書學劍皆不成。……今年父歿遺書賣,剩卷殘編看不快。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 揚州畫派最負盛名的代表人物,卻落到絕薪並被逼債的地步,令人不勝唏噓。
雖然學書不成,又落到出賣父親遺書的地步,但世代業儒的板橋,也只能效法父親的榜樣,授徒為生。 在村塾授課,也許能一濟的貧乏,卻絕無法滿足他的鴻鵠之志。到此為止的頓挫,也使得出生儒者家庭的鄭燮,對人生有更多的質疑:「幾年落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長嘯一聲沽酒樓,背人獨自問真宰。」 板橋集中的強烈佛教色彩和他的狂放性格,顯然和前半生的貧窮、落魄生涯,有直接的關係。
雍正元年(1723),板橋以一種不合時宜的姿態,展開了十年賣畫揚州的生涯。 這個時候的揚州,雖然還沒有達到袁枚所形容的那種漪歟盛哉的程度,也已經是鉅商雲集的江南重鎮。但對鄭燮這個功名未就的寒士來說,城市生活的繁華靡麗,卻更反襯出自身處境的淒涼。透過他的冷眼,我們總是在熱鬧繁華的場景中,感覺到落魄文人的傷感。
雍正十年(1732),四十歲的鄭燮考中舉人,在漫長而正規的讀書仕進之途上,有了初步的斬獲。四年之後,通過殿試,人生頓然光明起來。為了慶賀自己考中進士,他特別畫了一幅<秋葵石 圖>,並題詩道:「牡丹富貴號花王,芍葯調和宰相祥;我亦終葵稱進士,相隨丹桂狀元郎。」 相對於賣畫揚州時不合時宜的竹柏,板橋用俗麗的牡丹芍葯描述功成名就時的喜悅,讓人在孤高狂放之外,看到他正統、世俗的儒生面相。
高中進士後,鄭板橋並未立即謀得官職,只好返回揚州。但這個時候,他已經不是籍籍無名的貧困畫師,而一邁成為揚州上層士紳圈中的一員。從文集中寫給尹會一 、盧見曾 等人的詩作,我們不難推想他在此時揚州文化界的位階。
經過六、七年的等待,板橋終於如願謀取到一官半職。從1742到1753年間,他先後出任河南范縣和山東濰縣的縣令,最後因為賑濟災民的問題,忤逆大吏而罷官。板橋為官雖然清廉勤政,夙有聲名,不過還是累積了一定的財產,大大改善了窘迫的經濟狀況。1753年致仕退休後,一直到1765年過世為止,他重操舊業,靠著在揚州賣畫為生。
(三)儒佛之際
作為乾嘉考據學重要分支的揚州學派,雖然直到十八世紀下半葉才發展成熟,但在鄭燮的後半生,揚州學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已經開始漸漸嶄露頭角。像是以禮學研究名家的任大椿(1738-1789),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就已經受到戴震的贊賞。 汪中(1744-1794)、王念孫(1744-1732)在鄭燮生前,雖然都還沒有真正從事經學研究,卻已經是相當有名氣的儒生。
也許因為鄭燮在世時,揚州的經學研究尚未蔚為風氣,也許因為他的性情和經學研究不相契合,我們在鄭板橋身上並嗅不出經學家或禮學家的氣息。不過這卻不意謂著以放狂著稱於世的鄭板橋,擺脫了儒家價值觀的束縳。事實上,從他的出生、教育、仕宦到生計,都充滿了典型的士大夫的色彩。這和他留給後世最深刻印象的文人藝術家的形象,顯然有極大的差異。
板橋的儒生認同,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來。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儒家經典的重視。1728年,他還沒有中舉之前,曾經在興化天寧寺讀書,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親自手鈔一部。 雍正十三年(1735),中進士的前一年,在寫給弟弟的一封家書中,他特別強調傳統經典文獻在人生中的效用,其中儒家典籍就佔了主要的位置:「吾弟讀書,四書之上有六經,六經之下有左、史、莊、騷、賈、董策略、諸葛文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書,終身讀不盡,終身受用不盡。」
這種對儒家經世致用的價值觀的認同,在中年踏入仕途之後,透過實際的作為,而得到施展。這個時候,文人藝術家的角色,似乎顯得無足輕重。乾隆十三、四年間,板橋任官濰縣時,第二次刊刻自己的詩作。在序言裡,他對自己騷人墨客的角色,採取了一種道貌岸然的貶抑姿態:
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為,風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顏色,嗟困窮,傷老大,雖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騷壇詞客爾,何與于社稷民生之計,三百篇之旨哉!屢欲燒去,平生吟弄,不忍棄之。
「不忍棄之」的說辭,固然顯示板橋並未否定自己的文人角色。但「文章經世」、「社稷民生」的傳統儒生價值觀,顯然在他的思想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
這種對儒家價值觀的認同,在<骨董>一詩中,有更強烈的顯現。在這首兩百多字的長詩中,鄭板橋對當時流行的搜集骨董的現象,備極嘲諷。為了表示自己的超凡脫俗,他用對儒家經典傳統的珍視,來表達對流風俗尚的鄙視:
我有大古器,世人苦不知。伏羲畫八卦,文周孔系辭。洛書著《洪範》,夏禹傳商箕。<東山><七日>篇,班駁何陸離。
作為一個以書畫作品著稱於後世的藝術家,鄭板橋不好骨董好經書的價值取向,相當程度說明了他的複雜面貌。這樣的面貌又因為他和佛教的密切關連,而益發引人注目。雖然他對儒家的基本價值有強烈的認同,但對當時一些排佛的言論卻又大不以為然。在寄給四弟的一封家書中,他先是對歷史上的排佛之舉感到不平,接著又以一種嘻笑怒罵的口吻,用和尚、秀才各打五十大板的策略,輾轉為對僧人的各項指控加以開脫:
況自昌黎辟佛以來,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書,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時而猶言辟佛,亦如同嚼蠟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焚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后之意。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語云:「各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為然否?
鄭燮寫這封家書的背景為何,是針對歷史上宋明儒的排佛言論,或他所身處的十八世紀的儒生議論而發,我們不得而知,但他意欲為僧人辯解的意味卻很明顯。而他之所以特意為僧人開脫,又和他與和尚的密切交往有直接的關係。事實上,這封為和尚辯解的家書,不僅是寄給自己的弟弟,還送了一份給無方和尚。
雍正二年,板橋三十二歲時,在江西廬山認識了無方和尚。 乾隆十年,板橋赴京參加會試,和無方和尚再度相逢,特別寫了兩首詩送給無方。 無方並不是板橋贈詩的唯一僧人。在板橋集中所載的二百多首詩作中,有近三十首都是以和尚或寺廟為對象。題贈的對象除了無方上人外,還有博也上人、松風上人、弘量山人、巨潭上人、起林上人、青崖和尚等。從這些詩作在板橋集中所佔的份量,以及他與這些遍佈各地的僧侶的交往,我們不難理解他為什麼會提出「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主張。
士大夫和和尚、道士維持密切的關係,在中國傳統中,原本不是什麼新鮮的課題。鄭燮以各不相干來調和儒釋二家的說法,也不像主張三教合一的思想家那樣,有任何理論上的建樹。但他在價值觀上服膺儒家思想,在生活實踐層次上,和寺院、僧侶密切結合的作法,再一次提醒我們在處理明清上層文化思想時,將注意力只集中在儒家主導性上的缺失。這種缺失在將十八世紀簡單地等同於乾嘉考據、禮學復興或道德保守力量抬頭等詮釋中,格外顯得刺目。
如果我們放寬視野,將對十八世紀的描繪從思想、學術擴及到文化、生活史的細節,鄭板橋和揚州僧人、禪寺的交往,又為本文開頭所強調的揚州文化的豐富面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註腳。在本文的開頭,我特別提到以揚州為研究課題的主因之一,在於這個城市的豐富生活,讓我們能跳脫狹隘的思想、學術視野,用鮮活的例證,切入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的複雜面相。而在揚州多彩多姿的城市生活中,鹽商固然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文人、藝術家、妓女、工匠、小販和僧人的參與,也不容忽視。尤其是僧人、寺廟,讓揚州的文人和城市文化,憑添了許多脫俗雅緻的風味。
根據記載,揚州人不分貴賤,都喜歡戴花,逛花市因此成為揚州人生活中重要的活動。而新城外禪智寺就是揚州花市的起源地。 在花市之外,青蓮齋的茶葉也非常有名。青蓮齋座落在天寧街西邊,寺裡的和尚在六安山擁有一片茶田。春夏入山,秋冬則移居揚州城。所生產的茶葉,有很好的銷路:「東城游人,皆于此買茶供一日之用。」鄭板橋特地為此題了一幅對聯:「從來名士能評水,自古高僧愛鬥茶。」 跳脫塵世的僧人和名士一樣,為庸俗的商業城市,注入一份從容幽雅的閑情逸致。
在板橋詩集中提到的許多和尚中,和揚州有直接淵源的是文思和尚。乾隆初,鄭板橋在北京探訪老友圖牧山,提到江南友人對他的懷念。圖牧山是一位滿洲官員,善書畫,移居北京後,就和江南的文化圈失去聯繫。板橋因此鼓勵他多利用書畫來慰解江南友人的懸念,其中特別提到文思:「江南渺音耗,不知君尚存。願書千萬幅,相與寄南轅。」「揚州老僧文思最念君,一紙寄之勝千鎰。」
短短幾句詩文中,我們已經隱約體會到和尚和士大夫、藝術家的深厚交誼。進一步考察,我們知道文思不僅和圖牧山有深厚的交情,實際上還是當時揚州上層社會社交圈的中心人物之一:「文思字熙甫,工詩,善識人,有鑒虛、惠明之風。一時鄉賢寓公皆與之友。」 「鄉賢寓公」紛紛和文思和尚訂交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文思工詩文,有深厚的文化素養;一方面大概也因為他擅長作一些美食,來滿足士大夫挑剔的口腹之慾:「(文思)又善為豆腐羹、甜漿粥,至今效其法者,謂之『文思豆腐』。」 十八世紀士紳官僚對飲食的考究,從袁枚的<隨園食單>中可見一般。 任何士紳官僚獨沽一味的秘方,一旦經過品題,就像詩文一樣,在士大夫的交游網絡中傳佈開來。文思的豆腐羹和袁枚食單中傳頌的許多名家美饌一樣,都是馳名的精緻美味,唯一不同的只是出自禪師之手。
對鄭板橋來說,和文思的交往,除了詩文、豆腐之外,還有一層更切身的因緣,那就是文思住的枝上村,正是板橋出仕前讀書寄居的所在。在<李氏小園>一詩中,板橋對寄居庭園的雅緻,物質生活的貧乏、困窘以及母子兄弟間的至情,有哀感動人的描述。
板橋在<懷揚州舊居>一詩標題下,註明「即李氏小園,賣花翁汪髯所築。」 清楚指出李氏小園就是他在揚州的舊居。這個院落在東晉時原是謝安作揚州刺史時的宅邸,後來謝安捨宅為寺,成為天寧寺的基址所在,謝安又另外在寺西杏園內枝上村建立別墅 ,所以板橋在詩中說「謝傅青山為院落」。 枝上村既名為村,顯然是一個不小的院落。除了文思和尚的禪房正好建在謝安原來的別墅外 ,其他地點分別賣給不同的人作不同的用途。
板橋所住的李氏小園也在枝上村中,這個院落在乾隆初年被汪髯買下來種花。 板橋因為和文思和尚同住在天寧寺西邊的枝上村,得地利之便,和文思等僧侶建立了友好的關係。這種在寺院緊鄰院落中居住 ,和寺僧建立友善關係的經驗,讓鄭板橋在儒生的認同外,又極力為佛教和僧侶辯護。這一點是和那些堅持儒家本位的理學家不同之處。但在十八世紀的士大夫中,到底有多少人採取闢佛的立場,是值得懷疑的。鄭燮在揚州僧寺的經驗,反而為我們觀察士大夫的生活歷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考架構。
(四)對城市的回憶
十八世紀的揚州留給後人最強烈的印象,當然是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板橋的一些詩作,也明確無誤地反映出他所身處的這個城市的光影溫熱。但更多時候,他是用一種落魄的、文人的眼光,冷冷地看待這些不屬於他的塵世的的繁華。像是一個疏離的旁觀者一樣,鄭板橋讓我們在商人營造的迷離幻境外,看到不第文人的困頓和文化歷史的傷感。不論是對困阨生活的寫實性描述,或對城市景物的歷史想像,鄭板橋的文人觀點,都讓我們在李斗全景式的生活圖像,和鹽商炫人耳目的消費文化之外,找到另外一種想像城市的方式。加在一起,這些不同的視角呈現出更繁盛和誘人的城市風貌。
(a)落魄江湖載酒行
鄭燮在一首題為<落拓>小詩中,直指本心地勾勒出文人生活的要素:「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為看花。」 雖然背景和人物都顯得模糊,但按諸板橋的詩集,卻無疑是他個人及所來往的文人群落的寫照。
雖然窮困得必需在寺廟裡乞食讀書,鄭燮卻不曾放棄揚州所提供的聲色之娛。雍正十年,他第一次走訪西湖,在無限的美景之中,不禁追憶起揚州輕狂的歲月:
十年夢破江都,奈夢裡繁華費掃除。更紅樓夜宴,千條絳蠟;彩船春泛,四座名姝。醉台高歌,狂來痛哭,我輩多情有是夫。
從意象上看起來,這些文句有著杜牧「十年一覺揚州夢」的感喟,但更可能是板橋十年落魄揚州的實際感受。對抑鬱不得志的畫家和聲氣相求的「我輩」友人來說,在妓院中高歌、狂飲、痛哭,大概是他們對城市記憶中最鮮明的一幕,即使「夢破江都」,他們還不能掃除對揚州繁華景象的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