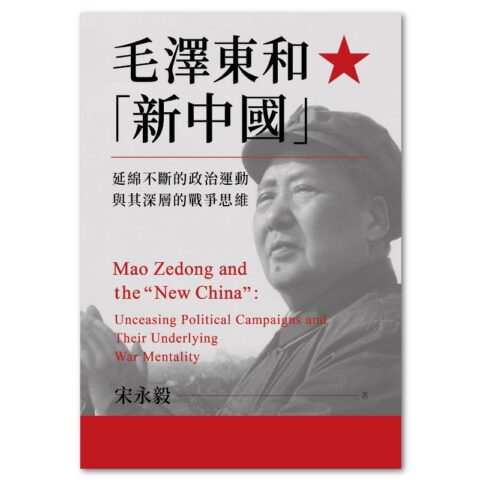這是一部生動的歷史著作,充滿了動感和細節。卜正民把明朝迷人和易變的世界鑲嵌在一個清晰的概念和編年框架上,使每位專家以外的人都可以領會。本書是一個有關明人及其所遇問題和所處世界的基本情況的寶庫:磚塊、橋樑、集市、寺院、郵件、饑饉、時尚、印刷、激情和兇兆。它是第一部描述沸騰而複雜的明代生活全景的著作。以上為耶魯大學歷史系史特林講座教授史景遷對本書的評價,可作為本書最好的介紹。
本書獲2000年美國李文森圖書獎─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以下之頒獎辭摘要,亦可作為本書之最佳詮釋。
《縱樂的困惑》是一塊史學藝術的寶石。運用一系列豐富而又鮮為人用的資料── 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對社會不滿的文人的軼事、觀察、抱怨──卜正民再現了明代中國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展示出商業在塑造公私生活文化上的力量。在進行他那仿佛生活在明朝的生動活潑的生命之旅的同時,卜正民展示了明代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正如他所說的:「大西洋的潮汐被中國的月亮牽引著。」巧妙地將木刻、地方誌、數據和文人對商業的抱怨結合在一起,他創造了一幅王朝成長過程中值得留念的社會圖畫。讀過此書後,沒有人再會無視明代中國對商業利潤的熱心和巨大的消費,因為本書生動地描繪了忙著從事各自生意以適應日益增長的金錢關係的瓦匠、商人、官員、妓女、織工、書商和土匪。本書將敘述、軼事和嚴謹分析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描繪早期近代中國社會經濟變化的富有情趣、生動活潑的典範。
作者:卜正民
1951年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市,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史學大家,師從孔飛力教授,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曾任教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伯達大學、多倫多大學、史丹佛大學等校,擔任過英國牛津大學邵氏漢學講座教授、美國亞洲學會前任會長。學術視野廣闊,主要從事亞洲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明代社會文化史、全球史。
主編並參與撰寫六卷本《哈佛中國史》,著有《縱樂的困惑》、《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維梅爾的帽子》、《社群.王朝》、《掙扎的帝國》等書。
目錄
英文版作者序
中文版作者序
明朝大事記
導言:明代的四季
出場人物
(第一章)冬(1368-1450年)
─ 牆磚
─ 交通的負擔
─ 集思成文
─ 經濟和貿易
─ 貧富間的距離
(第二章)春(1450-1550年)
─ 中央衰退
─ 國家與市場
─ 商業
─ 商業與文化
─ 正德年間的衰落
(第三章)夏(1550-1644年)
─ 錢神
─ 旅行與書信
─ 消費與生產
─ 貿易
─ 時尚
(第四章)秋(1642-1644年)
─ 明朝的覆滅
─ 最後的回眸
參考書目
譯後記
中文版作者序
當人們最後看到他們三個人的時候,他們正頂著非洲的烈日,望著大河的對岸。三人中,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非洲黑奴,另一個是呆在臨時搭起的帳蓬下的葡萄牙人。他們因所乘坐的船隻出事而滯留在今天我們稱作納塔爾的非洲東部,同行的其他人已經涉水過河,消失在這片乾燥和荒蕪的大地上。我們不知道中國人和非洲人的姓名,但葡萄牙人是個叫做魯博(Sebastian Lobo da Silveira)的商人。1647年2月當魯博離開澳門的時候,他也許是那裏最胖的人。他於1638年來到澳門,接任船隊總管一職,不巧他在曾經十分賺錢的遠航日本的商業活動接近尾聲的時候購買了這一航海專利,不能從中致富,他轉而交結耶穌會士,不擇手段地掠奪澳門的財富。當皇家行政官員對他有所阻撓時,魯博在1643年找人將他打死。魯博的行為在澳門街頭引起的騷動並不像當時席捲華北大地的反明叛亂那樣嚴重,在明朝被推翻的1644年,這位船隊總管被新任澳督卡瓦荷(Luis de Carvalho de Sousa)拘捕,但後者未能成功沒收他的財產或對他提出指控。1647年2月,卡瓦荷最終將魯博押上開往里斯本的船隻,讓他去那裏接受審判。
五個月後,魯博所乘坐的船隻在非洲東南海岸失事,生還者需要從內陸徒步走到莫桑比克。魯博因過度肥胖,加之長期奢華的生活方式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以致他每走幾步就要歇一歇。起先他用錢僱些士兵用吊床來抬他行走。但幾天之後,當這群人的食品用盡後,那些腳伕的精力和耐心也沒了。在一條大河邊,他們實在沒有辦法抬他過去,於是為他搭了個簡易帳蓬,留下兩個侍者後走了。
那位非洲人是葡萄牙奴隸販子在桑給巴爾海岸購買後被送到澳門的。他是澳門眾多沒姓沒名的黑奴之一。他們的容貌讓中國人吃驚,當地人叫他們「黑鬼」。雖然納塔爾在非洲,但船隻在那遇難對這位黑奴來講並不意味著可以返回家鄉,解除奴隸身份。關於那位中國人我們也是甚麼都不知道,只曉得他身材短小。他也許是魯博在澳門僱來的侍從,也許是廚師,更可能是一個自己主動或兒時被人綁架後賣給外國人的奴僕。雖然奴僕在晚明相當常見,但販賣中國人給外國人卻是違反明朝法律的,明朝的地方官員為這個問題擔心了幾十年。一位官員於1614年前後在澳門豎了一塊石碑,上面刻著五項葡萄牙人應該遵守的規定,其中第二條是他們不可以購買「唐人子女」,但無論是法律還是道德的屏障都不能阻止其他地方的中國人湧入澳門,「每歲不知其數」,正如當時另一位明朝官員抱怨的那樣。至少在窮苦勞工的眼裏,在澳門做奴僕比在福建打工要好。明朝的官員們也許不這樣想,但將中國人與外國人隔開的想法及做法並不能引起普通百姓的興趣,因為同外國人做生意所帶來的利潤實在太可觀了。
當同船的其他人丟下魯博、渡河而去的時候,很難想像那位中國奴僕留在他身邊是出於對主人的忠誠,因為魯博的名聲太壞了。繼續幫主人做飯?這更不可能,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任何剩餘食品了。作為奴僕,在主人給他離開的自由之前,他是不能走的。一但魯博死了(這肯定很快就發生了),他才有可能被解放。但那時他去哪裏?那個黑奴後來又怎樣了?我們都不知道。他們從歷史記載中消失了。唯一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那個中國人死在納塔爾,也許是獨自一人離開塵世的。
這位中國人只是生活在明代的數千萬人中的一個,絕大多數中國人生老病死在中國境內,但有些不是,而且這些人的數目在王朝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增長。十六、十七世紀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也是一樣。當時的世界正在日益變小,許多人(不光是歐洲人)在世界各地來來去去。財富和機會的引誘使得某些人長途跋涉,但更多的像那位非洲奴隸,是被強迫而不是機會拖進這種空間移動的。那位被帶到澳門的中國人應該也是這樣:為了賺取更大的利潤或僅僅為了生存。不管是哪種情形,席捲十七世紀多數地區的追求商業利益的潮汐,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將他從中國的南方海岸帶到非洲海岸。
1368年明代中國人的生活同1644年他們後人的生活有許多不同,前面講的這個故事顯示其中的一個。本書是有關明代中國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敘述。我寫此書時,留意到這些全球趨勢,雖然這些趨勢應被看成是影響明朝中國歷史的諸多複雜因素中的一部分。那位在納塔爾的中國人的故事告訴我們中國所處的世界在變化,也告訴我們中國內部的變化:商業活動正日益作為一種致富的手段而被人們實踐和稱頌,中國不再以明朝開國君主洪武皇帝所希望的方式與世隔絕。這個故事挫敗了洪武皇帝對中國的希望,我希望也挫敗讀者們的期望。幾個世紀以前發生在中國的事情看起來也許熟悉,但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應該小心。明代中國人居住於一個與當代中國人生活有著巨大不同的世界,那些相似的東西也許並不相同。
作為歐洲人後裔的加拿大人,我的社會文化背景似乎使我同魯博而不是他的中國侍從更加接近,但這並不意味著我認同或更加理解他。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的看法也許會妨礙我捕捉構成那位中國人生活經歷的某些細節,但它同時也替我免除了那種基於當代中國人生活經歷而自認理解他的幻覺。當然,讀者和我都想發現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連續,但對明代中國來講,我們都是陌生人。作為一個清楚知道自己是那個世界以外的人,我有著靜觀整個明代社會和文化風景,而又不必將明人的選擇帶到我自己生活中去的優勢。這是一種絕大多數中國歷史學家所沒有的奢侈品。他們書寫中國歷史,因為那是中國的,我寫中國歷史,是因為它提供了歐洲歷史以外的另一個選擇。中國的歷史學家尋求理解中國歷史,因為他們關心構成今天中國的種族或民族身份認同的基礎,而我則不必被束縛於將明代中國作為一個無法逃脫的過去。相反,它是一份如果我選擇就可以自由接受的遺產。對像我這樣不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來講,明朝是一種可以作為我的遺產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國的歷史學家也可以擁有這種沒有民族義務的自由。我覺得不妨嘗試一下,因為從這一立場我們可以像十七世紀的祖先一樣,審視那位被困在納塔爾的中國侍從、非洲奴隸和葡萄牙商人,一樣可以自由地認為那位富有、肥胖和腐敗的魯博是他們中間最奇怪的人的一個。
我很高興廣大的中國讀者現在能有機會讀到這本書。這要歸功於我的學生和朋友方駿。我很感激他願意承擔此書的譯介工作,也很欣賞他非凡的翻譯技巧。我的散文寫作風格並不簡單,但他和他的合作者王秀麗、羅天佑極其成功地將之譯成中文。我還要感謝孫競昊為本書所提供的出色編輯支持工作。
引言
明代的四季
明王朝是在冬季的安詳和靜謐中開始的。至少我們的晚明作者(在此姑隱其名)身處十七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回眺通向十四世紀的漫長的歷史之路的時候,是這麽想的。王朝的前半期對他來說是一幅真正的理性秩序和安定生活的圖畫。「家給人足」,他堅信,「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催科不擾,盜賊不生。婚媾依時,閭閻安堵。」男人和女人們遵循著由來已久的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男耕女織(見圖1和2),「詐偽未萌,訐爭未起。」一切都按照它們應該的樣子存在著。
我們的作者宣稱,在他的時代一個世紀以前,王朝的靜謐冬季開始讓位於春季的喧鬧。農業的莊嚴安定逐漸爲喧囂狡詐的商業世界所排擠:「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資交捷,起落不常。」隨之而來的是能力和社會階級的兩極分化。「高下失均,錙銖共競。」當發財的美夢點燃起貪婪的欲望的時候,維繫社會的道德秩序開始讓位。「互相凌奪,各自張皇。」在這個罪惡的環境中,「詐偽萌矣,訐爭起矣,芬華染矣,靡汰臻矣。」
明王朝春季的喧囂登場與在後來所發生的事情相比,還算溫和得多。在十六世紀後半葉開始的王朝夏季的瘋狂衝動中,「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資爰有屬,産自無恒。」社會的農業基礎被廢棄了。取而代之的是「貿易紛紜,誅求刻覈。奸豪變亂,巨猾侵牟。」隨著道德墮落的悄悄滲透,「詐偽有鬼域矣,訐爭有戈矛矣,芬華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
我們的作者將他對明王朝季節的描述終止於十六世紀七十年代他個人成年時代的世界裏。到了秋季,明代社會已經被搞得面目全非了。「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既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他聲稱,「貪婪罔極,骨肉相殘。受享於身,不堪暴殄。因人作報,靡有落毛。」他對於拜金狂性質的墮落的預言似乎具有世紀末的味道。「於是鬼蜮則匿影矣」,他警告說:「矛則連兵矣,波流則襄陵矣,丘壑則陸海矣。」防止這種嚴峻局面出現的唯一辦法就是「閉關商不行,安靜以養微陽。」但我們的作者自己似乎也感覺到了這種辦法的不可行。他所能做的就只有任絕望淹沒自我,發出那一聲最平凡的苦惱的哀歎:「嗟夫!」[1] 完了,一切都完了。
上述關於有明一代的敍述來自1609年的《歙縣誌》。[2] 歙縣是南京南面的一個風景如畫的內陸山區縣。1609年的《歙縣誌》,是由地方刊印的記述該縣政治生活和歷史的著作,是該縣的第一部地方誌。歙縣在方誌的編纂方面可謂姍姍來遲。那時,明朝的大部分縣都已有了自己的縣誌,或許只剩下爲數不多的幾個沒有。歙縣的貧困落後與它作爲那個時代最富有的商人的家鄉之顯赫地位比起來,顯得格外刺眼。但在當時,商人是被排除在多數士紳的社交圈子之外的,而正是這些士紳撰寫了歙縣的方誌。
執筆者是由朝廷任命的該縣知縣張濤。1607年上任後不久,張濤就與當地的鄉紳們商議要編纂一部地方誌。編纂機構成立了,次年委任了編纂人員。1609年方誌修成,刻板付印。儘管依照慣例任命知縣爲纂修,即使他並不參加任何具體工作,但歙縣的縣誌卻真的是張濤的著作,是他個人觀點的紀錄。不管有何種疑問,張濤給遍佈全書的編者按語加上了一個不那麼謙虛的署名:「張子曰」。其中的一段編者按語便是我們剛剛提及的關於明代的四季的論述,那是「風俗」[3] 一節後面的總結性評論。這一部分是編纂者對當地風土民情,考察其「剛柔緩急,……好惡取捨,動靜亡常」的地方。[4]。因爲本地人都想給自己的家鄉臉上貼金,所以這一部分的記述往往多有拔高之處,甚至與事實相反,正如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的那樣。
張濤在明代歷史上是個小人物。在篇幅龐大的《明史》中,他的名字僅僅出現過一次。[5] 但將歙縣和沿長江上溯500公里處他的家鄉黃陂縣的地方誌中關於他的材料拼湊在一起,我們還是可以對他這個人略有瞭解的。黃陂位於武昌的內陸腹地。武昌位於漢水的長江入口處,是中國內地的主要貿易中心,但黃陂卻遲遲未被捲入商業的大潮中去。在明代中期黃陂以寧靜的窮鄉僻壤而聞名,在那裏,「民皆勤農桑,寡游販駸。」婦女們幾乎足不出戶,從早到晚呆在屋裏紡織。然而,在張濤的青年時代,該縣正在受到一種地方士紳們以懷疑的眼光看待的影響。1591年的《黃陂縣誌》指出,近來「風氣漸薄,家無敝帚者,亦連車騎餙,冠裳為富貴客。」儘管該地十分貧困,「爾今且一切化質為文。」[6]
我們不知道張濤是什麽時候來到這個緩慢變化的世界的。關於他的身世,我們僅知他的父親是個有孝悌聲望的人,習醫爲鄉人治病,免費爲窮人置辦棺材。張濤履歷中的第一個確切日期是1586年,那一年他在北京考取進士。除非他出奇地聰明或格外地幸運,否則他考中進士時大概不會比三十歲小很多。這樣,他的出生年代大約是1560年或者稍早一點。
他的第一個職位是四川省的一個三年一任的縣官。他的出色表現使他得到升遷,被提拔到北京擔任工科給事中。這個職位賦予他調查官員腐敗的權力。張濤爲人耿直敢言。根據《明史》中他的僅有的一次亮相,他加入了彈劾舉止溫和的首輔趙志皋(1524-1601)的行列。趙志皋就任首輔時已年逾七旬,勉為其難地想竭力保住他的傑出前任們(如財政改革家張居正,1525-82)在位時聚集起來的權力。像張濤這樣的低級官員,想要阻止趙志皋行使他的前任早就明目張膽地使用過的威權,只有死路一條。正史上並沒有記載他遭受打擊的日期和細節,張濤僅僅是一個被順便提到的名字而已。與主宰京城政治的權貴發生衝突,張濤別無選擇,只好退居黃陂。在以後的十五年中,他在家中從事寫作,遠離政治。
當朝廷爲十六世紀八十年代敢於直言的青年激進分子們平反的時候,張濤重入明朝的政治生活。1607年他復出後的第一個職位就是歙縣知縣(見圖3)。他到任時,正好趕上當地鬧饑荒。春季的瓢潑大雨在年初就將田裏的莊稼沖刷得個一乾二淨。張濤將糧價的上漲看作是荒災的晴雨錶,當糧價漲到每斗130文的時候,他將縣倉中的糧食投入市場來調節糧價,並下令縣裏的富有人家從外縣糴糧,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在他的努力下,全縣沒有一人餓死。眼前的危機度過之後,他轉而開始修建堤壩,以便防止未來的洪澇災害。事實證明這種投資是明智的,在後來的年份中當暴雨再度襲擊歙縣時,並沒有造成大的損失。[7]
張濤還致力於象徵性資源的投資。那一年,他重修了縣裏爲紀念宋代偉大的哲學家和歙縣的子孫朱熹而修建的一所書院。他在一座山上建起了一個塔,希望這個風水勝地能保佑本縣的子弟在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他重修了兩座祠堂,一座是爲紀念本縣的前任賢官的,另一座則是爲當地一位孝廉修建的。祠堂、學校和寶塔,象徵著修身、尊崇和德行,張濤在他新風化俗的方案中身體力行想要培育的就是這些。張濤也曾意識到應該將現實的努力建構成他的道德理想藍圖,他還改革維繫縣政府運作的徭役,特別是驛傳服務。1771年的歙縣誌爲他寫的充滿讚語的傳記是以這樣的評論收尾的:「居二年,風移俗易。」[8] ─ 這正是張濤孜孜以求的。如果他知道後人對自己有這樣的評價,一定會心滿意足了。
正當張濤的努力開始在歙縣發揮作用的時候,他獲提升重返北京。在京城一連串的官職任命中,他宦途平步青雲,直到被任命爲遼東巡撫、達到事業頂峰的時候。當時的遼東是明朝東北地區的橋頭堡,[9] 張濤是在十七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擔任這一職務的,這在滿人1621年吞併該地區之前。[10] 之後,他告老還鄉,在黃陂縣的家中度過了他一生中的最後歲月。在那裏,他因豐富的閱歷和學識而享有很高的聲望,至少一直活到二十年代後期。
張濤批評自己的時代,但他也屬於那個時代。當他彈劾首輔趙志皋時,他並不是孤獨的十字軍,而是同時代的試圖限制首輔權力的衆多行動者之一。同樣,當他在歙縣誌中抨擊商業的時候,他也道出了困擾著他同代人中具有改革意識但卻比較保守的那部分人的共同憂慮。張濤對商業的猛烈抨擊與他同時代人的類似批評所不同的,是它那極端的口脗 ─ 正是這種極端的口脗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是在這樣的思考中完成這部明朝歷史的寫作的 ─ 試圖去理解他的那個王朝的歷史,試圖理解這種歷史對他來說有甚麽意義。通過將自己置身於與四個世紀前的歷史人物的對話中,我嘗試著從明人的角度去寫這部歷史,讓張濤當我歷史之旅的嚮導。
張濤心目中的明朝歷史是一部無情的衰落史。明朝從奠基者太祖(1368-98年在位,亦稱洪武皇帝)所強力推行的穩定的道德秩序最終滑向一個完全商業化的、在張濤眼中還是道德墮落的社會。張濤似乎敏感地觸覺到商業 ─ 被擬人化爲錢神的罪惡面孔 — 才是將曾經安定有序的中國改變成一個無序騷動的世界的罪魁禍首,在這個世界中商業使人們不斷地奔波、欲求不斷地升級,使社會禁忌徹底傾覆。通過放任消費去推動生産,商業瓦解了張濤認爲只有在純粹的農業社會關係下才能實現的道德團結,引起了競爭,正是這種競爭破壞了社會的共同準則。
張濤對明代歷史的這種解釋顯然是接受了洪武皇帝通過徹底和通常是嚴酷的手段干涉人們的生活、復活古老的道家理想的說教。本書開頭引用的《道德經》中的一章表達了這種理想。洪武皇帝相信由少數精英分子統治的封閉鄉村社會體系會給混亂的王國帶來秩序,給他的王朝帶來永久的穩定和安寧。在極度的貧窮中度過了他的童年時代 — 在一次饑荒中失去了雙親後在一所寺院中生活,直到那裏的和尚太窮而無法繼續收養他,轉而沿街行乞 — 洪武皇帝將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一輩子在自己的村莊中生老病死的圖畫看作是他從來也不曾見到過的天堂。作爲一個皇帝,他要不顧一切代價,將那個天堂帶到人間,儘管這種理想,像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僅僅是一種富有感傷懷舊色彩的人間神話,它的背後是靈活得多、也商業化得多的現實社會,當然無論是洪武皇帝還是張濤都不情願接受這種現實。這位皇帝不無愜意地運用高壓和通訊手段來強制推行他的理想秩序,並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的後代們並不像他那樣勵精圖治,最終也不再致力於實現他的上述藍圖。到了張濤的時代,洪武的理想藍圖 — 三分之一的世外桃源,三分之二的嚴刑峻法 ─ 已經大大失色,至多不過是書本中的歷史記憶,在現實生活中已變得一文不值。對於張濤來說,重構這樣的理想只是將他自己的和這位皇帝的感傷懷舊揉和到一起而已。
從張濤對中國文化所面臨危機的理解方面來說,這種理想的空想性並不重要;他或許未能抓住歷史的主流,這也不重要。我們今天的人看到了這種主流,並且在我們自己的分析中予以重視:有明一代,中國的人口增長了一倍多;商人們正在將生産者和消費者引向地區性和全國性的商業網絡,沒有這種網絡,生產者和消費者誰都無法生存;商品出口將日本和西班牙的白銀吸引到中國市場,使明朝經濟得以良性運轉;新的財富影響著資訊傳播和知識儲存的方式。張濤看到的僅僅是一種富人對窮人、貿易者對耕種者、利潤對美德的令人痛心的掠奪。這種看法使他無助,也感到無助。所有他能做的只是哀惋,在哀怨中給我們指出了漫足於他那個世界主要景觀的途徑。
並不是那個時代的所有人都讚同張濤關於明代正在經歷著的變化的嚴勵評論。張濤在一篇歙縣的〈昭告城隍表〉中向我們透露了他的觀點在當地並不很受歡迎,在這篇文章中他宣稱自己用「直筆」來修誌,冰心鐵臉。[11] 他在這裏暗示我們,他曾經面對壓力,要求他改動自己的稿子,但被他拒絕了。人們不贊同他寫的哪些內容呢?他的〈昭告城隍表〉言辭過於隱諱,不易明瞭,儘管很可能是他對該縣商業環境的譴責。當地人對1609年所修歙縣誌中張濤的評論不滿意,這就有了取而代之的1624年新誌,兩者相隔只有十五年(通常都是六十年重修一次)。主修1771年歙縣誌的知縣將1624年的新誌說成是「調停之作」。他承認張濤1609年的方誌體裁近史,但「公言紛囂聚訌。」 至於張濤關於金令(銀兩的主人)的言論,這位知縣以爲「語近猥褻,且箴戒缺焉。」[12] 歙縣的商賈仍然在承受張濤的過激言論給他們帶來的傷害。
張濤對白銀的抨擊是有先見之明的。白銀對張濤來說或許只是那個時代拜金狂熱的一個象徵。然而,那時白銀真的是在從日本和南美的西班牙銀礦流向中國,用來支付中國的出口物貨。白銀的流入帶來了輕微的通脹,刺激了商品的流通,某種程度上促成了使張濤悲傷的社會後果。但是白銀對明代商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並不比它對道德墮落的推動作用明顯多少。如果他僅僅知道白銀的話,它也只是維持和刺激在張濤出生以前就已很深地商業化了的經濟的衆多因素之一。金令並不是不請自來地進入中華大地的。他是被一個在西班牙人開採波多西山的銀礦和法國人派尼克雷尋找北美西北通道之前早已培育起可觀的商業能力的經濟體系拉進和吸納到自身中去的。
明代中國變成了一個商業世界,不僅蔑視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所竭力恢復的農業秩序,而且還借助了這種秩序的恢復。洪武皇帝限制流動的經濟目的是爲了增加農業生産量。在這方面,他獲得了成功。生産量的提高造就了進入貿易流通領域的剩餘農產品,剩餘農產品的經常性流通促成了從剩餘品生産向商品生産的過渡。與此同時,洪武以軍事供應和人員調動(張濤的官事遷調肯定走了至少20,000公里的路)爲目的的交通手段的投資使得各交通子系統得以改進,這使商品流通變得更爲容易。商人們的貨物與政府的稅收物資在同一條運河上運輸,商業經紀人與國家的驛遞人員走的是同樣的道路,甚至他們手中拿著同樣的路程指南。明朝政府從背後給人口和貨物的流動 ─ 同樣也包括思想和社會地位的變動 ─ 一個推動力,而市場則從前方加速了這種運動。商業化並非簡單地是從洪武設想的國家壟斷的交通系統和政府倡導的自給自足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反而恰恰是後者發展的結果。
商業有它獨特的社會和文化影響,因爲流動和財富改變甚至全然推翻了多數人的社會期望,尤其是像張濤這樣的士大夫們的社會期望。這些影響引起了我的興趣,發掘這些影響的意義 ─ 沿著從交通到商業、從商業到文化的軌迹[13] ─ 就是本書的目的。因此你將讀到的與其說是一部明代的經濟史,還不如說是一部文化史。我們關於明代經濟的知識至今還太粗糙,還不足以撰寫一部明代經濟史。我們現在尚未對離我們更近的歐洲中世紀經濟史上同類的經濟變動和轉折提出令人滿意的詮釋。這部書中粗線條的描述 — 沿著從十四世紀後期到十七世紀中葉看起來向前發展和不間斷的商業擴張的軌迹 — 只是勾勒出裂變、逆流、地區性變動等主要經濟現象,關於這些現象本身,我們尚未很好地給予解釋。然而,無情的商業化不斷加劇的大背景和它帶給明人的與日俱增的不安和恐懼是那樣的明顯,這又使得我們能夠將這些題目繼續寫下去。
方誌、文章、墓誌銘和當時的書信中留傳下來的明人的思想,使得這本書關於有明一代隨著經濟對新的消費和縱樂的欲望的刺激,中國人的經歷是怎樣發生變化的敍述成爲可能。那些明代觀察家所感受的興奮和困惑或許對我們今天來說只是遙遠的趣聞軼事,僅僅是中國社會自然發展過程的令人好奇的文化註腳。但是那勢必使我們忽視歷史的警示。讀者的任務應是記住明代的中國是另一個地點、另一個時間的一個世界和時代;在這裏,當今我們的一切假設,不管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都不大符合實際。他們對物質文明的疑問和喜悅也許都不是我們的,我們的疑問和喜悅也可能與他們的毫不相關。我們應當聆聽,帶著他們所有的恐懼和期盼,腦子裏時刻記著當像張濤一樣的人們在哀怨地訴說的時候,他們怎麽也不會想到我們今天的人會在這裏傾聽他們的絕望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