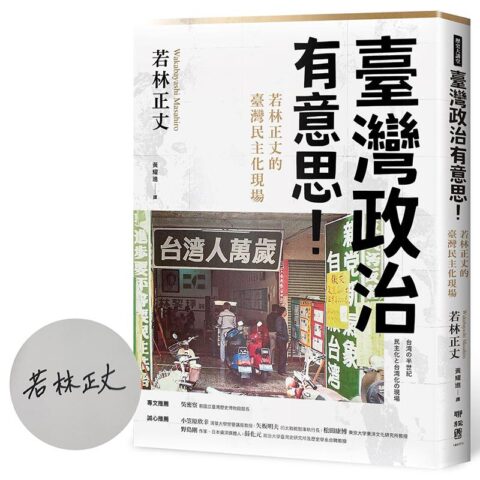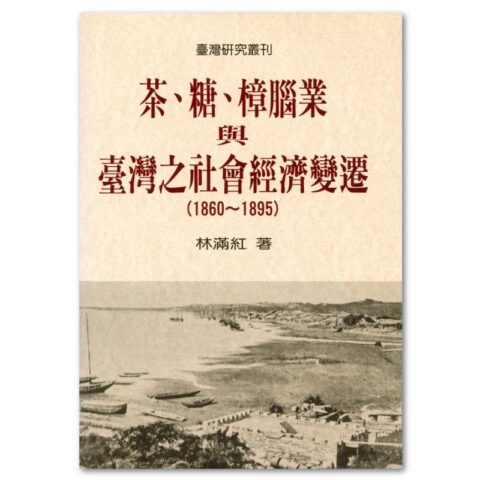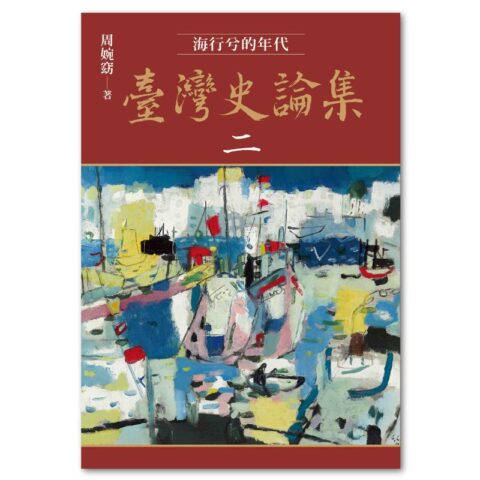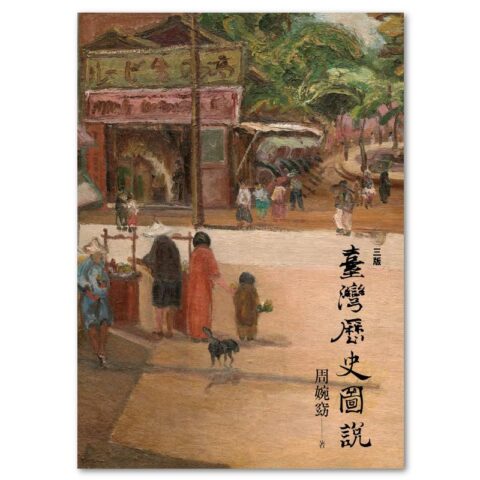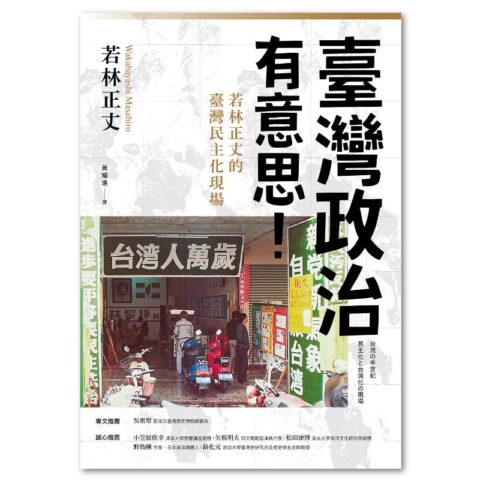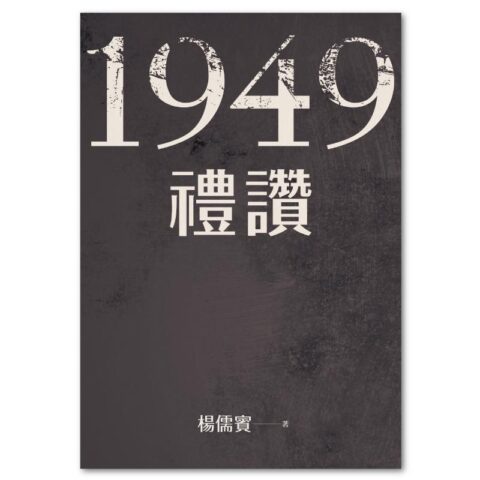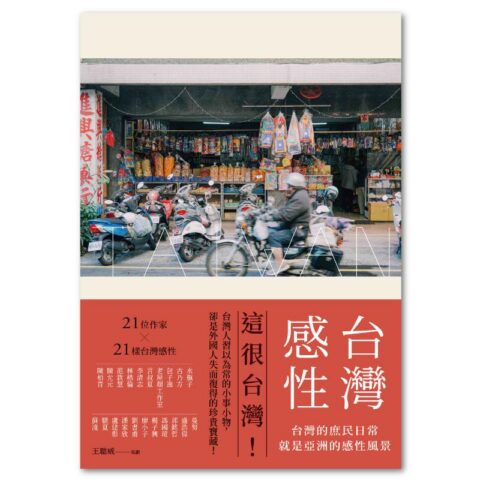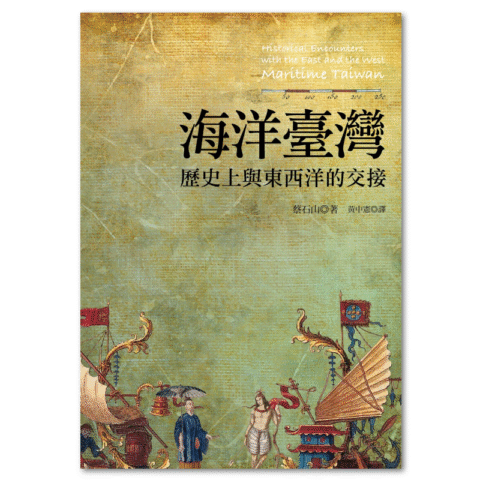單聲道:城市的聲音與記憶
出版日期:2013-04-30
作者:李志銘
印刷:半彩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44
開數:18開(寬17×寬23cm)
EAN:9789570841565
系列:當代名家
已售完
連續兩屆金鼎獎得主 李志銘
重訪台北的老聲音,台灣的老聲音
最新力作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畢恆達 專文導讀
台中市古典音樂台主持人 吳家恆
廣播人兼作家 馬世芳 誠摯推薦
「聲音確實有種看不見的力量,能使人安心,也能讓人焦慮。」
有誰記得螢橋河畔「露天歌場」水岸歌聲?一曲〈月夜愁〉是否迄今卻仍歌詠著台北三線路夜晚之迷人所在?至於那些城市深晚未歸人歌唱「今天不回家」的迷離身影,亦深情見證北投「那卡西」夜晚,流淌著比白天更多的浪漫。
金鼎獎得主李志銘,不僅爬梳台灣文化風景,也書寫城市聲景,用不同角度喚醒台灣走過的豐富歲月。
這部聚焦台北記憶與聲景之作,談城市印象也談聲音與地方的關連,城裡城外的聲音記憶,耳熟能詳的樂曲,帶出台灣早期的地方縮影,另一方面也將城市自農村到工業的快速發展,運輸工具日益便捷,南來北往的印記,藉由一些古調樂曲呈現。李志銘也探詢城市生態的轉變,試圖喚醒城市擁有過的大自然印記,在書中回顧台灣音樂史上一個個似曾相識的名字:舉凡日治時代鄧雨賢、江文也,乃至戰後初期文夏、洪一峰、紀露霞與鳳飛飛,並試圖以聲音景觀(Soundscape)解讀,有如戰後台灣城市文化史,別有一番風味。
眾聲喧嘩的二十一世紀,環境迫使人們聽聞的聲響是如此過度地嘈雜不堪,那些隱蔽於寂靜當中等待著人們去覺察的被隱藏的聲音,充滿許多耐人尋味的故事。
※ 名家推薦
1976年出生的李志銘,以對歷史的爬梳、社會學的趣味,以及文學的感性,兼以自身的記憶,寫出了許多早已消散、被遺忘的台灣音景(soundscape)。他的文字很安靜,讓我想起徐四金筆下沒有氣味的香水師葛奴乙,充滿對聲音和過往的愛戀。他能寫出許多聲音,但自己的聲音卻不喧鬧。正由於敘述並不張揚,讀者自身對聲音的記憶,也就一點一滴慢慢浮現出來,成為了這本書閱讀經驗的一部份。
──台中市古典音樂台主持人 吳家恆
作者:李志銘
1976年生於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具有天秤座理性的冷淡與分析傾向,對人對事缺乏諂媚的熱情,工作餘暇偏嗜在舊書攤中窺探歷史與人性,同時喜好蒐集黑膠唱片、聆聽現代音樂以及台語老歌。
著作獲獎眾多,備受肯定,《半世紀舊書回味》獲2005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裝幀時代》獲2011年金鼎獎,《裝幀台灣:台灣現代書籍設計的誕生》獲2012年金鼎獎、《單聲道:城市的聲音與記憶》獲2014年金鼎獎,以及談黑膠的《尋聲記:我的黑膠時代》。目前專事寫作。
推薦語 吳家恆
推薦序 聆聽城市的身世 畢恆達
第一篇 序曲
寂靜之城
第二篇 城市印象──聲音的地方
再會三重埔
晝夜邊境
一曲〈月夜愁〉歌詠台北三線路迷醉之夜
城內城外,兩個不同世界
城市深晚未歸人的迷離身影:從〈台北上午零時〉到〈今天不回家〉
北投「那卡西」夜晚流淌著比白天更多的浪漫
聲音如何以城市(地方)命名
驚雷與威權之聲
聽見遠方有戰爭:從《一八一二序曲》到「八二三炮戰」
空襲警報:關乎噪音轟炸的聽覺記憶
城市鐘聲何處尋
第三篇 城市晃蕩──聲音的速度流動
穿越街道的節奏與身體
蒸汽火車搖滾音樂文化史
鐵道歌唱:從蘭陽古調〈丟丟銅仔〉到現代合唱曲〈飛快車小姐〉
流動的城市:火車南北往返串連聲音鄉愁
時速四十公里:從鄉村滑向工業時代的聲軌
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的擴張與壅塞:四奇士合唱團〈討厭的公共汽車〉
失速的城市、失速的哀傷:工商時代汽車流動噪音蔓延
侯德健〈高速公路〉見證八○年代台灣汽車文化濫觴
蘇芮〈跟著感覺走〉體現城市速度與欲望
台灣「歐兜拜」(Auto-bike)城市機車狂想曲
叮叮車鈴聲懷念青春的飛
第四篇 城市生態──聲音的季節與風景
被遺忘的季節之聲
聽見城市裡的鄉村風景
遠去的市井叫賣
冬夏晨昏的叫賣音信
從行商招徠到江湖走唱:細聽郭大誠傳述台灣古早行業歌曲
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農諺測天,諦聽鳥音
鳥鳴召喚一座春天棲息的城市
夜裡秋蟲鳴聲皆美
聲音正凝結止水之靜
日本「水琴窟」靈妙清音
河岸旁,錦歌繁弦如夢:台北螢橋河畔「露天歌場」
當雨季來臨,屋瓦敲打樂響起
觀聽海潮,洄瀾拍岸
海洋是人類音樂的總和
第五篇 弦外之章
你的黃河長江其實是淡水河濁水溪──寫給台灣作曲家江文也的懺情書
後記‧致謝
聆聽城市的身世/畢恆達(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志銘還在台大城鄉所就讀的時候,我已知他除了是喜歡逛二手書店的書迷之外,也是會蒐藏黑膠唱片的古典音樂迷。等他陸續出版了《半世紀舊書回味》、《裝幀時代》、《裝幀台灣》這三本得獎好書後,我知道寫本古典音樂書只是遲早的事,但沒想到他在《單聲道:城市的聲音與記憶》,不只談古典音樂也論流行歌曲,不僅涉及音樂更關心城市中的音景。台灣不乏有作者寫古典、寫爵士、寫流行、寫搖滾,但是連結音樂與聲音/音景的作者卻極為罕見。這本書也就清楚凸顯志銘的個人風格,在看似龐雜的主題中,貫穿作者的核心關懷。
心理學對於空間認知的研究早期有賴於白老鼠走迷津,有的老鼠不按規矩走,總想翻牆而出,心理學家直接將這些老鼠視為不聽話將之放回迷津,而沒有深究翻牆的原因,錯失了推進認知理論的契機。1948年Tolman的關鍵性實驗,證實了老鼠並非機械式地對環境刺激給予直接反應,而是在走過迷津之後,對於迷津通路有了一個整體的概念,亦即證實了認知圖(或認知再現)的存在。空間認知的研究從此從行為論轉向認知論。1960年都市規劃師Kevin Lynch以波士頓、澤西市、洛杉磯的研究為基礎出版了空間認知的經典著作:《都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他將城市使用者的觀點納入都市規劃之中,此後,幾乎所有的規劃報告書都會出現地標、通道、節點、邊緣、地區的符號與說明。後繼者,持續深化他的研究,或加入方向感、意義、認同等面向,或研究認知圖發展演變的歷程。也有研究者走出Lynch的視覺偏向,將之挪用到環境聲音的分析,用音標、音域、聲道來理解環境。
不過真正的音景書寫的聖經,無庸置疑是1977年由加拿大作曲家R. Murray Schafer所撰寫出版的The Tuning of the World(1993年書名改成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在意識到聲音逐漸污染崩毀之際,他超越消除噪音的概念,轉而採取更為正向而寬廣的觀點教導我們如何讓聲音環境更為健康而悅人。在這本書中,Schafer討論工業革命前的音景(主要是森林、水、動物與機械尚未演進前的城鎮聲音)、工業革命後的音景(工廠機器、汽車、飛機的聲音成為音景的主宰,產生大量的低頻)、聲音的文化象徵,以及提出正向積極的音景設計。此書即使出版已經超過三十年,仍然是思考音景創意的源頭。對於熟悉視覺而對聲音相較遲鈍的讀者,閱讀的過程中絕對處處是驚喜。他告訴我們世界上音量最大的聲音,如何從打雷、地震、雪崩,轉變成機械、噴射機、太空梭發射的聲音。如何從測量一個城市中救護車的音量來探索該城市背景音的演變。教堂建築的高度讓它成為城鎮的地標,然而教區可以說就是一個由教堂的鐘聲(可及之地)所界定的空間。作者還指出最強的聲音其實是靜默,這時人可以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最動人心弦的不是管弦齊鳴,而是讓全城的活動停止,一片寂靜。此時寂靜將像教堂鐘聲一樣震撼人心,感動人情緒的深度無與倫比。
同時由Schafer所創立的世界音景計畫(the World Soundscape Project, WSP)除了從科學、美學、哲學、建築、社會學等不同面向研究音景生態之外,更為加拿大與歐洲等地留下無數的聲音記錄,目的在於促進人群與聲響環境的和諧。日本在翻譯Schafer的音景著作後,於1993年成立日本音景學會,成為音景研究的重鎮。除了調查東京鐘聲地圖、徵選日本百大音景、調查都市音景源之外,更推動將政府的政策從消極的噪音防治導向積極的音環境示範。台灣則有王俊秀引進此概念,針對台灣進行音景的調查與紀錄,例如請新竹市民票選「竹塹十大音景」(第一名是新竹風)。
這是一條理解志銘的《單聲道:城市的聲音與記憶》的重要線索。志銘以他對古典與流行音樂的熱愛,加上建築與城市規劃的學術訓練,相互衝撞啟發而有了這本頗具創意的書出現。《單聲道》並不是傳統討論音樂的書籍,他提及的古典音樂是加入聲音的音樂,如使用真實加農砲聲的〈1812序曲〉,融入街頭喧鬧與喇叭聲的〈一個美國人在巴黎〉,或是模仿動物聲音的歌曲與音樂。流行歌曲則成為理解台灣城鄉變遷的重要線索。在聲音與音樂這個交錯的主題下,他也討論了自然的聲音(如雷電聲、蟲鳴鳥唱)、人為的聲音(如空襲警報、鹽水蜂炮聲、城市鐘聲、市井叫賣聲),特別是各種交通工具(包括火車、電車、公車、自行車)的聲音。同時藉由這些聲音以及相關流行/廣告歌曲論及運輸工具的演進過程,以及其與城市發展的關係。讀者無論是喜歡音樂、城市、自然或技術,都可以從這本書得到許多知識與靈感。
閱讀《單聲道》也讓我有機會重新從感官的角度來省思我的學術研究:物的意義。回想當問及最懷念的台灣事物,留學生通常不約而同回答是:台灣小吃。留學生為了避免水土不服,則會將從台灣帶去的一杯米與水摻加在異鄉的第一頓飯中。而留學生最常提及的心愛之物,如照片、信件、地圖屬於視覺之物。但是如同幼兒難以割捨的取代照顧者的毛毯,留學生用來適應與家人分離的過渡物(如布娃娃、T恤)大抵倚賴觸覺(柔軟、溫暖)與嗅覺(媽媽身上的味道)。聲音也是物的意義的重要元素。一位學生提及曾在某個下雨的夜晚,聆聽洛史都華的歌曲,歌聲和著雨聲讓她沈醉。後來錄音帶卡帶損壞了,她急忙騎著腳踏車到唱片行買一卷相同的錄音帶,放進錄音機裡,卻再也聽不到雨聲了。
視覺的獨斷,擠壓了人類其他感官的發展。正如英文的I see既是我看到,也是我懂了;而中文的明瞭、視野、遠見也都與視覺有關。因此《香水》主角葛奴乙能夠用嗅覺「看」到視線之外人的身影,《盲人心靈的秘密花園》主人翁說:「如果我的房間會下雨,我就會知道哪裡是沙發、哪裡鋪了地毯」,就特別讓人印象深刻。事實上,耳朵是我們每天最早打開最後收工的感官。早上我們通常為鬧鐘的聲音所驚醒,夜晚則在心靈音樂的聲音中逐漸沈睡。更不用說,擾人清夢的通常不是光線,而是縈繞耳邊蚊子的嗡嗡聲、巷口呼嘯而過的機車聲,或是樓上住家的走路聲與馬桶沖水聲。
從都市的尺度來看,視覺霸權也顯而易見。絕大多數的交通指示幾乎倚賴視覺,如紅綠燈、平面圖、斑馬線、市招、禁止標誌。而現代人幾乎智慧型手機不離手,拍食物、拍街景、自拍,但是極少會想到錄下街頭的聲音。志銘書中這句話:「當視覺景觀幾乎壟斷現代城市生活印象時,人們是否亦需另行尋找一種由聲音串起、穿越人造城鎮與自然地貌交界的空間記憶?」就很值得我們細細思索。下回在用手機拍照之餘,也不要忘了駐足聆聽,按個鍵為許多稍縱即逝的街頭聲音留下歷史的紀錄。
再會三重埔 李志銘
每座城市或地方都各自承受著一種歷史宿命,而這種宿命幾乎完全決定了它的空間特色。
三重埔,我的出生地,一部幾乎被時間遺忘的戰後台灣歌謠文化工業城市史。
起自五○年代以降,那是台灣剛藉美援站穩腳步並摸索著靠加工業帶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年頭。當時島內物資匱乏、生活普遍困頓,許多待在家鄉沒有出路的農家子弟與鄉村女孩紛紛來到大城市裡找工作,甚至不乏繼承祖產者在南部賣了田地帶著妻小前來討生活。這些從中南部先來後到的城鄉移民,每個人都懷有無窮的夢想與決心,彷彿天生帶有趨光性的蟲兒無法抵擋微光希望誘惑般地一致湧向台北。
依稀記得年幼時好幾回從阿嬤的收音機裡聽過綽號「阿西」的黃西田操著一口憨厚嗓音唱了這麼一首老台語歌調〈田莊兄哥〉:「趁著機會,火車載阮要去喲……來去都市若賺有錢,我會返來」,曲中第一、二、三段開頭分別以「不願擱鼻田莊土味、不願擱騎犁田水牛、不願擱聽水蛙咯咯」吐露出當時年輕人普遍對於傳統農村生活的嫌惡與厭倦,為了負擔家計因素導致不得不離鄉背井前往大城市移居。
將內心悲愁藏在詼諧逗趣的外表下,〈田莊兄哥〉訴說著莊稼人從台南一路撘火車搖晃到台北的情境轉變,尤其是每句唱詞末段模仿火車行進規律節奏的那一聲聲「咻咻蹦蹦……咻……蹦蹦」迴盪起幾波餘韻與親切感,真叫我一輩子也難以忘懷。
恍恍惚惚耳邊似乎總是迴繞著曲中結尾這段口白:「台北到了,台北到了,請各位旅客,嘸通忘記別人的物件。」宣告了此番離鄉旅程終點站即將到來,同時也忐忑不安地迎向另一場無止盡城市流浪的異鄉起點。
待下車安置了行囊住處之後,他(她)們第一步走進繁榮城市的最初門戶,就是台北橋。沉重混濁的淡水河面上,台北大橋串聯起左岸「三重埔」與右岸「大稻埕」,區隔了北部城市與南部鄉鎮的空間界線。
跨過淡水河走出台北市「大橋頭」地界,步入對岸囊括生活成本低廉、工廠林立、就業機會多而成為外地人主要聚居場域的「三重埔」地區,混雜了來自雲林、彰化、嘉義等全台各地北上謀生者不同方言口音。他們齊搭上急速城市化的時代巨輪,各種聲音語境迴盪在鄰里巷弄住家兼工廠的狹小空間內。工廠裡無數作工幫傭而收入微薄的年輕學徒與生產線女工埋身於暗無天日的污濁環境下,幾乎是終年無休地茹苦咬牙儉樸度日。甚至有些初到異地的年輕人因無法正式謀職,便只能聚居在台北橋下,成為按日出賣勞力的臨時散工。
「阮是十八薄命農村女,離開家鄉出外來求利,想著歹命有時目屎滴,也是不~得已~咦~,離開阿母的身邊,阿母啊你現時~咦~像阮心內悲」,當時年方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紀露霞(1936- )初試啼聲來到台北成都路「民聲電台」正要展開駐唱生涯,而「中廣」製播「好農村」節目也找她去錄製三七五減租政令宣導主題歌。名氣漸開的她,初次灌錄了這首由周添旺將美空雲雀〈夕やけ峠〉原曲填上台語歌詞的〈黃昏嶺〉,黑膠封面散發濃厚的時代感。
〈黃昏嶺〉曲詞內容描述一位農村少女為忙於養家活口而前往台北找尋工作機會,每至黃昏夕陽遙望故鄉母親身影,便想起孤身流落他方感嘆命運弄人的惆悵心境。這首歌調,透過音色飽滿甜美淳厚的紀露霞來詮釋,特別是那一連串搭配自由節奏分句韻腳娓娓唱出~咦~啊~的綿長拉音,創造出所謂「紀式演歌風格」獨一無二的爵士台灣味,與同時期另一首時空背景相近的陳芬蘭〈孤女的願望〉在當年不知撫慰了多少滿懷希望遠赴大城市工業社會打拼、同為異鄉遊子的孤寂心靈。
三重埔歷來是一個臨岸接壤台北的轉口港,各鄉市各階級人等雜居,秉持現代都會的空間性格,所謂「三重人」與「外地人」的區分並不確鑿。作為鄰近首都台北最斑斕蕪雜且不斷快速更新的移民工業城市,三重埔不斷隨時有人懷著希望搬遷進來,也有人幾經游移漂泊之後黯自離去。
遠溯日治昭和年間(1930年代),因屢遭大水淹漶地貌低濕而得名的「三重埔」一地,原與蘆洲、板橋浮洲並列為北台三大蔬菜供應區,當地大多為農村木造屋舍或簡易土牆建築的地頭菜園遍佈、生活簡樸,取水則靠自鑿的幫浦汲水,有些人家便在河畔沙地沃土種植些蔬果以求溫飽。其後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日本殖民政府正欲大肆進行「侵華戰爭」與「南進策略」,乃開始計畫在島內發展軍備相關重工業。基於防空疏散政策考量下,為了避免作為戰時指揮所與行政首府的台北市遭受戰火波及,遂決定將市區周邊鐵工廠、印刷廠、紡織廠、化學廠等重工業設施經由台北橋疏散到三重、新莊、五股等近郊地區。
光復以後,國民政府為了防範中共軍事武力威脅,便繼續沿襲此一疏散計畫,再加上中興橋的竣工開通(1958),促使台北附近有更多工廠陸續匯集遷入三重。隨著1963年「頂崁工業區」開發完成,更讓三重地區躍居成為北台灣名聞遐邇的工業重鎮。
思念小時候喜歡醬油的味道,愛吃醬瓜、筍乾、鹹魚,以及每日黃昏沿街叫賣的蚵仔麵線。至今依然偏嗜酸辣重鹹口味的我,每當驀然回首之際不免串想:這般根植於意識深層的味覺記憶,難道竟是來自早期發跡於兒時故鄉「三重埔」多家知名醬油品牌(味全、味王、萬家香、鬼女神)不自覺醞釀口腹感官習癖的城市因緣?既屬物質慾念,又含氣味想像。
特別是過去廣受餐廳總鋪師與小吃攤青睞、素有「味原液」之稱的淡色醬油「鬼女神」,因以陶甕進行長時間發酵,有著時間加持出來的古老甘醇風味,如今卻也隨著歷史洪流而更增添鄉野傳說的神秘感。
除了與那童年熟悉味道一同造訪的醬油工業之城,「三重埔」在戰後1950到1970年代同時也是生產類比聲音媒材商品(LP黑膠唱片)的產銷中心,全盛時期全台幾乎有七成左右的唱片工廠先後匯聚於此。
舉凡沿著淡水河岸位於河邊北街的「大王」、「鳴鳳」唱片,通往台北大橋直抵重新路的「惠美」、「五龍」唱片,沿途向西行進,依序穿越交叉街口便是位在文化北路的「龍鳳」、「泰利」唱片,以及正義北路的「鈴鈴」、「中外」。
若論單一街道分布密度最高者,則莫過於三重市南區集中了「國際」、「台聲」、「海山」等十家左右唱片工廠的光明路一帶。放眼其餘各地更兼有安慶街的「電塔」、福德北路的「麗歌」、福德南路的「女王」、大有街的「皇冠」、信義西街的「第一」等多家唱片公司座落其間,可謂大街小巷四處遍佈,不少上台北找工作、人生地不熟而又喜愛唱歌的年輕人往往選擇來此就近落腳。
城市不斷地無限擴張,聲音紀錄的也只是死去的時間,其本身即為一種稍縱即逝的時間語言,僅將時空要素與事件內涵完全展現在流動過程當中。
隱約想起陳昇「新寶島康樂隊」專輯裡有條歌叫〈來去台北做歌星〉,故事背景即為當年這些身負歌藝才華的農村子弟想要北上打拼闖盪歌壇的歷史寫照。
六○年代三重埔,曾經滋養了多少畢生投注音樂志業的作詞作曲者及演唱歌手!早年來到三重市信義街上,這裡住著出生於台南鹽水、自幼隨寡母北上定居的寶島低音歌王洪一峰(1927-)。走到路口轉角相鄰中央北路上,便是街坊「厝邊」作曲家林禮涵的住處,好友周添旺(1910-1988)常由台北艋舺(萬華)住家來到林宅聊敘音樂事,而父親在中央南路開設鐵工廠的歌唱童星陳芬蘭(1948-)也會不時慇勤上門討教歌藝。
接著沿街向西行經正義國小通往地勢較低易於大雨淹水泥濘路滑的大同南路,則是來自基隆港都的作詞人葉俊麟(1921-1998)寓居所在,他與洪一峰兩人在此結識知交並且聯手創作出了膾炙人口的〈舊情綿綿〉、〈思慕的人〉、〈淡水暮色〉、〈寶島四季謠〉等經典歌調。至於位在北面邊陲的溪尾街,甚至還曾經寄宿著〈農村曲〉民謠作曲者、晚年落寞隱居在此終老的戲曲樂師蘇桐(1910-1974)。
連接台北大橋門戶的三和路老街,從東南往西北方向穿越了整個三重市區直抵蘆洲邊境,在這條路上早已消歿既久無人聞問的「陳木理髮廳」不知是否還留存著當年林春福、郭金發、陳木、賴謙祺等四名意氣風發少年郎組成男聲「四奇士合唱團」(1964)的多少流風遺跡?
從這端街頭到彼方巷尾,往後陸陸續續更有無數暫時棲居三重埔的遊子過客,在這邊緣縫隙裡頑強地生存,其中包括了來自嘉義太保市水牛厝莊的葉啟田,以及甫由桃園大溪來此投靠親戚寄人籬下、初期喚作藝名「林茜」在酒店駐唱的鳳飛飛。
對他(她)們來說,那些遙遠歲月困頓勞祿的日子似乎也談不上有何娛樂休閒可言,但總有些管道能夠予以苦中作樂自尋排遣。離開了故鄉,無數個想家的日子牽掛起來,像風箏般飛舞。雖然歸去時沒有燈火迎接,卻有了聲音。
有一種聲音叫作鄉愁,戒不掉也避不開,似遠猶近、雖近猶遠,它是一種由記憶、聽覺和泥土芬香揉製而成的珍貴汁液,足以讓人們滲透浸入耳膜度過心靈飢荒思念焦慮的貧瘠歲月。
早在電視媒體尚未普及之前,街頭巷尾經常迴繞著由老舊收音機調幅商業電台放送傳來陳芬蘭〈孤女的願望〉、文夏〈黃昏的故鄉〉、洪一峰〈舊情綿綿〉等本省人熟悉的台語歌調聲聲入耳,無論早晨、黃昏或者華燈初上,伴隨著「客廳即工廠」號召家庭主婦齊作手工勞動的普遍景象聽來既暖烘又溫煦,人們總是不自覺跟著低吟哼唱以紓解平日工作的單調。
透過空中電波傳送至真空管流洩而出的古樸聲響,唱的是:「叫著我,叫著我,黃昏的故鄉不時地叫我,懷念彼時故鄉的形影,月光不時照落的山河」,清新而嘹喨的歌聲彷彿來自天空流雲的呼喚,日式演歌(Enka)詮釋節奏慢吞如水銀瀉地粒粒滑順,那些內心遭受苦悶侵蝕得最嚴重的人們把它當作一帖清涼劑、一處心靈綠洲。
「寶島歌王」文夏以其特有慵散啜飲的噥軟嗓音見證了戰後六、七○年代台灣婦女家庭勞動史的聲音形象。
昔日輝煌歲月從早到晚開著英國製白色敞篷車搭載「文夏四姊妹」全省風光巡演,當他首度躍登大螢幕主演郭南宏導演第一部歌唱電影《台北之夜》的同時(1962),台灣第一家電視台誕生,「群星會」節目逐漸成為國語流行歌曲「淨化」而活躍的主流媒體舞台,也自此宣告了台語歌曲事業盛極而衰的凋零命運。
在我出生那年(1976),「廣播電視法」開始公佈實施,規定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一天只能播送兩首台語歌。由於晚間七點半後就不能播出台語節目,老家三重埔聽不懂國語(北京話)的阿嬤只能早早就寢,白天的台語電視節目也很少,只有中午一小時(老三台,每台只在午間新聞前後播半小時)。剩下的時間,她只能抱著收音機,聽一些未被查禁的台語歌。
凝望城市與城市之間,人類照亮黑夜的野心與能力永遠不足以真正將整個夜晚時空轉化成「恍如白晝」,任何大鳴大放的主流音調也不可能完全遮蔽其他聲音的存在-哪怕這聲音再怎樣微弱。
嘗試描述三重埔作為異質流動空間的存在,讓我庶幾不斷反思咀嚼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生前所說:「我喜歡變換語調,找出所有可能的聲音,追求每一種顏色,並且尋找任何可能的生命力量……當我探向越卑微的事物和題材時,我的詩就越明晰而快樂」。
對此,咱們實在不必過於戀羨隔岸首都台北追逐「現代性」光亮洗禮的中產階級城市優位象徵。儘管三重埔位處語言文化與地緣政治陰影下的附庸生存位置,加諸施行「洪水平原管制法」帶來整個空間規劃資源的相對匱乏,但其本身乍見凌亂無的常民生活脈絡序卻是極盡地多音喧嘩,各階層各性格的人都在摸索適應彼此的相處方式,無形之中提供了此處「七橋之都」發展地方生命力與獨特性的必要土壤,構成了「三重埔」文化身分的「混雜性」(hybridity)。
無疑地,遑論過去或現在,它都是一處普遍關照社會底層幽黯角落、充滿蕪雜草根活力的民間歌謠城鎮。
最好的詩人,就是給我們日常麵包的詩人。其實音樂與城市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