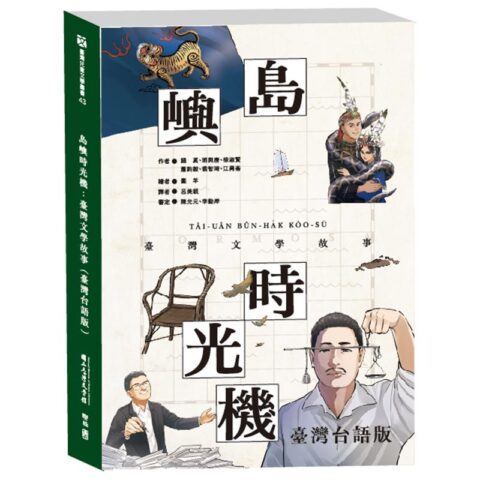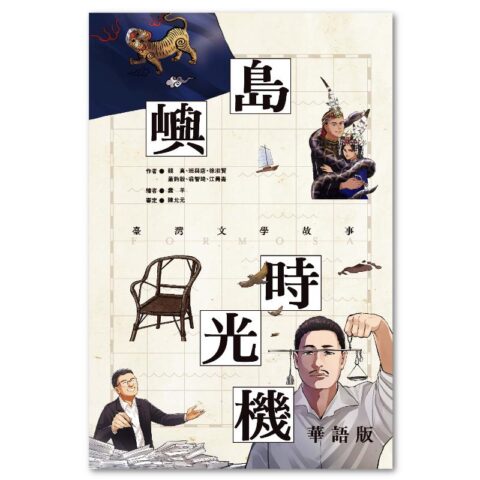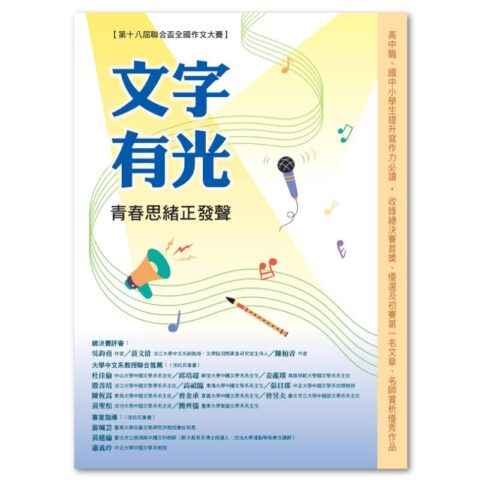山羊不吃天堂草
出版日期:2010-02-03
作者:曹文軒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52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5465
系列:曹文軒作品集
尚有庫存
山羊寧死也不吃天堂草。這幅景象震驚了明子。
他摸了摸口袋裡那筆並不屬於他的錢,開始察覺到什麼叫做「尊嚴」……
全書刻劃現實,深沉內斂,是當代一流少年小說家曹文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得獎紀錄
‧ 第三屆宋慶齡兒童文學獎首獎
‧ 1994年「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小說類類長篇創作最佳獎
‧ 1994年中國時報「開卷」周報一週好書榜
‧ 1994年誠品書店「青少年文學」寒假書單
本書特色
一隻隻山羊慢慢地倒下,牠們堅持不吃可以活命的天堂草,結果,牠們都死在夕陽遍照的草坡上……,這一幅景象震驚了鄉下少年――明子,像一拳重重地撞擊在胸口。他想著那一筆造陽台預收的工錢,他想著夕陽映照的雪白的羊屍――那一群不吃天堂草而死去的羊。明子還了那筆預收的錢嗎?他如何徘徊、掙扎在善惡一念之間?一部深沉內斂的長篇少年小說,描述一個鄉下少年在大城市生存的故事,不但成功刻劃出人性美的「真」,也現實揭露了惡的「真」。
曹文軒是中國當代少年小說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深厚的文學素養和寫作才華,使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種優美、浪漫、細緻兼具深刻幽默的高尚氣質,讀後令人難以忘懷。
內容簡介
少年明子來自偏僻的小豆村,生活異常困苦,家裡養羊失敗,負債累累,明子只得跟隨木匠師傅三和尚、師兄黑罐到大城市闖蕩謀生,但他們似乎永遠也不可能真正進入屬於都市人的世界。生活在一個金錢的城市社會中,他們為錢而哭,為錢而笑,為錢而分,為錢而合,就連明子的尿床也與貧窮緊緊地聯繫著。作品透過生活的艱辛、世態的炎涼,刻畫了主人公的坎坷心路,以及他們優劣並存的所作所為。
明子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孩子,跟師傅出來後,機伶的他很快掌握了木匠手藝,甚至超過了師傅。他敢愛、敢恨,富有同情心:偶遇雙腿殘疾的紫薇,他主動幫助;鴨子是他的好朋友,明子把差點誤入歧途的他及時拉了回來;對師傅的冷眼善心,敢於和師傅使臉色,最終使師傅屈服……。然而原本擇善固執的他,在進入了都市大染缸之後,生活的不順遂、一連串的打擊和金錢的力量,使他一度迷失了自我,他開始染上了打架、賭博、偷竊、說謊等惡習。
明子鑄下的禍越來越大,他竟意圖將客人給的一千塊錢定金吞了,然而此時腦中卻突然浮現昔日在小豆村養羊的那段回憶:天空下,那群羊在一隻一隻地倒下去……。當時父親說:「不該自己吃的東西,自然就不能吃,也不肯吃。」往事閃過明子腦袋,猶如當頭棒喝,喚醒了明子的良知,把他從犯罪邊緣拉了回來,讓他在善惡之間做了正確的抉擇。
專家推薦
曹文軒的這本長篇小說沒有落入「善惡分明、黑白判然」的俗套,他也沒有傳達強烈的道德觀。他只是嘗試描繪一個成長中少年面臨的種種困境,在徘徊於善惡邊緣時,如何做了正確的抉擇。這種啟示是本書的宗旨,也是本書如何值得一讀的主因。
(張子樟/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曹文軒的這部小說的語言風格是:流暢、平易,於樸實中顯出風味,也顯示出了他對比喻的鍾愛,這些比喻是屬於曹文軒自己的,因而有新意,而且一筆盡得風流。他的創作則是從理論裡逃出,化而為水,我們讀他的作品就像在明易清朗的流水中漂滑而下。
(朱家雄/作家)
目次
山羊不吃天堂草
作品導讀
撥雲見日少年路◎李潼
苦兒成長的故事◎張子樟
作家與作品
作者手蹟
大話曹文軒◎彭懿
我的爸爸◎曹征雁
曹文軒寫作年表‧得獎紀錄
內容摘錄
明子覺得自己被一泡尿憋得慌,便去找廁所。他很容易就找到了,但那個廁所總是朦朦朧朧的。他好像從沒有見過這個廁所。他有點猶豫不決。他想讓自己拿定主意,可頭腦模模糊糊的,生不出清醒的意識來。尿越來越憋人,小腹一陣陣刺痛,伴隨著,還有一種麻酥酥的感覺。他搞不清楚自己的這泡尿是撒呢還是不撒。他覺察到自己的身體很沉重,仿佛被捆綁了似的。他想掙扎,可意念似乎又不特別清楚。一會兒,這些感覺又慢慢地消失了……。
這是深夜時分。
城市在酣睡中。秋風好像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在無人的大街上遊蕩著。夜真是寂寞。發藍的燈光毫無生氣,疲憊地照著光溜溜的大街。秋風搖著梧桐樹,於是大街上就有斑駁的影子在晃動,像是一個灰色的夢。偶爾有幾片枯葉離了偎依了好幾個月的枝頭,很惶惑地在燈光下晃動著。其情形,像一片薄玻璃片扔進水中,在水中忽左忽右地飄忽著下沉,不時地閃出一道微弱的亮光。它們終於落到地上的枯葉裡。當風大了些的時候,這些枯葉就順著馬路牙子往前滾動,發出乾燥而單調的聲音,把秋夜的靜襯得讓人感到寒絲絲的。
仿佛在極遙遠的地方,傳來一聲火車的汽笛聲。
這裡有一座高大而古老的天主教教堂。教堂頂上,那個十字架在反射到天空中的半明半暗的燈光中,顯得既哀傷,又莊嚴神聖。在深邃的夜空下,這個凝然不動的簡潔的符號,還顯出一派難言的神秘和威懾力量。
在教堂的背後,沉浮在夜色中的,是一座座高大的現代化建築。它們的高大,使人有一種渺小感和一種恐慌感。它們是在僅僅幾年的時間裡面,令人吃驚地矗立在人們的視野裡的。它們把遼闊無垠的空間變得具體了,也使空間變得狹小了。它們使人無法回避。但這個城市裡的人,並不都知道,這些建築在白天或是在黑夜,到底是用來幹什麼的。這些建築的不斷凸現,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變化,仿佛它們是屬於另外一些對他們來說十分陌生永不可溝通的人的。
與教堂的神聖以及這些建築的高大形成一個極大的反差,明子他們師徒三人所棲身的小窩棚,在這夜色中,就顯得十分猥瑣和矮小了。
小窩棚搭在距教堂不遠的一座大樓後牆下的一片雜樹林裡,是他們用從建築物的廢墟上撿來的木頭、油氈和從垃圾堆裡撿來的塑膠薄膜以及紙箱板等搭成的。白天,當明亮的陽光把大樓照得更加華貴時,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大堆垃圾。
他們來到這個城市已經半年多了。至今,明子對這座城市還是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他覺得這個他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是遙遠的,陌生的,永不可到達的。城市對他來說,是永不可解釋、永不可捉摸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有時,他隱隱地還感到了一種恐怖感和一種令人難受的壓抑和悲哀。他在小豆村生活了十六個年頭,很少想到在兩千多里地以外還有這樣一個世界。他原以為,世界本沒有多大。他六七歲時,甚至認為,這個世界除了小豆村,只還有一處地方,離小豆村大概要走一天一夜的路程。世界就這麼大。當半年前,他和師傅、師兄又坐汽車又坐火車地行了兩天兩夜,被拋到這座城市時,一方面他感到驚奇和激動,一方面又感到暈眩和緊張。這個在小豆村機靈無比的孩子,常常顯得局促不安、愚蠢可笑。他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卑下心理。當他很呆笨地站在大街上,或呆頭呆腦地混在人流中時,本來就生得瘦小的他,就覺得自己更加瘦小了。那種隱隱約約卻緊追不捨的自卑感,一陣一陣地襲擊著他的心靈。
他常常地想念那個平原上的貧窮不堪但卻讓他感到自足的小村子。但回去是不可能的。他們必須生活在這個並不屬於他們的世界。
夜在一寸一寸地縮短。
明子又覺到了尿憋人。他又朦朦朧朧地見到了廁所。這回,來不及再考慮了。當廁所的形象一出現,幾乎就是在同時,尿就又急又沖地奔流出來了。尿熱乎乎地在身體下部的一條渠道流動著,又把一種微痛但很舒服的感覺散佈於腹部乃至全身。他有一種說不出的好感覺。他沒有想到尿尿竟是這樣一種讓人愉快的事情,當終於尿完時,他的身體像繃緊的弦鬆弛下來了。
不久過了多久,他覺得身子下面有點溫熱,心微微緊張了一下。
兩隻貓在不遠處的垃圾箱裡同時發現了一塊什麼食物,搶奪起來,並在喉嚨裡呼嚕著,各自警告著對方。後來竟互相廝咬起來,不時發出淒厲的尖叫聲。
明子突然一下醒來了。身子下面的溫熱感也一下子變得十分明確。一個意識猛然跳到腦海裡:尿床了!
他用手摸著褥子,證實著尿濕的面積。情況真使他害臊和不安:褥子幾乎都濕了,並且濕得很透,能絞出水來。
他一動不動地躺在濕乎乎的褥子上。
他幾乎是肯定地覺得,與他同睡一個被窩抵足共眠的師兄黑罐,此時此刻,是醒著的,並且正在十分清楚地用後背忍受著那醃人的潮濕。
明子心裡有一種深深的歉意。
明子的印象中,上次尿床距今大概才半個月時間。
這個壞毛病,像沉重的陰影一樣,一直攆著明子,使他很小時就有了一種羞恥感。隨著一歲一歲長大,這種羞恥感也在長大。明子的身體發育得很不好,又瘦又小,像一隻瘦雞,走起路來,顯得很輕飄。他的臉色總是黃兮兮的,眼睛深處駐著不肯離去的憂鬱。這大概與這毛病總有點關係。
明子認定,這個毛病是過去喝稀粥喝出來的。
在明子關於童年的記憶裡,有一個很深刻的記憶,那就是喝稀粥。家裡的日子過得十分窘迫,一天三頓,總是喝稀粥。那是真正的稀粥!把勺扔進粥盆裡,能聽到清脆的水音。如果用勺去攪動一下粥盆,會瞧見盆中翻起的水花,在水花中稀稀拉拉地翻動著米粒。他很小的時候,就能自己用一雙小手抱著一隻大碗喝這稀粥了,直喝到肚皮圓溜溜的,像只吃足食的青蛙。如果用手去敲肚皮,就像敲著一隻牛皮鼓。晚上那一頓,尤其喝得多。不知怎麼搞的,小時候是那麼困乏,一上床就睡著,一睡著就醒不過來。困乏與尿多的矛盾的直接後果就是尿床。天長日久,就成了習慣,夜裡有了尿,就不由自主地流瀉出來。
明子長到十歲以後,這個毛病雖然好了些,但卻一直不能根除。
當自己用身子去焐幹濕漉漉的褥子時,明子有時甚至對自己有一種深深的仇恨。
離家之後,明子總是小心翼翼的。他不能讓師傅發現尿床。在他看來,師傅是兇狠的,甚至是可惡的。他不願看到他滿臉惡氣的臉色。晚上,他儘量少喝水,並儘量遲一點入睡。入睡之前,他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往外跑,哪怕是一滴尿也要將它擠出來。可是,這並不能杜絕這一毛病的再現。
如果,他一人獨自睡一張床,也許能使他的心理負擔小一些。然而。這小小的窩棚,只勉強夠放兩張床,師傅自然要單獨占一張,他不得不和黑罐合睡一張,並且不得不和黑罐睡一個被窩,因為他們兩人只有這一床被子。他家勻不出一條被子來讓他帶上。
明子把雙腿張開,把雙臂攤開,盡可能多地去焐潮濕的褥子。他的臀部和後背已感到火辣辣的醃痛,但他只能一動不動地忍受著。他睜著眼睛,很空洞地望著棚頂。他想讓自己想一些事情和一些問題,可總是不能很順利地想下去,常被臀部和背部的火辣辣的灼熱感打斷。
黑罐也一動不動地躺著。
明子知道,這是黑罐在默默地忍受著痛苦,而裝出根本沒有覺察的樣子,以使他不感到歉意。可是明子在明白了黑罐的這番心意之後,心裡卻越發地感到羞愧和歉疚。
明子歪過腦袋去看睡在棚子另一側的師傅。遠處折射到窩棚裡的燈光很微弱。明子惟一能看到的,就是師傅那顆摘了假髮後的亮光光的禿腦袋。「三和尚!」明子在心裡情不自禁地默念了一聲,覺得這名字很有趣。他無聊地玩味著「三和尚」,暫時忘了身下的難受。明子和黑罐在背後開口閉口都稱師傅為「三和尚」。他們覺得他就應該叫「三和尚」。「三和尚」這個名字最自然,最真切,最得勁。
三和尚心中似乎有什麼重大的怨恨,翻了一個身,從胸膛深處長長地歎出一口氣來。有一陣,他似乎呼吸有點困難,吸氣出氣,都變得急促和沉重,還夾雜著痛苦的呻吟聲,像是在夢魘中掙扎著。
明子感到有點害怕,禁不住靠緊了黑罐。
作者:曹文軒
曹文軒,1954年1月生於江蘇鹽城農村。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生導師。
有文學作品集、長篇小說《憂鬱的田園》、《紅葫蘆》、《薔薇穀》、《白柵欄》、《甜橙樹》、《追隨永恆》、《山羊不吃天堂草》、《青銅葵花》、《草房子》、《紅瓦》、《根鳥》等15種。
主要學術著作有《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小說門》、《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面對微妙》、《曹文軒文學論集》等。
主編《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作品選》、《五十年中國小說選》、《現代名篇導讀》、《外國文學名作導讀本》、《外國兒童文學名作導讀本》等。
有人評價他的作品是「追隨永恆的力作」。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日、韓等文字。曾獲國家圖書獎、宋慶齡文學獎金獎、冰心文學獎、金雞獎最佳編劇獎、中國電影華表獎、德黑蘭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特別大獎「金蝴蝶」獎、義大利第十三屆Giffoni電影節「銅獅」獎、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優秀學術論文獎、北京市文學藝術獎、《中國時報》1994年度十大優秀讀物獎等學術獎和文學獎30餘項。
其文學作品在中國影響深遠,常在沒有刻意宣傳的情況下,保持常銷,為中國再版次數最多的兒童小說作家,讀者群廣及括孩子以及成人,並被譽為「青春文學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