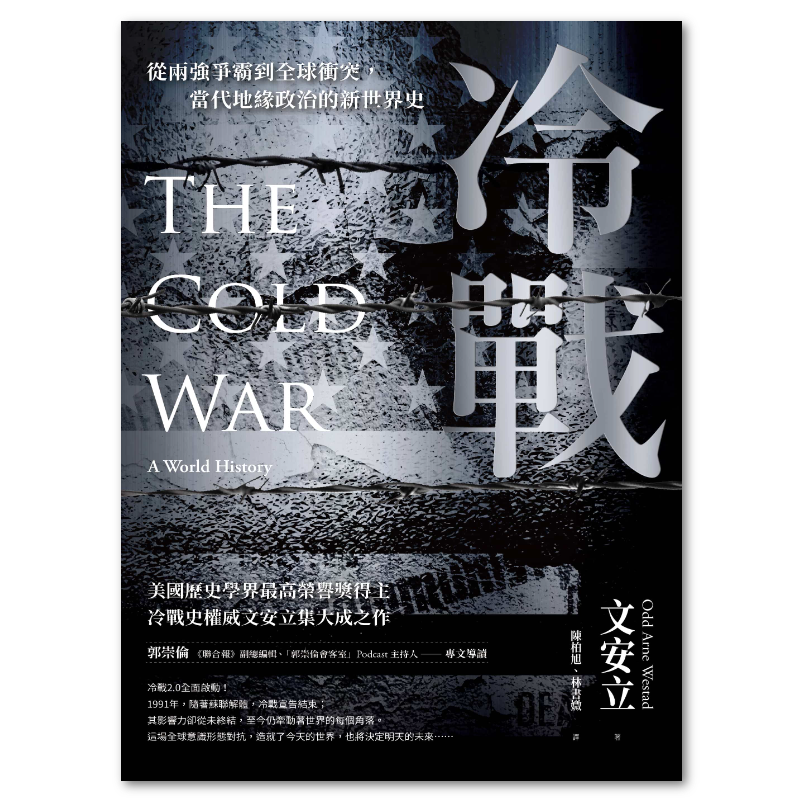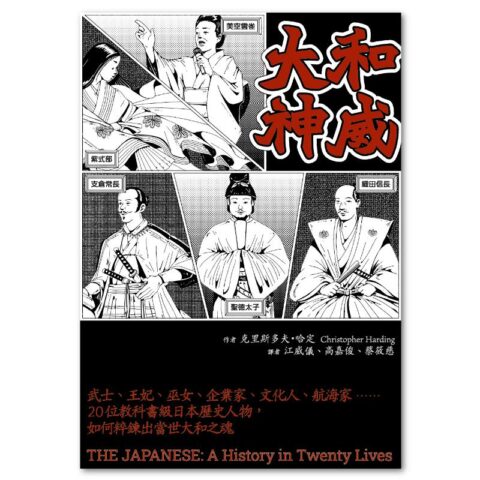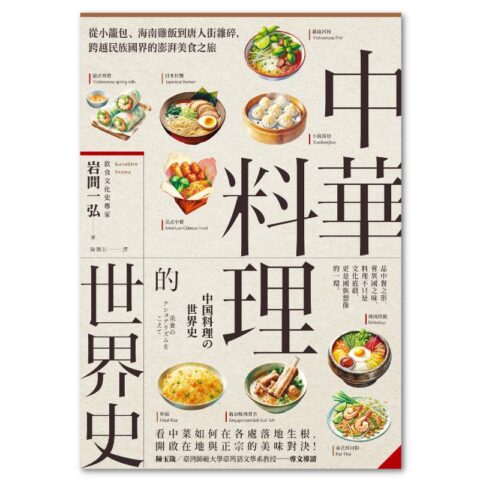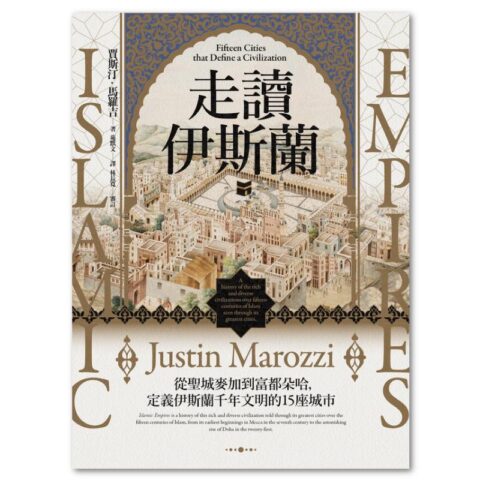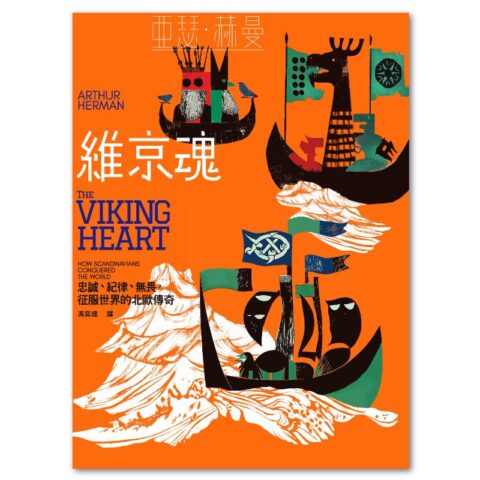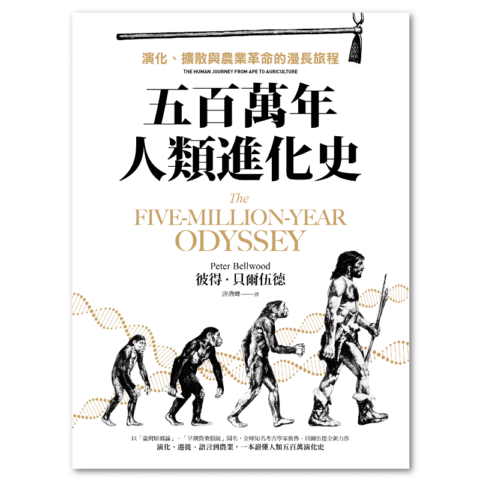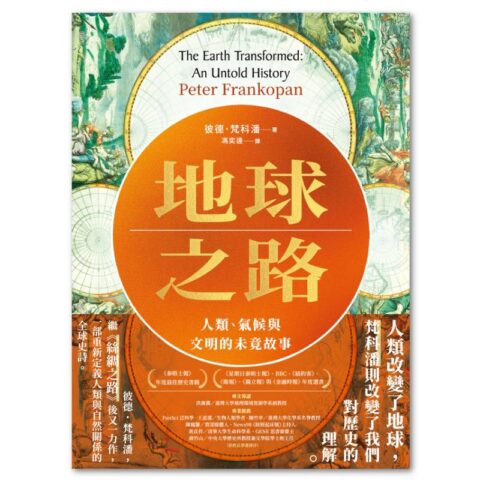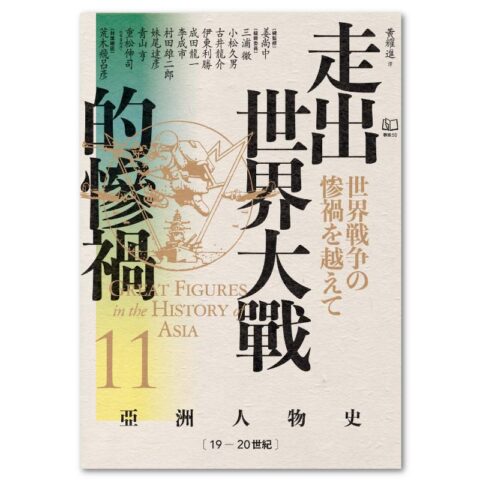冷戰:從兩強爭霸到全球衝突,當代地緣政治的新世界史
出版日期:2023-11-16
作者:文安立
譯者:陳柏旭、林書媺
裝訂:平裝
EAN:9789570871425
系列:全球視野
尚有庫存
「如果你只讀一本關於冷戰的書,這就是那一本書。」
首部以全球為視角、最完整的冷戰通史
美國歷史學界最高榮譽班克洛夫特獎得主、冷戰史權威文安立集大成之作
以宏大的時間跨度、寬闊的空間視野、睿智獨到的分析
對21世紀以來冷戰研究新方法、新領域的全面概括
冷戰的起點,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衝突,塑造了現今的地緣政治格局;
它是當今全球衝突的歷史源起,也是世界紛爭的燃點。
1991年,隨著蘇聯解體,冷戰宣告結束
但它的影響力卻從未終結,至今仍牽動著世界的每個角落
這場全球意識形態對抗,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也將決定明天的未來
*郭崇倫(《聯合報》副總編輯、「郭崇倫會客室」Podcast 主持人)專文導讀
過去,我們傾向於將冷戰視為一場有界限的衝突:美國和蘇聯之兩強相爭,脫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餘燼之中,隨著蘇聯垮臺而戲劇性地結束。但在這部重要的新著當中,美國班克洛夫特獎得主文安立主張,冷戰必須從全球意識形態衝突的角度來理解,可追本溯源至十九世紀,並在世界各地產生持續的影響。
文安立於本書提出一個新視角:在上個世紀,強權競逐和意識形態鬥爭改變了全球每個角落。冷戰也許始於歐洲的邊緣,但它在亞洲、非洲和中東產生了最深的反響,幾乎所有群體都不得不選邊站。這些選擇繼續定義著世界各地的經濟和制度。
冷戰攸關美國勢力的崛起及鞏固,但又不僅止於此。冷戰也是關於蘇式共產主義的潰敗,以及在歐洲的民主共識的形式透過歐盟建制化的過程。在中國,冷戰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在拉丁美洲,冷戰意味著沿著冷戰的意識形態分界線益趨兩極化的發展。
今天,許多地區都深受肇因於這個時期的環境威脅、社會分裂、族裔衝突之苦。意識形態影響了中國、俄羅斯、美國;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經被發軔於冷戰的那種單靠動武來解決問題之信念所摧毀。
本書的廣度驚人,富於灼見,就地理空間與時間歷程兩方面拓展了我們對冷戰的理解,提供了一部今日世界是如何創造出來的新歷史,引人入勝。
媒體讚譽
一部史詩……文安立的敘事如此有力的一個原因,在於他使用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檔案來源。冷戰的規模有多大?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如同本書所示,冷戰規模相當巨大,不只是因為形式危如累卵,也是因為主要兩方的規模。冷戰有多深?這個問題也很容易回答,而文安立回答得恰如其分,展現出冷戰如何觸及世上許許多多柏林圍牆鞭長莫及之處。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一部嚴肅的鴻篇巨製,對冷戰詳實睿智的研究報告。
——《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豐富的細節來自檔案研究,以及對政治家、軍人、科學家和其他親身經歷過冷戰人士的訪談。文安立是研究中國和冷戰的專家,他透過關於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的篇章,為冷戰憑添價值不菲的面向。雄心勃勃的研究,洞見敏銳,視野遼闊。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2017年最佳書籍
一部規模真正堪稱全球性的冷戰記載,一部明察秋毫的歷史。若我們想了解當今最緊迫的事態發展,從朝鮮獲得遠程核導彈、到西方民主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等議題,本書正是在我們必須掌握冷戰之動力的時刻到來。
——《新共和》(New Republic)
一項全面的研究。榮獲班克洛夫特獎的歷史學家文安立,在精準的主題式章節中,對十九世紀末以來形成冷戰核心的意識形態衝突敏於洞見。這是一個龐大的故事,而作者以清晰和優雅的筆觸加以處理,教人欽佩。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說,這是一堂巨大而及時的歷史課。
——《科克斯書評》(Kirkus)
文安立認為,冷戰使世界變成了今天這番樣貌。展讀這部精美的歷史著作,很難不同意他的觀點。這是有史以來關於冷戰最好的歷史著作之一。
——《雜食》(Omnivoracious)
今天,西方試圖遏制激進的伊斯蘭主義,這延續著自他對立的心態。憤怒的穆斯林譴責美帝國主義和異教徒自由市場的掠奪行為;自殺式炸彈襲擊者造成的威脅,使得古老的東西方對立相比之下顯得幾乎彷彿可以管控。在這些情事當中,文安立龐大的單卷歷史是智慧的開端。
——《衛報》(Guardian)
一部引人入勝的歷史匯編。
——《獨立報》(Independent)
《冷戰》體現了對此一主題皓首窮經之鑽研和思考。令人拍案的觀點和饒富價值的洞見俯拾即是。
——《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文安立長期以來一直論證冷戰在方方面面使得世界成為今天的樣貌。他的最新著作乃是對此主張之又一雄辯。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對一場全球衝突進行了清晰的總結……令人印象深刻的書。
——《倫敦時報》(The Times)
以果敢和氣度來講述這段重要的歷史……所有的館藏都必不可少,也是迄今關於冷戰的最佳著作之一。
——《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
文安立融會貫通當代的學術研究,得出一套平易近人的敘事,為此一衝突在全球造成的廣泛影響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令人印象深刻的壯舉,將得到學者、學生和一般讀者的讚賞。
——《出版商週刊》(Publishers Weekly)
文安立在其研究對象嚴酷的性質與時而驚心動魄的洞察力之間保持平衡,不斷以生動的、幾乎是對話式的散文形式。即使在充斥著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歷史著作的圖書市場上,這本書也能脫穎而出。
——《公開信月刊》(Open Letters Monthly)
《冷戰》所提供的,並非平鋪直敘的歷史概覽,而是直搗核心檢視彼此扞格衝突的意識形態底下的思維,以及這些體系對其社會、經濟的影響。這些複雜的觀念深入淺出,為讀者帶來了激動人心的散文。這本書是一個讓人清醒的契機,讓最近的歷史為我們自己的時代和持續存在的危險思想提供視角。
——《娛樂焦點》(Entertainment Focus)
敘事節奏分明,穿插著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隻言片語,教人讀來喜不自勝……本書應該放在家家戶戶的書架上,不斷提醒人們愚蠢、無知、傲慢是如何把世界帶往毀滅的。由於這三種特徵的化身此際在正蹲在白宮裡,這本書具有真實和當下的價值。
——《南華早報》(SouthChina Morning Post)
文安立對冷戰進行了恢宏的敘述。他將冷戰界定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以及一個兩極的國際體系,精彩地展現其意識形態、地緣政治、技術和經濟層面。舉世首屈一指的冷戰學者文安立再度以其分析之深之廣讓讀者眼花繚亂。
——梅爾文.萊夫勒(Melvyn P. Leffler),維吉尼亞大學美國史教授
文安立此書一出,我們便不能再把冷戰視為一場一對一的比賽。文安立為我們提供了一部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競逐的新歷史,將其追本溯源至1890年代,並揭示冷戰在1990年代餘威猶存。在闡明冷戰核心的華府與莫斯科之競爭如何與在邊陲構成第三世界戰爭的多場「熱」戰之間的聯繫方面,無人能出其右。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廣場與塔樓》(The Square and the Tower)作者
文安立對冷戰之起因、冷戰之意味,以及冷戰為何仍然重要,分析強而有力,特別是在闡釋完美的理念如何驅動極不完美(甚且往往暴虐無道)的領導人方面,更是鞭辟入裡。文安立的著作將冷戰之於全球化,冷戰之於近年的中東戰爭,以及冷戰之於美國與俄、中的競爭聯繫起來。這是一本所有對政治、外交政策感興趣的人都應該閱讀的書,由領銜的世界史學者講述的故事,引人入勝。
——傑雷米.蘇里(Jeremi Suri),《不可能的總統》(The Impossible Presidency)作者
對幾代人來說,冷戰是脈絡,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背景設定。這部歷史將冷戰本身放在世界史的大脈絡圖景之中,加以深刻理解,巧妙呈現。出自我們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的作品,強而有力。
——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到不自由之路》(The Road to Unfreedom)作者
作者:文安立
挪威歷史學家,現居美國康乃迪克州紐黑文,主要研究冷戰史和當代東亞史。現為耶魯大學歷史和全球事務伊利胡(Elihu)講座教授。
代表作包括《躁動的帝國: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緩和的衰落:卡特時代下的美國—蘇維埃關係》(The Fall of Déten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arter Years)、《決定性交會:中國內戰1945-1950》(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50)、《全球冷戰:對第三世界的干預與我們時代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等,編有《劍橋冷戰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曾以《全球冷戰》獲得2003年美國歷史學界最高榮譽班克洛夫特獎(Bancroft Prize),《躁動的帝國》獲得2013年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施瓦茲傑出作品獎(Bernard Schwartz Book Award)。
譯者:陳柏旭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中央大學英文系碩士、耶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博士,曾任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員,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系博士後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譯有《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
譯者:林書媺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中央大學法文系碩士,現為康乃爾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候選人,譯有《被詛咒的勝利: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
推薦序 文安立眼中的百年冷戰史/郭崇倫
緒論 創造世界
第一章 起點
第二章 戰爭的試煉
第三章 歐洲的不對等
第四章 重建
第五章 新的亞洲
第六章 韓國的悲劇
第七章 東半球
第八章 製造西方
第九章 中國的災禍
第十章 打破的帝國
第十一章 甘迺迪的偶發事件
第十二章 遭逢越南
第十三章 冷戰與拉丁美洲
第十四章 布里茲涅夫時代
第十五章 尼可森在北京
第十六章 冷戰與印度
第十七章 中東風暴
第十八章 緩和政策潰敗
第十九章 歐洲的預兆
第二十章 戈巴契夫
第二十一章 全球變遷
第二十二章 歐洲的現實
結語 冷戰塑造的世界
謝詞
注釋
緒論/創造世界
本書試圖以百年來的觀點安放冷戰這個全球現象。冷戰於一八九○年代開始發端,隨著全球資本主義首度遭逢危機,歐洲工運激化,到美、俄擴張為跨洲的帝國。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美國終於一躍而成為真正的全球霸權,冷戰於一九九○年告終。
採取百年觀點看待冷戰的目的,旨不在使其他重大事件──世界大戰、殖民體制的解體、經濟與科技變革、環境破壞等──都埋沒在單一縝密的框架之下,而是為了理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如何大幅影響了全球發展,復又受到全球發展所影響。這也是為了理解為何一組衝突可以貫穿整個世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以及為何所有其他權力──不論是物質權力還是意識形態權力──的角逐者都必須與冷戰勾連在一起。從十九世紀尾聲開始,就在歐洲現代性似乎達到頂峰之際,冷戰也沿著衝突的斷層線蔓延滋生。
我的論點(要是說這本長篇大論有單一論點的話)是:冷戰應運十九世紀末的全球轉型而生,而一百年後在快速的巨變中被埋葬。冷戰既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又是一種國際體系,因此可以從經濟、社會、政治變遷的角度來把握,這些變化又遠比冷戰本身所創造出的事件更加影響深遠。我在先前一部著作中曾論證,發生在後殖民的亞、非、拉那些寓意深遠且往往暴力的變革,是冷戰的主要結果。2但衝突也有其他意義。可以將衝突視為美國全球霸權降臨的一種進程,可以視之為社會主義左翼──尤其是列寧所主張的形式──(緩慢)的潰敗,也可以將之描繪為國際對立的切中要害的階段,這些對立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復又被七、八○年代新一輪的全球分歧所取代。
無論要強調冷戰的哪一個面向,都必須認可經濟、社會、科技轉型之劇烈,衝突在這種種轉型當中發生。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九○年代之間的百年,全球市場樓起樓塌,其步調之快,令人目眩神迷,前代人只能夢想的科技日新月異,而有些科技被有心人士用來增加主宰、剝削他者的能力。百年來全球的生活形態變幻莫測,幾乎所有地方的機動性與都市化程度都扶搖直上。所有形式的政治思想,無分左右,都受到這些變革之瞬息萬變影響至深。
除了意識形態之重要程度,科技也是冷戰作為國際體系能夠經久不衰的一個主因。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數十年,核武兵工廠四起。為了保全地球的未來,兩個強權都準備好要把地球摧毀──箇中諷刺之處,相信讀者不會錯過。如同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喜歡形容的那樣,核武是「新型武器」:不是戰場上的武器,而是一舉抹除整座城市的武器,一如美國一九四五年對日本的廣島、長崎所為。但只有美蘇兩大強權擁有足以一舉毀滅全球的核武數量。
二十世紀由許多或多或少平行發展的重要故事線所串起,歷史總是如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影響了幾乎所有故事的進行,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到了世紀尾聲,這些發展中的某些部分使得冷戰的國際體系及意識形態衝突顯得過時。因此,很可能將來的史家會將冷戰的複雜性顯著消解。他們可能站在歷史的制高點,為亞洲經濟實力的蜂起、太空探索的開端、天花的根除賦予更大的重要性。歷史總是一個縝密的意義網絡,撰寫歷史的史家之觀點至高無上。我所著迷的重點是冷戰在創造當今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但當然這不意味著貶抑支線,獨尊冷戰。這只是在說,長此以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深刻影響了人類如何過活,以及影響他們思考在地與全球政治的方式。
總的來說,冷戰是在國際政治兩個深刻的變革過程中發生。其一是新興國家的出現,這些國家多少是依十九世紀歐洲國家的形式立國。一九○○年,全球的獨立國家尚不滿五十,其中約莫一半在拉丁美洲。現在則有將近兩百個獨立國家,其中大多數都分享著相當類似的治理與行政組織。另一項根本的變革是美國躍居宰制全球的力量。如果換算一九○○年的美國國防預算,約合二○一○年的一百億美元,這比起數年前激增不少,這是由於美西戰爭爆發以及在菲律賓、古巴綏靖叛亂的行動。今日國防支出已經擴編百倍,來到一兆美元。一八七○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全球的九%,在冷戰臻至高峰的一九五五年是二八%左右。如今雖然美國已經下滑有年,但仍然在二二%左右。因此,冷戰形塑於國家數量滋生及美國權力上漲的年代,兩者都影響了衝突的方向。
這些國際上的變革也確保了冷戰會在民族主義當道的框架中運作。儘管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經體系的信徒似乎總是不滿於此,但訴諸某種形式的民族認同時而擊潰最精心構造的、為求人類進步的意識形態計畫。宏大的現代化計畫、縱橫捭闔或跨國運動一再在面臨民族主義或者其他身分政治所設下的第一道關卡就碰壁。儘管作為全球框架的民族主義──想當然耳──也有其顯著的限制(試看超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tic〕的德國、義大利、日本在二戰的敗北),但民族主義總是對那些未來屬於普世主義的意識形態設想構成挑戰。
因此,即使在冷戰方殷的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雙極結構總是有其限制。儘管蘇、美的體系在全球範圍內都有其吸引力,兩者皆無法在其他地方全盤複製。或許就算在最為慷慨激昂的意識形態理論家心中亦認為難以複製。就社會發展而言,其結果是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經濟,都難逃強大的地方特色影響。在某些案例中,政治領袖憎惡這樣的混合形式,因為他們想要他們自己的政治理念以未遭玷汙的形式施行,不過卻必須妥協,可以說這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件幸運的事。波蘭、越南雙雙支持蘇維埃的發展理念,但實際上又與蘇聯非常不同,一如日本、西德雖然深受美國影響,但仍與美國大相徑庭。印度以獨特的方式將議會民主制與詳盡的經濟計畫糅合在一起,更是與任何冷戰的理想型都大異其趣。在兩大強權的領導人眼裡,以及對其他地方的支持者來說,唯有美蘇強權是最純粹的,是其他地方仿效的模範。
某方面來說,這並不出人意表。美、蘇的現代性觀念共同源自十九世紀末,在整個冷戰期間也仍維持許多共通點。兩者皆源於歐洲(以及歐洲的思考模式)在過去三個世紀以來全球性的擴張。人類史上第一次只有一個中心──歐洲及其分支──宰制了全世界。歐洲人過去打造漸次掌握全球的帝國,並且讓歐洲人移居三大洲。這種絕無僅有的發展讓有些歐洲人(以及祖先來自歐洲的人)相信他們可以透過他們所發展出的觀念與科技,把全球的未來控制在手中。
儘管這種思考模式有更深的歷史淵源,卻是在十九世紀臻至高峰。這也並不出人意表:十九世紀無疑是歐洲人之於其他所有人之優勢臻至高峰的時代,不論是科技、生產還是軍力。對於一些史家所稱的「啟蒙價值」──理性、科學、進步、發展以及作為一套體系的文明等──抱持信心,致力奉獻,這顯然源自歐洲在權力上的優勢,也來自在非洲與東南亞的殖民,以及征服中國和泰半阿拉伯世界。及至十九世紀末,儘管歐洲及其分支(包括俄、美)內部容或有分裂,但他們的統治至高無上,他們所投射出的觀念亦然。
如同本書後面所將揭示的,在俄、美的擴張中,天命的概念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兩國的精英分子咸信其擴張師出有名,其特質就註定了各自在區域內──以及最終在全球範圍內──的霸權地位。在全球制霸的過程中,兩國的精英分子都認為他們正在遂行歐洲的使命。系出歐洲的他們在某方面來說,是在執行讓歐洲走向全球的大業,把歐洲一路帶往太平洋。某些知識分子領袖相信在此過程中,他們是在讓自己的人民更加歐化,更著重歐洲價值,並且願意在帝國的年代肩負起帝國的重擔。但同時,在兩國境內也都有人認為自己的擴張從根本上就與歐洲帝國有所不同。若說英、法是在探勘資源、尋求商機,那麼俄羅斯人和美國人的擴張則有著更為崇高的動機:推廣企業與社會組織的理念,以及在政治與宗教上救贖靈魂。
宗教在美、俄兩端同樣位居要角。7儘管到了十九世紀末,組織化的信仰在歐洲(以及其他多處)已漸趨沉寂,但俄羅斯人與美國人仍然把宗教看作是他們生命的中心。某方面來說,美國的福音新教主義與俄羅斯的東正教頗有相似之處。兩者都強調目的論以及信仰之篤實重於其他基督教派的共通之處。兩者都對原罪觀不以為意,相信社會可以臻於完善(perfectibility)。最為重要的是,福音教派與東正教徒都相信宗教觀直接啟發政治觀。他們要獨當一面,完成上帝對人類的旨意。
美、俄涉入全球事務的過程,各因他們分頭與十九世紀末的世界主宰強權──大不列顛──的競爭染上不同的色彩。美國憎惡英國在海外掌有之貿易特權,認為英方宣稱自由貿易原則以及投資的自由,實則自私自利,道貌岸然。儘管許多美國精英對英式途徑感到激賞,到了一八九○年代,兩國逐漸開始爭奪影響力,尤其是在美國全球勢力上揚首當其衝的南美洲。俄羅斯也將英式世界體系視為其崛起的主要屏障。在一八五○年代的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率領的聯軍遏止了俄羅斯對黑海地區的控制,自此,許多俄羅斯人都視英國為反俄霸權,意圖阻卻俄國勢力的增長。英、俄的利益在中亞、巴爾幹半島相互衝突。俄羅斯認定英國的支持是讓日本在一九○五年的日俄戰爭中勝出的關鍵。與美國不同的是,俄羅斯並未認為經濟發展可以讓自己取英國而代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霸權。但領土擴張與經濟落後的兩相結合,正是俄羅斯──以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一躍成為全球反體制勢力之道。
儘管冷戰代表美國在國際上崛起,成為大不列顛的繼承者,但要是認為這種承繼的過程和平順利,那就大錯特錯了。在二十世紀的大半時間,美國對全球政治與他國社會都有著革命性的影響力,於歐洲(包括英國)如是,於亞、非、拉亦如是。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於一八七○年代將他的美國英雄視為「偉大的西方野蠻人,以其天真和孔武踏步向前,端詳這個弱不禁風的可憐舊世界一陣子後,俯衝下來攫住它」,這麼形容倒也離實情相去不遠。8美國在國際上是麻煩製造者,起先拒絕按照英國霸權在十九世紀樹立起的規矩行事。美式觀念銳意革新,其公序敗壞良俗,其教條主義則置人於險境。唯有在冷戰行將結束之際,美國霸權才開始能在全球範圍內穩坐泰山。
因此,冷戰攸關美國勢力的崛起及鞏固,但又不僅止於此。冷戰也是關於蘇式共產主義的潰敗,以及在歐洲的民主共識的形式透過歐盟建制化的過程。在中國,冷戰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在拉丁美洲,冷戰意味著沿著冷戰的意識形態分界線益趨兩極化的發展。本書試圖揭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冷戰在全球範圍內之重要之處,儘管其形態各異,有時並不全然一致,教人困惑。以一部單冊的歷史書而言,本書力有未逮,只是在複雜紛呈的各種發展隔靴搔癢,但若是能夠邀請讀者一同繼續探索冷戰如何讓世界成為今日之世界,那麼,本書便可功成身退。
推薦序/文安立眼中的百年冷戰史/郭崇倫(《聯合報》副總編輯、「郭崇倫會客室」Podcast 主持人)
在國際冷戰史學界,原籍挪威的文安立以研究中國與冷戰的學術成就而著稱。到了倫敦經濟學院後,他開始將研究視角擴展到整個第三世界與冷戰方面,不但使用了公開出版的史料集、回憶錄、博士論文,而且駕馭多國檔案史料的功力驚人。文安立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美國與東亞關係史講座教授,也是當今的冷戰史權威,他的這部著作被譽為冷戰新史學集大成之作。
在文安立之前,冷戰研究多為歐洲中心史觀,只在意大國之間的關係與衝突,很少討論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影響與干涉,更狹窄的甚至以美國外交史角度來寫冷戰通史,譬如我在當研究生時必讀的,耶魯大學冷戰史泰斗蓋迪斯(John L. Gaddis)所著的冷戰史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描寫冷戰另有角度,稱其為「長和平」。如果從美、蘇兩大國之間七十年沒有戰爭來看的確如是,但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並非如此,因此有人批評蓋迪斯的書「是從美國的角度,基於美國的經驗,以最適合美國讀者口味的敘述」所寫成的著作。
在這本書中,文安立開宗明義定義冷戰為一種「國際體系」,其實與十六、十七世紀英國與西班牙的兩極對立,或是十一世紀中國宋朝與遼國的兩極對抗,都有相似之處,這種國際體系的特點是兩極意識形態尖銳的對立,積極動員盟國參與各個領域的激烈鬥爭。
但是文安立不只是要描寫國際體系而已,他要挖掘更根本的因素,最主要的面向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甚至還有南北之間的冷戰,以及中國革命成功後的新因素。他承認冷戰並不能解釋二十世紀所有的歷史事件,但冷戰卻是其中最重要的,而且是「創造世界」(World Making)的歷史現象,前所未有。
因為文安立從資本主義的興起與轉折來看冷戰,所以他對冷戰的編年有其獨到之處,將之分為四個時期:一、冷戰萌芽階段(一八九○-一九一七);二、冷戰初始階段(一九一七-一九四一);三、冷戰激烈對抗階段(一九四一-一九七一);四、冷戰衰退與結束階段(一九七一-一九九一)。
冷戰萌芽期,文安立並沒有定在雅爾達會議,或是一九四六年伊朗危機,而是採取百年觀點看待冷戰,定在世紀之交時,對抗性意識形態崛起之際,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興衰,到蘇聯解體,美國於一九九一年一躍成為全球霸權而終止。
文安立的論述不僅長遠,而且宏大,擴及全球五大洲,他眼中的冷戰,其實就是美、蘇兩國在第三世界的爭奪,凸顯冷戰對第三世界的深刻影響,包括紅色高棉的種族屠殺,南美洲的軍人獨裁政權,還有非洲的動亂等。冷戰雖然影響不一,但是對各國內政都有巨大的影響。
文安立的冷戰論述與他的背景有關,他一九六○年出生在挪威東北沿岸地區,那兒正好是和蘇聯接壤的地方,他承認自己一生有三次思想轉變;第一次思想變化發生在一九八○年代,在美國攻讀研究生學位,當時他的政治立場非常左傾,但後來認知到,是八○年代雷根保守主義推動了冷戰的終結。
第二個思想變化與中國有關,他早在一九七九年就來到中國,對於改革開放的過程與成就,一開始都抱持積極評價的態度,但現在就會多些批判性的眼光來審視;第三個變化則是對蘇聯的看法,起初覺得它很沉悶無聊,社會運轉得不好,但現在則抱持更積極的評價。蘇聯能夠在意識形態、經濟體制、政治模式上,創造出一個完全不同於美國並與其相抗衡的國家,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也因為這些想法的改變與衝擊,讓文安立兼容並蓄,二○一七年他在北京大學客座一年,在一次演講中談到他的治學方法,首先是「國際史的擴大化」,「國際史」超越了狹義上的外交史或是國際事務史,愈是以一種更巨闊的方式看待歷史就愈好。他舉第一次大戰爆發為例,固然可以透過研究一戰前的外交互動(diplomatic traffic)了解到一戰爆發前的事情,但是一戰並非僅僅是由一九一四年七月的危機造成的,它也是由戰爭爆發之前,一代人的時間裡,一系列不同層面的社會轉型所導致的。
其次是方法論問題,歷史學者必須獲得好的資料,但更重要的是,嘗試提出反事實的問題,關於事情如何可能變得不一樣,以及事情如何可能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如果想成為優秀的歷史學家,就必須學會自我反思,你必須能夠思考,為什麼我會問這些問題?為什麼這些問題對我重要?我還可以提出哪些其他的問題?為什麼擁有不同背景──民族背景、社會背景、世代背景的人,會對同樣的材料提出不一樣的問題?有這樣的反思,並不容易。
第三,可以稱作「研究的國際化」,過去由於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創造了現代世界體系,所以研究這些處於衝突中心的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從它們的內部入手。因此,對於美國和冷戰這一主題而言,討論的中心始終是在美國政治人物與決策本身;或者如英國和克里米亞戰爭,討論時往往集中在英國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現在,即使是那些主要研究美國史的學生,也傾向於學習掌握其他的語言和文化,這使得他們能夠進行更多的國際比較研究。這對於國際史的未來真的非常重要,可以從中發現更多的東西。
文安立並不是一般的美國歷史學家,事實上,他曾經出版過中國外交史專書《躁動的帝國》(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所以他對現實政治有獨到的看法。像是美國人常有誤解:美國和中國在上世紀七○年代的接觸,是因為「尼克森意圖改變中國」;但文安立說,更大程度上是中國領導人希望基於中、美關係的變化而改變中國。
當時他是在批判國務卿龐培歐的演說,在演說中,龐培歐把中國描繪成一個與西方以及與其他東亞國家完全不同的國家,並剝離中國政黨和國家的概念,強調「中共非中國」。但從文安立的眼光來看,這些論調與冷戰期間的論調沒有什麼兩樣,都在突出意識形態差異。他強調:「中國發展並不是由美國所創造,而是來源於中國本身的需要」,所以美中還是盡力要找到可以合作的模式。
文安立也隱約地批評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同事艾利森的論點──「中美註定衝突」的觀點,是對中美關係的一種誤解,這並不是大國政治的歸宿。而同時,從歷史經驗看,認為「衝突不可避免」的觀念常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書中第十五章〈尼克森在北京〉,就是在描寫當時毛澤東的心境:蘇聯在北,美國在南,「兩者攜手完成對中國的包圍之勢,而中國必須突圍」,在這個心態下,四位老帥的報告成為毛戰略思想轉變的契機,這就是中國自己選擇的決定。
這個冷戰中重大的轉變,文安立只用一頁交代,但是在熊向暉的回憶錄《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談到了那時的背景:在文革的時代,一九六七年參加二月逆流的四位老帥──陳毅、聶榮臻、葉劍英與徐向前,分別在四家工廠蹲點,但被交付一項特殊任務「研究國際形勢」。周恩來當時說,現在各外事部門集中力量「鬥、批、改」,熟悉國際問題的幹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於處理日常工作,實在擠不出時間過細地考慮天下大事,「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並且指派後來任總參情報部副部長熊向暉、外交部歐美司司長姚廣協助,提供外國材料參考。
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至九月十六日,在中南海武成殿,共舉行了十六次四十八小時的國際形勢座談「議論天下事」,陳毅在開場白中說:歡迎長篇大論,也歡迎三言兩語;可以插話,可以打斷;可以質問,也可以反駁;講錯了允許收回,更重要的是「第一,腦袋裡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戰略格局的發展變化」。
當時蘇聯與中國的關係緊張,邊界挑釁,南邊美國參與越戰正值高峰,官方的調子是擔心蘇、美勾結反華,但老帥們並不這麼看,他們認為:反華大戰不至於輕易發生,判定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蘇修擴張是在擠美帝的地盤。
九月十一日柯錫金總理參加越南國父胡志明葬禮後,在北京停留,與周恩來舉行會談,震動國際,當時美國情報部門限期蒐集柯錫金在中國三小時的詳細情況,老帥們在討論時稱,中蘇首腦會談震動全世界,一旦舉行中美總理會談,一定更會震動全世界。其中陳毅尤其有戰略眼光,提出:在華沙會談恢復時,要主動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問題,只要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動作,不提先決條件,並不意味在臺灣問題上改變立場,而是在會談中可以逐步解決。
老帥們的建議勾畫出剛剛成形並延續十餘年的國際戰略格局,為打開中美關係提供了路徑圖。一九七一年四月,毛澤東決定透過巴基斯坦邀請美國總統代表訪問北京,與中國領導人直接對話。同年七月九日季辛吉訪問北京,老帥們的戰略遠見證明是中國當時的最佳策略。
文安立書中特別寫中國的只有兩章,另一章是第九章〈中國的災禍〉,談中國建政之初以及文革期間的革命暴力,導致「舊中國」的消亡。北京大學據說在二○一八年要出中文版,但當時決定基於政治考慮,要刪掉整個第九章;現在已經二○二三年了,簡體版仍毫無音訊,只怕中共當局刺眼擔心的部分,只會愈來愈多了。
■ 第十七章 中東風暴
如同在亞洲和非洲一樣,我們應該將在中東的冷戰理解為殖民主義與其對手之間長期的鬥爭。讓中東截然不同之處,在於其國內外衝突的激烈程度之高,以及這些衝突在全球的層級所達到的程度之深。有些時候,例如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的戰爭,似乎在中東的冷戰裹脅了雙邊(bipolar)的世界,挪作己用。儘管並非所有在此區域的爭端都與全球的意識形態分野有所聯繫,但許多政治領導人使出渾身解數,讓它聽起來像是意識形態衝突,一來為了國內動員,二來也是為了打造同盟關係對抗他們在區域內的敵手。對蘇聯和美國來說,中東是一場威脅要把它們拉進漩渦的風暴。這起風暴是由蘇、美雙方的勢力所驅動,雙方都堅信這攸關己方的利益,但仍難以估量。
二戰告終之際,中東泰半落入外來勢力之手。英軍支持法國在敘利亞、黎巴嫩以及更加西邊的馬格里布的影響勢力。英國人自己占據巴勒斯坦,宰制在埃及、伊朗、約旦以及波斯灣的阿拉伯世界國家。阿拉伯半島泰半由保守派的沙烏地宗教貴族與美國石油公司的同盟控制。伊朗北部遭蘇聯占領,南部則由英國占領,顯然是為了避免讓豐厚的油礦落入德國手中。這是個徹頭徹尾的殖民世界,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在此總難免意識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十數年之後,此一政治景觀將有所變異。英法的宰制勢力逐漸成為明日黃花,而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則暴露出歐洲的孱弱,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戰爭失利亦然。阿拉伯的民族主義革命推動著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的政治能量。巴勒斯坦遭到由宗教來劃定的以色列新國家以及埃及、約旦的占領地聯手瓜分。接連幾任美國政權和美國的歐洲、日本盟友相信,在時局變遷的中東,確保石油供給以及保留西方戰略性的在場至關重要。同時,蘇聯希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會掙脫資本主義的控制並與莫斯科結盟。有些蘇共理論家認為,封鎖便宜的中東石油可以製造出資本主義終極的危機,而為紅軍獻策的人士則知道,要是戰爭爆發,北約的軍隊須仰賴石油進口。對雙方而言都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中東夢魘般的政治局勢就此與冷戰的衝突休戚與共。
除了石油供給之外,中東與冷戰之間還有兩個主要連結。一是區域內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之間的衝突。在中東的每個國家,世俗主義者──主要是(但未必總是)社會主義者──都槓上那些相信政府應該依循教令組織的人。在阿拉伯世界,占上風的民族主義者多半是奉行社會主義的世俗主義者。他們接受宗教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但往往迫害相信宗教統治的少數伊斯蘭主義者。沙烏地阿拉伯是一例外。但即便是在當地,掌權的保守貴族也忙著穩固自己從國家的油藏搜括的油水,以及利用同美國的盟友關係來達成國安目的,無暇冒任何獨立伊斯蘭主義活動的風險。在語言、文化、信念都與阿拉伯中東有所區隔的伊朗,有一位年輕的王室成員銳意讓他的國家現代化,在美國的指導之下,殘忍迫害相信宗教統治的什葉派神職人員。在五、六○年代,沙王有理由相信保守的穆拉(mullahs,按:受過伊斯蘭神學訓練的老師)會支持他對抗勁敵──左派與伊朗共產黨。
另一個連結是猶太人在中東立國。美、蘇雙方都自始即支持以色列立國,但是是基於迥然不同的原因。對美方來說,以色列是自歐洲的猶太大屠殺倖存下來的猶太人庇護之所,亦是實現《聖經》裡猶太人回到祖先家園的預言──至少對一些人來說。這讓西方的現代性引進中東,就美國的外交政策而言,也是在區域內培植潛在盟友。對蘇聯來說,以色列──至少起初──對英方是個麻煩,也是左翼錫安主義的勝利,因此即便骨子裡反猶的史達林也心想可以與左翼錫安主義合作。以色列可能也為他自己面對的猶太人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史達林樂於把老弱或者政治異己的蘇聯猶太人送往以色列,就如同他已經在蘇聯境內讓人口四處遷徙。
結果,對猶太人立國之於猶太人自己以及之於該區域的形勢,美蘇雙方都嚴重誤判。以色列於一九四八年擊敗阿拉伯國家,加上以色列社會內部眾志成城,使其本身也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勢力。以色列受惠於美援,卻不依賴美援,至少在一九六七年的戰爭以前是如此。以國在蘇聯集團當中槓上反猶主義,就是因為反猶主義在蘇聯比在其他地方更為猖獗。但兩大強權在中東所犯下的最大錯誤,莫過於誤判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能量,而這股能量有一部分是由於在阿拉伯領土上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所引燃。對許多阿拉伯人而言,以色列的存在與成功,映襯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難民數量之多,在在提醒他們必須打造出一個一統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強大運動,才可以救贖阿拉伯民族,並且加速現代性的進程。
如同在歐洲、亞洲其他形式的民族主義一樣,阿拉伯民族主義發軔於十九世紀。其當代的形式發端於一戰結束後初年在鄂圖曼帝國瓦解之後。當歐洲國家拒絕准予阿拉伯國家獨立,反而對中東繼續大規模重新殖民時,民族主義的團體就公開加以反抗。一九一九年,埃及的大規模示威要求全面自主,終結英國控制。翌年,伊拉克人民起而效尤。英方鎮壓起義,造成多達一萬名伊拉克人死亡。一九二五年,敘利亞和黎巴嫩反抗法國統治,造成至少六千人喪命。及至二戰結束時(或甚至更早),民族主義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遍地開花,殖民政權漸漸退潮。
但阿拉伯的民族主義並未止步於要求國家獨立。對許多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而言,逐漸取代直接殖民統治的君主制政體比起英法也不遑多讓。民族主義的領袖把這些國王、宗教領袖視為殖民勢力的遺緒,成天為了個人坐收漁利,想與前殖民勢力妥協。批評他們是「○.五%的社會」的運動把阿拉伯的國王一個接一個推翻,並在追求社會公平之餘要求快速現代化。一九五二年讓埃及法魯克(Farouk)國王退位的年輕官員,強調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以及廢除壟斷的政策。他們也把阿拉伯君王一九四八年未能戰勝以色列的失敗視為道德淪喪的結果。「阿拉伯人以同樣程度的熱情進入巴勒斯坦,」一九五二年埃及革命的領袖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寫道,「他們如此做的根據是……所有人對他們國安界線的預估都相仿。這些人帶著同樣的苦澀和失望離開巴勒斯坦;隨後,他們各自因自己的內政問題遭遇到同樣的因素,同樣導致他們潰敗並迫使他們屈辱低頭的統治勢力。」
從納賽爾針對巴勒斯坦的演說可以清楚看出:他和其他民族主義者已經把所有阿拉伯人看成一個民族。儘管阿拉伯世界自從十三世紀伊始在政治上就已經分崩離析,但銳意變革的革命分子很自然地希望阿拉伯的文化統合可以被轉譯成一個共同的目標,特別是因為這可以為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運動增添光彩。「當在巴勒斯坦的鬥爭結束時,」納賽爾寫道,「阿拉伯的圈子在我眼中已經變成一個單一的實體……我緊跟阿拉伯國家的發展,且發現他們在每一點上都相符。在開羅發生的事情,隔天就能在大馬士革找到對應,還有在貝魯特、安曼、巴格達以及其他地方……這是一個畫一的區域。同樣的情況、同樣的要素、甚至同樣的勢力團體一致抵禦外侮……這些勢力當中又以帝國主義為甚。」
出生於一九一八年的納賽爾是一名軍官,胸懷強烈的埃及民族主義與泛阿拉伯的大志。他把埃及獨立鬥爭看成是廣泛的阿拉伯解放鬥爭的一環。打從他的政治生涯之初,納賽爾就隱約相信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但這必須是由阿拉伯人自己發展出來的治理形式。儘管納賽爾欣賞蘇聯的經濟體系,但他害怕共產主義對埃及造成的政治影響力。他多次監禁左翼領袖,認為他們對政府的批評過了頭。但他在國內主要的敵手是他所認定的宗教右翼勢力。納賽爾公開嘲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在一九五四年有一名被激怒的兄弟會成員試圖暗殺他之後,他下令禁絕所有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對這位埃及領導人來說,伊斯蘭首先是阿拉伯解放與區域統合的靈感泉源。他廢除了伊斯蘭教法法院(Sharia courts),令被全球許多人視為主要伊斯蘭神學家的埃及宗教權威發布教令(fatwa),聲明所有的穆斯林,無論遜尼派、什葉派、還是宗派主義者都屬於相同的穆斯林共同體。
納賽爾對冷戰的觀點直截了當。他相信美、英、法即便在殖民主義終結後仍會試圖控制阿拉伯世界。他把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約旦、波斯灣國家的保守穆斯林君王視為政治經濟壓迫的工具。納賽爾轉投蘇聯,一如印度以及蘇卡諾治下的印尼,因為他相信莫斯科可以是另一個提供經濟、軍事援助和知識的選項。對納賽爾而言,在阿拉伯世界實現其政治目的的鬥爭中,蘇聯是一個可能的盟友。他的不結盟方案是:他保衛他的獨立,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聯合,並在追求納賽爾自己的目標上與蘇聯愈走愈近。對內,他的冷戰政策成功之明證,就是蘇聯對世界上最大的水壩工程阿斯旺水壩(Aswan Dam)的資助。納賽爾在認為美方可能會在美援上附加政治意圖之後,轉而向蘇聯尋求協助,並得償所願。當艾森豪政府憤而撤除援助時,蘇方設計出水壩的藍圖,並協助竣工,最終水壩於一九七○年完工。
對外,納賽爾從與蘇聯密切的關係中獲益。在六○年代,埃及為了支持葉門革命,與沙烏地發生衝突。納賽爾的目的是向區域內其他勢力展示,埃及在全中東都控制著阿拉伯革命的命脈。蘇聯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給予在葉門服役的七萬埃及大軍大量支援。英、美以及約旦、伊朗再加上沙烏地都支持葉門皇室。納賽爾的干預被葉門的部落關係和氏族歧見糾纏不清。由於沙烏地近葉門北邊的疆界,英國又能取道殖民地亞丁(Aden),納賽爾在後勤上也落居下風。這位埃及總統怒道,就連戰死的埃及士兵的鞋子「也比沙烏地國王和胡笙(Hussein)國王的王冠還要尊貴」。但到了六○年代末,納賽爾在葉門的努力逐漸消逝,賠了夫人又折兵,儘管埃及在阿拉伯的南部留下了激進主義的泉源。
但除了納賽爾以外,其他運動也著眼於泛阿拉伯主義。阿拉伯復興社會黨(Arab Ba’ath [Renaissance] Party)於一九四○年由出身敘利亞基督教家庭的前共產主義者米歇爾.阿弗拉克(Michel Aflaq)創黨,他相信組織嚴明的群眾運動可以使阿拉伯對政治、文化統合的追求脫胎換骨。阿弗拉克和他的追隨者擁戴發生在埃及的革命,但批評納賽爾自行其是,過於聚焦在埃及的利益上。復興社會黨的領導班子企求從下而上打造阿拉伯的一統,在各國都成立黨的支部,合力取得政權,把阿拉伯世界統攝在一個極權、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計畫之下。復興社會黨的領導人身先士卒,願與迂腐顢頇、四分五裂、又受歐洲宰制的世代決裂。阿弗拉克說,他們「有這個民族所缺乏的意志,是從沉睡到覺醒、被動到行動的英勇表率」。
就如同許多把統合放在其他美德之上的黨派一樣,復興社會黨自從成立之初,內鬥便不曾稍歇。儘管黨內對納賽爾容或有所批評,有些成員仍然支持敘利亞與埃及於一九五八年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三年後該聯盟不歡而散。在伊拉克,有些成員支持推翻君主制的一九五八年革命,但一年後黨就瓦解了。儘管分崩離析,復興社會黨各分支的影響力仍於五○年代末、六○年代初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增加。對許多嚮往革命性變革但不願擁抱共產主義的阿拉伯人而言,復興社會黨的思路正中下懷。
一九五八年伊拉克的革命是冷戰在中東的分水嶺。取得權力的軍事政權與不成氣候的伊拉克共產黨結盟,部分是由於新任總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 al-Karim Qasim)不信任復興社會黨。卡塞姆也想要與蘇聯結盟,以保護自己的政權不要像五年前的伊朗那樣受到西方干預。革命血流成河。國王和十四名家族成員在宮殿內成為槍下亡魂。英國大使館被洗劫一空。美國領導人嚇壞了。幾週之內,伊拉克竟一舉從在美國的國安結構中位居中心地位的盟友,搖身一變加入了納賽爾和蘇聯的敵營。「我們要不就立即採取行動,要不就撤出中東。」艾森豪總統對顧問說,「因為中東坐擁戰略地位和資源,若不採取行動,進而失掉這片江山,會比丟掉中國還更糟糕。」憂心骨牌效應的艾森豪想要正面迎擊來自蘇聯對美國在中東勢力的直接挑戰。「我們的軍事顧問相信,」國務卿杜勒斯對國會說,「我們現在仍占據顯著的優勢,蘇聯不會想要挑戰……所以,也許只要我們果敢快速行動,他們可能就會發現納賽爾太過魯莽。也許他們會在優勢地位受到威脅、冒著開戰風險前加緊撤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