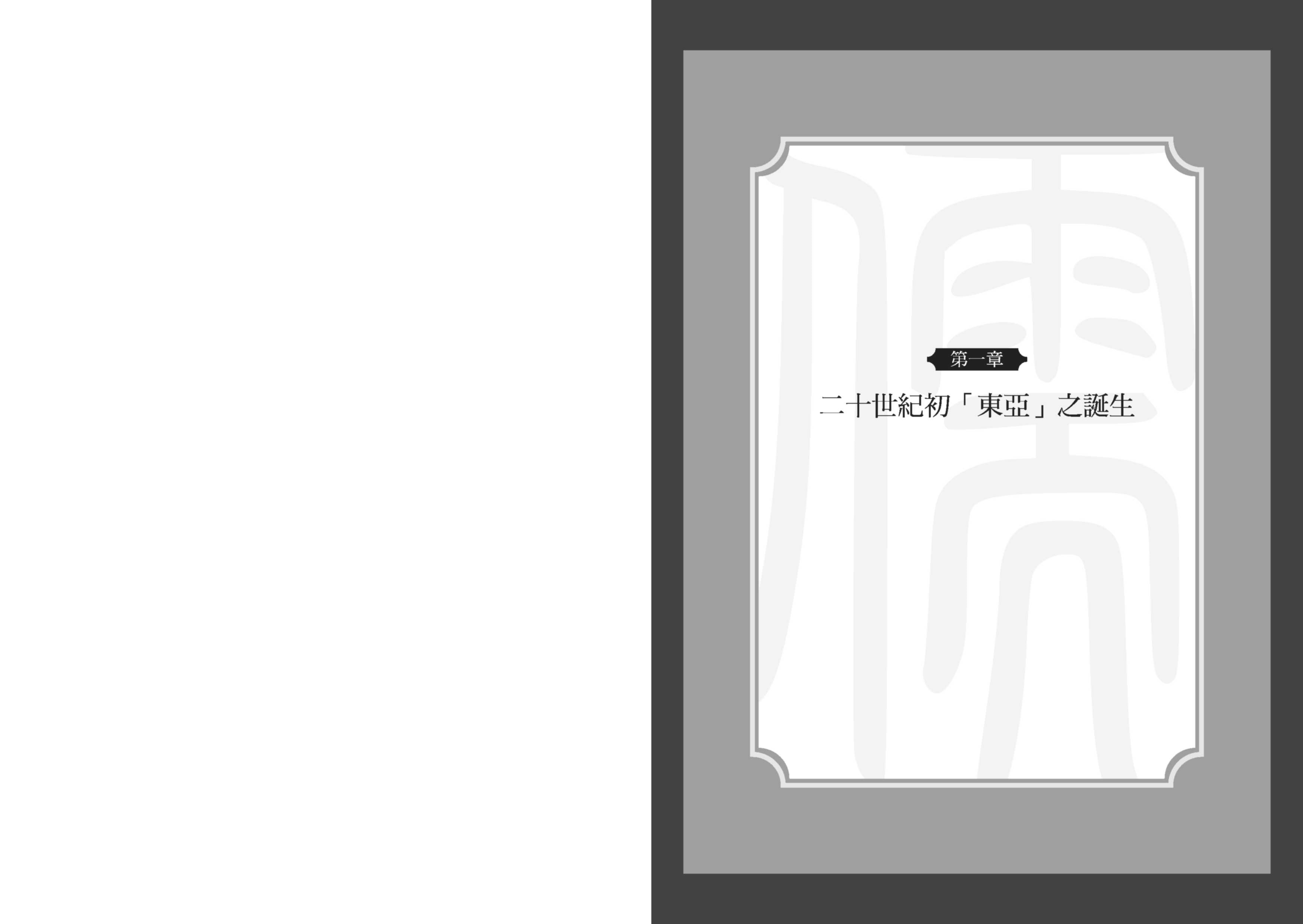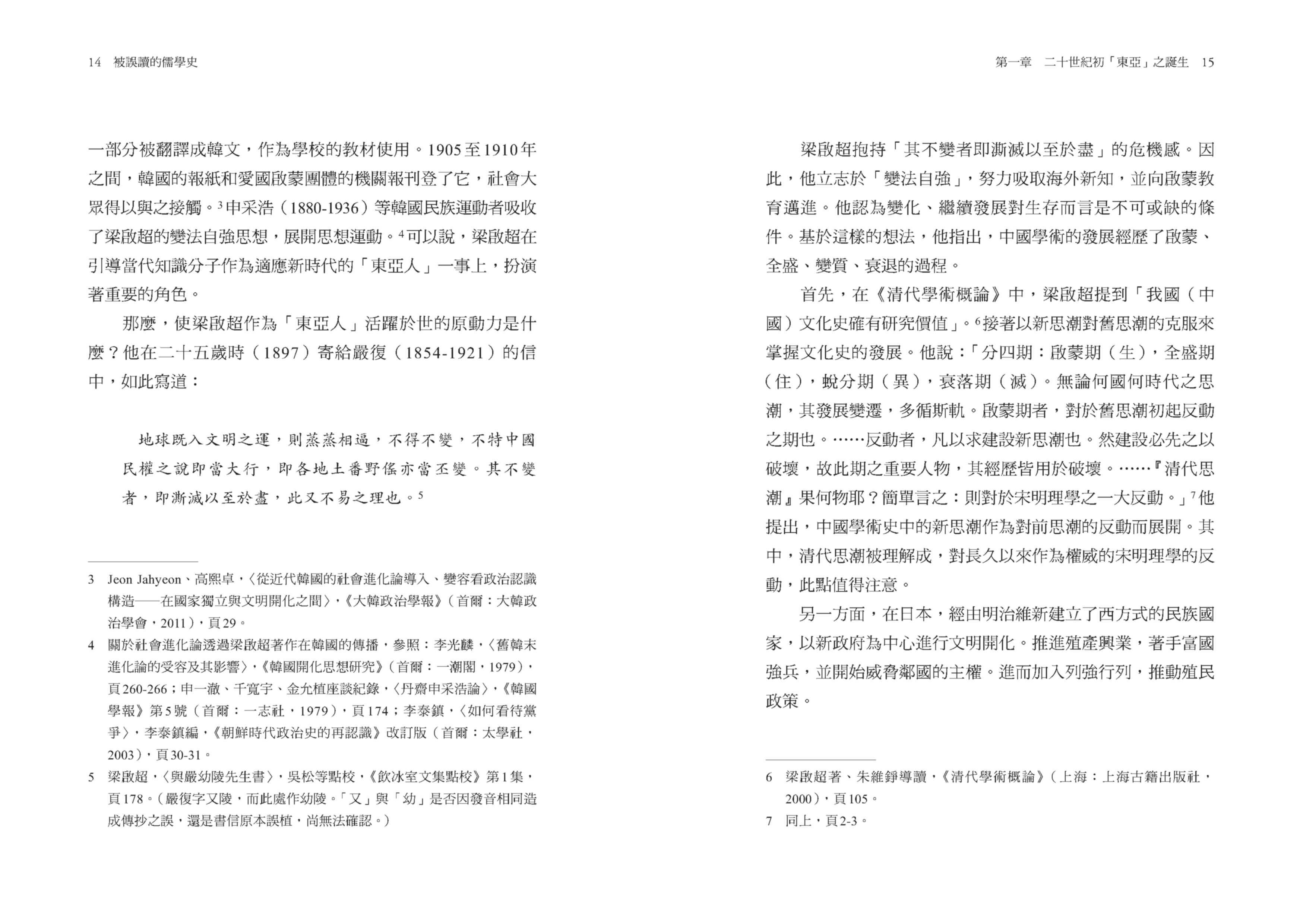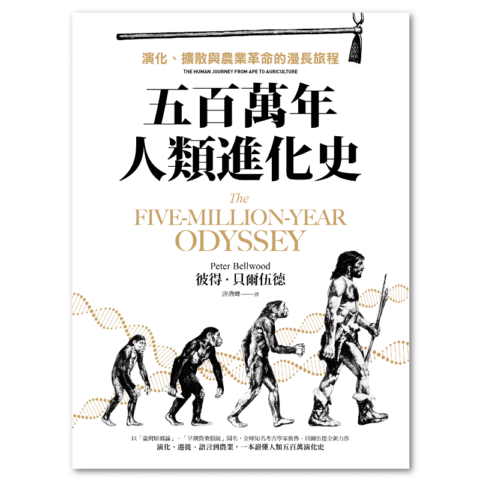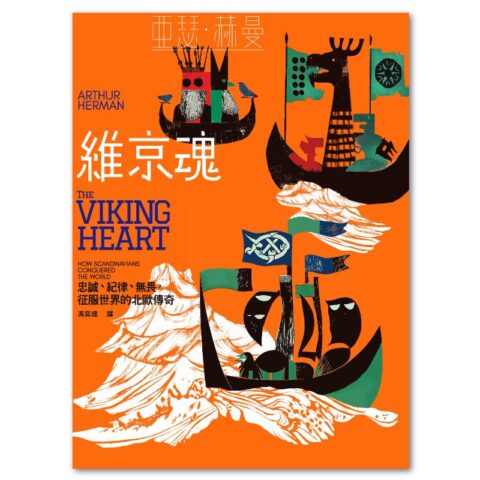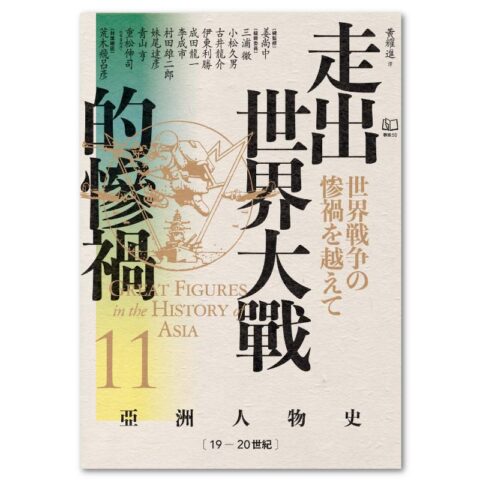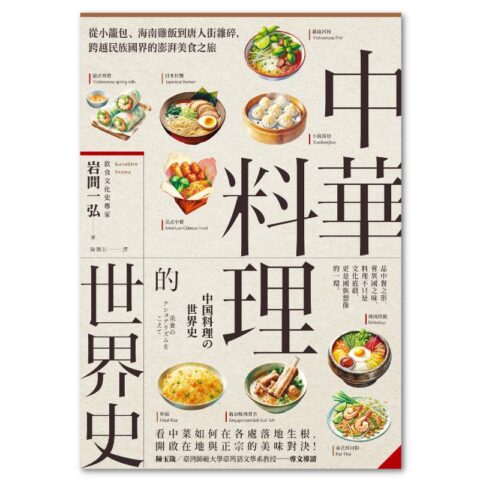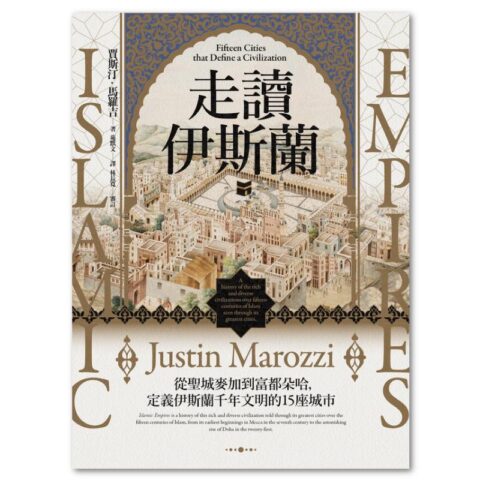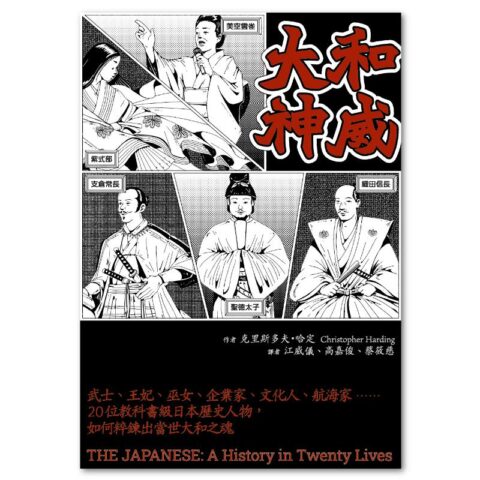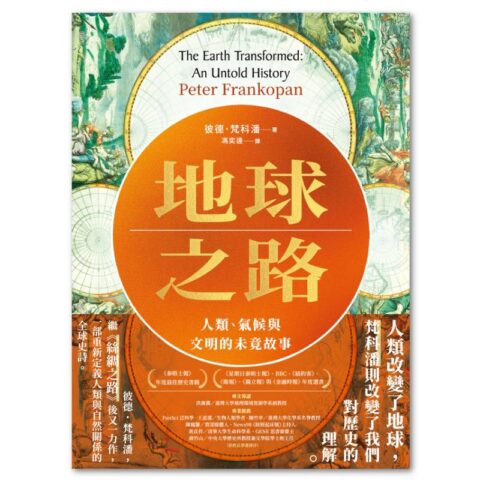被誤讀的儒學史:國家存亡關頭的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
原書名:朝鮮儒学史の再定位――十七世紀東アジアから考える
出版日期:2020-12-10
作者:姜智恩
譯者:蔣薰誼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96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1.8cm
EAN:9789570856507
系列:聯經評論
尚有庫存
面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十七世紀的韓國人,
是反對儒家道統,還是深化原有思想體系?
從東亞脈絡考察,挑戰近百年來的誤解與扭曲
重新定位朝鮮儒學,為韓國思想史提出新解釋
十七世紀的朝鮮受到中國、日本數度入侵,面臨建國以來最大的危機。長期以來,學者們認為,韓國思想史在此關鍵時刻出現了轉變:有些朝鮮儒者開始對正統的朱熹學說抱持懷疑、甚至提出批判,連帶產生出朱子學派與反朱子學派的對立。
《被誤讀的儒學史》透過深入考察史料,挑戰了上述論點。姜智恩指出,過往的研究受到近代東亞政治情勢遽變影響,產生了歷史圖像的扭曲:二十世紀初的韓國學者,在與日本帝國主義史觀對抗過程中,急於尋找挑戰權威的歷史人物,結果反而誤讀了朝鮮儒學史。
姜智恩認為,十七世紀朝鮮儒者所關心的,仍是如何繼承以朱子學為中心的道統。他們以高度精密的方法研究朱子學,並找出朱熹著作中的變化及矛盾,進而在此過程中衍發了新的見解,這才是十七世紀朝鮮儒學史的真相。
作者:姜智恩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韓國高麗大學校漢文學科畢業、韓國高麗大學校大學院國語國文學科碩士、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研究專長為韓國儒學史、東亞儒學史、東亞學術史。
譯者:蔣薰誼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與中文系雙主修畢業,政治思想碩士。現就讀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班。
前言
第一章 二十世紀初「東亞」之誕生
第一節 對於儒學史的關注
梁啟超、井上哲次郎、丸山真男的思想史敘述
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
第二節 對十七世紀的注目
第二章 十七世紀儒者世界的樣態
第一節 朝鮮的士大夫社會
遭逢華夷變態
士大夫集團的出生與成長
科舉和士大夫社會
第二節 無法取得共鳴的日韓儒者
「中華」與我國
以儒者為業
第三章 朝鮮儒者的信念
第一節 朝鮮朝儒者社會的思想基礎
儒者第一義
學術環境
學術討論之重點
第二節 新注釋登場之際
問題的焦點
圍繞「改朱子之注」的攻防
異見提出者之自我認同
第四章 朝鮮儒學史的展開關鍵
第一節 對朱子學的鑽研
追蹤朱熹學說之變化
朱子非聖人
從儒學史消失的「宋時烈門下朱子學研究方法論」
第二節 朝鮮儒學提出創見之模式
否定獨創性
作為出發點的朱熹注釋
第三節 如何定義新解釋
尹鑴之「精意感通」
朴世堂之「初學入德之門」
趙翼對於饒魯學說之接受
第五章 東亞之中的朝鮮儒學史
第一節 觀點轉換
經學的途徑
經學思想與現實思想的不一致
對十七世紀朝鮮儒者的合理要求
第二節 從東亞的視角出發
「古」
理解朱子學的方式
方法論──文脈重視或文本重視
終章
前言
本書旨在重新思考朝鮮朝(1392-1910)儒學史的展開過程,考察重點尤在於釐清朝鮮朝中期、十七世紀儒者活動及作為的思想史脈絡。然而,本書的討論並非始於十七世紀,而是二十世紀前後,進而言之,不是單純從朝鮮儒者出發,而是從東亞知識人所背負的時代使命開始追述。理由是,為了恢復朝鮮儒學史的真實樣貌,必須採取含括中、日、韓三國的東亞全體視野。同時,還必須要考慮到朝鮮儒學史研究正式開始時,研究者所身處的環境。
眾所周知,「中國」或「東亞」能否成為歷史研究的單位,至今仍有爭論。爭論的核心在於,歷史中的「中國」或「東亞」是否曾以具有同一性的單位存在。例如,對於學術史長期將「中國」當作「漢族」的「漢文明」敘述,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石橋崇雄、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所謂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研究者曾論證,清帝國統治者所打造的是多民族國家體制,且帝國經營的成功關鍵也非何炳棣一直以來所主張的積極漢化。
如此說來,「中國」若非以「漢族」的「漢文明」為一個整體,以其為單位講述的「中國〇〇史」或是「中華〇〇原理」等研究史,不就必須重新進行論述嗎?與此種困惑相對的,出現了質疑「東亞」視野的討論。例如,葛兆光主張,在接受漢唐所代表的中華文明的韓國、日本,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以漢唐中華為歷史記憶的文化認同逐漸瓦解。從那時開始,帶有歷史同一性的「東亞」空間便不復存在。近來他又指出,為了打破將現存民族國家看成是歷史上的中國的研究方法,「亞洲」被當作歷史空間來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在強化「東亞」的連帶性和同一性的過程中,時常有意無意地淡化中國、日本、朝鮮的差異,也因此導致亞洲之中的中國變得模糊。
本書礙於篇幅無法加入上述討論。只是,無關乎帶有歷史同一性的「東亞」是否存在,筆者認為「東亞」是能夠清楚認識「中國、日本、朝鮮之差異」的空間。如後所述,從十七世紀中葉日本的例子來看,過去持續認同中華的日本人,到了這個時點之後就不再認同――此種說法脫離史實。就朝鮮儒者而言,無論認同的中華是否實際存在於西邊,他們的中華認同都益發強烈,甚至可以説,真正意義上的東亞在十七世紀以後才誕生。若去除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便無法正確解讀朝鮮儒者遺留的著作。欲正確地了解朝鮮儒學史,東亞的視野便不可或缺。
朝鮮儒學史無論在形成過程,或是作為近代學術的研究對象開始被述說之際,都帶有跨越國境的性質。即,朝鮮時代立足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將該「天下」中自己所應有的狀態當作思考的基準。又,從十九世紀開始到殖民地時代,朝鮮儒學一邊強烈地意識著德川日本的儒學史及近代日本的學術研究成果,一邊設定自己的研究課題。對於欲納入統治之下的中國和朝鮮,日本曾詳細分析其歷史,而中國和韓國學界則不斷地學習日本的學說並加以反駁。即是說,朝鮮儒學史的研究,受到朝鮮外部因素的強烈影響,又與中國學界相似地,以應對外部影響的方式展開研究。
在二十世紀,找出朝鮮儒學史意義的工作,除了研究者,尚由愛國運動家、媒體工作者等各種領域中的人們所推動。他們肩負著時代的使命感,回顧朝鮮的歷史。他們對於朝鮮儒學史的思考與探索,被後人延展或補足,延續至今。然而,在當時的東亞情勢中所做的研究,是否對史料產生重大「誤解」?這是筆者最初所抱持的問題意識。
該「誤解」的內容如下。
朝鮮儒學思想史被認為在十七世紀發生轉折。朝鮮半島在1592至1636年的四十多年間,受到中國及日本的四次侵略。在那個苦難的年代,經書解釋中出現了與朱子學解釋不同的學說。那些新的解釋被定義為:一部分的儒者為了度過嚴峻的時代,摸索出取代現有朱子學的新思想,而新解釋之產生即為其中一環。
但是,本書對於這樣的定義,將進行如下的再檢討。
首先,考慮到二十世紀前後的狀況,朝鮮半島的知識分子們面臨國家、民族的危機,欲從朝鮮儒學史中找出「近代性」思想的萌芽。他們在過程中,從十七世紀儒者們的著作推導出以下見解:十七世紀儒者認為以往的思想──朱子學──無法度過眼前的危機。然而,儘管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存在此種問題意識,但十七世紀的儒者是否如此?本書擬就此詳細闡明。
為確認其過程,需先行考慮十七世紀朝鮮儒者的時代觀念,他們如何接受東亞當時發生的最大「事件」──「明清交替」,進而如何認識自己的時代使命?當「夷」取代「華」之時,朝鮮儒者是否開始對朱子學抱持懷疑?還是他們反而抱持更大的使命感來進行朱子學研究?本書擬透過分析史料究明此事。
其次,在十七世紀的朝鮮儒學界,異於朱熹(1130-1200)之經書詮釋的新解釋如何出現?新解釋在朝鮮儒學史的意義為何?這些新解釋的作者經過何種過程提出己見?當時的社會如何接受它?本書將分析這些儒者的同儕及政敵的反應,藉此考察他們對於此事的理解。提出新見解的行爲是否意味著對現有權威思想體系的挑戰?又,提出新學說之人是否自視為朱子學的批判者?
朝鮮儒者所生存的世界,與二十世紀前後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東亞情勢大不相同。因此,從西方殖民中尋求救國方法的近代知識分子,和抱持以中國為中心之天下意識的朝鮮儒者,兩者所立定之「為了國家」或「為了天下」的志向截然不同。然而,當殖民地時代的韓國知識分子為朝鮮儒者的活動及作為賦予意義時,卻遺忘朝鮮朝儒者所生存的社會現實與他們的生存方式。
在殖民地時代,韓國的知識分子視奪回主權乃韓國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最優先使命。因此他們無法從朝鮮儒者的視角觀看,也沒有餘裕踏實地考量朝鮮儒者窮極一生究竟追求何物,朝鮮儒學史的內涵與意義到底為何。二十世紀後半出生的筆者,對當年知識分子所背負之沉重的使命感實在難以想像。儘管本書的內容以朝鮮儒學史為主旨,並試圖修正它後來所應有的歷史定位,但是筆者願學習這些知識分子的志向與抱負,並追隨他們,腳踏實地的完成擺在二十一世紀學術界前頭的時代使命。
第三章 朝鮮儒者的信念
即使在以朱子學為治國方針之依據、以朱子學經書解釋為科舉考試標準的朝鮮社會,也存在提出與朱熹注釋相異見解的人,他們有不少人招來物議,最終遭受處罰。這些異於朱熹注釋之作者的登場及對於他們的牽制和批判,一直被理解為,抱持朱子學批判意識的一方被朱子學方所彈壓的狀況。因而產生「朱子學對反朱子學的對立架構」。該架構從兩個對立軸――朱子學的深化研究和教條化vs.對朱子學的懷疑和批判――來說明十七世紀朝鮮儒學史。然而,筆者認為,十七世紀朝鮮儒學史之展開樣態是更為廣闊的,不應該被局限在這兩個對立軸內。
如前所述,作為十七世紀東亞最大「事件」的明清交替,並非可促成批判朱子學意識產生之原因。接下來,下面所要論述的是,異於朱熹經書解釋和見解的著作未必誕生於對朱子學思想的懷疑,以及朱子學研究未必會因深化而走向教條化。
一般而言,研究某個對象到了極為細密的階段後,將產生視野的窄化或受限於刻板印象之可能。然而,研究之際發現思想體系的缺點,因此開始將研究對象客觀化,進行批判性之認識,此種可能性也會同時提高。即使是看起來完美無缺的思想體系,若徹底加以追究,也可能發現其破綻。如同後述,十七世紀朝鮮的朱子學者在研究朱子學的同時,一邊比對朱熹的各種著作,確認朱熹的學說曾歷經數度變化,進而證實朱熹在其各種論述之間,存在著不少矛盾。
承上所述,我們無法從朝鮮朝儒者的研究,就斷定它不會是產生異於朱熹注釋之創見的原動力,也無法單單認為這些研究只有邁向朱子學教條化一途。無批判地信奉,毋寧是對研究對象還未徹底了解時才容易產生的狀況。
再者,擁有數百年經書學習歷史的朝鮮朝士大夫,「只是不斷重複朱熹解釋就能獲得滿足,其中僅有尹鑴、朴世堂等數人對朱熹的注釋提出異見」,這個說法有說服力嗎?
朱子學研究的深化和異於朱熹的經書解釋,兩者皆由朝鮮儒者的信念所生。如果過往朝鮮儒學史研究描繪的架構脫離了這個信念,意味著它還有商榷的餘地。更進一步,若詳細分析朱子學的研究過程及異於朱注之注釋的誕生過程,此二軸――朱子學的深化研究和教條化vs.對朱子學的懷疑和批判――如何產生關聯當可確認。
第一節 朝鮮朝儒者社會的思想基礎
朝鮮儒學史研究的正式展開始於日本殖民時代,其研究基於深刻的反省,以圖究明朝鮮招致亡國之因。除了批判儒者社會輕視實用的傾向,同時也挖掘十七世紀重視實用、實踐的人物,並加以讚揚。但是,以二十世紀想定的「實用、實踐」來評論朝鮮儒學史,真的有意義嗎?如果考慮朝鮮儒者社會的思想基礎,對於輕視實用的反省、對於重視實用的讚揚,其實都與史實有所出入。此種研究方法比起從史實找到教訓,難道不是更近於生硬地套用當時的需求來解讀歷史?
儒者第一義
對於以經學為中心活動及作為的朝鮮士大夫來說,活化經書內容使其成為日常生活實用之物,並非他們關心的中心問題。如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在科舉所測試的,不是法律的詳細知識或徵稅計算等實務能力。此類實務是胥吏和幕友(地方官的私設祕書)的工作,對於官吏的要求是真正的道德能力。」同樣的,朝鮮朝社會向士大夫要求的,也是高道德能力。具體來說,例如宰相治國之事被稱為「燮理陰陽」。意即,作為官僚,最高責任是調和蘊生萬物的陰陽之氣。因此,以陰陽不調和為由要求宰相辭職之事並不少見。《朝鮮王朝實錄》有如下記載:
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溉,以災變辭職。……史臣曰,三公處百僚之上,理陰陽順四時,乃其責也。則其遇災而辭職宜矣。
這是三公負起災害發生的責任而辭職之紀錄。作為記錄者的史臣,比起追究未做好防災準備等具體責任,反倒將沒有完成理陰陽順四時的責任,視為三公應辭職的理由。此種看法在當時是基於普遍的認識。再舉一例,中宗二年(1507年)有如下記載:「以武夫,豈能燮理陰陽,不可久在相位」。就算武官有幾分能力,仍與理陰陽的宰相之位不相襯,此種主張在當時十分具有說服力。
因此,高位官僚如果給出例如「禁止百姓濫採山中枯木」的建議,獲得的反應,比起稱讚他注意細微民生,反倒會引起議論:「當獻可替否,引君當道,糾正百官,則庶職修矣。松木斫伐之禁是有司之事,不足以煩天聽而亦言之。識者譏其不知大體也。」即,高官介入瑣務,反倒成為被批判的理由。
在這樣的社會中,儒者於思考修己治人之際,實用的、具體的業務自然非其所管。儒者不以實用功夫為第一義的態度,不限於政事和經學的領域。以數學的領域為例,「兩班和中人(在兩班之下,身分居於第二階的技術官僚及其家系) 可説都屬於算學研究者,但是兩班的算學和中人的算學有極大的性質差異,有著相互斷絕的傳統。兩班身分的數學家對算學思想十分關心,亟欲認識西算等新的數學知識。相較之下,中人身分的數學家作為專家,對算術自身有極大興趣,追求技法的習得與完成」。無論是哪個領域,兩班士大夫都不認為他們需要竭盡全力去學習「實用的、具體的內容」,這才是一般狀況。
殖民地時代以來,朱子學者的理論展開被批評是無用的空論,而尹鑴、朴世堂等人的經書注釋,卻被認為帶有「重視實踐經書內容於日常生活中」的特徵。接著,此特徵又被定位為朝鮮後期所謂「實學」思想的先驅。舉例而言,朴世堂的如下注釋,被認為是他將王陽明「知行合一」置於念頭,所做出的注釋。
若程子言欲孝者當知奉養溫情之節,及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其不務此而徒欲泛觀萬理,吾恐其如大軍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及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程子認為,欲孝者比起遍知萬理,更需「明確知曉」奉養父母的方法、父母慈愛子女而子女須行孝親的道理。行孝須從身邊事物觀察,即「精確知曉,方為格物」。全句引用程子見解的朴世堂,強調「欲行某事者必要明確知曉它真正重要的部分」。如此觀之,上文中真的可以讀出實踐優先於知識的想法,並與陽明學的「知行合一」做連結嗎?
此外,朴世堂還提到,學習者讀經書之目的,是為了知道聖賢所示之準則並效法它。
聖賢之垂訓立言,無非為後世學者,示之以準則,使知其法,而今乃為不可名不可學之說,以釋其義,為後學空談無益之侈觀。不知其可乎否也。
因此,他未曾說過談論人之性是脫離實際的理論,還列舉程子對性之言論並說:
凡此數說者,其於開示性體為循率之尺度準則之意,略未見其有所發明,但覺其窈冥幽默莫可指擬,使讀者芒然無所措其思慮者,深為可疑,所以不敢求其必合。
朴世堂沒有說無用於日常之說非古之道,也未說因此而不需要它,但是他指出,程子之說未能明示性的本質。朴世堂的目標在於,賦予率性(順從天性而行)的尺度、準則,使其實際可行。
如果將「對於經書道理之理解」和「個人於現實中實踐經書道理」,想成前者是本體而後者是機能,此處所引用的朴世堂注釋重點在於本體而非機能。若從根本是「體」、機能是「用」來看,朴世堂的重點可說是以「體」為主。「用」不是沒有意義,但讀經書是為了「體」(理解道理),不是一個琢磨於「用」(實踐道理)的過程。比起從日常生活中自己的周遭尋求實踐孔子之言的方法,朴世堂解釋經書的方向,更著重於相信修己之身能實現聖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