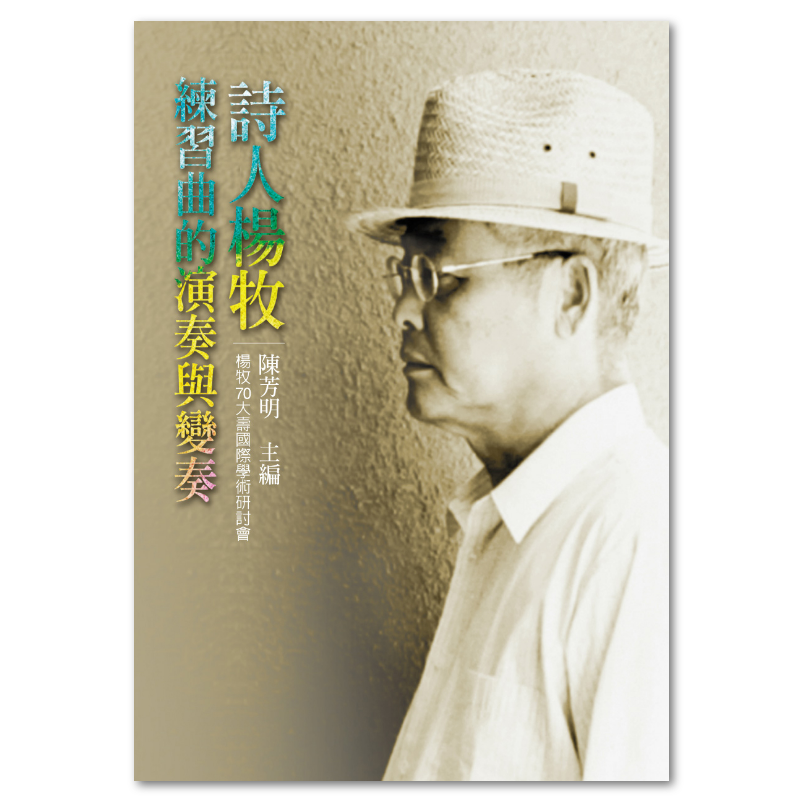練習曲的演奏與變奏:詩人楊牧
出版日期:2012-06-01
主編:陳芳明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32
開數:25開(21×14.8cm)
EAN:9789570839968
系列:聯經評論
尚有庫存
一行詩,一段文字,一則論述,一首譯詩,
都可視為生命裡有機的內在連結。
每種文體,每種技藝,形成詩人靈魂的巨大象徵。
楊牧孜孜不倦致力一個詩學的創造,
進可干涉社會,退可發抒情感;
兩者合而觀之,
一位重要詩人的綺麗美好與果敢氣度,
儼然俯臨台灣這海島。
詩人楊牧,超過半世紀以上的歲月,投身於詩、散文、評論、翻譯的經營,擘造可觀的文學知識,為戰後世代構築動人心弦的詩藝與語藝。詩學的累積,僅從單一的詩集或散文集,可能不易窺其規模;但是,經過五十年的時間延續,他的文字實驗與實踐,已經形塑成為一個時代的重要風景。
本書為研究楊牧文學成就之合集,結合國內外多位學者之研究成果,一窺楊牧文學抒情的奧秘。楊牧的藝術成就,無可否認,必然在文學史中熠熠發光。
編者
陳芳明
作者
奚密/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東亞語文系和比較文學系
賴芳伶/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
郝譽翔/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曾珍珍/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蔡明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上田哲二/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
張依蘋/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
許又方/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楊照/知名作家、《新新聞》周報總主筆
陳義芝/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石計生/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鍾怡雯/元智大學中語系
主編:陳芳明
從事歷史研究,並致力於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陳芳明,1947年出生於高雄。畢業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並於美國華盛頓州州立大學歷史學系取得博士學位。他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後赴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任教,同時受委籌備、成立該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目前獲聘為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以顯其治學和教學上的卓越成就。
陳芳明創作逾三十載,其編著的作品影響深遠,例如主編《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余光中跨世紀散文》、《練習曲的演奏與變奏:詩人楊牧》等;其政論集《和平演變在台灣》等七冊見證了台灣社會的歷史變遷,而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革命與詩》、《深淵與火》、《邊界與燈》,在在呈現了高度的文學造詣。
在文學創作之餘,陳芳明的詩評集《詩和現實》、《美與殉美》,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現代主義及其不滿》,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建立新的研究典範。
2011年,陳芳明終於完成歷時十二載的《台灣新文學史》,為全世界的中文讀者打開新的台灣文學閱讀視野。
1.楊牧:臺灣現代詩的Game-Changer╱奚 密
2.楊牧「奇萊」意象的隱喻和實現——以《奇萊前書》《奇萊後書》為例╱賴芳伶
3.抒情傳統的審思與再造——論楊牧《奇萊後書》╱郝譽翔
4.譯者楊牧╱曾珍珍
5.論葉珊的詩╱蔡明諺
6.鳥瞰的詩學——楊牧作品中的空間美學╱上田哲二
7.一首詩如何完成——楊牧文學的三一律╱張依蘋
8.讀楊牧《鐘與鼓》及其《詩經》研究╱許又方
9.重新活過的時光:論楊牧的「奇萊前後書」/楊照
10.住在一千個世界上——楊牧詩與中國古典/陳義芝
11.生死愛慾的辯證——楊牧詩文的協奏交響/陳芳明
12.孤獨的幾何:楊牧詩的數學美學/石計生
13.文學自傳與詮釋主體——論楊牧《奇萊前書》與《奇萊後書》/鍾怡雯
抒情的奧秘——「楊牧七十大壽學術研討會」前言/陳芳明
一行詩,一段文字,一則論述,一首譯詩,都可視為生命裡有機的內在連結。每種文體,每種技藝,形成詩人靈魂的巨大象徵。楊牧孜孜不倦致力一個詩學的創造,進可干涉社會,退可發抒情感;兩者合而觀之,一位重要詩人的綺麗美好與果敢氣度,儼然俯臨台灣這海島。
從十六歲出發的年輕詩人楊牧,在今年臻於七十歲。超過半世紀以上的歲月,他投身於詩、散文、評論、翻譯的經營,擘造可觀的文學知識,為戰後世代構築動人心絃的詩藝與語藝。詩學的累積,僅從單一的詩集或散文集,可能不易窺其規模;但是,經過五十年的時間延續,他的文字實驗與實踐,已經形塑成為一個時代的重要風景。
早期寫詩時,他還在摸索自己的美學途徑,追尋的痕跡遺留在最初的《花季》與《水之湄》。但是,到達《燈船》時,楊氏風格隱然可見。同時期完成的《葉珊散文集》,與他的詩行相互照映,一時迷醉多少年輕讀者。楊牧用力於詩最鮮明之處,莫過於他的敘事技巧,在每首詩背後往往暗藏一個故事。他擅長使用懸疑與推理的手法,讓象徵語法放在前面,使一則傳說或事件隨著詩行演進而巍巍浮現。正是他的敘事傾向,截然區隔了他與同世代詩人的意趣。
1974年是他進入豐收時期,三首傳誦甚廣的詩作〈林沖夜奔〉、〈瓶中稿〉、〈秋祭杜甫〉次第發表。尤其林沖角色與性格的塑造,透過山神、風聲、飄雪的交響聲音,構成一首速度極快的流動詩,使夜奔的動作歷歷在目。他以詩的形式表現說故事的技巧,在現代詩人中可謂無出其右者。在詩史上,一位詩人獲得注目與肯定,無非是依賴他所創造的語言。他擅長動用猶豫、遲疑的語氣釀造氣氛,但是詩的內部已經埋藏一個確切答案。這種文字藝術,也許受到中國傳統話本的影響,但是他也從西方戲劇裡接引火種。最重要的是,他有個人獨特的語言表演範式,選取的文字有時是白話,有時是典雅的文言文。他勇於嘗試把久已不用的古字置入詩中,為的是試探古代漢語的生命力。凡是經過他再次運用,把恰當的字安放在詩或散文的恰當位置,文字的魂魄便再度回到人間。
他的詩文發生明顯重要轉折,應是始於1970年代初期的《年輪》。文字不僅注入現實關懷,而且也對戰爭與性的主題進行質疑。他觀察遠在中南半島激烈爆發的越戰,也目睹他同一世代的美國青年被徵召投入戰場。戰爭是人性貪婪的延續與中止,性是生命的上升與下降。在愛慾生死的探索中完成後,他的生涯進入三十歲年代,也同時展開在海外任教的旅途。遠離自己的故鄉,在陌生土地開始體會歲月如何趨於成熟。他的散文《柏克萊精神》、《探索者》、《山風海雨》,終於表現出精神朝向故鄉花蓮回歸的慾望。既像回憶錄的文體,又像絕美藝術的追求,使他整個生命產生一種永恆的土地認同。然而,那又不只是一冊回憶,其中除了不斷挖掘記憶深處的啟蒙與成長經驗,他致力重建自己的人文價值與思想結構。在真實與虛構之間,他為一個世代的知識份子留下擁抱、關懷、批判、憤怒的蛛絲馬跡。就在這段時期,詩集《北斗行》、《禁忌的遊戲》、《海岸七疊》、《有人》先後出版,激越卻圓融的聲音於焉誕生。其中的長詩〈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果敢注視台灣社會的族群議題,在一位青年人身上看到台灣母親與中國父親的兩種文化交會,內在的衝突、矛盾、和諧躍然詩行之間。
楊牧詩風從此進入新的階段,台灣也開始進入1980代。微熱而活潑的島嶼,以鮮明的形象降臨在他的詩行。他探問的不只是時間,對生命之體悟與情愛之求索,較諸三十歲年代的猶疑怔忡有了更為確定的態度。歲月開始進入後中年時期,或者說,秋熟的季節緩緩逼近之際,他對文字的掌握更加純粹熟練。這可能是迎接黃金收割時期所展現的一份自在與自信,詩壇開始有人默默議論,承認他的詩頗有豁達氣象。
確然如此,他對自己的文學志業逐漸朝向重整收束的階段。從前的回憶散文系列,總結成為《奇萊前書》。進入新世紀時,他又向故鄉交出一冊《奇萊後書》。這時代一顆最佳心靈的塑造,都在抑揚頓挫的節奏中次第完成。《前書》是童年到青年的成長散文,他的知識啟蒙,朋輩過從,師長教示,都以迂迴方式帶出一顆灼熱的詩之魂魄。《後書》指向他在海外的漂流與停泊,知識的輝光,人性的洞澈,在幽微圓潤的文字裡琢磨提煉。美文之所以美,已非文字的鍛鑄而已,還溢出書籍之外,呈現他與世界訂下溫暖、和解的契約,使散文的重量恰如其分地置放在擾攘的人間。
柔軟而馴良的詩人,對於奇萊山有一種無可言喻的鍾愛。當這座山的名字出現在文壇時,所有的讀者都能感受他的強烈暗示,他的生命意義確然在故鄉土地得到安頓。在同一時期集結的詩作《完整的寓言》、《時光命題》、《涉事》與《介殼蟲》,也以更為隱晦的方式傳遞一個信息:他已不再以熱情的語言看待世界。因此有人議論他的詩越來越晦澀。事實上,晦澀僅是一種障眼法,他的句型語法更能放射歧義的抒情。在世紀之交完成的〈和棋〉,表面上是一場虛擬的棋賽,在陽光樹蔭下進行一場自我詰問。生命臻於峰頂之際,所有人事情愛並沒有任何輸贏,整首詩點出他看待人間時自有一份寬容。
他的文學整頓儀式,並非只集中在詩與散文。從《柏克萊精神》以降所探索的知識追求與學術議論,他總結成《隱喻與現實》、《人文蹤跡》、《掠影急流》,相輔相成地積極定義何謂人文精神。這種精神,與他的詩中抒情、散文言志的風格,可謂同條共貫。
一位詩人的藝術成就,也許不能限制在詩的領域去理解,還應延伸到散文、評論、翻譯作整體性的評估。一行詩,一段文字,一則論述,一首譯詩,都可視為生命裡有機的內在連結。每種文體,每種技藝,形成詩人靈魂的巨大象徵。楊牧孜孜不倦致力一個詩學的創造,進可干涉社會,退可發抒情感;兩者合而觀之,一位重要詩人的綺麗美好與果敢氣度,儼然俯臨台灣這海島。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決定以連續三天(9月24日至26日)的詩朗誦活動與學術討論,來迎接楊牧的七十大壽。會議規模極大,尚不足以概括他畢生建造起來的詩學格局。挖掘他,分析他,或許能窺探他抒情的奧秘亦未可知。時間不盡不止地跨越與消逝,可能催老了一位詩人的肉體,但是他留下的藝術業績,無可否認,必然在文學史中熠熠發光。
楊牧「奇萊」意象的隱喻和實現──以《奇萊前書》《奇萊後書》為例/賴芳伶(節錄)
一、前言:山海原鄉
把創造力和相關潛在皆訴諸神話傳說,毋寧是天地給你的賞賜,何況那並不只是一時的,是恆久,而且廣大,無限,支持著你探索,突破的勇氣。縱使在你遠遠離開那原始天地,長久之後,還存在你心神之中,即是惟一的自然界,甚至在闊別之後,依舊不改。自然於是存在你的思維和想像,並因為那思維和想像變化無窮,與你維持著強烈,略帶靦腆的秘密關係。
──《奇萊後書》〈抽象疏離 上 頁216〉
花蓮的山海自然與楊牧一直維持著強烈,靦腆的秘密關係,使他把潛在的創造力接合到相關的神話傳說,從而構築一抽象的總體象徵。楊牧所有詩文中的自然生息,一方面綴連敘事的背景,同時轉化成象徵修辭,生發出無窮的詩的蘊藉。無論是讀書或觀察得來的生態知識,他所關切的都不僅止於具象或昇華後的大自然,而是考量到「如何將其融通於人文價值」。一如雪萊“To a Skylark”詩中的雲雀,濟慈“Ode to a Nightingale”中的夜鶯,牠們的啼聲成為詩人抒發情感的依托,指出詩人思維運作,情感嚮往的方向。屬於台灣百岳群的「奇萊」山系,就在楊牧的家鄉花蓮,嵯峨盤踞,其偉岸奇詭的形象,久已成為他抒發情感的依托,提供他的作品排比典故的空間,更為他指示詩藝與生命嚮往的方向。
2003年,楊牧將八○年代中開始提筆,至1997年為止的散文創作:《山風海雨》(1987),《方向歸零》(1991),《昔我往矣》(1997),重新合為一帙,命名:《奇萊前書》(2003)。六年後,楊牧再以「奇萊」之名,完成了《奇萊後書》(2009)。觀此兩本詩文合體鉅著,前後寫作時間貫穿二十餘年,同樣意蘊幽深,前者屬一早期文學自傳之結構,旨在「探索山林鄉野和海洋啟迪,追尋詩,美,和愛的蹤跡,自我性格無限的猶疑和執著,並於回想中作荒遼幻化的前瞻,思維集中,風格刻意,一一在多變屢遷的散文筆路下展開。三書自成系列,脈絡延伸。止於一秘密作別的時刻,合帙為《奇萊前書》」。《奇萊後書》出版時序與內容結構可與《前書》銜接呼應,但楊牧強調「這不是一本回憶錄」,似乎已「告別原初之山林與海洋,置身多樣的人情和知識之間,惟詩的執著始終不變」;如他所說的,此作依然「在風雨聲中追求愛與美之恆久,感受學術,倫理,與宗教等及身的信仰和懷疑,如何通過我們對文字的單一體驗,於修辭比類,章句次第,亦隱亦顯的象徵系統中發現真實。」
誠然《奇萊前書》止於一秘密作別的時刻,而《奇萊後書》亦無意去指涉特定的人事,乃是以一種楊牧自己喜歡的方法,擷取若干他以為有意義的人生經驗,尤其是深深影響到他生命形塑與詩藝表現的人物,典故。儘管文章中的時間和地點皆是跳躍的,可是楊牧自述「核心的概念」卻一致,也許是想藉此分析自己,「到底在人生過程中有哪些關鍵之點?以及自身的感觸,生命的印記」等等。本論文希望能明悉其核心概念所指的「詩的執著」為何,如何?以及有哪些重—要的人生關鍵之點?若以《奇萊前書》之前已有三書定名為起源的思索,結合其一再援引「奇萊」意象直至《後書》來看,楊牧似乎有意創構一種以「奇萊」為主的隱喻和象徵體系,以之修辭比類,章句次第,欲於亦隱亦顯的象徵系統中發現真實。沿著這樣的線索,我們嘗試如他所期許的,以詩的形式,進一步探究其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奇萊」究竟為何?其中是否隱藏著甚麼深邃的開展與意涵,提供詩人在有限的生命中,屢屢衍生不絕的創作之力與迴環反覆的深情追尋?
二、「奇萊」的史源地緣
根據《花蓮縣志》記載:「花蓮古稱『奇萊』。稱花蓮始見沈葆楨奏疏,前此無聞焉。故老云,花蓮溪東注,其水與海濤激盪,紆迴澎拜,壯之以其容,故曰洄瀾。後之人諧為花蓮,至今沿襲之,知洄瀾者,百無一二焉。」據此可見,花蓮的兩種古稱有「奇萊」和「洄瀾」。稱「洄瀾」者,約是始自清代漢人到花蓮開墾之時。但稱「奇萊」,究竟始自何時起?
較確信的說法應是,「奇萊」兩字,乃取自世居此地原民族之族名:Sakizaya的諧音。當時外族接觸Sakizaya人,由於語言不通,加上發音不清楚,因此就誤把Sakizaya當作地名來呼之。阿美族人稱「Sakizaya」人為「Sakiraya」,於是用「Sakiraya」中「ki-ray」兩個音節,來稱撒奇萊雅人居住之平原為「奇萊平原」(位於花東縱谷的最北邊,北起三棧溪口,南迄木瓜溪口,北方為立霧溪三角洲平原,南連花東縱谷平原,西鄰中央山脈,東向太平洋;南北長約19公里,東西寬8公里,面積約90多平方公里,成弧形),而位於附近中央山脈的高山也稱作為「奇萊山」。另外,包括西班牙、荷蘭、清朝、日本、中華民國的地圖與文獻均予沿用此名。
而如今所稱之「奇萊」,係指奇萊山連峰,包括奇萊主山、奇萊北峰、卡樓羅山、奇萊南峰、奇萊裡山等,鄰近的屏風山、南華山等亦可同列。奇萊山群位於花蓮縣秀林鄉與南投縣仁愛鄉交界,大多隸屬太魯閣國家公園。奇萊山群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與合歡群峰隔著中橫遙相對峙。其三千公尺的稜線上有美麗的箭竹草原,從此往北可看到北一、北二段。往南視野可達玉山群峰。奇萊群峰主要有奇萊主峰以及南北兩座副峰,主峰標高3560m,三等三角點,從北方望去,基盤狀闊,山形穩重;北峰標高3605m,一等三角點,高過主峰,是中央山脈排名第八的高峰,名列臺灣十峻之一。
早在1636年,西班牙統治的文獻紀錄上已有「撒奇萊雅族」。當時,西班牙統治臺灣北部及東北部,在此區域劃分三省,其中即包含了撒奇萊雅族居住地。1638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探險隊至臺灣東海岸探尋金礦,得知撒奇萊雅居住地出產金礦,因此派兵進入與撒奇萊雅族多次衝突。清領期間,撒奇萊雅族取得奇萊平原領導地位。為了保衛領域,與清軍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1878年,噶瑪蘭族聯合撒奇萊雅族對抗清兵,即著名的「加禮宛事件」,撒奇萊雅的主要活動中心——達固湖灣部落(今慈濟醫院至十六股一帶)被火燒焚燬。為避免被清軍報復滅族,撒奇萊雅族開始流離隱居他族,從此自歷史紀錄中消失。日本統治時期,將臺灣原住民分類,撒奇萊雅族人對昔日衝突受創記憶刻骨銘心,選擇隱姓埋名,被歸為阿美族。依地理區分為奇萊阿美族。
楊牧《奇萊前書》〈他們的世界〉所說的「阿眉族」分佈在台灣東部的山地和海邊,從立霧溪口延伸到卑南溪,依居住地區又有恆春阿眉、卑南阿眉、海岸阿眉、秀姑巒阿眉;他小時候逃難誤入的山村,應該是秀姑巒阿眉部落,多年以後離開花蓮還無法忘懷,而覺得「他們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頁57)
另外,「花蓮」舊時亦有其它不同名稱:西班牙人於1622年在立霧溪、新城一帶採砂金,將花蓮地區稱為「哆囉滿」(Turoboan);後來又有「崇爻」(以前住在平地的阿美族稱住在中央山脈的泰雅族人為崇爻,意思是猿猴爬樹很敏捷)、「祈來」(應是取自「奇萊」之音)、「花蓮港」等稱呼。
從以上歷史、地理和族群大致溯源,《奇萊前書》與《奇萊後書》所運用的「奇萊」意象,確有其地誌書寫的深刻意蘊,隱含著社會,文化,與文學的力量,從中寄寓了作者的情感認同。至於「前後書」的命名,或如楊牧受訪時所言:「有一次在一個演講會,有人問我,有『前書』,那麼有沒有『後書』呢?後來我想想這個idea不錯,有了所謂的〈提摩太前書〉,也就有〈提摩太後書〉。」故結合兩者來看,「前後書」除指出版時間的先後外,最重要的應該是一以貫之的「奇萊信仰」,亦即以台灣花蓮為現實落點的自然萬象,並依此擴展延伸。
有關奇萊種種敘寫,很容易讓我們繫連到《一首詩的完成》裡的〈大自然〉,該文非常重視大自然對一個詩人的啟迪和影響:
我們崇尚大自然的堅定和美,那接近永恆的能量。……我們膜拜大自然,豈不是因為它那堅定的實質存在嗎?而當我們全面理解了大自然的力,孳孳勤勉以生命的全部去模仿它,藉我們的藝術之完成,企及那堅定的實質,說不定就可以同意東坡所說的,「我」竟然也是無盡的,長存於藝術的整體完成之中。所以大自然是我們的導師,雜然賦流形是它落實的示範。山的峻拔,海的浩瀚,江河的澎湃,溪澗的幽清;或是飛雲在遠天飄動,時而悠閒時而激盪,或是草木在我們身邊長大,告訴我們榮枯生死的循環也還有一層不滅的延續的道理。
可知詩人所創作的「詩」,如果能夠孜矻模仿大自然的力與美,從中領悟榮枯生死的循環道理,那麼詩人的藝術生命也就可以像大自然一樣接近永恆。再看以下的敘述:
我們有時面對大自然會感到恐懼,或許正因為我們太依賴著它的愛,像孩童耽溺著父母親的保護和扶持,並因為自覺那愛存在,而憂心忡忡,深怕有一天將失去那愛,因為我們犯了不能原宥的過失而失去那愛。
對我們扶持保護有如父母的大自然,的確有時是會令人恐懼的,尤其是在我們犯了不能原宥的過失,會深怕有一天失去那愛。這種心情在楊牧的〈俯視〉〈仰望〉這兩首詩中,表現得很細膩深澈。這兩首潛在攸關花蓮風土人情的山水詩,重現在《奇萊後書》末篇的〈中途〉,彷彿穿透悠遠的時間空間,見證詩人起伏跌宕的生命軌跡,而衍生出各種榮枯循環、生死輪迴的自然奧義。
從奇萊而大自然而生命的初始緣起,其間經緯著楊牧最深刻的,詩藝與生命的信仰。他曾在《介殼蟲》的〈後序〉中,說:
對華滋華斯而言,人之初生,即睡眠和遺忘的開始:嬰兒呱呱墮地表示他正從有知多識的前生睡去,僅保留殘存的記憶在童年階段閃爍發光,與神異世界的性靈交接,互動,但也勢必因今生歲月的推移和折損,因肉體成長,接受新知識,而逐漸將那些遺忘淨盡,甚至失去孩提曾經擁有過,親密的少許,我們慣習的「天真」,終於蕩然無存。
這種觀念,似乎把大自然當作母體,而「我們(孩子)」因為逐日的成長反而離那母體愈來愈遠。秉持如此的信念,《奇萊前書》「想到試探以通過童年追憶去接近永恆的途徑」,所書寫的童稚記憶與少年憧憬,無非強調「天真」的心靈和視野,實為一切藝術創發的源頭。所以緬懷「童年」樂土,家鄉故園一些無法忘卻的景致,人物,事件,當然是楊牧創作重要的生機,但卻不是唯一的生機。這當中還無時或已穿梭著成長的喜悅,甜美,災難和憂傷,讓他知感兼具地儆醒著自己的生命責任,詩人的使命。
《介殼蟲》「後序」之後楊牧繼續擴充思索:「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去日的自己」,指的是久違遺忘的純真,這或許較偏向時間;而《奇萊後書》的〈設定一個起點〉,應該時間空間兼而有之;縫合〈俯視〉立霧溪、〈仰望〉木瓜山的〈中途〉,則引現一鬢髮霜雪的詩人,如何在人生旅程的中途,返顧沉思,前瞻未來。「前後書」表面上好像都在回望過去,可是就在楊牧構築某種回歸的大象徵的同時,卻又不斷指向綿綿不已的未來,使未來和過去就在此際當下,渾融成一個相互辯證的圓,迂迴傾訴所有的終點無非就是起點。故楊牧說:「起點和終點同時存在於我自己的心,走到那裡跟到那裡。」(《奇萊後書》頁5)
走到那裡跟到那裡,可不是?《介殼蟲》「後序」最後一段提起荷馬(Homer,約紀元前9世紀~8世紀),若以繫年(2006)來看,詩人所思似乎正在為未來的《奇萊後書》(2009)盤算著。設定一個起點,終點,過程,莫非暗暗指向生命與文學的綺色佳(Ithaca)?
入冬以來,斷斷續續整理著這一本詩集,有時也在恍惚間以為是重複著過去已經做了的事,正確和不正確的執行,修正,但有些地方就由它去吧。從前如此,現在也應該就是如此。然而,冥冥中又感覺到心神有一種異乎平常的負擔,可能是甚麼思維的累積,揮之不去,再三出現如荷馬史詩裡鍥而不捨,勇敢的武士,被我這個最投入,一路尾隨已經到二十一世紀初葉的末代讀者所揶揄。
荷馬史詩裡鍥而不捨,勇敢的武士,為何再三出現讓他揮之不去,成為思維的累積,或自我鏡像的揶揄?為何楊牧說自己是最投入,一路尾隨已經到二十一世紀初葉的荷馬的「末代讀者」?是因為那年代堙遠的,美與哀傷的榮光與價值觀,已逐漸塵埋冰封?而自忖身處當代的自己,正如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般「以詩涉事」,猶似史詩中的武士,冒險犯難,以劍屠龍,意圖拯救人間亡失的公理正義,以及如此之相似的出發戰鬥,飄流回歸?
這些與奇萊相關的聯想──自然山海,族群衝突,童真性靈,神話信仰,英雄史詩…,或許將點滴匯聚成我們探索楊牧的「奇萊」意象,不可或缺的隱形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