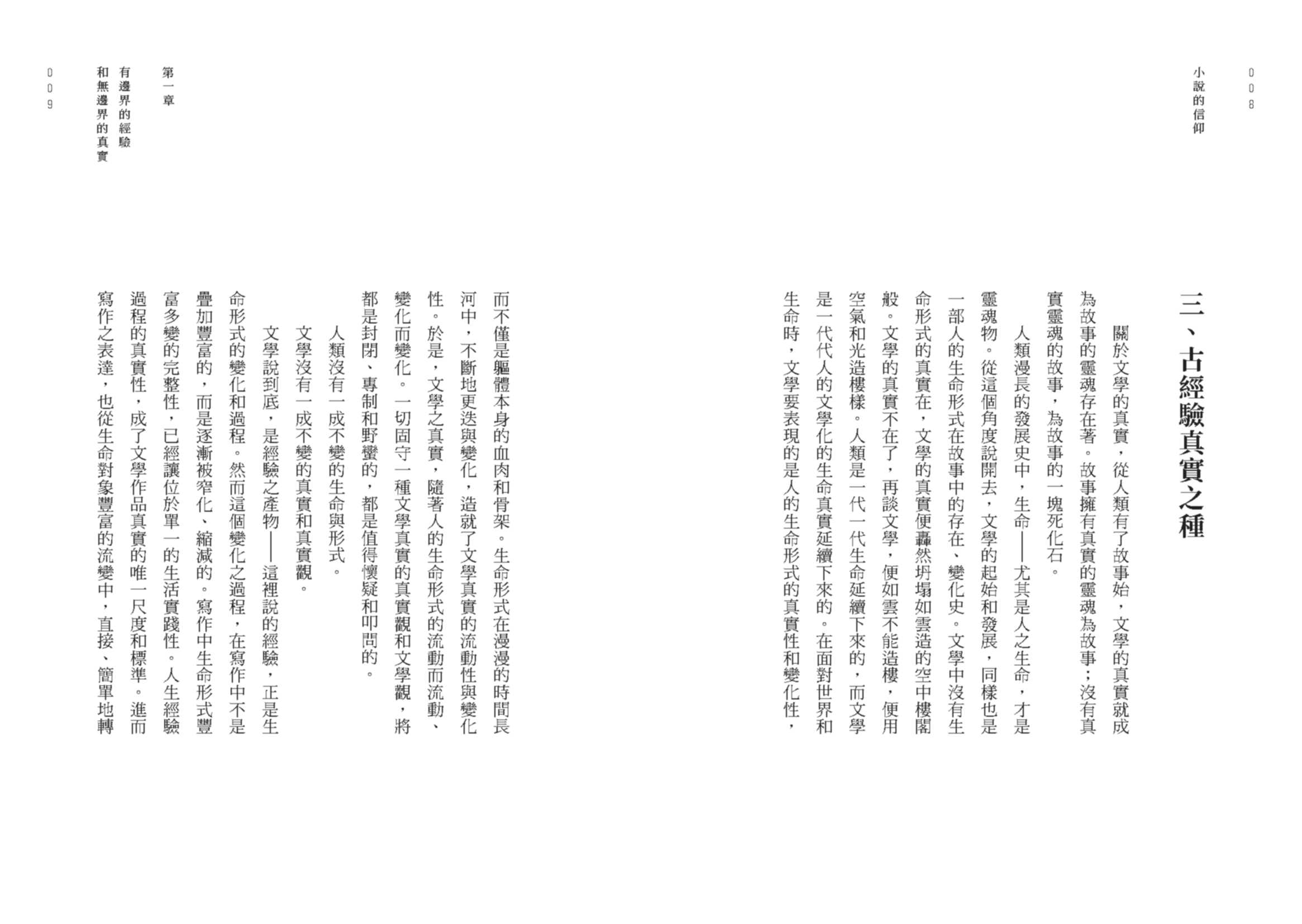小說的信仰
出版日期:2024-03-14
作者:閻連科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80
開數:25 開,長 21 × 寬 14.8 × 高 1.5 cm
EAN:9789570872255
尚有庫存
真實是小說的信仰,一如基督只有腳釘流血、背負十字才可為基督樣。
當代小說大師閻連科,數年深厚功力累積迸發,辯證文學的真與不真。
「從《發現小說》到《小說的信仰》,這兩本近乎理論的文學隨筆,應該是我更看中的寫作。讀這些,也更能從中瞭解我的寫作為什麼是這樣而非別的樣。」
──閻連科
真實的概念是流動的,並不侷限於一般人所理解的經驗真實。人類的生命經驗與知覺是有邊界的,而真實是沒有邊界而流動的,既可建立在生命經驗的基礎上,又可建立在不可經驗而只能依靠想像感知的基礎上,隨著生命形式的流動而流動、變化而變化。文學不僅為經驗而存在,更為超越經驗邊界的、只可想像感知的真實而存在。
除了一般讀者所理解的「經驗真實」之外,循歷史之脈而下,閻連科探索了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無法驗證的真實」、「不真之真」、「超真之真」和「反真實」,也深入討論小說形式之於真實性等等問題,並且回到當代,對新世紀的文學真實將如何突破發出探問。
這位被譽為「中國最接近諾貝爾獎」的文學大師,在本書中將細細解剖小說創造之「靈魂」和「信仰」,並云:「文學不僅要為經驗而存在,更要為超越這種經驗邊界的只可想像感知的真實而存在。」
閻連科究竟如何思考文學創作、被哪些作品影響,又如何將自身理論實踐於小說之中?
中國現代最重要的作家,四十年寫作生涯集大成之精華,熱愛文學的讀者必該一讀。
作者:閻連科
1958年出生於河南省嵩縣,是最具影響力的華語作家之一。
曾先後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馬來西亞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獎;2012-2016年三次入圍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和長名單;2014年獲捷克卡夫卡文學獎;2016年獲香港紅樓夢文學獎;2020年獲世界反飢餓組織圖書獎;2021年獲美國紐曼文學獎和英國皇家文學協會終身成就獎;2022年獲韓國國際和平文學獎。
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炸裂志》、《日熄》、《速求共眠》《心經》等;中、短篇小說集《為人民服務》、《聊齋本紀》等15部;散文、言論集《聊齋的幃幔》等12部;另有【閻連科文集】17卷。其作品在全世界被譯為30多種語言,出版外文作品200餘部。現服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教授、作家和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第一章 有邊界的經驗和無邊界的真實
一、真實是小說的信仰
二、從一句話說起
三、古經驗真實之種
四、人的經驗對神、仙、妖、異的真實取代
五、可實施、感知經驗對小說的最終統治
六、被窄化、限制的文學經驗與真實觀
七、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真實在哪裡?
第二章 從真實到不真之真
八、真實與真實性
九、無法驗證的真實
十、不真之真
第三章 超真之真與反真實
十一、超真之真
十二、現代小說中的超真之真
十三、反真實
十四、反真實與真實之經驗
第四章 形式與形式的真實性
十五、形式的真實性
十六、形式的時空與真實性--以「美國三部曲」、《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及《親和力》為例
十七、形式中的時空錯置與真實性--以《藍鬍子》、〈竹林中〉和《蘿莉塔》為例
十八、後設小說形式的真實性--以《項狄傳》、《寒冬夜行人》和波赫士為例
十九、多元形式和通向真實的路
二十、尾聲
第一章 有邊界的經驗和無邊界的真實
一、真實是小說的信仰
真實是小說的信仰,一如基督只有腳釘流血、背負十字才可為基督樣。
二、從一句話說起
「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
這句話不是事實,是真實;不僅是真實,而且隱含著敬拜和信仰。緣此,給我們帶來的兩個問題是:
一、每一位讀者都明白這句話是違背經驗邏輯的,都明曉太陽不會被人坐在屁股下,而是永遠覆蓋在人的頭上或身上,可為什麼沒有讀者去追究這個違背常識的邏輯呢?
二、太陽在人類的文化象徵和隱喻--在整個世界內,太陽都是文化至高的神聖與隱喻,如但丁在《神曲》中,把太陽喻為上帝樣。而也恰恰因為是這樣,這句話呼應了人們內心伏埋的敬拜與反敬拜的共鳴,獲得了超越日常經驗的反經驗的真實性,緣此那種反經驗的文學之真實,便如同人在碼頭上,能看到碼頭一樣日常、真切和實在。
三、古經驗真實之種
關於文學的真實,從人類有了故事始,文學的真實就成為故事的靈魂存在著。故事擁有真實的靈魂為故事;沒有真實靈魂的故事,為故事的一塊死化石。
人類漫長的發展史中,生命--尤其是人之生命,才是靈魂物。從這個角度說開去,文學的起始和發展,同樣也是一部人的生命形式在故事中的存在、變化史。文學中沒有生命形式的真實在,文學的真實便轟然坍塌如雲造的空中樓閣般。文學的真實不在了,再談文學,便如雲不能造樓,便用空氣和光造樓樣。人類是一代一代生命延續下來的,而文學是一代代人的文學化的生命真實延續下來的。在面對世界和生命時,文學要表現的是人的生命形式的真實性和變化性,而不僅是軀體本身的血肉和骨架。生命形式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中,不斷地更迭與變化,造就了文學真實的流動性與變化性。於是,文學之真實,隨著人的生命形式的流動而流動、變化而變化。一切固守一種文學真實的真實觀和文學觀,將都是封閉、專制和野蠻的,都是值得懷疑和叩問的。
人類沒有一成不變的生命與形式。
文學沒有一成不變的真實和真實觀。
文學說到底,是經驗之產物--這裡說的經驗,正是生命形式的變化和過程。然而這個變化之過程,在寫作中不是疊加豐富的,而是逐漸被窄化、縮減的。寫作中生命形式豐富多變的完整性,已經讓位於單一的生活實踐性。人生經驗過程的真實性,成了文學作品真實的唯一尺度和標準。進而寫作之表達,也從生命對象豐富的流變中,直接、簡單地轉化成了唯一的人和人的生活經驗。換句話說,文學的資源,不再是諸多生命形式豐富多彩的流變、振盪和更替,而是僅僅停留在人的可實踐的生活經驗上。如此每每翻開當下成千上萬的文學出版物,幾乎所有的作品,都近乎以相同的人生經驗,和相同的故事方式,去予以小說的供給和展開。作家幾乎就是純粹生活經驗的搬運工,其變化不過是包裝箱的大小、形狀之不同。打開這些包裝箱,除了一疊一疊人生經驗的更迭和堆砌,幾乎連花樣翻新的一點可以想像、但卻不能實踐的生命經驗都難看到。文學所慣常表達的,是作家的經驗之鏡子,寫作剛好可以映照作家個體和他與社會聯繫的某部分的經驗和可能。如此文學不僅成了那一部分生活經驗的對應物,而且文學的生命與真實,也被這部分可實踐的生活經驗所決定。
至少幾十年的中國文學大體為這樣。
至少當下中國文學中相當一部分、甚或絕多的寫作是這樣。
在這兒,不是說文學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觀念、意志讓它不得不這樣;而是說文學發展的內在力量,在驅動文學不得不這樣。是這種內在的力量,在驅動世俗、日常的生活經驗,逐步替代著豐富、寬廣的生命經驗;單純的經驗實踐性,在替代文學想像的真實性。如此我們不得不疑惑和省思,文學為什麼要如此傾盡所有地討好可實踐的生活經驗呢?可兌現、實踐的人生經驗,是如何完成了對文學的絕對統治呢?而在人類的生命經驗中,人類最普遍、恆久的可實踐經驗又是什麼呢?它對文學的真實有什麼影響和決定性?
最普遍、恆久的生命經驗是吃、穿和欲望。
從這個角度去考看,西元前七五○年前後荷馬行吟《伊里亞德》的一開篇,吃就首當其衝地出現在讀者面前了:「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憤怒--/他的暴怒招致了這場凶險的災禍,給阿開亞人帶來了/受之不盡的苦難,將許多豪傑強健的魂魄/打入了哀地斯,而把他們的軀體,作為美食,扔給了狗和兀鳥……」原來《荷馬史詩》這部人類最早的傑作,雖然幾乎吟唱的多是神和非人的英雄們,而荷馬竟也不敢忘記,人的最基本的生活經驗--吃和穿在神與非人英雄那兒的必須和存在。在宙斯謀畫的特洛伊戰爭中,他差遣「夢幻」去通知神阿特柔斯的兒子--非人的英雄阿伽門農,去攻打特洛伊城池時,「阿伽門農從睡境中甦醒,神的聲音/迴響在他的耳邊。他直身坐起,套上/鬆軟、簇新的衫衣,裹上碩大的披篷/繫緊舒適的條鞋,在閃亮的腳面/挎上柄嵌銀釘的銅劍,拿起/永不敗壞的王杖,祖傳的寶杖。」原來吃穿在神和非人的英雄中,是那麼的微不足道,近可忽略,然而詩人卻從未忘記過對它及時地書寫和交代。只不過神們的飲食是瓊漿玉液,而人的飲食是粗茶淡飯而已;只不過非人的英雄穿的是「碩大的披篷」,而普通人的穿是「草衣遮身」罷了。
來到人類更早的《聖經》中的〈創世紀〉,神創造了天地,但在沒有造人時,吃--食物便先自被神創造了。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它們作食物。」而當人在伊甸園中出現了,「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後,人「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了。--原來,人類最早的人生經驗--最原始的吃穿,無論任何故事憑藉任何語言的敘述,這種生活經驗便都最先在敘事中得到呈現和描述,哪怕是人從來沒有見過的神和非人的英雄們,他們只要借助語言敘事在故事中出現在人面前,人的吃與穿的生活經驗,便率先被作者敘述和呈現。原來,奧維德在《變形記》中重述人類開天闢地的第一個時代「黃金時代」一出現,「大地無需強迫,無需用鋤犁去耕耘,便自動地生長出各種需要的物品。人們不必強求就可以得到食物,感覺滿足;他們採集楊梅樹上的果子,山邊的草莓、山茱萸,刺荊上密密層層懸掛著的漿果和朱庇特大樹上落下的橡子……土地不需要耕種就生出了豐饒的五穀,田畝也不必輪休,就長出一片白茫茫、沉甸甸的麥穗。」於是,關於人和人類吃的問題,便在人剛出現的同一時間得到解決了。
但丁在昏暗的森林中醒來時,首先遇到了代表淫慾的豹,接著相遇了代表豪傲的獅子,繼而很快又遇到貪婪的母狼。淫慾、豪傲和貪婪,本就是人類最原始、普遍的三種行為與情感,詩人已經直擊了人類的精神與內心,雖然如此,偉大的但丁,也沒有忽略對人的最普遍的經驗欲望之書寫。於是寫貪婪的母狼時,她一出場,但丁就寫道:「她竟無法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食慾/吃了之後,她比先前更為飢餓/她與許多野獸交配過/而且還要與更多的野獸交配/直到那將使她痛苦而死的『靈犬』來臨。」從《荷馬史詩》到《聖經》,自奧維德的《變形記》到《神曲》,這些作品無論是產生於古希臘還是古羅馬、西元前或者西元後,從空間說來,是從天空寫到了地下;自對象說來,是從神寫到人及非人的英雄和動物--概而言之,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大多都還不是「人」,但作者卻沒有敢--或說沒有忘記書寫這些非人的「人物」們,都有和人一模一樣的吃、穿和欲望。即便是產生於西元前近四百年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作品中的吉爾伽美什「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以及敘事中所有的非人的妖獸們,也沒有哪個沒有生命經驗的「吃、穿和欲望」,在其身上和行為中。為什麼人最原始的「吃、穿和欲望」,這類最基本的生命需求和生活經驗,人類最早、最偉大的詩人和作家們,都要在作品中進行必須的描述和交代?難道不描述、交代不行嗎?更何況這些作品中的對象,他們本來就不是「人」,完全可以不有人生之經驗,可以不食人間煙火。而那些祖先的偉人們--人類最早的智者、詩人和作家們,他們之所以可以不這樣,卻又一定要這樣,那就是他們深明文學有不能逾越的局限:哪怕作品中的「人物」是多麼偉大的神,作者自己終歸還是人。他只擁有人的生命經驗,而不擁有真正的神和仙妖的生命經驗。其次,這些偉大的詩人們,即便傑出如荷馬或但丁,也從來不敢忘記,聽他們吟唱的聽眾和讀者,一概都是人--讀者只擁有人的生命經驗,而沒有神和非人的生命經驗。如此,人的生命形式和生活經驗,就給作家、詩人法定了每部作品的書寫,必須遵守的寫作憲法是--只有人可經歷、感知的生命形式的經驗,才是人類培植寫作的唯一的真實和根土--這就是今天人的可實踐的經驗,乃至是純粹的日常世俗,取代寫作中人的豐富生命經驗最早的源頭和伏筆。
今天,文學中可感知、實施的人生經驗對文學的統治,大約都緣於這些根土和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