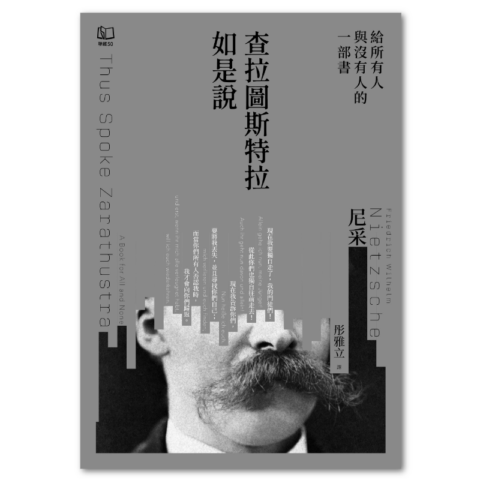莊子四講
原書名:Leçons sur Tchouang-tseu
出版日期:2011-10-05
作者:畢來德
譯者:宋剛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128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7797
系列:文化叢刊
已售完
瑞士漢學家畢來德,引用大量西方學術思想,使讀者更了解莊子思想的西方解讀方式。
本書自2002年在法國以法文出版後,再版多次,在西方漢學界和普通法語讀者中引起很大反響。作者在書中跳出了自郭象以降的莊子解釋傳統,提出了以「動能機制」等概念理解莊子的新思路,對莊子原典做出了獨到的闡釋。作者還引用了大量的西方學術思想,以幫助西方讀者由其已知的事物出發,從而更直接地去把握莊子的思想。本書中文版的問世必將有助於中文讀者進一步了解一種新穎的莊子思想的西方解讀方式。
作者:畢來德
1939年生於瑞士巴塞爾,於日內瓦大學法國文學系畢業後在巴黎學中文,1963-1966年在北京留學,於北京大學學中國古典文學,後又在京都、香港、巴黎深造。1972-1999年任日內瓦大學講師、教授,創立了中文系。
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社會學方面的著作有《論中國的「階級身分」》、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有《受非難思想家李贄》,美學方面的著作有《中國書法通論》,哲學方面的著作有《莊子四講》及《莊子研究》等。其著作和學術論文均以法文發表。
譯者:宋剛
1972年生,成都人,現任教於法國里昂高等師範學院。譯著有蕭沆《解體概要》、弗朗索瓦‧于連《道德奠基》等。
中文版序
原序
第一講 運作
第二講 天人
第三講 渾沌
第四講 主體
中文版序
本書四講是根據我2000年秋天在巴黎法蘭西學士院所作的四場系列講座整理而成的,在其中介紹了自己當時研究《莊子》的一些成果。
自我卸下日內瓦大學教職以來,我所從事的《莊子》研究主要有兩個目標:一是在研究《莊子》思想之外,想在《莊子》的啟發之下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問題;二是讓《莊子》將來有一天變成西方學人能夠深入理解的一部經典。在這方面,我只能做一點點鋪路的工作。
為此,我在這本小書裡採取了四種辦法:首先是翻譯,通過法文翻譯呈現我對文本的解讀。我認為,這是我工作的精華所在,也是這本小書能夠吸引法語讀者的主要原因。其次是闡釋,讓闡釋伴隨本文,使二者一樣地明晰而有共同的節奏,產生一種複調音樂的效果。第三,儘量參照西方讀者固有的一些知識和親身體會,讓他們更容易切入莊子的思想。第四,在出版選擇上,刻意跳出了一般讀者往往敬而遠之的漢學研究系統,更注意避開了風行於市,卻不為真正愛好哲學思考的人所接受的「東方智慧」叢書。本書發表幾年以來,一直受法語讀者的歡迎,可以說證明了這些辦法是有效的,當然更證明了莊子是一個極為精彩的思想家。
這本小書是給西方讀者看的,相對於中國讀者,可以說是背過身子講話;但也許,正因為如此,它會在中國引起一定的興趣。把這樣的一本書譯成中文,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我對《莊子》的解讀主要體現在我的翻譯當中,所以必須把我的法文翻譯翻回中文,不能徑取原文了事。我為了闡釋《莊子》思想創造了一些新的概念,中文沒有現成的相應辭彙,加上法語與漢語的句法、修辭相距甚遠,把清晰流暢的法文轉換成準確自然的中文,實非易事。其中的種種困難,譯者宋剛先生都一一努力解決了,我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謝。本書中文版增加了一些簡要的注解,對中國讀者可能不熟悉的人名、書名或概念作了說明。
這本小書的法文第一版於2002年問世,現已多次重印。隨後2004年出版的《莊子研究》(Etudes sur Tchouang-tseu)是我其他一些關於《莊子》研究論文的結集,篇幅比較長,難度也大一些,但同樣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
我對《莊子》的理解與闡釋,以及對中國思想史的一己之見,希望方家不吝指教。至於我提出來的哲學問題,則祈願能有「忘言之人而與之言」矣。
原序
本書四講係2000年10月13、20、27日與11月3日,應法蘭西學士院中國現代史教授魏丕信(Pierre Etienne Will)先生之邀,在該院所作的四場講座。在此,筆者對自己在卸下日內瓦大學中國研究教職之後所從事的一些研究做了一次檢視。
莊子是中國古代一位大哲人。一般認為其卒年當在西元前280年左右。彙集了他本人及其後學著述的作品沒有標題,習稱《莊子》。
這部舉世無雙的作品,西方漢學家很少有人曾認真加以研究。究其原因,恐怕在於,這本書我們若想入其堂奧,就必須先完成一種雙重批判:一是要擺脫我們普遍認定的那種所謂「中國思想」的概念,二則還得同時對我們自己某些最牢固的觀念提出置疑。
《莊子》目前還沒有一個稱人意的法文譯本。Liou Kia-hway(劉家槐)的譯本L’ uvre complète de Tchouang-tseu(Gallimard, 1969),雖收入「七星叢書」《道家哲人》(Philosophes taoïste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80),譯文卻委實薄弱;晚出的J. J. Lafitte譯本(Albin Michel, 1994)也沒有更理想。L. Wieger神父在其《道家學說的諸教父》(Pères du système tao ïste, 1913, Cathasia 1950年再版)一書中的譯文,則已是徹底過時了。最好的西文譯本當屬Burton Watson的The Complete Work of Chuang Tzu(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8)。A. C. Graham(葛瑞漢)的Chuang-Tzû,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Allen & Unwin, London, 1981)不如前者令人信服,但書中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書對原文引用出處的標示,第一個數位元為篇數,字母表示篇下的分節,之後的數字為《莊子引得》(哈佛燕京引得編纂處,1947,臺北承文出版社1965年再版)中文字句對應的行數。本書對漢學研究的引用力求簡要。
《四講》第七次發行時,筆者因2004年《莊子研究》(Etudes sur Tchouang-tseu, Allia, 2004)一書的出版,對原書略有更動。
第一講 運作
《莊子》可以有百種讀法,但原則上只有一種是好的,就是能夠準確把握作者賦予他作品及其各部分全部意義的那種。筆者就是試圖接近這樣的解讀──首先是因為它應該是最有意思的解讀,其次是因為這是研究的一個必要前提。如果學者們不朝這樣的目標努力,則始終無法整合眾人的力量,一同加深對文本的理解。
因此,筆者的態度是有別於許多漢學家的。他們彷彿彼此心照不宣,久已達成了一種共識,即所謂《莊子》一書,其文本如此艱深,其傳承狀態又如此疑雲重重,書中所表述的思想更是離我們非常之遙遠,所以企圖確切理解它,非為天真即屬妄想。在他們看來,千百年來無數注釋、衍義、解說又附加其上,而這些注解本身也都晦奧難通,所以障礙已呈不可克服之勢。其實大家之所以如此眾口一詞,恐怕是因為這樣的觀念,讓人大可不必細讀文本,盡可以人云亦云,生套些陳詞濫調,或對《莊子》隨意詮釋解說,也不必擔心遭到別人的反駁。
我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這一成見。我採取的作法不是試圖提出一種特定的解讀,而是要陳述自己是如何去嘗試理解莊子的,一方面要闡明我自認為已經取得的一些成果,另一方面也坦承自己遭遇的疑惑,以及自己還在追問的一些問題。我希望能夠讓讀者了解到,當我們本著一種既嚴謹又大膽想像的精神去研讀這一文本的時候,能夠有什麼樣的發現。
我的研究是這樣開始的。有好些年,我翻譯了《莊子》的一些段落,這既是出於對翻譯的喜好,也是因為想與一位朋友討論這些段落的思想內容。在這樣斷斷續續的翻譯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了原作之高明,不只是高明於西方漢學家的各種譯本和所做的各種詮釋,也高明於中國歷代文人及現代學者的諸種闡釋。從此,我對《莊子》原文的興趣日增,同時,對這些二手資料則越來越產生了戒心,導致我最後面對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研究議題:一是《莊子》本身,二是人們長期以來對它施以的種種簡化、歪曲或挪用。
這裡我得補充一點:我的研究,假如不是始於翻譯,而且一直把翻譯列為最終目的,就不會是它今天的這個樣子。因為沒有任何研究方法,任何學術規範會像翻譯那樣迫使我們如此全面審慎地考量一份文本的所有特點,包括它的架構、節奏、語氣,等等,──而這些也都一同決定了文本的意義。原文與其對應的法文文本之間的多次往返、多次對照是逐漸顯現文本含義的最有效的方法。我甚至認為,一種不曾經歷翻譯之考驗的詮釋,必然是主觀而片面的。
到目前為止,西方漢學家大致是以四種方式來研究《莊子》的。最常見的是借鑑傳統的中文注解來翻譯、評注《莊子》。另一部分人則試圖從中國古代思想史和宗教史入手,對傳統評注加以更新或是精緻化的研究。還有的人則偏重於文本的考據學研究,他們大多只關注文本的傳承、來源以及真僞等問題。最後一些研究者則試圖將《莊子》當中某些提法與西方某哲學家,特別是當代哲學家的某些觀點加以類比,由此構織新的論述。
這些方法儘管都是有用的,卻始終讓我感覺稍欠人意,只是很長時間也看不到別的可能。後來有一天,有了這麼一個想法:《莊子》不是一個普通的文本。它,至少它的一部分,乃是一位哲人的作品。我所謂的哲人,指的是這麼一個人:一,他進行獨立思考,而且是根據自己對自我、他人及外界的親身體會進行思考的;二,他注意參考在他同時及在他以前的別的哲人的思考;三,他對語言的陷阱又有敏銳的感悟,因此十分謹慎地運用語言。
這一想法在我面前開闢了新的視野。我自己對這樣的哲學活動有興趣,這在莊子和我之間便構成了一種原則上的平等關係。他既然根據他的親身體會進行獨立思考,我既然也願意這樣做,我們之間就產生了交會:他的經驗與我的經驗,必然或多或少有彼此印證之處。由此我便得出了自己的第一條研究原則。每次要去研究《莊子》的一段文字的時候,我首先要問自己的,不是作者在推演一些什麼概念,而是他在談論哪種具體的經驗,或是共通經驗中哪一個方面。
我的第二條研究原則是在維根斯坦那裡找到的,更具體地說,是他在下面這段文字。他在《紙條集》當中寫道:「我們在此遇上了哲學研究中的一個特殊的、典型的現象。可以說,難的不是找到答案,而是在看起來只是答案的入門階段裡辨識出答案來。……我想,這是因為我們期待的是一種解釋,而看不到描述已經是困難的答案──當然要給這一描述它應有的地位,要停留在這一描述上,不再試圖超越它。──難的是:停。」維根斯坦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提出過這一想法。在他最後的手稿中,他是這麼說的:「早晚要從解釋回到描述上來。」在他後期的哲學當中,他就是這樣,對一些最基本的現象耐心地、不斷地、反復地進行描述的。這也是他後期的筆記會顯得如此令人困惑的原因:他是以高度的注意力觀察我們可以稱之為「無限親近」或是「幾乎當下」的現象。
而我有一天意識到了,莊子在我最熟知的一些段落當中,也是這樣做的。我前面已經認定他是一位哲人,是一個獨立思考的,首先關注自己的親身經驗的人。而我現在發現,他是在描述這些經驗,而他的描述非常精確,非常精彩,也一樣是描述「無限親近」與「幾乎當下」的現象。這又為我打開了新的途徑,可以依靠這些描述去理解莊子的一些核心思想,而由此一步一步走進未能理解的區域。
維根斯坦說,要停在描述上。這意味著兩點:一是要放棄我們日常的活動,轉而全心全意地檢視我們眼前的或是甚至離我們更近的現象;二是要以精準的語言來描述所觀察到的現象,花足時間,找準辭彙,抵禦話語本身的牽引,強迫語言準確表達我們所知覺到的東西,而且只是表達那些。後一點則要求對語言有極高的駕馭能力。而維根斯坦和莊子,雖然如此迥異,卻都是出色的作家,這絕不是件偶然的事。
下面就是《莊子》當中這類描寫的一個範例。這是書中第三篇〈養生主〉裡的一則對話。人物有兩個,一個是與莊子同時代的魏國君主文惠君,另一個是一個屠夫──一個莊子想像的人物形象:
庖丁為文惠君解一頭牛。他或手觸牛體,或是以肩膀頂住牛軀,或是雙腿立地用膝蓋抵住牛身,都只聽嘩嘩的聲響。他有節奏地揮動牛刀,只聽陣陣霍然的聲音,彷彿是在跳著古老的「桑林舞」或是在鼓奏著「經首曲」。
文惠君歎道:「佩服!技術居然可以達到這種程度!」
庖丁放下刀回答說:「您的臣僕我所喜好的不是技術,而是事物之運作。我剛開始做這一行的時候,滿眼所見都是一整頭牛。三年以後,所看到的就只是一些部分而已。而到了現在,我只用心神就可以與牛相遇,不需再用眼睛看了。我的感官知覺已經都不再介入,精神只按它自己的願望行動,自然就依照牛的肌理而行。我的刀在切割的時候,只是跟從它所遇到的間隔縫隙,不會碰觸到血管、經絡、骨肉,更不用說骨頭本身了。(……)在碰到一個骨節的時候,我會找準難點,眼神專注,小心謹慎,緩慢動刀。刀片微微一動,牛身發出輕輕的『謋』的一聲就分解開來,像泥土散落掉在了地上。我手拿牛刀,直立四望,感到心滿意足,再把刀子揩乾淨收回刀套裡藏起來。(……)」
我只引用了這段文字的一個部分,因為我目前只關心文章開頭的那段描述,也就是庖丁對他自己學習過程的描述。
庖丁對文惠君說,在他剛開始做解牛工作的時候,「所見無非全牛者」,滿眼都是那一整頭牛。面對那樣一個龐然大物,他只會感到自己有多麼無能為力。之後,最初這種主體與客體間的對立狀態發生了變化。經過三年的練習,他就「未嘗見全牛也」,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部分了,也就是那些在切割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部分。庖丁已經靈活了,開始戰勝客體對他的對抗了,他所意識到的已經不再是客體對象,而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活動了。最後,這一關係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庖丁對文惠君說:「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即是說,到了現在,他只用心神就可以與牛相遇,不需再用眼睛看了。他的感官知覺都已經不再介入,精神只按它自己的願望行動,自然就依從牛的肌理而行。他練出來的靈巧,現在已經高明到了牛對他不再構成任何阻力,因此也就不再是他的一個客體對象的程度了。而客體的消失,自然也伴隨著主體的消失。庖丁在行動中是如此投入,以致他能夠「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了。在我剛剛勾勒出的這一進展邏輯當中,「神」不是外在於庖丁的某種力量,也不是在他身上行動的某個殊異力量。這個「神」只能是行動者本身那種完全整合的動能狀態。當這樣一種徹底的融合產生以後,活動也會發生變化,進入一個更高層次的機制當中。它似乎已經掙脫了意識的控制,只服從於它自身了。這便是庖丁描述的現象:「神欲行,依乎天理。」精神只按它自己的願望行動,自然依從牛的肌理而行。
我們只需略加思考,便能認識到,庖丁描述的各個階段是有根據的。這樣的階段,我們也是很熟悉的,我們自己也曾經歷過多次。譬如說,小的時候,我們學著把水倒進一個杯子裡,或是學切麵包,也都得先從戰勝物的慣性開始。等那些物對我們的抵抗逐步減弱了,我們才漸漸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難點之上──比如,小心不要把酒滴到桌布上,或是把麵包切成厚度均勻的薄片等等。最後,我們完成這些動作可以是毫不費力,完全不受物的限制。有時候,我們甚至也能夠達到那種渾整的狀態,讓活動產生質上的變化,賦予它一種奇妙的效率:譬如說,當我們一槌便將一根長長的釘子敲進木頭裡時,不也曾跟庖丁一樣,面對成果,「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嗎?
其實不只是在操控對象的時候,就連要協調我們自身的行動,其學習過程也都如此。我們都是經歷了這樣的階段才學會行走或是說話的。在學一門外語的時候,我們也有同樣的經歷。就跟庖丁面對他的牛一樣,我們看那門外語,開始也是一整塊橫亙眼前,阻撓著我們的表達願望,然後才開始只注意其中困難的部分,而最後才能「以神遇」,只用心神就可以了。在我們說這門外語的時候,也是「神欲行,依乎天理」,精神只按它自己的願望而動,自然就能依理而行。那語言不再外在於我們,不再是一個客體對象。此外,我們還可以想想音樂,想想掌握一種樂器,譬如說小提琴──想想從初學者的困難重重,到高超的音樂家在某些時刻所能實現的奇蹟,這中間又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我們都熟悉這些學習的過程,可是我們沒有想到要這樣去總結它:只短短四句令人叫絕的話。莊子給出了我們所缺乏的範式,使我們能夠把之前分散的許多現象聚合起來、組織起來,還能夠通過別的觀察去加以補充,進而以一種嶄新的視野來理解我們的一部分經驗。我們所有的有意識的活動,從最簡單到最複雜的都不例外,其學習過程都經歷過這些個階段。
讀者或許已經注意到,我給「經驗」(expérience)這個詞賦予了一種特別的意涵。我不是說那些在實驗室裡進行的實驗,也不是說我們在生活過程中,或是在某一職業中積累起來的那些經驗,也不是我們某一次,在某個特殊場合所感受到的某種具體的經驗。我所謂的經驗,指的是我們一切有意識的活動的基礎。我們非常熟悉的這一基礎,但一般並不注意它,因為它離我們太近,而且太過普通。我們平常不關注它,但是可以逐漸去察覺它,去認識它。這需要培養一種特殊的注意力,而要讀好《莊子》,正好需要培養這樣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