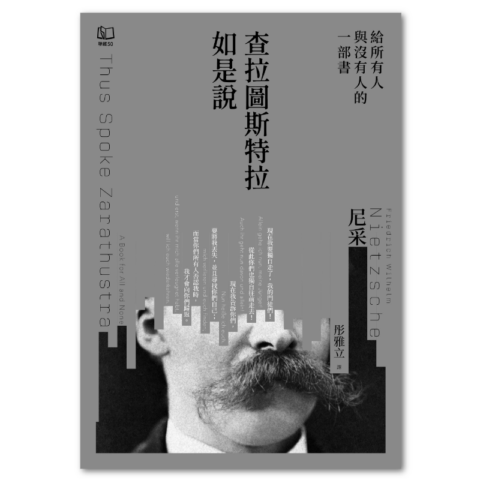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
出版日期:2017-09-07
作者:呂妙芬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402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9967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以明末清初理學文本與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
試圖重探明清之際思想轉型的重大議題。
從儒者的生死觀、工夫論、舜的聖人形象、孝行與家禮、
夫婦之倫、人性論等主題,
分析明清之際儒學如何在歷史發展及反思中自我修正與轉化,
建構一個能兼顧個人道德修養與家庭社群人倫,能對治晚明學風之弊,
並在日用人倫中重建社會秩序的思想體系。
呂妙芬新作《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鎖定明清之際(以十七世紀為主)的理學為主要研究範圍,試圖以更豐富而新穎的史料、新的研究議題與視角,來探討明清之際儒學的發展與轉型,也試圖回應一些過去學者提出的看法。
呂妙芬在本書裡認為理學的信念在清代仍是支持政治與社會的價值體系,理學的議題也仍是士人關心的問題,清代理學思想與話語也不盡然因襲舊說,而有其推陳出新之處,只是這方面較未被充分探討認知。
《成聖與家庭人倫》一書也強調當時儒學是在高度宗教對話的語境中發言,調整自我義理內涵,書中亦論及儒學宗教化與庶民化的現象,及對過去啓蒙論述的反思。
本書共分三部,第一部「成聖、不朽、家庭人倫」包含三章,主要探討明清之際儒學發展的延續與變化,並標出「成聖」與「家庭人倫」為核心議題。第一章〈生死觀的新發展〉探討明清之際理學話語中,是否出現類似個體靈魂的概念?是否有關於死後想像的論述?第二章〈儒門聖賢皆孝子〉延續了上一章的討論,主要根據的文本也相近,焦點則轉到清初儒學與晚明儒學的差異。第三章〈聖人處兄弟之變〉考察明清士人對於《孟子》記載舜、象兄弟故事的不同詮釋,說明士人對於舜的詮釋反映了他們對儒學理想與聖人形象的思索。
第二部「血脈與道脈的雙重認同」包含兩章,內容則離開思想觀念的分析,轉而探討萬里尋親、居家拜聖賢兩種實踐行為,藉此說明家族血脈與儒學道脈在儒家士人心目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第四章選擇與宗族文化密切相關的萬里尋親孝行為主題,支持此類孝行的理念正是儒家的孝道思想,以及「家」作為永恆歸屬的觀念。第五章討論明清士人在家拜聖賢的禮儀實踐。明清時期祭拜儒家聖賢之禮,除了在孔廟、鄉賢祠、學校和書院中,或在某些民間宗教的寺廟中舉行外,它也以一種堅持儒學正統、不與其他宗教混合的方式,走入士人家庭。
第三部「宗教對話語境下的儒學論述」共有兩章,分別討論夫婦之倫、人性論兩個主題。第六章探討儒學在夫婦之道的神聖性與戒淫之間的張力,以及因發言語境之差異所形成關於夫婦之倫的不同論述面向。第七章是針對明清氣學人性論的探討。結論部分則分別就「從晚明到清初學術思想的延續與創新」、「儒學的宗教關懷與庶民化傾向」、「再思17世紀儒學轉型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三方面,總結說明本書的主要論點。
作者:呂妙芬
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近世學術思想史,代表著作包括《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2017)、《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2011)、《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2003)等。近年主要研究課題為明清儒學與基督宗教的交涉、明清儒學的人觀、魂魄與生死觀,以及關於個體性、不朽、天人關係等論述。
序
導論
一、以理學文本為主要史料
二、核心議題
三、重視宗教的面向
四、反思過去的論點與分析架構
五、各章簡介
I 成聖、不朽、家庭倫常
第一章 生死觀的新發展
一、道德修養決定死後情狀
二、聖賢會聚的「天堂」意象
三、結語
第二章 儒門聖賢皆孝子
一、自古無不大孝之聖人
二、家庭倫職與成聖工夫
三、結語
第三章 聖人處兄弟之變
一、《孟子》的記載
二、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何為聖人之心?
三、舜「封」象有庳
四、向善轉化的象:以莊存與的詮釋為主
五、質疑《孟子》
六、結語
II 道脈與血脈的雙重認同
第四章 萬里尋親的孝行
一、萬里尋親的孝行實踐與相關文化生產
二、萬里尋親故事的敘述模式與意涵
三、故事的另一面
四、結語
第五章 在家拜聖賢的禮儀
一、禮儀實踐個案
二、禮儀實踐的意涵
三、結語
III 宗教對話語境下的儒學論述
第六章 夫婦之倫
一、論述夫婦之倫
二、廣嗣與寡欲的夫婦生活
三、結語
第七章 人性論述
一、氣學性論的兩個主張
二、闢二氏的發言語境
三、天人關係
四、比較天主教靈魂論
五、結語
結論
一、晚明到清初儒學思想的延續與變化
二、儒學的宗教關懷與庶民化傾向
三、再思明清之際儒學轉型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
參考書目
序
在我心目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史是一座難以攀越的高峰。這個領域的著作太豐富,名家輩出,更不乏許多早已被廣泛接受的觀點。我從碩士班在何佑森老師的課堂中開始接觸相關的討論,爾後又在不同的機緣中向學界前輩們學習,深受啟發,但也不免有困惑。無論明清之際思想轉型或學術典範轉移有多麼明顯,多年以來,我總是覺得理學持續構成清代儒學的重要內涵,晚清以前儒學的思想基調並沒有發生大變化,義理和考證、道德和知識多半不是互相對立,而是交織融合地被論述與運用。而那些高揚科學、重視啟蒙的問題意識,總不能令我心動,這應是個人習性使然。這本書的研究大概是帶著上述的「感覺」出發,摸索著進行。
另一個讓我決定以清初理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理由,則是比較務實的。相對於晚近明代理學、陽明後學的研究,清初理學仍較少被關注,不僅許多思想家和文本未被深入研讀,學術發展的整體輪廓也較不清楚。對於研究者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契機。我雖然花了約7年的時間完成此書,但心裏深知這僅僅是理解明清之際儒學的一個面向,還有太多的文集,我沒有讀過;其他重要的議題,我也沒有觸及。因此,即使書將出版,我其實沒有完稿或攀越高峰的感覺,更像是行旅中的駐足休憩,希望能在學術山林中,醞釀再一次出發的靈感。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我除了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提供優良研究環境外,也要感謝科技部連續多年的支持,以及我的助理們歐姍姍、徐維里、瞿惠遠、陳胤豪、吳冠倫協助蒐集史料和校稿。我也感謝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支持「明末清初學術思想史再探」計畫,讓我有機會與許多海內外學者交流。
本書部分的研究成果,曾經受邀在國立中央大學、廣州中山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等地演講,部分章節也曾發表於中研院近史所的學術討論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美國歷史學年會,以及由新加坡國立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復旦大學、中研院近史所主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與會學者的批評和意見,都幫助我進一步修改書稿。本書第一章曾發表於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家庭、宗教、物質的網絡》,第二章曾發表於《清華學報》(新44卷4期),第四章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本2分),第五章發表於《台大歷史學報》(57期),感謝這些期刊提供專業的審查與編輯,讓文章內容獲得修正。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本書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以及聯經編輯提供的專業協助。
本書討論清儒對於為學的看法:家庭是修德的場域,人應在自我追求與家庭人倫中尋找統合的理想;人生總帶著命定與限制,人應努力在日用人倫中成長與進步。這是平實而寶貴的人生智慧,我也願意再次將我最深的感謝獻給陪伴我成長的家人,特別獻給我的父親,他在去年寒冬離我們而去。
導論
明末清初學術思想史是學界熱門的議題,從梁啟超(1873-1929)提出清代學術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以來,環繞著明末清初學術延續或變化的討論便不絕如縷。胡適(1891-1962)承繼了理學反動說的基本看法,重視清代考證學的科學精神;錢穆(1895-1990)說治近代學術當始於宋,他更強調清初學風與宋明理學的接續;余英時從中國歷史上的智識主義和反智識主義兩個傳統,解釋明清之際學風的轉變;錢新祖(1940-1996)則從氣一元論對程朱學的挑戰,看到了某種儒學重構的跡象,以及明代理學與清代學術的關聯。雖然學者們的看法不同,但他們的問題意識頗接近,均欲追溯清代新學術典範產生的原因,以及兩個時代主流思潮的異同。張壽安提出「以禮代理」、張麗珠強調「清代新義理學」,也是在類似的問題意識下試圖說明宋明理學與清代學術的關係,雖然他們主要研究的是乾嘉學術。上述各家研究都是以主流學術思潮為焦點,藉著分析著名學者的思想勾勒出明清之際儒學思想發展的大趨勢。
描述或解釋明末清初學風轉變的著作十分豐富,尤以經世學風的興起最受矚目,著作亦最多。學者除了從制度、沿革、職掌、財賦實政、輿地實測等各方面說明經世之學日趨重要外,思想史常見的議題尚有:對晚明陽明學之批判與修正、明中葉以降持續發展到清代的氣學思潮、尊崇經史之學、重視形下器物、強調實踐力行、肯定人欲與功利等,學者更藉此論述中國近代啟蒙的歷史,也引發不少對所謂啟蒙的反思。上述各方面的研究雖然成果豐碩,但除了氣學思潮等少數研究課題緊扣著理學討論外,大多數的研究則是以「理學衰微」為前提,以探究清代新興學風為主要問題意識。簡言之,既往學界對明末清初時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新思潮、新方法、新學術社群的形成,是學術典範轉移的問題。加上清代理學又如錢穆所云是「脈絡筋節不易尋」、「無主峰可指」,故相對受到忽略。因此,儘管此時期留下的理學文獻並不少,但目前針對理學的研究成果仍然有限。
事實上,理學在清初仍有重要地位,程朱學受到朝野士人的重視,是清代官學,主導了科舉考試與教育的內容,也是當時普遍被社會接受的核心價值。因此,以理學衰微為前提的問題意識可能會錯失許多重要的歷史觀察。若我們不先主觀地認定清代理學沒有創意,願意更開放地去研讀那些尚未被充分研究的理學文本;若我們把研究的視角稍微轉換,不再只注意學術風氣的創新,也同時考量延續性的經典詮釋,及一般士人的閱讀經驗、想法與實踐;或者不僅重視科學和實證學風的表現,也願意留心日常生活與宗教關懷在歷史中的作用,我們對於理學在清代社會上的持續影響力及其內部的自我創新,可能會有許多新的認識。這個想法是本書研究的第一個發想。
我在思考明清學術變化的現象時,多受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一書的啟發,該書討論西方社會從1500年以降五百年間的重大變化:基督教從人們唯一的宗教信仰變成現代多元宗教中的一種選擇;宗教信仰從政治社會的公共事物變成人們私領域中的個人追求。這些事如何發生?泰勒不採取「科學取代信仰」的解釋,也不滿意只從知識菁英的學術變化來詮釋這段歷史;而是試著描述西方世界從16世紀以降,一系列宗教改革對全民教育的提升,科學發展與啟蒙思想對基督教的刺激與影響,政體變革、工業革命、商業及消費革命所導致政經條件與知識系統的變化,及其對人類生活之衝擊與形塑,並試圖在這種具全體社會的宏觀視野下來思考基督宗教信仰變化的過程。泰勒指出基督教並不是簡單地被科學所「取代」,它甚至在科學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督教也沒有在「世俗化」的過程中完全被揚棄,它本身與時俱進的變化甚至參與了「世俗化」的過程。而所謂的「世俗化」概念也需進一步說明,至少作者認為過去人們在宗教中所追求的一種對生命福至圓滿之感,並沒有在世俗化或現代化過程中消失,只是人們對圓滿的要求與感受,及所擷取的資源,有了相當的變化而已。
泰勒的研究對於我思考中國明清以降的儒學與社會的變化有相當啟發,至少提醒我:研究明清學術思想發展與變化,不應停留在思想的線型發展,或簡單的彼此取代關係描述上,也應留意儒學普及化或庶民化的現象,及其與整體社會的關係。錢穆所謂「理學本包孕經學而再生」也有類似的眼光,漢學與宋學並非壁壘分明、互相排斥的兩套學說,它們不宜被化約為對立的關係,所謂的漢宋兼採也未必是妥協或雜亂拼湊,而可能蘊含深刻的思想創新。
本書主要抱持上述的想法,認為理學的信念在清代仍是支持政治與社會的價值體系,理學的議題也仍是士人關心的問題,清代理學思想與話語也不盡然因襲舊說,而有其推陳出新之處,只是這方面較未被充分探討認知。基於此,本書鎖定明清之際(以17世紀為主)的理學為主要研究範圍,試圖以更豐富而新穎的史料、新的研究議題與視角,來探討明清之際儒學的發展與轉型,也試圖回應一些過去學者提出的看法。
第一章 生死觀的新發展
本章主要欲探討明清之際的儒學是否出現近似個體靈魂(individual soul)的概念?是否更具像地描述死後的情狀?中國傳統雖有關於魂魄和死後情狀的描述,但並未明確提出個體靈魂的概念,而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階段,早期典籍中人格神的色彩大幅消減,形上義理成分加重。理學家基本上以氣之變化來解釋生死現象,雖然他們沒有否認鬼神的存在,但對於生死議題主要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晚明社會動盪、戰亂頻仍、宗教氛圍濃厚,學者對於生死議題格外關切,晚明許多理學家都追求悟道,強調儒學的終極目標在於了究生死。本章主要研究清初儒者的生死觀,及其對死後理想歸宿的想像,將就此議題說明儒學在明清之際延續性的發展。
一、道德修養決定死後情狀
宋明理學從氣化的觀點講鬼神、不認為有永久不散的個體性神魂。舉例而言,張載(1022-1077)以氣之聚散講生死,氣聚生成人物,人物死後,氣散歸回太虛。鬼神乃陰陽二氣之往來屈伸,是氣之良能妙用。張載認為,人死後個體性的靈明便隨之消散,他也以此批判佛教的輪迴觀。二程對於張載氣化思想雖有批評,但同樣認為人死氣散的看法。朱熹(1130-1200)對於鬼神、魂魄的討論,包括「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死後「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鬼神乃陰陽二氣之靈」等,均可見其大體承繼二程與張載的看法。目前學界對於朱熹鬼神觀的討論較多,學者指出他在不同語境下使用「鬼神」二字,有意指氣之往來屈伸、陰陽二氣之靈、人身之精氣、造化之神妙等不同意涵。吳展良則指出朱熹的鬼神觀既非無神論,又非人格神論,而是具有統合神靈、精神、物質與人生界之特性。儘管學者對於朱熹鬼神觀的詮釋重點不盡相同,然仍有相當的共識,其中與本章論旨相關的是:朱熹沒有個體靈魂不朽的概念,也反對具位格的鬼神觀,此又與其反對佛教輪迴有關。朱熹認為人死後,氣會回歸天地間公共之氣,只有在子孫誠敬祭祀時,祖先神魂才可能被暫時性地感格而會聚,即使聖賢亦然。他說:
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
這段話一方面解釋祭拜山川神祇與祭祀祖先的原理差異,一方面解釋古書中記載人死魂氣不散,回到人世報仇的事例。朱熹承認確實有人死後氣不散的現象,但主要是因為凶死為厲作怪,或者如僧道是通過修養使氣不散,但朱熹認為此均非正道,亦非仁人君子所應嚮往追求的。生順歿寧、與道消息,才是儒者了然生死變化、大公無私的正確態度。
簡言之,張載、程朱等宋儒對氣之聚散的看法,基本上適用於所有人,即無論智愚賢不肖,生死聚散的原理並無差別,都是氣聚而生,死後氣散;人死後,個體性亦隨之消亡。生死的變化,並不是氣從有到無的變化(亦即氣仍存在),而是曾經聚集成個體生命的氣,隨著生命的死亡而散化,個體性亦隨之消失。朱熹明白說道:「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即使聖賢,死後氣亦散歸天地公共之氣,不再具有可區辨的個體性。這樣的看法構成理學論述的主流,影響後代學者甚鉅。宋儒中雖也有胡宏(1105-1161)、程顥(1032-1085)曾說心體不死,不過這樣的看法受到程朱的批評,在宋代較不顯。明代心學思想高漲,晚明以降許多儒者都強調儒學的終極意義在了究生死,有關心體或性體不死的論述也更多。例如,王陽明(1472-1529):「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其臨終遺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強力表達了對自己心體與道合一的信心。唐樞(1497-1574):「人之所以為人,其始也不始於生,而始於所以生;其終也不終於死,而猶有所未嘗死者。」文翔鳳(1642卒):「百年為有盡之身,萬古有不滅之性。」李顒(1627-1705):「形骸有少有壯,有老有死,而此一點靈原,無少無壯,無老無死,塞天地、貫古今,無須臾之或息。」楊甲仁(約1639-1718):「以形骸論,一生一死,百年遞嬗,乃氣之變遷也。至於此性,無有變遷,不見起滅,有甚生死。」其他如「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吾生有盡,吾生生之心無盡」這類相信心體或性體不朽的說法,在明中葉以降的理學文本中經常可見。儘管如此,此尚不足以說明這些儒者已具有明確個體性靈魂的概念,除非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個體性身分辨識(individual identity)始終存在的表述,才能作如此推論。
明清之際也開始出現許多質疑程朱鬼神觀與生死觀的聲音,我們從以下這段記載可以看到明代學者已有不同想法:
人有問劉獅泉(劉邦采):「為學人,死了,何歸?」獅曰:「歸太虛。」又問:「不學人,死了,何歸?」獅曰:「歸太虛。」詢諸渠(鄧豁渠),渠曰:「學人不敢妄為,死歸太虛;不學人無所不為,死亦歸太虛。何不效他無所不為?同歸太虛,豈不便宜!」
劉邦采(1528舉人)的看法接近朱熹,人死後氣散回歸太虛,是天道的自然變化,人不應該過分追求個體不死,因為那是違反天道的自私行為。但是鄧豁渠(1498-約1569)的疑問代表了另一種聲音,也是關於個體生命終極意義的思索:如果儒家所重視的道德修養,最終並不能在修練者個人生命中鑄成永恆性的變化,其價值何在?就生命終極存在的境界而言,若果真不分賢愚都同樣散回太虛公共之氣,同樣無知,那麼是非善惡的價值與最終的公義何在?此似乎不符天道善惡之理。
對於這個問題的思索,鄧豁渠並不孤單,許多後來的儒者都持類似的看法,反對程朱等「死後氣散無知」之說。下文將一一列舉明清儒者如何反對賢愚善惡同歸於盡,強調個人道德修養具有決定死後神魂歸趨的作用,甚至出現近似個體靈魂觀的論述。這些學者並不隸屬於特定學派或地域,但都生活於晚明清初時期;他們的思想也存有許多差異,顯示此時期思想創作的活力與複雜性。儘管如此,他們試圖賦予個人道德成就超越死亡、具有不朽價值的眼光,則又頗一致。以下讓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羅汝芳(1515-1588)認為人具有精氣凝成之形骸與神遊變化之靈魂,即魄與魂的二元組合。靈魂心智是修身入聖之關鍵,人死之後,形骸氣魄消散,至於靈魂之歸趨,則不相同。他說:
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為徒焉已矣。若人以己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于力為,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沒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為徒焉已矣。
人死後能否還歸太虛與造化者為徒,端賴生時之道德修養而決定。人若能妙用心知、感通得諸當下,生可望以入聖,歿可望以還虛;相反,若心思受限於軀殼,不僅生時難以成聖,死後也無法還歸太虛,終將與凡塵為徒。
王時槐(1522-1605)說聖門論生死,不以形氣言,身體形氣隨死亡而消散,人心卻死而不亡。他也反對人死神散、舜跖同歸必朽的看法:
夫學以全生全歸為準的,既云全歸,安得謂與形而俱朽乎?全歸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之所以悠久而無疆也,孰謂舜跖之同朽乎?
高攀龍(1562-1626)和王時槐看法類似,同樣強調生死僅就形而言,性無生死,也認為賢愚善惡不可能同歸於盡。高攀龍說:
伊川先生說遊魂為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即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
高攀龍雖知程朱是因為闢佛的立場而強調人死氣散,不欲落入輪迴之說,但他不同意程朱的看法,他認為聖人不可以存亡言、忠臣義士何曾亡減?高攀龍的弟子陳龍正(1585-1645)也看出老師的說法與程朱不同,他自己則在細體二說之後,認為老師高攀龍之說較長。陳龍正說聖人無生死,其心充滿古今天地,死後精神周遍,故「不可作散觀,亦無處說得聚,總與生前一般」。他又分辨聖人與忠臣義士,認為聖人死後之神靈,與忠臣義士之靈不同,一般鬼神(包括忠臣義士之靈)或靈於一方,或盛於一世,只有聖人之靈「無所專在,無所不在」。陳龍正的想法,可以說已具有永恆個體性存在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