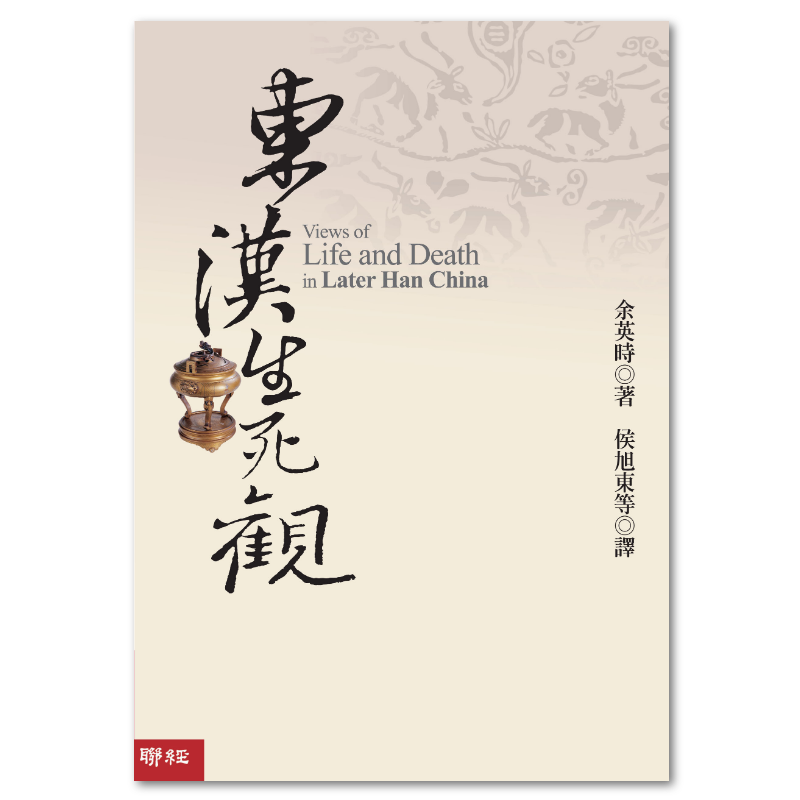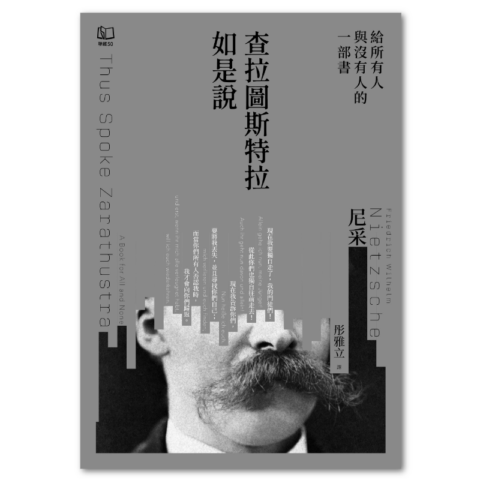東漢生死觀
原書名: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出版日期:2008-06-23
作者:余英時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16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2884
已售完
本書是余英時先生對於東漢民間生死信仰的考察,尤其是以「魂升天,魄入地」為代表的靈魂觀念,並強調中國人並不是等到佛教傳入才產生地獄觀念的。
目次
導言
一、 思想史及其若干問題
二、 方法與目的
三、 材料
第一章 生與不朽
一、 生的重要性
二、 長壽和不朽
三、 求仙的世間轉化
四、 民間思想中的「神仙」觀念
五、 小結
附錄:漢代專有名詞中的長壽類用語
第二章 養生長壽
一、 士人中的養生風氣
二、 養生術與求仙
三、 人的「命」與「壽」
第三章 死與神滅的爭論
一、 死亡的自然主義態度
二、 死後生活的流行信仰
三、 神滅的爭論
參考書目
Ⅱ. 早期中國來世觀念的新證據——評魯惟一的《通往仙境之路:中國人對長生的追求》(1981年)
Ⅲ. 「魂兮歸來!」——論佛教傳入以前中國靈魂與來世觀念的轉變(1987年)
複禮
魂和魄
來世信仰
陰間:魂和魄的各自住所
仙的出現和來世的重建
作者:余英時
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編者序言
我收集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初衷本是為了自己更全面地學習他的治學方法和理解他的論學旨趣。但在閱讀的過程中慢慢覺得,如果能將這些論著譯成中文,也許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意義在我看來至少有兩點:一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更全面地讀到余先生的論著;二是有助於對海外漢學以及中美學術交流的認識與研究。
《東漢生死觀》取名於余先生1962年在哈佛大學的同名博士論文。由於這篇學位論文中的第一章後經修改以同名發表於1964-1965年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刊》,因此在本冊中用後者取代了前者。此外,另收了同一主題的一篇書評(1981年)和一篇論文(1987年)。時隔20年作者續論這一主題,主要是因為考古的新發現。1978年末余先生率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中國月餘,漢代文獻與遺跡的親切感受大概也起了激活作用。
《漢代貿易與擴張》取名於余先生1967年出版的同名專著。此外,另收了兩篇論文和一篇書評。論文與漢代有關,發表的時間雖然分別是1977年和1990年,但後者是因所收入的文集出版延後所致,實際上它們同時完成於1973-1975年間。與這一主題相關,作者後來為《劍橋中國史》(秦漢卷)(1988年)撰有專章「漢代對外關係」,此書早有中譯本,故這裡不再收錄。1964年刊行的書評是關於唐代財政體制的,雖與漢代無直接關係,但考慮到主題同屬於社會經濟史,所以一併編入此冊。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由多篇論文組成,討論主題集中在中國思想史,涉及3世紀到當代,體裁有專論、書評、條目和序跋,先後發表於1980-2000年。之所以取名為《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是我以為這個提法能反映余先生的思想,他的所有思想史論著從根本的意義上說,也正是要釋證中國文化中的人文情懷和理性精神。(編按:繁體中文版出版時,依余先生的意思,增收〈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朱熹哲學體系中的道德與知識〉、〈歷史視野的儒家與中西相遇〉、〈20世紀中國現代化與革命崇拜之爭〉、〈歷史學的新文化轉向與亞洲傳統的再發現〉五文。)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取名於余先生作為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團長寫成的同名總結報告。此外,收入了由余先生 總的訪問活動與討論日記,以及差不多同時完成並與主題相關的一篇專論。這篇專論最初以中文寫成發表,後被譯成英文並經作者適當改寫後發表,收入本冊時相同部分照錄中文,不同部分則據英文而譯。
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在1970年代有一個明顯的變化,此後他的學術論著主要是以中文發表,大部分英文論著則概述他中文論著的主要思想,以及他對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分析性通論。前者顯然是因為他希望更直接地貢獻於中國學術,後者則表明他希望將中國的學術引入美國。促成這個變化的契機大概是他1973-1975年在新亞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的任職。雖然服務兩年後仍回哈佛任教本是事先的約定,且這兩年的服務也令他身心疲憊,但深藏於他心中的中國感情似乎更被觸動,更需要得到合理的安頓。1976年1月余英時先生46歲時,同在哈佛任教的楊聯陞將自己與胡適的長年往來書信複印本送給他作為生日禮物,在封面上題寫:「何必家園柳?灼然獅子兒!」大概正是體會到弟子的心情而示以老師的寬慰、提示與勉勵吧。
此後,余先生與兩岸三地的中國學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流。我在余先生小書齋的書架上翻覽時曾見到錢鍾書在所贈《管錐編》扉頁上的題詞,當時覺得有趣,便請余先生用他的小複印機複印了一份給我,現不妨抄錄在這裡,也算是一個佐證。題云:
誤字頗多,未能盡校改,印就後自讀一過,已覺須補訂者二三十處。學無止而知無涯,炳燭見跋,求全自苦,真癡頑老子也。每得君書,感其詞翰之妙,來客有解事者,輒出而共賞焉。今晨客過,睹而歎曰:「海外當推獨步矣。」應之曰:「即在中原亦豈作第二人想乎!」並告以入語林。
總之,讀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應當注意其中的中國學術背景,正如讀他的中文論著應該留心其中的西方學術背景一樣。
何 俊
導 言
一、思想史及其若干問題
思想史家通常將他們的研究對象劃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思想的「高」層次,或正式的思想;另一個是思想的「低」層次,或民間思想 。在歷史領域內,作為獨立的分支,高層次思想的研究久已得到良好地確立,大多數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屬於這個範疇。與此相反,民間思想極少得到思想史家的關注,儘管談得並不少。原因不難發現,思想史家如果從事民間思想的研究,便總是會使自己的研究面臨與社會史家的工作很難區分的困難 。因為民間思想顧名思義,不僅包括了老百姓的所思所信,而且還包括了他們的所行;有時人們的所思所信還只能通過他們的所行才能得到把握。在這個層次,思想史與社會史必須結合起來研究。而彼此間的區別,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各有側重而已。
民間思想有時被認為是「第一層次的思想在經過一兩代的『文化滯後』以後『滲透下來』的東西,在這樣的新環境中,觀念幾乎總是以通俗或扭曲的形態出現」 。作為一種工作假設,我知道這樣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對民間思想作如此界定,似乎仍是不夠的,因為只是從高層次的角度來看待民間思想時它才有意義。民間思想與正式思想的交流,特別是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交流,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單向的。當思想史的研究者發現一些來自偉大頭腦的偉大思想起源甚卑,有時便可能會感到尷尬。如果允許我們將任何相對穩定的社會或文化視為一個整體, 我們將會發現要在正式思想及與其相對應的民間思想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是困難的。正如布林頓曾指出的:
因而思想史家的全部工作是收集從抽象的哲學概念到人的具體活動間的所有可理解的材料。工作的一頭他要使自己盡可能成為哲學家,或至少是哲學史家;另一頭則要使自己成為社會史家,或只關注人類日常生活的普通歷史學家。而他的特殊工作就是要集兩任於一身。
在我看來,洛夫喬伊對於思想史研究的最大貢獻之一似乎在於,在追溯觀念的發展時他一再堅持超越純思想領域的必要性。觀念時常在思想世界的非常不同的領域中遊移,有時潛藏其中,這一事實使得洛夫喬伊的堅持是必要的 。例如在18世紀,中國庭院的自然觀便通過各種途徑傳入歐洲,其影響不僅可以在純藝術領域中深切感受到,而且也可在文學與哲學中感受到 。在《存在的巨鏈》中,洛夫喬伊通過追溯某些柏拉圖哲學的觀念歷經時代在不同領域——形而上學、宗教、藝術、科學、道德價值,甚至是政治傾向——中的展開與影響,從而令人佩服地示範了其方法帶來的豐碩成果。同樣令人欽佩的是他對那些二流作家作品的挖掘,這些作品據信甚至往往更加清楚地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傾向。
我們這一代思想史家特別面對的另一個長期存在的困惑是因果觀念的問題。受歷史唯物論,最近更直接的則是受知識社會學的衝擊,人們今天普遍傾向於從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出發思考觀念。將觀念隔絕在不受時間影響的真空裡的傳統習慣已經衰退。在許多方面,這種變化須被認為是人類認識技能的改善,但儘管如此,它也帶來了困擾思想史家的新難題,上述因果問題就是其中之一。的確,歸根到底觀念是否只應被視為特殊社會歷史過程的反映,或是否應當相信觀念在塑造人類社會中有些作用,無論這種作用多麼有限,這個問題只是自由論與決定論長久爭論的一個側面,這裡絕對不可能論及這個問題,即使是淺嘗輒止。我涉及這個問題只是因為它與本文的寫作有直接的關聯。如我所見,對於一個持決定論的歷史學家來講,決不可能有這種意義上的「觀念史」,即觀念也擁有它自身超越社會歷史環境的歷史,即便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所有的觀念必須要追溯到各自的社會起源,所謂的觀念史或思想史因而被還原為在寬泛意義上正當地帶有社會歷史的上層建築構件特徵的東西。另一方面,或者我們走到另一極端,只相信某些哲學家宣稱的「觀念創造歷史」 ,固執地拒絕將觀念與其社會淵源間的甚至非常明顯的聯繫考慮進來,這樣的研究結果將不再是令人滿意的。因此,實際情況一定是介於兩者之間。正如羅素曾說:「哲學家兼因果於一身:他們既是他們時代的社會環境、政治和制度的結果,如果他們幸運的話,又是塑造後代的政治與制度信條的原因。」 儘管這個觀點可能難於把握而無法實際運用,但它拓展出一個廣闊的空間使得思想史家能夠自由地發揮他的技能和判斷力,而捨此則無所適從。
令人鼓舞的是,現代的思想史家已普遍地認為,在一個有限的程度上,「人對局勢的有意識的反應構成了改變局勢的動力之一」 。或者,在某種限定的意義上,觀念的確具有自己獨立於社會環境的生命 。正如後文中我們的討論將清楚地顯現出來的,這種假定是我自己為本文設定的性質與目標的理由之一。
二、方法與目的
本文是一個寬泛意義上的思想史研究,通過對生死觀及相關問題的討論來尋求將東漢思想中的高、低兩個層面聯繫起來,其主題下文詳論。我先簡要解釋一下處理此問題的方法。我的研究將集中在與本文的主題,即東漢生死觀,相關的一些觀念上。我深知,以這樣一種方式來進行一種思想史研究,利弊參半。如我現在所理解的,其長處之一是它能使我們追尋一種觀念在各個時代及不同面貌下的變遷;另一方面,在我看來,其最大的缺陷之一,似乎在於對研究所涉及的單個著作家的關注非常不夠。因此本文並不試圖在總體上去呈現任何思想家的思想,無論他多麼重要;只有當某個人的思想與所要討論的問題有直接的關聯時,才會去引證並加以研究。換言之,涉及的只是每位作者的某些方面而已。
本文雖以東漢為題,大約時跨西元初的兩個世紀,但我的討論並沒有嚴格限制在該時段。有時一旦某一觀念在東漢時尚處於潛在的狀態而在後代變得更為活躍,我會將這一觀念的考察往後延伸到西元3或4世紀。不過更多的是,我試圖盡可能追溯它們各自的早期淵源,從而總體上能夠更確切地評價和更容易體會它們在這一時期思想史的重要性與意義。畢竟思想史家的任務不只是指出有這樣的思想潮流,而且還要指出它們流自何處、流向何方。
採取這樣的研究方法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我接受觀念也有自身的生命、自身的歷史這樣的看法,因此它們不應該只被看作一個既定社會的附屬物。觀念的變化是為了調整應對新的社會局勢,但是觀念的變化本身正可用作觀念擁有其自身的生命與歷史的很好證據。其次,如前所述,本文處理的是思想的兩個層面。在民間的層面上,我大量使用了那些作者或甚至若干作者不為我們所知的作品,這種作者的不確定性使得通過透視他們各自的社會背景來考察觀念變得困難起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忽視了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對觀念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性,事實上正相反。
史華茲依據他所說的「人們對局勢的有意識的反應」重新界定思想史的焦點,在許多方面是有道理的 。就東漢時期,我隨手能舉一個例子來支持他的觀點。王充的《論衡》在現代幾乎已獲普遍讚譽,它是東漢思想成就的凸出標誌之一,現在發現他的許多新觀念為西元3世紀重要的哲學運動的興起鋪平了道路;另一方面,《論衡》也是最好的一面鏡子,它清楚地反映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許多方面。此外,王充對他自覺到的局勢的反應決不是消極的,他的反應具有高度的自覺意識。王充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批評家,幾乎沒有一種流行的觀念、習俗、迷信、信仰或風氣能逃脫他的尖銳批評。只有佛教沒有遭到批評,而學者們已以此作為「默證」來否定西元1世紀或更早佛教已流行於中土的傳統看法。在本文中,我也將《論衡》作為一種主要材料在各種可能的方面加以引用。因此,將觀念盡可能地與其一般社會背景聯繫起來也是這項研究的目的。在如此做的過程中,我甚至有一個更好的證明自我的理由。正如前文所述,在思想的低層次上,思想史與社會史非常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任何將它們分開加以研究的企圖都會無望地勞而無功且令人絕望;對此,只要瀏覽一下一些社會史方面的權威著作就足以一目瞭然。塞繆爾‧迪爾(Samuel Dill)的《從尼祿到馬可‧奧勒留的羅馬社會》和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中世紀的衰落》對於各自關注的時代的觀念,特別是民間層面上的觀念,都做了富有洞察力與細緻的分析。在此方面,它們也可以有相當的理由被視為思想史著作。這兩本書,特別是前者中有關迷信、不朽信仰、宗教等章節和後者有關生死觀的章節,啟發了本文的撰寫。
我之所以研究生死觀,是考慮到這個論題的普遍性。東漢與任何時代或社會一樣,生死問題屬於困擾所有人——不論貴賤、賢愚、士俗、貧富——的具有最普遍意義的極少數問題。人們直接或間接,清楚或隱晦,自覺或不自覺,都會對此問題給出自己的答案。可以相信,通過周密、細緻地分析這些回答,儘管非常模糊,人們或許能夠看到該時代被稱為「時代精神」 或「輿論氛圍」的東西 。更不用說,所謂的「時代精神」或「輿論氛圍」,從界定上看是一種能感受到卻無法捕捉到的難以捉摸的含混之物。這解釋了為什麼一些思想史家認為這是一項特別困難的工作 。此外,如果這種東西存在,它顯現於人們生活的幾乎各個方面,因此,研究者可以從各個方向去接近它,並用不同的觀點去描述它。當然,下文我要說的只是從更為普遍的觀點去理解時代的一種可能方式。
根據我對漢代各種生死觀的研究,我確信漢代的精神活動的走向,正如洛夫喬伊所界定的,可以簡便地概括為「此世性」(this-worldness)。在對彼世性與此世性作一般性區別時,洛夫喬伊說:
我所用的「彼世」這一觀念,並不指對於未來生命的信仰和關心。繫念的死後將是什麼情況或一腔心思都想著你所希望得到的歡樂即將來臨,那顯然是對「此世」戀戀不捨的一種最極端的方式。如果把「彼世」想像成與「此世」並非截然異類,而是大體相同,則「彼世」不過是「此世」存有模式的延伸而已。在這一想像中的「彼世」,將和我們所熟知的「此世」一樣,依然是一個由變動、感性、多元與塵緣所共同構成的世界。所不同的只是塵世中的苦略去了,樂則提升了,以補償人在生前所遭受的種種挫折罷了。如果人們所嚮往的「彼世」是這樣,那麼它在本質上恰恰是對「此世」依戀的一種最極端的表現。
據此,我們可以簡單地概括一下漢代與生死觀尤其相關的此世精神。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人們對於此生的態度。一般來講,那時人們對人世具有強烈的依戀感,他們渴望長壽而害怕死亡。此外,他們關心世俗的事務並受世俗道德的約束,當然,這點在下文還將作進一步的解釋。其次,其來生觀念是這個時代此世精神的最好反映。這個時代的來生觀念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成仙而升至天堂,在那裡人欲不再遭受壓制;另一種是人性化了的死後世界概念。死肯定是件恐怖之事,但是當它最終到來時,人們不得不作為不可避免的事實而接受它。但是,人們並非無所作為,即仍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將人世延伸到死後世界使自己得到安慰。無論哪種情況,時人執著於依戀此世的強烈感受的程度顯現得非常鮮明。
不過,漢代的此世精神在不止一個領域清晰可辨。轉到思想史的另一個問題,即思想的高、低層面間互動,我們甚至仍可以對此點作進一步的闡明。
我們可以將東漢時期的儒學、民間道教分別視為代表思想的高層面與低層面,但是,這種一般性的區分需要作一些說明。由於儒學在漢代已成為國家所崇信的學說,它不僅得到帝國朝廷的支持,而且也不斷得到士人階層的完善,儒學被視為思想的高層面是容易理解的。確實,並不能簡單地用這個事實來表示漢代的儒學僅停留在上層社會;如其一貫所為,漢代儒學也意在教化社會下層,因此做出各種各樣的努力以普及其說教。儘管如此,就整體而言,尤其當我們聯想到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東漢的《白虎通》這樣的正統儒學著作時,將儒學與漢代有教養的士人聯繫在一起是有理由的 。另一方面,漢代的民間道教由於構成非常多元,要確定它是什麼相當困難。幸運的是,我們還有一部名為《太平經》的道教經典可以利用,現在一般都認為它包含著一些有關東漢的材料,並代表了東漢下層民眾的思想與感情。下文我們還將談到它,現在先讓我們簡單地假設它是一本民間道教的著作,進而來考察一下它在此世問題上及其與儒學關係上的一些基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