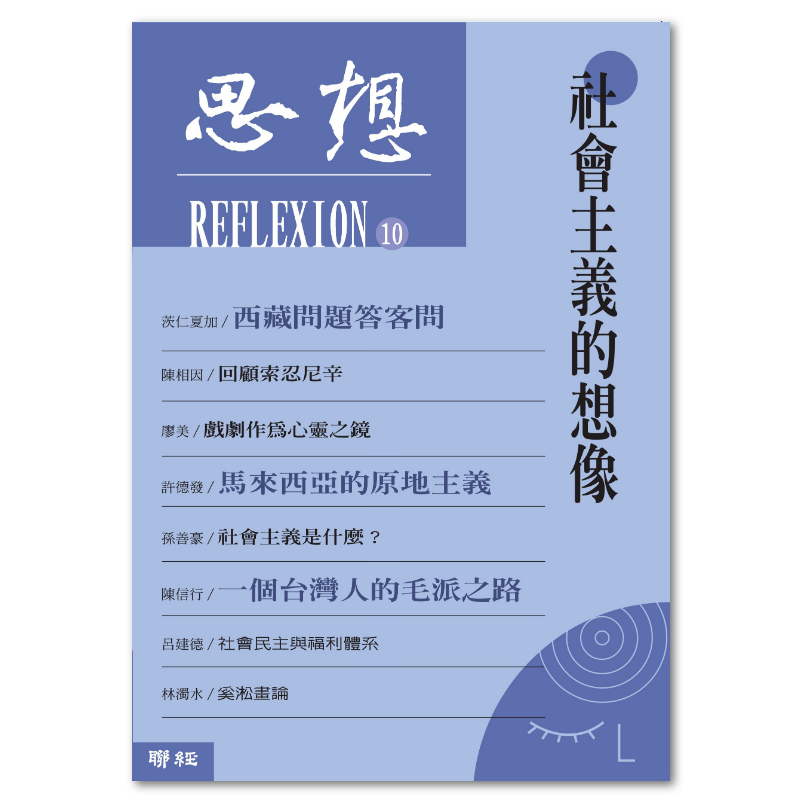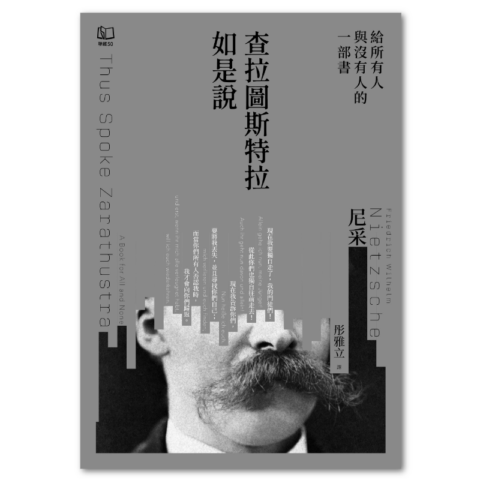社會主義的想像(思想10)
出版日期:2008-10-01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36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3263
系列:思想
尚有庫存
兩百多年前,當歐洲的舊體制正在崩潰、「現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逐漸成形之際,「自由、平等、博愛」三個理念一氣呵成,凝聚體現了整個時代的嚮往。但歷史演變弄人,這個口號所包容的一體社會理想,後來卻分化崩離,蛻變成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套意識型態,彼此呈現水火之勢。
這套理念之所以分化,關鍵在於有一個龐大的、具決定性力量的歷史結構──資本主義──必須面對,可是面對的方式卻有兩種迥異的可能。自由主義有條件地接受了資本主義的多數制度前提,而社會主義卻相信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如今,經過了上百年的爭鬥,資本主義依然健在甚至益形壯大,不過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反而雙雙陷入危機:蘇東的崩潰與中國的轉向,說明了社會主義傳統有先天性的盲點;而自由主義遭放任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鵲巢鳩佔,也顯示自由主義的價值意識不夠明確清晰。這兩種政治傳統有必要相互參考,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功過與動力,也重新整理「自由、平等、博愛」這套理念的現代含意。
歷史上,「社會民主主義」曾經特別有意識地想維持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有機結合,後來遂演成資本主義體制之下實行多黨民主、社會保障的福利國家。在西方,當蘇東式國家社會主義結束之後,社會民主對某些殘存的左派似乎是僅餘的選項。在中國,近年也有人在呼籲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轉化為社會民主主義。即便在台灣,雖然多年以來視社會主義為禁忌,但只要統獨這個雞肋爭議聲勢稍斂,便不乏有人想像社會民主或者「第三條路」。類此的發展,要求我們不僅去思考社會民主,也要思考整個社會主義傳統、包括它對內與馬克思主義、對外與自由主義的關係。
因此,本期《思想》的「社會主義的想像」專輯,有著很重要的時機背景。張君勱學會延續已經解散的中國民主社會黨香火,對社會民主自然關切,熱心幫助本刊規劃了這個專題。不過,社會主義所指不限於社會民主;在這個專輯的五篇文章之外,讀者會發現,本期「曹天予與民主社會主義」欄下的三篇文章,以及陳信行先生對前期《思想》上陳明忠先生訪談的回應,也都直接介入了社會民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參照可能性等嚴肅議題。不難理解,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社會主義就不會喪失存在的理由。問題是:它說得清楚自己存在的理由嗎?分辨得出自己該以甚麼形式存在嗎?依據現實條件、但是又不為現實條件所侷限地回答這些問題,即構成了社會主義的「想像」。
可以預期,既然涉及「社會主義」這樣敏感的議題,各方對本期這些文章的反應會多采多姿、甚至難免激烈高亢。我們很歡迎大家參與討論、相互攻錯。但不容諱言,歷來左派內部的爭論──從馬克思本人一直到今天的各路理論家──不時會陷入一種以「正確」自居、以「反動」誣人的窠臼,十分不健康。而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爭論,也往往以區分敵我為尚,少了一份包容心態與學習的欲望。本期陳信行先生對陳明忠先生的回應,雖然不惜以「毛派」這個引人側目的頭銜自許,卻既不失對前輩的尊敬,又表現了對自己信念的堅持,這種兼顧尊重與原則的爭論倫理,值得推許。我們自然還希望,社會主義之外的其他立場與意見,也願意各抒己見,彼此參考和理解。
必須指出,本期茨仁夏加和錢理群兩位先生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以及許德發先生關於馬來西亞華人處境的分析,都涉及了今年發生的事件,目前正在進行中,未來也還會有新的發展,極具現實意義。(馬國最近的「華人寄居論」風波,即為一例。)但在思想層面,兩篇文章都涉及了國族認同以及包容差異這兩項具有高度普世性的難題,值得台灣乃至於整個華人世界參考。
另外,還有陳相因小姐紀念索忍尼辛、單德興先生訪問哈金、廖美小姐從兩個面向呈現戲劇史的發展軌跡、以及林濁水先生挖掘奚淞畫作中「時間」與「平淡」兩項旨趣,均幫助本刊開拓了一些此前較為疏忽的面向,讓所謂的「思想」不以觀念的邏輯論述為限,反而延伸到其他形式、媒介的呈現、深入到更為細緻敏感的藝術與文學世界,取得豐富的內涵與表現。我們盼望類似的擴展延伸,能夠繼續。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茨仁夏家 西藏問題答客問
錢理群 尊重差異,尊重西藏
許德發 馬來西亞:原地主義與華人的「承認之鬥爭」
陳相因 時代的考驗:回顧與評論索忍尼辛
思想訪談
單德興 辭海中的好兵:哈金訪談錄
思想劇場
廖美 愛爾蘭的戲劇、劇場與劇作家
走上戲劇的時光隧道
戲劇作為心靈之鏡
社會主義的想像
楊偉中 在「社會民主」以外:關於社會民主主義歷史的筆記
傅可暢 「民主社會主義」討論的現代中國背景
萬毓澤 從社會民主到社會主義民主
呂建德 民主社會主義是東亞的選項嗎?:以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福利體系為例
石之瑜 民主與社會主義不在台灣或大陸?
曹天予與民主社會主義
孫善豪 甚麼是社會主義?
馮建三 到底誰雇用誰?
錢永祥 社會主義如何參考自由主義:讀曹天予
討論與回應
陳信行 一個台灣人的毛派之路:回應「新民主主義者」陳明忠先生
林濁水 奚淞畫中的時間性和道藝合一的策略
書評書序
馮品佳 亞裔美國研究的新輿圖與新典範:評單德興《越界與創新》
郝志東 走向民主與和諧:澳門、臺灣與大陸
致讀者
兩百多年前,當歐洲的舊體制正在崩潰、「現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逐漸成形之際,「自由、平等、博愛」三個理念一氣呵成,凝聚體現了整個時代的嚮往。但歷史演變弄人,這個口號所包容的一體社會理想,後來卻分化崩離,蛻變成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套意識型態,彼此呈現水火之勢。
這套理念之所以分化,關鍵在於有一個龐大的、具決定性力量的歷史結構──資本主義──必須面對,可是面對的方式卻有兩種迥異的可能。自由主義有條件地接受了資本主義的多數制度前提,而社會主義卻相信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如今,經過了上百年的爭鬥,資本主義依然健在甚至益形壯大,不過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反而雙雙陷入危機:蘇東的崩潰與中國的轉向,說明了社會主義傳統有先天性的盲點;而自由主義遭放任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鵲巢鳩佔,也顯示自由主義的價值意識不夠明確清晰。這兩種政治傳統有必要相互參考,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功過與動力,也重新整理「自由、平等、博愛」這套理念的現代含意。
歷史上,「社會民主主義」曾經特別有意識地想維持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有機結合,後來遂演成資本主義體制之下實行多黨民主、社會保障的福利國家。在西方,當蘇東式國家社會主義結束之後,社會民主對某些殘存的左派似乎是僅餘的選項。在中國,近年也有人在呼籲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轉化為社會民主主義。即便在台灣,雖然多年以來視社會主義為禁忌,但只要統獨這個雞肋爭議聲勢稍斂,便不乏有人想像社會民主或者「第三條路」。類此的發展,要求我們不僅去思考社會民主,也要思考整個社會主義傳統、包括它對內與馬克思主義、對外與自由主義的關係。
因此,本期《思想》的「社會主義的想像」專輯,有著很重要的時機背景。張君勱學會延續已經解散的中國民主社會黨香火,對社會民主自然關切,熱心幫助本刊規劃了這個專題。不過,社會主義所指不限於社會民主;在這個專輯的五篇文章之外,讀者會發現,本期「曹天予與民主社會主義」欄下的三篇文章,以及陳信行先生對前期《思想》上陳明忠先生訪談的回應,也都直接介入了社會民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參照可能性等嚴肅議題。不難理解,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社會主義就不會喪失存在的理由。問題是:它說得清楚自己存在的理由嗎?分辨得出自己該以甚麼形式存在嗎?依據現實條件、但是又不為現實條件所侷限地回答這些問題,即構成了社會主義的「想像」。
可以預期,既然涉及「社會主義」這樣敏感的議題,各方對本期這些文章的反應會多采多姿、甚至難免激烈高亢。我們很歡迎大家參與討論、相互攻錯。但不容諱言,歷來左派內部的爭論──從馬克思本人一直到今天的各路理論家──不時會陷入一種以「正確」自居、以「反動」誣人的窠臼,十分不健康。而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爭論,也往往以區分敵我為尚,少了一份包容心態與學習的欲望。本期陳信行先生對陳明忠先生的回應,雖然不惜以「毛派」這個引人側目的頭銜自許,卻既不失對前輩的尊敬,又表現了對自己信念的堅持,這種兼顧尊重與原則的爭論倫理,值得推許。我們自然還希望,社會主義之外的其他立場與意見,也願意各抒己見,彼此參考和理解。
必須指出,本期茨仁夏加和錢理群兩位先生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以及許德發先生關於馬來西亞華人處境的分析,都涉及了今年發生的事件,目前正在進行中,未來也還會有新的發展,極具現實意義。(馬國最近的「華人寄居論」風波,即為一例。)但在思想層面,兩篇文章都涉及了國族認同以及包容差異這兩項具有高度普世性的難題,值得台灣乃至於整個華人世界參考。
最後,身為編輯,我們要強調,「拓展視野」是本刊的夙願。在這個意義上,陳相因小姐紀念索忍尼辛、單德興先生訪問哈金、廖美小姐從兩個面向呈現戲劇史的發展軌跡、以及林濁水先生挖掘奚淞畫作中「時間」與「平淡」兩項旨趣,均幫助本刊開拓了一些此前較為疏忽的面向,讓所謂的「思想」不以觀念的邏輯論述為限,反而延伸到其他形式、媒介的呈現、深入到更為細緻敏感的藝術與文學世界,取得豐富的內涵與表現。我們盼望類似的擴展延伸,能夠繼續。
馬來西亞:原地主義與華人的「承認之鬥爭」
許德發
前言
馬來西亞人在2007年剛剛慶祝其建國50周年紀念。當紀念日迫近之際,舉國上下包括華人社團組織,也不落人後地加入這個集體大合唱的慶祝行列之中。值得注視的是,華人社會的紀念主題顯得高度一致,即各方不約而同都在強調馬來西亞華人在建國中的貢獻,並宣示效忠。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全國各州中華大會堂在獨立前夕(8月17日)同步舉行國家獨立50周年升旗禮,以“表達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國土忠心”(見《星洲日報》,2007年8月18日)。實際上,“周年”往往是人們藉以正視歷史的時刻,但是人們如何紀念並不是沒有客觀理由的,也不是不帶任何現實考量的。
馬華公會婦女組主席黃燕燕醫生最近就獨立慶典說,“每當接近國慶月,社會上就有一些冷言冷語,矛頭指華人不愛國,對國慶慶典冷感,這都不符事實”。她進而強調,大馬華人對建國之路有一定的貢獻,不容質疑,但同時她又“希望華人在大馬獨立50周年慶時,也反省該扮演的角色,確保得到其他民族的肯定。”(《南洋商報》,2007年8月28日)這段話在華社中是頗具代表性的,它說明了華人社會在“效忠宣示”中所面對某些困擾與背景。以當代西方哲學家泰勒的術語來說,華社之“效忠宣示”顯然表明,華人還在追求國家對其貢獻、忠誠之“承認”(recognition),而且“刻意”的要“確保得到其他民族的肯定”,這也正是泰勒所說的“求取別人承認”。儘管我們也常見馬來人高唱愛國歌曲及揮動國旗,但是他們的“忠誠宣示”似乎比較自然自在得多。這種對比,本身其實已是一個值得我們加以思考的現象了。
實際上,華人社會這種強調自身貢獻與宣示效忠的舉措並非今日始;它一直面對的“不被國家承認”窘境,可上溯至英殖民地時代。在西方學界,少數族群在大社會中的不利處境,業已成為當前政治理論討論的焦點所在(參見金裏卡,2005)。本文嘗試從歷史的縱向視角切入,並借用當代學界一些相關的研究論述,尤其是“承認的政治”理論所提供的進路,以解剖華人社會“不被承認/ 要求承認”之根源,及其所造成的困擾與影響。
馬來原地主義與移民的效忠問題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馬來人似乎無需刻意宣示效忠,也無人對之提出質疑,這是因為他們被普遍視為──而且也自視及自我宣稱──擁有這片土地的“主權”。有學者即指出,馬來人的“忠誠”比華、印二族更“自然”,非馬來人的忠誠度在許多方面則是“人為的”(artificial),而且兩者的“忠誠”存有本質性的差異,即非馬來人的效忠是政治性質的,而馬來人則多了一份文化歸屬感,即忠於歷史存在——固有的社會傳統與制度 (Ratnam,1965: 28-30)。因此不難看到,與華人的“宣示效忠”不同,馬來人所反復強調的則是自身的“土著/土地之子”(son of the soil)地位,並由此得到判斷他人“忠誠度”的道德制高點。然而,從世界與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宣示其實並不新鮮,它廣泛發生在近代世界各地,其思想源頭來自於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領地/原地主義”話語(參見霍布斯鮑姆,2000)。
因此,要理解馬來人的原地主義,我們首先有必要追述民族國家與公民權利相互關係的含蘊。自近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後,在其大纛之大力揮舞下,一個人的身份歸屬往往無不依據其國族身份。個人只有獲得公民身份,才能獲得權利,因此也才能和主權發生關係,才能承載主權。然而,一個人怎樣獲得公民身份?答案是“從原籍地獲得身份”,即一個人只能借助於他的出生,借助於他出生的地點和民族而獲得身份。一言以蔽之,現代的民族主義及其高漲的民族意識,使得國家被迫只有承認“民族的人”(nationals)才是公民,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只賦予特定民族共同體的成員。難怪阿倫特就相信“民族國家的衰落和人權的終結”存在著必然的聯繫(阿倫特,1995)。那些沒有國家的人或少數族裔們自己也知道,民族權利的喪失就等於人權的喪失,前者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後者。由此可見,所謂的天賦人權,一旦離開了一個國家的公民的權利形式之後,就缺乏現實性基礎了 —— 除非它植根於民族共同體 —— 正是這個共同體才能保護其民族同胞的權利。這意味著在一定意義上,國家由法律機器轉化為民族機器,民族可謂征服了國家。民族國家因此否定人類多樣性,其常態之一為打造一個“同質性的國家”。它沒有耐心去調適、包容分歧的其他族群文化之差異,而只想以所謂國家的標準改變、整合既有的不同規範。
之所以如此,阿倫特將之歸咎為民族主義“通過把公民與民族成員混為一談,把國家視為民族工具”的做法所導致,因而違反了多樣性的原則。在歷史中,這種尋求一致性的民族國家主義殘害了全球少數、移民族群的文化尊嚴。她認為,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各國內部“少數民族”備受挫折的命運,便是這樣產生的,它們至多只能安於二等公民的地位,最壞時則被大規模的逐出自己的家園和國家(阿倫特,1995)。簡言之,許多研究現代民族國家的學者已經指出,民族國家建構的常態之一是,對內它走向同質化,對外則具排他性。但更值得本文注意的是,民族主義又往往與土地/領地緊密地相聯繫,許多民族主義者都主張民族有其神聖的土地起源,而這是不可退讓的。這就是為何領土完整是民族國家神聖不可侵犯的範疇,自古以來即出現了層出不窮的土地爭奪戰。具體至現代“馬來民族”(Bangsa Melayu)概念而言,誠如一些學者指出的,它正是近代民族觀念的產物,尤其受到了西方的殖民知識及種族觀念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馬來民族是一種“政治性”的概念,是英國殖民時代的產物,最早也只始於1800年代,到1900年代初期才告穩固(詳見Shamsul ,2004:135-148;Hirschman,1986: 330-361)。馬來民族主義者基本上也模仿了“原地主義”邏輯操弄,把這個國家的土地本質化為“Tanah Melayu”(馬來人之土/ Malay Land ),即“馬來人的馬來亞”,並以此合理化、鞏固他們在馬來(西)亞不容挑戰之主體位置。根據這個邏輯,馬來亞的土地是馬來人的土地,馬來亞的文化是馬來人的文化。
從1920年代開始,當華人及印度移民人口大量增加之際,馬來人在深切的危機感作用下,開始覺得必須要有組織的力量來捍衛他們的權利(Radin,1960:11-13;Roff, 1994),有關他們屬於土地之子的論述也開始流行(Siddique and Leo, 1982: 663-664)。第一個馬來人政治組織——SMU (Singapore Malay Union)的尤諾斯(Encik Mohammad Eunos)在立法議會上就曾如此高分貝的喊出:
不論馬來人有怎樣的缺點,可是他們沒有共產黨分子,也沒有兩面效忠。不管其他民族如何講到土地的佔領,我確切地覺得,政府充分瞭解到,到底是誰把新加坡割讓給英人,與馬來半島的名稱是根據什麼人而來的。(Straits Times, 27 Jan. 1948)
對馬來民族主義者而言,馬來人的效忠與馬來人主權是不可質疑的,而華人則具有兩面效忠。在殖民地時代,華人對國家的效忠被無情的質疑,曾被似是而非的視為中國潛伏著的第五縱隊,隨時會向馬來人反撲。甚至英國人也如此想,大批左派分子即被驅逐回中國。對馬來民族主義者而言,他們自認在其他族群到來之前已經在此定居,並建構了自身的統治制度。因此,歷史絕不是空白一片的,打從麻六甲王朝時代始,他們就建立了以馬來統治者為主體的馬來主權國家之延綿系統,而這個歷史事實必需持續下去。他們認為,其他族群的湧入是殖民地統治的結果,這也扭曲了歷史的自然發展;既然馬來社會建制、傳統是固有的,那麼外來者需要“調適”自己於固有的馬來歷史境況之中,更甚於要他們(馬來人)放棄某些特殊要求(Ratnam,1965:30)。
在這樣的論述下,馬來人是國家主人(tuan),往後並逐漸據此建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馬來霸權(ketuanan Melayu)敍述,而其他民族是“客”,都是外來者、非原著民,他們必須融入馬來單一文化之中,不然就請“回歸祖居地”(這正是馬來政客經常提及的)。尤有甚者,當國家獲得獨立之後,經五一三事件後的馬來民族建國主義氣焰高漲時,國家對本國的人民普遍採用了“土著/非土著”(bumiputra/ non-bumiputra )二分法作為享用、分配國家發展資源和財富的資格確認方式(Siddique and Leo, 1982: 675),結果除了更進一步固化了馬來原地主義的論述,也激化了華人的困擾與意識危機。依據此“土著/外來者論”,馬來民族在此片土地上理所當然的擁有特權,其他民族則都被鄙視為外來者,不可享有國民平等的待遇。
同時,問題還有另一面,大英不列顛帝國本身基本上也是一個民族國家,它骨子裏也吃這一套。甚至於將馬來半島本質化為馬來人之發祥地,即上述的“Tanah Melayu”和“Malay Peninsula”稱謂的出現,亦與英國建構的殖民知識緊密相關,而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對“Malay Annals”(馬來紀年)之整理及重新命名,被認為是此一知識的一大源頭(參見Shamsul,2004:144-145)。這就把華印等移民社群置於先天性的身份與權利困境之中。從歷史及法律的觀點來看,英國在馬來亞的政治權力建築於各邦蘇丹的主權上(楊建成,1982:116)。在英國官員的眼中,這片土地的主權原本奪自馬來蘇丹手中,這就形成了他們“馬來亞歸馬來人”的意識形態定見。從1920年代開始,殖民地當局逐步實行“親馬來人”政策。
直到了二戰後,這項保護馬來人的特殊地位的政策一仍即往。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馬來亞獨立談判時期,一開始英國政府就認定了馬來人作為主權歸還的對象。當時的殖民地欽差大臣就曾針對華人公民權利益對陳禎祿說,只要巫統說“Yes”,英國這方面就沒問題。在現代民族主義之原地主義的作用下,作為移民的馬來西亞華人根本欠缺政治法統與現實實力,因此所謂的“民族解放”,自然不在他們“天賦”的權利之中(許德發,2007:233-46)。在現代國家依據國族身份獲得國籍概念下,既然華印等族被視為外來者,自然也都沒有與生俱來的“天賦”公民權利,其權利只能是被賦予的——歸化。東姑在獨立前夕曾就公民權事宜明確聲言,英國政府必須把國家主權歸還馬來人,再由馬來人決定是否賦予其他族群公民權。在另一方面,作為馬來人主權象徵者的馬來統治者,從來不肯承認華人是他們的臣民(subject),無論華人在此居留的時間有多長。
所謂歸化,涉及了宣誓效忠的問題,這是現代國籍概念的題中之義。故此,在獨立建國的過程中,華人等所謂外來族群之公民權必須是在宣誓效忠之下獲得的。“宣示效忠”註定從一獨立開始就永遠跟隨著華人,甚至直到今天,公民權與效忠仍然是一個常見的公共議題。這與馬來人作為“蘇丹子民”自動獲得公民權截然不同。實際上,即使華人公民權後來在政治妥協下(以馬來特權作為交換)稍有放鬆,大部分華人也都獲得公民權,但早期的巫統並不把它等同于“國族地位”。當時的首相東姑阿都拉曼,直到1966年之前從不承認“國族地位”是公民的基礎,而且一直拒絕談及國家的國族稱謂,這是因為擔心這將為馬來人及非馬來人之間的平等鋪路( Funston, 1980: 137-138)。由此可見,巫統在公民權課題上雖做出讓步,使得大部分華人獲得公民權,但他們絲毫不放棄“馬來國家”的建國理想:只有馬來人才具國族地位。如此一來,“國家的公民”與“民族的成員”已經變得不能混為一談,也就是說,對國家的“效忠”以及對民族的“認同”(identity),在概念上有相當的差別。當時巫統對此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他們“給予”華人的是“公民權”(citizenship),但公民不等同於國族(national),所以公民之間自是不平等的。在馬來民族對國家建構理想的壟斷之下,馬來西亞先天性的沒有建立普遍公民國家的條件,這也成為馬華人的基本難題。
基本上,一切親馬來人政策或馬來人特權之制訂的合法性,來源無不自此馬來原地主義話語,並都以此為前提,這是華人在馬來西亞所面臨的最本質性的凜冽挑戰。華人或印度人都在這套沉重的話語底下,開始了他們不平等的公民身份與效忠困擾。從此以後,華人一方面必需時時刻刻、小心翼翼地對待其與母國(中國)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必須時常、大力的宣張自己對馬來西亞的效忠與貢獻,來確保他人認可自己對這片土地具有不可置疑的合理地位,也以此作為平等權利爭取的理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