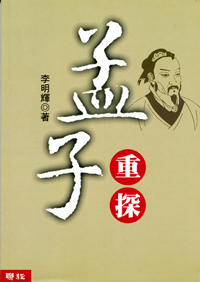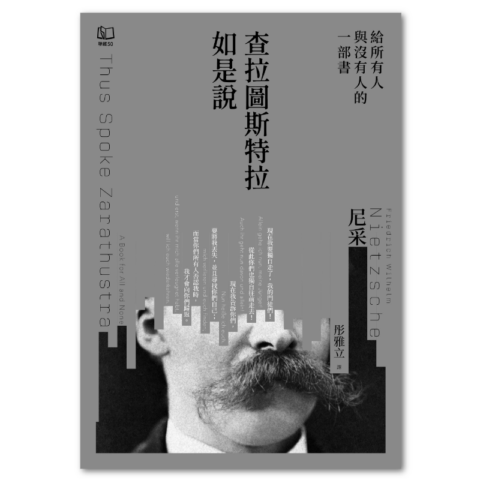孟子重探
出版日期:2001-07-04
作者:李明輝
印刷:平版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193
開數:正25開
EAN:9789570822366
系列:中國哲學與思想
已售完
宋代以後,孟子思想在儒家傳統中取得正統的地位。但自清代以還,孟子的性善說已不大能為學者所理解,不時有人對此說提出質疑、乃至批判。民國以來,在西方文化的強烈影響下,孟子思想在中國的知識界更乏解人。本書作者相信:孟子的心性論、乃至道德哲學,縱使放在現代學術的脈絡中,仍是極具意義的一套思想;但這需要經過一番重建的過程,透過現代學術的概念將孟子思想納入現代學術的脈絡中,使它與現代人的問題意識相激盪。從這個信念出發,作者先後撰寫了本書所收錄的五篇論文,從現代的觀點與問題意識重新詮釋孟子的心性論、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本書是作者繼1994年出版的《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之後,第二部專論孟子思想的著作。
作者:李明輝
原籍臺灣屏東,1953年出生於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及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其後獲得「德國學術交流服務處」(DAAD)獎學金,赴德國波昂大學進修,於1986年獲得該校哲學博士。曾擔任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客座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廣州)中山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目前已退休。主要著作有《儒家與康德》、《儒學與現代意識》、《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康德倫理學發展中的道德情感問題》(德文)、《儒家思想在現代中國》(德文)、《孟子重探》、《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儒家人文主義:跨文化的脈絡》(德文)、《儒學:其根源與全球意義》(英文)、《康德與中國哲學》,譯作有H. M. Baumgartner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康德的《通靈者之夢》、《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未來形上學之序論》及《道德底形上學》。
序 i
《孟子》知言養氣章的義理結構 1
孟子王霸之辨重探 41
焦循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及其方法論問題 69
再論牟宗三先生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 111
性善說與民主政治 133
參考文獻 169
人名索引 183
概念索引 189
1993及1994年筆者和鍾彩鈞先生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推動「孟子學主題研究計畫」,邀請國內外學者約二十人參加。 為此,我們於1994年5月20及21日舉辦了一場「孟子學國際研討會」,並且編了一套《孟子學研究叢刊》(目前已出版了五冊),收羅此項計畫參與者及其他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筆者曾在《孟子思想的哲學探討》一書的〈導論〉中將我們推動此一研究計畫的理由陳述如下:
清代以還,孟子的性善說已不大能為學者所理解,不時有人對此說提出質疑、乃至批判。民國以來,在西方文化的強烈影響下,孟子思想在中國的知識界更乏解人。一般知識分子或許會贊許其民本思想,視之為過渡到民主思想的預備階段;但對於其性善說,多半認為它經不起現代科學思想的考驗,至多視之為一種主觀的善良願望。〔…〕臺灣的學術界往往從現代心理學與社會科學的角度來質疑孟子的性善說。中國大陸的學術界過去在馬、列教條的禁錮之下,將孟子思想定位為反映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唯心論系統,自然不會贊同其性善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學術界逐漸開放,馬、列教條的限制有逐漸鬆動之勢,但是在孟子思想的研究方面,並無多少成績可言。根據筆者對於中國大陸近十餘年來孟子學研究的粗略印象,多數論文仍無法擺脫唯心、唯物的思想框框;少數論文雖已不再使用這套框框,但仍無法接上現代學術的脈動。民國以來,在中國的學術界真能接上孟子思想的慧命,並且能面對現代學術的挑戰的,大概只有一般所謂的「當代新儒家」了。除此之外,孟子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可謂難覓解人。〔…〕
據筆者的淺見,孟子的心性論、乃至道德哲學,縱使放在現代學術的脈絡中,仍是極具意義的一套思想。當然,這需要經過一番重建的過程,透過現代學術的概念將孟子思想納入現代學術的脈絡中,使它與現代人的問題意識相激盪。譬如,我們可以問:孟子的心性論如何面對現代心理學的成果,而有一個恰當的定位?其道德哲學如何面對現代社會科學的可能質疑而自我證成?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韋伯式的問題:孟子的政治、經濟思想與現代化的關係如何?是阻力還是助力?抑或可以在經過轉化後成為助力?筆者相信:孟子思想就像過去其他具有原創性的思想一樣,在經過重新詮釋之後,可以提供許多可貴的思想資源,幫助我們去面對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這正是我們推動「孟子學主題研究計畫」的主要目的。
在我們的研究成果陸續發表之後,有些學界的朋友對我們表示肯定與鼓勵,認為我們的研究開發了一些新議題,開拓了一些新視野,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進路。筆者在推動此一研究計畫的過程中,也不斷發現新的問題,而深感有繼續深入探討之必要。故在此一計畫結束之後,筆者仍繼續思考相關的問題,又先後撰寫了四篇論文,加上為此一計畫所撰寫的〈《孟子》知言養氣章的義理結構〉一文,共累積了十餘萬字的研究成果。為了便於學界同行的參考與指正,如今將這五篇論文輯成一冊。這是筆者繼《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之後,第二本關於孟子思想的書。
〈《孟子》知言養氣章的義理結構〉是在上述的「孟子學國際研討會」中發表之論文,其後收入筆者所編的論文集《孟子思想的哲學探討》。筆者並將此文改寫成德文,刊於德國期刊Oriens Extremus 。在《孟子》書中,〈公孫丑上〉第二章(一般稱為「知言養氣章」)是極具理論關鍵性的一章,因為它涉及孟子的基本觀點(特別是「仁義內在」說)及他與告子間的爭論。然此章向來號稱難解;尤其是對於告子的「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一語,以及孟子反對告子的理由,歷來的詮釋者無數,但難有善解。筆者在此文中同時從語法和義理這兩個層次入手,嘗試為此章提出一種可能的新詮釋。
〈孟子王霸之辨重探〉一文首先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1998年5月16日舉辦之「孟子學研討會」,其後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3期(1998年9月)。此文透過關於孟子「王霸之辨」的討論來說明其思想中道德與政治的關係,而展示了與前人不同的詮釋角度。
〈焦循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及其方法論問題〉一文係臺灣大學推動的「中國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之成果,曾先後於臺灣大學主辦的「中國的經典詮釋傳統」研討會(1999年3月27日)及香港城市大學主辦的「經典與評注:中國闡釋學傳統國際研討會」(1999年10月15及16日)中宣讀,其後刊於《臺大歷史學報》第24期(1999年12月)。此文係以焦循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為例,來檢討乾嘉漢學的方法論,並指出其盲點。
〈再論牟宗三先生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則是在鵝湖雜誌社、山東大學、中國孔子基金會與中央研究院共同主辦而於山東濟南舉行的「牟宗三與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1998年9月5至7日)中發表。筆者過去曾發表〈儒家與自律道德〉一文 ,討論牟宗三先生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並且反駁黃進興先生對牟先生的批評。〈再論〉一文則是針對後續的討論所作之進一步的回應與檢討。
本書所收的最後一篇論文〈性善說與民主政治〉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推動的「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之成果, 最初於1995年4月22及23日該計畫的研討會中發表,其後收入劉述先先生所編的論文集《當代儒學論集:挑戰與回應》(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此文主要是針對「民主政治必須預設對人性的不信任」的流行觀點,探討將孟子的性善說與民主理論相結合之可能性。
以上五篇論文雖是在不同的機緣下先後撰成,卻有一貫的思考線索,即是從現代的觀點與問題意識重新詮釋孟子的思想,故以《孟子重探》為總標題。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整個中國文化圈已逐漸顯示出一股力圖擺脫百年來占居主流的反傳統思想之趨勢,而體認到:人類理性之發展必須透過對文化傳統的重新詮釋而取得動力。本書之作可視為這種努力的一部分,希望能與學界同道分享,並得到其坦率的指正。筆者曾因〈《孟子》知言養氣章的義理結構〉及〈孟子王霸之辨重探〉二文而得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研究獎勵,且因後一文得到傑出研究獎,藉此出版之機緣特致謝忱。
《孟子》知言養氣章的義理結構
1
《孟子‧公孫丑篇》第二章記載孟子關於「知言」與「養氣」的理論,故通常稱為〈知言養氣章〉。此章所包含的哲學思想極為豐富,但因文字簡要,意義難明,以致在歷代的詮釋者當中引起不少爭論。這些爭論涉及兩個層次,即文字章句的層次和義理結構的層次。在筆者看來,歷代學者對此章的詮釋或偏於文字章句之訓詁,或偏於義理結構之闡釋,鮮能兼顧二者。過去的漢、宋之爭涉及訓詁與義理的本末先後關係。宗漢學者強調「有詁訓而後有義理」 ,宗宋學者則反詰道:「若不以義理為之主,則彼所謂訓詁者,安可恃以無差謬也?」 其實,訓詁與義理二者分別屬於詮釋的兩個相互獨立、而又相互關聯之層次,我們無法簡單地將一者化約為另一者。就二者之相互獨立而言,字義與語法基本上是約定俗成的,而非出於思想家之創造;但是反過來說,文獻所涵的義理亦非透過文字章句之訓詁所能完全確定,而有所謂「義理有時實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 的情況。就二者之相互關聯而言,我們固然須透過文字章句之訓詁來理解文獻所涵的義理,但由於文字本身所具的歧義性,特定字句在特定文脈中的意義有時反而要透過義理之解讀才能確定。這便形成當代西方詮釋學中所謂的「詮釋學循環」。
本文旨在闡釋此章所涵的基本義理,自然無法避免「詮釋學循環」的問題,而涉及字義與語法之討論。歷代注疏家有關本章字句的訓詁儘管汗牛充棟,但若干字句的訓詁對於本章基本義理之理解並無太大的重要性。因此,除非必要,本文將儘量避免牽涉到這類的討論,以免因枝蔓過多而使論點分散。質言之,本文的討論將集中在以下幾個義理問題:
1.「不動心」的意義為何?其類型如何畫分?
2.何謂「知言」?何謂「養氣」?兩者之關係為何?
3.孟子何以批評告子之「不動心」?兩人所根據的義理架構有何不同?
4.告子何以主張「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何以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在上述諸問題當中,第四個問題最具關鍵性,但也最難解。由於前三個問題均環繞著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若得不到恰當的解答,我們便不可能把握全章的義理結構。
這些問題主要出現在〈知言養氣章〉的前半部,為了便於討論,我們不妨將這整段文字摘錄於下,並且根據討論的進展將全文分為四段。
1.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2.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3.「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4.「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2
在第一段的記載中,孟子與公孫丑討論「不動心」的意義及其類型。公孫丑首先問孟子說:「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舊注對「動心」一詞的解釋無甚出入,在此可以舉朱注為代表:「〔…〕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 根據此注,「動心」起因於面對霸王之大業時所生的恐懼疑惑。趙岐以「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來解釋「動心」二字 ,大體亦是此意。周群振先生另有新解,以為「動心」意謂「此種居(加)相行道,以及霸王之事業,是否會當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而為之激盪或顛簸欣動其心也」 。此解強調當事人完成王霸之大業後在心理上所受到的影響。周先生為其新解所提出的理由亦能言之成理,可備一說 。但筆者以為舊注較能與下文相呼應,因為孟子在下文討論北宮黝等人的「不動心」之道時,總是關聯著「勇」之德而強調其「無懼」(所謂「勇者不懼」)。若依新解,「無懼」之意便無著落。不過,我們可以不去深究這個問題,因為不論「動心」之起因何在,公孫丑之提問僅是為了引發討論,而作為下文「不動心有道乎?」此一問題之伏筆。就字面意義而言,所謂「不動心」意謂「不受任何外在原因之刺激而動搖其心」,類乎古希臘斯多亞學派所追求的apatheia。但這只是從形式上規定「不動心」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之下,告子、北宮黝、孟施舍、曾子都可說達到了「不動心」之境地。但若究其實質,則此四人分別表四種類型的「不動心」。
第一種類型的「不動心」以北宮黝為代表。孟子形容其勇如此:「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朱注:「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也。」 其說大體可從。唯此處將「目逃」解釋為「目被刺而轉睛逃避」,殊不合常理。人的眼睛被實物所刺,豈能不轉睛逃避?依筆者之見,所謂「不目逃」當是意謂「面對他人直視的眼光而不轉睛逃避」。
北宮黝之勇表現在他對外來的橫逆一概以直接的對抗回應之,完全不考慮對方力量之大小。這是藉著排除外來的橫逆或反抗外在的力量,使己心不受其影響,朱子所謂「以必勝為主」是也。《荀子‧性惡篇》將「勇」分為上、中、下三等,而說:「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其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北宮黝之勇正是所謂的「下勇」。但問題是,一個人的力量再大,也有其限度,不可能期於必勝。這種必勝之心其實是虛妄的,故荀子說:「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 這種人一旦面臨無可抗拒的情勢或力量時,其勇便無可表現,唯有徒呼負負而已,如項羽在垓下之圍時所感慨者。
相形之下,孟施舍之「不動心」便大異其趣。他明白勝不可必(「舍豈能為必勝哉?」),故不求勝人,但求「能無懼而已矣」。其勇表現於「視不勝猶勝」,即無論勝負得失,其心均能不為所動。若是「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則猶懷有對失敗的恐懼,自不足為勇。故朱注云:「舍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子接著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為何以曾子來比擬孟施舍,並不難了解,因為他同樣稱許二人為「守約」。至於他為何以子夏來比擬北宮黝,舊注均不甚貼切。徐復觀先生以《墨子‧耕柱篇》所載子夏之徒與墨子間的一段爭論來解釋,較能言之成理 。根據這段記載,墨子主張「君子無鬥」,子夏之徒則以為:「狗豨猶有鬥,惡有士而無鬥矣!」 當時子夏之徒似有好勇之名,故孟子以子夏來比擬北宮黝。朱注云:「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 就氣象而言,曾子內斂,子夏外發,故孟子以二者來比擬孟施舍和北宮黝。相較於北宮黝之一味向外求勝,孟施舍在自己的主體上有所守,而較能得其要領,故曰「守約」。據孟子所說,孟施舍所守的是「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其實,北宮黝所憑藉的也是「氣」,他與孟施舍不同之處在於:孟施舍守氣以求超越勝負得失之心,北宮黝則恃氣以求勝。有些學者以為「孟施舍之守氣」一語與上文所云「孟施舍守約也」相牴牾,而主張將「約」字改為「氣」字,以求其一律 。此甚無謂,因為「約」並非像「氣」一樣,屬於主體的結構。「守約」猶如今語所謂「把握要領」,係相對而言。相對於北宮黝而言,孟施舍較能把握要領,故曰:「孟施舍守約也。」但是相對於孟施舍而言,曾子卻更能把握要領,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朱子語類》云:「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 其說是也。
「氣」這個概念像「心」一樣,在本章是個具有關鍵性的概念。孟子在下文即將「心」與「氣」相對舉,並且解釋道:「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朱注以「心之所之」為「志」 ,故論志即是論心。在《孟子》書中,論「心」之處不少。這個概念通常有其確定的意指,即是指「本心」或「良知」,亦即指人之道德主體。譬如,〈告子上〉第十五章所說「心之官則思」之「心」,顯然便是指道德主體。「志」即是心之意向(intention)。相較於「心」,「氣」屬於一個較低的層級,而從屬於「心」,故曰:「志,氣之帥也。」孟子以「體之充」來說明「氣」,這個「體」字顯然是指形體。趙注云:「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 便是以「形體」釋「體」字。故「氣」的概念在此與人的形軀相關聯,屬於同一層級。黃俊傑先生指出:中國古典中所謂的「氣」有「雲氣」、「氣息」、「血氣」諸義 。此處所言的「氣」當是指血氣。徐復觀先生在解釋「氣,體之充也」這句話時說道:「其實,古人之所謂氣,並非僅指呼吸之氣,而係指人身生理的綜合作用,或由綜合作用所發生的力量。換言之,氣即由生理所形成的生命力。」 簡言之,在〈知言養氣章〉中,「心」是指人的理性生命(此處偏重道德理性),「氣」則是指其感性生命,「心」與「氣」之關係相當於孟子所謂「大體」與「小體」之關係。
對於孟子而言,「心」在主體的整個結構中實居於核心的地位,而為真正的自我之所在;相形之下,「氣」居於次要的或邊緣的地位,其意義和價值必須透過它對於「心」的關係來決定。在這個意義之下,孟施舍之守氣,尚未真正把握住要領。反之,曾子之養勇,係在「心」上作工夫,這才真正把握了要領。曾子之勇表現為:「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即「自省」之意。至於「縮」字,趙岐訓為「義」 ,朱子訓為「直」 ,均可通。較難解而有爭議的是「吾不惴焉」這句話。焦循《孟子正義》引閻若璩《釋地三續》云:「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為『不敢』、『如』為『不如』之類。」 據此,則此為反詰語,而全句可譯為:我反躬自省之後,以為不合理義,雖然面對地位低下的人,豈能無所懼?我反躬自省之後,以為合於理義,雖然面對千萬人,亦勇往直前。自反所憑藉者為理性,故表示「心」之作用。在孔子弟子之中,曾子善於自反,故《論語‧學而篇》第四章載其言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總而言之,孟施舍與曾子在養勇工夫上的差別在於:前者所守者為氣,後者所守者為心;套用理學家的話頭,前者是「氣魄承當」,後者是「義理承當」。至於北宮黝,雖亦以氣為憑藉,卻著眼於對象,而一味求勝。
3
在〈知言養氣章〉第二段中,公孫丑追問孟子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則加以回答。這一段是最具爭議性、也最難於解釋的一段。筆者以為:迄今為止的絕大多數注疏均不得其解。第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是:孟子在這段對話中除了談到告子的工夫之外,是否也陳述了他自己的工夫?歷代注疏家似乎均理所當然地認為孟子在此亦陳述了他自己的工夫。但馮友蘭先生卻獨排眾議,而主張:
〔…〕我們可以斷定,此段俱為孟子述告子得不動心的方法的話。「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孟子直引告子的話。「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為孟子於敘述告子的話時,所夾入批評之辭。「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及「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為孟子代告子解釋之辭。此段述告子得不動心的方法,其方法為「持志」。
他並且提出三點理由,來支持他的說法:第一,「持其志,無暴其氣」一語之上僅有「故曰」二字,而非如下文所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可見前一句非孟子自己的話,而是他引述告子的話;第二,如果「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孟子得不動心的方法,則不但與下文所言「配義與道」的方法重複,而且這兩種方法大不相同;第三,如果孟子在此已自述其工夫,那麼,公孫丑接著問:「敢問夫子惡乎長?」豈非多此一舉 ?在這三點理由之中,第一、三點係單就語義脈絡來考慮,第二點則涉及思想內涵。
在筆者看來,這三點理由均不甚充分。就第一點理由而言,《孟子》書中有不少以「故曰」開頭的話顯然是孟子自己的話。譬如,〈萬章上〉第五章中所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及「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均係重複孟子先前回答萬章的話。又如,〈告子下〉第七章中的「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以及「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諸語,均係重複孟子自己的話。由此可見,「故曰」與「我故曰」的用法在《孟子》書中並無嚴格的分別。再者,第三點理由亦不足以反駁傳統的注疏。因為按照傳統的注疏來解讀,孟子在這段對話中只是如實陳述了告子和他自己的工夫,以及二者之差異,並未進一步評斷這兩者之高下;公孫丑「敢問夫子惡乎長?」之問則是要求孟子進一步評斷這兩種工夫之高下,故非多此一舉。
關於第二點理由,馮先生有一段詳細的說明。由於這段說明牽涉到「孟子何以反對告子不動心之道」這個關鍵性的問題,故值得引述於此:
告子得不動心的方法,為強制其心,使之不動。朱子《集注》說,告子的不動心,是「冥然無覺,捍〔悍〕然不顧」是矣。然若專就「不得於言」等十六字說,似尚不能見其強制之跡。如「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告子的話,則告子得不動心的方法,為「持志」。一「持」字,將把持強制之意,盡行表出。《朱子語錄》云:問:伊川論持其志,曰:「只這個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先生曰:「此亦似涉於人為。然程子之意,恐人走作,故又救之曰:『學者不恁地不得』」。(《語類》卷五十二)「持志」是一種把持強制的工夫。所以是「自私」,是「涉於人為」。說孟子以這種工夫,得不動心,伊川朱子,似亦覺有未安,但因滯於文義,故又只得說:「學者不恁地不得」。
馮先生對於告子不動心之道的詮釋基本上係根據朱子之說,因此他贊成朱子對「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這句話所作的詮釋 。只不過馮先生進一步根據朱子對於告子不動心之道的詮釋來理解「持其志,無暴其氣」這句話,而朱子卻以為這是孟子自述其不動心之道的話。
但在筆者看來,朱子對「不得於言」等十六字的詮釋大有問題,故馮先生據此所作的詮釋亦有問題。因此,要解決上述的爭議,我們必須先解決另外兩個問題:第一,告子所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何解釋?第二,孟子何以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依筆者之見,這兩個問題對於〈知言養氣章〉之詮釋最具關鍵性;而且它們是相互關聯的,必須同時解決。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我們不妨先檢討傳統注疏家對這兩個問題的看法。首先看趙岐注:
不得,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這段解釋甚為牽強,因為在〈知言養氣章〉中,「言」與「氣」是兩個具有獨立意義的概念,趙岐卻將它們當作一般的用語。再者,依趙岐的解釋,「言」、「心」、「氣」均是就他人而言,在此完全看不出在自己的主體上有任何工夫可言。更荒謬的是,根據趙注,「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所重的是外在的言辭,「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卻以內心的動機為重,告子的說法何致如此自相矛盾?或許正因為趙注過於牽強,後代的注疏家多不採納其說。
在後人對這段文字的解釋中,廣泛為人所接受的是朱子的解釋。朱注云:
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這段解釋似乎較為合理,因為相對於趙注,朱注至少將「言」與「氣」當作兩個具有獨立意義的概念。再者,依朱子的解釋,告子亦有工夫可言,即所謂「固守其心」是也。《朱子語類》中有兩段話說得更明白:
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先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
據此,告子「不動心」的工夫不免令人聯想到佛、道兩家的制心工夫。焦循《孟子正義》在疏解趙注之後,便長篇引述毛奇齡《逸講箋》之說,而將告子的工夫比作道家之「嗒然若喪」與佛家之「離心意識參」 。毛氏之說基本上係承襲朱子的解釋。
近人對這段文字的解釋亦率多沿襲朱注。譬如,徐復觀先生便如此解釋告子所說的「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告子達到不動心的工夫,既不同於勇士,也不同於孟子,而是採取遺世獨立,孤明自守的途徑。一個人的精神,常常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因而會發生擾亂(動心)。告子的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對於社會上的是非得失,一概看作與己無關,不去管它,這便不至使自己的心,受到社會環境的干擾。〔…〕「得於言」,即所謂「知言」,亦即對客觀事物作知識上的了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是對於不了解者,讓其不了解,不用心去求了解。這與莊子「知止於其所不止,至矣」(齊物論)的態度甚為吻合。告子「生之謂性」的觀點,也與莊子的性論非常接近。孟莊同時而未嘗相聞,告子或亦是莊子之徒。
至於告子所說的「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他解釋道:
他的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乃是把自己的心,和自己的生理作用,隔絕起來,免使自己的心,被自己的生理作用要求所牽累而動搖。因為心既求助于氣,氣便可拖累及心;不如乾脆把它隔斷。後來禪宗中土第一祖的達摩,為二祖慧可說法,衹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指月錄卷四)。外息諸緣,是由告子的不得於言(言乃是諸緣)的進一步;內心無喘,即是不動心。
顯而易見,徐先生的詮釋亦承自朱子。
儘管以朱注為本的這套解讀方式自成理路,但筆者始終不能無疑,理由有二:第一,說告子是道家者流,畢竟是揣測之詞,欠缺直接的證據。第二,如此理解告子的不動心之道,便無法充分解釋孟子在下文所發「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的批評,因而也無法使人明白在〈告子上〉篇中告子與孟季子何以會主張「義外」之說。就第一點而言,近人持這種看法者除了徐先生之外 ,尚有郭沫若和龐樸 。這種看法除了欠缺直接的證據之外,也是出於對於告子觀點的誤解。對於這種誤解,黃俊傑先生已提出有力的辯駁 。此處暫且先點出問題之所在,筆者在下文還會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