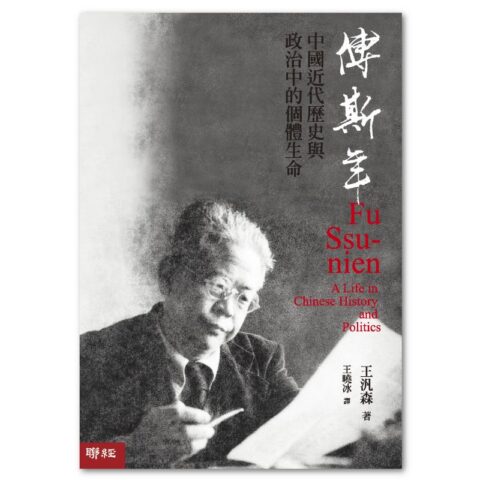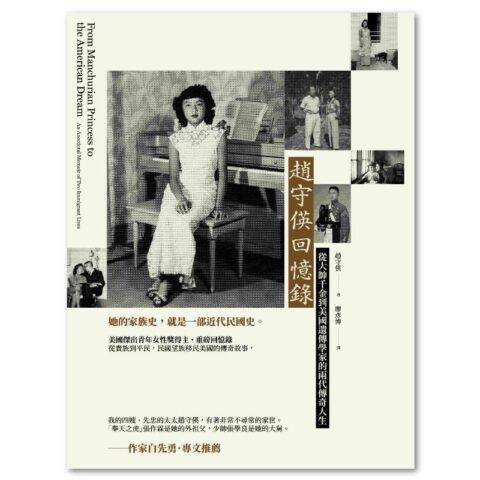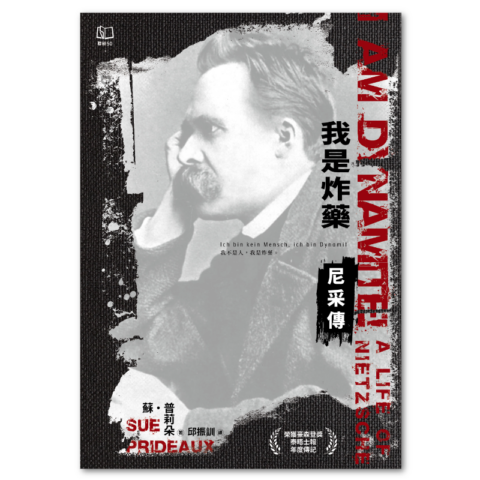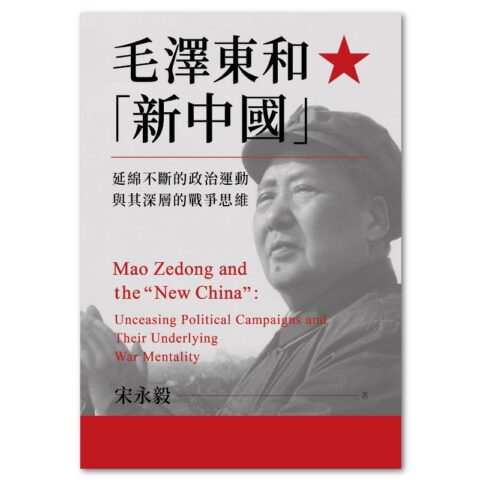從1917年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於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
在胡適個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階段,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他的博士學位問題,他的西洋哲學素養,他對毛澤東的影響,他和蔣介石的關係……隨著《胡適日記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問題已能夠獲得比較明確的解答。
本書根據《胡適日記全集》的內在線索,探討胡適在各個階段與中國現代史進程的關聯,並就上述引起議論的疑點,擇其較有關係者予以澄清,讓胡適自己說話,盡量還胡適一個原來面貌。
作者:余英時
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後記
為了趕上今年5月4日的出版時限,這篇長文是在4月中之前的十幾天之內匆促完成的,可以說是一篇急就章。當時我只能就手邊所有的資料,鉤勒出一個整體的大輪廓,而無暇在一切細節上面,廣事稽考,以求精確。
最近我讀到胡適的《英文信函》(《胡適全集》本第40和41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發現原文第五節「出使美國(1937──1946)」中的一些推斷都可以在英文信中得到證實。例如我曾根據《日記》,斷定1945──1946年秋季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正式任教一學期,但《日記》極為簡略,不足以定案。現在讀了他在1945年5月28日和同年6月13日給富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的兩封信,這個問題便完全解決了。從第一封信中,我們知道他的授課期間是從10月到第二年的1月,每星期講課兩次。從第二封信中,我們更知道哥大最後將他這4個月的講學待遇調整為4000美元。(見《全集》卷41,頁510-511;524-525)這都證明他所擔任的是一學期的專任教職。
不但如此,他在1942年9月大使卸任後的出處問題,《日記》中語焉不詳,只有從當時英文信件中才能獲得比較清楚的記述。他在1942年9月24日給女友韋蓮司(E.C.Williams)的信中說:
我已經接到許多美國大學的邀請,包括康奈爾、哥倫比亞、哈佛、芝加哥、威斯康辛、巴恩斯基金會(Barnes Foundation,原注:羅素正在那裡任教)和其他地方。但是我已決定先休息一段時期,然後再考慮何去何從。(《全集》第41卷,頁325)
這時他的卸任消息才傳出十幾天,各大學已爭相聘請如此,可見當時美國學術界對這位 「學者大使」的尊重之一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大學的重金禮聘案。他在1942年12月22日給芝大校長赫琴斯(Robert Maynard Huchins)的回信中,特別申謝芝大以美金1萬元的年薪聘請他前往任教的誠意,他說:「這比我的大使年俸還要高。」但是他為了全力撰寫未完成的「中國思想史」,已決定接受美國學術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研究補助費」(“grant in aid of research”),因此不得不辭謝芝大的聘約。(見《全集》第41卷,頁350-352)「研究補助費」只有6000美元,(見1942年11月25日給waldo G. Leland的信,同上,頁332-335),遠不能與芝大的待遇相比。但在這一出處取捨之間他的中心價值所在也充分顯露了出來:他始終是一位「學人」,把原創性的學術研究放在第一位,世俗的名位和金錢不在他的主要考慮之中。
最後,我要對「赫貞江上之第二回相思」這一有趣公案(在第五節之末)稍作補充。這一段文字,台北《聯合報》副刊曾以〈赫貞江上之相思〉為題在今年5月3日和4日單獨刊布,引起不少讀者的興趣。5月30日傅建中先生在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了〈胡適和R.L.一段情緣──回應余英時先生的「大膽假設」〉,對於胡適和Roberta Lowitz之間的一段情緣進行了「小心求證」的工作。他首先根據一部最新的杜威傳記,將有關Lowitz和杜威、胡適交往的基本事實扼要地呈現了出來。(這部傳記是Jay Martin, 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其次,更值得稱道的,傅先生還直接向南伊利諾大學的杜威研究中心索取了胡適給Lowitz的兩封親筆信,並譯成中文以饗讀者。這樣一來,我根據《日記》所做的「大膽假設」便基本上證實了。由於胡適親筆信的發現,我們現在確切知道,胡適稱Lowitz為「小孩子」(Hsiaohaitze),而自稱「老頭子」(Laotoutze),這是他們兩人之間的親密隱語,具有極不尋常的涵義。
在新資料的啟發下,我現在對於「赫貞江上之第二回相思」要重新加以檢討。我在原文中判斷,這一段情緣的發生,Lowitz似乎是原動力。「老頭子」和「小孩子」的暱稱則進一步支持了我的判斷。我相信這是由於Lowitz開始向胡適示愛時,後者以年齡為搪塞,說對方還是「小孩子」而自己已是「老頭子」了。事實上,胡適在這裡運用了傳統詩人、文士對於「紅粉知己」一種「欲迎而故拒」的手法。吳梅村〈無題〉之三結句說:
年華老大心情減,辜負蕭娘數首詩。
這兩句詩便是「老頭子」和 「小孩子」的「典雅」版。何況胡適很早已有「倚少賣老」的結習(見趙元任1930年慶祝胡適40歲生日的賀詞,收在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171-173);這時當然免不了要重施故技,以緩和Lowitz的攻勢。現在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胡適用「老頭子」、「小孩子」兩個暱稱究竟始於何時?傅建中先生所引的英文信,最早的一封是1938年11月30日,已遠在「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1938年7月12日)之後。我最近又發現了一條絕妙的證據,使我們對這一段情緣的認識更清楚了。去年出版的《北京大學圖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收入了一封「小孩子」給胡適的電報(“Hsio Hai Tze to Hu shih”),日期是1938年7月7日(頁262)。這時胡適正在密西根大學講學,所以電報是由密大教授霍爾(Robert Hall)轉交的。電文如下:
“Recieved forwarded letter today. Miss Laotouze unbelievably. Returning New York. Love. Hsio Hai Tze”(今天收到轉來的信。想念「老頭子」到了令人不能相信的地步。即返紐約。愛。「小孩子」)
顯而易見的,Lowitz並不熟悉中文的拼音,以致「老頭子」和「小孩子」都各漏去了一個英文字母。但這是小問題,可以置之不論。這一簡短電報的證據價值是多方面的,而且無比的重要。讓我一一道來。
第一、我在原文中說,胡適7月10日從密西根回到紐約,Lowitz當天便來看他,大概是胡適首先將歸期告訴了她,或事先通過電話。從電文中「收到轉來的信」一語,現在我們可以確定:胡適是寫信通知的,因為這是一封回電。第二、「老頭子」、「小孩子」早在胡適6月30日動身去中西部之前便出現了。自從4月14日Lowitz邀他吃茶開始,兩個半月之中胡適和她交往頻繁,五、六兩個月已達到了幾乎形影不離、時時「久談」的地步,而6月29日兩人的「郊遊」則更標志著情感上的一次跳躍。所以Lowitz向胡適示愛而終於引出「老頭子」和「小孩子」的暱稱,最遲也是6月29日「去郊外遊」的時候發生的,或者更在其前。此時胡適尚不滿47歲,固然不能說是「老頭子」,而Lowitz則已30有4(她生在1904年),無論如何也和「小孩子」沾不上邊。所以這兩個稱呼只能是兩人之間的情感已達到公開談論的階段才可能出現。在確定了Lowitz的意向之後,胡適大概曾對她表示過下面的意思:「我已是一個『老頭子』了,而你在我看來還是一個『小孩子』,我們之間的年齡距離太大了。」這是這兩個暱稱之所以產生的事境和語境,否則胡適不可能忽然異想天開地自稱「老頭子」,稱對方為「小孩子」,而且還鄭重其事地將這兩個暱稱的英文拼法寫出來,讓她記住。第三、「想念『老頭子』到了令人不能相信的地步」,是一句份量極重的話,道盡了小別七日的「相思」之苦,大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風味。「老頭子」讀到這一句時,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第四、電報的最後一個字是「愛」,更能打動胡適的心。試讀他在1941年的一首「無題」詩:
電報尾上他加了一個字,
我看了百分高興。
樹枝都像在跟著我發瘋。
凍風吹來,我也不覺冷。
風呵,你儘管吹!
枯葉呵,你飛一個痛快!
我要細細的想想他,
因為他那個字是「愛」!
(《嘗試後集》,收在《全集》第10卷,頁344)
此詩自注「三十年(一九四一)冬」作,本事已不可考。但1941年1月11日胡適獲知Lowitz丈夫(Robert Roy Grant)的死訊,曾去電致悼。他是不是因此而勾引起3年前的一段記憶,才寫了這首「無題」詩,我們並不能輕下斷語。無論如何,「小孩子」的這個「電報尾上」則千真萬確地加上了一個「愛」字 ;此外在1938到1941這3年間胡適所收到的電報之中,我們還沒有發現第二封是 以「愛」字結尾的。「無題」詩也許與「小孩子」完全無關,但通過它,我們卻不難想像,胡適當時讀到這封電報時,一定也是「百分高興」,甚至「發瘋」!
詳細分析了「小孩子」1938年7月7日的電報之後,對於5天後(7月12日)「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我們便再也不會感到一絲一毫的意外了。胡適即使有過一點「心防」,也被「小孩子」這封電報徹底攻破了。Lowitz給胡適寫過信,也打過電報,但保存到今天的則只有這一封了,而它的證據作用竟如此之大,我們不能不特別感謝北大圖書館這部《未刊書信日記》的貢獻。
投桃報李,讓我對《未刊書信日記》中有關英文釋文的失漏處,略作訂正。
一、“Bert to Hu shih”,(頁198-199):“Bert”的全名是Bertha Mah。她是Wing Mah的妻子,見下條。Bert也是當時胡適的女性崇拜者之一,所以信末明白表示:她希望胡適不但是「冬秀的丈夫」而且也是「我的丈夫」,此外則不能再是「任何別人的丈夫」(“but no one else’s”)但這只是極端崇拜的一種表達方式,與愛情無關。讀者不可誤會。
二、“Ibing Wah to Hu shih”(共二信,頁265-267)。按:“Ibing Wah”是“Wing Mah”誤釋。他的中文姓名是「馬如榮」,自1930年代起便在加州大學柏克萊(Berkeley)分校政治系任教。他一家人(包括妻子和兩位女兒)都是終身「胡迷」,詳見《胡適日記》及《英文信函》。Wing Mah在1938年10月9日賀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的信中也特別提到:Bert早在9月初便希望當時的大使是胡適,而不是王正廷(C.T. Wang),見頁266。
三、“V.K. Willingtucker(?)to Hu shih”(共二信,頁330-332)按:釋文在英文名字之下加一問號,表示不能十分確定之意。其實“V.K. Willingtucker”應讀作“V.K. Willington Koo”即大名鼎鼎的顧維鈞。他當時(1938)是中國駐法大使,所以兩信首頁都用的是「巴黎中國大使館」(“Ambassade de Chine, Paris” )的信箋。這兩封信都是討論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的問題。其中第二函(8月27日)是答覆胡適8月20日的信,胡信收在《全集》卷40,頁340-341。兩信都出自顧的親筆,是很珍貴的原始文件。
四、“Someone to Hu shih(1938.7.25)”,頁347。這也是顧維鈞的親筆信,簽名是“V.K.W. Koo”。胡適在7月27日有覆函,見《全集》卷40,頁337-338。
五、“Someone to Hu shih (1938.5.11)”,頁346。按:簽名是 “ H.J. Timperley”。他是 Manchester Guardian報的駐華記者,熱心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他有一封給E.C. Carter的信,已收入本書作為附錄(“Appendix: H.J.Timperley to Edward C. Carter(1938.6.9.)”,頁224-225。Timperley5月11日給胡適信首段所提到的他一部即將刊行的新書便是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書局的介紹辭也收入本書頁226。
六、“Someone to Hu shih (1938.9.27)”,頁349。按:簽名是“Archie Rose”,全名為“Archibald Rose”。他是英國文化教育界的一位領袖人物,1926年胡適為中英庚款委員會事到英國訪問,他便是一位主要接待人。所以1926年12月30日胡適離英前夕,他親筆寫了4頁的告別信,感謝胡在英國留下的積極影響,筆跡和本書所收的信完全相符。
七、“Someone to Hu shih”,頁353。這是本書所收的最後一封信,寫於1922年10月23日。作者的簽名是“Osvald Siren”。他是瑞典Stockholm大學的教授,專治中國藝術史,著作甚多。他的六巨冊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6-1958)至今仍是中國畫史研究中的基本參考書。胡適初識他在1922年3月18日,地點是北京的六國飯店,見《胡適日記》。
以上僅就所知增補於上,其餘還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因手頭資料不足,一時又無暇廣徵博考,唯有俟之異日。總之北大所藏《未刊書信日記》的史料價值極高,上引「小孩子」的電報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任何關於胡適生平與思想的深入研究都不能完全依賴中文史料,英文文獻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這是我寫完這篇〈後記〉所得到的一個最深刻的感想。
2004年9月4日 余英時
赫貞江上之相思
胡適不為人知的一段情緣 (上)
余英時
我在《胡適日記全集》(以下稱《日記》)中發現了胡適一九三八年夏季的一段短短的情緣。讓我先把材料抄在下面,再逐步解說。
4月14日:
Roberta Lowitz邀吃茶,她談在Jamaica看英國人的荒謬,我很感興趣。她去參觀其地之醫院,為揭發其種種弊政,頗引起反動。殖民地之政治,至今猶如此,可恨。
4月16日:
今天Robby來談,同吃飯,下午始去。
4月20日:
與Robby同飯,久談。
4月29日:
與Robby同飯。
5月11日:
與Roberta Lowitz去看Susan and God,是去冬最好的戲。
5月22日:
訪Robby小談。
5月23日:
與Miss Lowitz同吃飯。
5月26日:
Robby來吃午飯。
5月31日:
R.L.從Washington回來,邀去談話。
Robby即Roberta的親切稱呼,R.L.則是Roberta Lowitz的縮寫。胡適在一個半月之間和她吃茶、吃飯、久談、小談、看戲至九次之多。其間隔較長的空隙則是胡適外出演講和公事忙迫的日子,我在《日記》中已一一查證,5月26日與31日之間則因Robby有華府之行。換句話說,只要胡適在紐約,他幾乎每天或隔一天都和Robby一起吃飯和交談,這是引起我對Robby其人好奇的起源。胡適這次為救亡而來,《日記》中的人物無一不和爭取美國的支持與同情有關。他在紐約期間所接觸的美國人很多,而頻率之高則未有能比Robby者。然而到5月31日為止,《日記》完全沒有透露Robby對胡適究有何種重要性,她又是以什麼身分見知於胡適的。直到6月3日Robby的真面目才開始顯露,這天的日記寫道:
到Dewey先生家,他剛把他的大作Logic: Theory of Inquiry今天送去付印,故他很高興,要我去談天。我們談得很高興,許久沒有這樣痛快的談天了。後來Miss Lowitz也來了,我們同去吃晚飯。
至此我才能初步斷定,胡適認識Robby是由於杜威的關係。下面兩條日記便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推斷。
6月21日:
杜威先生邀我與Robby同吃飯,在Crillon Buffet。飯後他們同到旅館中談。
6月26日:
早上杜威先生與Robby同來,約去Shelton Hotel吃早飯,飯後與他們告別,他們出城遊行,我回旅館收拾行李。
第二條日記毫無問題說明Robby是杜威的助手或秘書之類。這時胡適也將離美遊歐了,所以要收拾行李。
雖然如此,胡適與Robby兩人之間的交往則遠多於他三人共同聚會的次數。整個6月,胡適大忙,也偶有三兩天的外地活動,但他和Robby的單獨往來還是相當頻繁。
6月11日:
看Robby的病,久談。
6月12日:
與Lowitz同吃飯。
6月15日:
Robby進醫院割扁桃腺,下午我去訪問。
6月22日:
今天是畫像最後一次,約Robby同去看看,他說不壞。
6月24日:
(下午)九點半到Columbia Broadcasting Network,十點我廣播"What can America Do in the Far Eastern Situation",共用十三分鐘。(中略)回到旅館,(李)國欽夫婦打電話來賀,Miss Lowitz打電話來賀,I. C. Lee(?)打電話來賀。他們都說廣播字句十分懇切明顯。
這件事很說明Robby對胡適一言一行多麼密切關注,和他最好的老朋友李國欽一樣。第二天(6月25日)日記寫道:
晚上與Miss Lowiz同去Long- champs吃飯。
在此百忙之中他還抽空與Robby單獨進餐。27日和28日他到外地去講演,30日起,他將有11天(6月30至7月10日)的中西部講演之旅。在唯一空檔的6月29日,他記道:
Miss Lowitz邀去郊外遊,是一種休息。
郊遊似乎預示著他們關係將進入一個新的起點。胡適7月10日下午回到紐約,《日記》說:
Robby知道我回來了,自己開車與我同去遊Hudson Parkway,回到他寓所小談。
Robby「知道」他回來了,若不是胡適事前已將行程表告訴了她,便是回來後給他打了電話。他去歐洲的船期已定在7月13日,12日他有李國欽的飯約,討論王正廷大使「大借款」的案子,下午去海關領取航行許可證,晚上有三十餘位友人的送行宴會。午夜以後更須趕火車到華府,以便12日上午向大使館、國會圖書館、國務院各處辭行。他是下午回到紐約的。在如此馬不停蹄奔走了兩天一夜之後,《日記》說:
Robby開車與我去遊Henry Hudson Parkway,到Arrowhead Inn吃夜飯,月正圓,此是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也。
(參見「胡適手跡」)
這條日記清楚顯示出兩人的情感發生了一個跳躍。「月正圓,此是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已道盡了一切,本不須再說什麼。但胡適在「相思」兩字之下塗去一字,又在條末添了一句帶括弧的註語:
(看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附鈔的小詩。)
從字跡的濃淡和位置判斷,似乎是幾年以後加上去的,若是當時所寫,那是不到三個月以前的事,須註明年份?塗去一字也必與註同時,濃得完全看不見原字了。我猜想塗去的或是「債」字,因為太明顯了,所以不能留下。註也是障眼法,所指「小詩」,現在已廣為人知。詩曰:
四百里赫貞江,
從容流下灣,
像我的少年歲月,
一去了就不回還。
這江上曾有我的詩,
我的夢,我的工作,我的愛。
毀滅了的似綠水長流,
留住了的似青山還在。
這首詩主要為思念早年女友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而作,所以第二天日記中便有「作書與Clifford」一語。「月正圓」則是他回念一九二三年和表妹曹珮聲在西湖煙霞洞「看月」的一段「神仙生活」。但胡適加註而又塗字是為了故意誤引後世讀者掉進他特設的陷阱,以為他又再度想起了少年時代的往事。其實他當天寫這條日記的真實心情毋寧更近於晏殊一首〈浣溪沙〉的下半闋: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債)」是落在「眼前人」的身上。這是他和Robby離別的前夕,第二天他便有歐洲之行,是否重來,當時是無法預測的。
胡適在船上有一條日記很有趣味:
7月16日:
開始寫信。(Prof. Hall、孟治、Robby)
得Clifford一電:"Young 173 Holland Park Ave. Clifford American Express August 6th."
有趣的是他給「眼前人」寫信,但卻同天收到「舊時人」的電報。韋蓮司的電報是說她將於8月6日到倫敦,並以倫敦友人Young的地址相告。後來他果然在一位Mrs. Eleanor Young家和韋蓮司相晤(8月21日),並有參觀博物館(8月22日)和吃下午茶(8月24日)等等活動。更絕的是Robby竟也在8月底趕到了倫敦,但陰錯陽差,胡適已於25日抵達蘇黎世(Zurich)開世界史學大會,Robby便只好從倫敦給他打長途電話了(8月29日)。「舊時人」和「眼前人」同於8月下旬到了倫敦,偶然巧合乎?有心追蹤乎?現在只有天知道了。(上)
【2004-05-03/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赫貞江上之相思
胡適不為人知的一段情緣 (下)
余英時
7月12日月圓之夜「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是他們兩人情感的高潮,但也是「月盈則虧」的始點(the beginning of the end)。10月3日他以中國駐美大使的身分重回紐約,便也已不可能和Robby再續「郊遊」之樂了。10月3、4、5日,他都「在紐約」,但《日記》上卻是空白,不知道和Robby見了面沒有,即使見過,大概也是在稠人廣坐之中。10月6日他便赴華府上任了,11月13日的日記說:
Dewey先生來吃午飯,Miss Roberta Lowitz同來。
這是一九三八年《日記》中最後一次提到Robby。但一九三九年《日記》還是記載了多次和Robby交往的事蹟:兩人「共飯」有兩次,一在紐約(6月20日),一在華府(7月30日),而且6月7日胡適到哥大接受榮譽學位之後,還特別去拜訪她。《日記》說:
去看Robby Lowitz,不在,也留一片。
回到旅館,劉敬輿(哲)來看我。
孟治來,幫我收拾行李。
Robby來,用車子送我到965 Fifth Ave, C. V. Starr的家中。
車行一二十分鐘之內,是他們唯一能單獨談話的機會。此外相見則在人多的場合(見《日記》10月9日、10月23日),不必一一引原文了。但最可見他們之間關係親切的是12月22日一次電話中的交談。《日記》說:
祖望回來過節。
Mrs. Grant(Robby Lowitz)打電話來說:昨天她同Dr. Dewey到W. 49th St.一家中國飯店裡去吃飯,她看見祖望同一班中國學生吃飯,她說,「那是胡適的兒子。」Dr. Dewey不相信,叫人去問,果然是的。Robby沒有見過祖望,竟能猜著,真是聰明。
她能猜著,當然是因為她對胡適的面貌神情太熟悉了,胡祖望確長得像父親,她不是毫無根據的胡猜。這也是《日記》中唯一的一次稱Robby為Mrs. Grant,這是她丈夫的姓,他們夫婦好像是分居。《日記》一九四一年1月11日條:
得Dewey先生信,又得Robby自己的信,都報告她的丈夫之死耗,為之嘆嗟。
這也是胡適在日記中最後一次提到Robby的名字。但《日記》有一段很大的空白,即胡適一九三八年12月5日得心臟病住進紐約Presbyterian Hospital的Harkness Pavillion,共77天。這77天完全沒有日記,但我們確知Robby在這段期間必曾多次來探訪胡適。有什麼證據呢?說來很有趣,證據是胡適在《日記》中塗抹掉的一句話。若無此抹去的一行,一個極重要的環節便脫落了。此句僅見於遠流影印本,大陸排印的《全編》本反而不「全」了。讓我把這條日記(一九三九年9月23日)引在下面:
我的舊日護士Mrs. Virginia Davis Hartman到美京,我請他在Wardman Park Hotel吃飯。(他談Robby事,頗耐尋味。)
括號中的末句是塗去的,但字跡仍清晰可辨(參見「胡適手跡」)。這位哈德門護士從一九三八年12月6日開始看護他的病(《日記》一九三九年3月13日),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一直照顧了20年,直到他一九五八年回台北定居為止。哈德門本來未必認得Robby,她們之所以熟識起來,一定是由於Robby在此77天中常來探病的關係。以胡適為軸心,哈德門也就開始和Robby有了交往,因而對後者的一言一行瞭如指掌。她當然知道胡適和Robby的關係,所以在談話中報告了Robby的近況。究竟Robby有何「事」使胡適覺得「頗耐尋味」,已成一永不能解之謎。但其「事」或與胡適不無關係,則可由他抹去此句而約略推測其如此。他之塗去此句與他在「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條下之塗字與加註是出於同一心理,這是可以大致斷定的。《日記》中所見胡適與Robby的一段短暫情緣,已盡於此。
現在我要進一步追問:胡適為什麼在此作「秦廷之哭」的緊張氣氛中,忽有此個人情感上的波動呢?首先我們必須從他的心情方面觀察:第一、一九三八年4月16日Robby第一次請他吃茶暢談時,他來到美國已半年多了,雖到處奔走呼籲,取得了不少民間社團的同情與支持,但畢竟緩不濟急,無助於國家的危難,心中充滿著焦慮。第二、在3、4、5、6幾個月,他非常注意報載戰爭形勢的推移。例如4月5日的日記:
今天戰訊不佳,台兒莊已失守,敵軍侵入江蘇境。此次徐州戰事已近三個月,成績雖不劣,然犧牲精銳太多,念之心寒。
4月20日他記道:
今天報紙說臨沂又失了。
5月15日:
今早報載日本兵的一路已截斷隴海路的一段。
5月31日:
晚歸看報,見武漢各政府機關正在準備搬移。此是意中的事,但使我心更煩,加上牙痛,終夜不能睡。五點半始稍睡。
所以6月8日他記道:
今日實在忍不住了,晚上寫長信與某公,此為第一次作「秦廷之哭」。
此「某公」不知是不是羅斯福總統?可見戰爭失利給他多大煩悶和痛苦。第三、本年從1月24到3月18日,他作了一次巡迴整個北美洲的演講之旅,中間無一日之停。3月16日他自己統計:此行共51天,演說56次(美國境內38次,加拿大境內18次)。他的神經繃得太緊,但又鬆不下來,因為下面還有許多演講和會議在等著他。第四、到了4月25日,他日常能解寂寥的中國友人都走光了,留下他一個孤身在紐約的人海之中。與他同來的張忠紱和錢端升先後於1月27日和4月6日回國了,他的北平老朋友林行規(斐成)於3月29日到了紐約,從《日記》看,他們只要有空,幾乎每晚都談到深夜,給他情感上以極大的支持。但4月25日林行規也走了,他在這一天的日記寫下了一段話和一首詩,最可以顯示他的孤寂心情,原文如下:
極感覺孤寂。斐成先生住此地,我們常見面,常談天,給了我不少的快樂。他今早走了,故我今天甚覺難過。晚飯時,獨自走出門,尋到他和我同吃飯的「俄國熊」小館子,獨自吃飯,真不好受!
孤單客子最無聊,獨訪「俄熊」吃「劍燒」。
急鼓衰絃燈影裡,無人會得我心焦。
此詩的後兩句幾乎把上述四種複雜的情緒都包括進去了。所以4月尾是胡適在情感上最脆弱、最煩躁、也最孤寂的時候,Robby便恰好乘虛而入,闖進了他的生活。
我說Robby闖進了他的生活是有根據的,因為4月16日第一次暢談明明是Robby一方面發動的。Robby既是杜威身邊的人,胡適當在一九三七年10月6日到紐約後不久便認識她了。10月16日,孟治邀了十位美國朋友同飯,其中便有杜威。其時他已年近80,Robby很可能隨侍同來。無論如何,胡適稍後去拜訪老師時也一定會遇到她(杜威的生日在10月19日,胡適常常送花賀壽或參加宴會)。因此他們一直要在六、七個月後才開始單獨交往,可以說明胡適並沒有什麼「一見傾心」的經驗,也沒有主動地去接近她。至少從《日記》看,是如此。他們之間最後發生了一種微妙情感,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他和Robby的一段情緣似乎並不很嚴重,決不能與違蓮司的關係相提並論,也未可與曹珮聲的纏綿悱惻同日而語。胡適即使不任大使,也會很快結束了它,即美國人所謂「不待發芽成長便把它捏死了。」("to nip it in the bud"),「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也是胡適「偶然論」的一個例子。他在最孤寂的時刻偶然遇見一個聰明而又善解人意的Robby,未及設防的城市竟被她攻破了。但胡適的自衛機能和責任感向來都是很強的,他決不會在臨危受命,作「秦廷之哭」的特殊情況下,鬧出舉世喧騰的笑話來。他在一九三八年4月27日寫下一句自省的話:
我不大赴娛樂場,只是因為國家在破敗狀態,我們應該自己慎重,不可讓人因我們而訕笑我們這民族全無心肝。
我相信這是他的真心話,並無矯飾。為什麼墨瀋未乾,竟有了「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呢?古人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世說新語‧傷逝》)胡適不是「聖人」,而是「我輩中人」,具有「我輩」同樣的弱點,這一偶然的意外是不足驚怪。但他畢竟很有智慧,這件事由濃而淡,化解得了無痕跡。一九四一年Robby的丈夫死了,還特別寫信告訴胡適,可見彼此的交情始終是存在的。不過自此以後Robby的名字也從《日記》中消失了。
如果Robby的事僅止於此,我也許不會有興致寫這一段「事如春夢了無痕」的「相思債」。但是我偶然讀了杜威大弟子胡克(Sidney Hook)的自傳,得到一個十分意外的發現,使我覺得胡適與Robby的情緣陡然增添了「傳奇」的意味。讓我先把胡克有關的一段記述譯出來,再說其他。胡克說杜威晚年幾乎對他事事都言聽計從,但只有一件事他保持緘默。下面是他的原話的譯文:
唯一的一件事我閉口不說的是他和Roberta Lowitz Grant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把他和他的兒女及其家庭都分斷了,最後他和兒女們竟致發生了一場陡然而不愉快的大破裂,那是因為他和她在相處差不多十年之後(她主要是照顧他的生活),他以88歲的高齡竟和她結婚了。Roberta先是Lowitz小姐,後是Grant夫人,再後是杜威夫人,她和杜威在一起的生活是怎樣的,她和杜威的兒女們之間究竟有些什麼困難酖酖這整個故事只有當作杜威傳記的一部分來說,才更合適。不幸得很,到現在為止,這段故事還沒有在適如其分的層面和方式上寫出來。
Robby最後竟變成了杜威夫人酖酖胡適的師母,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奇峰突起。杜威生在一八五九年,88歲當在一九四七年,前推10年則是一九三七年,可知胡適初識Robby之年也就是她剛剛隨侍杜威之年。杜威比Robby大45歲,則一九三八時Robby年34,比胡適小13歲。Robby既成了杜威夫人,她的事蹟當不難在杜威傳記中找到詳細記載,何況他們結婚所引起的風波又是如此之大,當時報章雜誌中恐怕也有不少「流言」(gossip)。這是值得有興趣的人去追蹤的,我則只能說到這裡為止,不過最後我還要補上兩條《日記》。一九五悾年12月24日:
今天Mrs. John Dewey在電話上告訴我說,「昨晚王文伯在旅館房間裡被火燒傷……」
一九五二年6月1日,胡適寫道:
今夜八點半,得Mrs. John Dewey的電話,說杜威先生(John Dewey)今夜七點死了。
這兩處Mrs. John Dewey便是當年的Robby。胡適一九四九年重回紐約之後,和杜威交往仍多,一如既往。他和杜威夫婦在一起時,他是不是依照中國習慣,一律改口叫她 "Mrs. Dewey"呢?還是有時也依美俗叫她"Robby"呢?這是一個再也無法求證的「大膽假設」,然而也是「頗耐尋味」的。(下)
【2004-05-04/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後記
Lowitz向胡適示愛(上)
余英時
一代學人胡適的情感生活,一直是大家感興趣的話題。今年五月聯副選載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中有關
胡適情緣的段落,題名〈赫貞江上之相思〉,引起文化界廣泛討論,知名的新聞學者傅建中更在人間副刊發表長文回應。
上月,余先生再根據胡適的英文信函,一首詩,及一封電報,寫了一篇〈後記〉,對胡適的出處取捨、情緣公案,做了更細
膩的論證,聯副訂題「Lowitz向胡適示愛」,鄭重推薦予讀者!(編者)
最近我讀到胡適的《英文信函》(《胡適全集》本第四十和四十一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發現原文第五節「出使美國(一九三七酖一九四六)」中的一些推斷都可以在英文信中得到證實。例如我曾根據《日記》,斷定一九四五酖一九四六年秋季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正式任教一學期,但《日記》極為簡略,不足以定案。現在讀了他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和同年六月十三日給富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的兩封信,這個問題便完全解決了。從第一封信中,我們知道他的授課期間是從十月到第二年的一月,每星期講課兩次。從第二封信中,我們更知道哥大最後將他這四個月的講學待遇調整為四千美元。(見《全集》卷四十一,頁五一○酖五一一;五二四酖五二五)這都證明他所擔任的是一學期的專任教職。
把原創性的學術研究放在第一位
不但如此,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大使卸任後的出處問題,《日記》中語焉不詳,只有從當時英文信件中才能獲得比較清楚的記述。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給女友韋蓮司(E.C. Williams)的信中說:
我已經接到許多美國大學的邀請,包括康奈爾、哥倫比亞、哈佛、芝加哥、威斯康辛、巴恩斯基金會(Barnes Foundation,原注:羅素正在那裡任教)和其他地方。但是我已決定先休息一段時期,然後再考慮何去何從。(《全集》第四十一卷,頁三二五)
這時他的卸任消息才傳出十幾天,各大學已爭相聘請如此,可見當時美國學術界對這位「學者大使」的尊重之一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大學的重金禮聘案。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給芝大校長赫琴斯(Robert Maynard Huchins)的回信中,特別申謝芝大以美金一萬元的年薪聘請他前往任教的誠意,他說:「這比我的大使年俸還要高。」但是他為了全力撰寫未完成的《中國思想史》,已決定接受美國學術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研究補助費」("grant in aid of research"),因此不得不辭謝芝大的聘約。(見《全集》第四十一卷,頁三五○酖三五二)「研究補助費」只有六千美元,(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Waldo G. Le-land的信,同上,頁三三二酖三三五),遠不能與芝大的待遇相比。但在這一出處取捨之間他的中心價值所在也充分顯露了出來:他始終是一位「學人」,把原創性的學術研究放在第一位,世俗的名位和金錢不在他的主要考慮之中。
「老頭子」、「小孩子」是兩人間的暱稱
最後,我要對「赫貞江上之第二回相思」這一有趣公案(在第五節之末)稍作補充。這一段文字,台北《聯合報》副刊曾以〈赫貞江上之相思〉為題在今年五月三日和四日單獨刊布,引起不少讀者的興趣。五月三十日傅建中先生在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了〈胡適和R.L.一段情緣酖酖回應余英時先生的「大膽假設」〉,對於胡適和Rober-ta Lowitz之間的一段情緣進行了「小心求證」的工作。他首先根據一部最新的杜威傳記,將有關Lowitz和杜威、胡適交往的基本事實扼要地呈現了出來。(這部傳記是Jay Martin, 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其次,更值得稱道的,傅先生還直接向南伊利諾大學的杜威研究中心索取了胡適給Lowitz的兩封親筆信,並譯成中文以饗讀者。這樣一來,我根據《日記》所做的「大膽假設」便基本上證實了。由於胡適親筆信的發現,我們現在確切知道,胡適稱Lowitz為「小孩子」(Hsiaohaitze),而自稱「老頭子」(Laotoutze),這是他們兩人之間的親密隱語,具有極不尋常的涵義。
在新資料的啟發下,我現在對於「赫貞江上之第二回相思」要重新加以檢討。我在原文中判斷,這一段情緣的發生,Lowitz似乎是原動力。「老頭子」和「小孩子」的暱稱則進一步支持了我的判斷。我相信這是由於Lowitz開始向胡適示愛時,後者以年齡為搪塞,說對方還是「小孩子」而自己已是「老頭子」了。事實上,胡適在這裡運用了傳統詩人、文士對於「紅粉知己」一種「欲迎而故拒」的手法。吳梅村〈無題〉之三結句說:
年華老大心情減,辜負蕭娘數首詩。
這兩句詩便是「老頭子」和「小孩子」的「典雅」版。何況胡適很早已有「倚少賣老」的結習(見趙元任一九三○年慶祝胡適四十歲生日的賀詞,收在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八年,頁一七一酖一七三);這時當然免不了要重施故技,以緩和 Lowitz的攻勢。現在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胡適用「老頭子」、「小孩子」兩個暱稱究竟始於何時?傅建中先生所引的英文信,最早的一封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已遠在「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之後。我最近又發現了一條絕妙的證據,使我們對這一段情緣的認識更清楚了。去年出版的《北京大學圖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二○○三年)收入了一封「小孩子」給胡適的電報("Hsio Hai Tze to Hu Shih"),日期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頁二六二)。這時胡適正在密西根大學講學,所以電報是由密大教授霍爾(Robert Hall)轉交的。電文如下:
"Recieved forwarded letter today. Miss Laotouze unbelievably. Re-turning New York. Love. Hsio Hai Tze"(今天收到轉來的信。想念「老頭子」到了令人不能相信的地步。即返紐約。愛。「小孩子」)
顯而易見地,Lowitz並不熟悉中文的拼音,以致「老頭子」和「小孩子」都各漏去了一個英文字母。但這是小問題,可以置之不論。這一簡短電報的證據價值是多方面的,而且無比地重要。讓我一一道來。
以「愛」字結尾的電報
第一、我在原文中說,胡適七月十日從密西根回到紐約,Lowitz當天便來看他,大概是胡適首先將歸期告訴了她,或事先通過電話。從電文中「收到轉來的信」一語,現在我們可以確定:胡適是寫信通知的,因為這是一封回電。第二、「老頭子」、「小孩子」早在胡適六月三十日動身去中西部之前便出現了。自從四月十四日Lowitz邀他吃茶開始,兩個半月之中胡適和她交往頻繁,五、六兩個月已達到了幾乎形影不離、時時「久談」的地步,而六月二十九日兩人的「郊遊」則更標誌著情感上的一次跳躍。所以Lowitz向胡適示愛而終於引出「老頭子」和「小孩子」的暱稱,最遲也是六月二十九日「去郊外遊」的時候發生的,或者更在其前。此時胡適尚不滿四十七歲,固然不能說是「老頭子」,而Lowitz則已三十有四(她生在一九○四年),無論如何也和「小孩子」沾不上邊。所以這兩個稱呼只能是兩人之間的情感已達到公開談論的階段才可能出現。在確定了Lowitz的意向之後,胡適大概曾對她表示過下面的意思:「我已是一個『老頭子』了,而你在我看來還是一個『小孩子』,我們之間的年齡距離太大了。」這是這兩個暱稱之所以產生的事境和語境,否則胡適不可能忽然異想天開地自稱「老頭子」,稱對方為「小孩子」,而且還鄭重其事地將這兩個暱稱的英文拼法寫出來,讓她記住。第三、「想念『老頭子』到了令人不能相信的地步」,是一句份量極重的話,道盡了小別七日的「相思」之苦,大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風味。「老頭子」讀到這一句時,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第四、電報的最後一個字是「愛」,更能打動胡適的心。試讀他在一九四一年的一首〈無題〉詩:
電報尾上他加了一個字,
我看了百分高興。
樹枝都像在跟著我發瘋。
凍風吹來,我也不覺冷。
風呵,你儘管吹!
枯葉呵,你飛一個痛快!
我要細細的想想他,
因為他那個字是「愛」!
(《嘗試後集》,收在《全集》第十卷,頁三四四)
此詩自注「三十年(一九四一)冬」作,本事已不可考。但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胡適獲知Lowitz丈夫(Robert Roy Grant)的死訊,曾去電致悼。他是不是因此而勾引起三年前的一段記憶,才寫了這首〈無題〉詩,我們並不能輕下斷語。無論如何,「小孩子」的這個「電報尾上」則千真萬確地加上了一個「愛」字;此外在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一這三年間胡適所收到的電報之中,我們還沒有發現第二封是以「愛」字結尾的。〈無題〉詩也許與「小孩子」完全無關,但通過它,我們卻不難想像,胡適當時讀到這封電報時,一定也是「百分高興」,甚至「發瘋」!
詳細分析了「小孩子」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的電報之後,對於五天後(七月十二日)「赫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我們便再也不會感到一絲一毫的意外了。胡適即使有過一點「心防」,也被「小孩子」這封電報徹底攻破了。Lowitz給胡適寫過信,也打過電報,但保存到今天的則只有這一封了,而它的證據作用竟如此之大,我們不能不特別感謝北大圖書館這部《未刊書信日記》的貢獻。(上)
【2004-10-05/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後記
Lowitz向胡適示愛 (下)
余英時
英文文獻是研究胡適不可或缺的資料
投桃報李,讓我對《未刊書信日記》中有關英文釋文的失漏處,略作訂正。
一、"Bert to Hu Shih",(頁一九八酖一九九):"Bert"的全名是Bertha Mah。她是Wing Mah的妻子,見下條。Bert也是當時胡適的女性崇拜者之一,所以信末明白表示:她希望胡適不但是「冬秀的丈夫」而且也是「我的丈夫」,此外則不能再是「任何別人的丈夫」("but no one else’s")。但這只是極端崇拜的一種表達方式,與愛情無關。讀者不可誤會。
二、"Ibing Wah to Hu Shih"(共二信,頁二六五酖二六七)。按:"Ibing Wah"是"Wing Mah"誤釋。他的中文姓名是「馬如榮」,自一九三年代起便在加州大學柏克萊(Berkeley)分校政治系任教。他一家人(包括妻子和兩位女兒)都是終身「胡迷」,詳見《胡適日記》及《英文信函》。Wing Mah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九日賀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的信中也特別提到:Bert早在九月初便希望當時的大使是胡適,而不是王正廷(C.T. Wang),見頁二六六。
三、"V.K. Willingtucker () to Hu Shih"(共二信,頁三三○酖三三二)。按:釋文在英文名字之下加一問號,表示不能十分確定之意。其實"V.K. Willingtucker"應讀作"V.K. Willington Koo",即大名鼎鼎的顧維鈞。他當時(一九三八)是中國駐法大使,所以兩信首頁都用的是「巴黎中國大使館」("Ambassade de Chine, Paris")的信箋。這兩封信都是討論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的問題。其中第二函(八月二十七日)是答覆胡適八月二十日的信,胡信收在《全集》卷四十,頁三四○酖三四一。兩信都出自顧的親筆,是很珍貴的原始文件。
四、"Someone to Hu Shih (1938.7.25)",頁三四七。這也是顧維鈞的親筆信,簽名是"V.K.W. Koo"。胡適在七月二十七日有覆函,見《全集》卷四十,頁三三七酖三三八。
五、"Somenone to Hu Shih (1938.5.11)",頁三四六。按:簽名是"H.J. Timperley"。他是Manchester Guardian報的駐華記者,熱心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他有一封給E.C. Carter的信,已收入本書作為附錄("Appendix: H.J. Timperley to Edward C. Carter (1938.6.9)"),頁二二四酖二二五。Tim-perley五月十一日給胡適信首段所提到的他一部即將刊行的新書便是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書局的介紹辭也收入本書頁二二六。
六、"Someone to Hu Shih (1938.9.27)",頁三四九。按:簽名是"Archie Rose",全名為"Archibald Rose"。他是英國文化教育界的一位領袖人物,一九二六年胡適為中英庚款委員會事到英國訪問,他便是一位主要接待人。所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胡適離英前夕,他親筆寫了四頁的告別信,感謝胡在英國留下的積極影響,筆跡和本書所收的信完全相符。
七、"Someone to Hu Shih",頁三五三。這是本書所收的最後一封信,寫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作者的簽名是"Osvald Siren"。他是瑞典Stockholm大學的教授,專治中國藝術史,著作甚多。他的六巨冊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6-1958)至今仍是中國畫史研究中的基本參考書。胡適初識他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八日,地點是北京的六國飯店,見《胡適日記》。
以上僅就所知增補於上,其餘還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因手頭資料不足,一時又無暇廣徵博考,唯有俟之異日。總之北大所藏《未刊書信日記》的史料價值極高,上引「小孩子」的電報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任何關於胡適生平與思想的深入研究都不能完全依賴中文史料,英文文獻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這是我寫完這篇〈後記〉所得到的一個最深刻的感想。(下)
【2004-10-06/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文藝復興乎?
啟蒙運動乎?*
──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近年來,五四運動普遍被視為中國的啟蒙運動。1930年代後期與1940年代早期,中國的作家最初賦予五四運動這一新的身份(identity)時,他們顯然是要借重比附(analogy)的方式對「五四」盡可能作出最高程度的禮讚。然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今天,這一身份最初所蘊涵的榮耀,竟迅速地變得很可疑了。目前吸引著史家、哲學家、文化批評家的目光的,是啟蒙運動幽暗的一面。於是,以理性的觀念為核心的啟蒙規劃,往往被許多人看作是一場「失敗」或者更糟地,是一種霸道的「宰制」(domination)。因此,很自然地,當前這股反啟蒙理性的後現代狂潮正開始對「五四」規劃投下了一抹陰影。
稍後我會回到啟蒙運動這一問題上。現在我先要指出一項重要的事實,即在啟蒙這一身份出現之前,五四運動在西方是以「中國的文藝復興」而廣為人知的。首先,我想探討這些比附概念的個別歷史意涵,以及解釋為什麼「文藝復興」最終讓位給「啟蒙運動」〔注1〕。
在西方宣揚「中國的文藝復興」的理念,胡適(1891-1962)比任何人都更為重要。1926年11月,他前往英國巡迴演說時,在不同的學術機構,諸如皇家國際關係研究院(Hu 1926)、(都柏林)三一學院、牛津大學、利物浦大學,以及Woodbrooke Settlement,反覆講述「中國的文藝復興」。有一張演講海報,甚至還介紹他是「中國文藝復興之父」(參見胡適,1990,冊5:1926年11月9、18、23、25、28日)。1927年1月,他抵達紐約時,在紐約市發行的《國家》(Nation)雜誌報導說:「胡適已回到美國……他大膽提倡使用被鄙視的土語(vernacular tongue);他為中國人所做的事,正如但丁(Dante)與佩脫拉克(Petrarch)為義大利人所做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無法精通複雜的古典語文(classic tongue),而他為這些人打開了讀寫能力的大門」(胡適,1990,冊6:1927年1月20日)。這當然也是尊他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的另一種方式。
1933年,在芝加哥大學Haskell講座的一場演說中,胡適毫不含糊地解釋他所謂的「中國文藝復興」的涵意:
《文藝復興》(Renaissance)是1918年一群北京大學學生,為他們新發行的月刊型雜誌所取的名稱(按:即《新潮》的英文名稱)。他們是在我國舊有傳統文化中,受過良好薰陶的成熟學生;他們在當時幾位教授所領導的新運動裡,立即察覺到它與歐洲文藝復興有顯著的類似性。下面幾個特徵特別使他們回想到歐洲的文藝復興:首先,它是一種有意識的運動,發起以人民日用語書寫的新文學,取代舊式的古典文學。其次,它是有意識地反對傳統文化中的許多理念與制度的運動,也是有意識地將男女個人,從傳統勢力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運動。它是理性對抗傳統、自由對抗權威,以及頌揚生命和人類價值以對抗其壓抑的一種運動。最後,說來也奇怪,倡導這一運動的人了解他們的文化遺產,但試圖用現代史學批評和研究的新方法來重整這一遺產。在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一個人文主義運動。(1934:44)
關於此一「中國文藝復興」理念的起源之說明,可以作幾點觀察。首先,1918年,北京大學學生刊物《新潮》(New Tide),其英文副題是由新潮社創社一位成員所提議。這的確是事實。然而,由於自謙的緣故,胡適沒有點出一個重要事實,即從最初構想到問世,他自己實際上一直是此一深具影響力雜誌的護法(傅斯年,1952)。其次,1917年,正是胡適最早把他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比附歐洲文藝復興。1917年6月,在返國途中,當前往溫哥華的火車穿越加拿大境內的洛磯山脈時,他閱讀著Edith Sichel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1915)(胡適,〔1939〕1986b,冊4:240-247)。令他相當喜悅的是,他發現,他提倡用白話文對抗文言文,來作為中國文學的媒介,恰好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土語文學的崛起上得到歷史的印證。但丁與佩脫拉克,胡適指出,最早在他們的寫作中使用土語。他特別注意到下面這個事實,雖然Leon Battista Alberti已公開宣稱拉丁語是「一種死的語言」的但最後還是靠Cardinal Pietro Bembo在Prose della volgar lingua中支持用土語取代拉丁語,才完全解決了文學語言的問題。〔注2〕毫無疑問的,採用「文藝復興」作為學生刊物的英文副題乃源於胡適的啟示。第三、上引胡適文中所列三項特徵中,其第二項──「理性對抗傳統」、「自由對抗權威」──在性質上顯然更像是描述啟蒙運動而不是文藝復興。然而,這應該不必詫異。畢竟,儘管胡適口口聲聲說文藝復興,相較於義大利人文主義,胡適更直接是法國啟蒙思潮的繼承者。對於他同時代的西方人而言,胡適往往使他們聯想到伏爾泰(Voltaire)(Fairbank ,1982: 45-46;余英時,1984:62-63)。不但如此,從他針對現代世界的文化趨勢所作的公開演說來看,我們得到一種清晰的印象,胡適視文藝復興為西方現代性的真正肇端,而將所有的相繼發展,諸如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化、民主革命,甚至社會主義運動,都看成跟隨文藝復興而來的直線性進展,並從而不斷擴大了現代性的內容。可能正是因為他強調啟蒙運動上承文藝復興而來,如上引文中的描述所示,他有時未能在兩者之間劃分出界線。〔注3〕
現在,我們需要更加仔細地考察啟蒙運動的概念,看看它是怎樣應用在五四運動上面的。就我所知,最早從啟蒙運動的角度詮釋五四運動的,正是馬克思主義者。1936年,好幾位地下共產黨員在上海和北京發動了「新啟蒙」運動。根據1985年版《哲學大辭典》的說法,這一運動是這樣界定的:
新啟蒙運動亦稱「新理性主義運動」。中國思想文化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為適應抗日民族鬥爭而展開。是五四啟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1936年9月至10月,由當時的共產黨人先後發表《哲學的國防動員》、《中國目前的新文化運動》兩文所提出,建議共同發揚「五四」的革命傳統精神,號召一切愛國分子發動……一個大規模的啟蒙運動,喚起廣大人民的抗戰與民主的覺醒。……至1937年底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和抗日救國統一陣線形成,新啟蒙運動前後進行了近一年,對廓清蒙昧和宣傳抗日,起了積極的作用。(pp.676-677)
這一段文字清楚顯出,共產黨人之所以將五四運動重新詮釋為「啟蒙運動」,是因為他們當時需要一種「新啟蒙」運動來執行黨的新 「統一陣線」的路線。引文中提到的兩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陳伯達(1904-1989)和艾思奇(1910-1966);兩人都是在偽裝下活躍於北京和上海教育與文化界的黨的主要理論家。明白這一點很重要。我也必須強調,兩人之中,陳伯達是個更資深、也更重要的共產黨員。發動新啟蒙運動的正是陳伯達。乍看之下,簡直令人不解,一個實際上在中國思想界默默無聞的人,竟能隻手發動一場運動,而且立即引起了北京與上海左派雜誌的熱烈嚮應。然而,一旦我們了解陳伯達的真正身分,困惑便消散了。1936年初,劉少奇(1898-1969)前往天津擔任共產黨地下北方局的領導時,陳伯達被任命為宣傳部的負責人。正是以這一新的黨方身份,陳伯達借「啟蒙運動」之名來運用五四遺產,完成黨新近交給他的任務。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們要和一切忠心祖國的份子,一切愛國主義者,一切自由主義者,一切民主主義者,一切理性主義者,一切自然科學家,……結成最廣泛的聯合陣線」(轉引自何幹之,1947:207)。在此,必須指出,「我們」這一詞不是一種社論式的用法,而是共產黨的暗碼代號。不用說,從一開始所有來自左派報刊的正面回應都是由共產黨通過其地下網絡統一指揮的。不但如此,新啟蒙運動與1935年著名的一二.九運動,有著密切關聯。有些參與者向來把一二.九看成 「1919年學生運動的目標的直接延續和實現」(Schwarcz, 1986: 218)然而,1935年的一二.九在一個關鍵性的方面,斷然不同於1919年的五四。正如傅斯年(1896-1950)在1946年時所作的回憶:「五四與今天的學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動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著大旗,直赴趙家樓。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傅樂成,1969:62-63)然而,就1935年一二.九學生示威運動而言,今天我們知道,一如新啟蒙運動,它也是由共產黨地下基層組織細密策劃與執行的。根據北方局黨書記高文華(活躍於1930年代)的第一手記述:學生動亂在一二.九運動中達到高潮。我們在北方局裡支持且領導了此一愛國運動。趙升陽、柯慶施、陳伯達等同志為黨中的領導。公開場合的直接領導人,則包括李昌、蔣南翔(清華大學支部黨書記)、林楓、姚翼林、徐冰、許德珩等同志」(高文華,1982:187;葉永烈,1990:102)。此外,1935年,在一二.九示威運動中被Edgar Snow描述為「中國的聖女貞德」的學生領袖陸璀(活躍於1930年代),在她紀念這一事件六十周年的宣傳文集中,公開承認,她那時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直接指揮下工作(陸璀,1995:7,19)。明顯地,被巧妙策劃來相互奧援的這兩場運動──一二.九與新啟蒙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不免讓人聯想到狹義的五四(1919年學生的示威運動)與廣義的五四(胡適與新潮社所謂的「文藝復興」)之間的關係。但是一二.九與新啟蒙運動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北方局的地下共產黨組織,因此說前者是「1919年學生運動的目標的直接延續和實現」,而後者是「五四啟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似乎沒有什麼意義。
既然新啟蒙運動從最初構想開始便是為隱匿的政治目的服務,〔注4〕它的倡議者根本便不覺得有必要從思想根據上去證明,為什麼對於五四運動而言,「啟蒙運動」是比「文藝復興」更適當的稱呼。從政治觀點出發,他們把五四運動與新啟蒙運動兩者都和愛國主義掛上了鉤。依艾思奇的看法,中國的新舊啟蒙運動必須以愛國主義為其主要任務(何幹之,1947:209)。但是,任何熟悉歐洲啟蒙運動的人都知道,將愛國主義連結到啟蒙運動是何其荒謬的事。除了盧梭(Rousseau)這一可能的例外,啟蒙哲士無一不是世界主義者。他們自任的天職是:陶冶人類、啟迪人類,和提高人類的尊貴,而非提升國家利益(Gay 1966: 13-14)。
有趣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般說來對啟蒙運動的偏好,遠甚於文藝復興。較早的作者不論以文藝復興跟中國史的哪一段時期作對照,他們都照例把這一比附改為啟蒙運動。除了五四的例子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範例。梁啟超(1875-1929)在其早期和晚期的生涯中,堅持將清代學術思想史特徵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Liang Ch’i-ch’ao 1959:14)。但馬克思史家侯外廬(1906-1988)反駁梁啟超的比附,取而代之地,他持續又有系統地把同一時期詮釋為「啟蒙運動早期」(1956)。那麼,我們必須追問: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何如此著迷於啟蒙運動的理念呢?我想大膽提出一些看法。首先,依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當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勢必經歷類似於法國啟蒙運動的一種大規模布爾喬亞意識的社會表現(expression)。五四作為一種思想運動,相當符合這一框架。其次,狄德羅(Diderot)曾寫信給伏爾泰,稱讚他「在我們心中」激發出「一種對說謊、無知、偽善、盲目崇拜、專制的強烈憎恨」(轉引自Becker, 1932: 92)。很多五四知識分子的打破偶像與反孔教的文字,具有類似的特質(何幹之,1947:122-133)。對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特別具有吸引力的,正是五四的這一破壞面。第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擁護革命的。他們注意到,歐洲各國的啟蒙運動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前驅,因此他們也需要某種啟蒙運動來證明他們在中國提倡革命的正當性(何幹之,1947:97)。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傾向於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斷由啟蒙運動的觀點重新界定五四,並不是對歷史作任意性的解讀。相反地,他們可能出於這一信念,即與文藝復興相比,啟蒙運動更有利於為他們的政治激進主義服務,因而作了一種蓄意而又經過精打細算的選擇,畢竟文藝復興太過遙遠、也太過溫和,對他們所嚮往的革命沒有直接又實際的關聯。
基於同一理由,我們也必須嚴肅看待胡適與其他自由主義者所賞識的文藝復興。從1917年起,胡適始終堅持,五四運動作為一種思想或文化運動,必須被理解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這不僅因為他提倡以白話文作為現代文學的媒介,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對歷史連續性有深刻的體認。對他而言,「文藝復興」暗示著革新,而非破壞中國的傳統(胡適,〔1970〕1986f)。儘管胡適經常有猛烈的批評,但他對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的抗拒,遠非全面的。他深信,文藝復興含有一個中心觀念,即有可能把新生命吹進中國的古文明。早在1917年,他清晰地陳述此一問題如下:「我們如何才能找到一種最好的方式來吸收現代文明,使它與我們自己所創造的文明配合、協調且又連結呢?」他那時提出的解決之道是:「端賴新中國思想領導人的先見之明與歷史連續感,同時也有賴於機智與技巧,使他們能將世界文明與我們自己的文明裡最好的事物作成功的連結」(轉引自Grieder, 1970: 160-161)。這聽起來,完全不像是要和中國的過去全面決裂的呼聲。後來,他在1933年從具體的角度陳述,什麼是每一文明裡「最好的事物」,以及兩者間何以能夠有技巧地「連結」:「慢慢地、靜悄悄地,但也很顯然地,中國的文藝復興變成了一種實在。此一重生的產物帶有可疑的西方的外貌。但是,刮掉其表面,你便會發現,它的構成要素本質上是中國的根柢,因大量的風化與腐蝕才會使得重要處更加清楚──由於接觸新世界的科學與民主的文明,使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復活起來」(Hu, 1934: ix-x)。事後看來,對於這位「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這是胡適的朋友給他的稱號──的過早的樂觀,我們忍不住會發笑。然而,即使在生命的盡頭,他的信心依舊沒有動搖。1960年7月,在華盛頓大學舉辦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上,他以「中國傳統與未來」(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為題所作的公開演說中,最後一次試圖將文藝復興的概念,有系統地應用到中國史上。他對五四之前的中國歷史,總計區分出三次文藝復興。第一次是第8與第9世紀中國文學的文藝復興,那時白話開始出現在禪僧的詩與語錄中。第二次文藝復興出現在哲學,這裡,他主要是指第11與第12世紀新儒學的崛起。第三次文藝復興是第17與第18世紀的「學術復興」,那時人文學者開始使用「科學方法」大規模研究古籍與史籍。在此,明顯的是,他接受了上文提及的梁啟超關於清代學術思想史的詮釋(Hu, 1960: 17-18)。〔注5〕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能接受他圍繞「文藝復興」的主軸所編織出關於中國史的大敘事。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與他徹底反傳統的公眾形象相反,胡適在他早期與晚期的生涯中,始終需要中國傳統的某些部分,來證明他所倡導的中國文藝復興的正當性。於是,在演講的結尾,他帶著強調下結論說:簡言之,我相信,『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傳統,不曾被毀滅,也決不可能被毀滅」(Hu, 1960: 22)。在1960年對於他所特別愛護的中國傳統作出這樣的論斷,這祇能是個人信念的一種表述,而不是符合當時實際的歷史事實。然而,他除了堅持那一信念之外,別無選擇。因為,要是那一特殊傳統被毀滅了,那麼五四時期的中國文藝復興也蕩然無存了。胡適和五四的文藝復興是從頭到尾合而為一的。這樣一來,他自己的歷史存在也完全喪失了。
為了總結這部分的討論,讓我首先指出,不能輕率地把「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僅僅看作兩個不同的比附性的概念,由人任意借用以刻劃五四運動的特性。相反地,它們必須嚴肅地看作兩種互不相容的規劃(projects)各自引導出特殊的行動路線。簡言之,文藝復興原本被視為一種文化與思想的規劃,反之,啟蒙運動本質上是一種經過偽裝的政治規劃。學術自主性的概念是文藝復興的核心。追求知識與藝術,本身根本上就是目的,不能為其他更高的目的服務,不論它們是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或道德的。正因這一理由,胡適經常感到遺憾的是,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的愛國主義本身雖值得讚揚,然就中國文藝復興而言,它仍舊是個不受歡迎的干擾。因為,五四學生運動標示了中國學術界政治化的肇端,從而在現代中國學術自主性能夠牢固建立以前,便破壞了它(胡適,〔1970〕1986e)。相對而言,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構思的啟蒙運動規劃,最終則是革命導向的。由於徹底強調愛國主義與民族解放,新啟蒙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提倡者,只認可文化與思想為革命服務的意識形態功能。總的來說,學術自主性的理念與他們是無緣的。無怪乎毛澤東(1893-1976)對五四的看法,與胡適大相逕庭。他的最高讚美是保留給1919年的五四學生運動,因為依照他的看法,這一運動導致了1925-1927年的革命(毛澤東,1969,冊2:659-660;李長之,1946: 38-39)。諷刺的是,甚至新啟蒙運動本身也證明是「錯誤的意識」。一旦完成了統一陣線的任務之後,它便消失了。直到1970年代的尾闌,啟蒙運動的理念才再一次浮現,因為那時共產黨在全新的環境下,需要「思想再解放」來調整自己。
時間上,文藝復興概念的流行比啟蒙運動早二十年,最後卻讓位給後者。或許,與其說是緣於作為五四運動描述詞的啟蒙運動具有內在的價值,不如說是因為中國人在心態上的激進化(radicalization)了。中國的民族危機在1930年代持續深化時,深植於英美自由主義的文藝復興規劃,不能適應當時的中國現狀。馬克思激進主義,一方面與民族主義結合,另一方面又隱匿於啟蒙運動的背後,則對全中國的學生中的活躍分子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在新一代的大學生之間,文藝復興的理念已不像1918年那樣,能夠激起巨大的共鳴了。
上文,我勾勒了五四運動中,由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所呈現的兩種對照的規劃。儘管「啟蒙運動」這一詞語直到1936年才用之於五四,但馬克思主義的規劃本身在1920年已經啟動,至少,那時陳獨秀(1879-1942)把深具影響力的《新青年》(亦稱作La Jeunesse)從北京移到上海,也把雜誌轉型為「《蘇聯》(Soviet Russia)」──亦即紐約共產黨周報──「的中國版」(Chow, 1960: 250)。這也使得新青年社之中,陳獨秀領導下的左翼,與北京以胡適為首的自由派右翼之間,產生了分裂。自此,左翼開始積極地參與不斷擴大群眾的組織與動員,將五四轉向政治革命,反之,自由派人士繼續在文化與思想畛域,發展原先的文藝復興規劃。
現在,關於文藝復興規劃,我必須作進一步的釐清。晚近以啟蒙運動替代文藝復興來作為五四的描述,一如上文所言,根本上緣於193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努力。基於這一原因,我認為,在五四作為啟蒙運動的馬克思主義詮釋,與五四作為文藝復興的自由主義詮釋之間,作一鮮明的對照是很有用的。我所指的「啟蒙運動規劃」因而實質上是馬克思主義規劃。但我絕非暗示說,從啟蒙運動的角度理解五四的人都必然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正如我在上文已指出的,如果一定要走五四與啟蒙運動之間作某種比附,我們不難找到許多令人信服的理由;不過在歷史研究中是不是必須採用比附的研究方式,其本身則是大有問題的。有趣的是,胡適的另一及門弟子,也是《新潮》創辦人之一的羅家倫(1897-1969),在很多年後,也將五四與啟蒙運動相提並論。他說:「五四是代表新文化意識的覺醒。……正似18世紀歐洲的啟明運動……18世紀歐洲的啟明運動的健者如伏台爾、盧騷、第德羅、孟德斯鳩等以猛烈的批評,來廓清陳腐思想的障礙,而以科學的態度、自由的精神,不僅重定文學哲學的趨向,而且審核政治社會的制度」(轉引自Schwarcz, 1986: 256)〔注6〕。羅家倫捨文藝復興而運用啟蒙運動來作比附,最有可能是受李長之(1910-1978)的影響。1940年代羅家倫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李長之正在那裡執教。
對於中國和歐洲的文學與哲學傳統同樣熟悉的李長之評論五四作為一種文化運動,提出了別開生面的觀察。他從學術思想的角度出發,仔細衡量了上述兩種關於五四的比附概念的正反議論,得出結論說:與五四真正相似的並非文藝復興,而是啟蒙運動。但他得到這一結論,跟馬克思主義的新啟蒙運動毫無關聯,而且是基於完全不同的理由。他是要頌揚文藝復興,貶低啟蒙運動。根據他的看法,五四心態是理性的、批判的、懷疑的、破除偶像的、實踐的、科學的以及反形而上學的,就這些特徵而論,將五四等同於啟蒙運動是完全持之有故的。然而,這種啟蒙運動心態的主要困境在於膚淺;它無法欣賞任何思想深邃的事物。於是,在哲學上,杜威(Dewey)、赫胥黎(Huxley)、達爾文(Darwin)與馬克思(Marx)風行一時,而柏拉圖(Plato)、康德(Kant)與黑格爾(Hegel)則無人問津。他進一步指出,五四的精神與文藝復興正好相反,因為文藝復興在定義上是古典傳統的回歸與復興。五四的知識分子表明他們既不欣賞自己的舊傳統,也不了解西方的古典文化。孔子被猛烈地抨擊為「封建秩序」的辯護者,至於柏拉圖則被摒之為純粹的「玄學家」。西方學者為胡適貼上「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的標籤,便是一種誤稱的典型例子。儘管李長之有嚴厲的批評,但我必須接著補充說,他對於五四作為一種文化運動,並非全然持否定的態度。五四通過破壞工作,清掃了舊文化的基礎,從而為中國開啟了文化重建的真正可能性。但重要的是,他總結道:必須超越啟蒙運動,開啟真正的中國文藝復興(李長之,1946:14-22)。他對「文藝復興規劃」的修正版本,在戰火瀰漫、政治兩極化的1940年代中國的思想界,似乎未引起熱烈回響。但是,今天新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逐漸擺脫馬克思主義的實證思維模式,踏上人文科學的「詮釋轉向」(interpretive turn),卻開始對他的論點發出一種共鳴的聲音(參見李振聲,1995;Hiley, Bohman and Schusterman, 1991)。
關於李長之對五四的重新評價,我特別感到高興的是:他公開承認,五四作為一種文化運動,首先必須清楚地理解為一種文化外借的運動;或者用他的話說,一種移植西方文化到中國的運動,然而並沒有在中國的土壤中生根(1946:12-13,19-20)當然,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為什麼我竟重視這一人人皆知的事實呢?我相信,基於幾種理由,它值得注意。第一,就我所知,沒有人如此強調,且這麼嚴肅地陳述這一淺顯的事實。其次,這一陳述基本上是對的,但仍不免有點誤導:我們不禁要問:難道五四時期激動了無數中國知識分子的那些西方觀念和理論,都是一些不相干的舶來品,在當時中國的文化現實中完全沒有任何立足點嗎?我在其他地方也曾試圖說明,19世紀晚期與20世紀早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一般說來,會真正熱心回應的,只有在他們自己的傳統裡產生回響的那些西方價值與理念(余英時,1995)。最後,這一淺顯的事實根本動搖了在五四與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之間建立比附的基礎。原因不難找尋:在它自己的歷史脈絡中,無論是文藝復興還是啟蒙運動都不是文化外借的結果;兩者都是歐洲文化歷經好幾世紀的內在發展與成長之後才開花結果的。為了釐清五四作為一種文化運動的性質,我想進一步評論的正是最後這一點。
首先,我提議在中國史的研究中,完全拋棄比附。如果我們既不承認歷史有通則,也不視歐洲歷史經驗的獨特型態為所有非西方社會的普遍模式,那麼我們又何須提出關於中國史上是否有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這類的問題呢?我們祇是如實地去發掘五四運動的真相,便足夠了。一如李長之正確觀察到的,它首先是回應西方理念刺激的一種文化運動。五四的知識分子確實有意識地從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那裡借來了若干理念。正因如此我們無論用兩者之中的任何一個來詮釋五四,都可以言之成理。但同一段時期,除了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之外,各式各樣不同時代的西方觀念和價值也被引介到中國。這一簡單事實便足以說明:五四既非中國的文藝復興,也非中國的啟蒙運動。要是我們把比附的思考推展至其邏輯的極端,那麼我們勢必要把好幾世紀的歐洲歷史,擠進20世紀中國的十年或二十年之內,不用說,這是極其荒謬的。
一旦我們不再固執於死板的比附,我們便能夠開始從五四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五四。在我稍早對20世紀中國的激進化所作的研究,我指出,「五四期間,以1917年的文學革命為嚆矢,現代中國在激進主義的發展過程裡,發生了某種典範的變遷(paradigmatic change)。從那時候開始,不論批判傳統或提倡變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必然地訴諸某些西方理念、價值或制度,以作為正當性的最終根據(Yu, 1993:130)。在當前討論的脈絡中,我還要補充一句,相同的原則也適用於五四時期的中國守舊派,因他們在維護中國傳統時,也多半求助於西方的作者。李長之將五四界定為西方文化向中國移植,也涵有這個意思,即西方文化從此在中國成為一切判斷的標準。如果我們把「啟蒙」的概念當作一個隱喻,而不用之於比附,我們可以說,五四在一個最基本意義上與歐洲的啟蒙運動截然不同。啟蒙運動的哲士在抨擊基督教、經院哲學與「黑暗」中古時,他們是用古希臘和羅馬經典來武裝自己的。換句話說,他們接受了西方內在之光的引導。相形之下,為了見到白晝的光明,五四知識分子必須走出黑暗的洞穴──中國,而引導他們的光照則來自外部──西方。或者,借用毛澤東的名言,「19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向西方尋找真理」。
初期,五四也以「新文化」或「新思潮」的名稱在中國廣泛流行,而這樣的名稱反而比「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似乎更能表達歷史真相,也比較不會引起誤解。事實上,以「新文化」等同於五四,至少在中文著作裡,比起其他用語,更有堅實的基礎。在這一關聯上,我想用胡適的定義作出發點,來重新考察新文化這個觀念及其在中國20世紀思想史上的地位。1919年,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開宗明義即點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該文稍後繼續列舉了三個特定的任務,並在下述的評判精神指引下加以實踐:首先是「研究問題」。中國有很多具體的問題──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學的等等──都需要我們立即關切。必須評判地研究它們,才能找出解決之道。其次,輸入西方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它們不但滿足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需求,而且在他們找尋中國具體問題的解決之道的過程中,可以提供理論引導。第三,則是在「整理國故」這一吸引人的口號之下,應用批判精神來研究中國的思想傳統。為了自我了解,必須評判且有條理系統地重新考察中國的舊傳統。惟有如此,我們才能透過歷史觀點,對我們自己不同部分的文化遺產,有一客觀的理解,並決定它們的價值。最後,該文總結道,新文化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再造中國文明(胡適,〔1930〕1986c:41-50)。
在此,胡適所提出的新文化規劃,是以最廣闊的視野並在極高的層次上構想出來的。以這種方式定義的新文化運動,不僅僅是提倡西方價值與理念,諸如民主、科學、個人的自主性、女子解放等等,它的中心意義也不是局限於譴責中國傳統,包括儒家的理論與實際在內。從他的觀點來看,所有上述的實際問題──項目是無盡的──好像都可以納入「研究問題」的範疇。然而,胡適一方面在提倡輸入西方思潮與學術的同時,另一方面也著手「整理國故」;他似乎回到1917年提出的主題,亦即如何「將西方文明與我們自己文明裡最好的事物作成功的連結」。在此,我不打算詳評胡適的文章。相反地,我只想以它作為出發點,指出探究五四思想史的一種新方式。
如果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中心意義是在批判精神指引之下研究西學與中學,而研究的目的又是使二者互相闡明以求最後獲得一種創造性的綜合,那麼「新文化」或「新思潮」的概念便必須擴大到可以包括參加了五四運動的每一個活躍分子。這樣一來,我們便立即發現:當時批評五四的所謂「守舊派」,也和他們「進步的」對手一樣,不但具有批判的精神而且也採取了西化的立場。姑舉一例以說明我的論點。根據一般的看法,梁漱溟(1893-1988)是文化「守舊派」的一位典型代表。但是,他的名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否也宜看作1920年新文化的一部分呢?令人訝異的是,胡適在1926年針對「中國文藝復興」的演講中,提出對該書的看法:
在歷史上我們首度察覺到一種新的態度,一種了解現代文明基本意義的欲望,以及了解西方文明背後的哲學。讓我引用中國學者梁漱溟的作品,作為此一新意識的最佳範例。……他呼喚出對新時代的思慕。他的著作受到廣泛的閱讀,而且從那時起,便有很多著作撰寫同一主題。……我可以指出,在這些討論中,一方面我們發現了一種完全新穎的態度,一種坦白承認我們自己缺點的態度,而這種缺點也是所有東方文明的缺點;另一方面,一種對西方文明的精神求了解的坦率而真誠的態度,不只是了解它的物質繁榮,而且是它所提供的精神的可能性。(Hu, 1926: 273-274,亦參見馮友蘭,1984:201)
我徵引胡適的文字稍長,因為他的話對於我的論點是一個重要而又直接的印證。他在梁漱溟的作品中所察見的「新態度」,恰恰和他在1919年「新思潮的根本意義」中所描述的完全一致。胡適在這裏已明白承認,梁漱溟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研究正是所謂中國文藝復興的一個構成部分。以下,我想引用梅光迪(1890-1945)的例子,支持我的主張。眾所周知,梅光迪是胡適青年時期最親密的朋友之一,由於梅光迪極端反對文學運動,他們在1917年才變成激烈的思想對手。
梅光迪與吳宓(1894-1978)同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重要的中國門徒。1922年,他們兩人所創辦的《學衡》(1922-1933),正如1934年一位中國作家所生動描述的,支持「任何胡適博士反對的事物。《學衡》揭櫫的目的……是對抗白話運動,且竭力支持固有的寫作方式。它是一場失敗的戰役,然而終不失為一場英勇的奮鬥。」(溫源寧,〔1934〕1990:27)。因此,梅光迪與《學衡》被胡適與魯迅(1881-1936)等五四領袖輕蔑地斥之為頑固的胡鬧(Chow, 1960: 282;參見魯迅,1973,冊2:98-101、114-116)。我們似乎可以由此斷定,梅光迪不但把他自己放在五四時期新文化之外,而且也是新文化最無情的一個敵人。然而,最近梅光迪致胡適的四十五封信第一次刊布了,這些信使我們對他與後來胡適所推動的新文化之間的關係,有了全然不同的認識。細節不必詳究,以下我只報告幾點我認為是有意義的發現。
首先,1911年起,梅光迪寫了幾封長信給胡適,討論現代中國的儒學問題。此時,可能由於還籠罩在父親的影響下,胡適在相當大程度上仍是程朱理學的信徒。梅光迪激烈抨擊程朱的正統,並且敦促胡適轉向顏元(1635-1704)與李塨(1659-1733)之學。他認定顏李所強調社會與政治實踐,在孔孟原始教義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與程朱理學的玄想恰恰相反。(耿雲志輯,1994,冊33:313-322、327-333、398-399)。 一開始,胡適抗拒這種建議(〔1927〕1986a,冊1:73、75);然而,這為他十幾年後熱心提倡顏李學派播下了種子(〔1927〕1986a:3-8)。
其次,梅光迪不僅相當不滿漢儒和宋儒,而且也嚴厲批評當時中國極為風行的國粹派,認為他們仍舊不加批判地接受傳統的經典注解(耿雲志輯,1994,冊33:387-389)。他的目標在於儒學傳統與西方文化的高度綜合。這勢必要兩個階段才能實現:徹底淨化過去兩千年來的儒學傳統,以及牢固掌握歐學,探其文化之源。他說,中國古籍現在必須根據西方的知識分類如文學、哲學、法學等等來重新加以研究(耿雲志輯,1994,冊33:334-336)。
第三,在1916年3月19日的信中,梅光迪說:「將來能稍輸入西洋文學智識,而以新眼光評判固有文學,示將來者以津梁,於願足矣。……來論宋元文學,甚啟聾聵,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folk, popular poetry, spoken language)人手,此無待言。惟非經一番大戰爭不可,驟言俚俗文學必為舊派文學所訕笑、攻擊,但我輩正歡迎其訕笑、攻擊耳」(耿雲志輯,1994,冊33:436-437)。由這封信看來,儘管梅光迪極不同意胡適的文學品味,但在胡適的文學革命早期,他事實上是個熱忱的參與者。此外,我也把胡適所引用的梅光迪來信,與原文作過詳細核對。毫無疑問,胡的引文斷章取義,以致把梅光迪塑造成文學革命的反面人物。在這些信裡,梅光迪不斷試圖把他的立場向胡適說清楚:他同情文學革命,但是無所節制地美化白話,他則無法贊同。他斬釘截鐵告訴胡適,他在破除偶像上不輸給胡適(耿雲志輯,1994,冊33:450);他不輕易附和文學與藝術的「新潮流」,並非他「守舊」,而是因為他「too skeptical, too independent」(太過懷疑,也太富於獨立精神。譯按:這兩句話在梅氏原信中本是英文)(耿雲志輯,1994,冊33:443)。根據這些新證據,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正是胡適在論辯中不斷滋長的激進主義才一步一步地把梅光迪推向極端的保守主義。然而,要是梅光迪在1952年還活著的話,他也許會有一種沉冤昭雪的快意,因為那時候,輪到胡適對於美國學院裡的「新詩」和「新文學」發生徹底的厭惡了(1990,冊17:1952年2月25日)。
最後,梅光迪的政治與社會觀一如胡適,始終是穩健的自由派。他自始支持共和革命,後來袁世凱(1859-1916)背叛民國,他是完全同情國民黨的。對於胡適在美國的雜誌上發表反對袁世凱的聲明,他雖與胡適在文學與哲學上有重大分歧,卻仍然向胡適表示敬意。他甚至主動寫信給革命領導人黃興(1874-1916),推荐任命胡適為共和事業的發言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足下為民黨,多為文字,以轉移此邦諸議,有為胡君適之者,久兼中西語,留學界中,絕無僅有」(耿雲志輯,1994,冊33:437-438)。在1916年12月28日的信中,他繼續針對文學革命與胡適辯論,他以和解的聲調,試圖在一般「人生觀」上,與胡適達成基本共識。他誠摯地建議胡適,他的白璧德式人文主義與胡適的杜威式實驗主義,彼此間所具有的共同處,遠大過差異處。兩者皆支持改革,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白璧德認為,應從個人著手,而後逐漸擴展至全社會;而杜威似乎對這種改革流程,採取相反的看法(耿雲志輯,1994,冊33:464-466)。此外,儘管強烈回護孔孟的道德信念,梅光迪徹底拒絕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帝國儒學。他責難漢宋儒者將儒教曲解為替專制政治與社會不均服務,也一再譴責「三綱」的說法(耿雲志輯,1994,冊33:374-375、384-387)。像這類的反傳統的激論,如果也出現在《新青年》裡,不會有人想到,這些說法的作者身份是個《學衡》的創刊成員。這解釋了為何遲至1922年,他還毫不猶豫、不隱瞞地稱讚胡適的自由主義政治觀(胡適,〔1924〕1986d:61)。
梅光迪與《學衡》的例子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亦即五四時期新文化的真正身份。首要的是,假使一如胡適的定義所提示,新文化由輸入中國的西方理念組成,那麼對中國五四思想界而言,明顯地,白璧德式的人文主義正好與杜威式的實驗主義同樣「新穎」。就某種意義說,胡適及其追隨者與梅光迪和《學衡》之間的衝突,或可視為杜威式的實驗主義與白璧德式的人文主義之間的對抗,不過從美國移轉到中國來了。〔注7〕這相當正常,因為在文化外借的過程中,祇要有人拾取了一種外來思想,便不可能不引另一個人對於這一思想的對立面的注意。那麼我們能夠視白璧德式人文主義,為五四時期新文化的一部分嗎?至少,五四運動的著名成員梁實秋(1901-1987)與林語堂(1895-1976),都以肯定的語氣答覆了這個問題。1924-1925年,梁實秋在白璧德的門下作研究,他回到中國後,對白璧德的古典人文主義深為信服。1920年代晚期,他選收了許多《學衡》上的文章,主編了一本討論白璧德的文集,且以《白璧德與人文主義》的書名刊行。該指出的是,發行者不是別人,正是上海的新月社,這是當時以胡適為護法的新文化的根據地(梁實秋,〔1963〕1969:57-64)。1919-1920年間,在哈佛跟隨白璧德作研究的林語堂,也寫信告訴胡適,與白璧德談話的期間,他察覺到胡適對白璧德的觀點有某些誤解。然而,他補充說,白璧德雖說反對每一現代事物,但他對視最新為最好這種尚新心態(neoteric mentality)的批評仍舊是對的。對林語堂而言,中國文學革命能在白璧德與梅光迪這類人身上得到一種自覺而又具反思性的抗爭,是一件大好事(耿雲誌輯,1994,冊33:314-315)。胡適與魯迅把梅光迪和《學衡》完全摒在新文化之外,不用說,梁實秋和林語堂顯然沒有抱持這種黨派的精神。有趣的是,正如美國1980年代以降,對白璧德重新產生若干興趣(Nevin 1984; Schlesinger 1986)1970年代以降,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重新發現了梅光迪和《學衡》(侯健,1974;林麗月,1979;李賦寧、孫天義、蔡恆編,1990)。現在,似乎愈來愈有必要在陳獨秀與魯迅的激進主義和胡適的自由主義之外,將梅光迪和吳宓的文化保守主義,置於與五四新文化的同一的論述結構之中(林麗月,1979:396-402;樂黛云,1990:255、264-266)。
在結束我的反思之前,我想稍微談談胡適的新文化規劃的另一部分──「整理國故」。這是一個對於中國傳統所有方面進行歷史研究的廣大領域。如果我們必須將「國故」學者包括在五四新文化之內,那麼「新文化」這一概念便更不能不隨之擴大了。舉幾個例子便足以說明問題。普遍被認為是最具「科學心靈」與原創性的古代史家之一的王國維(1877-1927),政治上是效忠清廷,文化上則是極度守舊。重要的中古專家陳寅恪(1890-1969),政治上與文化上都是保守主義者,終其一生未嘗以白話文寫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毫不諱飾地指出,自先秦以降,中國不只在科學方面,而且在哲學與藝術方面也不如西方(吳學昭,1992:9-13)。中國佛學史權威湯用彤(1893-1964),實際上是《學衡》的撰稿人,而且,一如陳寅恪,始終使用文言文寫作。不用說,他們三人都不同情狹義與廣義的五四運動。但在國故領域,胡適對他們都推崇有加,也在他們身上找到一種精神的契合。他們對胡適也偶爾予以善意的回報。我們如以狹義的五四標準來衡量「國故」學者,諸如白話文、實證主義心態、反傳統主義、政治激進主義或自由主義、倫理相對主義、社會平均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那麼他們之中的大多數而且是最有成就的都必須排除在這時期的新文化之外。這樣一來,所謂新文化還剩下什麼呢?那將只剩下一個純文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唯有意識形態衝突的種種胡言亂語,而思想和知識卻不可想像的貧乏。
貝爾(Daniel Bell)曾描述自己為「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者,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以及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Bell, 1978: xi)。我相信,同樣的描述方式──當然,有非常多種可能的組合──也可以用之於概括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不同的人而言,五四始終是也仍舊是很多不同的事物。對我而言,根本上它是一個文化矛盾的年代,而矛盾則注定是多重面相的(multidimensional),也是多重方向的(multidirectional)。我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把它看作是一個單純而又融貫的運動,導向某一預定的結局,好像受到一種歷史的鐵則的支配一樣。在我看來,每一個五四知識分子都似乎是獨特的,他們之中,很多人都隨時在改變自己的想法,既快速,又劇烈。一如革命前的俄國知識分子,他們「可以是早晨的西化派,下午的斯拉夫文化擁護者(Slavophil),而晚餐後則批評一切(Greenfeld 1992: 270),五四的知識分子,即使不是在幾天和幾星期之內,也能在幾個月的期間裡不斷移轉他的立場。當然,在廣義的五四運動中,我們也未嘗不能模糊地看出
若干較大的思想類型和某些理念模式。但是,整體而言,概括論斷這些類型和理念則是極端危險的。強森(Samuel Johnson)將啟蒙運動中的文人共和國描述為「心靈社群」(community of mind)的展現,因為在那個共和國裡有某種共同的核心(轉引自Gay, 1966: 39)。因此,所謂「啟蒙運動規劃」當然是一個可以談論的題目。(MacIntyre, 1984: 117-118;Bernstein 1992: 202-208)。但對照之下,五四的思想世界由很多變動中的心靈社群所構成。於是,不僅有許多不斷變動又經常彼此衝突的五四規劃,而且每一規劃也有不同的版本。或許,關於五四我們祇能作出下面這個最安全的概括論斷:五四必須通過它的多重面相性和多重方向性來獲得理解。
注文
*本文英文原題“Neither Renaissance Nor Enlightenment:A Histo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rment”,由江政寬譯成中文。這次重印,作者作了全面修正。
〔注1〕Chow Tse-tsung(1960)簡要地討論過「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概念,以及它們對五四運動的適用範圍。他視兩者為「自由主義觀點」的代表(pp.338-342)。然而,Vera Schwarcz(1986)則在「五四」與「啟蒙運動」之間劃上等號,而未提及「文藝復興」。同一年李澤厚(1987:7-49)在一篇討論五四運動的著名文章裡,持論相同。
〔注2〕以後幾十年關於文藝復興時期土語文學的研究,已大大修正了土語文學與拉丁語文學勢不兩立的觀點。15世紀後期與16世紀早期,土語與新拉丁語之間是一種並立且相輔相成的關係。如果胡適採用1917年以後有關文藝復興的見解,那麼他也許便不得不放棄以文藝復興的比附五四了。詳細的討論,參見余英時(1976:305-308)。
〔注3〕然而,依Peter Gay的說法,儘管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之間有根本的親近性,但差異也是無可否認的。就像Peter Gay所說,「一如啟蒙運動,文藝復興也借助於遙遠的過去,來征服晚近的過去,但不同的是,文藝復興在希望渺茫中建立其激進主義。的確,閱讀伊拉斯謨(Erasmus)或馬基維利(Machiavelli)時,無不感受到,文藝復興也在希望渺茫中落幕:對於理性與人道的最終勝利,他們皆未顯示太大的信心」(1966:269)。
〔注4〕根據可確定為1936年後期中國共產黨的可靠檔案,中國共產黨在1936年9月以兩種重要的方式改變其路線。首先,它採取一種推動中國「民主共和」的溫和策略,取代無產階級革命。其次,在戰略上它呼籲結束內戰,盡一切可能與中國的所有政黨和團體,建立一種「統一陣線」。胡適於1940年獲得此一檔案,當時他是駐美大使(參見冊6,《中共的策略路線》,胡適,1990:未標頁碼)。毛澤東在1937年5月的記述,印證了此一檔案的可靠性(1969,冊1:233、246-247,注6)。1936年9月,陳伯達和艾思奇發動新啟蒙運動,而共產黨的新路線也剛好在那時候開始,這絕非是巧合。此外,那時為共產黨工作的青年作家王元化告訴我們,1938年前後,共產黨突然決定禁止「啟蒙運動」這一名稱,從而造成新啟蒙運動唐突地結束,這也是極具啟示性的(林毓生等,1989:3)。
〔注5〕胡適在1923年首度提出中國前現代歷史上有三次文藝復興的理論,但是他對前兩個文藝復興的分期,經過往後的幾十年,有了重大的修正。參見胡適,1990:1923年4月3日。
〔注6〕許孝炎在1920-1926年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1973年5月4日,他在香港的演說裡,也將五四文化運動特徵化為「啟蒙運動」(參見周陽山編,1979:679-685)。
〔注7〕Thomas R. Nevin將白璧德與杜威作了以下的對比:他重視意志,而以理智為其伙伴,這使他與當時主導性的哲學趨勢,特別是受杜威影響的那些趨勢,有著一種互相協調的基礎。但白璧德的焦點在於內心與個人,是對於潮流的反抗。他輕蔑解決問題的科學技術,然而他也擔心其對人文價值的侵蝕。他認為,同時代的「工具論者」與工程師的樂觀主義,無確定根據,又誤人歧途,因為不論如何靈巧規劃或付諸實驗,始終沒有任何社會能夠躲開人性脆弱的大問題。希臘悲劇詩人、但丁與歌德(Goethe)的作品以及人文修養均衡者的智慧無不顯示出:人性的脆弱是無法消除的。(1984: 147)。這段話完全適用於梅光迪與胡適之間的思想緊張關係,包括前者試圖讓他的白璧德式人文主義與胡適的杜威式實驗主義作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