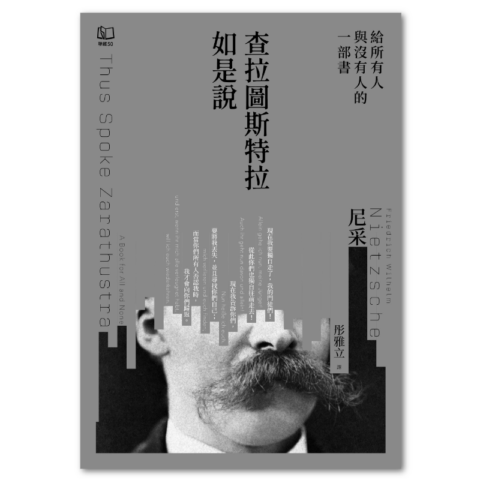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出版日期:2003-08-25
作者:王汎森
印刷:平版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33
開數:18開
EAN:9789570825930
系列:中國哲學與思想
尚有庫存
近代中國經歷了一些範疇性的轉變:在經學上,否定了過去兩千年的經學傳統,認為它們都是圍繞著一批「偽經」而積累的學問(康有為)。在文化上,充分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終存在著一個不安定層(傅斯年)。在道德上,發現過去兩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訓,關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關於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啟超)。在政治上,認為過去兩千年是無治狀態(劉師培),國其實不成其為國,因而有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轉化為「國家」,將「臣民」轉化為「國民」。對專制體制的深刻反省則發現中國沒有「社會」,並認為過去兩千年的政治理論都是「在空架之上層描摹」。除了上述之外,社會上的文化菁英也由傳統的「士大夫」變為「知識分子」。不管近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有多少實質的轉變,但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層次上這是一個斷裂和跳躍。而這些斷裂或跳躍並不是突然而來的,它們有深遠的文化、學術根源。本書基本上認為從道光以來,中國思想界便進入不安定期,每一種學問都因內外的挑戰,而產生了分子結構的變化。收在這本論文集中的文章,除了都觸及上述種種問題之外,並討論現代學術風格的形成與現代學術社會的建立。
作者:王汎森
臺灣雲林人,1958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研究領域以十五世紀以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近年來將研究觸角延伸到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學思想的政治意涵等問題。
著有《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譯本《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主編《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等書。
目 次
自 序 i
第一編 舊典範的危機
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 3
清季的社會政治與經典詮釋──邵懿辰與《禮經通論》 23
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太谷學派的研究 39
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 61
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 95
第二編 傳統與現代的辯證
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胳的分析 111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兼論思想的本質與思想的功能 133
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161
「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 181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195
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 221
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 241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275
第三編 新知識分子與學術社群的建立
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305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321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343
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 377
「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 463
附 錄
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 489
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 517
索 引 527
自 序
本書探討道光到1930年代大約一百年間思想學術變化中的幾個問題。這裡必須聲明的是:我並不是在寫一部通論近代思想、學術的書,而只是對這一段歷史中比較為人所忽略的層面做一些研究。我個人認為從道光以來,中國思想界便進入不安定期,每一種學問都因內外的挑戰,而產生了分子結構的變化。它們催化了後來一些範疇性的轉變:在經學上,否定了過去兩千年的經學傳統,認為它們都是圍繞著一批「偽經」而積累的學問(康有為)。在文化上,充份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終存在著一個不安定層(傅斯年)。在道德上,發現過去兩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訓,關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關於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啟超)。在政治上,認為過去兩千年是無治狀態(劉師培),國其實不成其為國,因而有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轉化為「國家」,由「臣民」轉化為「國民」、「公民」。對專制體制的深刻反省則發現中國沒有「社會」,也有人認為過去兩千年的治政理論都是「在空架之上層層描摹」(毛澤東)。不管近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有多少實質的轉變,但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層次上這是一個斷裂和跳躍。同時,這些新思想新概念,也回過頭來極深刻地改變了近代的學術論述。
收在這裡的文章並不是有系統地寫成的,因此先天上有了兩種限制。首先,因為機緣不同,所以文章有詳略之異。第二,正因為這些文章是隨著不同的需要而寫成的,所以並沒有預想一個系統。我之所以將它命名為《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是因為這些文章中似乎仍有一條線索。第一部分:「舊典範的危機」,從晚清內部思潮的變動開始。方東樹的例子,是討論方氏對漢學的攻擊在晚清思想史中之意義。方氏此舉,顯然並不只是理學的回潮,同時也代表了新時代的動向。有關邵懿辰的文章,則是探討邵氏的一本小書,如何在堅如磐石的堤防上鑿了一個小洞,這個小洞,後來逐步擴大,成為近代龐大的疑古運動的一個根源。邵氏的一些論點,代表了在時代的催化之下,傳統內部的思想因子產生的蛻變。太谷學派的出現,則代表當時的下層知識分子利用傳統的思想資源,以因應時代困局的一次並沒有成功的努力。這三篇文字,各自從不同的側面,說明晚清思想的不同面貌;〈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一文則在說明晚清漢族歷史記憶的復活如何改變當時的政治文化,同時也討論了新的歷史記憶資源如何顛覆了官版的歷史記憶,而為晚清的歷史變動埋下種子。以上四篇文章分別談清季上層及下層知識分子的四種變化,它們設定了一個背景,並作為以後諸篇文字發展的張本。
第二部分是「傳統與現代的辯證」。其中的兩篇:〈從傳統到反傳統〉、〈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都是提綱式的文字;〈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一文,儘管是針對特定的現象而寫,但也可以看做是從特定的角度談從傳統到現代曲折而蜿蜒的發展路徑。「傳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詮釋與使用中獲得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詮釋中改變它的風貌。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到:想瞭解傳統與每一個時代的關係,必須將那個時代主動的詮釋與使用考慮進去,而不應局限於線性的因果關係。
傳統與現代複雜的糾纏,也表現在私人領域上。近代中國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即是無所不在的國家化、政治化,公領域如此,思想、學術如此,即使日常生活也有逐步政治化的傾向,而以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為其高峰。本書收了一篇〈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便是有關這個現象的舉例性探討。
中國歷史上有過幾次「思想資源」的重大變化。在〈「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一文中,我用晚清的例子來說明:「思想資源」之轉移以及「概念工具」的變動,如何改變一個時代的思想面貌。在這篇文章中,我主要討論了當時中國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但我決不是想通盤討論所有相關的細節,而只是想藉此說明,如果不考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之變化,對當時思想界的變遷就難以理解了。
人是詮釋性的動物,當一個新的概念出現之後,人們會用它來作為思考自己處境及命運的工具。在William H. Sewell 研究法國大革命之勞工問題的書中,作者發現新的詞彙與概念使得勞工們用來思考他們的經驗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境況的方式產生了改變。在工廠中過著艱苦生活的人,可能渾然不覺,也可能用許許多多理由來解釋自己的處境,但是有了「階級」的概念時,便可能賦予當前處境一種全然不同的意義。語言與概念非但表達了社會的現實,它也「建構」了社會事實。在近代中國,文化菁英先是使用一群舊概念去詮釋新東西,但慢慢地一批又一批新的概念湧入,並逐步建構了現實的發展。大約1920、1930年代,「階級」概念逐漸取得壓倒性的優勢。胡適說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名詞運動,並在一次演講中說「一些抽象的,未經界定的文詞發揮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別小看一些大字眼的魔幻力量」,其實即說明了新名詞、新概念建構現實的力量。
〈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一文,說明西方的學說如何能以中國的面貌出現,而中國當時的困境又何以能夠逼使這類思想更易於為人接受。同時,從劉師培身上可以看到一種兩難,一方面是反西化的西方主義,一方面又是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從他身上可以看出一個既傳統又現代的學者掙扎於一個艱苦時代的痕跡。
第三部分是:「新知識分子與學術社群的建立」。1905年廢除科舉,千年以來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了,一方面解放了儒家正統文化思想的限制,一方面也迫使八股文化下的舊士人走投無路,一批文化菁英由傳統的「士」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的出現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作官不再是他們惟一的出路,他們尋找到了一個新的任務:「建立一個學術社會」(顧頡剛)。讀者會發現這一組文字大多和傅斯年有關。傅斯年當然不是「建立學術社會」的惟一代表,但他毫無疑問的是一個靈魂人物,而我個人恰好對他做過比較集中的研究,自然也就多寫了幾篇和他有關的文章。在這一組文章中,〈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是姐妹作,它們都討論古史多元觀的形成與傳播,我希望用它們作例子來說明一個學術詮釋典範形成的歷程。而在當時的學術界,有許許多多這種新詮釋典範出現。此外,這兩篇文字也可以看出現代思想中講求多元、強調變化的觀念如何體現在學術研究上。〈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則以身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傅斯年為例,說明他成學的經過、他的志業以及當時學術界「新」、「舊」、「公」、「私」之間的糾纏與衝突。〈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一文,則以一件個案來說明學術上從舊到新的轉變,以及牽涉其中的社會政治因素。上述各文直接或間接說明了現代知識分子在建立一個新「學術社會」上的努力。
〈「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則指出近代中國有兩種力量:一種是要求學術獨立,免於政治及道德教條之干擾;一種是愈來愈強的「主義崇拜」,希望以「主義」來指導一切。這兩股力量的衝突表現在許多事物中,本文則是以陳寅恪為例,考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學、仕分途以後,這個新「學術社會」的命運。
同時,在本書的一些文章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一個始終不曾消失的緊張性。道光咸豐以來,傳統學術極力掙扎著改變自己,以求扣聯政治、社會,而在民國新學術運動開展之後,我們也可以發現學術的社會性與平民性始終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一方面是想步趨西學,建立以問題意識為取向的新學術,同時也希望「為學術而學術」,將政治與道德教條對學問的干擾減到最低。但人們很快地發現:追求學術獨立王國的同時也帶來了學術研究與現實致用之間的緊張、及學術社群的自我異化的問題。而把所研究的事物徹底「對象化」、把「價值」與「事實」分離之後,也使許多學者產生了生命意義的危機感。
在編輯這本小書的過程中,我曾對其中的一些文字加以刪改;為了使眉目更為清楚,幾篇文章的名字也作了更動。〈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原題是〈方東樹與晚清學風〉(《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清季的社會政治與經典詮釋〉一文,原題〈邵懿辰與清季思想的激烈化〉(《大陸雜誌》90卷3期)。〈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原題〈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太谷學派研究的回顧〉(《新史學》五卷四期)。〈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原題〈王國維與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為主的討論〉(孫敦恆等編《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20週年學術論文集》),〈「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原題是〈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45期)。〈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原題是〈劉師培與清末的無政府主義〉(《大陸雜誌》90卷6期)。〈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原題為〈讀「傅斯年檔案」札記〉(《當代》116期)。〈價值與事實的分離?〉原題為〈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羅志田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原題是〈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兩種危機〉(《當代》123期)。此外,我也對幾篇文章的副標題作了增刪。〈從傳統到反傳統〉一文發表在《當代》一個討論反傳統思想的專輯(《當代》13期),其中也採擷了我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書的一小部分及《章太炎的思想》的一篇附錄。〈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思與言》34卷3期)有一篇姐妹作〈歷史記憶與歷史:以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發表在《當代》91期(1993)我所編輯的「歷史記憶」專輯,這應該是台灣學術界最早討論「歷史記憶」的一篇文字,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有關太谷學派的一文,發表於1994年,當時並未能直接讀到太谷學派的經典,而是以回顧二手研究的方式寫成,所以逕注頁碼於文中。該文主要是想探討它在晚清思想脈絡中的意義。我個人得以見到大量太谷學派的遺經是晚近的事。
此書編校的過程遷延至三、四年,拖了這麼多年才完成,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對我而言,將這些文章收集出版是一件痛苦的事。多年前與出版公司簽訂了一張契約,言明要編成一本近代思想史的論文集,但這件事一再延擱,始終不曾付諸行動。如果沒有陳平原兄為河北教育出版社向我苦苦催逼(按:本書有一個所收文章較少的簡體字版在該社出版),我大概是無法輯成這本小書的。本書的聯經版原與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同時進行,但因為增補了一些新文章,並進行了一些修改,所以稽延至今,應該在此鄭重說明。在此,我要感謝我的老友劉季倫先生,他對本書的編輯過程費過很大的心血,提過寶貴的意見。林志宏學弟及家弟王昱峰等人費心校對本書,我要特別在此謝謝他們。初編此書時,我個人適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作客,我也想趁這個機會感謝那裡的朋友們。
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
近代思想變化的起點究竟是什麼時候?是鴉片戰爭嗎?討論近代思想時,可以直接從漢學談到新學嗎?在兩者之間是不是有第三種思想力量,也就是宋學的復興?而宋學的復興究竟只是一種古代學說單純的回潮,還是代表一個新時代的動向?
首先必須指出,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內部已面臨幾種挑戰。第一是內治的問題,動亂接踵而來,各種制度也出現問題,尤其是風俗道德方面,其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官僚的貪污腐化。正因為人們對貪污腐化觸目驚心,所以會出現像魏源(1794-1856)等人的「挑菜會」以及倭仁 (1804-1871)等人的「吃糠會」 。第二種挑戰是大家所熟知的鴉片及外夷的問題。
鴉片戰爭之前傳統學問已經起了種種變化。這些變化的原因很複雜,有的是學術內在發展的結果;漢學內部出現了許許多多因內在問題而產生的所謂「典範危機」。但最重要的是知識與現實、知識與人生的關係出現裂痕。當時知識分子有一個疑問:為何考證學如此發達,出版的書這麼多,而現實世界如此齷齪混亂?這個現象顯然與清初大儒的主張相違背。清初大儒說,研求聖經賢傳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能再返三代之治。但是清季學者開始質疑這個大前提:將三代社會的真相弄得愈清楚,好像也愈不可能把三代的理想付諸實行?是因為人們不肯留心致用,還是因為六經的社會與清代社會已經完全不同,以致不可能將六經原原本本地行諸當代?簡言之,這時候產生了一種深刻的「知識與現實世界斷裂」的危機感。人們懷疑當時居學術界主流地位的漢學考據,究竟與現實政術及道德風俗有何關聯?這一門學問是不是完全失去了現實關照性,以致於學術自學術、社會自社會,汗牛充棟的考據學著作非但不能為現實世界帶來一尺一寸的進步,反倒有惡劣的影響?
在《書林揚觶》一書中,方東樹(1772-1851)便將當時學問與現實世界的巨大斷裂說得非常坦白、非常激烈。這本書雖然是在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的,但發願撰寫則在道光五年(1825)的春天。他說當阮元(1764-1849)創建學海堂書院的隔年,阮氏首先以「學者願著何書」問堂中學生,方東樹聽了覺得非常感慨,他認為這個問題大錯特錯,阮元不應該只問學者想寫什麼書,而不問所寫的書有什麼用。故他慨歎後世著書太容易,「殆於有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於是發憤寫成十六篇文章,其中有不少直接或間接批評清儒拚命著書而不管現實的風氣。他在終篇中說:
藏書滿家好而讀之,著書滿家刊而傳之,誠為學士之雅素,然陳編萬卷,浩如煙海,苟學不知要,敝精耗神與之,畢世驗之身心性命,試之國計民生,無些生益處,……此只謂之嗜好,不可謂之學 。
這段話必須放在道光學術的背景下看。方氏是針對乾嘉學者拚命考證著書,只管在學術社群中樹立地位與聲望,而不管他們的專業研究與整個社會的福祉是否有任何關係而發的,所以他說那樣拚命著述,如果「驗之身心性命,試之國計民生,無些生益處」,則只能說是「嗜好」,不能稱之為「學」。所謂「學」,照傳統儒家的理想,應該是承擔天下國家的實政實務。故他說:
君子之學,崇德修慝辨惑,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之於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達則兼善,明體達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不然,雖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 。
方東樹代表道光年間一大批希望轉弦易轍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他們都不滿意當時學問的性質以及學問與社會的關係,他們想追求一種理想的人格,簡言之,一種整合政事、文章與道德為一的整體觀念。
他們也為宋學,乃至整個宋代伸冤,認為許多考據學領袖無情地攻擊宋學,乃至於「使有宋不得為代,程朱不得為人」 。他們認為宋學不但是中國學術的高峰,而且宋儒對先秦儒家的把握,其實是最高明的,宋儒對現實的關照也遠勝於考證學者。這一個將文明發展之注意力由漢轉向宋的方向,是清代後期思想史中一個關鍵性的變化。
以上這些觀點基本是鴉片戰爭以前知識圈中的一個「意見氣候」(climate of opinion)。不過毫無疑問的,鴉片戰爭的失敗,使這一發展變得更加激烈。如果不能掌握上述的「意見氣候」,便不能了解方東樹的思想傾向,而如果不能掌握方氏的思想傾向,就不能了解他為什麼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寫出了《漢學商兌》這部奇書。
一
在這裡我要先用《儀衛軒文集》中的材料,來說明方東樹的思想意趣,然後再談《漢學商兌》。
方東樹尊宋頌宋的態度與桐城文派有關。他的父親是姚鼐(1732-1815)的學生,而他自己也曾經長期從學於姚氏;他的交遊圈基本上也以桐城文派為主,這些人都看重朱學,對於陸王不能沒有懷疑 ,對於考證學,則常持激烈批判的態度。方氏在許多著作中都透露了他尊朱的熱情,如〈重刻白鹿洞書院學規序〉:
慨然想見朱子當日所以集群儒之大成,使斯道昭明,如日中天,其遺文教澤一字一言,皆如布帛菽粟,後之人日游其天而不能盡察也。……必欲興起人心風俗,莫如崇講朱子之學為切。
他說六經都是為了致用的──「六經之為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而這個宗旨「唯宋人為大得」 。《文集》中有幾篇長文,都是為了辯駁漢學家中相當流行的「理學亡國」論 ,譬如在〈明季殉難附記序〉中說:
世之鄙儒乃猶痛詆道學,力攻程朱,甚且以明之亡歸咎於講程朱之學,是惡知天下古今得失之大數乎?
他又說清儒「畢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為經之事盡於此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 他認為這是因為考據家只為了求在學術社群中的名聲,而不顧其他。他鄙薄考據學大師錢大昕(1728-1804),在〈書錢辛楣《養新錄》後〉中說:
然則其所作《廿一史考異》亦何用也,不過搜覓細碎眩博以邀名而已 。
他痛斥考據大家閻若璩(1636-1704),在〈潛邱劄記書後〉中一再強調,為了名,這些學者可以不要天下國家 ,說他們:
雖竊大名,亦徒榮華於一朝,而末由施用而不朽 。
他也批評清儒之學有愈走愈窄,愈來愈小,愈來愈瑣碎,也愈來愈離開現實的趨勢,對於宋人之學也愈來愈不能以公平的態度去對待。在〈潛邱劄記書後〉中,他說顧炎武(1613-1682)的書還有「本領根源」,所以其書尚莫能廢;到了閻若璩,已經變小了──「其體例不免傖陋,氣象矜忿迫隘,悻悻然類小丈夫之所發」 。到了惠棟(1697-1758)、戴震(1723-1777)、臧琳(1650-1713)等,又變得更小,更無是非,而且「專與宋儒為水火」 ,他們的學問不過是取漢儒破碎之學加以穿鑿而已。他特別點出揚州江藩(1761-1831)等人是使得漢學走入窄小狹仄之局的關鍵人物,在〈復羅月川太守書〉中他說:
此其風實自惠氏、戴氏開之,而揚州為尤甚。及其又次者,行義不必檢,文理不必通,身心性命未之聞,經濟文章不之講,流宕風氣,入主出奴 。
引文中的「揚州」指江藩等人。在他們主導下,學問風氣「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殺,名為治經,實足亂經,名為衛道,實則畔道」 。所以他要向這些被「揚州佬」所窄化的學問開火。這也是為什麼此下我要花費一些篇幅談方東樹與揚州學圈的關係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