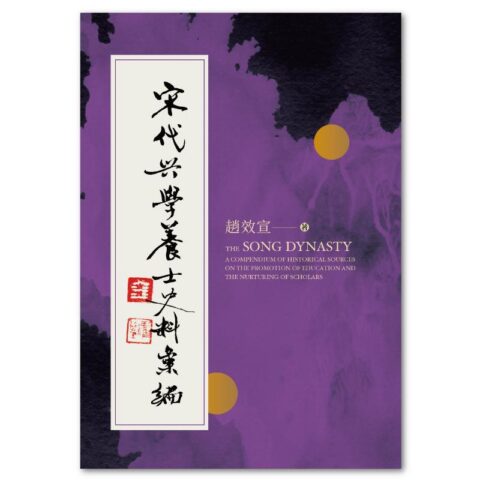歷史、身體、國家
出版日期:2001-01-31
作者:黃金麟
印刷:平版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22
開數:正25開
EAN:9789570821697
系列:中國近、現代史
已售完
這本書基本上想要回答三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的身體究竟經歷了甚麼樣的歷史變化,才有現今的樣子?這種身體的發展狀態隱含了甚麼樣的歷史特定性與危險性?它能否被當成是一種普遍、永恆的身體模式來看待?對這些問題的質疑與回答構成了本書的基本論調。作者希望透過這些討論來澄清,身體的存在和意義是怎樣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演變中,因隨著國族命運的更動而被積澱、型塑出來?這本書將以四個議題來證示身體在近代中國的變化。它們分別是:身體的國家化、法權化、時間化、與空間化發展。在身體的國家化發展方面,作者以出現在清末民初的系列國民改造運動,以及伴隨而來的教育體制改變,來省察身體的國族化發展。身體的法權化發展探討的是,近代中國的法系由舊有的倫理法演變為權利法時,身體的發展和建構在其中經歷了甚麼變化。這種改變對獨立的身體和國族化的身體建構有甚麼作用?至於在時間化方面,作者論證「世界時間」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侵入中國,對中國的身體所造成的關鍵影響。而在空間化方面,作者以清末民初的學生運動為例,以游移在街道和公共廣場上的身體來檢視身體的建構與空間的關聯。透過這些討論,作者希望呈顯一個圖像,那就是身體的生成其實是一個非常政治性的過程與結果。這種為了國家,以及經由國家,而形成的身體認知方式,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與世事的演變而消減,相反地,它正以強勢的態度主導著當代中國和台灣的身體發展。這本書的撰寫就是想要開啟一道門,讓我們一窺這種偏狹發展的危險。
作者:黃金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社會學理論、近現代中國的文化與政治,身體社會史、戰爭與現代性等。著有《歷史、身體、國家》(2001, 2006),《政體與身體》(2005),《戰爭、身體、現代性》(2009)等書及相關論文。
自序 i
第一章 身體與政治 1
為何是身體? 1
身體的社會學思索 9
近代中國的身體發展與身體研究 20
第二章 軍國民、新民與公民的身體——身體的
國家化生成 33
「模範生」的言說生產 33
改造人作為改造一切的基礎 44
軍國民、新民與公民的思想牽演 55
格式化的身體規訓 97
結論 105
第三章 禮法鬥爭下的中國身體——法權身體的誕生 109
刑律與身體 109
舊律與身體 114
身體的法權化 125
禮法之爭:一場身體的從屬戰爭 139
民法上的「人」與身體 157
結論 169
第四章 鐘點時間與身體 175
身體與時間 175
世界時間的採納 183
鐘點時間的興起 197
身體的時間化與鐘點計值 202
教化性身體與時間 215
結論 228
第五章 游移的身體與空間的身體建構 231
空間與身體 231
「示威」:身體的空間展演 239
法權與時間的空間實踐 261
空間的挪用與身體行動 271
結論 280
第六章 身體的去從 283
參考文獻 293
索引 315
這本書所以以「歷史、身體、國家」作為標題,並將身體夾放在「歷史」與「國家」之間,並不是一個任意的選擇。這個排列組合相當程度反映身體在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的存在景況。這種前有特定歷史結構的束限,後有國家需求的賦加,正是身體在當時所遭遇的兩重羈絆。這個特定的歷史格局和其所具有的結構性限制,是我們在觀察近代中國的身體生成時,不能忽略的部分。這本書的寫作基本上是想要回答三個簡單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的身體究竟經歷了甚麼樣的歷史變化,才有現今的樣子?這種身體的發展狀態隱含了甚麼樣的歷史特定性與危險性?它能否被當成是一種普遍、永恆的身體模式來看待?對這些問題的質疑與回答,構成了本書的基本論調。雖然書中所談的歷史階段離現今已有一段距離,但許多書中提及的問題與現象,對現今的身體發展仍具有一定的診斷作用。這種兼及歷史研究與文化批判的工作,是我想透過這本書一併完成的工作。
在討論這個攸關近代身體生成的關鍵時程時,我的內心一直有著一個衝突性(ambivalent)的思慮存在。我想這是大部分研究和反省現代性(modernity)的學者都容易有的心理情結。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現代性的發展和輸入(特別就中國而言),的確讓身體經歷了某種前所未有的「自由」與「快樂」,讓身體得以擺脫傳統倫理與秩序的專斷統治,進入一個新的發展紀元。但是在做這樣的認證與讚許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現代性和其所產生的認知框架已經變成一個類似孔恩(Thomas S. Kuhn)所說的典範性思維,主導著身體的發展和價值評量。這種認知形勢和其所包含的潛在危險,從二十世紀初葉後就逐步在侵吞著中國人的身體。這種無意識的身體發展形式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遞減的跡象,它依舊潛藏在身體的背後,限制著身體的發展可能性。這種典範化發展和它所意含的局限,在以後現代的視角來檢視時,特別顯得明顯突兀。在無意暗示後現代就是一種出路的前提下(我還沒有看到這種可能性),我希望本書的討論能使讀者重新思考「身體的存在究竟應該如何被看待」的這個問題,使身體的國家化與工具化發展,這兩個隱而不顯但卻持續侵蝕身體的發展趨勢,獲得某種的超脫。本書對於現代性身體的質疑或許還不夠周延完整,這個不足只能以更多的深思、研究、和努力來補足,我希望自己的未來研究能對這個缺失有更多的補足。
過去三年來,這本書的寫作和修改幾乎佔去我教學之餘的大部分時間。沒有東海的幽靜與自由,以及社會學系的良好研究環境和同仁鼓勵,這本書將無法在這麼有限的時間內順利完成。這個得天獨厚的環境,和她所給予我的幽靜、自在、與舒適,是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原因。我感謝林松齡教授在過去六年中所給予我的持續鼓勵。雖然斯人已遠,但感念的情份沒有因此而稍減。國科會在過去幾年來對我的研究計畫的持續贊助,讓我能夠心無旁騖地優游於社會學和史學的浩瀚領域,探討一些有趣的課題,也是我衷心感謝的。本書的第二章和第五章曾分別在1999年的社會學年會,與「間別千年:臨界空間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做過口頭發表,與會學者的建議與鼓勵,以及評論人的批評,均令我受惠甚多,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除此之外,我也要感謝丘為君、沈松僑、和蔡篤堅幾位對本書部分章節內容的批評與資料提供。「身體史學」與「身體╱政治」課程學生金世康、謝雨絜、葉於婷、李孟漢、蔡文騰、廖旋妙、陳淑真、施嫦芬、楊宗瀚、許世一、劉慧璇、陳惠萍、許裕昌、許絜嵐、和沈佩儀等人的閱讀討論書中大部分章節,也讓我受惠甚多。參與這個研究計畫的助理唐珮珍、林庭瑤、許絜嵐、許裕昌、和林銘溢,也是我要感謝的對象,沒有他們的費心與投入搜尋資料,這本書將無法以現有的面貌呈現在讀者眼前。聯經的編輯委員會對本書部分內容的中肯批評與建議,張運宗先生的協助排版與製作索引,以及林載爵總編輯的慨然協助出版、安排評審、與效率配合,也是我要衷心致謝的對象。
我的家人對我的長期支持是撰寫這本書不可或缺的要件。雖然我母親沒有機會看到這本書的出版,我還是要在這裡感謝她一生的照顧與撫養,並將這本書的完成歸功於她的努力與付出。安婕的出生讓我在忙碌中享受著許多初為人父的喜悅;咸惠的費心照料家務與精神支持,權充所有初稿的審查者,更是我必須深切感謝的對象。本書的出版雖然有這些人的協助,但他們都不應該為書中的任何可能錯誤負責,這個責任應該由作者個人來負擔。
第一章
身體與政治
為何是身體?
在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格局裡,身體的存在究竟處在一種怎樣的景況,這個問題一直未有清楚的闡釋。對許多研究近代中國史的學者而言,身體的存在是一個事實,但礙於各種條件的阻滯,這個議題一直沒有成為他們著墨考究的對象。這種輕忽和低估或許並不能歸咎於任何學者的偷懶,而是因為長期以來學界已經習慣以一些既有的典範來思考和觀察問題。這種偏好雖然可以使我們對某些已經發生的事件、重要的個人、主流的思想、或區域化的政經發展有熟稔的瞭解,但它也使得我們無法再以一種新鮮的角度來觀照世界的變化,以及人在其間所經歷的種種命運變化。身體在漢學或中國研究領域中的低度顯影,甚至處在一種存而不論、視而不見的狀態,和這種既定思考的框限有一定的關聯。雖然這種長期的輕忽最近已經隨著女性主義、性別研究、醫療史、和儒道身體觀等的探討而有些微的改善,系統性的討論和規模性的反思仍處在萌芽的階段。
當然,在做這番反省與檢討的同時,我們也不必過於苛責漢學界或中國研究領域學者的學術定見與偏執,因為這種「蔽於人」或「蔽於己」的學術思考習慣,並不為我們所專有,而是一個遍及於中西方學術界的普遍毛病 。艾坡比(Joyce Appleby)等學者對出現於十八世紀後的英雄主義科學原則的批評,以及這種科學思考所隱含的絕對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弊病的檢討,就清楚說明這個源於十八世紀的科學革命對後世學術發展所造成的嚴重影響 。以身體這個議題的探討而言,西方學術界也是到1980年代初期才因為女性主義運動的高漲、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對身體的攻占、人口老化問題的焦慮、以及傅柯(Michel Foucault)對遍布人身周遭的「生命權力」(bio-power)的揭露與批判,而開始對此問題有所覺醒。然而,在整個中國研究的領域中,特別在中文書寫的世界裡,這個問題卻還是處在一個相對低度開發的境域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過去的認知積習依舊主宰著整個學術研究領域,這個狀態使身體研究遲遲無法成為一個檢視歷史走向和觀察人身價值的著力焦點。
研究身體在近代中國的演變具有以下三個意義。首先,以身體的生成來觀看歷史的演變,可以讓我們對許多已經發生的史事或史實有一個不同的考察切入點,讓原來以王朝、政治、經濟、或社會階級等作為聚焦的分析,改為以身體作為考究的出發點 。這個觀察除了可以讓我們對過往的史實有更多面的認識外,也可以讓我們對許多過去視為零散、索然、甚至不相關的史事,有一份新的體察和警惕,警醒到其間可能存在的連續發展。除了這個層面的顯露外,以一個歷史的角度來思索身體的生成,也可以讓我們對出現於1980年代後的各種身體議論,特別是有關身體的類型學分析,以及那種以西方身體發展為參考對象所形成的身體理論,有一個反省檢視的機會。這種透過歷史討論以檢討理論思維的做法,也能讓我們在審視理論發展之餘,對中國身體生成的特殊性有所照顧。本研究將證示,這些理論性的劃分和區辨容或具有啟發思考的功能,但在面對具體的歷史現象時,它們的脆弱和簡化,以及隱含在其中的以歐洲為中心(eurocentric)的趨向,將立刻顯露無遺。在中西方各具有特定的歷史發展軌跡的前提下,我們必須小心,避免以西方的歷史經驗,和建立在這種經驗上的身體理論來直接解釋中國的身體生成。這種理論和概念的暴虐運用是應該謹慎避免的。如何營造一個切合、有趣、有對話的討論,同時避免一種「義和團式」的反外情結,是我們必須慎重對待的問題。最後,研究身體在近代中國的生成也可以讓我們對自身的存在,有一個不算全新、但卻更深入的瞭解。這個「認識自己」的目的是我所以會對此問題著迷,甚至有著強烈探求動機的原因。我希望透過這個討論來澄清,身體的存在和意義是怎樣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演變中,因隨著國族命運的更動而被積澱、型塑出來?這個有著特定歷史背景的身體發展形式,最後怎樣變成一個普遍、共通的身體開發形式,這一路是怎麼走過來的?
雖然這本書裡面討論的問題都是清末民初時期發生的一些史事,但這些攸關身體生成的重要過程和面向卻是決定往後數十年,甚至百年,中國身體發展的主要力道所在。以當代身體所具有的國家化、法權化、時間化、和空間化發展而言,這四個本書著力探討的面向,其實早在百年前就已經走上現今發展的道路。因此,本書的撰寫,除了是希望對這一段歷史發展有一個客觀的陳述外,也期望透過時間的拉長而對自己的存在和其所以然,有一個更清楚的理解。當然,這樣的聲稱並沒有否定台灣在經過日據五十年的統治後,已經產生一個和中國本土不同的身體發展歷程,甚至在1949年之後產生一種後殖民論述所謂的「混血」的新身體經驗。不過由於國民政府的遷徙台灣,甚至搬置許多民國初期的身體論述和制度來統治台灣,因此本書所談的內容對許多生活於台灣的人也具有一定的認識自我作用。
當然,身體的存在並不始自清末民初時期。我之所以選定清末民初作為身體研究的起點,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中國所面臨的困頓局勢,以及因此困頓而產生的許多改革措施,如由清政府推動的自強運動、變法、修律、和教育改造運動,以及由民間知識分子所發動的軍國民、新民、新文化、和公民運動等,都和身體的打造或再造有著直接的關聯。甚至以愛國作為名義的各種學生運動,也都對近代身體的型塑和使命化產生一定的強化作用。這些密集、接續開展的活動,它們的形成和出發動機或許並不一致,有些甚至也不是以身體的生成作為獨立的訴求,但在結果上卻都對身體的改造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些出現在論述上和制度改造層面上的變化,使身體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改變。這些一波波的改革措施,雖然沒有全部去除儒、墨、道、法等傳統思維對身體形成的拘繫,卻使得它們的議論快速淪為一種邊陲論述(marginal discourses),不再掌握有型塑和指導身體作為的主導地位。這些重大的變化說明,如果我們要瞭解近代中國身體的生成,以及所以產生這種重大變化的原因,對清末民初歷史的看重,特別是以身體的生成作為切入角度,重新審視這一段的歷史發展,是一個不可少的工作。
雖然本書無意於以一種鉅細靡遺的考證工夫,或一種編年纂述的形式,來檢討身體在近代中國所經歷的巨大變化,但清楚交代身體的意含,以及本書側重的分析面向卻是必要的。就身體的生成而言,它自然包括一個生物性的存有以及一個文化性的成份在內。這種自然與文化的交雜混合是所有古今身體都具有的共通特質,也是它所以不易被限定化,或單一化呈顯的主要原因。這種看法幾乎是所有研究身體的學者都共同持有的基本立場 。因為當身體的生成不單牽涉到一個生物性的存在,還牽涉到文化性的區辨和認定時,各種政治和社會的任意就可能滲入身體的建構過程中,使它成為一個無始無終的生成過程。這種不確定、成為(becoming)某種狀態的發展流程,泛現在各種身體的生產過程中。而也在這個身體是一個未完成(unfinished)的發展過程上,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教育、和公共衛生的力量,正試圖透過它們所能掌握的細微管道,在肉體已然存在的前提下,主宰或影響身體的建構過程。這種多種力量同時作用在個體身上的發展局勢,可以在不同的個人、性別、族裔、身分團體、或階級的層次上觀看出來。然而,在做這般的考量時,我們也必須留意,這其間並沒有一個唯一、獨大的主宰力量,或一個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聲稱的歸根結底(in the last instance)都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在統合著各式身體的生成。作為一種生物和文化交融的產物,身體的發展一直受制於時間、空間、和各種力量交加、互制的影響,其間並沒有那個力量永遠超越和主宰其他力量的問題。
在強調了身體的可能變易,以及這種變易和身體的存在本質的關聯後,接著我要交代的是本書側重的分析面向,以及採取這種分析立場的理由。整體而言,我希望這本書能給讀者一個清晰的圖像,那就是身體的生成是一個非常政治性的過程和結果。它不是一個自發、天成、生物決定、甚或個人意志反影的結果。雖然我們都擁有一個身體,而「我」的存在也源自於我的「身體」的事實存在,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或經常掌握、主控身體的全部發展樣貌。存在主義和現象學層次上的「我等同於我的身體」的聲稱,容或可以給予我們一個體悟身體觸覺,以及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生活世界建構的關連的思考,但這並不能去除身體的存在必然交雜著許多力量的同時存在,以及身體必須存在於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場域的這個事實。這些牽涉著身體的生成,甚至外於身體而存在的客觀力量,它們的實際存在和對身體所造成的影響,已經清楚說明意向性這個概念並不能用來解釋身體生成的全部過程。在承認並嚴肅看待身體的生物性限制(如生老病死)和需求之後,我希望能以一個身體社會史(socio-historical study of body)的方式來探究和表現身體在近代中國的發展與變化。這個以建構論為基底的探討方式,它的重點在於強調身體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它的發展和變化深受當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環境的制約影響。這種多元、泛及於論述和非論述層次的深度浸透,不單對身體的生物性構成產生開發和指引的作用,同時也對身體的社會文化發展產生前導性的效果。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些建構身體成為一種主體載體的社會性力量,進行一個同時性與歷時性的討論,進而才能對這個主體的誕生有更適切的瞭解。
就像所有其他的社會研究一樣,身體研究並不具有任何先驗的標準可以作為探究的指引,或形成一個絕對正確的進路。這種尋找唯一正確的道路,在研究上是一個不必要的心理負擔和欲想。在不能窮盡,也沒有必要窮盡所有的面向才能對身體做一個
深度、有趣探討的情況下,我們所要努力的毋寧是對特定時空條件下所形成的特定身體形式,進行一個因果性的評論和分析。縱然這樣的討論在一些後現代史學者的眼中,可能被視為是一種意識型態的縮影,或一種文本衍生的結果,我們仍然不能放棄討論和辯詰是認識世界最有利的方式的這個立場。空洞的懷疑主義或虛無主義立場並不能真正為人的存在以及身體的解放,找到鬆脫的出路。在這種體認下,我以四個攸關身體生成的基本面向來檢討近代中國的身體發展趨向。我希望透過這個討論顯露身體在中國的特定與局限發展,以及這種發展所造就的「合法」危險。這四個面向分別是身體的國家化和使命化開展,身體的法權化發展,身體的時間化走向,以及身體的空間化展演。我無意宣稱這個討論的整全性,也無意將其視為是研究身體的唯一正確進路,這四個分析面向本身包含的高度選擇性已經否定這兩種可能性。我所期望完成的只是在於解剖身體在近代中國所遭遇的過度政治性支配,以及這種支配所以產生的原因和過程。這種討論並不否定我們的確還可以從其他的面向或活動,如宗教、禮儀、性別、思想、育嬰、人口、或公共衛生等,來檢視身體的建構與生成。
為了適切顯示這四個面向的確對近代中國的身體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將採取一種年鑑史學所謂的趨勢(conjuncture)的視角,來檢證這一系列的身體開展過程。這種為時三十到五十年的歷史發展趨勢,將較短暫的事件史更能提供我們一個觀測身體發展的基礎視野,同時也能超越偶發性(contingency)可能造成的判斷失誤 。我將以1895到1930年代的政治、社會發展作為主要的時間軸向,在必要的時候回溯到1860年代,來討論身體的發展狀況。我希望透過時間的拉長,以及事件之間的細微關聯,來凸顯身體在當時所經歷的綿延變化。至於在分析角度的抉選上,我將以宏觀(macro)的方式來觀察和分析身體在這四個面向上的發展,微觀(micro)部分由於必須落實在個別身體及其行動的細部觀察上,為了維持書中立論層次的一致,我將不在本書中議及這個部分。
身體的社會學思索
身體成為社會學關注的焦點,當和其他眾多議題,如宗教、生產、分工、組織、階層、和政治支配等作一比較時,是一個為時甚短的新起研究領域。在1980年以前,除了Goffman和Elias等人曾以個體身體的社會展演,以及身體禮儀的文明進展作為討論外,幾乎沒有甚麼重要的社會學著作是以身體作為深度探討的對象 。古典三大家,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雖然各有曠世的巨著討論人類的文明發展,和相應而起的生存困頓,但身體在他們的討論中泰半是以隱而不顯的方式存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非人性化發展的批判,和其顯露的人作為一種「類存在」(species being)在這種生產體系中所經歷的危厄,以及對異化(alienation)問題的關注等,都顯示一種生產性身體的存在,以及這種身體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所正經歷的艱難發展。涂爾幹對社會分工發展的探討,對集體意識的講究,和對「個體崇拜」(cult of the individual)的看重等,也都和身體的發展脫離不了關係。甚至在涂爾幹有關人性二元論的討論中,我們也可以清晰發現他的身體觀和古希臘哲學、基督教傳統、以及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立場有高度的傳承關聯。他將身體視為是一個短暫、世俗、充滿肉慾危險的生物機體,是一切私心的出發點;而相對應於身體存在的則是一個職司精神活動的神聖靈魂,它主掌著一切概念的活動以及道德教化的發展,這兩者之間經常處於一種矛盾、對立、和拉鋸的發展。這種將身體視為是一個非理性、充滿激情、情緒、和慾望的場域,必須受到心靈無時無刻的節制,否則便會釀成社會災害的看法,其實是一種希臘哲學、基督教傳統、和笛卡兒身體觀在二十世紀初葉的翻版 。這種將身體與心靈一分為二的做法,也影響著韋伯對西方歷史發展的觀察與探討。例如,韋伯對新教禁慾倫理的討論,對理性化發展的焦慮,以及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所包含的理性計算和組織的檢討,就明白表露身體可能具有的危險性,以及整個西方文化發展所以走上科層化和理性化的根本原由。這些不約而同的討論,雖然都不是以身體的顯性存在作為討論的基架,但它們的議論都顯示身體正在經歷一個「文明化」的洗鍊和約束,身體並不是存在在一個社會或歷史的真空中發展。身體的建構、形成、發展、和價值認定,與這些歷史性力量的發揮與再生產有著緊密的關聯。
到了1980年代初期後,由於女性主義對父權化社會和身體建構的批評與質疑,以及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高漲和文化工業的極度發展,導致身體成為一個消費商品的戰場,身體在社會學領域中的重要性與能見度因而獲得大幅提升。除了這兩個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激發因素是傅柯作品的問世。這個以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作為探討主軸,以全景敞視式的圓形監獄作為類比的分析基調,將隱含在人類社會中的身體規訓機制和策略方案,做了一次全面性的清算。從人文社會科學中的論述建構,醫療院所中的診療對待,到刑罰體系的變更發展和同性戀的禁制發展,傅柯以生命權力的概念對隱藏在身體四周的規訓技藝,以及因為這些外在技藝的無所不在與內化而形成的一種自體看管技藝(technology of the self),做毫無保留的揭露 。在他鋒銳的筆調與觀察下,身體如何因為各種不同的微權力機制(micro-power mechanisms)的行使,而在肉體、精神、動作、時間、和空間的層面上被建構成特定的模樣,開始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而也在這種書寫和觀察的雕琢下,溫馴的身體(docile body)——一個既具有生產性,又具有紀律性的身體——自此成為品評身體規訓效果的最佳標誌。這些源自於社會運動、品味變化、和批判性論述的出現而產生的能見度擴張,是身體所以在1980年代初葉後變成社會學矚目的焦點的重要原因。在這些新的分析思維的主導下,過去一分為二的身體與心靈對立的身體觀開始被打破,並且不再成為觀察身體的主要基調。
除了延續上述三個發展取徑繼續進行各種的經驗詮釋外,理論性的思維和建構也構成一個重要的身體研究面向。這個由Bryan S. Turner領銜進行的工作,使身體的類型學分析變成研究身體的主要開展形式。這種發展容或是一種對過去的研究所進行的總結性分析,但是它的出現卻也造成後續的討論落入類型學分析的窠臼,只以補充或修正的方式在既有的身體類型與框架中討論身體的建構,走不出一條更具恢弘性或深度性,以身體的存在和解放作為最終關懷的理論道路出來。這種對人以及人的身體欠缺終極關懷,只以身體的存在進行形式、客觀、和外在的分類與分析,是這些理論性思維共同具有的特徵。古典社會學家所秉恃以存的人文和道德關懷,以及傅柯作品中所展露的犀利批判精神,那種令讀者在閱讀之後會產生反省與亢奮的精神,在這些後起的討論中已不復可見。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缺少歷史縱深的、形式的、實證的、科學的、靜態的、和理念性的類型分析而已,Turner本身的討論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證。
按Turner的說法,每一個社會都會面對一個霍布斯(Hobbes)所謂的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這個古典的問題並不會因為時勢的改變或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消逝 。在此情況下,如何對身體的存
在進行一個秩序化的工程,使身體與社會的秩序發展產生一個同一、綿密的關連,便成為每一個社會都必須審慎面對的問題。在參酌了一些古典與當代的討論後,Turner提出了一個以社會生存為考量,同時深具功能論味道的身體理論出來。它將身體的討論劃分成人口和個別身體兩個部分來說明。在人口的層次上,每一個社會都會面對著如何在時間和空間上進行一個人口的延續與管制的挑戰。這個分別由馬爾薩斯和盧梭作為理論陳述代表的社會需求,說明一個社會必須在時間的面向上克服人口再生產的諸種問題,同時也必須在空間的議題上想像如何將眾多的身體做一個有效管制的問題,以免社會的生存因為人口的數量變化與流動,而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至於在個別身體的層次上,社會必須要求每一個身體具有一個內在、自我克制的理性發展,使慾望不至於超越集體利益的講求,使秩序可以在個我的情慾上發生規制的效果。這種以規約、束縛、和禁慾作為取向的身體發展,是社會在建構秩序狀態時不可或缺的條件。韋伯對新教義理的探討,和其中顯現的克己、禁慾精神,就充分顯現這種身體規約的功效所在。除此之外,社會也會對個我身體的外在表現,做出一些可見或不可見的規範性要求,以使身體的表現不致挑戰社會的集體訴求。Goffman對形象經營和形象創造的討論,和其中所顯現的社會計算,就說明身體的展演並不是一個私我意志表現的問題,因為這其中還包含有濃厚的社會可接受性考量在內。這些顯現在身體之上,並且為社會所刻意對待的工作(tasks),如人口的生育與空間管理,身體的內在克制與外在表演等,顯示社會是以一種戒慎恐懼的心理在對待身體的存在。對身體的有效統整和管理,在此成為社會秩序所以存在的重要基礎。
這種站在社會生存的角度上所進行的類型學功能解釋,和其顯現的身體秩序建構,雖然成功地表述社會期望於身體,並且加諸在身體之上的種種作為,但對身體本身可能具有的不同類型表現或行動則缺少著墨。Arthur W. Frank的利用身體的可否自我控制,慾望的是否涉入,以及身體與自我和與他人的關連作為條件,劃分身體成為四個不同的類型—即規訓性身體、支配性身體、鏡像身體、和溝通性身體等—就是希望將身體顯現在個我層次上的差別,做一次仔細的區別 。這種以身體自身,而非大社會的功能展演,作為出發的身體鑽探,的確可以讓我們省視到身體的結構化發展究竟是怎樣在日常的行動中實際開展,以及這種開展最後賦予身體一個怎樣的特色。透過對這些不同身體活動的觀察,以及相應而來的建構劃分,我們看到身體的多元和多變面貌,以及身體所以不是一個僵固不變的生物領域的理由。當然,也在這個事實的呈顯上,我們體會到Turner在書寫《身體與社會》一書時的感慨—「我愈來愈不能確定身體究竟是甚麼」—其實並不是一句多餘的閒語。他的發言憨然道出身體的多樣性格,以及研究身體的不易。
雖然Turner的理論建構有著嚴重的類型學和靜態分析的毛病,這種分析方式甚至也影響到後來學者的努力方向,但無可否認的是,他的確將身體生成中所包含的社會成份做了一次詳細的討論。不論是就人口的再生產或就其空間活動的規劃而言,我們都可以看到社會在其中留下許多干預的痕跡。透過節育和家庭計畫的推廣、公共衛生的要求、都市空間的規劃和使用、以及戶口警政制度的實施,人口的繁殖與活動被置入一個社會管控的範圍,受到各種政策的管束和指導。這種社會介入身體生產的過程,同樣也出現在個別身體的範域裡。不論是就宗教義理的闡述、普遍化教育的實施、消費倫理的崛起、或國族意識的強化而言,我們都可以看到身體正在經受一個內在和外在的約束與規制,或者說,一個理性與情慾、存有與工具性使用的爭戰。這些圍繞在身體四周,隨時企圖使身體成為某種理念或建制管束對象的力量,是我們在觀察身體生成時,不能忽略的部分。它們的事實存在也是身體所以能夠以一種建構論的方式來加以觀察的基礎所在。以一個較長的時程來觀察,我們將發現,從古典三大家以下,這種思考脈絡一直是社會學的主流,也是社會學所以能夠以實證和歷史的方式來考究社會與身體生成的主要原因。
而相對於這種將身體的生成歸諸於社會與文化力量的行使,自然論者則比較傾向以生物差異的角度來評述身體的發展。這個以1970年代興起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為主要角色的理論發展,它的最早根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後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與達爾文進化論等的興起 。在「優勝劣敗」成為普世接受的生存法則下,身體基因的優劣和男女荷爾蒙的差別也開始被援用來解釋種族的差別以及殖民的必要。這種以生物差異作為人支配人的「道德」基礎,也在男女的社會分工與性別角色的期待上產生過支持性的作用。這種看似客觀、科學的論證,其實對已經存在的種族、性別、和階級支配有著莫大的支撐作用,而這也是它所以被統治階層所接受,並且為反對者所排擠,指稱為一種保守主義的護符的主要原因。在後現代主義高漲的今天,以及在差異(difference)已然成為一種必須加以維護的自然狀態,甚至是一種美德的認知支持下,這種訴諸於生物基因與荷爾蒙的做法,和其中所暗含的進化、同一論調,自然難再受到學界的道德青睞。雖然有這些潛在的危險,這種立基在生物學上的觀點還是不應該被摒除在身體的解釋範圍之外,因為它的存在警醒我們,身體並不是一個社會與文化的單純建構物而已。沒有肉體的先決存在,以及其間隱含的形體、性徵、數量、和年齡等的差異,建構論不能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一種身體出來。
除了這種建構論與自然論的解釋差異外,隱含在理性化發展過程中的身體計算和規訓也是我們在進行身體研究時,必須特別留意的部分。這個分別由韋伯和傅柯集大成,做過詳盡探討的議題,在透過Turner的連結和提醒後,已經成為當代思索身體發展與建構的重要線索 。不論是從國族建構的角度,或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所需要的理性計算的角度來思考,對身體進行一個工具性的計算和一個科層化的組織與動員,已經成為一個無可避免的歷史趨勢。這個泛現在論述和非論述層次上的身體開展過程,說明理性化所要達致的效率控制,其實和傅柯所聲言的規訓性教養所要完成的狀態,沒有絕對的差別 。雖然韋伯並沒有對工具性理性極致發展後的身體狀態做過明確交代,但可以想見的是,在科層體系的籠罩下,身體的理性化和客體化發展最後極可能以一種傅柯所謂的溫馴的身體作為終結。雖然韋伯和傅柯兩人是從一種非常不同的角度來討論身體的生成,前者強調歷史的連續性和權力的集中性,後者強調歷史的不連續性與權力的散落性,但在刻畫身體所遭遇的理性計算和規訓對待時,兩者卻有相似的深層感應。這種對身體發展的敏銳感受、人文關懷、以及對現代性(modernity)的質疑和保留,是我們在閱讀韋伯與傅柯作品時同樣可以感受到的成份。
在無意過度渲染這種有限的相似的前提下,我希望能以傅柯和韋伯的這份交集作為出發,以一種趨勢的轉變來觀看身體在近代中國的發展。相同於傅柯之處是,我將不把精神或心靈,或一般熟知的國民性,當作是分析的焦點,而是將肉體的活動與心靈意志的開發同時當作對象來觀測。因為不論是就身體的國家化和法權化發展來觀看,還是就身體的時間化與空間化發展來檢討,這其中都沒有一條身與心劃分開來進行的界限存在。這些言談、動作、和制度化的規制對身體的影響是同時、整體地在進行,其中並沒有刻意的先後之分。因此,舊有的身心二分法,或一種「以心馭身」的思想史看法,將不再適合於這種分析的開展。這是我們在進行身體的社會史探討時,特別不同於思想史式的討論的部分。至於在研究的手法上,我將以宏觀的社會學分析作為主要的切入角度。這種分析方式不但較能凸顯趨勢發展的相關結構性面貌,同時也能賦予我們一個不同於微權力機制的身體討論格局。另外,在身體生成的觀察上,我將以歷史的連續性,而不是傅柯所著重的不連續性,作為思考和探討身體發展的軸線。這些是我的討論和傅柯的著眼點不同之處。
由於中國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葉時,仍舊稱不上是一個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主要營生模式的國家,而她所經歷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司法侵略等也不是當時的歐美國家所能比擬,因此在進行身體的觀察時,我們應留意歐洲中心身體觀在此可能具有的不適切性。這種保留並不代表這些理論必須被根本棄置,這種「愛用國貨」式的態度並不值得鼓勵。相反地,這些既存的特定論點正足以提供我們一個反省、對照、和出發的起點,以中國的特殊歷史局勢和脈絡來評析身體在中國的發展。例如,在生產方式依舊處於農業生產為大宗的情況下,以資本主義為主要發展軌跡的身體形式,和建立在這種發展軌跡上的身體理論,自然有些不適用於解釋中國的身體經驗。但若就民族國家的建立而言,歐陸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國民」思想,卻和中國的歷史發展有著高度的牽連。這個以資本主義生產作為基底的國家形式,甚至曾經是後者的主要學習和模仿對象。中國的著意在農業為主、工業為輔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富強的國家,和傾向以國家主義來統整人民的心智與身體,是一個非常特出的徵候。特別當和中國過往的歷史相較時,這更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這種經濟發展比重的差異,和對「國」的重要性的刻意強調,是我們在進行歷史性思考時不能忽略的部分。這種以「國」的生存做為無限上綱的身體發展形式,自然是和以布爾喬亞階級利益馬首是瞻的身體發展模式有極大的不同。這些歧異是我們在進行中國的身體研究時,必須小心計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