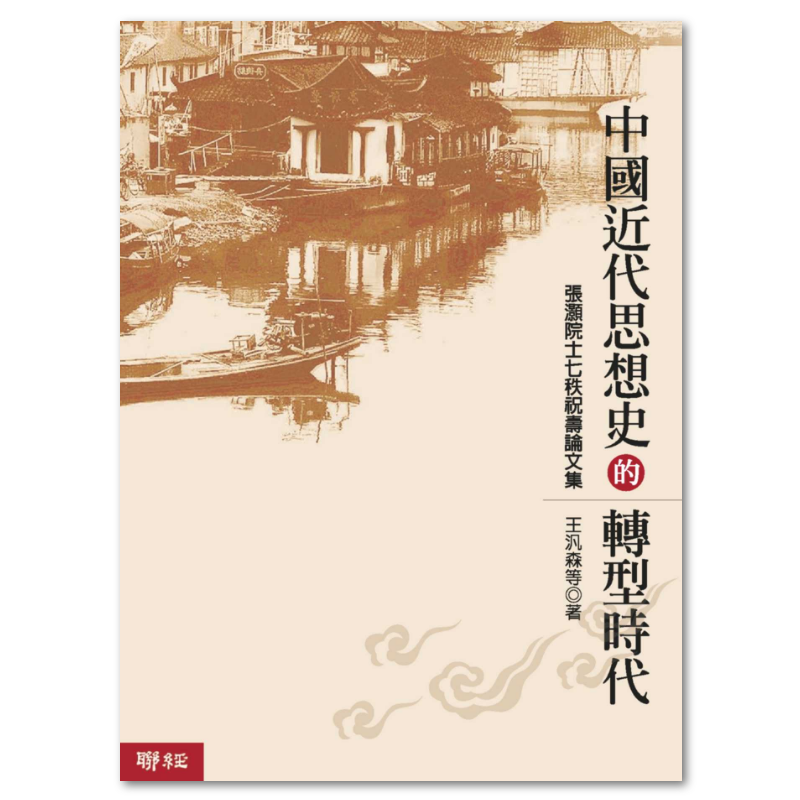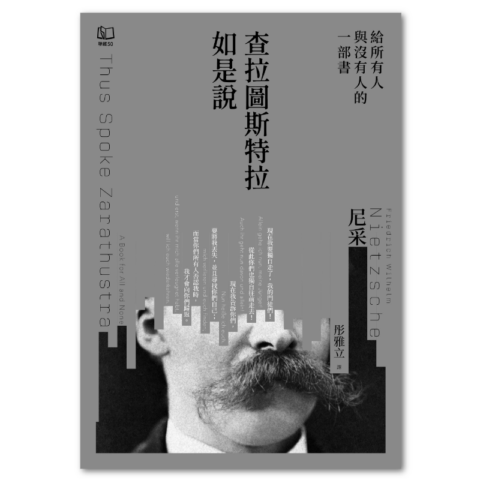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版)
出版日期:2022-11-03
編者:王汎森
裝訂:精裝
EAN:9789570865851
尚有庫存
張灝院士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等文章中指出:1895至1925年是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在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是思想內容方面,皆有突破性的劇變。就前者而言,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學會等制度性的傳播媒介大量湧現,同時新的社群媒體──「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出現了。在思想內容方面,除了有文化取向危機,同時也產生新的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本書是從上述的框架及議題出發,請各相關領域的專家,就個別論題進行探討,希望比較全面地呈現近代思想轉型期的複雜風貌。
編者:王汎森
臺灣雲林人,1958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研究領域以十五世紀以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近年來將研究觸角延伸到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學思想的政治意涵等問題。
著有《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譯本《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主編《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等書。
序
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
1-1 李仁淵,〈思想轉型時期的傳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報刊與新式出版業〉
1-2 沙培德(Peter Zarrow),〈啟蒙「新史學」:轉型期中的中國歷史教科書〉
1-3 孫慧敏,〈新式學校觀念的形成及影響〉
1-4 范廣欣,〈從鄭觀應到盛宣懷:轉型時代中國大學理念走向成熟〉
1-5 許紀霖,〈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
思想內容的變化
2-1 王汎森,〈新民與新人:近代思想中有關「自我」的幾個問題〉
2-2 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後中國的心理危機與宗教興趣〉
2-3 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
2-4 羅志田,〈理想與現實:清季民初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互動〉
2-5 王東杰,〈「反求諸己」:晚清進化觀與中國傳統思想取向(1895-1905)〉
2-6 黃克武,〈近代中國轉型時代的民主觀念〉
2-7 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
2-8 潘光哲,〈中國近代「轉型時代」的「地理想像」(1895-1925)〉
2-9 陳建華,〈1920年代「新」、「舊」文學之爭與文學公共空間的轉型??以文學
雜誌「通信」與「談話會」欄目為例〉
其他
3-1 丘為君,〈轉型時代:理念的形成、意義,與時間定限〉
王汎森
一、
2005年4月30日,我應邀前往香港科技大學參加「張灝教授榮退學術座談會」,雖然座談會只有半天時間,但在會前會後的閒談中,有不少張先生的門生故舊紛紛提議應該出版一本張先生七十歲祝壽論文集,並推我負責其事。
當時幾位與聞其事的朋友商量要以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來纂輯這本論文集,也就是放棄「盍各言爾志」的徵稿方式,改採議題比較集中的作法,當時就商定以張先生的文章〈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一文中所提及的種種主題作為對話的依據。因為這篇文章涉及的層面很廣,年代斷限確定¬¬──即1895至1925年──也就是甲午戰爭以後,一直到五卅運動、「主義時代」的來臨;我們決定就個別主題約一位曾經在相近領域作過研究的學者撰寫論文。大部份文章都在交稿期限內收到,不過也有幾篇延遲了相當長的時間,使得編輯工作頗有拖延,但整體而言整個過程相當順利。
本書共有十五篇文章,分成三大類,基本上是照著張灝先生〈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以下簡稱〈轉型時代〉)中所提到的相關主題的順序編排下來。此外也有幾篇文章稍稍軼出原先想定的主題,我們也盡可能作了適當的安排。
二、
張灝先生以「1895-1925」作為「轉型時代」,我認為這是他多年以來深思熟慮的結果。講授近代思想史的朋友恐怕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從鴉片戰爭一路講過來,每一個階段都有新的變化,尤其是1860年代以後,幾乎每年都有新東西,然後一直變到20世紀。問題是在這紛紜萬狀的變化中,其快慢強弱及寬狹深淺並不容易區分。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序中說明代心性之學太過發達,每個人都講一套,看不出大分別來,他用「黃茅白葦」一望皆是來形容,而黃宗羲最重要的工作是在這茫茫一片中識認出各家的「宗旨」,分出學派的不同,並加以綜合及論斷。黃宗羲的工作當然有不盡滿人意之處,但是沒有這部學案,研究明代思想史便有不知從何下手之感了。張先生把「轉型時代」斷在1895年至1925年,並由許多方面來加以論證,也是在「黃苐白葦」一望皆是的思想狀態中,提供一個可用的架構。
我個人教近代思想史多年,觀察1840年以來的變化,完全同意如果以思想變化的劇烈度、深刻度、傳播的廣度三個標準而言,1895至1925年確實稱得上是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由於甲午戰敗對當時中國人的刺激太大,所造成的變化非常劇烈,層面也非常之廣泛,以個人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為例,許多人對人生道路的安排、職業軌跡(career pattern)的設計都產生劇烈變化,關於這一點,我曾經提議進行「人群學」(prosopography)研究計劃,將近代人物年譜或傳記中,1895前後生命軌跡的重大改變作一統計,必能比較清楚地看出這個年代的重要性。 他們有的放棄蟲魚鳥獸的考據之學,有的放棄八股文,有的開始狂熱渴求西學,不一而足。這一類因時代的刺激而轉弦易轍的例子真是難以計數,也是在這個時代,放棄科舉考試、不事功名,從自古以來相沿不變的人生軌跡甌脫出來者逐漸增多,官方功令的力量吸引不住他們了,他們成為改變近代中國的「自由流動資源」(free floating resources)。
再以具里程碑意義的思想文獻及關鍵性行動的出現為例:1895年嚴復刊〈世變之亟〉及〈救亡決論〉,康有為公車上書、開「強學會」,1896年譚嗣同在南京完成《仁學》,嚴復初譯《天演論》,康有為撰《孔子改制考》,梁啟超撰《變法通義》,且與人合刊「時務報」於上海,1897年,譚嗣同、梁啟超等創「南學會」於湖南,康有為至京師上書陳事變之亟,1898年,張之洞刊《勸學篇》,嚴復始譯《原富》、《群學肄言》,擬上呈萬言書,接著發生戊戌政變,六君子被殺,康、梁出走……,一幕又一幕,也都是以1895年為重要分界點。
我推測張先生是以「主義時代」的興起為「轉型時代」的下限,因此可以定在聯俄容共的1924年,可以定在五卅慘案的1925,也可以定在北伐開始的1926年;張先生把它定在1925年,是因為在五卅運動中,「黨」的動員與「主義」的宣傳等形式都集中展現了。「主義時代」興起之後,原先那種充滿危機與混亂,同時也是萬馬爭鳴的探索、創新、多元的局面,逐漸歸於一元,被一套套新的政治意識形態所籠罩、宰制,標幟著「轉型時代」的結束。
以上是我對「轉型時代」何以定在1895至1925年的理解。以下我想略為說明本書各篇文章的安排。我將約略介紹〈轉型時代〉一文的大旨(有時不可避免地襲用原文),再提到本書相應的各章。
本書的第一部份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轉型時代〉一文一開始便指出「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及「思想的內容」兩部份的轉變,前者主要的變化有二,一為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及學會等制度性傳媒的湧現,一為新的社群媒體──知識階層的出現。
如果沒有大量的新式傳播媒介出現,思想的變化當然不大可能擴大影響範圍,並深入一般群眾,〈轉型時代〉一文中指出:「1895年以前,中國已有近代報刊雜誌的出現,但是數量極少,而且多半是傳教士或者商人辦的。前者主要是有關教會活動的消息,後者主要是有關商業市場的消息。少數幾家綜合性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循環日報》,又都是一些當時社會的「邊緣人士」,如外國人或者出身買辦階級的人辦的,屬於邊緣性報刊(marginal press),影響有限。」在1895年之後,報刊數量激增,而且主持者由邊緣人變為士紳階層,由「邊緣性報刊」,變為「菁英的報刊」。關於這個問題,本書收錄了李仁淵〈思想轉型時期的傳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報刊與新式出版業〉。除了報刊雜誌外,新式出版事業出現,有三大書局之稱的商務、中華、世界書局都是在轉型時代成立,而它們廣泛散佈新意識與新思想的一個重要管道,即是替新式學校印制各種教科書。沙培德(Peter Zarrow)的〈啟蒙「新史學」──轉型期中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以歷史教科書為例,說明這一現象下,新式印刷出版機構所編寫之教科書如何造成歷史教育在功能目標上的改變。
〈轉型時代〉一文提到,1895以後教育制度大規模改變,「首先是戊戌維新運動帶來興辦書院與學堂的風氣,設立新學科,介紹新思想,1900以後,繼之以教育制度的普遍改革,奠定了現代學校制度的基礎。一方面是1905年傳統考試制度的廢除,同時新式學堂的普遍建立,以建立新學制與吸收新知識為主要目的。當時大學的建立在新式學制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它們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溫床與集散中心。」本書中孫慧敏的〈新式學校觀念的形成及影響〉討論新式學校觀念的形成,而范廣欣的〈從鄭觀應到盛宣懷──轉型時代中國大學理念走向成熟〉,則以鄭、盛二人為例討論其大學理念從構想到實踐的形成。
〈轉型時代〉一文中以1895以後「學會」大興為例說明新社群媒體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的出現,本書則有許紀霖〈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思想內容的變化」。文中首先提到在1895之後出現文化取向的危機,最顯著的危機是「傳統政治秩序在轉型時代由動搖而崩潰,……使得中國人在政治社會上失去重心和方向,自然產生思想上極大的混亂與虛脫」,尤其是「普世王權」的崩潰,「不僅代表政治秩序的崩潰,也象徵基本宇宙觀受到震撼而動搖」,同時與宇宙觀綰合在一起的一些儒家基本價值也受到侵蝕而逐漸解體。
〈轉型時代〉進一步提到,傳統文化的主體──以禮為基礎的規範倫理與以仁為基礎的德性倫理,在1895之後皆因衝擊而動搖,三綱之說被嚴厲抨擊,《大學》中所強調的三綱領八條目──也就是「大學模式」──解紐。「這模式包括兩組理想:(1)儒家的人格理想──聖賢君子;(2)儒家的社會理想──天下國家。所謂解紐,是指這兩組理想的形式尚保存,但儒家對理想所作的實質定義已經動搖且失去吸引力。」張先生舉梁啟超《新民說》及劉師培《倫理學教科書》為例,說明「聖賢君子的人格理想」與儒家修身觀念中「工夫」的一面的分離,「儒家德性倫理的核心思想的基本模式的影響尚在,但這模式的實質內容已經模糊而淡化。」王汎森的〈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即是在這個框架下的進一步討論。
〈轉型時代〉中討論了「精神取向的危機」:在傳統意義架構動搖之後,人們必須重建生命意義的架構,因此紛紛走向佛學,或提出「人化的宗教」、「新宗教」等,不一而足。為了討論相關問題,本書中有葛兆光的〈孔教、佛教或耶教──1900年前後中國的心理危機與宗教興趣〉。
張文中提到新思想論域時提到「轉型時代制度性的傳播媒介促成了公共輿論的產生,這種輿論內容極為駁雜,各種問題都在討論之列」。他接著提到當時報刊雜誌中使用的新文體、新語言、新詞彙,而這些詞彙有的是西文直接譯來,更重要的是轉借日文的翻譯。在討論日本詞彙像海潮般輸入中國,並大幅改變人們的意識世界的現象,本書有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
張文提到當時中國的危機意識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三段結構:「(1)對現實日益沈重的沈淪感與疏離感;(2)強烈的前瞻意識,投射一個理想的未來;(3)關心從沈淪的現實通向理想的未來應採何種途徑。」在「對未來理想社會的展望」中,張先生提到從甲午以來,民族國家觀念是一個核心成份,但是同時也有以大同理想為代表的各種烏托邦主義,五四時代亦復如此,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交纏不清;本書中羅志田的〈理想與現實──清季民初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互動〉一文即是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在談到「由現實通向理想未來的途徑」中,張先生提到一種稱之為「歷史的理想主義」的世界觀,「這個新的歷史觀主要是由西學帶來的演進史觀,把歷史看作是朝著一個終極目的作直線的演進」,故本書中有王東杰的〈「反求諸己」──晚清進化觀與中國傳統思想取向(1895-1905)〉。
張先生在〈轉型時代〉中同時提到一種「以政治為本位的淑世精神」,一種高度的「人本意識」,「認為人的思想與意志是改造外在世界的動力」,所以直線向前發展的歷史觀念所形成的強烈的歷史潮流感並不能排斥「人的自動自發的意識與意志」的強大力量,在這個方面,王汎森有關「自我」與「政治」的文章中對此也有些許的討論。當然轉型時代新的思想領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是民主思想,故本書中收錄了黃克武的〈近代中國轉型時代的民主觀念〉。
在本書第二部份中,還收入三篇文章,分別是陳平原的〈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陳建華的〈1920年代「新」、「舊」文學之爭與文學公共空間的轉型──以文學雜誌「通信」與「談話會」欄目為例〉,潘光哲的〈中國近代「轉型時代」的「地理想像」(1895-1925)〉。表面看來,它們所討論的主題與張先生的文章似有出入,但事實上,陳平原關心近代中國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說」,如何與「報章」、「學校」結盟,促成了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並實現近現代中國文章的變革;陳建華的文章則關心1920年代「新」、「舊」文學之爭與文學公共空間的轉型,它們都與〈轉型時代〉一文中對新文體、新文學的討論有關,所以收在這裏。至於潘光哲討論近代「地理想像」之大變化,自然也可被視為是轉型時代種種新論域中的一環。
本書的第三部份收入了丘為君的〈轉型時代──理念的形成、意義,與時間定限〉一文。作為張先生的弟子,丘為君長期關心張先生「轉型時代」觀念的形成,所以該文是一篇研究「轉型時代」的「論述形成」(discourse formation)的文章。他從張先生的各種相關著作中勾稽出張先生的「轉型時代」概念,至少經過四期的發展。
第一期是將「轉型時代」定義為辛亥之前的中華帝國最後二十年左右,即是1890年至1911年,代表性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第二期是正式確立1895年的甲午戰爭為「轉型時代」的起點,「轉型時代」的概念由1890年至1911年修正為1895年至1911年,在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是〈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1978)。
第三期是「轉型時代二十五年說」的出現,「轉型時代」由晚清延伸進入民初,由甲午到「五四」,代表性作品是〈形象與實質──再認五四思想〉(1990)。第四期是正式確立「轉型時代時代三十說」,「轉型時代」定義為1895年至1925年,代表性的作品收錄在《時代的探索》中的論文(若干先前發表過的論文,在此書中,多將「轉型時代」的下限由1920年修正為1925年)。
就時代劃分而言,第一、二期可以歸類為「轉型時代晚清說」,第三、四期則向下延伸進入「五四」時期,成為「轉型時代晚清民初說」。
三、
以上是冒著簡化的危險,對〈轉型時代〉一文與各篇文章的關係所作的介紹。在本書形成的過程中,我主要是負責集稿,潘志群學弟則依據出版社所適用之標準統一各篇文章的格式、核對引文有疑義處、並進行加註人物生卒年等工作。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發行人、方清河先生、沙淑芬小姐都提供了許多幫助,特此致謝。
最後我希望代表本書的作者們說幾句話:本書的作者們雖然不一定是張先生的門生,但都希望藉這個難得的機會向張先生表達隆重的敬意。
王汎森謹識
於中研院史語所
中國近代「轉型時代」的「地理想像」(1895-1925)
潘光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
夏敬渠(1705-1787)的《野叟曝言》是清代著名的「才學小說」之一 ,是他個人才情的具體表現。在夏敬渠汪洋泓肆的想像裡,非僅主角文素臣自己功業崇隆,他的友朋也是際遇不凡。像是文素臣的好友之一景日京便「領兵航海」西行,「征伏歐羅巴洲二十餘國,建國號曰大人文國」,還讓「意大里、亞波而、都瓦爾、依西把尼亞,各率附屬小國,降伏大人文國主,受其節制。俱秉天朝正朔,亦如中國之制,除滅佛老,獨宗孔聖。頒下衣冠禮制,用夏變夷」 。待得進入20世紀,市面上則出現了陸士諤(1877-l944)的《新野叟曝言》(1909年初版) ,「故事新編」,述說文素臣的子裔文礽作為多才多藝的發明家,發明了可以遠征到金星、木星的「飛艦」之後,奉了皇上聖旨,先「牛刀小試」一番,擔任征歐大元帥,出征歐洲,振翮西行,不過一晝夜就到了歐洲,瞬即橫掃無敵,讓全歐洲七十二國爭先投降。隨後,文礽更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征服了月球和木星,不僅中國的黃龍國旗飄揚在月球上,木星更成了中國的殖民地 。夏敬渠和陸士諤的小說家言,好似荒誕不經,那種將自己步履從來未可及之的遙遠異域,納為己身臣屬之土的意欲,卻是躍然紙上。固然,夏敬渠和陸士諤因身處時代不同,他們吹奏的兩闕狂想曲所展現的思想涵義,亦不可等量齊觀;卻可想見,當小說家在無限寬廣的想像空間裡自由馳騁的時候,仍自有其知識憑藉,特別是既存的地理學知識,正是他們融鑄真假逞其幻思文采的思想動力之根源。
考究這股推動夏敬渠和陸士諤揮灑巧想幻思的知識與思想潮流,自然和「西潮東漸」的大背景密切相關。自17世紀以降,耶穌會教士帶來的(由西方建構的「現代」)地理知識,已曾引發相當的知識震撼與爭辯 。在18世紀大清帝國對外擴張的過程裡,來自西方的地理知識即為帝國擴張之所需,如康熙與乾隆年間分別竣工的《皇輿全覽圖》與乾隆《內府輿圖》,便是傳教士的功勞 。在帝國擴張的歷程裡,以各式各樣的地理文字資料和圖像視覺表述來界定其子民與領土範圍的成果(如《皇輿全覽圖》或是《蠻獠圖說》和各種「采風圖」等),也紛紛問世 。各種官修《方略》陸續纂修 ,也是炫耀帝國武功之盛的表現,可以視為「地理帝國主義論述」(geo-imperialist discourse)的張本 ;流風所及,19世紀上半葉各種關於現今中國邊疆事務的大量私家著述問世,固可視為考據學風與經世思想的結合反映 ,更是展現帝國榮光的歷史書寫 。約略與此同時,伴隨著基督教傳教士重啟傳播「福音」的浪潮,各式各樣的地理知識與資訊,也鋪天蓋地襲來 。大約在1830、1840年代,中國士人自己也開始(以傳教士提供的資訊為取材來源之一)纂輯述說世界地理和世界局勢的作品,如魏源(1794-1857)的《海國圖志》(1842年首度出版,此後更陸續增補) 與徐繼畬(1795-1873)的《瀛寰志略》(初刻於1848年) ,就是箇中名著。各式各樣相關的地理文本,源源不絕,同時並起,千奇百怪的大千世界與不可思議的知識,迎面撲來。由於地理知識的成長和變遷,既對源遠流長的「知識世界」的內部結構提出了挑戰 ;那些外在於中國的世界與國家,也成為知識的對象(an object of knowledge) ,各式各樣的探索述說,絡繹而生。可以說,隨著地理知識的增減更易而引發的「地理想像」 ,讓近代中國的思想及觀念世界,得到了無限寬廣的變化空間。
然而,在1895年以前的歲月裡,那些可以具體表現人們的「地理想像」的物質基礎,基本上還是局限在傳統的範疇裡,王錫祺(1855-1913)纂輯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可稱集其大成 ,但他們仍屬書本形式,即為一例 。相形之下,從1895年至1920年初前後大約25年的時間,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在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領域方面,也展現了突破性的巨變,報刊雜誌做為「制度性傳播媒介」的表現之一,不僅報導國內外的新聞,並具介紹新思想及刺激政治社會意識的作用,影響深遠 。在這個「轉型時代」,大量出現的報刊雜誌則正是生產與表現「地理想像」的最主要載體,不但確證與轉化中國既有的地理知識,更將中國與世界聯結起來,從而提供源源不絕的認知想像動力。「天涯若比鄰」,足可震驚一時的大事,迅即為人們共知同曉,也就是說,在現代新聞傳播的過程裡,總會出現「把國外的事務國內化」(domesticating the foreign)的現象。當然,在這個「國內化」的過程之中,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國內文化社會意識型態的編碼,以自己的觀念和語彙來解讀、認識形形色色的外國新聞 ;同樣的,人們透過這些「制度性傳播媒介」所表達的「地理想像」,往往形成真實和想像雜揉並陳的「第三空間」 。總言之,在中國近代「轉型時代」呈現的「地理想像」,實是五彩斑斕,誘發的歷史結果更是繁複多樣。
二、
在中國近代的「轉型時代」裡,「制度性傳播媒介」做為生產、表現「地理想像」的最主要載體 ,也有巨大的變化。特別是資訊生產流通的廣度與速度,較諸先前大幅提升,故任何重大事件往往迅速引發多樣的迴響。
例如,1898年春天的唐才常(1867-1900),正在長沙肩負編輯《湘報》的工作,那也正是大清帝國講求變法推動「新政」的熾熱時分。唐才常始終筆耕不輟,宣講世界大勢,為改革變法維新的時代風潮張目。只是,僻處在長沙的唐才常,已然可以多方尋書覓報,既擴張自己的「思想資源」,也強化了自己立論暢說的說服力 ,像他旁徵博引,聲言當時「湖南新政」的局面竟然廣受日本方面的注意,而日本政教社創辦的《日本人》裡的言論 ,也成為他鼓動湖南同鄉的依據:
才常又見日人新出一報,名其端曰《日本人》(以日本人三字名報,甚奇),所言多中國事。其臚中國名大臣,則首督部張公、撫部陳公,稱陳公振湘政,尤津津不一二談,又從而幟之曰湖南黨。自餘則豔稱南海康工部門下諸君為獅子吼。於是湖南之名重五洲,泰西泰東則莫不引領望之,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氣,而可俠可仁者惟湖南。唐才常喟然而嘆曰:微日本言,吾幾忘吾湘人之大有為至於如此,吾幾忘吾湘人之受撫部賜與一時捄世君子恢張能力以存種教之功至於如此!
回到歷史原來的場景,可能正是政教社成員之一的佐藤宏以《時務報》經理汪康年(1860-1911)為仲介,將《日本人》寄到《湘報》編輯部 ,遂讓唐才常有機會讀到上面這段文字。然而,政教社以《日本人》為觸媒,和大清帝國治下投身於報刊事業的士人結交,並不是日本報刊界偶一為之的罕見個例。當時比《湘報》發行量更大,影響更為廣泛的《時務報》,更是幅輳所集。《時務報》館經理汪康年與日本報刊界聯絡,顯得興致昂然。汪康年曾將《時務報》的縮印本寄給《大阪朝日新聞》,請其代為推廣,《大阪朝日新聞》也刊出介紹《時務報》的文稿,雙方儼然有意合作 ;在近代日中關係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東亞同文會」,參與其創建工作的白岩龍平(1870-1942),既寄奉《日本人》給汪康年,也推動《中外時論》和《時務報》的交換工作,並在日本代售《時務報》 。汪康年與日本往來密切,以致友人如山本憲(1852-1928),為了報答獲贈《時務報》的情誼,甚至於主動投寄他閱讀《朝日新聞》的「摘譯」文稿 ;當「東亞同文會」的機關報之一《亞東時報》在上海創刊(1898年6月25日),汪康年本人則為之撰〈《亞東時報》敘〉 ,表達支持之意;彼時方甫辭卸《湘報》編輯工作,離開長沙的唐才常,也參與了《亞東時報》的創辦工作,「為報務牽纏,幾無暇晷」 。至於就《時務報》而言,它刊登了各式各樣譯稿,都以外國報刊為「眼睛」來觀照世界,是人們理解認知世局變異的憑藉 ,它仰仗之訊息來源,更是繁複多樣,如《時務報》刊出58篇「路透電音」(即今日所謂「路透社[Reuters Telegram Company]新聞」) ,做為大英帝國最關鍵的資訊掮客(the information broker)的路透社 ,在1889年時便開始提供關於「中國與印度的特別服務」 ,《時務報》選譯其消息,良有以也 。然而,就《時務報》刊佈的1706篇譯稿來說,多達682篇來自日語報刊(比例達39.98%),舉凡日本當時重要的報刊,如《時事新報》、《東京日日新聞》、《國民新聞》、《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日本新報》、《讀賣新聞》、《東邦協會會報》、《太陽雜誌》、《國家學會雜誌》、《東京經濟雜誌》、《地球雜誌》等,都是《時務報》譯稿的取材對象。列名為《時務報》「東文繙譯」的日本人古城貞吉(1866-1949)提供的譯稿 ,更多達571篇,居《時務報》諸譯者之首。由此可見,日文報刊實是《時務報》譯稿的最重要來源。
如果放寬觀察視野,近現代中國報刊從日本取材者,報刊業者與日本有密切關係者,實不知凡幾。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報界擁有獨特地位的《大公報》,自1902年6月17日創刊初始,也屢屢利用日本報刊的資料,提供關於世界大勢的新聞資訊。以1902年7月16日《大公報》的「譯件」部分為例,刊載14則新聞,來自日本報刊的資訊即達8則,分別取材於日本的《大阪朝日新聞》(2則)、《國民新聞》(3則)、《萬朝報》(3則);1902年9月3日《大公報》的「譯件」,刊載13則新聞,7則取自日本的《東京日日新聞》。20世紀中國存在時間最長久的大型綜合雜誌《東方雜誌》,是另一例證。創刊未幾的《東方雜誌》,即從日本《國民新聞》、《東方協會會報》等報刊取材 ;下逮1910年代,亦復如是。僅以1919年7月15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第16卷第7號而言,便刊布多篇取材自日本的譯稿:
彼時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高潮時分,做為當時最具代表刊物的《新青年》,引介「新思潮」,即屢屢泉源於日本的報刊。如李大釗(1889- 1927)的〈戰後之婦人問題〉(《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15日〕),基本上便是山川菊榮(1890-1980)的〈一九一八年と世界の婦人〉(原刊日本《中外》1919年2月號)之翻譯 。《新青年》也登有直接譯自日本報刊的文稿,例如日本一代「漢學」名家桑原隲藏(1871-1931)的〈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譯稿問世後 ,胡適(1891-1962)讀之,乃大生感懷,對桑原主張「採用科學的方法」研治「中國學」,頗有同感,對桑原聲言「中國籍未經『整理』,不適於用」,也大發感懷 ;日後胡適倡言「整理國故」,嘗倡說要「下一番真實的工夫」,讓「國故」成為「有系統的」學問 ,其思緒所及,則是一脈相承。顯然,在胡適的思想世界裡,關於「整理國故」的主張與論說,日本方面的影響,自是一股潛流 。
即使是學生輩創辦的刊物如《新潮》,刊布之文稿,亦有取材於日本報刊者,如譚鳴謙(即譚平山,1886-1956)即從日本《太陽雜誌》取材,譯出〈勞働問題之解決〉一文 。同一時期正努力圖謀革命事業之再起的國民黨人,也重行步上接觸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潮的衢道 ,來自日本的書籍報刊,則猶如指南針一般,如戴季陶(1891-1949)主編的《星期評論》刊載這個主題的文章,參照《新社會》、《批評》、《社會主義研究》、《改造》等日語雜誌新聞而寫成者,更是繁多難數 。
此外,就資訊流通的速度而言,新聞消息的傳遞速度,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實是息息相關。以大英帝國為例,1850年代從不列顛本島到澳洲的新聞傳播,要三個月之久;即使後來到了1860年代使用蒸汽輪船了,兩地之間,仍需45天 。不過,在1850年時,英、法之間首先搭起了海底電纜,開創了讓新聞在世界快速傳播的可能空間,此後十年,更建立了海底電纜的環球體系。就大英帝國而言,這項工程大大改變了帝國的核心與邊陲之間的空間關係,各式各樣的資訊,可以在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裡散播開來,讓人們可以想像自己就是某個國族共同體(national community)的成員,維繫了帝國認同。即時的新聞,讓那些即便是出生成長生活於帝國領地的人,也會覺得自己同各種帝國事務與政治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東亞地區的情況方面,日本的電信事業既提供了經濟活動裡迅速傳達情報的效果 ,也讓日本新聞媒體可以廣為利用 ,甚至於在1877年「西南戰爭」的新聞報導戰裡,電信更是大起作用 。在中國的相關場景方面,電報對晚清政府體制及政治局勢已深有影響 ,如1910年湖南長沙「搶米暴動」的訊息亦賴電信傳達,讓清廷得以迅速發動鎮壓 ; 1911年武昌事起後,革命黨人也利用電報傳遞訊息,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潛在動力之一 。
凡此可見,報刊雜誌等傳播媒介在中國近代的「轉型時代」裡,固然是生產、表現「地理想像」的最主要載體;仔細分疏起來,資訊生產流通的廣度與速度,愈形提昇,特別是日本以其地利之便,則好似「看不見的手」,提供了相當的動力來源 。因此,如果能夠注意報刊雜誌上的各式文獻的資訊來源、取材依據,也重視資訊生產流通過程的物質條件與基礎,應可深化我們對「地理想像」在這個「轉型時代」之多重樣態的認識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