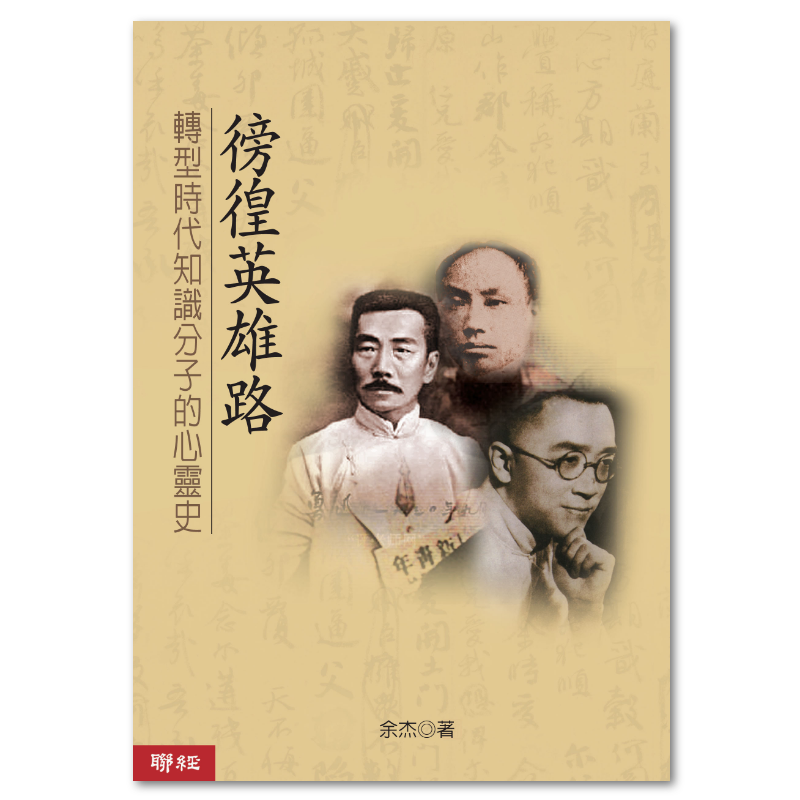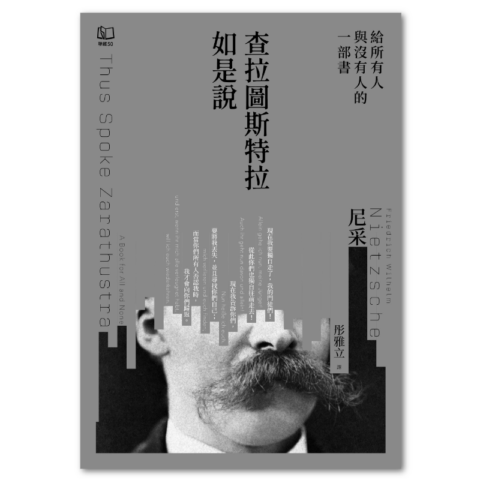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出版日期:2009-02-25
作者:余杰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20
開數:25開西式橫排
EAN:9789570833836
尚有庫存
本書是作者近十年來所寫的關於近現代文史方面論文的合集。作者關注的重點是近代中國思想、學術和文學的轉型,尤其致力於探討從戊戌變法至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的文學、學術和思想的變遷,以及知識份子的心靈史。作者認為,「戊戌變法 」這一代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和「五四運動」這一代知識分子——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人,均處於文化基本價值之轉型期,他們在創造性地汲取傳統資源和開放地面對西方文化之後,以生機勃勃的思想文化學術建設及政治活動、社會參與,對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發揮了重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研究這兩代知識份子的寫作風格、思想傾向、學術脈絡及生命歷程,對於百年之後的當代知識界來說,極具不可忽視的啟示意義。
這本論文集之研究對象,集中在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這一革命性的時間階段,亦有上溯至清代中期及延伸到當代的部分內容,因為歷史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在這本論文集中,既有對單個人物、單部作品或特定報刊「解剖麻雀式」的個案研究,也有在更為寬廣的時空視野中的古今、中西的比較研究;既有若干相對純粹的對文學史本身命題的深入討論,也有諸多跨越文學研究領域而具有新聞史、思想史意義的獨特思考。「從戊戌到五四 」是一段迫切需要重估的傳統,也逐漸為當今學人所重視。這本論文集較為充分地展現了作者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才華和潛力,同時也為對相關問題有特殊興趣的讀者提供了充滿刺激性的思想體驗。
作者:余杰
余杰,1973年10月生於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13歲開始嘗試文學創作,199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在北大求學期間,創作了近兩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和思想隨筆。1998年,部分作品結集為《火與冰》出版,被視為九○年代以來大陸知識分子批評立場回歸的標誌。
近年來,寫作的主題主要集中於近代思想史和學術史、基督信仰與文化使命、知識分子的精神變遷、現行教育制度的弊端、美國的憲政制度、俄羅斯的文學傳統以及中日關係等方面。
1998年,處女作《火與冰》被席殊讀書俱樂部評為「十大好書」(文學類)之一;2000年,評論《為自由而戰》獲《亞洲週刊》(英文版)「年度最尖銳評論獎」;2002年,獲紐約萬人傑基金會之「萬人傑文化新聞獎」;2003年,入選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問者計畫」;2004年,入選法國外交部訪問學者;2006年,長篇小說《香草山》獲香港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基金會之「年度文藝獎」;2008年,入選德國外交部訪問學者。先後赴歐美及港臺數十所大學訪問和演講。
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張灝序)
人文知識分子的學術思考(夏曉虹序)
上卷 分水嶺前的思索
盜火者與殉難者——論譚嗣同思想體系及生命實踐中的基督教因素
(一)西書、傳教士與教案
(二)耶、孔、佛三教同一說
(三)向死而生的烈士精神
「秦制」:中國歷史最大的秘密——論譚嗣同對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批判
(一)政治傳統:「秦制」的核心是君權之神聖化
(二)文化傳統:「秦制」的學術淵源是「儒表法裏 」
(三)中國歷史的二元結構:「秦始皇」與「孟薑女」的對立
「拚卻名聲,以顧大局」——從曾紀澤與慈禧太后的對話看晚清改革開放與道德倫理之衝突
(一)最高統治者的西學知識
(二)士大夫參與外交事務所面臨的道德壓力
(三)外語教育的滯後與外交人才的匱乏
「清流」不清——從《孽海花》看晚清之「清流政治」和「清流文化」
從士大夫到當代知識分子
(一)「知識分子」的概念和緣起
(二)中國的士大夫傳統
(三)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產生與發展
中卷 文學內部的奧秘
最是文人不自由——論章學誠的「業餘」文章
(一)「撰著于車塵馬足之間」——章學誠之生平
(二)「儒林內史」——章學誠傳記中的清代士人群像
(三)「毛」與「皮」之間的尷尬——從章學誠給畢沅的兩封信看章氏對自由的追求
棋局已殘,吾人將老——論劉鶚之《老殘遊記》
(一)政治·寓言·讖緯
(二)史傳·酷吏·清官
(三)遊記·散文·小說
(四)舊情趣與新思維
何處蒼波問曼殊——略論蘇曼殊小說《碎簪記》中尷尬的敍述者
狂飆中的拜倫之歌——以梁啟超、蘇曼殊、魯迅為中心探討清末民初文人的「拜倫觀」
(一)梁啟超:「民族」的個人
(二)蘇曼殊:「浪漫」的個人
(三)魯迅:「現代」的個人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識——魯迅與加繆之比較研究
(一)肉體與精神的疼痛
(二)被隔離的「局外人」與回不去的「故鄉」
(三)「肩住閘門」與「推石頭上山」
下卷 《知新報》研究
提要
第一章 晚清報刊熱中的《知新報》
第一節 晚清的報刊熱與《知新報》的創辦
第二節 《知新報》的命名、發行與報頭變化
第三節 《知新報》的報刊意識
第四節 《知新報》的影響
第二章 《知新報》的核心人物
第一節 《知新報》的主要作者和譯者
第二節 《知新報》與康有為
第三節 《知新報》與梁啟超
第三章 新舊之交的詩文
第一節 論說
第二節 詩歌
結論
跋:未完成的轉型
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
張灝序
去年夏天,我有幸讀到餘傑的近著《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這是一本討論近現代思想與文化發展的論文集,裏面穿插著作者對現代文學史與現代報刊初建的研究,內容極為豐富。令我特別有興趣的是:作者與我在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上有著一些共同的問題與視野。這使我在讀這本書時,不但常常產生共鳴,同時也給我帶來一份空谷足音的驚喜。
這本書使我產生思想共鳴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是,餘傑在書中強調:近現代思想文化的劇變主要是發軔於由戊戌到五四這一段時期。這也是我近些年來的一個基本看法。如今讀了餘傑這部書,更增強我對這看法的信心。我相信說明一下這個看法的思想背景,更會幫助讀者體會此書的價值與意義。
大致而言,強調由戊戌到五四這段時期在近現代思想文化轉型中的關鍵性這個觀點,是針對時下流行的兩種看法而提出的。一個是“五四本位”的看法。長久以來,在國內和海外,學者常常認為近現代思想文化的劇變是由五四時代開始。但近些年來的學術研究使我們越來越質疑這種“五四本位”的看法。首先,新文化運動是由近現代的雙重危機激發起來的。所謂“雙重危機”,是指空前的政治次序危機與文化思想危機。認識這“雙重危機”的來由與性格,是瞭解五四的一個必要條件。但要滿足這必要條件,不能只看五四這個時代,必需上溯至由一八九五開端的戊戌時代。因為這“雙重危機”是在由一八九五至五四時代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出現和定型的。其次,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幾個主題思想,如民主、自由、科學、極端反傳統主義以及政治激化與白話文學,都經過長期的醞釀,都必需在綜覽一八九五以後三十年的歷史劇變的前提下,才能對這些五四主題思想的發展作深入的認識。
總之,“五四本位”的看法可議之處甚多,此處無法深論,僅就上面提出的兩點而言,即可看出,近現代的思想文化轉型,並非孤峰突起於五四時代,而是突破於由甲午到五四長期積累的思想演化。
除了“五四本位”的觀點之外,近年來尚有一個很普遍的趨勢,把近代思想轉型的時間往前推,推到十六、七世紀,也就是晚明清初的時代。學界持此看法的人甚多。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就是其中鼓吹最力的人。
就思想文化發展而言,明末清初之重要性,幾乎是今日學界之共識。但這些重要的發展是否可定位為轉型的變化?我認為這問題端賴如何認識思想轉型,需要在此稍作厘清。在我看來,思想轉型必需有兩面:質的一面與量的一面。也即不但思想內容要有轉型的變化,同時這變化必需能夠在社會上大規模地、持久地擴散出去。
什麼是思想內容的轉型變化?大致說來,這是指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基本價值與知識的轉變。晚明清初有沒有這種轉型的變化?那就要看看當時中國文化傳統的主流——儒家思想的發展情形。大致而言,儒家思想傳統發展到明清時代,它的核心結構是由一組特定的基本價值與宇宙觀的結合。更具體的說,就是以儒家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價值觀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的結合。同時,儒家這套核心思想經過唐宋以來長時期的擴散,在明清時代業已滲透入儒家以外的兩個宗教傳承——佛教與道教。換言之,這套核心思想多少已經變成中國文化傳統的三個主要傳承所共認的基本觀念。現在就要問:在十六、七世紀的明清之際,這套思想是否已有解體的趨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需看明清之際的新思想發展對正統儒學有什麼樣的衝擊?首先是西方的衝擊。由耶穌會帶進來的基督教義與科技,在當時曾引起一些士大夫的注意。因此,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但耶穌會教士在傳播基督教與西學的時候,大致採取一種緩和妥協的態度,見之於他們提出的“天儒同理”的主張,而把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佛教,遂有“補儒易佛”的口號。因此,大約而言,西學的傳入對當時思想界與學術界注入一些新的成分,但震盪不大,更談不上對儒學的核心思想產生突破。
更重要的是,由晚明到清初,儒家傳統內部變化所產生的激蕩。此處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王陽明學派所引發的一些激進思想,反映于所謂的左派王學與泰州學派的出現。他們認為儒家聖人之學的重點在於“心即理”與“致良知”這些觀念,也即強調個人內在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因而時有產生激進的批判意識的趨勢。這一發展在當時又與新興的唯氣論匯合。後者攻擊儒家主流的理氣二元論,聯帶針砭程朱正統學派的理欲二元對立的觀點,從而認可情欲與私利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因此,對儒學主流的禁欲主義與權威主義提出質疑與批判,對當時的文化與思想產生了相當大的的影響。不可忽略的是,明清之際的激進思潮在儒學內部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動與圍堵,以致在十七世紀末葉以後,這些激流多半已不見餘響了。
此外,針對宋明理學主流的修身學以及隨之而來的內省靜觀的趨勢,明清之際的思想界也出現了一些反彈的變化,那就是強調儒家思想中的政治社會意識,引發經世觀念在儒學中復蘇。這種趨勢大約有兩面:一面是士大夫為了進行政治社會活動,而結社組黨,造成中國傳統文化中別開生面的一頁。同時,儒學傳統中也出現一些對政治權力安排的深刻反思。如顧亭林透過郡縣與封建制度的討論而思考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權力的問題;甚且如黃宗羲,追根到底,以公私對比的道德觀以及強調君師二元權威分立這些觀點去質疑與挑戰傳統皇權體制的思想基礎。
正如我前面討論的其他幾個明末清初新的文化思想趨向,經世思想的批判意識發展下去,有突破儒家主流的核心觀念的潛勢。但這方面的趨向,與其他幾個趨向一樣,都未能充分發展其潛勢。總之,根據上述分析,我們不能誇大明清之際的新思潮的影響。一則因為,這些新趨向所產生的思想衝擊都未能達到一種深度與強度,可以在基礎上撼動儒家主流的核心思想。其次,就這些新思潮影響的廣度而言,它們多局限於當時某些學術流派或某些地域的學者士大夫,未能真正擴散出去造成廣泛的社會文化震撼。再其次,就其影響的時間性而言,這些新思潮都只能在明清之際的兩個世紀間發生一些或久或暫的沖激;也就是說,它們在十七世紀末葉以後幾乎都已變成強弩之末,而逐漸式微消退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明清之際的思想變化,雖然重要,但並未能突破傳統而產生文化轉型。這轉型要等到十九世紀西方文化第二次衝擊中國時才發生。此處我要強調的是:這第二次西方衝擊開始於十九世紀初葉,鴉片戰爭前後,但開始以後劇變並未立刻展開,而是要再等半個世紀,到甲午戰爭以後的二、三十年,傳統文化才真正開始解體,文化轉型才真正湧現。理由大致可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在甲午戰爭以前的五十年,西學的散佈限於政府少數的辦理洋務的官員以及沿海沿江幾個大城市裏的“邊緣人”,如商賈買辦及教會人士等,並未深入中國社會主流——士紳階級的思想世界。同樣重要的是:當時西學的流傳,不但廣度很不夠,而且在少數受西學影響的朝野人士的圈子裏,其影響的深度也很有限。他們大致認為西學只有工具性與技術性的價值,至於基本政治社會體制與價值規範,則仍以傳統儒家核心思想為主導。這就是當時以“中體西用”觀念為標誌的主流態度。
一八九五年以後,變化情形大為改觀,從餘傑書中的論文,讀者不難看到:思想文化的變化,無論就廣度與深度而言,都有空前的突破,同時也多方面開啟了未來的新機,為後來的五四奠基鋪路。放在這樣一思想發展的大脈絡中去看,他強調戊戌到五四是中國近現代文化轉型的關鍵時期自是不爭之論。
讀這本書另一個使我感到共鳴的地方,是餘傑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討論,見之於他書中的長文——《從士大夫到知識分子》。其實縱覽全書,我們不難發現,書中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從思想史、文學史、報業史等各種不同的角度,直接間接地去認識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說知識分子是此書的研究主題也不為過。
關於這個主題,我覺得此書有三個特色,值得在此指出。首先,作者把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放在一個文化與歷史的比較視野裏去看。例如,一方面他以西方知識分子的歷史發展為借鑒,看到西方大學制度在中世紀末與近世初期出現,是西方近代知識階層的興起的一個重要支柱。同時,他也以中國傳統士大夫作為瞭解近代知識分子的背景,看到傳統科舉制度與士大夫階層之間的密切關係,透過一番中西古今的對照,他才能指出一八九五年以後科舉制度的式微與大學制度的建立是近代知識分子問世的一個重要條件。我並不完全同意他作文化與歷史比較所涉及的一些具體論述,但他書中所展現的比較視野,毫無疑問替知識分子的研究提示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這本書中最長的一篇論文,幾乎占全書五分之二的篇幅,是作者對中國近代早期報紙《知新報》所作的研究。這篇長文使我們看到近代報刊的興起與新知識分子的出現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同時,也展現了余傑研究知識分子的另一特色。
此處必需指出的是:中國在戊戌時代以前,報刊已經出現,但數量極為有限,而且多半是“邊緣人”,如商人與傳教士辦的。前者主要傳佈商業市場的資訊,後者主要報導教會的訊息。少數幾家綜合性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等,因為主辦人不是來自社會主流的士紳階層,影響未能廣為擴散。但是,一八九五以後,來自士紳階層的知識分子開始創辦一些新型報刊,針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時事演變發言,立刻使報紙銷路與影響遽增。《知新報》就是這種新型報刊的一個先鋒,在當時的聲勢與影響,如餘傑指出,僅次於《時務報》。
關於這種新型報紙,中外學界歷年來出版了不少綜合研究,但是對於個別重要報刊的研究,像餘傑對《知新報》作的那樣精細深入的個案分析,則甚少見。
透過餘傑的分析,我們看到了《知新報》以及它所代表的新型報紙替中國報刊帶來的一些空前的變化。例如他指出《知新報》反映了一種嶄新的“報刊意識”,認為報紙負有一種新的時代使命:開民智以促進國家富強;向政府建言提供新的觀念,並從事監督;同時也表達民意,開始顯露主權在民的意識。
更重要的是:這種新型報刊對於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社會所發生的長遠影響,餘傑是從三個方面去剖示這些影響的。首先,他認為新型報紙是散播外來的新知識的媒體。其次,他看到在《知新報》裏出現了一種他稱之為“新舊交替”的文體與詩體。它們可以說是由傳統舊文學到現代新文學的過渡。再者,他指出新型報刊與近代社會的另一個重要的新發展有著密切關係:那就是戊戌時代開始在傳統以官僚體制與家族為主軸的社會之外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空間,可以供給一般受教育的人從事廣泛討論公共事務與政治社會問題以及其他社會文化活動。這種“公共空間”當然也是近代知識分子主要發揮影響的場所。總之,我認為餘傑這本書透露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一八九五年以後登上歷史舞臺的近代知識分子與傳統士大夫型的知識分子有著一個很大的不同。後者在社會上的核心地位在於他們與以皇權與官僚體制為基礎的現實權力中心有著緊密的聯繫。在一八九五年以後,隨著科舉制度以及其他傳統的聯繫機制逐漸式微與消解,知識分子與現實權力中心自然發生疏離、隔閡,甚至矛盾、抵觸,但這並不意謂知識分子失去他們在現代社會的核心地位。因為隨著舊的制度式微與瓦解,社會組織上出現一些新生事物,如餘傑指出的新型報刊與公私學校以及各種類型的社團與政黨組織。現代知識分子憑藉這些新的文化媒體與社會組織,一方面可以掌控輿論,左右時代思潮;另一方面也可以發動大規模的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變成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主要動力,其地位與影響較之傳統士大夫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余傑研究知識分子,提出一些他治史的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這是他這方面研究的另一個特色。首先是他以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的觀點。余傑是一位知識分子,應該說是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後者,他對時代有強烈的關懷與責任感。他要針對時代的問題說話,他是以這些問題為基點去回顧與檢討近代知識分子這個傳統。因此,他很明白地說,他的歷史研究不是發自歷史的好奇心,關在象牙塔里做的,而是發自他所謂的“現實關懷”,希望能與近代知識分子這個傳統的“先哲”對話,從他們的思想吸取教訓,從而認識知識分子對當今的時代問題,應採取的立場,以及應該走的道路。是從這樣一個觀點,他響應了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名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
借用時下學界的名詞,這種觀點可稱之為“效應史觀”。這種史觀最大的長處是認識到史學研究不可能做到十九世紀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所揭櫫的主流史學目標——全面客觀地去瞭解歷史真相。主觀意識不可避免地進入歷史研究,因為歷史瞭解受史家的問題意識支配,而問題意識則往往來自對時代環境的回應與感受,把這種主觀的時代意識與問題意識提出來加以認清,加以控制與提煉,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去作進一步的史料搜集與分析工作。我多年來很受這種史觀的影響。現在很高興發現在這方面我和餘傑也有共識。
盜火者與殉難者
——論譚嗣同思想體系及生命實踐中的基督教因素
晚清一代士人,“所值之時世,一內訌外釁、更迭無已之時世也;所處之環境,一憔悴悲傷、永無休止之環境也”(汪詒年語)。此刻傳統政治秩序之基礎已開始動搖,支撐於其後的儒家宇宙觀和價值觀,如陰陽、天地、五行、四時以及綱常名教等也受到了震撼。一個嶄新的西方世界挾船堅炮利之勢一擁而入,而到中國傳播西學的先行者卻是西方各國之傳教士。這些傳教士所宣揚的西方政治、文化乃至背後的基督教信仰,已非“中體西用”之說所能界分。此次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其背景與此前三次傳教的高潮迥異,它直接觸動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安身立命”之根基。此種環境下,思想者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之中,難以保持心靈的平靜,也難以取得某種思想的“客觀性”。因此,戊戌維新一代士人,其治學著文、為人處世,無不帶有某種“神經質”的性格。具體到譚嗣同身上,在其文字中更可看出烈火焚身般的苦痛,正如張灝所論:“譚嗣同在感到政治秩序瓦解的同時也感到文化價值和基本宇宙觀所造成的‘取向秩序’的解紐……他的思想在許多方面都是反映他在面臨這雙重危機時所作的思想掙扎。”
基督教因素由此逐漸在維新派人士身上浮現出來。在思想相對比較開明的維新派士大夫當中,有少部分人完全同意基督教是西方各國“變法富強之本”,認為中國要強大必須改宗基督教 ;也有少部分人對基督教採取排斥的態度,認為在學習西方制度文明的同時,必須警惕基督教傳播,並保有中國自身的儒教傳統。 介於此兩種較為極端的看法之間,許多士人對基督教採取的是一種“近而不進”的態度。也就是說,他們願意接觸、接近甚至贊同基督教的某些教義及思想,但決不願意受洗成為基督徒。維新派的幾位代表人物,大抵都是這樣的立場,如王樹槐所論:“若就維新派份子對基督教的態度而言,則傳教士的目的,有其成功的地方,亦有其失敗的地方。成功的地方是維新份子態度開明,無反基督教的言論,有平等對待教士的意念;失敗的地方是維新份子,並不相信基督教為西學、西政的根本所在。他們承認宗教可以救世救國,但他們所要發揚的是孔教,而非基督教。”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一代的維新家中沒有出現一個教徒,此一現象值得深入探究。
往上追溯,晚明時期基督教第三度進入中土,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馮應京、葉向高、王征等高級文官和傑出學者均受洗歸主。往下觀察,二十世紀初孫中山一代之革命黨人大半都是基督徒。為什麼會有如此鮮明的對比呢?顧衛民認為:“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出身於科甲的士大夫,他們的改革主張雖與西方傳教士有許多相似之處,然而,他們心靈深處積蘊悠久的儒學意識和民族情結,使他們在信仰上與西方基督教保持著很大的距離,其中橫隔著幾千年來的夷夏之界的民族心理防線。” 與之相比,明代基督教進入中土並未動搖儒學之根基,因此徐光啟等人選擇成為基督徒,並沒有遭受“文化撕裂”之痛苦。而比康梁晚一代的孫中山及其革命同志,許多人自小就生長在海外的基督教家庭,他們接受基督教信仰本來就有良好的外部環境。而夾在中間的康梁這一代人,大都受儒學薰陶極深,他們在遇到新學(包括基督教信仰)巨大衝擊的時候,有選擇地接受其政學部分,而將基督教信仰作為外在於個體生命的文化參照系。他們不甘於放棄傳統之文化及道德倫理,尚存保全儒學、復興儒教之理想,堪稱最後一代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士大夫。
儘管許多晚清士人意識到了“神州多難,桃源在西方”(宋恕語),但此時西學之盛並未同步帶來基督教信仰的拓展。 對於此種奇特的落差,美國學者列文森分析說:“當近代悄無聲息地開始之後,基督教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雖然重要,但是替代性的。中國終於需要了它,但不是作為一種信仰的物件,而是作為一種批評的物件而需要它的。近代傳教士對於中國的西方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這只是世俗上的或次一級的成功,他們那更為重要的宗教事業卻失敗了,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在衰落的傳統真正死亡之前是如此。因為人們不可能冷靜地改變他們的思想信仰。” 戊戌變法前後,康梁甚少論及基督教。與之相比,譚嗣同是當時最為關注基督教的思想家。譚氏未經科舉,官學對其學術視野之限制甚少,故其對基督教的涉獵最為廣泛與深入。梁啟超在論及譚嗣同的學術淵源時指出:“少年曾為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此後,譚嗣同受康有為的啟發轉而研讀孔學,進而以《華嚴》為門徑研讀佛學。 儘管譚氏不是基督徒,甚至算不上“文化基督徒”,但基督教因素在其思想體系和生命實踐中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探討這一因素,是一個被長期忽視的進入清末時代氛圍以及那個時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視角。
(一)西書、傳教士與教案
在維新一代名流中,最為廣泛地閱讀基督教書籍和結交西方傳教士的人無疑是譚嗣同。在譚氏的著作、詩文和書信中,多次提及對西書的研讀以及同傳教士的往來。
譚嗣同大約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接觸《新約全書》。他所閱讀的譯本可能是大英聖公會一八五二年出版的“委辦譯本”,為當時質量最高之譯本,由於知名學者王韜參與翻譯和潤色,使之具有古典漢語之優雅。 譚嗣同在其詩歌中嘗試使用新名詞,其中便有來自《新約》的辭彙與概念。梁啟超稱讚譚詩“獨辟新世界而淵含古聲”、“沈鬱哀豔”、“遣情之中,字字皆學道得語” ,並不過譽。在譚氏贈梁的四首詩中,有“三言不識乃雞鳴,莫共龍蛙爭寸土”之句,梁氏分析說:“蓋非當時同學者,斷無從索解;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 當時另外一位詩人夏穗卿也有類似的詩句,梁啟超進一步闡發說:“當時吾輩方沉醉於宗教,視數教主非我輩同類者,崇拜迷信之極,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所謂經典語者,蓋指佛、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面,絡繹筆端焉。譚、夏皆用‘龍蛙’語,蓋時共讀約翰《默示錄》,錄中語荒誕曼衍。”
如果說閱讀《新約全書》還只是譚嗣同的一種紙上的“文化冒險”,那麼與傳教士的交往則為其打開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門。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介入戊戌變法最深,與譚嗣同也有較多往來。戊戌政變後,譚、梁約見李提摩太,希望他通過英國公使營救被幽禁的光緒皇帝。李氏亦表示願意幫助譚脫險。譚嗣同還徵引過李氏的文章:“英教士李提摩太者,著《中國失地失人失財之論》。” 李氏此文,原名為《擬廣學以廣利源議》,發表于《萬國公報》。譚氏服膺于李提摩太關於中國失地、失人、失財之論。受到此文之刺激,他“當饋而忘食,既寢而復興,繞室彷徨,未之所出。既憂性分中之民物,複念災患來於切膚。” 由此大聲疾呼“籌變法之費”、“利變法之用”、“嚴變法之衛”、“求變法之才”,這些變法建議明顯是受李氏之啟發。李提摩太對中國現狀的尖銳批評,被譚嗣同迅速轉化為呼籲變法的思想資源。
譚嗣同不僅與多名傳教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更把傳教士當作獲取新知的視窗。一八九三年,譚氏應傅蘭雅之邀,到上海格致書院訪問。此次訪問為譚氏學術思想變異之轉捩點。譚氏記載說:“于傅蘭雅座見萬年前之殭石,有植物、動物痕跡於其中,大要與今異。天地以日新,生物無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奈何自以為有得,而不思猛進乎?由是訪學之念益急。” 此次會面,譚嗣同向傅蘭雅詢問了許多關於科學技術方面的問題,兩人交談甚歡。不久,譚氏還訪問了江南製造局等洋務企業,並購買大量由江南製造局翻譯的西書帶回湖南。傳教士及西書,確實給了僻居內地的譚嗣同以“知識系統”意義上的震動。
後來,譚氏“重經上海,訪傅蘭雅,欲與講明此理,適值其回國,惟獲其所譯《治心免病法》一卷,讀之不覺奇喜。” 譚氏認為這本書探究“本原”、具有“真義”,解開了自己多年來思想上的疑惑:“遍訪天主、耶穌之教士與教書,伏讀明析,終無所得,益滋疑惑。殆後得《治心免病法》一書,始窺見其本原。今之教士與教書,悉失其真義焉。” 他還指出,此書也顯示出傅氏本人學術路向的轉變,即以“玄學”(心之本原)補救“科學”(格致)之局限,“傅蘭雅精於格致者也,近於格致亦少有微詞,以其不能直見心之本原也。”
《治心免病法》本是一本簡陋的小冊子,經譚嗣同“點石成金”,書中“乙太”的概念成為《仁學》中的核心概念。如果說戊戌時期的康有為更多著眼於政治改革層面的問題,那麼此時的譚嗣同則將改革擴展到了文化、道德和宗教上。他在《仁學》中用“乙太”這一西來的觀念取代了中國傳統哲學中“氣”的概念,並致力於建構一個獨特的哲學體系。可以說,如果沒有基督教的思想資源,譚嗣同之《仁學》則會形成一處無法彌補的缺陷。譚氏本人亦不諱言,他所標示的《仁學》之思想背景赫然列有《聖經》,並列為西學之第一:“凡為仁學者,于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于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
對於譚氏而言,西書和傳教士的價值之一在於“鏡鑒”。譚氏在書信中論及曾國藩、左宗棠、鄭觀應、郭嵩燾等名流受西學刺激走向洋務的過程,也回顧了自己思想觀念的變化:“夫閱歷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護前,不自諱過,複何難寐之有?即嗣同少時,何嘗不隨波逐流,彈詆西學,與友人爭辯,常至失歡。久之漸知怨艾,亟欲再晤其人,以狀吾過。” 可以說,沒有西學這面鏡子,像譚嗣同這樣的士大夫在思想上絕對不會如此變化,中國也必然在昏睡中滅亡。正如顧衛民所論:“戊戌維新作為一種民族精神的亟變和覺醒,除了中國人對於日益深重的外患慷慨激憤之外,更包著對本民族自身的弱點和弊病的反省與懺悔。西方傳教士種種對中國時政的批評,使得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從中窺見了自身的醜陋,具有警醒奮起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