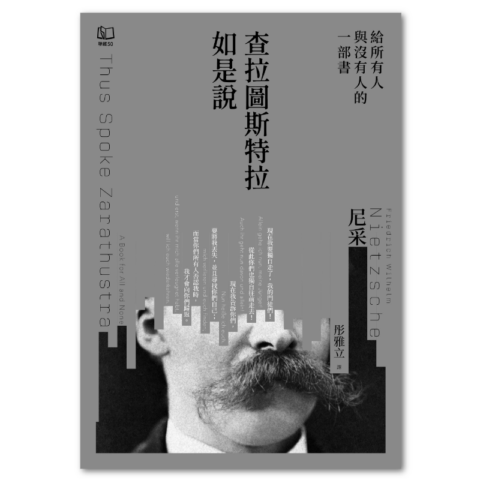儒家與現代政治(思想20)
出版日期:2012-01-16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36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9494
系列:思想
尚有庫存
本期的專輯是「儒家與現代政治」,本期專輯收錄的文章及簡介如下:
1.張灝,〈政教一元還是政教二元?:傳統儒家思想中的政教關係〉:
儒家政教關係思想的演變取決於兩個因素。其一是原始典範的觀念,其二是天道觀念的實化。這兩個思想因素維持了「政教一元」觀念的主流優勢,也使得政教二元觀念退居次位,而終於流產。
2.姚中秋,〈儒家復興與中國思想、政治之走向: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立場〉:
自由主義,假如要有一個未來,就必須在政治上成熟。而政治上成熟的最為重要的標誌,就是放棄百年來的反儒家意識型態。
3.陳昭瑛,〈徐復觀與自由主義的對話〉:
在政治上,儒家一直在各種重大政治改革運動中缺席,而所有重大的政治改革也多援引西方政治思想作為社會實踐的理論基礎。儒家不論在實踐或理論方面都是缺席的。
4.劉擎,〈儒家復興與現代政治〉:
一種型態的文化或政治的弊端,並非自然地等同於另一種型態的優勢。中國在發展中遭遇困境與危機,並不意味著轉向儒家傳統就是理所當然的拯救之道。
5.周濂,〈哪種公民 誰的宗教?:評陳明〈儒教之為公民宗教〉〉:
在一個合法性敘事發生嚴重危機的獨裁政府或者黨國體系裡,不加區分地引入公民宗教觀念,很可能遭致被政治權力徵用乃至濫用的危險。
6.成慶,〈當代大陸政治儒家的迷思〉:
今日試圖恢復儒家道統的知識分子,往往只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而對法家之「非人性化」性格不置一言,似乎在傳統政治生活中,單靠儒家就已足夠完成治理的任務,實難讓人信服。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葛兆光
╱「前近代」、「亞洲出發思考」與「作為方法的中國」:重新理解溝口雄三教授的一些歷史觀點
朱嘉明
╱哈耶克經濟思想的現實意義:21世紀以來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危機及其出路
劉世鼎、史 維
╱去政治化的台灣政治
■儒家與現代政治
張灝
╱政教一元還是政教二元?:傳統儒家思想中的政教關係
姚中秋
╱儒家復興與中國思想、政治之走向: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立場
陳昭瑛
╱徐復觀與自由主義的對話
劉 擎
╱儒家復興與現代政治
周 濂
╱哪種公民 誰的宗教?:評陳明〈儒教之為公民宗教〉
成 慶
╱當代大陸政治儒家的迷思
■思想訪談
陳宜中
╱公民儒教的進路:陳明先生訪談錄
■思想評論
高維泓
╱後全球化時代的愛爾蘭劇場
致讀者
儒家這個長遠的傳統,一直是華人世界乃至於東亞社會的重要文化資源,為個人生命提供敘事架構,從生活倫常為社會秩序提供基礎,也在政治上構成了正當性論述的依據。但從近代以來,儒家全面敗退,並且與其說是被證明為錯謬,不如說是儒家與現代生活已經互不相干:「現代」人的生活所需要的意義、秩序、以及理據,另外找到了比儒家更合適、強大、更有說服力的資源。儒家這種「不相干」,反映在它的思想創造力的枯竭:既然生活中的各項問題根本無需、無法用儒家的語言來陳述,它也就不可能面對問題而產生新的說法。如果有人大膽斷言,儒家的經典到了明末就可以全編定稿,此後的儒門思想只能圍繞著前人這些經典從事詮釋、辯解、附會的工作,今天的儒者會如何回應呢?跟(例如)基督教神學思想至今仍然強勁的創造活力相比,儒家真的無力再推陳出新嗎?
儒家傳統與現代生活的不相干,在政治領域相當明顯。但也正是在政治這個領域,今之儒者致力最勤。一方面,無論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者其他政治思考,在基本政治價值、基本制度、以及關於政治共同體的想像三方面,都無需再訴諸儒家,甚至於完全顛覆了儒家的思路。但在另一方面,在20世紀中葉,港台新儒家曾經嚴肅面對現代政治現實,力圖證明自由主義與儒家是相通的;晚近的大陸「通三統」之說,則企圖在儒家與「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建立延續。如果說這類努力尚屬於守勢,最新的「政治儒學」、「儒教」、「儒家憲政主義」等運動就更為主動,不再著意於辯護,而是直接根據儒家原則來陳述與思考政治價值、政治制度、政治共同體的性格。這些發展,值得關注。
本期《思想》以「儒家與現代政治」為專輯,呈現了這股思想新動態的部分面貌,除了邀請儒家一方的代表性人物如陳明、姚中秋先生闡述他們的觀點,也邀請了幾位對儒學政治思想有所質疑的學者提出評論。這兩方看似針鋒相對,立場上其實都接近廣義的自由主義,相互有著同情的理解,爭論起來也就更能夠直指本題。
張灝先生關於儒家歷史上政教分合關係的文章,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余英時講座」時的演講稿,與當前儒家復興運動所引起的爭論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此文對儒家政治意識的一個根本糾結提出了縝密的分析,對當前的爭議實際上是深具啟發意義的。
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出版以來,本刊前後發表過三篇評論,正反意見並陳。如今葛先生將他紀念溝口雄三、評論日本漢學傳統的演講稿交給本刊發表,其中除了追溯日本漢學的學術史,更廣泛涉及歷史意識、學術政治、以及學術發展等重大議題。值此亞洲、東亞、中國等概念受到矚目的時刻,本文特別值得參考。
在此,我們要向一群熱心、認真的朋友道歉。在10月份,《思想》與台灣哲學學會合作,以「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為題,舉辦哲學論壇,邀請了學界、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參加討論,並且準備將他們的正反論點在《思想》發表。但是由於本期篇幅有限,必須將整個專題移到下一期的《思想》,特此說明。
最後,沉痛悼念本刊作者高華先生(1954-2011)。
■思想人生
李懷宇
╱余英時:知人論世
一、未成小隱聊中隱
如果人間真有世外桃源,對我而言,夢裏桃源便是普林斯頓。
2007年秋天,當我準備美國之行時,設想的第一訪問對象是余英時先生。中秋節下午,我給余先生家發了一份傳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門外。中秋之夜,我給余先生家打了一個電話,接電話的是余師母陳淑平女士,從聲音裏可以感覺是一位大家閨秀。我大喜過望:余先生願意見我。赴美之行恍如夢境。2007年11月5日,我到美國的第二天,從紐約坐火車到普林斯頓,余師母早在車站等候。
余先生在普林斯頓的生活近乎隱居。余家是樹林裏一幢獨立的房子,屋前一個小漁池,屋後一片小竹林,後來我多次陪余先生喂魚散步,頗有「悠然見南山」之趣。大書房上掛鄭板橋的書法「小書齋」。客廳中的字畫多是余先生的師友所贈,印象中有錢穆、俞平伯、張充和的作品。胡適的字是:「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余先生「集坡公詩句放翁詞句」而請他岳父陳雪屏先生寫的對聯是:「未成小隱聊中隱,卻恐他鄉勝故鄉。」我覺得此聯頗見余先生晚年心境。
冥冥之中有緣,我在普林斯頓盤桓了多日,與余先生暢談了五天三夜。如今回想,我的訪問生涯中從未有此奇緣。
在普林斯頓的日子,我受到余師母無微不至的照顧。每天從旅館到余家都由余師母開車接送。第一天晚上,因為時差的緣故,我失眠了,天剛一亮,我匆匆吃過早餐,便到普林斯頓大學裏閒逛。雨後空氣格外清新,校園之美,令我心醉。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聯翩,愛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胡適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微笑,仿佛就在眼前。多少年來,我對普林斯頓心嚮往之,無非是因為已故二公與當代余英時。
那天早上在余師母的車子裏,閒聊得知我喜歡二公。有一天中午,余先生夫婦專門帶我到愛因斯坦常去的校園餐廳吃飯,飯後兜到愛因斯坦的故居門前,如今的屋主剛拿了諾貝爾獎。余先生沒有見過胡適,余師母的父親陳雪屏與胡適是至交,她告訴我:「我們家常常我開門。胡先生就常常會問我:你現在幾年級,家裏有什麼功課?他把我們小孩子也看成人。」後來從余先生夫婦的待人接物中,我恍然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小孩子。
別後,我時常打電話到普林斯頓,人間趣事,心中煩惱,事無巨細,余先生夫婦總聽得津津有味。有時讀了余先生的著作或是和余先生通過電話,我會冥思時空的奇妙,古人今人,天涯咫尺,竟在神遊與笑談中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隔閡,這也許便是歷史研究的魅力。
二、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
研究知識人的歷史世界,家學與師承不可不考,天賦與勤奮自然重要,胸襟與見識尤為可貴。
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但對歐洲史、美國史興趣更大,1926年至1928年赴美國考爾格大學和哈佛大學讀美國史。1929年余協中繼蔣廷黻出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時在天津出生,母親張韻清女士因為難產去世。余協中傷心欲絕,舉家離開天津。余英時童年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抗戰爆發後,余英時回到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官莊鄉。
王元化先生《一九九一年回憶錄》中說,在夏威夷開會時他談到中國的農民意識問題,引起了余英時的批評。余英時說抗戰初在農村住過,所見到的農民都是很質樸老實的,王元化則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軍軍部的親身經歷為例申辯。這段回憶錄引起了我的興趣,因此當面向余英時問起。余先生說:「佃戶跟地主的衝突到處都發生,但是那個衝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謂‘階級鬥爭’呢?個人所見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戶欺負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兒寡婦,那是沒有辦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強的退休官員,有勢力,欺負佃戶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論。王元化的這個回憶錄我看過,但我們後來也沒有拿這些問題去爭辯了。我常常說,中國這麼大一個社會,比整個歐洲還大,不可能每個地區都是一樣的。」鄉下生活使余英時對傳統文化有參與的體驗,後來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的中國調查,在他看來有隔靴搔癢的感覺,並沒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經驗,只停留於數位上。
1943年前後,桂系有一個營的軍隊駐紮在潛山官莊,營長杜進庭大概做了不少貪贓枉法、欺壓鄉間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騰。余英時才十三歲左右,並未見過杜營長,但聽鄉中長輩說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體,所以心中頗為憤怒。不知怎樣異想天開,竟寫了一個很長的狀子,向政府控訴杜營長的種種罪行。這篇狀子寫完了,余英時便留在書桌上,後來自己也忘記有這樣一回事了。無巧不成書,余英時去了一趟舒城縣,有好幾天不在家,恰好杜營長的一個勤務兵到余家詢問什麼事,被引進余英時的書房,無意中發現狀子,大驚之下便把狀子送給杜營長。據說杜營長讀後不但憤怒而且驚恐萬分,懷疑狀子不是一個小孩子寫的,必是官莊鄉紳合謀控告他,要致他於死地。杜營長抓不到余英時,便召集鄉中有地位有頭面的人,當面追究,這些鄉紳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認,都說不過是一個淘氣孩子的遊戲之作。當晚鄉紳準備了豐盛的酒席為杜營長解憂,杜大醉後失聲痛哭,說這狀子如是官莊鄉人的陰謀,反正他活不成了,一定要大開殺戒,把余英時等相關的人全部槍斃。事隔一二日後,余英時在夜晚從舒城回到官莊,先經過鄉間唯一的一條街,街上熟人見到他好像見到鬼一樣,臉上帶著一種恐懼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催余英時趕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亂跑。余英時當時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闖下大禍,使全家都吃驚受累。家人怕杜營長聞風來抓人,把余英時連夜送到一位行醫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風險。余平格平時很嚴肅,不苟言笑,當晚接待余英時,開口便說:「我因為你年紀小,一直把你當孩子。但你做了這件事,你已成人了。從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余英時回憶:「這一事件在我個人生命史上構成了一個重大的轉捩點。一夜之間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進入了成人的世界。這一轉變並非來自我自己,而是我周邊的人強加於我的。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結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譏評。我可以說是被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是不自然的。」這一「告狀」事件還有一個尾聲。時間稍久,杜營長大概已接受鄉人的解釋,也認為是一個頑皮孩子的戲筆。不過,他還要派一個受過較多教育的政治指導員來談一次。這位指導員經族人安排,在一個晚上和余英時吃酒用餐,談話中順便考考余英時的詩文知識,最後他相信「狀子」是出於余英時之手,而余英時並無真去控告杜營長的意圖。臨走時,指導員緊緊和余英時握手,表示願意成為忘年交之意。
余英時在鄉間很少正式上學,小學、中學都是分散地上過一兩個學期的學校。唯一與後來研究有關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啟蒙。1945年至1946年,余英時在桐城縣城舅舅家裏住了一年。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余英時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響,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他的二舅父張仲怡能詩,善書法,是清初張英、張廷玉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與方、姚、馬、左齊名,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來往,余英時從他們的交談中,偶爾學得一些詩文的知識。余英時至今還記得舅父在鍾馗畫像上題了一首七絕:「進士平生酒一甌,衣衫襤褸百無求。誇人最是安心處,鬚髮鬅鬙鬼見愁。」舅父的初稿首句最後三個字原作「仕不優」,以詩稿示一位詩友,那位詩友立即指出:「仕不優」當改作「酒一甌」。舅父大喜稱謝,稱他為「三字師」。「酒一甌」自然渾成,遠比「仕不優」的生硬為佳。余英時在一旁聽到這改詩經過,很受啟發,懂得詩句原來是要這樣「推敲」的。
在抗戰期間,余協中在重慶考試院做參事,父子分隔兩地九年,余英時在鄉間根本沒有碰到西方的書籍。多少年後余英時回想,父親無形中還是產生了影響:「我對西洋史有興趣是從父親那兒來的。他編著一部幾十萬字《西洋通史》,對我很有啟發。小時候看不大懂,但漸漸入門,對著作肅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對中國史有興趣,還對西洋史有興趣,看看西洋史是怎麼變化的,我用比較的觀點來看歷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關。」
抗戰勝利後,余協中受杜聿明委託到瀋陽創辦東北中正大學。1946年夏天,余英時從桐城重回安慶,然後到南京轉北平,最後定居瀋陽,期間找老師課外補習英文、數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時考進了中正大學歷史系。他回憶:「我選擇歷史為專業,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數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親的影響。我家所藏英文書籍也以西史為主,我雖不能閱讀,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讀西史的強烈願望。我課外閱讀則由梁啟超、胡適的作品開始,種下了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通史由一位青年講師講授,用的是錢穆的《國史大綱》,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錢先生的學術。因此,我在這所新辦的大學雖然僅僅讀了三個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卻大致決定了。」
此後戰局變幻。1947年12月,余英時隨父親從瀋陽飛往北平,當時機場一共有三架飛機,余協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時則在第三架。當余英時正在排隊登機的時刻,余協中忽然招手要他過去,因為第一架還有一個空位。於是余英時在最後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結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時在北平閒居,開始接觸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影響他最大的要算儲安平辦的《觀察》以及結集而成的《觀察叢書》。他回憶:「這當然是因為我的心靈深處是接受五四以來的現代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人權等等。我記得1948年夏天讀到胡適〈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刊在《獨立時論》上),非常興奮,因為胡適在文中強調爭取自由在中國有很長的光輝歷史;他指出孔子‘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說法,我也認為很有說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國既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素,經過調整之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種極端的觀點,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只有專制、不平等、壓迫等等負面的東西。」
在二十歲以前,余英時親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動時代,接受了並不完整的學校教育。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時成為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憶。2008年余英時為巫寧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憶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學〉為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