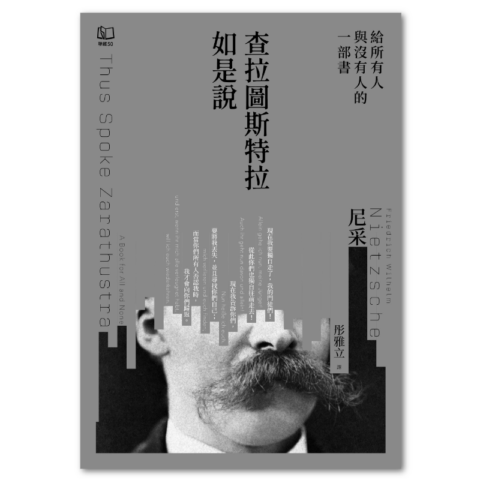必須讀《四書》?(思想21)
出版日期:2012-06-01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52
開數:25開,21×14.7cm
EAN:9789570839982
系列:思想
尚有庫存
本期的專輯是「《四書》應該必讀嗎?」,起源是民國100年10月22-23日,台灣哲學學會假台北醫學大學舉辦2011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除發表60餘篇專業論文之外,大會也特別設立了「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哲學論壇,邀請各界賢達各抒己見,並與在場學界人士切磋琢磨,共同探究其中所涉及的議題。
本期的訪談人物有高放先生和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女士;思想評論單元有談李斌的歷史主義繪畫、評劉小楓的施特勞斯轉向等;思想對話單元是對談動物倫理與道德進步。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徐 勝╱東亞人權的探索
高全喜╱論中國自由主義的政治成熟
潘婉明╱戰爭‧愛情‧生存策略:馬共女戰士的革命動機
■思想訪談
陳宜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高放先生訪談錄
葉蔭聰╱挑戰麻木和無力感:訪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
■思想對話
錢永祥、梁文道╱動物倫理與道德進步
■思想評論
李公明╱批判的歷史主義繪畫:懺悔者的歸來——寫在「生於1949:李斌畫展」前面 155
胡昌智╱《朵伊森傳》簡介
蘇光恩╱哲人的面具:評劉小楓的施特勞斯轉向
■必須讀《四書》?
台哲會論壇╱《四書》應該必讀嗎?──又一次爭議
■思想人生
陳永發╱南港憶高華
致讀者
致讀者
2006年《思想》復刊之初,曾在〈出刊說明〉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基於全球化的現實趨勢與中文的國際性格,我們想要建立一個跨越國際的中文論壇,不願意再劃地自限。南洋、港澳、東亞、北美、乃至於歐洲、大洋洲各地使用中文的知識分子,都將是我們的作者與讀者。」
如今這份刊物已經出刊二十一期,積累了眾多作者數百萬字的心血文字,也探討過台灣、大陸、香港、澳門,乃至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各地的多樣議題。然而回首清點,自問當初的心願實現了多少,答案卻令我們汗顏:努力或許並未唐捐,成果卻仍嫌貧瘠。究其根本,編者不夠努力固然是原因之一,不過紙本刊物的流通受到很大的限制、「尋找讀者」的成本太高,也是原因所在。
為了舒緩這些困難,最近我們在新浪微博建立了「思想Reflexion」官方帳號。透過微博,我們既可以將新出一期的目次儘快傳達給外地的無數讀者,也準備逐漸將以前各期的合適文章貼上微博,讓無緣見到紙本刊物的讀者也有機會讀到這些文章。藉這個途徑,這份刊物可望跟散佈廣遠的更多讀者對話;這是一件令我們興奮與告慰的事,盼各位讀者多多關注、利用這個新的交流平臺。
回到這一期的內容,所刊文章的來源地覆蓋甚廣,除了台灣,還包括了馬來西亞、日本、香港、歐洲以及中國大陸。這些文章或者觸及了獨特的在地歷史,或者發展了只有在特定環境中才能進入視野的問題意識,又或者提出了在其他地方尚未排上「日程表」的議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期好幾篇文章中,「歷史」都是反思與推敲的焦點。
一旦涉及歷史,李公明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批判的歷史主義」,應該是一個很有分析力量的觀點。「歷史主義」本來是一種保守的卸責路徑;它將一切發生的事情「歷史化」,從而解消了個人的能動性與責任。但李先生在分析畫家李斌的文革繪畫時,卻借由「批判的歷史主義」指出,所謂「歷史化」同時也是反思者以高度的倫理自覺捲入歷史。因此我們如何面對歷史,也構成了歷史之所以如此的成素,「過去」變成了一個沈重的倫理問題,要求反思者藉著記憶,正視自身的自私與冷漠,節制道德上的優越感與不在乎。吳乃德先生談台灣的二二八受難「人數」的爭議,所突出的也是「我們如何面對歷史」的倫理思考,強調歷史倘使作為正義的法庭,它除了追尋真相、安慰亡靈之外,更應該按照「民主和正義社會應有的審判方式」面對歷史,用這種具有高度倫理涵蘊的方式不自外於歷史。
梁文道與錢永祥兩位對談關於動物的倫理思考,所關注的固然是「動物倫理」這個新生題目,但是其思考的脈絡仍然是人類的「道德進步」這個幾個世紀以來的老話題,並且試圖讓這個老話題獲得新的生命。梁文道先生借用列維納斯的「臉」,說明道德關係的基礎所在。對於一般以平等或者人道為基礎的動物倫理學論述,這是很激進的挑戰。畢竟,倫理的關係應該不祇是普遍規則的適用,或者發揮情緒愛心,而更應該涉及生命之間的「表達」與「互動」,其背後預設了有生命、有感受的主體的存在。梁文道把這個分析應用到人與動物的關係上,相信會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也會引起更多人的不解與質疑。
本期的專輯以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發表臺灣哲學學會與本刊合作舉辦的「《四書》必選」座談會,檢討爭辯教育部將四書列為高中必選課程的是與非。讀者可以發現,爭論者在表面上意見強烈、立場鮮明;不過讀下去,又會發現大家接受的論述基本理路與評價原則是極為接近的。正反兩方的差別所在,似乎多在於「判斷」與具體的評價,少在於「原則」與所嚮往的教育目標。對這類公共議題的爭辯,意義或許就在此:我們爭辯,不是為了找到最好的政策與方針,而是在社會上形成相互學習與適應的習慣。讓社會成員相互學習與適應,才是公共說理的真正價值所在。
歷史記憶中的模糊與未知:二二八死難人數的爭論(吳乃德)
歷史記憶幾乎是所有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幾乎所有的民族主義論述也都以民族的歷史為重要素材。這些歷史記憶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捏造的;歷史傳統可能延續自真實的歷史,也可能是當代的創造。無論真實或捏造,延續或創造,沒有歷史記憶的民族認同幾乎無法想像。正如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所說,「要消滅一個民族,只須消滅其歷史。」而歷史記憶、或集體記憶則是「懷抱民族意識的個人,組織其歷史的基本原則。」
歷史記憶並非「民族主義計畫」的專利。在民族認同早已解決的國家中,歷史仍然是社會和政治符號的重要素材和標的。古蹟、歷史事件、紀念碑、歷史人物,不斷地被保存、複述、教導、豎立和紀念。在「理性」滲透入政治生活每一層面的現代社會中,歷史仍然被緬懷和重視。因為,要回答「我們是誰?」正如回答「我是誰?」一樣,不只需要知道:我目前在做什麼,和什麼人一起生活;也不只需要知道:我希望將來成為什麼。更為重要的或許是知道:我過去做了什麼,什麼事情曾經發生在我身上。當我們理解自己的時候,鮮少只看現在,而未來則幾乎不可知;過去才是自我認同更重要的部分。現在的努力來自過去的困頓和受難;現在的悔恨來自過去的錯誤和無知。剝奪了對過去的深刻情感,人、以及民族的生命,將只是膚淺、世俗的感官和欲望的滿足。
同時,歷史記憶超越民族現實中的階級、性別、族群、種族、甚至世代的差別,創造民族共同的過去。然而不同族群、或種族之間鮮少能有共同的過去,特別當它們的歷史經驗具有顯著的差異。歷史記憶因此經常呈現政治優勢團體的觀點。例如美國內戰結束後,在全國各處廣泛豎立的內戰紀念碑中,只有三個紀念碑提到黑人的貢獻;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甚至小心地避免提到奴隸制度,完全抹除黑人的歷史記憶。權力的不對等、以及歷史經驗的分野,正是保存、及呈現歷史記憶的難題之一。這是幾乎所有國家,包括現時的台灣,面臨的共同問題。
保存、再現歷史記憶的另外一個難題是:歷史記憶不只是曾經發生過的歷史;它也是對過去的闡釋。而這樣的闡釋又經常和現今的期待互相共鳴。記憶乃成為「一個達成理解、正義和知識的有力工具。」歷史記憶因此也經常因為現今的政治需要而被剪裁。以二二八事件為例,政治學者邱垂亮闡釋的二二八,「是台灣最光明、悲壯、崇高的日子,因為台灣人民開始站起來,悲情呼喚要出頭天,要當家作主,要爭取基本人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要追求自由民主。最終,不可避免、沒有選擇餘地、台灣人民走上建立自己主權獨立國家的艱辛道路。」因此,雖然二二八和台灣獨立運動或台灣民族認同毫不相干,可是該事件持續成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最重要的歷史泉源,因為它啟示了重要的歷史教訓:「外來」的政權可能帶來的災禍,對民族可能造成的巨大傷害。歷史當然不只是過去發生過的事,不只是民族成員的行動紀錄。歷史如果要有意義,它必須提供啟發和教訓。民主化之後,兩個政黨的政府在保存歷史記憶上都漫不經心,可是民間在稀少資源的困頓中仍然努力試圖保存、再現威權時期的歷史記憶,難道不也是因為白色恐怖歷史能為後代帶來的啟發和教訓?
為了和民族當前的想像和渴望產生共鳴,歷史記憶必須加以剪裁。「記憶」和「歷史」因此經常不完全重疊。「集體記憶是非歷史的(ahistorical),甚至是反歷史的(anti-historical),對某一個事件作歷史性的理解,是了解其複雜性,是從疏離的立場、以不同的角度加以觀看,是接受其道德的模糊性。集體記憶則將歷史中的模糊加以簡單化,甚至加以消除。」可是簡化的、甚至錯誤的歷史記憶,不論它負載多麼巨大的道德教訓和啟發,顯然違反理性社會對真實的追求,而且也將不斷受到歷史學者、後代、特別是不同立場者的挑戰。同時,模糊的歷史記憶或能點燃某些人的熱情,卻必然失去對其他人的號召。由於不同族群、不同立場的團體具有不同的歷史經驗,模糊的歷史必然無法成功地營造共同的歷史記憶。而共同的歷史記憶卻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條件之一。或許──只是或許──如某些歷史家強調的,「除非歷史記憶以學術標準為基礎,否則我們對記憶的責任只是一個空殼。」
民主化之後,台灣民眾終於有機會提出對未來的各種不同想像,也終於有機會挖掘久被掩藏的歷史。過去二十多年正是台灣認同快速形塑的階段,雖然我們難以確知其結局。這個階段也是台灣社會再現歷史記憶的階段。認同的形塑和歷史記憶的再現,這兩項政治計畫經常結伴同行。而歷史記憶的呈現,苦難是其中重要的內涵。因為,「在民族的記憶中,苦難通常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苦難要求責任、號召集體的奉獻。」
檢視過去、保存其中苦難的紀錄,不一定非得以形塑認同為目標。身為民主公民,即使不懷抱特定的民族認同,仍然會珍視保存歷史記憶中的醜惡和不堪,因為那是社會創建美好將來的必要基礎。要「讓它不再發生」(Never again!),必須以過去為警惕,為反省的教材。歷史記憶因此不必然是認同的基礎和材料,也可以是民主教育的素材。
然而,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們的歷史記憶仍然充滿諸多模糊和未知。不論是為了形塑、鞏固認同,或為了民主教育,這樣的歷史記憶可能無法充分發揮預期的功能。目前我們的歷史記憶中,至少有下列幾個未知和模糊的地帶:二二八未知的死難人數,內戰背景造成的模糊迫害,「官僚化」加害體制中的模糊加害者。
歷史記憶中的模糊地區
內戰是白色恐怖的重要背景,卻也造成歷史記憶的「不方便」。共產黨的滲透經常是國民黨壓制、構陷反對者最便利的藉口,然不論在中國或台灣,共產黨對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積極滲透,卻是不爭的事實。除了共產黨直接派至台灣的工作人員外,因為軍事進展迅速,1947年底共產黨指示台灣的省工作委員會次年發展2000名黨員,組織5萬人的武裝力量,同時逐步展開游擊戰。這個輕率且不實際的指令,讓許多台灣人遭受不必要的傷害。雖然我們傾向於將他們稱為受難者,可是其中有些人卻寧願被稱呼為「革命者」,而非受難者。歷史記憶不只是記憶發生過的事。歷史記憶同時也是一個具有倫理意涵的故事。及至目前,我們對這段時期的歷史記憶,似乎經常故意忽略甚至否認部分白色恐怖受難者為中共地下黨員,故意忽略國共內戰實是白色恐怖的重要成分。更由於中共革命成功後對人民的殘暴,以及現階段中國共產黨對台灣自主的敵意,讓歷史記憶更疏於理會這個事實。以現在的歷史情境去評斷過去,當然不合理。不過,從轉型正義的角度,歷史記憶必須包含歷史的真實整體,同時也不應規避與現今價值與論述歧異之處。
歷史記憶的另一模糊處來自台灣政治迫害的特性:官僚化。除了二二八事件以及少數案件(如林義雄家血案、陳文成死亡案、江南謀殺案等),所有的政治壓迫都同時以「正規的」體制加以輔助,因此我們對加害「體制」有較多的了解,如戒嚴法、懲治叛亂條例等法律,以及各種情治單位和軍事審判等執行法令的機構。可是我們對加害「者」的面貌,卻非常模糊。由於政治壓迫的官僚化,讓加害體制中的工作者都成為國家法律的單純執行者。然而,歷史記憶同時也是帶有倫理意涵的故事,迫害體制中執行者的倫理色彩和倫理情境乃成為重要的記憶元素。他們只是沒有個人意志和好惡的螺絲釘,還是勉強不情願的執行者,或是熱衷的擁護者?即使體制中的執行者必須執行不正義的法令和指令,他們在執行過程中有沒有自由裁量的彈性空間?這是對加害體制中的工作人員,必須提出的問題。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曾經對全國的法官和檢察官發出一封信,要求他們回答兩個問題:1)為什麼你當時沒有任何抗議地、甚至非常熱衷地執行不合乎正義的[種族隔離體制]法律?2)為什麼當你對法條的解釋和引用具有裁量空間的時候,你的決定仍然幫助政府和安全單位?這樣提問的用意不是為了在道德上加以追訴,而是促成司法執行人員的反省。然而這兩個問題剛好也能回答體制中工作者的倫理責任。如果有機會對目前所保存的檔案作深入的研究,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可是至目前為止,我們仍然沒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