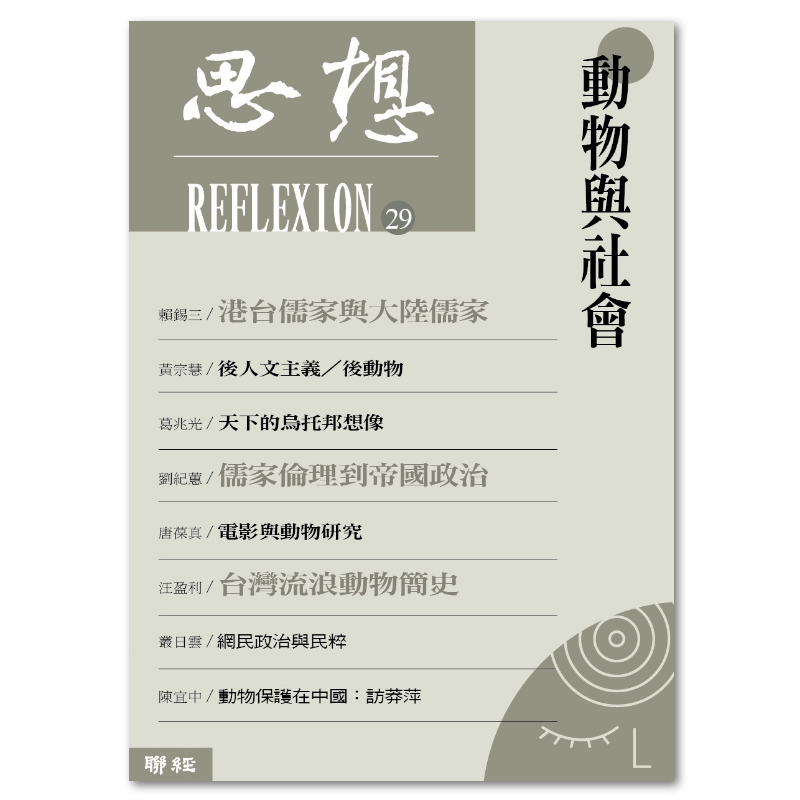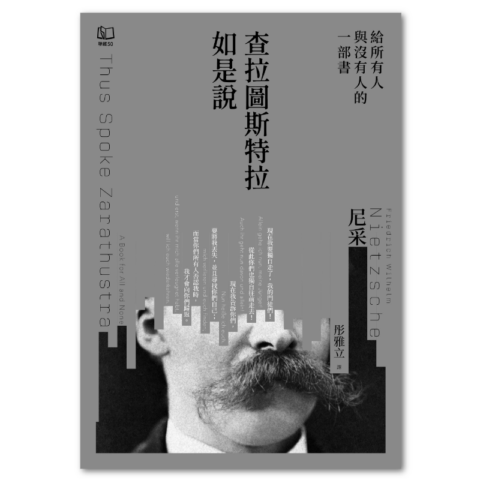動物與社會(思想 29)
原書名:思想編輯委員會
出版日期:2015-10-02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52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6287
系列:思想
尚有庫存
動物倫理學的出現,不僅為動物的命運爭取到道德的地位,
也突破了西方道德思考傳統體質上的盲點。
一種動物倫理學,必然同時是一種從評價的角度想像「動物的生命」的方式:動物的生命固然是自然的事實,但這種生命是否自有其價值,在實現某種值得人類承認的好事,故能要求人類的尊重與關懷呢?動物倫理學的一個關鍵主題在於,動物的生命是不是足以指向某種具有應然意涵的價值,從而用尊重與關懷為標準,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就有了「對與不對」可言。
本期的人物訪談是莽萍先生,談動物保護事業在中國。本期另一個專題是「兩岸儒家」,包括:關於「新儒家」的爭論、港台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的兩行反思、對於大陸新公羊學的初步省思等各篇專文。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葛兆光)
網民政治參與中的民粹主義傾向(叢日雲)
動物與社會
台灣流浪動物議題概述(汪盈利)
是後人類?還是後動物?從《何謂後人文主義?》談起(黃宗慧)
回首第一代英國反動物實驗運動(李鑑慧)
簡談電影與動物研究(唐葆真)
「人與動物關係學」與動物保護政策:台灣經驗的啟示(吳宗憲)
動物的生命:《動物解放》四十週年的反思(錢永祥)
思想訪談
動物保護事業在中國:莽萍先生訪談錄(陳宜中)
兩岸儒家
關於「新儒家」的爭論:回應《澎湃新聞》訪問之回應(李明輝)
「港台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的「兩行」反思(賴錫三)
新儒家、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能否會通?(何乏筆)
開出說?銜接說?(楊儒賓)
對於大陸新公羊學的初步省思(劉滄龍)
知識的生產:為何儒學?什麼政治?如何現代?(劉紀蕙)
致讀者
致讀者
本期《思想》以「動物與社會」為封面專輯,或許會引起讀者側目。不過「動物」(non-human animals)本來便是人類這種動物的關鍵他者,與人性相互襯托界定,是人性的限定所在。人類之所以忽視動物,不是因為動物不重要,而是因為人類的道德意識被成見所蔽。歷史明確顯示,必須等到社會本身的道德意識正在醞釀著大變革,動物的議題才會破土而出。
近代西方第一次動物保護運動,寄身於19世紀英國的社會改革,與解放奴隸、保護少女、保護童工、救助遊民,乃至於要求婦女投票權,勞動條件的改善等等改革訴求一起出現。20世紀後半葉,動保運動又一次復興,其背景則是1960-7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反越戰、生態保護,以及年輕人的「反文化」。在這片追求「解放」的氛圍之中,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適時問世,將人類對於其他物種的歧視與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相提並論,從而把動物議題提昇到與人類問題同樣重要的地位。在台灣,動保運動同樣藉助於1980-90年代的民主化以及各種社會運動,與勞工、環境生態、婦女、消費者保護、原住民、學生等各方訴求先後出現。總之,動物議題是時代的產物,也是社會求變的一個環節,是不應等閑視之的。
這個專輯題為「動物與社會」,一則突出動物議題乃是整體人類與社會問題的一個側面,但也呼應當前學院中「動物研究」的整體問題意識。在當前的台灣以及香港、大陸,動物研究與動保運動都方興未艾,很值得系統地討論。受限於本刊的篇幅,這次的專輯只能呈現台灣學院與運動界的局部現況。需要指出,專輯尚包括了莽萍女士的專訪,相當全面地描述中國大陸的動保運動,特別有其參考價值。
近年來儒學在中國復興,尤其以「政治儒學」為名的公羊學傳統引導風騷,是大陸知識界的一件大事。「政治儒學」有意識地與所謂「港台心性儒學」對比,自許為儒學在新時代的重大進步。本期的另一組文章「兩岸儒家」,便是幾位台灣研究儒學的學者對大陸政治儒學的評論。這個專題由楊儒賓與何乏筆二位推動,整個討論的緣起與其中的意義,特別是儒學在大陸蓬勃發展的宏觀背景,在他們所撰寫的前言中有詳盡的說明,請讀者參閱。
晚近儒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與新世紀以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天下」概念的興趣是相關的。「天下」之說被視為中國獨特的傳統,據說有足夠的資源去設想一套新的世界秩序,也為中國在其中找到自我定位。本期葛兆光先生的長文以歷史為據,對這套論述多所質疑。文章的措辭始終溫和,不過用心的讀者不難在字裡行間感受到作者對知識真誠的嚴峻堅持。
動物的生命:《動物解放》40週年的反思(錢永祥)
一、前言
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一書問世於1975年,至今四十週年。這本書開啟了學院裡的動物倫理學這門學科,也為當代的動物保護運動提供了一套樸素踏實但動能強大的理論基礎。由於西方的道德思考主流一向排斥動物,不願意賦予動物道德地位,辛格這本書卻用主流的倫理學資源為據,為動物在道德思考的範圍之內擠出一些空間,其貢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本文想要探索這個意義所在,但同時也想進一步檢討辛格這種動物倫理學的限制。動物倫理學的出現,不僅為動物的命運爭取到道德的地位,也突破了西方道德思考傳統體質上的盲點。這是它的特殊意義所在。不過一種動物倫理學,必然同時是一種從評價的角度想像「動物的生命」的方式:動物的生命固然是自然的事實,但這種生命是否自有其價值,在實現某種值得人類承認的好事(the good),故能要求人類的尊重與關懷──尊重其存在(的權利),關懷其遭遇的好壞──呢?動物倫理學的一個關鍵主題在於,動物的生命是不是足以指向某種具有應然意涵的價值,從而用尊重與關懷為標準,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就有了「對與不對」可言。
讓我舉一個例子,說明我的意思。假設地球上的遙遠某處發生嚴重地震,許多人死傷,我們不會說這些人的生命以及遭遇僅僅是一件自然事實;相反,我們會認定這是一件嚴重的災難,認為受難者的遭遇是不幸的、不應該發生的,是令人難過、惋惜的事情。我們的這種判斷其來何自?當然是因為人類的生命具有某種獨特的價值,其死亡──即使完全是自然過程所造成──是一種傷害摧殘,不應該發生。對比之下,假定在這場地震中,尚有珍貴的古蹟遭摧毀,大面積的樹木植被田地房舍也淹沒不見。對這些損失,我們也會深有所感甚至於有所惋惜,不過這些損失,畢竟與人的死亡不同。人類生命所具有的價值與意義,並不取決於它對於旁觀者可能具有的價值:即使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罹難者是誰,有甚麼特色,具有什麼身分或者道德品質,我們也會假定他們的生命自有價值。簡單言之,在人類的道德意識中,每個人的生命本身便是價值之源,生命過程彷彿是一個實現某種「善」的過程,自然擁有一些深重的道德意義。結果,我們所想像的「人的生命」不可能僅僅是有生有滅的自然事實,或者需要由他人來賦予價值;相反,我們一般會假定,人的生命自有價值,因此具有一個不言自明的「應然」面向:每個人的生命都應該過得平安、圓滿,因為這是人生內在的目標(或者說權利);而事實上的傷亡、剝奪則總是構成了道德上的「不應該」,需要合理的說明。至於植物、古蹟、財產,當然還包括動物,若是遭受傷害或者毀滅,當然很可惜,卻由於他們的存在本身似乎說不上在成就甚麼有價值的結果,也就說不上道德的「不應該」,至少不同於人類傷亡時的「不應該」。
動物倫理學認為,由於動物與人類的某些相似之處,動物的遭遇應該進入人類的道德考量範圍。但是上述對人類生命的「應然」想像,是不是也適用於動物,也就是承認動物的生命本身有其價值?西方倫理學的傳統,一向不承認動物的生命能有道德的意義,本文想指出,這個想法來自一種雖屬自然但是錯誤的想像人類生命的方式。筆者認為,辛格的動物倫理學扭轉了西方倫理學傳統的生命觀。不過辛格的觀點有其限制,低估了動物生命的豐富含意,未能充分發掘動物生命與人類生命在價值內容上的相類似;動物倫理學接續的發展,可以看做延續辛格的思路,進一步探討動物生命的道德意義。
二、正統道德思考為什麼排斥動物?
為什麼人類會把動物排除在道德關懷的範圍之外?為什麼「道德」這件本應遵循普遍視野的思考模式,會淪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堡壘?撇開各種外緣的因素(人類的社會生存條件,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文化成見)不論,道德思考本身的問題意識如何構成,也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用辛格的理論作為對比,正統道德思考的這個問題意識的走向會顯得更明朗。
《動物解放》一書從效益主義(功利主義)的角度為動物尋找道德地位,由於效益主義的基本評價概念是「苦痛」與「快樂」,於是在關於動物的倫理思考中,「痛苦」取得了關鍵的地位。「減少動物所承受的苦難」,成為當代動物倫理學的共同訴求所在。
思考動物時,賦予「苦痛」關鍵的地位,當然有很好的理由。在現實中,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製造規模龐大無比的痛苦與死亡。動物所承受的苦難逼在人的眼前,既真實又刺目,人類的道德思考不能不設法回應。而就理論言,動物所表現的某些情緒與行為模式,即使看起來具有明顯的倫理含意,但是由於人類所設定的道德價值預設了一些動物不可能具備的能力(理性、自我意識、語言、等等),人類始終擔心,對動物行為賦予價值含意,是不是一種「擬人」的觀點在作祟?道德評價需要被評價者有能力反思與選擇,但是動物即使表現了親情、友愛、互助、哀悼之類的行為與情緒,我們通常會說那只是本能天性,並不具有道德意義。何況,動物需要獵食、爭奪地盤以及交配的機會,也會做出許多殘酷的「壞」行為,一般認為這些「暴行」出於本能天性,並非出自動物的選擇,所以無須受到道德的譴責;那麼同理,動物所表現的「好」行為,同樣是本能天性使然,也就沒有資格受到道德的推許。但是如果本能天性說明了一切,動物所表現出來的任何特色便都不可能具備道德上的價值了。這時候,「痛苦」正好足以為動物爭取到一點道德考量的位置:畢竟,即使痛苦乃是出於本能天性,無須假定受者具有道德能力,但是人類的痛苦也一樣是生理機能之一,卻具有無疑的道德地位,那麼動物的苦痛,當然也可以納入道德考量的範圍。辛格的貢獻在於,他藉著痛苦的普遍性,讓動物在道德領域獲得了一席之地。
傳統的倫理學當然深知「痛苦」這個明顯的事實存在,但不僅對人類痛苦的道德迫切性不夠重視,並且有意識地將動物排除在道德領域之外。這聽來很奇怪,痛苦不是明顯的「惡」嗎?為什麼道德竟然能忽視它?通常的說法是動物缺乏道德能力,但是感受痛苦所需要的能力門檻並不會排除大多數動物,何況人類呢?我認為,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傳統的道德觀急於將人性從其動物性分離出來,想將「人」理想化,認為道德旨在幫助人實現「真正」的、獨屬於人類的價值;只有那些能體現更崇高、正面的價值的人,才能獲得道德的正面評價;結果,痛苦雖是人間的普遍事實,卻由於表現了人性中屬於生物、動物的一面,因此若是把痛苦看做道德的焦點,不啻貶抑了人的地位與價值。
有意思的是,人類思想發展史中早期的「軸心時代」,顯示了這個思路在人類思想的模式中其實是源遠流長的一條脈絡。
「軸心時代」的說法由德國思想家雅斯培斯所提出,指從公元前八百年到二百年之間,希臘、中國、希伯來、印度等地區,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思想上的革命:一種突破現世侷限,追求超越性的價值的思想變動。美國史學家史華慈曾經指出,這裡所謂超越,指「一種退後一步,抬頭仰望──一種對現實所發的批判的、反思的質疑,一個新的超越世界的想像」。簡單言之,軸心時代的重大意義在於,在這個時段,幾大文明關於人、關於世界的想法先後成形,其間的共同特色就是與現實世界拉出距離,開始設想一個超越的境界。
學者在討論這個「軸心時代假設」的時候,多認定了這種對「超越」的追求代表人類文明的一次「躍升」,代表人的自我意識、關於人性的認知不再滿足於「實然」,進而開始設想各種發展、提升、乃至於獲得救贖的方向,也就是追求一種更好的、「應然」的人性境界,具有完全正面的意義。由於所謂軸心時代所涵蓋的幾個文明之間相異極大,這裡的「實然」所指為何,「超越」所想像的新生命又需要如何理解,陳述與答案大異其趣,在此不論其詳。不過至少在希伯來與希臘文明中,都包含一種知覺到實然人生之「脆弱」的意識:此世的個體生命狀況有其本質上的短缺不足,並不符合我們對人類尊嚴的高遠期待。所謂脆弱,可以包含幾個方面。人們意識到此身陷在動物性、生物性的飲食男女、生老病死的規律之中,無時不受到各類肉體需求與欲望的騷擾支配,並非自給自足;生命的維持、延續所需要的眾多資源與條件,幾乎都不是當事者所能自行掌控的;進一步言,人們盼望生命能超出這種生物、動物、肉體條件所給予的限制,臻於「美好」,但什麼事物能使生命趨於「美好」?如果在此世的條件之下,人們所嚮往、追求的事物與目標竟然鏡花水月,只具有偶然、相對的「脆弱」價值,不僅說不上絕對、恆久,甚至於相互衝突無法兼顧,「活得美好」豈有可能?如果生命在物質面以及價值面所仰仗的事物居然都受制於機運(luck)與外力,人生豈不是注定軟弱而無助,焉有「美好」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