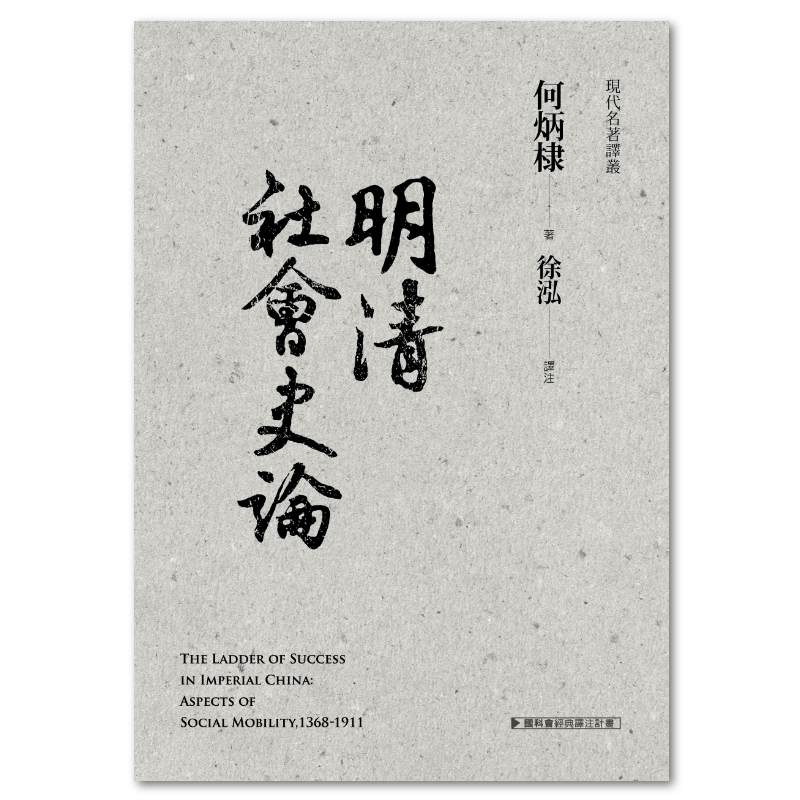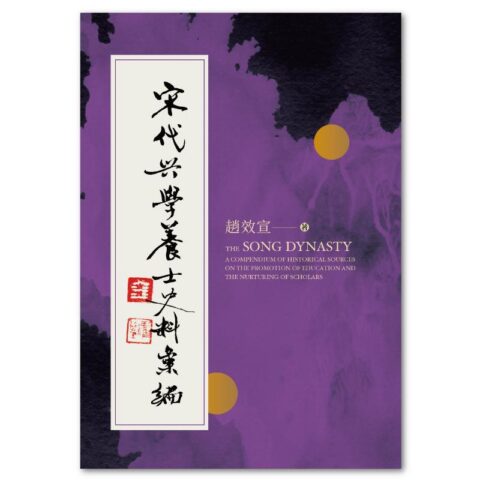明清社會史論
原書名: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出版日期:2013-12-16
作者:何炳棣
譯注者:徐泓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72
開數:25開(高 21×寬14.8cm)
EAN:9789570842142
系列:現代名著譯叢
尚有庫存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作者:何炳棣
浙江金華人。1917年生於天津,民國101年卒於加州。先生於民國23年入清華大學,一窺中西史哲學門徑。民國27年,再入燕京大學,為歷史系研究生。民國32年再試第六屆清華庚款留美公費考試,取魁西洋史;於民國34年始赴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留哥期間,師從英史巨擘John Brebner,研修近代英國農業經濟史。民國37年完成博士候選人口試,赴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講師;隔三年,獲得哥大史學博士學位。民國41年,先生轉治國史,鑽研明清人口財稅史,民國51年,轉任芝加哥大學正教授,主授明清史,研究視野回溯至上古、中古、甚至考古,研究興趣更趨多元,分治城市史、文化史、農業史。先生治史之廣、研究之精,於民國55年,獲選中央研究院第六屆人文組院士。更於民國63年當選亞洲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副會長,隔年任首任華裔會長。民國76年,先生致休,轉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訪問教授;民國80年再休,閒居爾灣左近,再拓先秦思想、制度、宗教研究。致休二十餘年,講學筆耕不輟。先生畢生未仕,窮究國史,秉性狷介,不染迎合阿諛惡習;其《讀史閱世六十年》足為後世立身治史借鑑。
譯注者:徐泓
1943年12月25日生,福建建陽人,臺灣大學歷史系文學士、文學碩士及國家文學博士。現任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廈門大學終身講座教授。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藝術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香港科技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創部部長及人文社科院署理院長,暨大歷史學系創系主任、教務長及代理校長,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座教授、中國明代研究會理事長,中研院史語所學術委員,中華奉元學會創會理事長。已發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史學史,明代婚姻與家庭及國內大移民與城市,清代臺灣自然災害等論著九十餘種、會議論文一百二十餘篇,學術評論三十餘篇與歷史普及讀物三十餘篇,近著有《何炳棣著〈明清社會史論〉譯注》(2013)、《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2016)、〈「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2016)、〈「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範式與明清經濟史研究〉(2018)、〈明朝國號「大明」 的緣由及意義〉(2019)及〈龍德而隱: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老師〉等。
前言
第二版自序
第一版自序
譯者序:何炳棣教授及其《明清社會史論》
目錄
圖表目錄
第一章 社會意識形態與社會階層
第一節 基本反論
第二節 社會階層
第三節 教育與財富同為決定社會地位之主要因素
第二章 社會身分制度的流動性
第一節 法理上缺乏對社會流動的有效阻礙
第二節 明代特殊身分進士的統計
第三節 社會文學所見身分制度的流動性
第四節 社會為儒家意識形態滲透
第三章 向上流動:進入仕途
第一節 史料的簡要評述
第二節 統計分析
第四章 向下流動
第一節 抽樣的家譜記錄
第二節 人文環境
第三節 競爭激烈的考試制度
第四節 有限度的蔭敘
第五節 財富的減少
第六節 家庭制度
第七節 小結
第五章 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
第一節 科舉與官學
第二節 社學與私立書院
第三節 幫助應試舉子的各種社區援助機制
第四節 宗族制度
第五節 刻書業
第六節 戰爭與社會動亂
第七節 人口與經濟因素
第六章 科舉的成功與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第一節 各省的人口
第二節 以省分區分的科舉成功者之地理分布
第三節 社會流動率的地域差異
第四節 科甲鼎盛的地區
第七章 概括與結論
附錄 社會流動的案例選
引用書目
譯者註與按語引用書目
譯者序/何炳棣教授及其《明清社會史論》
何炳棣教授於2012年六月七日清晨七點十一分在睡夢中安然去世,享壽九十五歲,史學界失去一位跨世紀的大師。何炳棣先生原來念的是英國史,後來轉治中國史,他的研究領域廣,包括揚州鹽商、明清至民國的人口、明清會館、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美洲新大陸作物輸入中國、北魏洛陽城、明代土地數據、清代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黃土與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和近年研究的先秦諸子等。何先生收集史料之辛勤,運用史料之精妙,方法與史識之獨創,轟動史林,驚動萬教(教育界),當今華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
何先生不滿於中國文史研究被洋人歸類為「漢學」(Sinology),因為「漢學」是西方人「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其「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產物,他們卑視漢學,不置之於西方為主流的學術殿堂正殿。因此,何先生治中國史都選重要的大問題,成果都由重量級的西方大學出版社和學術期刊出版,與西方史家進行對話。何先生的學術受到西方學界的肯定,1965年榮獲芝加哥大學聘為地位崇高的湯普遜(James West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並於1975年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首位亞裔會長。
何先生擅長於廣泛運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又能吸納西方史學的長處。他在《東方的搖籃:紀元前5000年至1000年華夏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以文獻、考古資料及古動植學證明中國古代文明源於本土,打破西方學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亞的一源說,連強力主張這種學說而撰寫《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著稱的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教授也為之折服。
何先生為人率真,不假顏色,很多人怕他。他成長於對日抗戰之中,有濃厚的民族意識,雖因工作關係入美國籍,但熱愛中國之心過於常人,曾質問一些華人學者:你是中國人怎麼可以不愛國?從何先生的訃聞中知道他要歸葬老家金華。1979年底,在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MIT)討論中美關係的會上,面對滿場洋人學者,親見何先生獨排眾議,大聲指斥研究中國的洋人學者的反華情結。其敢言直言的態度在西方學界的華人學者中極為少見,一般華人學者在洋人屋簷下總是低頭,何先生決不示弱。
1996年,「新清史」的代表羅友枝(Evelyn S. Rawski)教授發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就職演講:“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針對何先生1967年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發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批判何先生對滿清王朝「漢化」問題的論斷。他認為清王朝能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主要原因不在於「漢化」,在不同地區採取不同文化政策,才是清朝統治成功的關鍵。兩年後,何先生像大砲一樣地強力反擊,發表“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捍衛漢化:駁斥羅友枝的《再觀清代》〉)。首先,何先生說他的論文是宏觀的,論題是多面性的,羅氏卻單挑漢化這個單一主題來討論,模糊文章的真實意義。更甚者是羅友枝曲解何先生的論點,何先生說:他的基本觀點,明明是滿族創造了一個包括滿、漢、蒙、回、藏和西南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羅友枝無視於此,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係之間,構建一個錯誤的二分法。他無視於滿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統治人口最多、政治傳統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國,就在他們成功地運用漢族傳統和制度。羅友枝又主張:遼、金、元、西夏政權統治漢人與漢地,都只任用漢族官員,他們都拒絕漢化。其實,這四個政權最終都採用漢文化和制度,甚至以漢族五德終始的正統論合理化其政權。征服王朝要鞏固其統治,漢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本是國際學術研究的共識,而羅友枝卻全然視而不見。何先生在文章中,以極大的篇幅,論述九千年以來,漢文化和漢化發展的歷史的各個方面,並且討論非漢族政權如何採用漢化政策,統治以漢族為主的中國。這真是一篇擲地有聲的大文。
廣泛運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又能吸納西方史學的長處是何炳棣教授治史的特色。他治明清社會史即運用社會学理論,專攻這一長久以來為社會科學家重視的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研究課題。何先生於1962年出版《明清社會史論》,是第一位大量運用附有三代履歷的明清進士登科錄及會試、鄉試同年齒錄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根據這些史料,何先生作量化統計,分析向上與伺下社會流動;在資料的數量與涵蓋面,均遠遠超越前人,統計分析的樣本,進士達一萬四五千名,舉人貢生達兩萬多名。分析結果,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總數50%,清代則減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見平民向上流動機會漸減。清代,尤其清代後期,大行捐納制度,富與貴緊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
何先生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社會流動,而且也討論向下社會流動及其導因,闡明促進社會流動的各種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管道的存在。何先生認為明清社會幾乎沒有制度化的機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長期的向下流動,均分遺產的習俗可能是最有力的的因素。除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外,何先生又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和影響社會流動的各種因素。社會流動比較研究的結果,何先生認為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社會流動的數據,也可能很難超越」。
近年來,何先生的論點遭到部分學者質疑。較著名的有美國的郝若貝(Robert M.Hartwell)、韓明士(Robert P. Hymes)、與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中國的沈登苗。1982年,郝若貝的論文〈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的轉型: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分析宋朝官員傳記資料,發現宋朝政府被幾個或幾十個大家族所壟斷,科舉造成的社會流動並不大。韓明士在1986年發表《政治家與士大夫》(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書,則認為研究科舉所促成之社會流動,不能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為據,應該擴大「精英」定義的範圍,將寺廟捐獻者與從事地方公益事務者及其親戚族人、學生等均列為分析的對象,於是大大縮減平民範圍,把平民在科舉上的成功率大為低估;他進而懷疑科舉制對統治階層與平民間的「血液循環」有促進作用。稍後,艾爾曼發表〈科舉制下帝制中國晚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再生產》(“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與《帝制中國晚期的科舉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也認為何先生估計出身平民進士之比例過高,過分低估中式家族及其婚姻對向上流動力的作用,進而論定:「近千年來,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統治階層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再生產』而已。」沈登苗則於2006年發表〈也談明代前期科舉社會的流動率——對何炳棣研究結論的思考〉,批評何著對「明代前期」的界定,及以何先生未能使用天一閣獨家收藏的31種明代進士題名錄為憾,並指出「明代前期科舉流動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造成的,何先生的「結論在科舉史上並不具備典型的意義」。但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使用的21種(其中5種為天一閣獨家收藏前人未使用過的)明代前期題名碑錄,分析的結果,仍然支持了何先生的結論。對於韓、艾二氏的批評,何先生並未撰專文反駁,僅於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簡單回應稱:自己的統計「完全是根據八十幾種中試者的祖上三代履歷,最能反映社會階層間的上下流動」,而艾氏所用的資料卻「沒有最能反映社會血液循環的祖上三代履歷」;而且根據艾氏的統計,明清出身平民的舉人,占總數的54.27%,出身平民的進士,占總數的61.78%,反而坐實了何先生的結論。至於韓氏的評論,何先生則認為是對「精英」的定義混亂而誤導的。其實明朝政府早已認識到科考中試者多平民出身,《明神宗實錄》卷535載,禮部言:「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寒素之家。」可以說近年來少數學者質疑科舉制與社會流動的關係,似乎是難以撼動何先生論點的,大部分學者仍認為「科舉為寒門子弟架起了通向『天門』的階梯」。《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影響中國社會史與明清史及東亞史研究甚鉅。如許師倬雲教授的《先秦社會史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B.C.)、毛漢光的《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吳金成〈中國의 科擧制와그政治.社會的機能──宋.明.淸時代의社會의階層移動을中心으로──〉《科擧》(서울:一潮閣,1981)、吳建華〈科舉制下進士的社會結構與社會流動〉(《蘇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及研究韓國科舉與社會流動之崔永浩(Yong-ho Choe)的Th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Yi Dynasty Korea, 1392-1600(《朝鮮李朝初期的科舉制度與社會結構》),均以此書為典範。
近年來,研究科舉與社會流動的史料陸續公開,已較五十年前何先生出版《明清社會史論》為多:明代鄉試錄313種、會試錄54種、進士登科錄54種、進士同年序齒錄15種及進士履歷便覽17種。整理編印的工作,也不斷展開。伴隨著《明代登科錄彙編》、《清代硃卷集成》與《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會試錄》等明清科舉史料的整理印行,科舉的研究,再度興盛,而有所謂「科舉學」的出現。于志嘉利用《萬曆三十八年(1600)庚戌科序齒錄》,分析77名軍籍進士祖孫五代社會身分的變遷。而論述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相關研究,更是在方法上、資料的運用上,都很明顯地看出沿襲何教授《明清社會史論》的痕跡。2003年,張杰的《清代科舉家族》,即用統計分析法,處理《清代硃卷集成》中的家族背景資料,討論中舉者的垂直流動、應試者的水平流動,及科舉與士人居住地遷移的關係。2007年,廈門大學鄭若玲發表《科舉、高考與社會之關係研究》,將科舉與大陸、台灣及東亞地區大學入學考試類比,討論其與社會的關係;其第四章論述科舉與社會流動的關係,也是「基於清代硃卷作者之家世」,用統計方法所作的量化分析。其分析的樣本雖多達八千餘名科舉人物,但仍較何教授的近四萬名樣本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其特別之處,在何教授分析科舉人物的祖上三代家世,鄭若曾則延伸到五世,多考察兩代祖先,兼及妻系與母系情況,而且還統計分析了功名大小之間的流動。其結論雖部分有異,但主體仍與何教授的論述一致:「科舉制是清代社會流動的重要途徑。盡管獲得功名的舉子大多數還是出身於較高社會階層,但一定比例的布衣藉著科舉得以升遷的事實,說明他們仍有一個較為公平的向上流動渠道。」
近年來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研究趨勢,除研究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及橫向的水平流動外,又注重區域研究。在相關資料的整理方面,1980年,朱保炯、謝沛霖在房兆楹、杜聯喆編《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的基礎上,編輯《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確認全國進士的籍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何教授《明清社會史論》最早注意這一論題,並在該書特立第六章〈科舉的成功與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論述之。中國地大,地形複雜,各地發展不平衡,差異性極大,是治中國史者當特別放在心上的;否則便會把中央集權體制視為極有效率的,誤以為所有制度實施時,是全國一致的。何教授認識這一特性,深入討論地域的差異。1993年,何教授更發表〈明清進士與東南人文〉,論述東南進士人才輩出的人文環境。同年,王振忠翻譯《明清社會史論》第六章“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為〈科舉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發表於《歷史地理》第11輯。這一章的中譯本方便許多中國學者直接閱讀何教授的論著,受其啓發,而開展對進士地域分布和分區的研究。為照顧邊遠落後地區,不致因其文化水平劣勢,而乏人參與政府,尤其唐宋以來,因北方戰亂及經濟重心南移,導致南北文化水平之鉅大差距;因此,明廷確立各鄉試省解額,建立會試南、北、中卷制,依地域比例,訂立錄取名額,使全國各地均有人才加入政府,鞏固明朝作為代表全國各地人民的統一帝國。對於科舉錄取題名。靳潤成、檀上寬、李濟賢、林麗月、劉海峰、王凱旋研究明代科舉的區域配額與南北卷,汪維真研究鄉試解額,沈登苗研究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進士的地域流動,曹國慶研究江西科第世家,范金民與夏維中研究江南進士的數量與地域分布,分析其數量眾多的原因。其他地區如安徽、浙江、福建、廣東、貴州、山西、山東、四川等地均有學者研究。
除了上述學者的研究外,近年來有關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的論著與論點,多與何教授相似,不過在資料的運用上有新進展,如對於現存登科錄的調查整理及個別登科錄的考證,近年來也頗有進展。1969年,臺北學生書局編印《明代登科錄彙編》。2006年,寧波出版社影印《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是目前規模最大的明代科舉文獻彙編,給學者們在研究上很大的方便。其他與科舉相關研究,近年來大量湧現,對譯註工作,大有助益。
何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自1962年出版至今雖已半個世紀,此期間這個研究領域雖有上述的發展,但無論在論題的開創,運用史料與統計分析方法的精到,獲致結論的堅實,仍是其他相關著作不可倫比的。《明清社會史論》可說是一本中國史研究、社會史研究與東亞史研究及社會科學界譽為劃時代之經典鉅著。尤其在科舉與傳統中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動的。
何教授的《明清社會史論》至今已有意大利文、日文和韓文譯本問世,但仍未有中譯本刊行,實為一大憾事。泓最初讀到何教授的鉅著,是1965年的夏天,剛考上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所長劉壽民(崇鋐)教授將何教授送給他的這本《明清社會史論》,賜贈於泓。於是開始一頁一頁地讀,初讀英文寫的中國史論著,最頭痛的還不是英文,而是中國史上的人名、地名、官名與書名等專有名詞,如何從英文還原為中文,尤其這些字詞,在一般英文字典是查不到的,只好試著猜,猜到一個自以為是的,就高興得不得了。當時邊看邊試著翻譯,居然譯了四章半,後來因為忙著寫論文而中斷。泓之治明清鹽業史,完成碩士論文《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與博士論文《明代的鹽法》實受何先生大著〈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與《明清社會史論》啓發,是從中得知什麽是鹽户、灶户,什麽是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明清鹽業與鹽商在中國史上有多重要;因而投入明清尤其是兩淮鹽業的生產與運銷的研究。取得學位以後,有幸留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任教,由於教學工作忙碌,也就擱下翻譯《明清社會史論》的工作。時值七十年代前期,正是保衛釣魚臺運動的高潮,許多留美學人學生不滿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軟弱,而投身運動;遭國民政府或吊銷護照,或視為拒絕往來户,何教授便是後者。當時國民政府對外雖軟弱,但對內卻很強硬,臺灣在威權統治下,校園氣氛甚為嚴峻,尤其身為學術教育界龍頭的臺灣大學,更是陷於「白色恐怖」中;先有哲學系事件,兩次整肅之後,幾乎完全改組;繼而傳說矛頭指向歷史系,於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何教授既然已列為臺灣的拒絕往來户,當然不宜再談他的著作。直至八十年代後期,解除戒嚴,何教授也恢復每兩年回來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權利,泓乃重拾舊譯稿,以完成這一對泓學術生涯有重要關鍵作用的工作。無奈當時承擔學術行政,正負責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研究所;1991年卸下重擔後,榮幸地被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副校長錢致榕教授與校長吳家瑋教授找了去創辦人文學部;1993年底回臺以後不久,又為袁頌西校長找了去創辦暨南國際大學的歷史學系與研究所,並擔任教務長,尤其九二一大地震後,代理校長承擔校園復建及延聘新校長等善後工作;沉重的學術行政工作,阻擋了大部分研究工作。直到2002年自暨大退休,轉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的教職,教學工作單純,遂能重拾研究寫作工作。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是劉壽民老師創辦的,泓擁有的何教授《明清社會史論》,原是何先生送呈他讀清華大學歷史系時的業師和系主任劉壽民老師的,後來劉老師賜贈予泓,真是機緣凑巧。於是重拾舊譯稿,矢志完成此未竟之業。不久,又蒙何教授約見,鼓勵泓繼續翻譯,並惠允協助解决翻譯中遇到的困難,隨後又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贊助此翻譯計畫,工作於是再度展開。
《明清社會史論》於1962年出版後,何教授又獲得到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翁同龢收集的清代進士履歷便覽、會試錄與會試齒錄、舉人鄉試錄、貢生同年齒錄及在台北中研院史語所見到四種明代進士登科錄等新資料,1967年第二版即據以修訂,重新估算表9、表10、表12之數據,並修改其文字;因此,1967年修訂版與1962年原版中本章的內容有所不同。本譯文即以1967年修訂本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為底本。
這次翻譯時,一一查對何教授引用之原始文獻,還原於譯文之中,若有出入則以「譯者注」形式說明。由於這本書出版已五十年,此期間有不少相關文獻與研究論著出版,與何教授對話,對於不同的意見及補強或修正的文獻資料,也要以「譯者注」形式說明。由於何教授徵引之資料,有許多不見於臺灣的圖書館,也一一向何教授請教。有了何炳棣教授的協助,相信這個《明清社會史論》譯註本不同於其他文字譯本,而為較好的譯本,也是較理想的中文版本。
第三節 教育與財富同為決定社會地位之主要因素
明清政府在法律上界定官僚體系各階層的地位,明顯地與其社會地位相符,但在我們研究平民階層時,也發現各個主要平民群體間的法律與社會地位,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傳統中國政府既尊儒也「重農」;所以,在法律規定上有其強烈的偏見。不難理解,儒家政府把士民的地位置於其他庶民之上;因為士民是庶民中唯一勞心的群體。作為重農主義國家,農民是財富的主要生產者,國家,特別是統治階級的生存,就依存於農民的勞動之上。因此,農民雖然是勞力的,卻比較能免受不平等的法律之害,常有權參加科舉考試。《管子》這本書服膺的社會概念與孔子便相去不遠,主張庶民應「世守其業」,嚴格地執行世襲的社會職業與社會地位,但也歡迎具「秀才之能」的農民子弟可上升為士,最終進入封建官僚之列。另一方面,工與商在傳統中國社會中,被視為財富的次要生產者與中間人;因此,在法律上給予不公平的待遇。他們受到差別待遇及反奢靡法律的制約,禁止過於奢華的生活,其中較嚴重的是國家拒絕給予他們進入官僚階級的權利;直到宋朝末年,法律還禁止工商之子弟參加科舉。傳統中國社會以工商為四民之末,輕視工商,歧視工商,這樣的態度一直持續到近代。
但深入研究歷史社會現象,卻顯示一個與法律文本不同的圖象。西漢政府雖然採「重農抑末」的政策,令商人不得衣絲,乘馬,操兵器,又規定商人算賦加倍,子弟不得為官;但這些大資本商人、放高利貸者與工業家卻「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教,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其社會地位等同王侯。其勢力令人畏懼,對小民與平民是一大威脅,而被當代人稱為「素封」,即「沒有秩祿爵邑的貴族」。唐代的許多富商與大資本家成功地規避商人不得奢靡的禁令,過著只有上流社會才能過的生活方式。雖然宋代法律禁止工商子弟參加科舉,可是有許多落第士子與官吏公開經商,而工商子弟設法通過科舉考試走入仕途的,也不在少數。元代許多色目商人(來自中亞及中亞以外的非蒙古與非中國人)的勢力更大,控制了國內外貿易,甚至政府的財政。明清時代,更取消最嚴重的歧視工商的禁令,這可以視為政府對勢力日益強大的工商遲來的認可。
接著討論另一明清社會階層的基本難題,那就是教育(或更具體的措辭:任官的機會)與財富是決定社會地位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由於官方的法令與文書主要處理法律的社會階層,因此微妙的社會現況,只能從社會小說與私人的文學作品中去找尋。以下所舉幾個事例也許過於極端,不能作為一般社會實情的反映,但是這些極端的事例,還是可以幫我們強化理論的觀察,認識到官職及可望得到的官職與財富,在決定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中相對的重要性。與反映社會類型的一些統計資料相對照後,我們就可以作出較平衡的估量。
我們很幸運地有《儒林外史》,這一部最能透露內情、最寫實的小說,也是研究明清社會重要社會階級不可少的著作。小說中許多令人大開眼界的片斷之一,是關於一位貧苦的南方學者范進,這個窮童生,多年靠著他的岳父胡屠戶為生,當他考上秀才,進了學之後,胡屠父對他說:「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個體統來,……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這下子社會地位可算提高了一些,但家庭經濟可以說毫無改善,連參加鄉試的盤費都沒有,等他出了考場,家裡已是餓了兩三天。一直要到中舉人的消息傳來,才大有改善,所以當他聽說中了第七名「亞元」時,竟歡喜得瘋了,報錄的建議胡屠戶打他一個嘴巴就會好了,胡屠戶卻說:「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文曲星);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拏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卻是不敢做這樣的事。」在他的心目中女婿已是天上的文曲星了。這下全然改變了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地方上一位也是舉人出身和做過一任知縣的張鄉紳,馬上親自登門拜訪,並送給他賀儀五十兩與一所大房子;自此以後,地方上的小老百姓也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僕圖蔭庇的,不到兩三個月,家中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更不消說了。
在另一部社會小說《醒世姻緣》裡也有一個細節不同的片段,這是個關於晁思孝突然改變命運的故事。他也當了多年的生員,是個財產有限的人,鄉試屢考不中,後來因資歷而成為貢生,使他能參加低級政府官員的特考,得了個知縣。消息傳來,地方上窮人也有願為其僕人的,也有願送土地給他,放債者願無息貸款,晁家驟然間成為當地最富與最有權勢的人家。上述一位南方、一位北方小說家分別獨立地寫出的兩個故事片斷,可以看出教育的重要,通常更高的科名(舉人)會導致個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驟然提升。
明清社會中,財富本身並不是權力的根源,這一論點可在此進一步闡明。至少從明代中葉起,安徽南部山區的徽州府商人成為全國最富有的商業集團之一,許多富商鉅子以家財上百萬兩銀子自豪。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謝肇淛,是一位廣博的旅行家與不凡的觀察家,他的那本包含天、地、人、物、事五類記載的著名筆記《五雜俎》,曾經是江戶時代日本人瞭解晚明中國最受歡迎的指南。他在書中提到,徽州的一位百萬富商汪宗姬的事例,因為他有錢,總是鮮車怒馬,帶了大批隨從姬妾出遊,有一次,路遇一地方官,未及時讓道以致於長期訴訟導致破產。我們不能肯定汪氏是否曾捐過功名或官位,但顯然財富的力量本身是敵不過官府權力的。
甚至有官銜的富商家庭,在特殊環境下,面對官府也是無能為力。徽州富商吳氏的事例更能令人大開眼界,這家人在十六世紀初正德年間,以鹽商起家,一直很富有,到十六世紀末與十七世紀初之際的萬曆後期,又常捐鉅款從事地方慈善事業,包括建書院,刊刻十六部經書,免費提供給需要的學生。由於對學者的贊助,長期以來,吳家已被接納為地方精英的一分子;通常的情況下,這已能給吳家有效的社會保護。而且吳家又非常實際的捐了三十萬兩銀給國庫,家中有六人取得七品京官銜。以吳家新獲得的正式官員身分,配合其財富;因此使他們毫無困難地占有黃山的木材,孰料天啟六年(1626),因一個背叛的僕人告到一個貪婪而有權力的宦官那裡,誇大吳家霸占公共山地的說法;於是,不但吳氏所有在徽州地區的家產被政府沒收,而且他在天津、河南、揚州、與杭州各地的鹽業與當舖的各種投資,都遭調查,最終都被政府沒收。
這些事例並不限於徽州地區,也不限於晚明。十八世紀前半期的雍正、乾隆年間,《儒林外史》有另一個生動地描述揚州大鹽商萬雪齋的例子;揚州位近大運河與長江交會處,是個文化中心和奢華消費城市。即使以揚州的消費標準而論,萬氏招待著名文士的方式,也被認為是奢侈浪費的。他的七姨太有些文學天分,熱心社交,就組織了個詩會。儘管萬雪齋有精英的身分,他還是成為貪婪成性的地方官下手的對象;經過與寵愛的七太太深思熟慮之後,萬雪齋決定從他正迅速縮水的家產拿出一萬兩銀子,去買一個邊遠的貴州省知府實缺,因為在法律許可範圍內買得一個立刻可以上任的高官,萬雪齋才能逃脫他與其姨太太認為正逼近的死亡危機。吳敬梓在評論萬雪齋的事例時,引用了一句包含當代基本社會事實的通行中國俗語:「窮不與富鬥,富莫與官爭。」
李贄較為人知的是筆名李卓吾(嘉靖六年至萬曆三十年,1527-1602)。他做過地方官,也是思想界的離經叛道者,曾做過大略的觀察:「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眾,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 這也是明清時代商人常為官員立碑以表達謝意的原因,因為只有受到那些有同情心官員及時保護,商人才得以免受地方政府的吏員及其手下的威脅與榨取。
十九世紀末的社會小說《官場現形記》在序文中說到明清社會權力的根源:
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貴矣!官之權,大矣!官之威,重矣!一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古之人:士、農、工、商分為「四民」;各事其事,各業其業;上無所擾,亦下無所爭。其後選舉之法興,則登進之途雜;士廢其讀,農廢其耕,工廢其技,商廢其業,皆注意於『官』之一字;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若官者,輔天子則不足,壓百姓則有餘。
以上的實例與觀察無疑地包涵了相當多的社會實況,然而這不應扭曲我們對事情的真正瞭解。其一,這些被官員勒索而終致破產的商人案例,雖有啟發性,卻是例外而非常態。其二,財富是社會地位的決定因素之一,雖然理論上其重要性還不及高階功名與官職,但財富真實的力量隨時間的前進而穩定成長。在景泰二年(1451)以前,財富最多不過能幫助人得到較好的教育機會,便利最終達成高等功名或官位而已;直到當時選官之法,完全由正途的科舉或特別的保薦、或由國子監監生、吏員和胥吏升遷。但由於正統十四年(1449)士木之變,蒙古瓦剌入侵,嚴重地威脅首都北京,迫使明政府不得不開捐納官位、官銜與國子監生之例,為富人的社會流路開啟重要的前管道邁開了一大步。長久看來,販售官位與官銜及國子監生資格,對社會流動的影響,遠比法國舊政府(ancien regime)實行的波萊特制度(Institution of la Paulette),在促進中產階級(bourgeoisie)上升為貴族的影響要大得多。
從當代的士人與官員部分的統計資料與證詞,我們得知明代賣官位、官銜與監生資格是在一定範圍內進行的。崇禎十七年(1644)早春,北京陷落之後,一個明朝的親王(福王)在南京即位,繼續抗清。他的主要籌餉方法就是大規模地賣官鬻爵。這個流亡政權的賣官,隨著順治二年(1645)清軍攻下南京而終止。但這個賣官政策對清初的政策有不可忽略的影響。清朝政府在1660和1670年代(順治朝及康熙朝前期),需錢孔亟,首先是為供應南方強大的三藩,然後是供應平定三藩之需。的確,在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678-82),清朝政府不但大規模地賣官,而且幾乎是史無前例地,全國性地進行生員資格販賣。雖然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歸附,全國平定之後,生員資格販賣政策永遠不再繼續實行,但每逢軍事出征、重大天災及興建公共工程時,仍常以捐官來解決財政需求。
我們無法確知清代前半期捐官的數量,但難能可貴的一件嘉慶三年(1798)名單透漏了那年捐官的數字:京官1,437、省級與地方官3,095,這還不包括許多從九品以下及不入九品之流的下級官員。其中最大宗的是縣丞1,258,其次是筆帖式547,他們是京官捐買之最大宗。其中甚至還有十歲以下男童的捐官案例,因為捐了官之後不是馬上可以上任,得等一段時間,早捐就可早任官。雖然這不是常例,不會每年都捐這麼多官,但嘉慶三年這年捐官的總數4,532,已超過中央政府品官總數至少三分之一。這個數字,再加上嘉慶四年至道光三十年(1799-1850)捐監人數 ,顯示至少在清代中期的大部分時間,金錢直接轉換成高社會地位,遠比明代容易得多。
官員中捐官的比例有多少,可由分析兩種官員初任官職資格的系統性資料得知。第一種,是各種版本的《爵秩全覽》,也就是官員品級與俸祿的手冊,在北美能找到的最早版本是十八世紀五、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中期(乾隆中期),最大宗的是十九世紀(嘉慶至光緒)。其中一個樣本顯示,經過百多年,中央政府官員中正途(高階科名與蔭敘)與非正途(如捐納等)出身的比例,只有相當小的變動。這是因為習慣上,某些中央政府官職員額,分別保留給正途與非正途出身的人。例如,高官與學官,照例是保留給高階科名出身的人,某種官職,特別是「筆帖式」,也就是滿人書記,是保留和供滿、蒙、漢軍八旗捐納的。六部與其他幾個中央機關的三個等級的筆帖式,也按一定比例分配。隨著捐納的筆帖式人數逐漸增加,一種叫做額外主事的額外資淺書記人數也相對增加,這個額外主事的位子通常是撥給新科進士的。為平衡起見,通常中央政府官員中,正途出身的人數,比非正途出身的人數,在幅度上要稍多一點。
正途與非正途出身官員比例之變遷,可由分析地方官員初任官職資格的資料,更好地呈現出來。由於要對那些不計其數的「佐雜」,也就是最低的兩個品級(八品與九品)地方官做完整分析非常費時;至少在十九世紀的清末,這些八、九品的官員,其職位大部分是捐納來的。因此,我們分析官員的出身,只限於地方行政的中堅,即四品至七品的地方官階級。我們選擇了可以代表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與後太平天國時期的官吏人名錄《爵秩全覽》,以見證捐官急速增長的趨勢。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帝國正值和平、繁榮與行政秩序井然的巔峯,這一年的《爵秩全覽》中登錄的地方官員中,超過70%是貢生以上正途出身的。道光二十年(1840),當國家仍處於和平之時,非正途出身的官員增加的百分比並不太大。但是咸豐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64)的太平天國之亂,迫使清廷賣官,其規模之大,是以前做夢都夢不到的。亂事平定之後,非正途出身官員的百分比一直都超過正途出身者。
上述數據的資訊並不完整,《爵秩全覽》並未指明那些最初以正途出身官員,是否再度捐納,或甚至在初任官員時就以捐納做為其加速進入仕途或晉陞的手段。第二類的數據是《同官錄》,也就是各省官員的人名錄,比較令人滿意。由於《同官錄》未包含大量的「佐雜」,因此我們只能分析七品以上省級與地方官員的出身背景。
光緒十二年(1886)版的浙江官員《同官錄》相當完整,包括佐雜及府州縣學的教授、教諭等,特別具啓發性。府州縣學的教官做為一個群體,有別於任官常規的例子,是格外孤單而可悲。道光三十年(1850)以後,決定官員身分的因素中,金錢遠比學術來得重要。90名教官中,60名出身正途,26名捐納,4名保舉;但60名出身正途的教官之中,又有26名進一步以捐納取得官職。在排除大量以捐納取得從九品官位及不入流的吏員之後,剩下的272名佐雜中有238名取得官位唯一的方式是捐納。
系統性的統計資料之外,個人的傳記證明,大部分情況下,在捐納官位之前,需要物質幫助才能得到好的教育,高的功名,最終達到官員的身分地位。這一事實,或可以一些出身貧寒而奮鬥不懈的學者來說明。例如沈垚(嘉慶三年至道光二十年,1798-1840)是道光十四年(1834)的「優貢生」,也是一位歷史地理學家,曾做如下的一般性觀察:
[自宋以後]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於是…非父兄先事業於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
沈垚從他與一些天資好卻遭挫折的朋友們的經驗,得到一個結論:「當今錢神為貴,儒術道消」。儘管這一印象想來是誇大而單方面的看法,也很可能只適用於清代後期;但能幫助現代學子瞭解,一般認為明清時代全國競爭性的考試體制下,只靠個人的才能就能決定個人社會價值與地位的看法,是多麽地誇張。
總之,從我們所舉的實例與全體的統計,可清楚地知道,在明清時代的中國,錢財本身不是權力的根本來源,它必須轉化成官員身分,才能讓人充分感到錢財的力量。從明朝創建到蒙古入侵的正統十四年(1449),財富只能間接地幫助獲得一個較高的功名與一個官職。景泰二年(1451)以後,不時出現的賣官,對富人開啓一條社會流動的新管道,使錢財在決定社會地位上,成為重要性不斷增強之因素。但直到太平天國叛亂的咸豐元年(1851),國家一直把科舉制度,做為首要的社會流動管道,捐納做為次要管道。太平天國之亂爆發後,國家開始失去其管理控制能力,錢財的重要性才超過高等功名,成為社會地位的決定性因素。
比較明清中國與西方早期近代及近代的社會階層,我們發現其間只是程度不同,而非性質的相異。勞力者與勞心者的界線,儒家中國可能比西方來得清晰;但這樣的界線,在所有的前近代與近代的文明社會差不多都存在。即使在現代的北美,雖然對勞力者的偏見已是最少的,但社會階層體制的根本區別,仍在白領與藍領職業之間。儒家傳統與價值,可能會對富人在得以進入統治精英時造成較大的壓力,但同樣的驅策與社會弱勢情結,也在大多數前近代與近代社會的新富(nouveaux riches)身上可以看到。教育,或更準確地說大學學位,在最「物質主義化」的北美社會階層,越來越重要。甚至傳統中國對各階級生活方式詳細的法律規定並非獨一無二,中古與後封建時代的歐洲也有同樣的情況。明清社會特別之處,在於除了這五個半世紀時期的最後六十年之外,官僚制度與國家權力具有壓倒性的力量,一直是管控社會流動的主要管道,這多少符合當時確立已久的儒家傳統的指導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