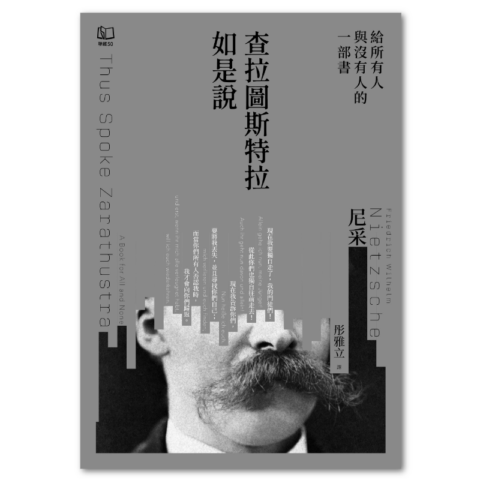本書由余英時先生的25篇論文組成,討論主題集中在中國思想史,從先秦到當代,釋證中國文化中的人文情懷和理性精神。體裁有專論、書評、條目和序跋,先後發表於1980-2006年。內容包括「魏晉時期的個人主義和新道家運動」、「清代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初論」、「孫逸仙的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20世紀中國國史概念的變遷」等。
作者:余英時
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第一章 天人之際
第二章 魏晉時期的個人主義和新道家運動
第三章 唐宋轉型中的思想突破
第四章 田浩《儒家論說和朱熹的優勢》序
第五章 重訪焦竑的思想世界
第六章 清代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初論
第七章 對17世紀中國思想轉變的闡釋
第八章 戴震與朱熹傳統
第九章 戴震的選擇
第十章 章學誠對抗戴震
第十一章 黃進興《18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序
第十二章 桐城派(詞條)
第十三章 孫逸仙的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
第十四章 商業文化與中國傳統
第十五章 民主、人權與儒家文化
第十六章 20世紀中國的激進化
第十七章 20世紀中國國史概念的變遷
第十八章 民主觀念和現代中國精英文化的式微
第十九章 中國史學思想反思
第二十章 在2006年克魯格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講
編者序言
我收集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初衷本是為了自己更全面地學習他的治學方法和理解他的論學旨趣。但在閱讀的過程中慢慢覺得,如果能將這些論著譯成中文,也許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意義在我看來至少有兩點:一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更全面地讀到余先生的論著;二是有助於對海外漢學以及中美學術交流的認識與研究。
《東漢生死觀》取名於余先生1962年在哈佛大學的同名博士論文。由於這篇學位論文中的第一章後經修改以同名發表於1964-1965年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刊》,因此在本冊中用後者取代了前者。此外,另收了同一主題的一篇書評(1981年)和一篇論文(1987年)。時隔二十年作者續論這一主題,主要是因為考古的新發現。1978年末余先生率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中國月餘,漢代文獻與遺跡親切感受大概也起了激活作用。
《漢代貿易與擴張》取名於余先生1967年出版的同名專著。此外,另收了兩篇論文和一篇書評。論文與漢代有關,發表的時間雖然分別是1977年和1990年,但後者是因所收入的文集出版延後所致,實際上它們同時完成於1973-1975年間。與這一主題相關,作者後來為《劍橋中國史》(秦漢卷)(1988年)撰有專章「漢代對外關係」,此書早有中譯本,故這裡不再收錄。1964年刊行的書評是關於唐代財政體制的,雖與漢代無直接關係,但考慮到主題同屬於社會經濟史,所以一併編入此冊。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由多篇論文組成,討論主題集中在中國思想史,涉及3世紀到當代,體裁有專論、書評、條目和序跋,先後發表於1980-2000年。之所以取名為《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是我以為這個提法能反映余先生的思想,他的所有思想史論著從根本的意義上說,也正是要釋證中國文化中的人文情懷和理性精神。(編按:繁體中文版出版時,依余先生的意思,增收〈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朱熹哲學體系中的道德與知識〉、〈歷史視野的儒家與中西相遇〉、〈20世紀中國現代化與革命崇拜之爭〉、〈歷史學的新文化轉向與亞洲傳統的再發現〉五文。)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取名於余先生作為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團長寫成的同名總結報告。此外,收入了由余先生總的訪問活動與討論日記,以及差不多同時完成並與主題相關的一篇專論。這篇專論最初以中文寫成發表,後被譯成英文並經作者適當改寫後發表,收入本冊時相同部分照錄中文,不同部分則據英文而譯。
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在1970年代有一個明顯的變化,此後他的學術論著主要是以中文發表,大部分英文論著則概述他中文論著的主要思想,以及他對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分析性通論。前者顯然是因為他希望更直接地貢獻於中國學術,後者則表明他希望將中國的學術引入美國。促成這個變化的契機大概是他1973-975年在新亞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的任職。雖然服務兩年後仍回哈佛任教本是事先的約定,且這兩年的服務也令他身心疲憊,但深藏於他心中的中國感情似乎更被觸動,更需要得到合理的安頓。1976年1月余英時先生四十六歲時,同在哈佛任教的楊聯陞將自己與胡適的長年往來書信複印本送給他作為生日禮物,在封面上題寫:「何必家園柳?灼然獅子兒!」大概正是體會到弟子的心情而示以老師的寬慰、提示與勉勵吧。
此後,余先生與兩岸三地的中國學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流。我在余先生小書齋的書架上翻覽時曾見到錢鍾書在所贈《管錐編》扉頁上的題詞,當時覺得有趣,便請余先生用他的小複印機複印了一份給我,現不妨抄錄在這裡,也算是一個佐證。題云:
誤字頗多,未能盡校改,印就後自讀一過,已覺須補訂者二三十處。學無止而知無涯,炳燭見跋,求全自苦,真癡頑老子也。每得君書,感其詞翰之妙,來客有解事者,輒出而共賞焉。今晨客過,睹而歎曰:「海外當推獨步矣。」應之曰:「即在中原亦豈作第二人想乎!」並告以入語林。
總之,讀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應當注意其中的中國學術背景,正如讀他的中文論著應該留心其中的西方學術背景一樣。
何俊
天人之際
「天人合一」觀念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宗教和哲學的獨有特點。天人判然兩分的思辨方式,早在遠古時期已是中國哲學分析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莊子》中一再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天」和「人」之間的界限應如何劃分。莊子強調天的觀念,後來被荀子(西元前3世紀)批評為「蔽於天而不知人」。但是,荀子自己也確信,要對世界有真正的認識,必須先明於天人之分。
最遲到了西元前2世紀,天人相對的概念已牢牢確立,成為基本思考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陰陽宇宙論廣為傳播所致,尤以董仲舒(西元前2世紀)的影響為最。綜觀整個漢代(前206-220),天道與人事互為影響的看法,無論在上層文化還是庶民文化中都幾近風靡一時。在這種看法蔚然成風的情況下,太史公司馬遷(前145-前90?)窮畢生精力撰著《史記》,並自言目的是為了「究天人之際」。自此他成為後世史家仿效的楷模。唐代史家劉知幾(661-721)被同時代人譽為「學際天人」,就不是單純的巧合。到了18世紀,堪稱中國歷代史家中最具哲學思維的章學誠(1738-1801)也自豪地說,他的撰述旨在「綱紀天人,推明大道」。在這兩個例子中,都可清晰看到司馬遷的影響。
天人相對的觀念也淋漓盡致地體現在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之中。何晏(卒於西元249年)和王弼時相過從並樂在其中,因為他們彼此「可與言天人之際」。不用說,「天理」和「人欲」之間該如何分野,衍生了錯綜複雜的哲學問題,構成了宋明理學的核心。這點已是眾所周知,無須在此贅言。
「天人合一」這個概念歷久彌新,直到20世紀仍然縈繞在中國人的心頭。在20世紀40年代初,鑽研西方哲學的中國哲學家金岳霖(1895-1984)和馮友蘭不約而同地以各自的方法在哲學範疇上發展天人合一概念,此舉的目的明顯是要探討天人合一概念對於現代世界是否有其意義。金岳霖在比較中西哲學時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最突出的特點」。他充分意識到這一概念之包羅廣泛和複雜,但他傾向於將之解釋為「人與自然的同一」,而且把它與西方盛行的「征服自然」思想相對照 。另一方面,馮友蘭將此概念用於他所稱的「天地境界」(即他所認為的最理想的生活境界)之上。用他的話說:「在這種最高的生活境界中的人的最高成就,是與宇宙合一,而人自身與宇宙合一時,人也就否定理智。」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學術界就天人合一概念聚訟紛紜。在這個至今未輟的論辯中,人們圍繞這一古典概念的確切意思提出了諸多問題。有些人承襲金岳霖的解釋,但把重點放在以下難題上:人如何在與自然達致和諧合一的同時,又把科學和技術納入中國文化之中。另一派人則重複馮友蘭形而上學的、道德的或宗教的關注,但比他更進一步,從這個概念中擷取出對於中國精神的現代甚至後現代意義。對於這一辯論的細節在此無須深究,我提及它僅僅是要顯示,天人合一並非一個僅能引起人們歷史興趣的陳舊僵化概念而已。反之,它仍然是中國人思維的核心部分。事實上,它或許是打開通往中國精神世界的其中一扇門的鑰匙。然而,身為歷史學家不會只滿足於猜測臆想。以下我將論述天人合一觀念的源起和發展,並嘗試解釋它如何演變為中國思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我所用的方法以歷史追溯為主。
讓我從介紹上古的「絕地天通」神話開始。簡單說來,這個傳說講,古代人與神不相混雜。人敬神而又安守其在宇宙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神不時透過巫覡降臨人間。結果,神和人的世界相隔分開。神賜福世人,又接受人的供奉,人間禍災不至。其後衰落的時代來臨,民神雜糅,以往祭祀是由巫覡進行的,現在則家家為「巫史」。結果,民匱於祀,神狎民則,禍災遝至。聖王顓頊(傳說生活於西元前25世紀)受命於上天而加以干預,最後為重新整頓宇宙秩序而絕地天通 。
這個神話有多重意義,可以用不同方法來詮釋。在這裡我只想提出一個簡單的歷史觀察,它或可證明,在遠古中國,只有帝王可以與上天直接交通。根據傳統,在夏、商、周三代,祭天是帝王獨有的特權。封建諸侯有權在他們的領地祭地,但不可祭天。換句話說,「天人合一」只限於天子,而現代的一種看法認為,天子也就是首巫。
但是,這樣不免出現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本文一開始提出的 「天人合一」概念,是建立在與「絕地天通」神話完全相反的假設上的。它假定世界上所有的人原則上都可以和天溝通。誠然,在這兩個觀念中,「天」的涵義稍有不同。儘管如此,應這樣說,就這兩者的結構而言,我們應該視它們為互相扞格的。人人可以獨自與天溝通而無須巫覡幫助,這一觀念明顯指出,天人交通不再是帝王的專利。個人式的天人合一最早只可追溯至西元前6世紀(下文會說到),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它的發展至少部分是對多個世紀以來一直支配中國人思想的古代「絕地天通」傳說的有意識的響應。現在我就要論述中國思想的這一重要發展。
《莊子‧天下篇》的作者(也許是莊子的後世門徒),扼腕痛惜地描述原本完整一體的「道」的「裂」。他把道術之「裂」與中國「百家之學」的興起聯繫起來,認為各家學說「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因此,「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這一對古代中國首次哲學運動的描述中,作者把原來莊子所說的一則寓言化為歷史,這則寓言是這樣的: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應帝王》,Watson, p. 97)
我相信,上引〈天下篇〉所記述的歷史,是脫胎於莊子的這一寓言。因為兩者皆以人的五官作喻,清楚顯示莊子筆下的渾沌,是代表原來合一的道體。莊子寫下渾沌之死這則著名寓言時,心中必定想著這場今天史家視為「迅速」(儵)和「突然」(忽)發生的中國古代精神啟蒙運動。老子、孔子和墨子(他們僅是中國哲學史上眾多聖哲中的三位佼佼者)均在西元前6世紀和前5世紀出現。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場突如其來的精神啟蒙運動,以及怎樣把它和天人之分聯繫起來。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先以一種比較的視野來加以考察,因為中國並非古代世界唯一經歷這種啟蒙的文明。四十年多前,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指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事實,在西元前一千年內,即他所稱的軸心時期,包括中國、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臘的幾個高級文明都相繼經歷了精神上的「突破」,這種突破的形式或見諸哲學思辨,或體現在後神話時代的宗教想像,或反映在一種集道德、哲學、宗教於一身的混合觀念,中國屬於最後一種情況。軸心時期各文明的突破,顯然是各自獨立發生而沒有互相影響的。我們從中可以推論的是,當文明或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經歷一個共同的精神覺醒過程。雅斯貝爾斯進而指出,這種軸心突破的終極意義在於,一個文明的形態和性質,就是在這個階段定型和確立的 。在過去幾十年間,對於雅斯貝爾斯的「突破說」聚訟紛紜,而大家都普遍認為,孔子時期中國的思想巨變可理解為軸心時期的大突破之一。這樣,更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和及其門徒早已領悟了他們參與掀起的這場精神運動的歷史意義。「渾沌之死」或「道術將為天下裂」確實切中了「軸心突破」概念的宏旨。
對於軸心突破的特徵,可以用許多不同方法來描述。考慮到本文討論的目的,我選擇將它視為中國的首次精神覺醒,而其核心包括一個原初的超越。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指出的,這一「超越」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批判性、自省性的詰問,也是觀照超越世界的一種新方式」 。之所以說這種超越是「原初的」,因為它大體上自此即成為貫穿整個傳統時期中國思維的核心特徵。
學者大都同意,軸心突破是現實世界和超越世界二元分立出現的直接導因。超越的精義就在於,現實世界被超越了,但沒有被揚棄。然而,另一方面,超越的確切形態、經驗內容和歷史過程,則因不同文明而迥然相異,因為它們所依憑的是突破發生前各自獨有的文化基礎。接下來我要談一下中國超越的獨特性。有些西方學者已察覺到,相比於其他文明,中國的突破是「最不激烈」 或「最為保守」的 。我認為這一判斷是有道理的。對於這種情況可以有許多解釋。其中之一是中國人注重歷史延續性,這在軸心時期及以後都是如此。儘管發生了「突破」,但它並非跟突破前的傳統完全決裂。另一種解釋是探究現實世界和彼岸世界間的關係。在中國的突破中,現實和超越這兩個世界並沒有明確的分野。早期的中國哲學思想不曾提出過柏拉圖的想法,即現實世界是一個不可見的永恒世界的不完整的摹本。像基督教那種把上帝的國度和人間截然二分的看法,在中國宗教傳統裡也付諸闕如。在芸芸中國古典思想中,我們也找不到與近似於早期佛教那種認為此世是虛幻和無價值的極度消極思想。軸心時期中國出現了「道」的概念,它是超越世界的象徵,與日常生活的現實世界成一對照。無論儒家或道家都是如此。對這兩家來說,道都是不遠離於日常生活的。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也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之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這裡強調道是尋常人都可以接觸的。但老子和莊子都認為,道是與現實世界相對的生活的「更高境界」。雖然一般來說,道家對此世和彼世的分野較儒家明確,但道家也沒有把這兩個世界作截然二分。因此,當有人向莊子問道:「所謂道,惡乎在?」他就回答:「無所不在。」他向提問者進一步解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莊子‧知北遊》)莊子的弟子們曾這樣描述他: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莊子‧天下》,Watson, p. 373)
換句話說,莊子活在「此世」,但靈魂卻同時徜徉於「彼世」。
至此我想證明的是,軸心時期的中國也發展出超越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二元分立。但中國的這種二元分立跟其他文明不大一樣,因為它沒有截然區分這兩個世界。套用中國的典型說法,這兩個世界的關係是「不即不離」的。那些慣於把事物截然二分的人,也許會覺得這種說法難於索解,但它確實是中國超越的最重要特色。本文之所以題為「天人之際」,也是要點出這種獨特的中國式思維。現在我將更進一步,以「內向超越」來解釋中國的事例。
要理解中國超越的內向性,不能不略述古代中國發生的軸心突破的歷史過程。有人指出,希臘的突破是以荷馬史詩中的神話世界為背景,以色列的突破繼起於舊約聖經和摩西故事的宗教淵源,而印度的突破則建基在悠久的吠陀經典傳統。那麼,中國突破的發生背景是什麼呢?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綿延夏、商、周三代的禮樂傳統。這種禮樂傳統自夏以來即體現在統治階層的生活方式之中。據孔子講,禮樂傳統是歷經夏、商、周三代損益而一脈相承的(《論語‧為政》)。孔子這一論斷基本上已得到新近考古發現的證實,除了夏代尚待考古發掘的進一步證明外,周代傳統繼承於殷商已無異議。然而,逮至孔子時代,這種禮樂秩序已幾近全面崩壞,這主要是由於當時的王侯貴族僭越禮制所致。這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了歷史上重大的突破,往往有一個崩壞的階段為之先導。
接著,我們必須從超越的角度著眼,將軸心突破與禮崩樂壞兩相參合,建立兩者的歷史聯繫。為免本文過於拖遝,這裡只指出禮樂傳統是軸心突破時期中國超越的出發點。孔子超越現存禮樂儀式的中心思想之一,是尋找「禮之本」。眾所周知,他將「仁」解釋為禮的精神內核,至此他的尋找之旅告一段落。因此,他的「禮樂」觀念煥然一新,與以往認為禮是源於人類模仿「天之經」、「地之義」這種神聖模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的傳統看法大相徑庭。他不是向天地這些外在事物去尋找「禮之本」,而是求諸人的內心。同樣地,繼孔子之後,墨家和道家的突破也把改革禮樂傳統視為要務。墨子認為傳自遠古的禮樂已日益繁縟,正在不可逆轉地趨向淪落。他更猛烈地批評孔子的改革未能徹底根除在周代發展起來的所有現存禮樂制度,因此他主張返回簡樸的夏禮。至於道家,他們可能是先秦諸子中突破最激進的。因為較諸其他學派,道家對現實世界和彼岸世界所作的分野更為確切清晰。尤其是莊子,他是中國傳統思想中彼岸世界觀念的主要源泉。但必須強調的是,道家也是針對傳統禮樂而提出其理論的。《道德經》第三十八章也明言:「禮」是「亂之首」,意謂原始的道體正在逐漸衰落倒退。另一方面,莊子也教我們如何從忘掉禮樂開始,從而達到「坐忘」來超越現實世界,回歸大道(Watson, p. 90) 。所以,《道德經》所論的「失道」過程,與《莊子》所說的「得道」歷程,恰成一往一復。莊子雖然把所有現有的禮樂制度斥為無意義的人為事物,但他並沒有提出要揚棄禮樂,甚至還提及「禮意」。不過,顯然在他看來,對著已過世的妻子鼓盆而歌,是比哭哭啼啼更有意義的喪禮(《莊子‧至樂》)。以上三個例子說明儒、墨和道三家都傾向賦予現有的禮樂以新解,而不是將之棄絕。韋伯認為這點「極其重要」 。我可以大膽指出,這種賦予新解而非棄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助於解釋中國何以在所有軸心突破中是「最保守」和「最不激烈」的。
最後,讓我們從「天人合一」概念的變化來觀照內向超越。在人們普遍相信「絕地天通」神話的時代,只有帝王在巫覡幫助下能直接與天溝通。因此,「天人合一」也成了帝王的禁臠。帝王受命於天,是地上所有人的唯一代表。中國軸心突破是作為一種精神革命而展開的,它反對王室壟斷與天的聯繫。
雅斯貝爾斯在進一步概括軸心突破的特徵時,特別指出兩個重要特點:首先,這場突破是人類作為個人的精神覺醒和解放,他們首次「敢於依靠個人自身」踏上一場精神上的旅程,透過這一旅程他們不但要超越自己,還要超越現實世界;第二,在這種突破中,精神上業已覺醒和解放的個人,似乎有必要把他在現世的存在,有意義地聯繫到「存在的整體」(the whole of Being)。
在我看來,這種概括提出了一個比較視野來觀照軸心突破時期中國「天人合一」概念的個人化轉向。以「天命」觀念為例。孔子說「五十知天命」(《論語‧為政篇》),又說君子「畏天命」(《論語‧季氏篇》)。劉殿爵在他的〈英譯《論語》導論〉中講得很對:「到孔子之時,關於天命的惟一拓展就是不再局限於君主。每個人都受命於天以修其德,踐天命就是他的職責。」*小野澤精一在1978年有相似的發現。他把天命概念與金文中的「心」和「德」(「心」是「德」字的組成部分之一)聯繫起來,指出天命概念在孔子時代經歷了微妙的變化,即「從支撐王朝政治,天降之物向個人方面作為宿於心中物的轉換」 。由此,由於每個人都受命於天,經過長期的「絕地天通」後,人和天的直接聯繫再次建立起來。因此,從孔子的說話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他彷彿經常與天有著個人的接觸,例如他說過:「天生德於予。」(《論語‧述而篇》)又說:「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篇》)這些說話清楚顯示,身為個人的孔子能夠直接和天溝通。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借孔子得意弟子顏回之口,說出以下一段話: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莊子‧人間世》,Watson, p. 56)
莊子在此以他獨有的方式來表達道家的激進觀念:借著「內直」(即人心中的「德」),人人皆可為天子。莊子憑著這種獨樹一幟的看法,推翻了帝王自認為只有他才是天子的想法。只要保持內心誠直,則人人都能成為天子,從而也就能與天直接溝通。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天人合一的個人化轉向,怎樣一方面使得天人之間的直接交通得以重開;另一方面又使個人得到精神上的覺醒和解放。而且,無論是小野澤精一的研究,抑或上引《莊子》的那段話,似乎都指出溝通的重點在於人的內心。現在讓我們探討內向超越的問題。
整個天人合一觀念的核心就是天人之間的交通。所以首先我們必須問:在前軸心時期,帝王是如何和天溝通的?這個問題把我們的目光引領到禮樂的溝通作用。上文提到,帝王一直依靠巫覡的協助來與天溝通。巫覡是深得帝王信任的宗教官員,他們自稱唯有他們才能與天接觸,其方式有二:或是代表帝王向天上神、帝王的先祖尋求指引,或是請神靈降臨人間。但是,要做到這點,他們需要借著各種祭器進行一些儀式。很大程度上,軸心突破是反對禮樂儀式中的巫術成分的。我們也由此來理解孔子對禮樂的重新詮釋。孔子身為業已精神覺醒和解放了的思想家,不需要巫為中介就可以直接與天聯繫。因此,從前被認為是由巫壟斷的強大溝通力量,現在已賦予了「仁」,即「禮」的精神內核,而「仁」只能求諸人的內心。到了西元前4世紀,隨著新的氣化宇宙論出現,這個內在轉向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種新的宇宙論認為,天地之間充塞著氣。氣是不住流動的,一旦二氣相分,陰陽初判,世界也就形成。大體來說,氣分兩種,清氣輕揚而成天,濁氣凝滯而為地。人受二氣之調和,其體為濁氣所形成,其心則為精氣之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