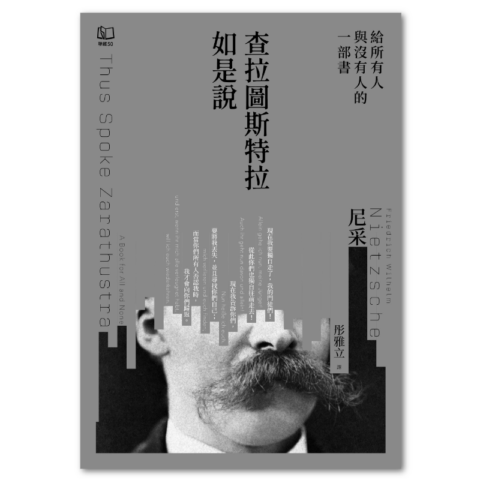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
出版日期:2013-07-03
作者:何炳棣
整理:范毅軍、何漢威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544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860369007
系列:院士叢書
已售完
何炳棣先生退休二十年研究之大成──《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
何炳棣先生初治近代英國農經史,再入明清人口財政史,
最後總結上古中國農業文明起源;
自19世紀始,上溯至西元前五千年終,
在中國史學界遍尋不出第二人。
本書為思想制度史專著,何炳棣先生畢生「久久不跳進思想史」,因為他認為「如果自青年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寫作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著地。」
由此可見何炳棣先生治學,一向用「紮硬寨、打死仗」的方法,正面「攻堅」歷史學界的重大議題。其「攻堅」利器就是「考據」,以考據為功的思想史,不同於「當代大多數思想史家所關心的,往往僅是對古人哲學觀念的現代詮釋,甚或「出脫」及「美化」,置兩千年政治制度、經濟、社會、深層意識的「阻力」於不顧。
哲學大師馮友蘭曾說:「敘述─時代─民族之歷史而不及其哲學,則如『畫龍不點睛』。」何炳棣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窮究中國明清至上古農經制度,告誡後學「不畫龍身,龍睛從何點起?」龍身指的是政經社會制度;龍睛則是文哲思想體系。何炳棣先生在退休二十年間,「一往直前,義無反顧」,「踏進先秦思想、制度、宗教、文化的古原野」,積四十年畫「龍身」的經驗,點五千年中華文哲思想的「龍睛」,本書可說是何炳棣先生畢生學術的畫龍點睛之作。
作者:何炳棣
浙江金華人。1917年生於天津,民國101年卒於加州。先生於民國23年入清華大學,一窺中西史哲學門徑。民國27年,再入燕京大學,為歷史系研究生。民國32年再試第六屆清華庚款留美公費考試,取魁西洋史;於民國34年始赴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留哥期間,師從英史巨擘John Brebner,研修近代英國農業經濟史。民國37年完成博士候選人口試,赴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講師;隔三年,獲得哥大史學博士學位。民國41年,先生轉治國史,鑽研明清人口財稅史,民國51年,轉任芝加哥大學正教授,主授明清史,研究視野回溯至上古、中古、甚至考古,研究興趣更趨多元,分治城市史、文化史、農業史。先生治史之廣、研究之精,於民國55年,獲選中央研究院第六屆人文組院士。更於民國63年當選亞洲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副會長,隔年任首任華裔會長。民國76年,先生致休,轉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訪問教授;民國80年再休,閒居爾灣左近,再拓先秦思想、制度、宗教研究。致休二十餘年,講學筆耕不輟。先生畢生未仕,窮究國史,秉性狷介,不染迎合阿諛惡習;其《讀史閱世六十年》足為後世立身治史借鑑。
整理:范毅軍
范毅軍。美國Stanford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計畫執行秘書。
專長:明清與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歷史地理、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整理:何漢威
第一章 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
第二章 商周奴隸社會說糾謬:兼論「亞細亞生產方式」說
第三章 「天」與「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
第四章 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
第五章 原禮
第六章 「克己復禮」真詮
第七章 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
第八章 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變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的論證
第九章 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
第十章 從《莊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關懷
第十一章 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
第十二章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
第十三章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
第十四章 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附錄 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
後記(何漢威)
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
一、物質基礎:村落定居農業
華夏人本主義文化的發祥地是華北黃土高原與毗鄰平原的地區。產生這人本主義文化的物質基礎是自始即能自我延續的村落定居農業。為正確了解這一基本史實,我們必須首先澄清中外相關多學科的一個共同錯覺:原始農耕一般都是「游耕制」。實際上這不過是一個假定,而且是以某類地區特殊的歷史經驗硬行作為普遍歷史經驗的大膽假定。他們共同的理由是:原始農夫不懂施肥,而土地的肥力因耕作而遞減,在當時土曠人稀的條件下,農人隨時都得實行休耕,並同時非開闢新耕地不可。他們認為開闢新耕地最直截了當的辦法是砍伐及焚燒地面上的植被,這就形成了所謂的「砍燒法」,也就是「游耕制」。
最早討論黃土物理及化學性能與農作方式關係的,是本世紀初美國地質學家和中亞考古發掘者龐波里(Raphael Pumpelly)。針對著世界最大、最典型的黃土區,也就是華北黃土區,他曾作以下的觀察和綜述:
它(黃土)的肥力似乎是無窮無竭。這種性能,正如著名德國地質學家李希特浩芬(Ferdinand Richthofen)所指明,一是由於它的深度和土質的均勻﹔一是由於土層中累年堆積、業已腐爛了的植物殘體,雨後通過毛細管作用,將土壤中的各種礦物質吸引到地面﹔一是由於從(亞歐大陸)內地風沙不時仍在形成新的堆積。它「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的性能可從這一事實得到證明:在中國遼闊的黃土地帶,幾千年來農作物幾乎不靠人工施肥都可年復一年地種植。正是在這類土壤之上,稠密的人口往往繼續不斷地生長到它強大支持生命能力的極限。
筆者從60年代末即懷疑游耕制說真能應用於中國黃土地帶。為謹慎計,我於1970年夏天在電話中請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舉世公認的大麥源流的權威伊利諾州立大學哈蘭(Jack R.Harlan)教授,根據他對華北古自然環境、各種農作物起源及地理分布的專識,再就比較原始農耕的觀點,坦白地對華北最早耕作方式作一臆測。他毫不遲疑地作了以下的答覆:(1)華北地區最早的耕作方式決不是一般所謂的砍燒法或游耕制,因為經典的游耕制一般需要每年實耕八倍的土地:換言之,土地耕作一年之後要休耕七年之久,肥力才能恢復。(2)華北遠古農夫大概最多需要每年實耕三倍的土地,內中有些可以一年耕作兩年休耕,有些可以連續兩年耕作一年休耕,性能較好的黃土可以連年耕作而不需要休耕。(3)砍燒法或游耕制一般限於熱帶及多雨地帶,這類地區農業的樞紐問題是肥力遞減,而黃土地區農業的樞紐問題不是肥力遞減而是如何保持土壤中的水分。應該强調的是,哈蘭所提的第三點是他個人獨有的論斷,不是一般考古、人類、歷史、經濟學家們所能洞悉的。聽他講完之後,我才告訴他以上的臆測與中國古代文獻所述不謀而合。
兩三天後,我把哈蘭上述幾點推斷在電話中向畢都(George W.Beadle)博士(1958年諾貝爾獎得主、分子生物學家、芝加哥大學將退休的校長)作一簡報,並說明中國古代文獻確是反映出一個最多三年的輪耕週期,內中的確包括不須休耕、三年中休耕一年或兩年的土地,但第一年清理平整了的土地照例不馬上播種,要到次年才播種。
畢都博士立即作了科學解釋:由於初墾土地地表雜草等野生植物雖已經人工清除,土塊雖已經翻掘平整,但土壤內仍有大量植物殘體沒有腐爛,如立即播種收穫一定很少。這是因為土壤中植物殘體在逐步腐爛過程中所生的氮素,極大部分都被土壤中多種微生物所吸取,種籽所能得到的氮素非常有限。但是,如果第一年僅僅維持地面的平整而不立即播種,第二年開始播種的時候,土壤中原有的植物殘體已經徹底變成了富氮的腐質,此時微生物不但不再吸取氮素,並且放出大量的氮素來滋養種籽,因此第二年的單位產量必然很高。他笑著說他本是以小麥牛肉著名的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農夫」,深明此中道理。他相信聰明的遠古華北農夫從實際觀察和經驗中很自然地就會實施第一年平整土地暫緩播種的耕作體制。
以科學原理重建華北最早的農耕方式必須與我國古代文獻互相印證。古籍中所言耕作方式必須從「菑」、「新」、「畬」三個專詞意涵中去尋索。《爾雅.釋地》: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這清楚地說明一、二、三歲的田各有其專名,專名合起來就已反映出一個三年輪流休耕制。此三詞中「新」和「畬」比較易解:「新田者,耕之二歲強墟剛土漸成柔壤……畬者,田和柔也。」需要詳釋的是第一年的「菑」。「菑」的音和義都含有「殺」意。《尚書.大誥》:「厥父菑」,孔穎達《正義》:「……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詩經.小雅.大田》鄭玄注:「反草曰菑。」《爾雅.釋地》郭璞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曰菑。」「菑」的主要意義是使土壤中所有的植物殘體化為腐質。
「菑」是第一年待耕而未耕之田之義,在《尚書》及《詩經》中得到充分的證明。《尚書.大誥》:「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明明指出「菑」在播先。《詩經.周頌.臣工》:「如何新畬?於皇來牟。」極其明顯,小麥大麥只種在第二年的新田和第三年的畬田。
此外,《周禮》也有兩處述及周代授田通則。〈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地官司徒.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兩種概述稍有不同。後者上中下三等授田正額雖同是百畝,但萊(備休耕輪作之地)的授予原則仍與前者同樣反映一個最多三年週期的輪耕制。
科學與訓詁互證密合有如此者﹗
惟有自始即是自我延續的村落定居農業,才能合理地解釋華夏文明起源的三個事實,即何以距今7,000多年前一些早期新石器文化聚落的農業生產已達遠較想像為高的水平﹔何以渭水下游南岸與終南山麓間多條小河沿岸仰韶文化早期半坡類型文化聚落遺址──類皆具有房屋、窖穴、陶窰、墓地等組成部分──分布能如此密集﹔何以只有在累世生於茲、死於茲、葬於茲的最肥沃的黃土地帶才可能產生人類史上最高度發展的家(氏、宗)族制度和祖先崇拜。
二、氏族制度和祖先崇拜
構成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最主要的制度因素是氏族組織。最主要的信仰因素是祖先崇拜。制度和信仰本是一事的兩面,二者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無法分割的關係。事實上,人類學理論也認為只有將二者一起研究才能收相得益彰之效。
我國新石器時代以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3000年)分布最廣、延續最久、文化堆積最厚、已發現遺址最多。內中保存最好的是西安附近的半坡和臨潼姜寨等聚落遺址。對這類型聚落布局的中心意義,資深考古學家蘇秉琦有代表性的看法:
半坡、姜寨那種環壕大型居址,其中以大房子為中心,小房子在其周圍所體現的氏族團結向心的精神,以及居址之外有排列較整齊的氏族墓地,……說明氏族制度發展到了頂點。
仰韶聚落布局中最能反映宗教信仰的是墓葬方式。誠如著名《西安半坡》專刊撰者石興邦所綜述,在已經系統發掘的仰韶遺址中,一般成人屍體有條不紊的排列方式反映每個家族或個人在氏族中最後都有應佔的歸宿和位置。屍體大都頭向西方或西北方。墓葬方向可以認為是「祖先崇拜和靈魂信仰的表現之一」,因為「墓葬方向的選擇和決定,在任何一個民族都是相當嚴肅而慎重的」。數量上次於仰身葬的二次葬似乎也反映當時的信仰:要等到血肉腐朽屍骨正式埋葬之後,死者才能進入鬼魂世界。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小孩死後一般都舉行所謂的「瓮棺葬」,這類陶瓮通常都放在居住區,不葬在墓地:瓮頂留一小圓孔以供靈魂出入,繼續承受母親關愛之用。
近年仰韶精神文化研究有多方面突破性的詮釋。首先,半坡彩陶中最重要的魚紋飾已不能再像60年代那樣釋為圖騰了。因為半坡和姜寨文化上確有血肉的聯繫,兩處彩陶中共有魚、蛙、鳥、鹿多種動物紋飾﹔此外,兩處遺址都發現大量多樣的捕魚工具,說明魚是當時人們經常的美食。這些都與圖騰理論衝突。比較合理的新解釋是:魚,特別是抽象的雙魚,是女陰崇拜的表現﹔而姜寨那種體內充滿卵子的蛙的圖案,也是象徵生殖能力的崇拜。早在1946年,聞一多先生在遇難前數月撰就的〈說魚〉一文裏已經闡發魚在中國古代文學裏一向是「匹偶」、「情侶」的隱語,因為「在原始人類的觀念裏,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傳種是婚姻的唯一目的,……而魚是繁殖力最強的一種生物」。
生殖能力的崇拜完成了祖先崇拜必具的三個時式:過去、現在、未來。
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早期45號墓發現三組以蚌殼擺塑的圖案。古文字和天文史家馮時具有說服力地說明第一組墓主人兩旁的龍虎圖案是後來發展完成的二十八宿「四陸」中的「二陸」──蒼龍和白虎;墓主屍體下邊移入的兩根脛骨代表「北斗」。墓形反映當時已有天圓地方的說法。總之,第一組蚌殼圖案可以認為是二十八宿宇宙觀的濫觴。張光直先生提出第三組圖案中的龍虎鹿正符合《道藏》中保存下來的原始道士的「三蹻」──巫師騎乘上天下地與鬼神交通的媒介﹔並認為這樣早的巫覡宗教(或稱薩滿教Shamanism)證據,「對世界原始宗教史的研究上有無匹的重要性」。
西水坡45號墓中驚人的天文知識和具有高度魔術幻想力巫覡宗教的結合,強有力地說明該墓的主人已不是平常的氏族長,甚至也不僅是張先生認為的巫師,而是─部落酋長般的人物了。夏代的建立者大禹不就是以「巫步」聞名於後世、三代權位最高的「王」還不一直兼有大巫或大司祭的職能嗎?西水坡的「三蹻」也正說明半坡、姜寨同期文化裏亦有巫覡的存在。那種由圓形黑白(陰陽)人面向頭頂、兩耳、兩頰外射的五條或三條三角形魚飾的神秘圖案,還不是巫師的有力證據嗎?半坡、姜寨相隔50公里,而半坡陶器上的字符卻出現於150公里外郃陽莘野村的同期仰韶文化遺址。這樣長的宗教、文化交流半徑似乎在說明這已不僅是氏族間,而是部落間的交流了。
仰韶人民雖然崇拜多種自然神祇,但由於聚落布局中居住區和墓地同是組成部分,生著累世相信不時可獲逝者靈魂的祐護,而逝者又需要生者不時祭薦,祖先崇拜很可能在整個宗教信仰中已佔相當大的比重。
上承仰韶、下啟三代的龍山時代(大約公元前3000-2000年),出現了一系列多姿多采的區域性文化。它們在經濟、社會、政治、宗教、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發展雖各有各自的特色和步伐,而且華夏中原地區的文化在此時期並非處處領先,但各文化間千年之久的雙向吸收和反饋卻使它們大致朝向同一方向演進:祖先的神靈隨著部落的擴展漸漸變成部族至高的保護神:政治權威和等級社會的出現加速了氏族制度的蛻變。
最能顯示龍山時代多方面演變的是玉器群和禮器群。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2200年)的大本營遠在浙西太湖以南,其玉器群最有代表性。從公元前第三千紀前半即已有象徵軍事統轄權的玉鉞和宗教重器玉琮的出現。更值得注意的是玉製神獸、神鳥、獸面或獸身的「神人」和「神徽」。這些「神人獸面紋的普及和規範化,說明在其通行的地域內,良渚文化的社會結構和原始信仰,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統一性,對至高無上的神人的崇拜,實際上是從信仰意識方面,統治者起到了維護獨尊地位的作用」。稍後遼西紅山文化中也具有地域特色的玉器群,再稍遲山東海岱區系的玉業也開始形成獨特色格,「並給予三代玉器以深遠的具體的影響」。
陶製禮器群以山西襄汾陶寺類型最富代表性。禮器中除為設奠用的桌子是木製的,其餘陶製的各種炊器、食器、酒器、樂器等類不但式樣功用各各不同,而且嚴格地反映這些隨葬品墓主人身分等級的不同。「從隨葬品組合的角度看,後來商周貴族使用的禮、樂器在公元前第三千紀中葉的陶寺早期已初具規模。……墓中的禮器和牲體已成為墓主身前權力和地位的標誌。……在形成三代禮制的過程中,中原處於核心地位」。
山東龍山文化研究在80年代有重大的突破。壽光邊線王城發現邊長240米,面積57,000平方米的外城和配套較小的內城,並發現祭奠所用的豬牲、犬牲與人牲。而城子崖的城東西約430米,南北最長530米,面積大約200,000平方米(即1/5平方公里、50英畝、相當公元後十三世紀英國首都倫敦城的1/6)。高廣仁教授認為這已不是單純軍事防禦性的小城堡,而已是「具有永久性統治權力中心的都邑性質」。這樣規模的城和十米寬夯築牆體,「除非靠大量的強制勞役,否則是難以完成的」。此外,泗水尹家城和臨朐朱封大墓內的隨葬品說明當時「社會上財富分配不均,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
綜結以上,龍山時期的主要考古發現說明當時氏族內部已有社會分化,造成了貧富分配不均和等級化的身分制度萌芽﹔宗教方面,祖先崇拜已提升到以部族至高祖宗神為對象。這些現象與傳說中炎、黃大部族同盟,英雄魅力式領袖人物的出現是大體吻合的。
有關夏代的考古資料仍在多方慎重鑒定中。從君主世襲的觀點看,夏不愧被稱為朝代。但「所謂的夏朝,實際上是以夏后氏為盟主,由眾多族邦組成的族邦聯盟」。《左傳.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呂氏春秋.用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古籍中所謂的諸侯和萬國,實際上是由眾多部族所構成的「邦邑」。筆者此處必須指出,極大多數中國古代史專家和考古學家所借用的古代希臘「城邦」(city states)一詞甚不妥當,容易引起錯覺。古代希臘polis一詞雖英譯作「城邦」,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原著的較慎重英譯往往作為community 「(政治)社群」。公元前第五、第四世紀的希臘城邦,除了雅典和科林斯(Corinth)外,商業都不發達,都是以農立國的。其首都的主要部分是宗教及政府建築,所以全國連首都也不是具有複雜經濟活動的「城市」。這種政治社群的最大特色是遵守法律,保持極嚴格的公民籍,所有公民都是成年男子,都有直接選舉、參政、充陪審、服兵役的權利與義務。雅典豐富的碑刻資料證明,不但最高長官按期由公民選舉,而且一般公民一生之中至少有一、兩次輪充官吏的機會。雅典這種草根民主政治共同體的本質、精神、意識,與夏商周的家有世襲的邦邑(patrimony)制確有基本的不同。
商代武丁以後的大量卜辭也顯示氏族邦邑林立的情況。已故丁山教授於40年代中曾對甲骨骨面、骨臼、甲冉、背甲等部位非占卜的刻辭紀事做了原創性的考釋和統計。這類卜辭記事包括為商王侍夜之「婦」的「氏」名、王畿內外人都為王守夜氏族之名及其人數等等。這些記事雖屬片面性質,而氏族之可確定者已達二百左右。因此,丁山做了兩個綜述:(1)「殷商後半期國家組織確以氏族為基礎。」(2)「商代所封建的氏族,都就其采地中心建築城邑,也可名之曰『城主政治』。」此說高明之處在用「城主」而不用「城邦」一詞,因為城邑及其郊野是「主」世襲私有的「產業」,「城主」就是諸侯,如果借用古代希臘城邦一詞就與「城主政治」實際的宗教、政治、制度、意識內涵大相逕庭了。
近年商周史研究方面可喜的成果之一是對有關商代姓、氏、宗族制度的一些錯覺的澄清。其中最重要的是糾正了王國維著名的「殷周制度論」的看法──殷周制度最基本的不同是殷商沒有西周式的宗法制度。實際上,武丁以後王位傳子的原則已經確定,大宗、小宗之分已相當明顯,類似西周的宗法制已經存在。換言之,西周的宗法制對商代的姓、氏、宗族制不是革命性的改變,而是系統化、強化和大面的推廣與應用。
宗教方面,商王雖祭祀天神、大神、昊天、上帝及日、月、風、雲、雨、雪、土地山川等自然神祇,但祖先崇拜在全部宗教信仰中確已取得壓倒的優勢。自然神祇的祭祀有一定的季節或日期,而商王室和王室貴族的「周祭」──由五種祀典組成的,輪番周而復始的對各世代祖妣的祭祀系統──卻是終年不斷地排滿了三十六旬,偶或還有必要排到三十七旬。這是祖先──廣義的「人」──已成為宗教體系重心的鐵證。
此外需要─提的是商人邈遠的始祖(帝)嚳隨著商部族力量的擴張和商王朝在中原威望的建立,已逐漸變成了人類的至上神。卜辭中稱之曰「帝」,但商人也稱之為「天」。據筆者年前的考證,海內外不少學人認為「帝」是商人的至上神,「天」是周人的至上神,「帝」與「天」對立的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事實上在周族文化落後、羽毛未豐、臣服事殷的期間已把商族的宗教、祖宗、至上神全部引進。這正說明何以周代文獻所述古代譜系裏商周兩族是同祖的。
西周才開始有了文獻,兩周金文又可與文獻不時互證,因此我們對周代宗教及氏族制度所知較史前和夏商兩代更為深廣。茲摘要分述如下。
(1)《禮記.祭統》:「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五經,提指吉、凶、賓、軍、嘉五類的禮,極大部分的祭祀都屬於吉禮,所以最為重要。近年一篇根據西周金文極具功力之作,一方面指出西周二十種祭禮之中,有十七種祭名與商代一致,這說明《論語.為政》:「周因於殷禮,其捐益可知也」是大體正確的﹔但另方面證明西周祭祖禮的重點和精神與商代有重要的不同:西周王室特別注重「近祖」。金文中最重要的「褅」禮晚周皆釋作「追遠尊先」始祖之祭,事實上不免有儒家猜測成分,與西周史實不符。西周金文中除了康王祭文、武、成王三代以外,其餘諸王所祭俱以祖考兩代為對象,並無追祭三代者。這種重心的轉移反映西周王室對祖先崇拜的想法越來越「現實」。
(2)周王室和各級貴族祭祖的宗教儀節也反映同一趨勢。《禮記.禮器》:「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尸」是受祭者的後嗣,在祭祀中扮演神(鬼,受祭者)的角色。由於周族的昭穆制,「尸」一般是受祭者的孫子。周初祭祀最主要的對象是文王,祭文王時嫡孫成王充「尸」。在全部儀節中,「尸」不但威儀棣棣地坐著受膜拜,並接受多道酒肉蔬穀的奉獻,「尸」還隨時都向與祭者招呼還禮,最後還通過專職通神司儀的「祝」,向子孫作以下這類嘏辭:「承致,多福無疆,於女(汝)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生性是浪漫詩人、藝術家,喜道家的超越、厭儒家的現實的聞一多先生,曾作以下的案語:
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在,乃是物質的存在。惟怕其不能「如在」,所以要設「尸」,以保證那「如在」的最高度的真實性。這態度可算執著到萬分,實際到萬分,也平庸到萬分了。
究竟是平庸還是智慧,尚有待深究。從立尸之禮和聞先生的案語,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人類史上從來沒有比古代華夏宗教更「人本」的了。
(3)討論周代宗教,不能不涉及宗廟制度。晚周文獻所述周代宗廟制度甚詳。《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廟。庶人祭於寢。」而《禮記.喪服小記》卻說:「天子五廟。」徵以西周諸王褅祀限於兩代近祖,我們有理由相信〈王制〉之說可能代表戰國儒家對古制的誇張。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很多的士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建造維修─廟。但對古制的誇張和整齊化並不影響我們對宗廟制度功用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周族遠祖古公亶父初建都城之時,最早動工的建築就是宮室和宗廟。周族強大克殷前後所營建的幾個京城和別都的設計,無一不以宗廟宮室為核心。開國的諸侯,始封的大夫,營建都城時亦無不如此。廟與寢前後接連,廟是祖先神靈之所居,寢是今王的經常住處。廟也稱為室,既是祭祀系統的中樞,又是朝覲、聘、喪、射、獻俘、賞錫臣僚、會合四方諸侯等重要典禮舉行的場所。一切軍國要政必告於廟。生者與逝者之間世代永存一種雙向關係:生者經常以祭祀方式向祖先報恩,祖先經常對後代庇祐降福。人鬼之間關係密切的程度是其他任何宗教所不能比擬的。
(4)周代宗廟制度,以至全部宗教、政治、社會體系,無一不是建築在宗法制度之上。周代宗廟制的淵源可以上溯到克商以前的遠祖公劉。《詩經.公劉》追述公劉率領部族遷居於豳,有「君之宗之」一語。《毛傳》曰:「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是正確的解釋。但這雛形的大宗之制在克商以前頗有例外。武王克商以後,原自西土的周族不斷向東發展,疆域和人民都有了革命性的擴張。但武王逝世後,成王幼,三監叛。各地區殷人勢力仍很強大。在嚴峻的情勢下,周族最高領袖周公急切需要一個對廣土眾民的高效統治網﹔組成每個商周貴族階層統治網的基本單位是宗法氏族,而樹立全域性宗法體制的先決條件是創建天子制度。雖然現存《尚書》自堯以降君主皆稱天子,筆者近年的考證,肯定了天子之稱始自成王。經過周公、召公周密的籌劃,在周公「保文武受命」的第七年春,在剛剛營建完成的洛邑舉行了一個重要的多民族大集會,充大司儀的召公重申商王紂失德遭天罰,天命轉移到成王。當這莊嚴儀式達到戲劇性的高峰時,召公才點出主題:「有王雖小,元子哉﹗」作為「天」之「元子」或嫡子,成王當然即是人間至尊的天子。
後記(節錄)
何漢威
本書所收十五篇論文,最早一篇〈北魏洛陽城郭規劃〉刊於1965年,最末一篇〈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完稿於2010年,前後歷時四十五年。十五篇論文中,除了〈北魏洛陽城郭規劃〉及〈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兩篇外,其他十三篇都發表或完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何院士二次榮退後近二十年間,這歷程充分反映了何院士治學取向的前後轉折,具有極不尋常的學術意義。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一文刊行前,何院士的研究對象側重於明、清,本文是他踏足於明、清課題以外的成果,也是去國多年後首篇以中文撰寫的學術論著。〈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則梓行於1978年。上述兩篇論文而外,其他十三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或取徑都與先前的研撰,不大一樣。除〈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一文外,其他十二篇論文探討重點明顯聚焦於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的思想及制度等領域。
何院士在其教研生涯的頭五十年間,盡量避免涉足思想史領域的主要考量是:如自青年階段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對部份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他也無法接受;他認為這些思想史家學問上「思考之單軌與見解之偏頗」,甚至「不斷地以自己的新義詮釋古書」,「語境跳躍」,「專找『歧出之義』作為突破口而任意大轉其彎的論證方式」,以及因堅持發揚儒家「原來理想所具備的正面價值與方向」,而無視或避免討論儒家思想中的負面影響及作用,對儒家思想內涵往往過分「美化」、「淨化」,甚至「宗教化」。在芝加哥大學退休前十年,何院士面對各種困頓,開始自修西方經典哲學及當代哲學分析方法,並孜孜埋首於中國古代經典及其注釋,不斷思索,以期對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方面作出原創性的貢獻,並對部分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及著作予以嚴肅的批判。從1991年起,他便毅然跳進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等領域而義無反顧;針對上述的不正學風,〈「克己復禮」真詮─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一文,既為何院士進軍中國古代思想史領域吹起戰鬥號角,形成一股阻嚇力量,對學界歪風迎頭痛擊,也為接踵而來他所撰寫的多篇饒富原創性的考證論文掀起序幕。
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何院士的論文及專著俱以英文發表;他的不少重要而富開創性的論文,發表於歐、美第一流社科刊物,如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及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等,影響深遠,不以研治中國歷史者為限,而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及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二書更是明、清社會經濟史基石之作,不單在國史上,甚至在世界史上也極具重要意義;前書更是二十世紀華人人文社科方面唯一引起英國《倫敦泰晤士報》(1960年2月12日)主要社論論及的書籍,西方重要歷史及漢學期刊對該書的書評即多達二十餘篇。從去國直到〈北魏洛陽城規劃〉問世前,他沒有用中文撰寫過任何著作。向先秦思想及制度領域進軍的歷程中,何院士作出一個重大決定:這類研究的一系列論著只用中文撰寫。他的權衡是「生平主要英文著作在華語世界讀者有限(尤其是在大陸),更由於年事日高,自覺有節省精力的必要。──如果研究成果真有原創意義,遲早還是可以在西方漢學界產生影響的。」
作為大史學家,何院士並不以考證為滿足,蓋他堅持「考證是治史必要的方法與手段,治史最終目的是綜合。」唯就收進本書的相關論文所見,除〈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一文,基本上為大綜合及大詮釋之作外,其有關中國古代思想及制度的著作,與前期相較,明顯看出確實在考證方面著力尤多,其中〈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從張載的《西銘》談起〉一文,他更毫不諱言是「采取生平罕用的大題小作法。」何院士強調考證的基本原則及方法繫於常識和邏輯,突破性考證「有時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與擴展考證視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平素多維平衡思考的習慣。」事實上,何院士對多樣史料的嚴格考證、甄別,以及平衡合理的運用,無不充分反映於書中相關論文中。
何院士早期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以幾近竭澤而漁蒐羅史料見長,取徑較偏重於宏觀綜合。他完成博士論文後,於1954年發表的第一篇中國社會經濟史論文〈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即引用罕見乾隆《兩淮鹽法志》中的〈成本冊〉及鹽政高恒的私人文件,在研撰《明代以降中國人口研究》及《明清社會史論》時,數年間翻遍北美各大圖書館所藏近四千種方志,並盡力搜集登科錄、同年齒錄近百種。單是玉蜀黍一項,〈美洲作物〉一文中所列舉的俗名便多達65個,就是何院士從哈佛燕京圖書所藏近三千種方志中爬梳所得的成果。在中國大陸上世紀九十年代大規模從國內外翻印各種珍稀的史料前,何院士所用的原始史料,不少為海內外難得一見的孤本秘笈。近時的先秦及古代史撰著,雖受益於近三十年來山東臨沂出土的大量兵書、殘簡,以及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帛書老子》和其他古籍的發現,但史料方面主要還是取資於每人都能用到的材料。難得的是,何院士卻說出絕大多數學者不能說的話,發前人之所未發,難度比前期研究明、清史時更高,唯成果及業績則不遑多讓,因這類課題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並不取決於史料蒐集的多寡珍稀,而主要取決於方法與思路。
何院士決非尋常的歷史學家。他一向以選題攻堅,享譽學林,力主研究大題目,解決基本大問題,不屑作二流題目,認為浪費時間及精力。在人文歷史領域內,連續鑽研基本大課題的難度甚高,但何院士在其漫長而卓越的學術生涯中,再三向高難度挑戰,將國史研究帶進一個累累碩果的紀元,對重新描繪歷史面貌貢獻良多。本書所收論文中,北魏洛陽城是中古史第一等的課題;美洲作物的討論對象,就是中國近千年以降,開始於十六世紀,美洲四種農作物,花生、甘藷、玉蜀黍及馬鈴薯傳入的第二個長期糧食生產的革命;老子年代是先秦思想史上困惑歷代學人的最為關鍵的大問題,也是最為頑強難攻的堡壘,即便是這基本性關鍵課題中所要澄清的枝節問題,如大史公司馬遷行年考,本身便是國史上的第一等專題。至於以堅實的新考古及文獻資料,闡明產生「宗法基因」文化的自然環境和物資基礎,初步證明恩格斯影響深遠的「家庭、私有制、國家」三大人類歷史演進階段,並不適用於古代中國,進而考釋華夏文化中「宗法基因」一直在傳統及當代中國發揮主宰的作用,被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已故講座教授鄒儻認為是何院士「近十五年來最重要的論文」的〈華夏人本主義文化〉一文,更是一等又一等的最上乘課題。
因當代學人對上述部份相關課題的著述堪稱汗牛充棟或已有相當業績,發前人未發之覆為極高難度的挑戰;何院士因早年學習西洋史時便已養成不同文化(intercultural)及歷時(diachronic)兩種比較的習慣,故能拓展歷史視野,啟發新思路,治學勇中有慎,勝義紛陳,探驪得珠,得出與眾不同的結論,每能帶給讀者意外的驚喜。難得的是他所討論的都是國史上的重大課題,卻能從大處著眼,掌握主要線索脈絡,而不拘泥於枝節,見樹不見林,致為史料淹没;他雖旁徵博引史料,但決不迷信史料,不單考釋史實,也考釋史料。他以合理適中的篇幅把紛亂如麻的史實清釐還原,深得史家要刪割愛之旨。可以這樣說,書中大多數論文,專就方法論批判古史研究中,默證的極端應用,誤以為治學態度嚴謹,而致方法失之偏頗的〈「天」與「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一文而外,事實上都是史學方法課程(特別是內考證部分)的理想實習資料,為後學指引迷津,好學深思者,定可從其論著中學到真正的史學方法。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文中,何院士縱橫交錯,先從比較觀點及世界史視野,直指唐代長安城垣所佔面積(逾三十方哩)遠大於西、東羅馬帝國兩個京城(羅馬及君士坦丁堡,各僅九方哩)及13世紀末倫敦(僅半方哩多),由此可推知直接影響唐代長安都城建置的北魏洛陽面積及規劃。這兩都城規模宏大,「不特在我國歷代帝都之上,且為工業革命前人類史上所僅見。」接著經歷時比較,從中國都市長期演變中,點出北魏洛陽城的中軸意義這一前人所忽略的重大發現:北魏洛陽坊里制主要特徵是四郭坊里之間的劃分大致以社會階級為依據,這種「寺署有別,四民異居」的規劃大有別於西漢長安宮室、衙署、市廛、民居雜處,正反映出兩個時代的社會觀念及現象;唐、宋以降,隨著經濟發展,階級身份日趨流動,汴京「里卷之間,第邸同閙市毗鄰,仕宦與庶萬間擦,身分行業區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遺意盡失。」故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Arthur F. Wright致函何院士,盛讚此文「考證細密,敘事有條有理,描寫洛都生活文筆生動。」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一文中,何院士對儒家學說的要旨作了嚴肅的新反思。對華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有更為深刻的體會及反思後,以張載〈西銘〉為視窗,上溯至《易傳》及董仲舒,旁及二程及朱熹等理學宗師,通過對史料的精讀及仔細推敲,盡可能以周密平衡的理性思維,加以考釋評估,得出與絕大多數當代思想家及新儒家截然不同的結論─「秦漢以降的儒家的宇宙本體論是宗法模式的」;張載〈西銘〉冠冕堂皇詞語的深層意義實質是為專制帝王的合法性作形而上的辯護。
書中所收一系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文中的一大特色為,既有微觀的細緻考證,復有宏觀的通識綜合,考證處處與綜合相結合。因涉及的都是基本大課題,何院士極重視論證的積累,務必搜羅大量多樣的相關史料作為基礎,決不以孤立證據立論。〈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一文中,他深入鑽研西漢官制後,重新鑒定《史記》與其他古籍內的相關數據,通過探索太史公父子的師承,抽絲剝繭地窮究老子諎糸,以解決這一撲溯千古,重要而棘手的課題;何院士並在細讀《史記‧太自公自序》後,敏銳地觀察到王國維極具影響力的〈太史公行年考〉論證的嚴重失當;司馬遷生年應為前135年,而非王氏所主張的前145年。筆者感到文中論述司馬談為其早慧愛子教育用心之苦古今罕見,相當程度上或為何院士對其尊人壽權先生為他所早期教育所擬定的方針的強烈感情投射。
在〈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及〈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辯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的論證〉兩篇論文中,通過文字、專詞、語義、稱謂、思想內涵、命題與反命題先後順序等多維度縝密論證,何院士得出先秦思想史研究中人所未言的結論,並為重新考訂、分析、權衡與界定先秦、兩漢政治哲學思想的「軸心」奠下堅實的基礎。何院士認定《孫子兵法》成書早於《論語》至少半個世紀,實為中國現存最古的私人著述;經《孫子兵法》、《老子》、早期的儒、墨兩家的多邊相互驗證,他發現《老子》在體用及思辨方法上都與《孫子》具有特殊的親緣關係:人類史上《孫子》是最先以「行為主義」心理學原則治國;淡化、緣飾《孫子》的坦白冷酷,愚民語句最為微妙成功者便是《老子》,輩份的正確定位應是《孫》為《老》祖。
值得注意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一文,是何院士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文字組主任劉雨合撰,也是何院士生平唯一與他人合撰的論著。何院士一向認為西周年代考訂是研治西周史的學人絕不應迴避的嚴肅課題,也是他在中國上古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關注。針對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葉起國內進行,以釐清夏、商、周三代的年代為目標的大型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其中所呈現方法論及資料運用不當或嚴謹度不足而衍生的問題,文中提出有力的批判及質疑。何院士和劉雨對斷代工程攻關所取得的業績,特別是在測年技術方面,使用先進進口設備,測量精敏度極高的加速器質譜法(簡稱AMS),與其[也技術如樹輪校正曲線配合,1997年對陝西灃西遺址發掘出土的木炭、獸骨、炭化小米等標本進行測試,並參照晚商賓組卜辭中的五次年代月食進行核對,對過去各種徧頗主觀說法作大規模刪汱工作,將克商年代範圍限定在前1050-前1020年間,予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他們對斷代工程據傳世文獻如《國語》、《尚書,武成》及《逸周書‧世俘》和出土數據運用方法的失當,特別是將古本《竹書紀年》肆意肢解後,所選出的武王克商確切年代為前1046年之說,則──展開有力攻擊。何院士和劉雨針對斷代工程誤信《國語》伶州鳩所稱周武王伐紂時「歲在鶉火」之說,經縝密論證後,對其中迷惑作如下澄清:「伶州鳩這段話所記的星象詞句是典型的星象家的星占說,用春秋時代的人伶州鳩的口講出戰國人編造的故事來,這本身就近於胡言亂語。他所述的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只能是推算出來的。」至於《尚書,武成》及《逸周書‧世俘》,他們以現存這兩篇文獻,已大致被公認是合二而一的,但兩者的干支曆日、月相卻頗有不同,疑點重重;他質疑「在這種情況下,貿然使用這些曆日、月相材料去推論伐商年,」「是不慎重,方法論上看也是十分危險的。」何院士和劉雨認為斷代工程沒有充分利用古本《竹書紀年》這樣在年代學上史料價值至高的史籍,是研究一大敗筆。他們透過以古本《竹書紀年》與文獻(特別是將中國有明確紀年的時間上推至西周初及其世系來源有自的《史記‧魯周公世家》)和天文現象(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夏、商、周總積年,合於中國古代的「極端天象」[「禹時五星聚」];該天象經中、美的天算專家測算發生於前1953年,約夏禹晚年)互證後,得出「『武王克商年』無須捨近求遠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書紀年》的公元前1927年」的結論。何院士和參與斷代工程,並對西周史及金文資料至為熟悉的古文字學者劉雨教授合作,提出既有破,又有立,非常科學的精闢探析,可謂相得益彰。本文實為史學方法中內考證不可多得的最佳範例。
〈從《莊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關懷〉一文中,何院士以《莊子‧天下》篇首中幾個關鍵詞,尤其是「道術」作切入點,探討百家爭鳴前,先秦哲學思想重心及其基本關懷。他發現「道術」一詞,並非源於道家,而是初見於《墨子‧尚賢上》;《墨子》所言的道術,根本為最現實功利的君王統治術。何院士一本嚴謹治學態度,檢視《論語‧子路》、《鶡冠子‧天則》及《淮南子‧兵略訓》等文獻,察覺都出現與《墨子》論道術文義相同的文句,指出「五重文本迭合的證據已足有力地說明先秦思想中的基本關懷,決不是對『宇宙人生本原』的形上探索,而是不出日用人倫範疇的最現實的『君人南面之術』」。《莊子‧天下》所諱言的學派為孫子;何院士認為其中癥結所在,實因孫子徹底奉行行為主義,其在應用方面對墨子的影響則為「不得不將孫武的行為主義全都加以倫理化」;這樣墨子便對行將爭鳴的百家產生一種「道義」上的威嚇。影響所及,「迫得百家的理論都不得不披上道德、清靜、無為、心性及其他形上外衣。」
〈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一文完稿於何院士去世前兩年,其時他已年逾九十,在文獻不足的情況下,仍能以高度的歷史想像力對「秦墨」這一千古歷史迷團,撥雲指日,提出縝密而具說服力的解釋。筆者認為此文重要貢獻如後:就戰國史而言,史家咸認為秦孝公用商鞅變法,方奠定強盛基礎;何院士則登高致遠,直指秦獻公才是其中關鍵。他在文中開端以歷史文獻如《水經注》、乾隆(1784)《韓城縣志》,結合近代歷史地理學者的研究,從河西地貌揭示戰國初期的秦魏之戰的歷史意義,秦獻公即位之初的嚴峻形勢,以及其如何藉墨者之助扭轉局面,落實一系列軍政新措施雪恥圖強,商鞅變法不過順其勢而弘揚,凡此俱為研治戰國史學者多所忽略,幸賴何院士心細如髮,發前人未發之覆。就墨學研究而言,晚清以來,墨學復興,名家輩出,在文本考訂、思想史,以至軍事史等領域俱有相當建樹。唯何院士另闢蹊徑,點出前人在墨學這一領域尚未能圓滿解決的問題,如鉅子制興替始末、秦墨在秦國變法圖強中的作用,以及墨家集團的命運一走向湮滅無聞,推陳出新,提出卓見。鉅子制前人雖有所探討,但因史料所限,語焉不詳,點到即止;何院士雖受同樣制約,唯因充分發揮史家技巧,以《呂氏春秋》幾條相關記載為定錨,逐層剖析,從人所周知的史料切入,卻能化腐朽為神奇,編織出一幅人所未悉的歷史圖像,提出目前為止最為周延的探討。至於墨家湮沒無聞的原因,《莊子‧天下》篇及《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所言,俱有相當道理,見解卻不如何院士從正反的異化辯證角度點出墨家與統治集團關係演變那樣鞭辟入裡。文中最後以漢宣帝一段話及毛澤東詩作為總結,畫龍點睛,更能彰顯課題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