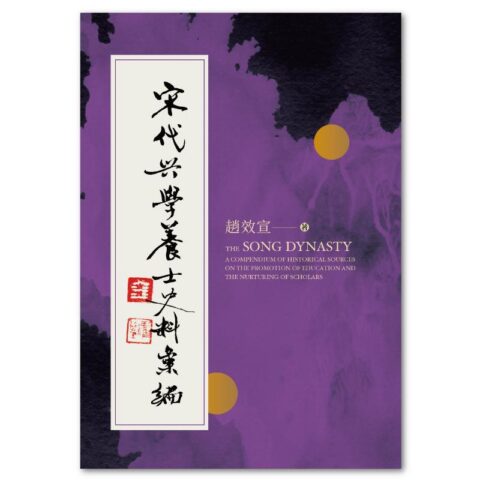中國歷史的再思考
出版日期:2015-07-29
主編:劉翠溶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504
開數:18開(高23×寬17cm)
EAN:9789570845594
系列:聯經學術
尚有庫存
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先生在獲得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後,即於 1956 年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服務,由助理研究員以至研究員,其間曾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於 1962 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繼續服務,並在臺灣大學任教。後來赴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於 1999 年退休。許倬雲先生始終關注國內的學術發展,而且著述不輟。
《中國歷史的再思考》共收錄十八篇論文。主題涉及史學理論、考古文物、文化思想、君臣關係、地方觀念、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近代戰爭、殖民經驗、城市環境問題;時間則涵蓋史前至當代,前後不下五千餘年。就此而言,許倬雲先生給予受業學生和晚輩學人影響可以說是 「多樣的傳承」,恭賀許倬雲先生八秩晉五壽辰。
※ 作者簡介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
黃俊傑(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副院長)
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退休研究員)
黃翠梅(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教授)
邢義田(中央研究院院士)
孫鐵剛(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高明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趙雅書(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張元(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李弘祺(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陳芳妹(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徐泓(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劉錚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秀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劉翠溶(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編:劉翠溶
劉翠溶,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副院長(2003/10-)。曾獲國立臺灣大學學士(1963)、碩士(1966)、美國哈佛大學碩士(1970)、博士(1974);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66-68)、美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1974-78)、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及研究員(1978-98)、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主任(1998-2003)。她的研究領域為經濟史、人口史與環境史。
序(劉翠溶)
1 史學之空間思維的雜想╱杜正勝
2 再現傳統中國的思想──邁向論述化、命題化的哲學?╱黃進興
3 中國歷史寫作中史論的作用及其理論問題╱黃俊傑
4 近代史家的研究風格與內在緊張╱王汎森
5 史前至夏時期玉器文化的新認知╱鄧淑蘋
6 瑤環百疊,瑜珥琤瑽──雲南滇文化的玉耳玦╱黃翠梅
7 從《太平經》論生死看古代思想文化流動的方向╱邢義田
8 漢高帝如何從白登之圍脫困的?╱孫鐵剛
9 唐代的身分制社會╱高明士
10 五代吳越國末代君王錢俶(928-988)的歷史地位╱趙雅書
11 略談五代宋初君臣關於讀書的記載╱張元
12 什麽是近世中國的「地方」?──論宋元之際「地方」觀念的興起╱李弘祺
13 十三世紀桂學釋奠二圖的新發現╱陳芳妹
14 明代河東鹽銷區的爭執╱徐泓
15 檔案所見清代社會夫妻關係的斷裂與終止╱劉錚雲
16 關鍵的一年──蔣中正與豫湘桂大潰敗╱陳永發
17 臺北帝大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從成立到接收╱張秀蓉
18 臺灣與福建城市環境問題的比較研究╱劉翠溶
劉翠溶
這本書收入十八篇論文,作者包括了曾經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和美國匹茲堡大學受業於許倬雲先生的學生,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晚輩研究人員。這十八篇論文的主題涉及了史學理論、考古文物、文化思想、君臣關係、地方觀念、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近代戰爭、殖民經驗,以及城市環境問題;而時間則涵蓋了史前至當代,前後不下五千餘年。就此而言,許倬雲先生給予受業學生和晚輩學人影響可以說是「多樣的傳承」。
許倬雲先生在獲得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後,即於1956 年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服務,由助理研究員以至研究員(1956-1971),其間曾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但於1962 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繼續服務,並在臺灣大學任教。後來赴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1970-1998),於1999 年退休。許倬雲先生始終關注國內的學術發展,而且著述不輟。
在受教於許倬雲先生之後,我們這些晚輩各自以個人的興趣繼續努力進修,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這本書收入的論文呈現的是大家最近的研究成果。我個人是許倬雲先生在臺灣大學任教時的第一班學生,謹代表大家撰此序文,恭賀許倬雲先生八秩晉五壽辰。
檔案所見清代社會夫妻關係的斷裂與終止/劉錚雲
一般認為,在傳統中國社會,男女兩性關係是建立在「男尊女卑」的基準上。這個「男尊女卑」的道德規範落實到行為上,就成就了後世奉為禮教的「三從」之義與「男女內外」之分。前者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而後者則指的是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或是男主外,女主內。本文旨在利用本所典藏內閣大庫檔案中的刑案資料,主要是近三百件夫妻失和的案例,來檢視這個道德規範是如何在社會上被實踐的。本文將以「三從」,尤其是其中的第二從,即既嫁從夫,與「男女內外之分」兩個觀念來檢視這些案件,希望透過夫妻衝突癥結的分析,瞭解雙方對「三從」與「男女內外」之分奉行的程度,藉以說明清代婚姻關係中兩性認知的複雜性,以及「男尊女卑」在釐清清代夫妻關係的局限性。
這些失和案例都是涉及人命的家庭暴力事件,多數是丈夫殺死妻子,但也有不少是妻子與姦夫共謀殺死丈夫的案子,也有妻子獨自殺死丈夫的例子。由於是命案,有一方當事者已不存在,刑案口供就成了另一方當事者的獨腳戲。這當然不利於我們對案情的全盤掌握。另一方面,當事人在陳述案情時多少會避重就輕,或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陳述,往往造成口供內容過於偏頗,旁人難以瞭解事件的真像。然而,如果我們不求斷定雙方是非,只在乎瞭解婚姻出狀況的原因;只求觀察當事人對案情的陳述,以釐清導致雙方衝突的導火線,這些案例仍有可取之處。
依據大清律,謀殺人與誤殺、過失殺傷人的刑罰不同;同時,丈夫若毆死有罪妻妾,毋需償命,只杖一百。所謂有罪妻妾,是指毆罵丈夫之祖父母或父母之妻妾。為了減輕刑責,涉及人命案的男性當事人在堂上往往採取將命案導向誤殺或過殺的策略;他們一般會在口供中指出,因為妻子行為不當,未盡為管家之責,或是出於一時氣憤,或是為了教訓對方,以致失手殺人,絕非故意殺人。另一方面,殺夫的女性當事人則多會供稱原本無意謀殺丈夫,都是受姦夫唆使好作長久夫妻,而協同謀害丈夫。但無論是為求脫罪,或諉過他人,當事人的目的只有一個,即設法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只是出於一時衝動的過殺,而非蓄謀已久的謀殺。這些當事人的說辭雖然可能有所偏袒、誇大,但不論他們的說法如何有利於自身,他們對對方的指控必須很明顯的顯示對方行為有違當時夫妻相處之道,如此方能合理化自身的行為,以避免更重的刑罰。而我們從這些當事人為自己行為辯護的言辭中,從夫妻雙方對彼此不滿的陳述中,應該可以分梳出當時社會認可的夫妻關係,掌握到當時夫妻雙方對彼此的期待。
其實,大陸學者王躍生曾在其分析清代中期婚姻的專書第三章,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366件刑科題本處理過同樣的問題。他是從「夫權的表現方式」與「妻子對夫權的違抗」兩個角度,以夫妻衝突案件為主的方式來討論。本文捨棄「夫權」這個現代學者發明的概念,而是考慮到夫妻關係既然不對等,故將導致雙方衝突的導火線,分成「丈夫的不滿」與「妻子的抱怨」兩部份來觀察,並將妻子外遇造成夫妻失和的案例納入討論,以突顯夫妻雙方對彼此期待的差異。
一、丈夫的不滿
夫妻朝夕相處,日常身邊瑣事往往成為引發衝突的來源,而一旦感情生變,即使芝麻細事都會引爆爭端。不過,在檔案中,就日常家事而言,丈夫對妻子不滿的比例遠高於妻子對丈夫的怨懟;而在夫妻感情問題上,妻子情變的比例相對較高。在我所見的案例中,丈夫對妻子的不滿大致有幾種情形:不順從自己或父母、不安分持家或家事失當、心向本家、嫌棄妻子、妻子與人通姦。前面二種情形多與日常細事有關,而後面三種則多涉及夫妻感情生變。以下分別討論:
(一)不順從自己或其父母
在這些婚姻失和案件中,引起爭執最多的起因是丈夫認為妻子不聽話,不順從自己或其父母的意見,約佔總數的四分之一。在這些案例中,丈夫的指控極為多樣性,如不肯做飯,不肯燒洗臉水,不肯燒茶水,不肯熱茶,不肯縫補掛子,不肯下田割禾,不肯生火,甚至不願與丈夫同房,不接受丈夫白日求歡,反對丈夫娶妾都是爭執焦點。這些爭執的發生大多是由於妻子未依丈夫的囑咐做事,夫妻口角,丈夫失手殺死妻子。乾隆十年二月間江西雩都縣民胡廷器因妻子不願遷往庄上居住,一時氣忿,把妻子打死了。他的口供詳細的描述了夫妻間口角的經過:
小的是本縣人,今年五十五歲,平日與妻子王氏和好,並無什麼嫌怨。只因小的向有庄田一所,離家三里路遠,耕種不便。今年二月十六日小的與妻子王氏商議說,如今春耕時候,我與你搬到庄上去住,就近好耕田。妻子不肯,與小的鬥嘴。小的原罵他懶婦,他就回罵小的。小的正要打他,他就摸取門邊糞把先向小的打來,小的拿過糞把隨手打去,不覺傷著他左耳輪,連左耳根。他越發亂罵,連及小的父母。小的一時氣忿,又把糞把掉轉柄來打去,不覺傷著他頂心偏左,倒地擦傷左眉叢并墊傷右腮脥。後是鄰人謝利才們走來勸解,小的就把妻子扶到床上。不料,妻子傷重,救不好,到十七日早上就死了,是實。
另一個例子是,乾隆二年六月十七日早晨,陸勝先向正在洗衣服的妻子林氏要飯吃,好下田去拔草。林氏答以飯還沒有煮,要他吃些酒去,回來再吃。陸勝先依言吃了碗酒,就去田中上工了。可是當他因為「喫了餓酒,酒湧上來,就回家要飯吃」時,發現林氏還未煮飯,不禁說了林氏幾句,「這時候怎麼還不煮飯。」林氏遂以「餓鬼」回罵。陸勝先聞言,「惱起來」,趕進房去打林氏,正好桌上放著壹把劈柴斧頭,他「酒醉了,一時模糊,看不清是什麼家伙,就拏起來打他幾下,不想竟把妻子砍死了。」
第三個例子是,乾隆二年六月一日,湖北安陸府荊門州人車君儒夫妻倆同在田裡耨草。車君儒因為肚子餓要妻子張氏先回去做飯,張氏以天色還早不肯回去,二人發生口角,張氏言語中還辱及車君儒的父母,車君儒「一時氣不過」,就用鋤頭朝張氏頭上打去,張氏哭著回去,不久傷重而死。
在上面三個例子中,陸勝先強調他是「因一時酒醉模糊」,把妻子砍死了,不是「有心要把他致死的」。胡廷器表示,他是「一時氣忿」,才掉轉糞把將太太打成重傷,不治身亡的。車君儒也說,他是「一時氣不過」,「原只想打他去做飯,不期適打著他頭上右邊,打重了些。」根據檔案所見,這幾乎是所有「生活細事」類案件丈夫口供的模式。他們都會表示因為妻子不僅不聽話,而且回罵,也有的會像胡廷器一樣,強調妻子的辱罵甚且「連及父母」,也有些甚至指出妻子潑悍,先動手打人,他們才還手,只是一時失手,打傷妻子身死。他們也都會指出他們不是有意殺人,而是一時迷糊,或一時氣忿,才會打死妻子的。雖然我們無法確定這些丈夫是否要利用《刑律》〈人命〉第二百九十三〈夫毆死有罪妻妾〉條減輕刑責,但衡諸當時兩性關係,這是極有可能的。然而,對大多數的男子而言,在傳統禮教的影響下,作妻子的絕對服從乃天經地義之事。藍鼎元的《女學》第一卷〈女學總要〉開篇即引孔子曰,「婦人伏于人也。」而我們翻閱《女誡》、《閨範》一類的書,映入眼簾的不外「敬順」、「孝敬」、「曲從」等字眼,要求婦女絕對的順從。同時地方上也有「天字出頭夫作主」的諺語。對丈夫而言,妻子必須「敬順無違,以盡婦道。」如果他們所作所為有虧婦道,丈夫理應勸戒。例如,一位縣官問道:
你妻子就是于王公林的妻子吵鬧過也是小事,你怎麼就毆打他多傷以致身死呢?明有別故,有心要致死他的了,快實供來。
這位丈夫答道:
妻子與人吵鬧雖是小事,小的因他在家不賢良,一味悍潑,要打他一頓,儆戒他下次的。不想他反混打、辱罵,小的纔氣極亂打他幾下,那知他就被打傷死了。實出無心,並無別故。
另一位丈夫對類似問題的回答是:
小的買驢肉回來,叫妻子張氏煮著。妻子先吃了些,原是小事,但他不該背地先偷吃。小的回家看見鍋裡驢肉剩得不多,故此罵他偷嘴,原是要他學好的意思。不料,他不但不聽,竟回罵小的。故此小的氣起來,拾了柳棍要打他,因他轉身走避,小的隨手打去,誤打著了他腦後的。小的與他夫妻情分一向相好,並沒別的緣故,為什麼有心要打死他呢?
他們都是要妻子規過向善,孰料妻子並不領情,反而「一味悍潑」,竟然回罵,導致他們氣極而生事。
如果妻子「潑悍」的對象是自己的母親,做丈夫的更有理由教訓妻子了,因為他們忤逆不孝。二十歲的詔安縣民張寧就說:「肆月初陸日傍晚時候,母親叫老婆挑水下缸,老婆把缸掽裂,母親罵他不小心,他就與母親鬥嘴。小的見他忤逆,用拳打他髮際壹下,他和小的撒潑,小的氣忿,拾起搗衣木棒打他額顱壹下,不想他倒在地下救治不活。……」其實,檔案中可以看到不少這樣因為婆媳不和而導致夫妻衝突的例子;多數是不理會婆婆的吩咐,如不肯替婆婆洗衣服,不理婆婆要他煮飯的要求;或是像張寧的妻子一樣,對婆婆出言不遜。有趣的是,檔案中較少見到翁媳不睦的案例。惟一的例子是,公公和五個兒子都是硝皮生理,媳婦不滿公公連著兩天向兒子借皮硝使用,口裡咕咕噥噥地說:「供著他的飯,還連日使俺的硝」,而且還「娘長娘短的」咒駡。公公因為耳聾聽不見,丈夫趕集去了,可是同父異母的叔公聽不下去,出面指責侄媳婦。侄媳婦不服,不斷咒駡,還說,:「你是後老婆生的,管不著我。」這一說,把叔公給激怒了,推了侄媳婦一把,侄媳婦就上去撕抓他,還說:「你手裡現拿著斧子,敢殺我嗎?」叔公因為侄媳婦他罵得刻毒,一氣之下,就照他胸膛上砍了一斧子。侄媳婦跌倒在地,口裡又是一陣胡罵,叔公性起,決心把他砍死償命,就照他咽喉食氣顙連砍了五斧子,姪媳婦當場斃命。
其實,很多時候妻子不是不聽使喚,只是一時忙不過來,不能應命。例如,雲南廣西府人李忠秀只因妻子彭氏要哄啼哭的娃兒,分不出手來替他盛飯,要他自己盛飯,心生不滿,不斷詈罵,彭氏回嘴理論,就大打出手,最後弄出人命。而不少時候丈夫更是有錯在先,弄得妻子心情不佳,與其鬧彆扭,堅拒所求。直隸人賈三槐在參加伯父娶媳婦的喜宴後回家,講起伯父家新娶的媳婦來。賈三槐取笑妻子李氏說:「新嫂子比你生得齊整,你那裡如人家那樣好呢?」妻子有些嗔怒地說:「這也是各人的命,你命裡不該娶好老婆,說他做甚。」賈三槐隨走到院裡餵羊,回到房裡,妻子已睡下。賈三槐想要與妻子行房,李氏推說:「身子不乾淨」;賈三槐他「不曉得甚麼乾淨不乾淨,就拉開他褲子硬爬在他身上。」李氏把他推下來,說:「我原是醜陋的,你看誰家的女人好,就往誰家睡去罷了,來纏我做甚麼。」一陣扭打,賈三槐為了不使李氏喊叫,驚醒母親,掐住李氏咽喉,沒有想到就這樣把新婚一個月的妻子給掐死了。
在口供檔案中常見一句話,「你合他女人吵什麼呢?」顯示出當時人所有的一種俗話所謂「男不跟女鬥」的心態。有些人也在公堂上作同樣的陳述,表明不會與女人一般見識,但以上的例子顯示,許多男子一旦與自己女人起爭執時,則又是另外一回事,儘管有時還是自己有錯在前。唐甄(1630-1704)就曾指出,「今人多暴其妻」。這些檔案中的故事證實其所言非虛。
當然,莽夫固然是家庭暴力嚴重的原因,但家中悍妻恐怕也需負部份責任。這裡所用「悍妻」一詞是套用檔案中涉案當事人的用語。在口供中,常見男子用「悍潑」或「潑悍」二詞形容他們「不賢良」的妻子。這固然有可能是當時人的策略,但無可否認檔案中可以看到有些婦人的確「潑悍」。例如,「姜氏平日極悍潑,常嫌小的家窮,每日合兒子吵鬧,不安心過日子」;又如,「因王氏性賦悍潑,向日夫婦也常口角」;又如,「劉氏心多不足,性復潑悍,時常吵鬧」;又如「妻子潑悍,以致常被房東攆走」。現在我們就以這常被房東攆走婦人的故事為例,看一看丈夫口中的「悍妻」是如何潑悍。
這位婦人姓劉,曾是吳姓人家的妾,因為常與大婦吵架,吳家不要了,改嫁給王得府,時年二十一歲。以下是王得府對劉氏的描述:
小的是本縣人,三十六歲,小的父母都死了,並沒兄弟、子姪。劉氏是吳得宣的妾,後嫁與小的,有九年了,並沒生有子女。他性子潑惡的。小的先賃姬宗玉家房子住,因女人偷了姬宗玉家兩包煙,向貨郎擔換布,被姬宗玉見了,對小的說過,就叫小的謄房。小的又搬到姬熬子家房子裡,因小的外邊掉了一件布衫,女人只是混吵,小的打了他右胳膊上一柳棍。姬熬子見了,把小的喝住;姬熬子怕鬧出事來,也不叫小的們住。乾隆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纔賃張興福家房子住下。二十三日晚,小的往家裡取衣服穿,見女人和張興福的母親李氏在院裡說閒話。女人說小的偷聽他說話,就罵小的;小的說你們說什麼話我並沒有聽見,與他辨白了幾句。小的又怕房主聽見不像模樣,就躲進屋裡去了;女人嗔小的與他回嘴,就拿著一個尿罐子進屋,照小的劈面打來;小的閃躲,沒有打著,把罐子打爛了。小的就去睡了,總不理他,女人就叫罵了一夜。到天明時,小的心裡暗氣,想自娶了他連房子也住不穩,又聽見房主李氏臨走說,像這樣就不敢留你們住的話,眼前又是要攆的了,窮人家如何當得起,越想越氣要這潑悍女人做什麼,不如害死他倒得乾淨。
那天,王得府就把劉氏勒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