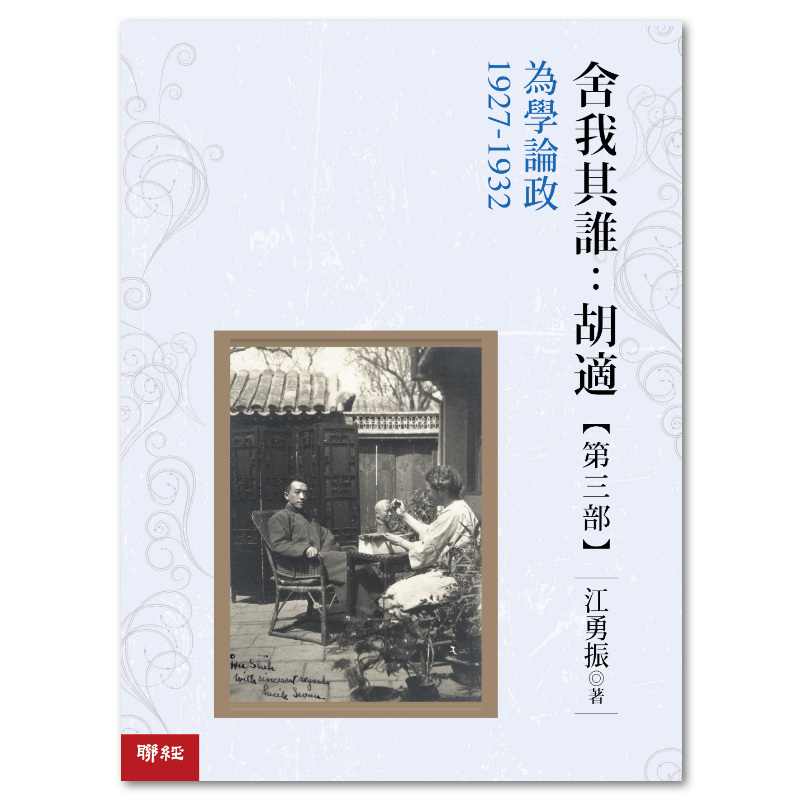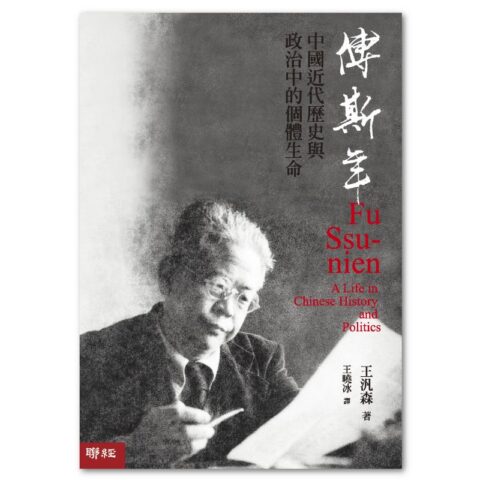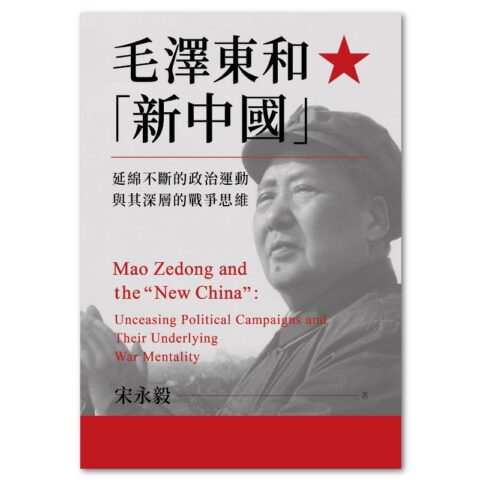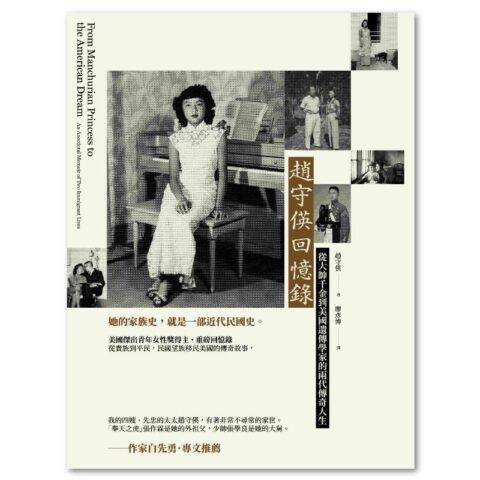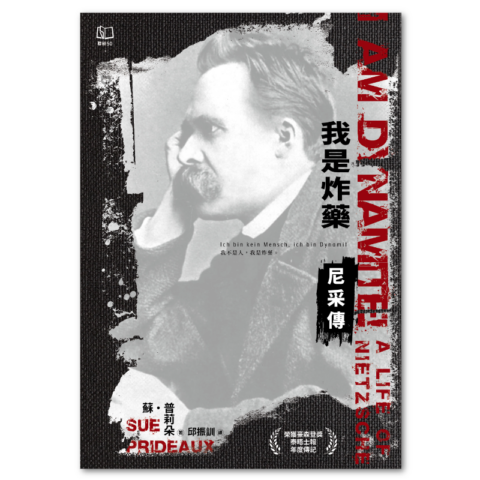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
出版日期:2018-01-30
作者:江勇振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656
開數:18開,高23×寬17cm
EAN:9789570850710
系列:舍我其誰:胡適
尚有庫存
胡適認為:中國思想史,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
繼《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和《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後,江勇振教授推出《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
1927至1932年這段期間,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一方面,他提出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他說,中國思想史,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
胡適在1926到1927年歐遊期間,患了法西斯主義急驚風,禮讚國民黨以黨統軍、領政的偉大。這個急驚風退燒以後,他在《新月》雜誌上演了一齣看似單挑國民黨,其實是「閻王好惹、小鬼難纏」的精彩戲碼。然而,這個時候的他,已經開始走近蔣介石。他在1930年底回到北大,從事北大中興的工作。從這個時候開始到1930年代中期,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一方面,他比較中日兩國的現代化,提出了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他說,日本是現代化其表,而封建其實。反之,中國的現代化看似迂迴遲緩,其實是最徹底的。在另一方面,當時的胡適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他說中國思想史,只是一部寒傖史。胡適一生當中沒有完成他的《中國哲學史》的全卷。其原因除了他狐狸才、刺蝟心的矛盾以外,還有他1920年代在中國哲學史詮釋上所產生的一個斷層,以及他在抗戰、冷戰時期的曲筆。更重要的是,中國思想史對晚年的胡適而言,已經味同嚼蠟,索然無味。
作者:江勇振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學歷史系教授退休。著有《張君勱傳》、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舍我其誰:胡適》 (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留美半生緣:余英時、錢新祖交鋒始末》等書,多篇論文散見於各刊物、選集中。
前言
序幕
第一章 從自由人權,到安定為先
從對國民黨幻滅到妥協的開始
聯美反制國民政府:中基會改組
閻王好惹,小鬼難纏:人權與約法
借反蔣的東風向蔣介石要約法
第二章 中日現代化,還是中國行
從「島夷」到「完全歐化之國」
日本是亞洲現代化的典範
日本:現代其表、封建其實
「杜威教我怎樣思想」──日本篇
中日比較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不絕如縷
第三章 天字號學閥,明星級教授
人在上海、心在北大
中興北大
締造北大成為「文科的北京協和醫學院」
努力作學閥:作得大、教得棒、活得好
第四章 中國思想史,一部寒傖史
中國哲學史詮釋的斷層
重新定位中國哲學史的詮釋:1920年代
寒傖中國思想史觀的成形:1930年代
抗日愛國史觀
反共史觀
幕間小結
前言(節錄)
任何作者在自己的作品出版以後,就對其作品失去了詮釋的掌控權。毫無疑問地,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一定有其主張與想法。然而,作品一旦發表,就好像是放在美術館裡的展覽品一樣。觀眾要如何品頭論足,已經不再是作者所能置喙的了。諺語說瞎子摸象,意指以偏概全。然而,作品一旦發表以後,就已經超越了瞎子摸象的層次。如果一個讀者覺得大象的鼻子是大象之所以為大象的理由,而執意從象鼻來觀全象,那是讀者的特權。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提出的「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概念,把傳統作者獨尊的角色給根本否決掉了:
當我們相信「作者」的時候,他是被視為是其著作的歷史:作品與作者自動地被視為是站在一條分為「之前」與「之後」的一條線的兩端。作者是孕育了這本書的人。這也就是說,他是在書之前存在的人;是為之勞神、為之吃苦、為之而活的人。作者跟他的書的先後關係,就像是父親跟孩子一樣。
羅蘭‧巴特說,所謂作者所炮製出來的文字,說穿了其實不值一文錢:
我們現在知道一個文本(text),並不是一串釋放出一種「神祇的」(theological)意義(作者─神的「旨意」)的文字,而是五花八門的著作──其中沒有一樣具有原創性──摻雜、碰撞於其間的一個多維的空間。一個文本,就是從各色各樣的文化中心(innumerable centres of culture)所擷取過來的引文(quotations)的組合。
換句話說,從羅蘭‧巴特的角度來看,所有的作者都是文抄公:「他唯一的能力(power),就是調配不同的著作。用其中的一些說法來反駁其他說法,而從來就不站在任何一方。」那能賦予一個作品以意義的,是讀者:
讀者是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作品的引文可以鐫刻於其間而不虞有任何遺漏的空間:一個文本的統一性不在於其起點,而是在於其終點。然而,這個終點已經不再是個人:讀者沒有歷史、傳記、與心理。
羅蘭‧巴特這篇文章讓人石破天驚的結語就是:「讀者的誕生,就必須以作者之死作為代價。」
我認為羅蘭‧巴特「作者已死」的論點過分極端。從他所有的作者都是文抄公的角度來看,作者根本就不是寫作的人,而是語言本身。這個「語言本身」是作者的說法,以及讀者不是「個人」、「沒有歷史、傳記、與心理」的說法,都未免太先驗、玄緲了。同時,這也等於把作者視為像傀儡一樣,完全抹殺了作者──至少是傑出的作者──的原創力。
我比較喜歡的,是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觀點。他在〈何為作者?〉(What Is An Author?)一文裡說:
作者的名字不是其人在民法上的身分,也不是虛構的;它是處於那能讓新論述群(new groups of discourse)及其特殊的存在模式誕生的斷裂處的裂縫中。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我們的文化裡,作者的名字是伴隨著某些特定的──而非其他──文本而出現的一個變數:一封私信有署名者,但他不是作者;一個合約有擔保人,但他不是作者;同樣地,一張貼在牆上的無名海報也許有製作者,但他不可能是作者。在這個意義下,作者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an author)在於顯示出一個社會裡某種論述的存在、流通,以及運作。
傅柯把「作者的功能」放在論述的脈絡之下來檢視。這種詮釋既有顛覆、又有解放作者這個概念的優點。一方面,它能解釋為什麼大多數的作者都是屬於羅蘭‧巴特所鄙夷的文抄公的類型,因為他們都只是在當下流行的論述裡吐絲作繭;另一方面,它又能解釋歷史上代代常有開山之作出現的光輝燦爛的現象:
然而,很明顯的,即使在論述的領域裡,一個人可以不只是一本書的作者。他可以是一個能讓無數的新書與作者在其理論、傳統、甚至其所創的整個學科裡滋生繁衍的創始者。為了說明方便起見,我們可以說這些作者是站在一種「超論述」(transdiscursive)的位置。
荷馬、亞理斯多德、基督教的元老,以及最早的數學家、希波克拉底傳統(Hippocratic tradition)〔注:希臘醫學傳統〕的締造者所扮演的就是這種角色。這種類型的作者,我相信跟我們的文明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但是,我認為十九世紀歐洲出現了一種異類的作者。我們不能把他們和文學「大師」、宗教經典的作者、或科學創始者放在一起。我隨手拈來,就稱呼他們是「論述的創始者」(initiators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佛洛伊德、馬克思,就是傅柯心目中的十九世紀歐洲的「論述的創始者」的典型:「這些作者最特出的貢獻在於他們所創製出來的,不只是他們自己的著作,而且是讓後繼者能夠據以創製其他文本的可能性與規則。」他們「在他們所創始的論述領域裡,除了他們自己的學說以外,還留下了可以引介入其他成分的空間。」換句話說,佛洛伊德與馬克思的貢獻不只在於他們各自所留下來的鉅著。更重要的,是「他們為論述創建了無窮的可能性。」
相對於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論,傅柯的「作者的功能」論提供了一個更具有說服力的角度來看讀者所占有的地位。大多數的作者,亦即,羅蘭‧巴特意義下的「文抄公」的作者,誠然都只不過是在當下流行的論述裡打轉,毫無新意。然而,絕大多數的讀者何嘗不然?絕大多數的讀者所咀嚼、並引以為是的,也不啻「文抄公」作者吐絲而成之繭而已。
絕大多數的作者與讀者都是活在當下流行的論述裡。因此,任何與當下流行的論述牴觸的說法,都不可能會立即被接受。學術的成長固然有其積累的部分。然而,斷裂也是學術成長一個重要的因素。所謂的學術的成長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說法就是一個似是而非之論。文化人類學家克理福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說得好:
我們對文化──不管是複數還是單數意義下的文化──的認識,是以跳躍式(spurts)的方式進展的。文化分析不是一條逐步積累成長的曲線,而毋寧是類似那種以斷裂、但卻又具有連貫性關係的越來越濃密的點狀來呈現的(a disconnected yet coherent sequence of bolder and bolder sorts)。研究並不是建立在先前研究的基礎上的,亦即,不是在前人所歇息之處接手挺進的;而是基於更好的訊息、更好的觀念,而對同樣的問題作更深入的分析。任何嚴謹的文化分析都是從另闢蹊徑開始,一直到它窮盡了其思想的激力而後矣。它會去運用前人所發現的事實,它會去使用前人所發展出來的觀念,它會去測試前人所建構出來的假設。但其進程不是從已證的命題去發展出新證的命題,而是一種跌跌撞撞式的摸索(an awkward fumbling)。從最基本開始,從已證的主張到超越它。一個研究之所以能被視為是一個突破,是因為它比先前的研究更為精到(incisive)──不管我們如何定義這個字眼。我們與其說它是建立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如說它是在前人的挑戰之下挑戰前人,與他們競逐。
又:
文化研究在本質上是殘缺不全的。更糟的是,我們越往深處走,它越是不完整。它是一個詭異(strange)的科學。其最能動人心弦(telling)的詮釋,往往就是建立在立足點上最如履薄冰的基礎上(tremulously based)。這種詮釋會──在研究者自己心裡與別人心裡──激起強烈的懷疑,質疑其正確性。但這──再加上用丈二金剛抓不著頭腦(obtuse)的問題去折磨心思細膩的人──就是民族學者所作的事……人類學,至少詮釋人類學,是一種科學,其進步的象徵不在於達到意見一致(consensus)的境界,而毋寧是在於精益求精的辯難(a refinement of debate)。那進步的所在,就展現在我們唇槍舌劍時招招精準的表現(the precision with which we vex each other)。
序幕(節錄)
胡適1950年在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在史達林戰略裡的中國〉(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在這篇文章裡,胡適回憶了他1927年4月經過東京的時候,在《東京朝日新聞》的一個展覽之所見:
1927年3月24日,北方軍閥軍隊逃離以後,國民黨軍隊進入南京,野蠻地攻擊了南京的外國人,劫掠、破壞外國人的住所以及領事館,殺死了一些外國人,包括美國金陵大學的副校長〔威廉斯(John Williams)〕。外國駐在長江上的軍艦被迫開砲制止進一步的暴力,並引領逃生的外國人避難到軍艦上。
〔耶魯大學的〕賴德烈(Latourette)教授說:「這個(南京)事件激怒了外國人,使得在一時間裡,眼看著全面干預(extensive intervention)即將發生。」
「南京事件」發生當天,我正在從紐約到芝加哥的旅途上。我可以感覺得到美國對北伐軍一直到當天為止具有的好感的輿論,一夕之間逆轉。
然而,一直要到將近一個月以後,在我抵達東京,一個外務省的日本朋友帶我參觀的時候,我才真正瞭解到這個事件距離造成「全面(外力)干預」有多近。當時《東京朝日新聞》正在其新大樓舉辦一個「現代新聞展覽」。我的日本朋友對我說:「胡適博士!我要你參觀一個小房間。」這個小房間的三面牆上貼滿了當時從南京、上海送到《東京朝日新聞》總部的電報原件:劫掠南京日本領事館、褻瀆日本天皇玉照、日本領事館上尉因為不准抵抗的命令而準備切腹,等等的電報。在1927年3月24日當天,就有超過400件的緊急電報。
我的朋友對我說:「你甚至在今天都還可以感受到日本在那浩劫的一天的感受如何。」他接著告訴我列強如何嚴肅地會商是否干涉。根據他所得到的消息,日本是反對干涉的政府之一。
胡適這個二十三年以後所作的回憶究竟有多信實是值得懷疑的。晚年的胡適,為了反共,有作偽的傾向。這是我在第四部第三、第四章分析的重點之一。然而,胡適在《東京朝日新聞》的小房間裡所看到的展示,以及他外務省日本朋友對他所說的話究竟有多信實不是重點。重點是胡適用這段回憶所要表達的主旨。胡適這篇論文名為〈在史達林戰略裡的中國〉。顧名思義,就是要強調史達林在中國的陰謀。胡適的重點是在強調所有從「五卅慘案」以後的反英示威與杯葛運動,占領漢口英租界,到北伐軍在南京、上海的暴行,都是排外的行動,而且都是由史達林利用「聯俄容共」的陰謀嗾使共產黨挑釁造成的:
我們今天回顧過去,南京事件可以說是這一系列蓄意造成的排外舉動。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列強用武力干預,以至於造成一個「帝國主義戰爭」的形勢──我們必須記得,那就是史達林以及「共產國際」認為革命成功所必須要有的「客觀條件」。
史達林的陰謀沒有得逞,胡適說是由於列強與蔣介石的明智,沒有墮入共產黨所設計的圈套。因此,成功地化解了共產黨的詭計:
1925到1926年間「五卅慘案」以後那洶湧澎湃的反英示威與杯葛運動,其目的就是在粉碎英國在華的權力,迫使英國用武力干預。但是,英國選擇不反擊。甚至在漢口的英租界在1927年1月4日被用武力的方式占領以後,英國政府堅持同樣的政策,命令其公使到漢口與當時被共產黨所控制的武漢政權交涉。英國在漢口、九江的租界,就在這次的談判歸還中國。
但是,英國這種不抵抗的態度,擊敗了共產黨試圖把英國推到牆角以造成國際戰爭的策略。3月24日的南京事件,非常可能也是一個蓄意的策略,試圖一舉引起列強武力的干預。一如我所指出的,那幾乎成為事實。
胡適說列強之所以沒用武力干預,是因為英國沒有落入史達林製造共產革命的條件的圈套。更重要的,是因為蔣介石識破了共產黨的詭計,而適時「清黨」的結果:「蔣介石以及國民黨的溫和派決定與共產黨『分道揚鑣』(split)、並把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清出黨外的決定,化解了列強干預、共產革命的危險。」
這是胡適1950年在〈在史達林戰略裡的中國〉一文裡,對從「五卅慘案」一直到國民黨「清黨」這一段歷史的回憶。值得令人省思的是,胡適自己在二十三年以前所寫的文字則大異其趣。首先,我要用胡適自己在1927年間所寫的文章,來指出胡適在這個晚年的回憶裡說,美國的輿論對北伐軍本來一直具有好感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我在《日正當中》第八章裡提到了《紐約時報》從1927年3月2日到5日,連續四天刊載了費德列克‧穆爾(Frederick Moore)四篇有關中國的特稿。穆爾的特稿形容當時已經進逼上海的北伐軍「完全沒有訓練,其實就是土匪而已。」穆爾說,在租界的歐美人士都嘲笑中國人怕死,嘴巴喊自決、平等、排外,外國軍隊一到,就噤若寒蟬了。他輕蔑地說,歸國留學生號稱中國為中華民國。他說,其實連中國人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他們的新國號。他說一般中國人也不稱自己為中國人。他是甘肅人、直隸人,或者是湖南人。北京對一般支那人來說是遠在天邊。他說那一生貢獻給中國的傳教士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他們夢想一兩個運動就可以把中國現代化。他說一個全國加起來只有八千英里長的鐵路、五千輛汽車、大學的水平甚至比不上美國的中學的國家,怎麼可能成為一個民國呢?帝制其實要更適合中國。
胡適連看了穆爾這四篇用輕佻的語氣侮蔑中國的話。盛怒之下的他在1927年3月5日,打了一封電報給《紐約時報》的主筆尼克拉司‧羅斯福(Nicholas Roosevelt),向他提出抗議:
費德列克‧穆爾的幾篇通訊,讓我憤慨已極。在目前這樣一個危機時刻,這種反動、特別是輕佻的態度,除了造成反感以外,什麼好處都沒有。一個到現在仍然相信帝制適合中國、同時又譏詆一個偉大的國民運動的人,完全沒有資格代表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大報。
當時在英國、美國自願充當國民黨義務宣傳員的胡適,極力地試圖扭轉英美兩國反對北伐軍的輿論。由於當時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西方國家很自然地是以布爾什維克來描述北伐軍,而且以「赤色將軍」(Red General)來指稱蔣介石。胡適堅決反對這種標籤。他說北伐軍連粉紅色都談不上!他在紐約《太陽報》(The Sun)的專訪裡說:
作為一個超然的自由主義者,我預測這個運動終會成功,把中國統一在國民黨所組織的政府之下。
這不是一個排外、反美的運動。但是,它有一個我認為是很自然而且合理的要求。那就是所有外國人在過去八十年中所享有的特權必須要廢除,所有今後想要在中國居住、貿易的外國人,都必須和中國人一樣服從中國的法律。
就以「南京事件」來說,他在1950年所作的回憶,也迥異於他在事件發生當下的說法。他在1927年4月1日寫信給他美國的好友葛內特(Lewis Gannett)的信裡說:
我對南京發生的事情仍然百思不解。威廉斯(Williams)之死絕對不是排外的預謀。你看到了鮑威爾〔注:John Powell,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發行人〕發送、發表在芝加哥報紙上的包文(Bowen)博士〔注:Arthur Bowen,金陵大學校長〕的證詞了嗎?早先有關他〔威廉斯〕死亡的報導純粹就是謊言──雖然是具有基督教感化意義的玩意兒。包文博士說他們(包括威廉斯)當時正走著,看見了一個在搶劫的兵。威廉斯用中文教訓他,他轉身對威廉斯開槍。
但接著發生的事情,就完全不是我的想像力所能理解的了。報紙上發表的許多報導,那些新聞記者都該被關到精神病院裡去。很顯然地,有些人希望把那兒的問題無限地渲染。
第一章 從自由人權,到安定為先
胡適在1927年5月20日結束他歐美之遊回到上海。這是他一生中在政治上最為膾炙人口的一段,原因就是他膽敢用約法跟國民黨要人權。胡適的好友高夢旦的九兄在讚佩之餘,為胡適取了一個「龍膽公」的諡號。事實上,胡適「龍膽公」單挑國民黨的這個故事已經被演繹成了一個「神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大家不去深究胡適約法與人權的來龍去脈,以及他所抨擊的對象;另一方面,是因為大家懵懂於這是胡適一生在政治思想、意識形態上大起大落的階段。把這個「神話」拉回人間,此其時也。
胡適在1927年確實是帶著滿腔對國民黨的憧憬回到上海的。他回國以前,特別是在英國、美國的時候,根本就是國民黨在海外義務的宣傳員。當他抵達日本,在報上讀到國民黨清黨、屠共的消息以後,他為國民黨辯護,認為國民黨已經清醒、找回自己了。他的朋友、學生都勸他留在日本觀望一陣子。然而,他執意回中國為國民黨效勞。只是,他一回國就立刻掉入了失望的深谷。胡適對國民黨憧憬的幻滅,反映在他足足一年多的沉默。幻滅不只讓他疏於記日記,也讓他對國外的朋友封筆。然而,就在他幻滅與沉默的時候,他與國民黨妥協的種子已經開始埋下了。
就在胡適已經開始跟國民黨妥協的時候,卻發生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改組的風波。這個1928年國民政府改組中基會的事件,所知的人並不多。歷來的研究,都把這個事件詮釋成為胡適維護中基會獨立的努力。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在改朝換代之際,罷黜曹錕所派任的中國董事,以新朝所任命的董事取而代之。此舉違反了中基會董事出缺由董事自行遴選的原則。誠然,這個中基會改組的事件是牽涉到了政治干預基金會獨立運作的問題。然而,其所反映的,同時也是北伐成功、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試圖展現其主權,貫徹其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國民政府與列強角力的外交事件。中基會不但是管理美國所退還的庚款──中國近代帝國主義滄桑史上最為屈辱的一頁──的機構,它而且是北洋政府時期所成立的。國民政府要外抗強權、內除軍閥,還有什麼比改組中基會更能作為展現其主權的試金石?
這個中美外交角力事件,國民政府在一開始就注定是要失敗的。中國駐美的公使不只是不戰而降,而且根本就是倒戈輸誠。在中國,胡適又處處與派赴中國斡旋的孟祿(Paul Monroe)配合,一直到逼使國民政府收回改組中基會的成命為止。國民政府改組中基會失敗,除了是在中美外交角力上吃了一場敗仗以外,它更意味了留美菁英陣營的分裂。留學生回國以後,各自選擇了不同的政治勢力。改朝換代之際,既是政治勢力的重組,也是歸國留學生保護並推展各自利益與理念的時刻。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基會的改組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兩層深意:一、以胡適為代表的親美菁英擊潰了民族主義派的留美菁英;二、他們成功地聯美反制了國民政府。
胡適聯美反制國民政府改組中基會,是在他發表約法與人權政論的前夕。這是胡適一生當中最看不起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時刻。胡適跟國民黨爭約法、人權的政論誠然膽大、犀利、而且鏗鏘有力。然而,歷來的研究與分析都只著重於政論的本身,而忽略了其來龍去脈以及胡適抨擊的對象。首先,我們必須把胡適約法與人權的政論放在他當時的政治思想的脈絡下來分析。人權並不是胡適跟國民黨要約法的初衷。在他右傾法西斯主義的巔峰,胡適所憧憬的是有組織、計畫、與幹勁的政治。他回國以後,對國民黨幻滅,但仍然不改他對有組織、計畫、與幹勁的政治的憧憬。換句話說,在胡適1927年回國的當初,他追求約法,是在為中國立下一個建設現代國家的根本大法,與人權是無關的。
約法之所以會從建設現代國家的根本大法轉而成為保障的人權基礎,完全是一個意外。那讓胡適此可忍孰不可忍地起而向國民黨要約法來保障人權的人,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宣傳部長暨上海市教育局長陳德徵。胡適約法與人權的政論一共三篇。他所抨擊的就是這些狐假虎威、把羽毛當令箭的地方黨工。對胡適群起而攻之的,也是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為代表的地方黨部。這些地方黨部呈請嚴懲胡適的議案誠然一直上達國民黨中央黨部,而且還由國民政府指令教育部向胡適提出警告。然而,胡適在1929年「龍膽」單挑國民黨,其實是一個典型的「閻王好惹、小鬼難纏」的故事。而且,胡適自己也很清楚,他所棒打的不是「閻王」而是「小鬼」。試想:如果胡適所激怒的是「閻王」,則何須等待區、市、省黨部層層「等因奉此」的呈請嚴懲胡適呢?如果「閻王」真的有心要懲治胡適,則所有「撤職」、「緝捕」、「逮捕解京」等等令人怵目驚心的隆隆雷聲,如何會化解成為霑衣若濕的「警告」的小雨點呢!
胡適約法與人權的政論看似犀利與尖銳。事實上,他在當時的日記以及其它言論裡,已經處處表明了他與國民黨妥協的意願。我們記得胡適在1920年代初期宣揚「好政府主義」。到了1930年,胡適公開宣布他已經退而求其次,只要「有政府主義」就可以了。「好政府」他已經不奢求了。他只求中國有一個能「保境安民」的政府。邵建一向好說胡適不懂洛克,不懂古典自由主義。其實,胡適這個能「保境安民」、「有政府就可的主義」,就是回到了洛克的「政府越小越好」(limited government; little government)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精神。這個「有政府就可」主義,胡適在1930年代,又會把它進一步地引申成為「無為的政治」或者「幼稚園的政治」。但這是第四部第一章的主題。
當時的胡適仍然不看好蔣介石與國民黨。然而,放眼當時的中國,他找不到可以取代蔣介石或國民黨的權力中心。胡適從1929年到1930年的日記裡黏貼了許多汪精衛、改組派、閻錫山、馮玉祥、擴大會議派等等口誅筆伐蔣介石的電文。在許多場合裡,胡適也似乎擺出他與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政敵有共識的所在。所有這些,都容易讓人誤解胡適當時的政治立場。比如說,陳漱渝就認為:「在國民黨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間,胡適是腳踏兩隻船。」同時,他更進一步地認定:「人權與約法問題就成為了胡適和改組派反蔣的共同武器。」事實上,這不但高估了「改組派」在胡適眼中的地位,而且也沒瞭解到胡適已經押寶在國民黨的事實。胡適並沒有跟「改組派」合作,而毋寧是借反蔣的東風向蔣介石要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