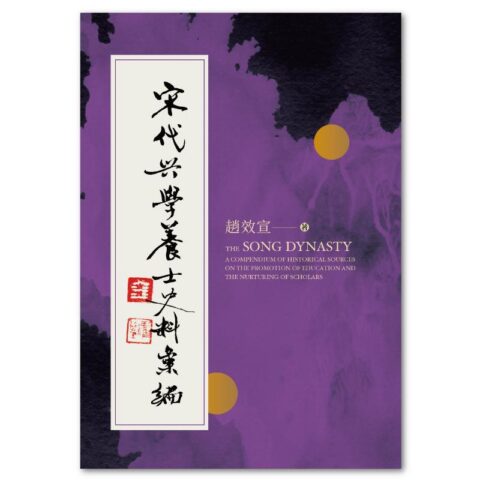想像「天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
出版日期:2023-12-21
作者:梁治平
裝訂:平裝
EAN:9789570871692
尚有庫存
《想像「天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對「天下」這一古時顯赫、後歸沉寂、於今為盛的中國大觀念之近代以來的命運,尤其是其最近十數年間的復興加以考察,一覽其消息,梳理其脈絡,以明其軌跡,知其所以,究其所以然之故。
梁治平認為,當下這一跨越政治、思想和學術領域的文明復興思潮,代表了一種重新認識中國、尋獲主體性的努力,同時也是不同社會力量建構新的意識形態的嘗試,其共享的語彙和話語之下,存在著關於中國的不同認識、理念和冀望。通過展示諸天下話語之間及其與現實間的複雜關聯,揭示其內部的種種緊張,以及來自外部對天下論的抵制和批判,本書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批判的初步嘗試。
作者:梁治平
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中西書院、光華法學院兼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律史、法律文化、法律與社會。著有《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法辨:法律文化論集》、《清代習慣法》、《禮教與法律:法律移植時代的文化衝突》、《論法治與德治》、《為政:古代中國的致治理念》等,編有《法律的文化解釋》等,並有兩卷本自選集《法律史的視界》、《法律何為》。
寫在前面的話
致謝想像「天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
舊章新篇:「家國天下」的當代言說
「文明」面臨考驗:當代中國「文明」話語流變
附錄 重新認識「中國」:當代中國的天下論說
寫在前面的話
本書是我另一本書的副產品,却也是一個應當獨立完成的研究。
上年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拙著《為政:古代中國的致治理念》,裡面第一篇文章的主題就是「天下」。寬泛些講,說那部書就是圍繞「天下」觀念展開的亦無不可,因為書中其他各篇的主題,若不是「天下」觀念某個面向的展開,就是「天下」秩序的制度性表達,而在中國古代的觀念世界中,「天」及「天下」無疑屬最基礎、最核心的那一類觀念,具有統領、聯接、支配其他觀念的作用。
誠然,《為政》所講述的只是歷史上的「天下」觀念,然而,就在沉潜於往昔思想世界的同時,我分明聽到了那些古老觀念的當代回聲。起初,它們只是零星地傳入耳際,不絕如縷,逐漸地,那些聲音連成一片,此呼彼應,喧囂不止。想到人類歷史上的這種思想激蕩、觀念沉浮,以及反映於其中的人心變幻、歷史變遷,我開始有一種衝動,想增補一篇勾畫當代「天下」論述的跋文,為生活在當下的讀者理解過去、思考未來增加一種觀照。《為政》「自序」末尾的一段話記述了當時的想法和之後寫作的情形:
在經歷了近百年的衰落和毀壞之後,「傳統文化」如今又煥發新生,在思想、學術、文化、社會乃至政治方面被賦予新的意義。在此過程中,「歷史」重新成為思想的焦點,各種當代「天下」論述也競相登場。眾聲喧嘩之中,新話語開始顯露,新意識形態的輪廓也隱約可見。有感於此,本書原擬以「眾聲喧嘩,『天下』歸來」為題,作跋一篇,置於書末。但是最終,這篇計劃中的「跋」因為篇幅過大而沒有收入本書。
這篇「因為篇幅過大而沒有收入本書」的計劃中的「跋」,就成了讀者面前這部書的主幹。書中其餘篇章,儘管各有機緣,也都是由此生發出來的。
前文寫成當年,我受邀在北京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院報告,那次報告的主題就出於這項剛完成的研究。報告時,為能在有限時間內相對完整地呈現這項研究,我改變了文章的敘述方式,轉而採用一種更具結構性的主題處理方法,這樣一來,同一項研究就有了兩個不同的「版本」。報告版後出,雖然簡略,却也有文章版所沒有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種不同的論述方式呈現。二者並列,對照呼應,或有助於讀者更好地了解和把握這一主題。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和期待,我把報告版也附在書後供讀者參考。
另外兩篇後來寫成的文章,一篇以「文明」為主題,另一篇討論「家國天下」的當代言述,二文均圍繞當代「天下」論述中的關鍵詞展開,其內容雖與前文略有重複,但側重點不同,可以被視為本書主題的細化和拓展。因此,這兩篇文章雖然都獨立成篇,但放在前文提供的框架裡來閱讀顯然更合適。
在這一研究以文章和報告形式發表之後,我不止一次聽到讀者和聽眾發問:你介紹了那麼多人的觀點,那你的觀點是什麼?具體言之,這個提問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問:你的「天下」觀是什麼?二是問:你對提到的那些觀點持什麼看法?應該說,讀者和聽眾有這樣的反應不難理解。因為一般說來,人們除了有了解事物的好奇心,還期望得到解决問題的答案,尤其是涉及那些容易引起爭議的人和事的時候。如果期待落空,他們就會覺得不滿足,「不過癮」,因而提出上面那類問題。我承認,這類期望和要求有其合理性,事實上,有很多人、很多文章也回應和滿足了這種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也應該做同樣的事情。對於讀者和聽眾的這一反應,我的回答是這樣的。
首先,「你的天下觀是什麼?」這個問題所期待的,是我能在流行的各種「天下」論述中提出我自己的一種。坦白說,我既沒有這方面的興趣,也沒有這樣做的意願。甚至,為了避免給人某種躋身其中的印象,我還謝絕了一些相關學術活動。我這樣說,並非表示我對這類論述抱有某種成見,更不會改變我一直採取的傾聽和理解的立場。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因此對這些思想和觀點沒有自己的看法呢?這要看問者想要聽到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意見。本書「特拈出『天下』這一古時最為顯赫、後歸於沉寂、而於今為盛的中國大觀念,對其近代以來的命運、尤其最近十數年間的復興略加考察。一覽其消息,梳理其脈絡,以明其軌跡,知其所以,究其所以然之故」。(引自前文,見本書)要做到這一點,不能只做描述,也要有分析與評斷,本書對當代「天下」論述興起背景的分析,對其性質的探究,對其與意識形態關係的討論等等,即屬此類。自然,問者更感興趣的也許不是這類「意見」,而是那些意在臧否人物、評點文章的「看法」:比如如何論列某人,如何評價某文,對某個具體命題贊同與否等等。我不否認,本書基本不提供這類意見,而且,我也不認為這類意見的有無對本書主旨有何影響。本書既然試圖以真實、完整、客觀方式呈現當代中國一種重要思潮及其變化,就應避免以一己好惡為取捨標準,或者以論辯方式去表達己意,而應當客觀公正,不因人廢言,也不因言廢事,盡可能完整地介紹相關論述,同時揭示這些論述所面對的內外批評,也包括它們彼此之間或隱或顯、有形無形的「對話」關係:從資源共享、觀點呼應所形成的相互支援,到意見分歧、立場相左而造成的緊張和對立。的確,比較那種以表達己見為快的做法,我更願意去展現那些包含多個層面和面向的交織纏繞的複雜關係,而把比較、鑒別和評判的工作留給讀者。我相信,在這些問題上,激發讀者思考比讓他們接受我個人的意見更有意義。也是出於這種想法,在展現那些微妙關係的時候,我也避免以論斷方式得出結論,而是排比材料,引而不發。這樣做的結果,便是留下更大的閱讀聯想空間,以便讀者通過自己的思考去建立關聯、做出判斷和得出結論。誠然,設定問題、取捨材料、排列觀點、確定敘述結構與方式,這些也都是選擇,也透露出作者的立場、關切、見解和意圖,就此而言,讀者想要從中窺見他們感興趣的那類意見的蛛絲馬跡也未嘗不可。雖然,這到底不是一部供索引之書,其中並無微言大義。
說到這裡,需要提到對本書主旨的一種錯誤解讀。
在一篇對本書主文的譯介中,有人將拙文視為對政府和知識界的「籲求」(plea),請求允許知識人自由參與中國當下的意識形態建設:「讓我等效勞吧」(「let us serve」)。1 這種解讀是對拙文基本立場的錯置。拙文最後部分以引證他人的方式談到意識形態與國家機器的關係,談到意識形態的性質及其力量所在,以及「知識人自由參與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性。但這與其說是一種籲求,不如說是一種診斷。診斷者的立場是傾聽、觀察和判斷,當然,通常還包括提出建議,開列藥方,而拙文則止於診斷,不涉療治。
當下諸「天下」論述的提出,借用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趙汀陽教授的說法,意在「重思中國」,進而「重構中國」。與這種志向和期許相比,本書為自己設定的目標要微小得多,它只是試圖理解中國,包括上述種種「重思」「重構」的努力。而這一嘗試理解的事業,在我看來,不但十分重要,要獲致進展也相當困難。比較這種困難,這項工作不易得到恰當的理解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想像「天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
一
2018 年央視春晚在北京的主會場之外,設有四個分會場,其中之一設在山東泰安,用的是泰山東麓燭峰腳下「泰山封禪大典」的舞台。一時間,媒體上充斥了歷史上有關封禪的釋義和記載。於是,普通民眾都知道了「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的泰山封禪,是一樁象徵國家鼎盛、天下太平的盛事。而有 35 年歷史且已成為國家項目的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選擇泰山腳下封禪大典舞台為其分會場之一,同時以多語種向海內外播出其節目,當然也不單純是為了娛樂。也是在 2 月,央視春晚播出後 3 日,央視網推出 1 分 35 秒的微視頻《家國天下》,視頻讓人們「透過習近平總書記濃濃的家國情懷」,看到「他對家庭、對國家的使命與擔當」。這些節目和視頻,透過電視、互聯網和移動終端設備,為數以億計的觀眾接收和觀看。熟悉近代以來歷史的人,對於這些現象一定印象深刻。因為,出現於上述場景中的那些概念、名號和意象,如家國、天下、封禪、教告、天命、太平等等,曾經是中國歷史上居於支配地位的大觀念,而近代以降,這些觀念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傳統,又成為各色革命質疑、批判甚而毀棄的對象,其地位一落千丈,乃至不保。因此,它們在今天的重現,尤其顯得意味深長。不難想見,在這種變化後面,發生了多少社會變革,有多少思潮激盪,又有多少智慮與努力、成敗與希望,潮起潮落,動人心魄。我們因此也想了解,這些變化究竟緣何而來,意義何在,又會把我們引向何方。為此,本文特拈出「天下」這一古時最為顯赫、後歸於沉寂、而於今為盛的中國大觀念,對其近代以來的命運、尤其最近十數年間的復興略加考察。一覽其消息,梳理其脈絡,以明其軌跡,知其所以,究其所以然之故。
二
古之所謂「天下」,實為一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文明秩序。此道德文明秩序中,天生烝民,王受天命,敬德保民,推廣文教,由中而外,由近及遠。如此建立起來的天下,或狹或廣,可伸可縮,隨歷史條件而變化,卻可以規範家國,安頓人心。古人言「天下」,兼有描述、想像、理想、規範諸成分,因此,在古代思想世界中,「天下」觀念既是人倚為認識和想像世界的概念架構,也是人用來證成或批判既有秩序的判準,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天下」這一對古人如此重要的基本觀念,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之際,卻被認為是造成國家積弱的主要原因而受到猛烈抨擊。批評者認為,以「天下」觀念為依託的華夷之辨,守持中國中心論,故步自封,不知世界之大,最終招致外侮。不僅如此,中國人過去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只見天下,不見國家。改朝換代,無關其痛癢,故不以異族統治為意。此種天下主義不敵近世之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其勢甚明,其理不言而喻。因此,中國欲圖強,就必須拋棄家族主義、天下主義,改宗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在這種看法的支配下,「天下」觀念漸次被萬國、國家、世界等觀念取代。尤其是 1900 年以後,中國國勢日頹,國家主義的呼聲日益高漲,建立民族國家的步伐加快,「天下」觀念終於退出國家論述,幾至銷聲匿跡。儘管如此,作為中國歷史上長期支配人心的大觀念,「天下」概念雖已遁形,其神猶在,而以不同方式潛存於、表現於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即使是在包括各種舊觀念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徹底毀棄的革命年代,其影響仍依稀可見、有跡可循。這意味著,要理解中國近代的政治、社會及思想、文化變遷,人們需要深入到各種流行話語背後,細心尋繹傳統思想的痕跡。以下列舉數點,以見其影響大概。
天下既為一普遍有效的道德文明秩序,必不以地域、種族為限制。所以,傳統的夷夏之辨立基於文教,而非其他。然則,宋以後,尤其經歷元明及明清鼎革,一種基於種族和地域的夷夏觀逐漸興起,而在清末發展為漢族中心的民族主義。於是,在清末的民族主義思潮中,人們可以看到兩種互相競勝的民族主義,一種「以種族為民族」,一種「以文化為民族」。此種差異表現在民族國家建構上,前者便是基於所謂「中國本部」十八行省的漢族國家,後者則是融合了漢、滿、蒙、回、藏、苗諸族群,承繼清王朝統治疆域的中華民族國家。民國肇始,五族共和,採取的正是後一種民族主義。中華民族由此確立,成為中國現代國家的基礎。可以注意的是,這樣一個建構近代國族「想像的共同體」的事業,不僅從一開始就承繼了古代天下觀的文明論視野,且事實上繼承了清王朝的「天下」,其完成也可以被視為對傳統「天下」觀的消化。進入 1920 及 1930 年代,受到列強尤其日本肢解和瓜分中國的壓迫和刺激,中國學術界對邊疆史地及民族問題的關注空前高漲,並藉助於現代學術分科如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人類學、民族學諸方面的研究,為中華民族的統一性提供堅實的證據。此一努力,被學者稱為納「四裔」入「中華」的嘗試。實際上,這種通過納「四裔」於「中華」、建構中華民族的努力一直延續至今,在當下有關諸如新清史的論辯和某種貫通古今的歷史哲學思考中都能夠見到。不過,在關注這段歷史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儘管支配原則不同,同樣是整合諸民族的構建「想像的共同體」的工作,早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前數百年就已經開啟並且獲得成功。正如清初諸帝強調文化的夷夏論來為清王朝統治的正當性辯護一樣,清代思想學術的顯學今文經學尤其是其中的《春秋》公羊學,標舉大一統觀念和禮儀原則,致力於構建一個根據禮儀原則而非地域和種族組織起來的政治共同體。因此,毫不奇怪,清代注重邊疆史地研究的輿地學也是在今文經學的背景下發展起來。這些發展和改變不但為日後國人的中華民族想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資源,甚至直接構成了中國現代國家的物質基礎。
天下觀念的另一特徵是其超國家性,這種超國家性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天下觀念與普遍的文明秩序和王道理想相連。「天下」的這一道德特性令其在價值上優於國家一類政治實體。其次,天下因文明而立,其範圍伸縮無定,漫無際涯。因此,對現代國家極具重要性的領土及疆界諸因素,在天下觀念的視野中並未受到同等重視。誠然,這也正是晚清以來天下觀念日漸式微、終至為民族國家觀念取代的根由。然而,近代中國知識與政治菁英對天下主義的棄絕並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樣徹底。儘管在文化與政治、天下與國家之間,他們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後者,但在他們內心深處,古老的天下觀念與王道理想並未絕滅,它們不但作為某種思想上的習性存在,而且作為一種精神上的價值仍具感召力。畢竟,天下觀念乃是與其文化認同相關的歷史記憶的一部分,而且,天下觀念所具有的那種超越性的道德理想,不只是強者包納四夷的文化意識形態,也是弱者對抗強權、增強本民族精神持守的思想文化資源。民國初年,中國知識界一度痴迷於互助主義尤其是世界主義,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的勝利是「公理戰勝強權」、「大同主義戰勝種族偏見」。這種樂觀情緒所表露的,與其說是時人對於現實的冷靜判斷,不如說是其心底乃至無意識中對於天下大同的固執信念。儘管這種對公理勝於強權的信念在巴黎和會之後歸於破滅,國人對世界主義的熱情再度讓位於民族主義,是這種民族主義仍然是參雜了世界主義的,或是以世界主義為其更高目標的。比如,孫中山在強調民族主義對世界主義的優先性的同時,就主張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基礎和前提。他說:「我們要將來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這便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真精神」。這裡,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的緊張轉化為一種歷史演進上的遞進關係,而這種朝向世界主義、大同之治演進的潛在可能,被認為恰好植根於中國固有文化的精神之中。這當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