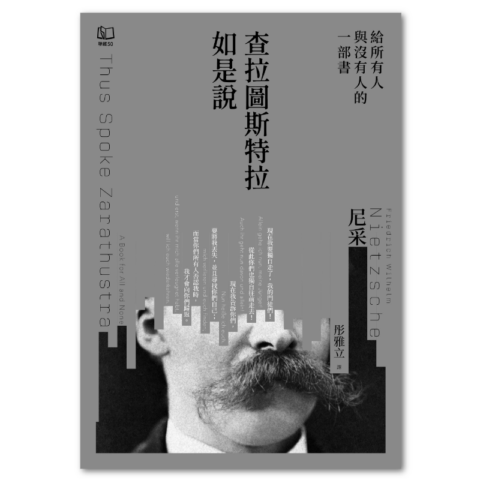莊子的風神:由蝴蝶之變到氣化
出版日期:2010-02-09
作者:趙衛民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24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5489
系列:文化叢刊
尚有庫存
莊子生於亂世,卻是中國思想家中唯一會做夢和發笑的思想家。夢和笑對他的思想有積極的意義,突破了日常成見的束縛和封鎖,指出了一條超越之路。他也是中國思想家中特別突顯文學想像的力量:卮言如詩,狂醉而深情;寓言若夢,恢恑譎怪。在他的哲學劇場裡,萬物都粉墨登場:無論是神話中的鲲鵬,還是樹神精怪;無論是聖賢孔子、顏淵,還是殘缺醜怪,都成為他牽線的木偶,演出殘酷而又溫柔的批判劇。「大鵬怒飛」、「莊周夢蝶」、「庖丁解牛」、「壺子示相」這些寓言已成激動人心的美妙傳說,到底能表達出什麼深刻的意義呢?看過本書,都能得到完美的答案。
氣化之道 ── 釋〈逍遙遊〉
忘我與物化 ── 釋〈齊物論〉
技藝與養神 ── 釋〈養生主〉
生活的智慧 ── 釋〈人間世〉
殘缺的美學 ── 釋〈德充符〉
道與命運 ── 釋〈大宗師〉
無與深淵 ── 釋〈應帝王〉
在莊子的哲學劇場裡,以上都得到了完美的答案!
作者:趙衛民
趙衛民,浙江東陽人。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組畢業,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所教授,曾任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所教授、聯合報副刊資深編輯。青年時代寫詩,曾獲中國時報長詩優等獎、國軍文藝長詩及散文銀像獎計十餘種。著有詩集《猛虎與玫瑰》、散文《遊戲人生》及論著等二十餘種。研究範圍以老子、莊子、尼采、海德格及後結構主義思潮德希達、德勒茲、傅柯等為主。
前言 莊子的夢與死:由蝴蝶之變到氣化
第一章 莊子的寫作方式
一、寓言
二、重言
三、卮言
四、結語
第二章 氣化之道 ── 釋〈逍遙遊〉
一、風的哲學
二、聖人無名
三、有用與無用
四、神人無功
五、氣化之道
第三章 忘我與物化 ── 釋〈齊物論〉
一、人籟、地籟、天籟
二、真宰與真君
三、平齊物論
四、道通為一
五、天府和葆光
六、夢與物化
第四章 技藝與養神 ── 釋〈養生主〉
一、善與惡
二、技藝之道
三、庖丁解牛
四、養生
五、養神
第五章 生活的智慧 ── 釋〈人間世〉
一、道德與名實
二、心齋
三、命運與義務
四、言語和行為
五、用與不用
六、狂人之歌
第六章 殘缺的美學 ── 釋〈德充符〉
一、德與形的關係
二、過錯與全德
三、才全德不形
四、天養與無情
五、殘缺與得道
第七章 道與命運 ── 釋〈大宗師〉
一、天與人的關係
二、道與時間
三、生死存亡為一體
四、遊乎天地之一氣
第八章 無與深淵 ── 釋〈應帝王〉
一、聖人之治
二、壺子示相
三、何謂深淵
四、聲音與聽覺
五、無的實踐
第九章 結論:從水的元素到風的元素
一、由〈天下〉篇至魏晉玄學
二、水的哲學
三、風的哲學
前言 莊子的夢與死:由蝴蝶之變到氣化
夢是真實還是虛幻?莊子紀錄下他的夢境,並作了「夢的解析」,莊周夢蝶,這與佛洛伊德多麼不同,我們無法從中讀出任何伊底帕斯情結。蝴蝶輕盈飄然,哪裏來弒父戀母的沉重罪惡感?在夢中栩栩然化為一隻蝴蝶,這是適合莊子志向的(「自喻適志與」)。在夢中莊子完成了蝶變,夢還不只是夢想而已,故而在夢中不知道自己是莊子(「不知周也」)。
在夢中完成的蝴蝶之變,醒來還持續嗎?當然還持續,只是不能還認為「我是蝴蝶」,這樣就會被認為是神經病。醒來後,意識清醒,必須認清自己不是真的成為蝴蝶(「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但潛意識的影響,必然造成意識的變化,這是莊子生命中重大的生成變化。套用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的意思,這是生成-蝴蝶(becoming-butterfly),蝴蝶之變改變了莊子的生命型態,完成了莊子-蝴蝶在人間的新身份。莊子釋夢曰:「此之謂物化。」從受到蝴蝶的影響而變化,而成為隨順蝴蝶而變化;莊子不是捕蝶人而是蝴蝶人。生命太沉重,故而莊子想飛,尼采說:「人已學習了一切動物的美德,只有飛鳥還超過他。」「想飛」的真實感受,到最後完成了一大超越現實生命的變化,故名之曰蝶變;沒有蝴蝶之變,就沒有大鵬之變。在哲學家中,莊子不也是一隻不凡的神鳥嗎?蝴蝶輕盈飄逸,莊子風格(無論生命或行文)也是瀟灑飄忽;神鳥本是風鳥,從蝴蝶到大鵬,只是一氣之化而已。物化與變形,其義一也;不是形體真的變了,而是蝴蝶或大鵬進入了他的身體-知覺中。
如果稍加衍伸,蝴蝶多少帶點美少女意味,蝴蝶之變也是女人之變。不是雌雄合體,而是女人進入了他身體-知覺中引發他身體-知覺的變化,所以神人才是「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皮膚晶瑩剔透,像擦了雪花膏似的。
郭象注此段曰:「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把夢與醒視為死與生,錯過了蝴蝶之變的精采處。郭象只把「物化」解釋為生死的變化,這是郭象的狹隘。透過郭象,不是以理解莊子的風神;甚至透過魏晉玄學,無法恢復先秦道家的風貌。持傳解經的成規,也只是陋規,必須跳出成規之外。郭象為小,莊子為大,這才是小大之辯。
同樣,從〈逍遙遊〉中惠施的大樹無用論,莊子說:「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莊子提出「逍遙無為」的思想對治。以至於〈人間世〉中匠人的「櫟社見夢」,大樹神說以不材之木之無用,乃成其大用。那麼,匠人也完成他的神木之變。匠人在夢中完成了神木之變,匠人-神木就是在人間的新身份,醒來後,潛意識完成的,在意識上收穫,神木必將進入他的身體-知覺中,這是人成為神人的企機-這也是南伯子綦見商丘大木,以不材之木而成大木,終能悟道。
物化當然也包含死生變化,物化本以「喪我」為工夫。既已「喪我」,生死不過一氣之化,生死存亡為一體。這是在自然時間上的生成變化,不及於在精神開展上的時間變化。雖說生死存亡為一體,但道家仍有養生之道,可以保護身體、保全生命(「可以保身,可以全生。」)。
物化之道的生死之變(「辯」),在〈內七篇〉中首先出現的是「庖丁解牛」。「庖丁解牛」也是藝術之道。
「桑林之舞」是國家祭祀的大典,宰牛以為犧牲,祭祀桑樹神。桑樹的桑葉用以養蠶,蠶吐絲以製絲綢,運銷各地,是國家經濟命脈。犧牛濺血,滋潤大地,讓桑樹可以繁衍生長。「庖丁解牛」是國家級的演出,也是民族傳統的節慶。
首先是藝術家庖丁。由族庖處理牛體的輕慢,到良庖的技術熟練,花費了近三年工夫,都不見直接面對活體的牛。由良庖製解牛體的技術到庖丁面對活牛的神乎其技,並未說明花費多少年工夫。時間上的斷裂是一異質的跳躍:良庖成為庖丁,是由好廚子-躍成藝術家。藝術家的創作活動,是讓活牛得以解體的超完美演出。解牛的過程,是藝術作品;活生生的牛,是藝術家所面對的力量-世界。
藝術家的創作活動,除累積了技術經驗以外,「臣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才能超過熟練的技術,成為巧妙的藝術。創作活動以身體-知覺為基礎,「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是像有節奏的舞蹈般一樣的身體-藝術。解牛的過程成為舞蹈,不僅只是表面的身體姿態,牛並非靜止的自然素材,任他隨意加工,牛所展現的是自然的渾沌力量。在人與牛之間,必有力量對抗力量的搏鬥過程,身體的手、肩、足、膝各部分協作,必然發揮最大的力量,進而產生運作的節奏。牛的抗拒、奏刀的進程,必在力量的節奏間產生姿態的美感。
藝術家所面對的世界或自然,見現在一隻躁動不安的牛身上,而力量卻產生於氣化活動的空虛之處。藝術家在某種型態上也有暴力美學,他必須發揮最大的力量,奏刀得以進入牛骨中的空虛之處。欣賞者可感受到的美感,除了有節奏的身體姿態外,還有「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奏刀的聲音、牛骨分離的聲音莫不合乎音律,甚至視覺上的美感是配合聽覺的美感的。
藝術家的創作過程,必面對創作過程的艱難,在細微處要小心謹慎。「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行為變得緩慢,動刀微妙,奏進筋結的空虛處。筋結空虛處,正是氣處,藝術家庖丁此時視覺停止,神行於糾葛複雜的筋結之間,在空虛之處亦即氣化之處,裂解了狂暴的力量,碩大的牛體才像土塊般委落。庖丁對自己的身體-藝術的表現,「躊躇滿志」,但他所完成的是「道隱於小成」的小成之道,他的世界仍須依待外在的條件即解牛來完成。生命的藝術仍得依賴養生之大道來完成。
庖丁解牛的技巧,是可見的形象或形式,至於「道」,「進乎技矣」是不可見的思想或內容。文惠君初則贊歎高超的技巧,庖丁的解說,才使得長期的專注和苦心得以見到,藝術之道必得在身體-知覺的感受上伸展,並發揮最大的力量而產生節奏,才得以進入自然狂暴的力量之中。文惠君的「吾得養生哉!」則取得了人生的維度,欣賞者別有會意的神態,是悟得了「神游於物之虛」的道理。超過解牛的藝術的是生命的藝術。人生的複雜糾葛,在物事變化之處,小心謹慎,養神於虛空之處,不發生實質的磨擦,才能涵養生命。
尼采說:「藝術提醒我們動物精力的狀態;它在一方面是把生理性發揮到意象世界的過度和滿溢;在另一方面,通過強化生命的意象和渴望而刺激動物的功能-增加生命的感覺。」這種增加生命的感覺在莊子這邊,逐漸轉入養生存神。在〈人間世〉中,自然暴烈的力量-轉為以暴君為代表的戰爭集團性暴力,解牛的神完氣足是也就轉為支離疏的「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天下已不可為。
莊子的時代,戰爭兵禍不斷,「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幸福比羽毛還輕,不知能承載什麼;災禍比大地沉重,不知如何趨避。要避開災禍,就如糾葛複雜的筋結間回身,離開見用於天下的世俗思想,在更廣闊的自然空間中,尋求逍遙的至福。面對戰爭年代的沉重,你得有蝴蝶之輕;先完成蝴蝶之變,才有大鵬之變。先有物化,才得以逍遙。死生存亡至此,也就成為外在事件的變化和命運的進行了。
第五章 〈人間世〉:生活的智慧──莊子的風神
活的智慧,是深刻的生活體驗所得到的智慧。 真理是遲到的真理,智慧是晚熟的智慧,只能是結論。真理或智慧,當然是融入了道家的特殊實踐方式,借用〈應帝王〉的話說「體盡无窮,而游无朕」。對人生有無窮的體驗而優游於沒有朕兆、形跡的地方。這句話可表達〈人間世〉的總綱,但這是如何可能的呢?何謂生活體驗?似乎應該給予哲學的說明。如果比配於〈養生主〉中日常操作、專門技術、技藝的三層次,日常操作「習焉而不察」,自無待論,莊子似展示專門技術的規則,即說明何謂生活體驗,而更展示技藝,即生活的智慧。
現在面對的不是善於養生的文惠君,而是代表暴力的政治權力,可否施展宰牛的「必殺絕技」呢?莊子顯然對於國家體制無論是由聖君或暴人統治,是持保留態度的。
壹、道德與名實
顏淵想要拯救衛國,顯然是懷抱著文化理想。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
衛君正值壯年,行為專制獨裁,結果是輕率地濫用人民去送死,遍死溝野如草芥。衛君看不見自己的過失,什麼是過失呢?「所有對別人造成物質上的或精神上的損失,而且還有對他人的辱罵,就構成了對他人的過錯」。 濫用人民送死,這過失是很大的,顏淵如何讓衛君看見自己的過失呢?
孔子顯然不贊成顏淵,道德教化對於一個暴人是可能的嗎?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與己者未定,何暇於暴人之所行?
古時候所謂的至人,道德修養是存之於自己,才能夠存之於別人。如果存之於自己的還不能確定,怎麼能讓暴人看見他自己的過失呢?為什麼以顏淵的道德修養,還不能確定什麼「存之於自己」?孔子提出道德修養艱難的問題,就是道德與名實的問題。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札者也;知也者爭之器者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者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道德為什麼被名聲敗壞?儒家把道德視為人類社會最高的價值,這道德理想的價值必要爭取別人的承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在死後名聲要相稱於他的道德理想。即使在世時不求名,道德求的是一生的名聲,就孔子而言,在世時,名聲是在道德「之外」的。那麼在世時,道德與美名俱有,如為求美名而行道德,道德就被美名所敗壞。這是種「形象與自我的異化的話,我稱這種現象為『物化』,形象的物化。」 換言之,美名是道德的異化或物化。而「知」是由「聞」所規定,即所謂見多識廣的見聞之知。有美名的,彼此相傾軋,見聞的多少也產生了競爭。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認為:「人們並不是為了知識而認識,也不是為了遍求純粹真理,而是為了獲取權力,排除他者。」 人間社會的爭端就由此開始,莊子把此二者視為「凶器」,看來戰爭並非只如老子所說的:「佳兵者,不祥之器。」《老子.三十一章》是在戰場上。求美名,多見聞,不可以用來處身行事。如果道德純厚,信用實在,卻不通人情;不爭美名與多見聞,卻不解人心。強要以道德理想在暴人前面表現(術)的話,這是想要用道德理想約束盲目的衝動與暴力,人家就討厭你的美德,這是害人,害人的人必被人反來加害。這多少呼應老子:「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你如果不說話而保持沈默,王公必欺壓你而騁其敏捷的才思。你的眼睛被眩惑,你的臉色和順了,你的口也揣摩衛君的心意,心裡就想成就他的意思。所以沈默無言還是不行,慢慢就變成順從衛君的心意了。如果衛君逐漸不信任你道德的提醒,你就會死在暴君之前了。如果一種擁有政治權力型態的暴力,卻又有敏捷的才思,光憑道德就很難處理其中複雜的糾葛了。
人間世就是人類的生活世界,生活體驗在生活世界中。如果把胡塞爾(Edmunt Husserl,1859~1938)的思想定位在意識主體的意向性活動,很容易錯過他試圖闡述生活經驗的內在結構的企圖。「這裡對象是像它們出現那樣,這樣說,像它們在生活經驗的脈絡裡作用那樣。我們在我們的活動中所回應的並非『只是表象』,而是在經驗裡出現的實在。」 意識到對象,對象就是在經驗裡出現的實在。衛君作為一暴人,就如實地站在那裡,而被經驗到。那麼莊子如何構想這種具體經驗的呢?「為了把握住本質,我們設想一具體經驗,然後在思想中使它變化,想在想像它在所有方面有效地修改。通過這些變化而不可改變的,是追問中心現象本質。」 這種具體經驗是設想的,譬如說:可以經由對與嚴父相處的經驗出,揣摩與暴君相處的經驗,再設想各種可能的變化,通過這種變化而不可改變的,是「經驗的模式(mode)」,一個有道德理想如顏淵與暴君相處各種可能的經驗中最本質的經驗。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且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止。……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桀、紂是暴君,關龍逢和王子比干都修養德性,未居君位而能愛護百姓,以下位觸犯君王而遭殺身之禍,這兩位暴君無實卻好名。但是堯和禹是聖君,攻打的叢枝、胥敖、有扈三小國,燒殺而成一片廢墟,國君也被刑戮,用兵不止,求「實」無已。這裡的實是什麼意思呢?福柯說:「戰爭實際上是歷史話語真理的子宮。『歷史話語真理的子宮』的意思是:真理或哲學或法律同使人相信的那樣相反,真理或邏各斯在暴力停止的地方就不存在。」 堯和禹已有聖名,故要求文明教化廣被之實,將三小國視為野蠻,故征伐之,卻使其亡國。兩暴君是好名,兩聖君是已有美名(對莊子而言,可能他們的美名超過了道德理想),造成的一樣是殺戮。道德所隱含的暴力,已被明確的提出,莊子認為儒家聖人所不能勝過的就是名實問題。莊子有沒有勝過的方法呢?其實在〈消遙遊〉中,假託為道家聖人的許由已說出「名者,實之賓也。」換言之,實為主,不需要名,這節是說明「聖人無名」。老子說:「道常無名。」(《老子.第三十二章》)莊子自可說得道者「聖人無名」。
貳、心齋
在這裡,出現了類似〈齊物論〉中南郭子綦的「喪我」功夫。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徙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庇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之徒。
顏淵想出向自然、向人、向古人的學習方式,看是否可與暴君相處。學自然,內心保持天然的正直,就認為國君和自己都是天的兒子,還求什麼人家稱道為善或指責不善的呢?這樣似可避開名的干擾。這樣的話,回復了天真的童子。學人,執笏、長跪、鞠躬都是人臣之禮,大家都這樣做,我也這樣做,人也不會指責我了,對人要表現得能變通。內外既成,就向古人學習,教化的言語,也實際是諷責他。古時人也是這樣,不是我獨有的。這樣,雖然保持正直,也不會被人怪罪了。顏淵分內、分外、分歷史,主要還是內心保持天然的正直,但對外是另一套,要有禮數,而教化的語言則是古己有之。主要在歷史文化的脈絡中試圖擺脫名的干擾,行人臣之禮,化己言為古之教言,看能否行教化之實!
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孔子批評他太多方法而沒有條理,也只能做到無罪,因為他仍效法自己的成心。換言之,顏淵的天然的正直,在孔子看來仍是成心。內心保持的天然的正直,對外有禮數,卻假託古人之言,好像自己免於承擔話語指責暴君的重量。保持在內的天然的正直就是成心,因為它樹立了一套道德標準。福柯說:「如此描述的『前概念』……不是呈現一個來自歷史深處並貫穿著歷史的範圍,恰恰相反,它是在最『表面』的層次上實際應用的規律整體……在我們提出的這種分析中,形成的規律不存在於『思想』或個體的意識中,而在於話語本身。因此,它們以一種統一的匿名形式,強加給所有試圖在這說話場中說話的個體身上。」 福柯的意思是:說話的個體在「說話場」中所形成的話語,形成的規律是一種統一的匿名形式;不是我說,而是「我們說」。雖然傅柯所探討的「前概念」是當代的話語,不是來自歷史深處,但以莊子時代的「古人說」卻一直貫穿到當代,並且形成「我們說」。福柯說不存在於「思想」,前概念是在概念以前發生;不在個體的意識中,因為話語的規律不是個別的,而是共同的「說話場」。成心當然不是個別的,而是共同形成的價值標準,就有在於話語的規律中。
若一志,無聽之心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之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這是孔子教顏淵「心齋」的妙道,心齋就是齋戒掉成心。若一志,只是「好像」專心一致的注意,其實並非如此。不要用耳朵(感覺器官)去傾聽,而是用心(專心一致)去傾聽,但用心去傾聽,也止於符合。 談話時用耳朵聽是閒談(idle talk),在談話中所說的被理解,所談及的只是被近似地和表面地理解 ,是日常談話。那麼用心聽,是意向性:胡塞爾……是去顯露意識的意向性洞見:我們的認知有一意識到某物的基本性格,在反省現象出現的是意向對象,我對它有思想、有知覺、有害怕,等等。 意向性指向某物的意識,那麼是意識與意向對象的符合。但這樣的專心一致無法避免成心,「主體性並不包含偶然的特殊性,而也有一超級性的層次……(超越)主體作為人格,包含了一些主體性層次。」 這正是孔子批評顏淵的「猶師心者也」,仍想行教化暴君之事。所以不要用心去傾聽,而用氣去傾聽。
孔子說要「虛而待物」,虛是虛其成心,虛其自己。心齋就是忘我、喪我,才能等待事物向我們顯現。「在斷片50中,logos和『傾聽』中的聯結是直接地表達了:『如果你聽到的不是我而是logos,那麼聰明的當然是說:一切是一。』這裏losos確然視為某些可聽的。」 不是聽到說者的意向,而是聽到一,聽到道的聲音,那不是人為的聲響,是萬物與我為一的氣化之聲,恰正是實質的意向性所不是的。所以道集合於一片虛空當中。
如果把談話的三層次,比配於〈養生主〉中庖丁解牛的三層次,似乎有一對應。日常操作=閒聊,專門技術=意向性,技藝=聽之以氣。那麼庖丁「臣以神遇」的「神」相當於氣化,文惠君的「養生」則相當於「心齋」了。即虛見氣,即氣化神,仍是莊子哲學的總綱。
為明〈人間世〉以上的概念關係,試以一表明之,並可與〈養生主〉的概念比較。
日常操作 專門技術 技藝
聽之以耳 聽之以心 聽之以氣
閒談 意向性 虛而待物
耳目 心知 物化
坐馳 師心 心齋
常人 儒家聖人 神人
由此可知,〈人間世〉是要展現神人的實踐工夫入路。〈養生主〉中,文惠君「得養生焉」是得到養生或養神的要旨。但在〈人間世〉中,卻表現出在暴君前如何養神的實踐工夫了。庖丁的神乎其技,對養神只是小成之道,如能在濁世中面對暴君,時有生殺之危,仍能養神,這就是神人。
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跡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
如果你能像游戲一樣進去衛國,不要被名聲影響。如果進去了,就像鳥聲天然鳴叫一樣,不進去的話就停止。不要空門大開,給人毒害的餘地。不出門,應事是出於不得已,這樣就差不多了。人不留下形跡很容易,但不走路卻是困難的。出自於人為,容易產生虛假;出自於天然,就難產生虛假。聽說有翅膀的才能飛,沒有聽說過沒翅膀的也能飛。聽說有智慧的才能知道,沒聽說無智慧的也能知道。你看那空缺的地方,正如空虛的房間發出白光,吉祥就棲息在那地方。
「正見到是認知的本質,在『見到』中常有某些比視覺過程的完成更多的在作用……『見到是關聯到在場自己發光,見不是由眼睛,而是由存有的亮光決定……知識是存有的記憶,這是為何記憶(女神)是謬思之母。』」 知識是道的記憶,有智慧才能有知識,認知的本質正是見證到道,「見到」不是視覺感官的見到,而是道的出現,存有之光聚集在空虛的地方。如果心不保持虛靜,意念就向外飛馳,這叫「坐馳」。如果使耳朵、眼睛的感覺向內通達而離開心智的機巧,鬼神都來聚集,這是神秘化,何況是人呢?這是萬物的變化,即是物化。道而物化。「這凝聚、聚集,讓-停留是物的物化(thinging),這天和地,必死者和神性統一的四元,停留在物的物化,我們稱『世界』。」 道凝聚在物化中,物化即天地,即自然,自然也是道的別名,天和地,凡人與得道者是統一的四元。物化,形成了世界,世界也世界化,即天地,即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