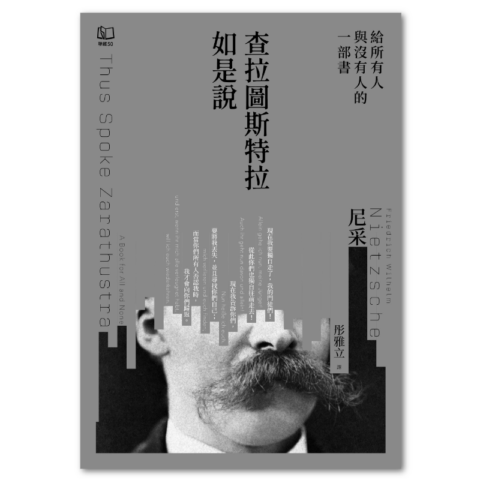泰鄂提得斯
出版日期:2016-05-04
作者:柏拉圖
譯注者:何畫瑰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344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7215
系列:聯經經典
尚有庫存
《泰鄂提得斯》(Theaetetus)是柏拉圖知識論的代表作
為許多知識論議題提供了豐富而沒有僵固立場的探討
一如當代倫理學家本那‧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形容,《泰鄂提得斯》具有柏拉圖呈現「問題、駁難或謎題」的特點。全篇對話錄圍繞著「知識究竟是什麼?」
這個看似在探求定義的問題,另一方面,卻又不是在回答這問題,而是由這問題引導出「感覺╱知覺」對人認知的影響、知識的條件、信念與知識之間的關係、「假」的問題、假信念的產生、知識所要求的合理說明、言說、證成等等這些「知識」周邊的討論。
對話中,泰鄂提得斯為知識提出三次定義,最後全都被蘇格拉底否決了。我們無法確定柏拉圖究竟要我們相信什麼,卻在他筆鋒的刺激下,進入對知識更深更細緻的思索。
作者:柏拉圖
427-347 B.C.,生於雅典,是西方最早留下完整作品的哲學家,著有《理想國》、《饗宴》等約三十五篇作品。他的作品以對話錄形式寫成,像在邀請讀者一同思考、甚至「與他爭論」。他一生探討哲學,對自己的思想持續反思。
譯注者:何畫瑰
1971年生。曾遠走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追問柏拉圖將詩人趕出理想國的原因,經濟因素輟學考回台大,反問柏拉圖將詩留在理想國的可能,2003年取得哲學博士。曾任教真理大學,現任教文化大學,繼續研究柏拉圖哲學。
導讀
壹、簡介與文本分析
貳、從「信念」朝向「知識」的進程
《泰鄂提得斯》
文本說明
譯文
哲學討論
對話形式
○、開場與問題的釐清
一、第一個定義「感覺就是知識」與檢驗
二、第二個定義「真信念就是知識」與檢驗
三、第三個定義「真信念加上說明就是知識」與檢驗
柏拉圖年表
研究書目
導讀(節錄)
壹、簡介與文本分析
柏拉圖(Πλάτων, Plato, 427-347B.C.),古希臘雅典人,家世好,相貌堂堂,是西方最重要的哲學家。這位哲學家如此重要,以至於二千五百年西方哲學傳統都可以被視為是「一系列對柏拉圖的註腳」。當代重要分析哲學家如維根斯坦,重要歐陸哲學家如海德格,都回應過柏拉圖,回應過他這篇《泰鄂提得斯》裡的問題。他的哲學書寫以「對話錄」的形式呈現,像在創作戲劇,也有人稱他為「哲學劇作家」。的確,這位哲學家年輕時曾經寫過悲劇詩,但「正當他要參與悲劇競賽,在戴奧尼索斯劇場前,他聽受了蘇格拉底的話之後,便燒了他的詩一面說著:『赫菲斯多斯(Hephaestus,希臘火神),請到這來,現在柏拉圖需要你。』」然而,蘇格拉底(Σωκράτης, Socrates, c. 470-399B.C.),這位引導柏拉圖走向哲學、長相難看卻有著奇妙魅力的老人家,卻在西元前399年,柏拉圖二十八歲的時候,經由雅典城邦民主制度下的法庭審判,以多數決的投票方式,被判處死刑。蘇格拉底死後,這個老愛纏著人家問問題的怪異角色,卻出現在柏拉圖的絕大部分的作品裡,在對話錄中扮演著引導人們思考哲學的角色。有人把這種用問問題引導哲學思考的方式稱為是蘇格拉底的「助產術」,並津津樂道蘇格拉底有個助產士媽媽。實際上這些有關「知識助產術」的說法,正是出自柏拉圖《泰鄂提得斯》這篇對話錄裡(148e-151d)的橋段。
柏拉圖的《泰鄂提得斯》(Θεαίτητος, Theaetetus),是一篇討論「什麼是知識?」的對話錄。就柏拉圖哲學而言,這是了解他「知識」概念的重要文本;就整個哲學領域而言,這也是開始建立起「知識論」這一哲學分支的重要文本。英文「知識論」這個字,epistemology,正是源自希臘文的「知識」──ἐπιστήμη(讀作epistēmē)。做為希臘第一篇真正以知識論問題為主題的文本,《泰鄂提得斯》自有其分量。然而,這篇對話錄並不只是一篇哲學史上的重要文獻而已,對話錄的內容本身,也提供許多對當代知識論思考的刺激。柏拉圖的哲學具有一種不可能脫離當代的特質:這位文采洋溢的哲學家,雖然放棄了悲劇詩的創作,但他那宛如劇本的哲學對話錄,是一種邀請讀者一同思考、甚至「與他爭論」的書寫方式。這種書寫方式,在論點與論證的文字表達上,套用當代倫理學家本那‧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形容,充滿了「彈性」(flexibility),而威廉斯心目中最能展現柏拉圖「彈性」的哲學作品,正是《泰鄂提得斯》。由於這種特質,即使經過了將近兩千五百年,《泰鄂提得斯》所討論的知識論問題,仍是當代知識論──不論英美或歐陸──持續關切的議題:「感覺/知覺」對人認知的影響、知識的充分必要條件、信念與知識之間的關係、「假」的問題、假信念的產生、知識所要求的合理說明、言說、證成等等。一方面全篇對話錄圍繞著「知識究竟是什麼?」這個看似在探求定義的問題,另一方面,卻又不是在回答這問題,而是由這問題引導出更豐富的知識論討論。
這篇對話和柏拉圖所寫的大部分對話錄一樣,以蘇格拉底為主角。這裡,與蘇格拉底進行對談的,主要是泰鄂提得斯(Θεαίτητος, Theaetetus,因而對話錄以他為名),其次,還有泰鄂提得斯的幾何學老師,泰歐多洛斯(Θεόδωρος, Theodorus)。文中先從另外兩個希臘人對泰鄂提得斯的感嘆開始,再間接引入當年蘇格拉底和泰鄂提得斯的這場討論。蘇格拉底向年輕的泰鄂提得斯詢問「知識是什麼?」泰鄂提得斯提出答案,蘇格拉底便加以檢驗而否決;泰鄂提得斯又提出新的答案,蘇格拉底又再加以檢驗而否決;有時泰歐多洛斯也被迫加入談話,一樣受到蘇格拉底的檢驗與否決。這樣的檢驗過程一再延續,直到對話最後,仍沒有找到適當的答案。但對話當然不是徒勞無功的,經過蘇格拉底的檢驗,泰鄂提得斯已經有所進展,而且也比較不會以為自己知道自己並不知道的事。下面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到這整個回答和檢驗的過程,以及對話錄的論證結構與思路安排:
外層對話:對話者為尤克里迪斯、泰波希翁。
142a-143c尤克里迪斯、泰波希翁兩人談到泰鄂提得斯命危,並追憶起當年蘇格拉底和泰鄂提得斯的談話,於是尤克里迪斯取出他對那場談話的記錄,由僕人拿著筆記朗讀。
貳、從「信念」朝向「知識」的進程
《泰鄂提得斯》這篇對話的主題很清楚,就是「知識」。*這一點很少引起爭議。當我們進一步想要由此探討柏拉圖對「知識」的整體想法時,卻會引發某些問題。問題與爭議正是使柏拉圖知識論活潑迷人的地方。在導讀的第二部分,我將以全篇對話錄作為一種從「信念」朝向「知識」的進程,並試著針對其中一項關鍵性的問題進行討論:我們可不可能經由某種過程,使信念(δόξα, belief)轉變成為知識?
這問題的主要癥結在於,《泰鄂提得斯》最後顯示,當我們對信念增加條件,將信念修正為真信念、並加上說明之後,仍無法拿來界定知識(187a ff.);然而,另一篇研究柏拉圖知識概念的重要文本《米諾》(Μένων, Meno),卻顯示信念可以被某種說明「綁住」而轉變成為知識(98a)。這兩份文本之間的差異,也許可以這樣解釋:雖然兩篇對話錄都在探討知識,但《泰鄂提得斯》呈現的是失敗的探討,《米諾》呈現的則是成功。關於《泰鄂提得斯》所呈現的「失敗」,Cornford的看法具有鉅大的影響──他認為這篇對話錄之所以無法成功界定出知識,是由於沒有以「理型」(Forms)來界定;《泰鄂提得斯》沒有援引理型論,而真正的知識必須要以理型為對象。然而,這樣的看法其實是有爭議的。這看法之下隱含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直接以形上學的設想來理解柏拉圖的知識論?或者,以《泰鄂提得斯》的討論脈絡而言,我們是否只能以「理型」來界定知識?如果我們和Cornford一樣抱持肯定的答案,便要以可感事物和理型之間的懸殊作為切分信念與知識的依據。這樣的思路或許可以和《理想國》中的線喻(Πολιτεία, Republic, 509d-511e)互相映照。因為線喻似乎就是以認知對象的不同來劃分出認知狀態的不同。不過,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信念與知識的區分完全建立在認知對象的不同,基於兩種在存有學上截然不同的對象,真信念如何可能像《米諾》中所說的「被綁住」而「成為知識」?既然,信念一定是以可感事物為對象,可感事物當然不是理型,那麼,被綁住的信念的對象也是可感事物、不是理型,因而永遠不可能轉變成為以理型為對象的知識。
至少還有另一種可能的答案。《泰鄂提得斯》呈現的是單純的知識論探討,而這討論不必依賴在形上學上,所探討的「知識」也不必一定要以理型來界定。這絕不是說知識論與形上學無關,更不是說柏拉圖的知識與理型無關。只不過,像《泰鄂提得斯》這樣不提及理型而單純地只就知識問題去探討知識,也有其意義。當我們不再依賴從這篇對話錄之外引來的形上學,而和裡面的角色們一樣以單純的知識論議題進行討論,信念與知識的關係可以獲得另一重理解。信念與知識,在概念上有著嚴明的區分,但嚴明的區分並不是在切斷關聯。就存有學而言,可感事物無法變成理型,但不表示在知識論上信念無法成為知識。反過來說,如果知識論上信念可以成為知識,那麼,這知識論上的討論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理型」,作為知識的對象,是怎樣的一種存有。至於,究竟如何才能「綁住」信念、使信念成為知識?針對這點,我希望可以指出《泰鄂提得斯》裡信念與知識之間的正面關係,並指出信念(甚至是假信念)在整個追求知識的過程中所具有的意義。這層正面關係將幫我們把信念「綁住」。
接下來,我將從「信念」和蘇格拉底如何檢驗信念的過程,去解釋《泰鄂提得斯》對話的進展與柏拉圖的「知識」概念。
一、檢驗信念
當泰鄂提得斯了解蘇格拉底所要問的「定義」是指什麼,但又不敢提出他對知識的定義時,蘇格拉底鼓勵他「努力用各種方法,尤其是在知識的問題上,掌握合理的說明,它究竟是什麼?(προθυμήθητι δὲ παντὶ τρόπῳ τῶν τε ἄλλων πέρι καὶ ἐπιστήμης λαβεῖν λόγον τί ποτε τυγχάνει ὄν.)」(148d)我相信這正是全篇對話所要做的。這裡的「掌握合理的說明」(λαβεῖν λόγον)並不只是去說出「知識」,它本身也不是知識。因為,泰鄂提得斯這裡提出的只是嘗試性的定義,充其量只是真信念,等待著被檢驗。泰鄂提得斯並不知道知識是什麼,他的定義來自信念,而且很有可能是假信念。但蘇格拉底鼓勵他提出來。再者,這裡的「掌握合理的說明」也不只是去說出一個信念而已,因為蘇格拉底不只是要一個光溜溜的答案,答案還需要跟著某種說明。否則,他就不會在泰鄂提得斯提出答案後追加那許多的問題。「說明」也不是單單說出信念而已。說明也是要被檢驗的。蘇格拉底連續不斷的問題引導著泰鄂提得斯為他所提出的每個信念提出說明,又為說明中的每個信念再做說明。這是一個漫長的檢驗信念的歷程。
就《泰鄂提得斯》全篇結構來看,按傳統的劃分,除前面的場景交代與引導性的談話之外,依照泰鄂提得斯所提出的三個定義,可以將整個討論分為三部分:第一,「感覺就是知識」(151d-187a);第二,「真信念就是知識」(187a-201c);第三,「真信念加上說明就是知識」(201c-210d)。最後,對話的結論是:這三個定義都無法界定知識,而對話也結束於無解的困惑(aporia)中。為了展現出從信念朝向知識的歷程,這裡我將特別注意每一項定義到下一項定義之間的轉折,試圖釐清:從「感覺就是知識」的討論如何引到「真信念就是知識」的定義;從「真信念就是知識」的討論又如何引到「真信念加上說明就是知識」的定義。
1. 從「感覺就是知識」到「真信念就是知識」
實際上,在蘇格拉底檢驗泰鄂提得斯第一項定義的過程中,第二項定義「真信念就是知識」已經逐漸浮現出來了。要追索其中的痕跡,可以檢視第一部分的文本裡,使用「信念」(δόξα或δόξασμα)及「抱持信念」(δοξάζω)等字的地方。這幾個字在151d-186e之間出現了許多次。就文脈來區分大致有三處:一、158e,那裡的用字緊隨著一段有關對象「同一性」(identity,指一事物和自身相同或不同、相似或不相似等問題)以及「是」(οὐσία)的討論,和後來184b-187a正式將心靈中「感覺」與「信念」兩種機能區分開來的段落,非常吻合。二、從170a到171c,則是在談不同的人之間不同信念的衝突。三、然後,在179b-c,蘇格拉底和泰鄂提得斯達成共識:「並非所有人的所有信念都是真的」。達到這樣的共識後,柏拉圖接下來好幾頁都沒有使用「信念」、「形成信念」等字,直到187a。但是,179c-187a的段落中,仍不時回應著這幾個字在先前段落裡的相關議題,並為後來有關「信念」的討論鋪路。
在179c,柏拉圖行文上先將「感覺」與「信念」一併處理;另一方面,那些比較可能形成某種系統性知識的信念,則被區別開來。「並非所有人的所有信念都是真的」這共識是就後者而言的。所謂「比較可能形成某種系統性知識的信念」是指文脈中提到的健康、音樂、釀酒、尤其還有法律與正義方面的信念。這點回應到170a-171c出現的「信念」一詞。那裡討論的「信念」,如對軍事、疾病、航海以及對勃泰哥拉斯「人是萬物尺度」學說的信念,也都不是直接從感覺而來的。接著,蘇格拉底隨即在171e將熱、乾、甜等事物,和有關健康與疾病這類事物,區別開來。於是我們可以區分兩種信念:一種是直接來自感覺,另一種不是。但後者(軍事、疾病、航海等方面的信念)也可能是以感覺信念作為基礎,如果是這樣,那些信念仍然是間接來自於感覺。如此一來,「感覺」和「信念」這兩個概念便仍糾結在一起。
對話形式
142a-143c 外層對話
《泰鄂提得斯》這篇對話的結構安排上,在進入主要內容之前,先有一段外層對話:其中,馬格拉城的尤克里迪斯和泰波希翁兩人談到泰鄂提得斯命危的事,緬懷泰鄂提得斯的好,並追憶起多年前蘇格拉底和泰鄂提得斯的一場談話。我們從尤克里迪斯和泰波希翁對泰鄂提得斯的惋惜,可以感受到:長大後的泰鄂提得斯是個優秀的人。而他青少年時期與蘇格拉底的談話,不論當時的討論是否獲得明確的結果,似乎都因此染上正面的意義,讓人覺得是一場很有價值的談話。後來,尤克里迪斯在泰波希翁的央求下,取出他對那場談話的記錄,由僕人拿著筆記朗讀,更增添了這篇「對話錄」「值得一聽」的氛圍。
在這段外層對話中,尤克里迪斯和泰波希翁談到的科林斯戰役,可以作為一項時間指標,幫助我們標示出《泰鄂提得斯》這篇對話的寫作時間可能晚於369年;即使對柯林斯戰役採取394-391年份之說的學者,也不認為對話成書時間會提早。(Cf. Gill 2012 103)大部分學者認為,這篇對話是在所謂中期對話錄的代表作(如《斐多》、《理想國》)以後。柏拉圖作品大致分為早、中、晚期。一般而言,在哲學風格方面,早期對話錄蘇格拉底問答色彩濃厚,也被稱為「蘇格拉底對話錄」,對話常以「無解」(aporia)作終;中期則已發展出所謂理型論(theory of Forms);晚期則對理型論等中期思想進行反省。這篇《泰鄂提得斯》雖然最後也以「無解」作終,而且似乎沒有提到理型論,但就年份推斷上卻屬於中到晚期作品。這表示:「無解」問答的特點並不完全限於早期對話錄,而《泰鄂提得斯》的「無解」結局也很可能帶有與早期對話錄不同的意涵(見導讀「貳」);另一方面,未使用理型論解釋知識這一點,也表示中期以後的對話錄不見得都要討論到理型。
另外,在對話中尤克里迪斯表示他是聽了蘇格拉底講述對話,然後寫下來,現在又預備讓小僕人拿著他寫的筆記朗讀給泰波希翁聽。這裡,柏拉圖展現出一種特殊的書寫方式:間接轉述主要的對話內容。間接對話的書寫方式增加了一種閱讀上的距離感。身為讀者,我們原本就不是直接參與蘇格拉底和泰鄂提得斯的談話,但這裡我們甚至也不是直接讀到這場談話的記錄,而是間接去讀別人的轉述,甚至這位轉述者也並沒有參與當年的對話,而是聽蘇格拉底講的。此外,按柏拉圖這裡的安排,寫下這篇對話的作者不是柏拉圖,而是尤克里迪斯。這又更增加了讀者和真正的作者柏拉圖之間的距離。柏拉圖使用間接轉述手法的作品有四篇,除了《泰鄂提得斯》,還有《斐多》、《饗宴》(Συμπόσιον, Symposium)和《巴曼尼得斯》(Παρμενίδης, Parmenides)。其中,《泰鄂提得斯》是唯一明白指出被寫下而且真正「被讀」的對話錄(Benardete 1984 I.85; Waterfield 2004 136),主要對話內容經過「書寫」媒介而被轉述。(《巴曼尼得斯》也涉及一份筆記,但並非單純去讀出對話錄。)不過,卻也正因為藉由「書寫」的媒介,尤克里迪斯從開始寫下他所聽到的部分,到後來一有機會就詢問蘇格拉底加以修正的過程,使對話錄展現出「書寫」而非「口說」可以達到的完整度。這使得整篇對話具有一種對書寫的實驗性。
○、開場與問題的釐清
143d-146b 進入主要對話
尤克里迪斯的小僕人開始朗讀筆記後,進入這篇對話錄的主要內容。其中的對話者是蘇格拉底、泰歐多洛斯和泰鄂提得斯。開始時,泰歐多洛斯向蘇格拉底介紹年輕優秀的泰鄂提得斯,說他「很能學」,蘇格拉底隨即開始檢驗泰鄂提得斯。由於泰鄂提得斯跟隨泰歐多洛斯學習幾何,蘇格拉底就從幾何與其他知識的學習這點,開始詢問泰鄂提得斯「什麼是知識?」。
在這段引導性的談話中,可以從話題如何引入「什麼是知識?」來了解柏拉圖對知識的定位。外層對話兩位談話者尤克里迪斯和泰波希翁都是馬格拉學派的人,馬格拉學派注重邏輯與數學;至於主要對話裡的泰歐多洛斯、泰鄂提得斯,也都是數學家。柏拉圖讓這場探詢「知識」的對話發生在這些數學家之間,似乎是將數學視為是「知識」的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此外,這裡也出現類似早期對話錄以「技藝」(τέχνη, techne/expertise)檢驗知識的模式:當蘇格拉底開始和泰鄂提得斯談話時(144e- 145b),他先用「琴音的事必須問音樂家」、「長相的事必須問畫家」為例,表明各種不同領域的事物應當要尋求專業有技藝的人來判斷,以此說明自己為什麼要檢驗泰鄂提得斯。早期對話錄常出現檢驗對話者專業技藝的情節,並以此檢驗對方的知識:例如《伊安》(Ἴων, Ion)檢驗詩人的知識,《勃泰哥拉斯》(Πρωταγόρας, Protagoras)檢驗詭辯家的知識,《高吉亞斯》(Γοργίας, Gorgias)檢驗演說家的知識等等。這裡,對話中的蘇格拉底要檢驗的,是數學家(泰歐多洛斯)對數學學生(泰鄂提得斯)在「學習」「知識」上的評判。但檢驗的目的,既不是針對泰歐多洛斯的專業技藝與知識,也不是針對泰鄂提得斯有沒有幾何學知識,而是直接將泰鄂提得斯視為一起探究知識的夥伴。不同於早期對話錄對個別技藝與知識所進行的檢驗,這裡是要更後一層地去討論「知識」是什麼。
用字上,平常在柏拉圖對話錄裡常常將「智慧」與「知識」二詞互換,這裡蘇格拉底正式地和對話者取得同意,將「智慧」和「知識」視為同一回事。(145e)這使得「有智慧的人」(οἱ σοφοί, the wise)或「智者」(σοφιστής, sophist)可以被「有知識的人」取代,因而也可以藉由檢驗「是否有知識」這種清晰的要求,來檢驗有智慧的人。不過,作為一名年輕的學子,泰鄂提得斯並不是被當作有智慧的人而受檢驗;這裡對「知識」的討論,比較接近《米諾》(Μένων, Meno),是從「學習」的角度來進行的。泰鄂提得斯在此是被當作很能「學習」「知識」的人,而不是已經擁有「知識」的人。
另一方面,「知識」這個詞又代表什麼意思?Bostock藉法文中的savoir和connaître來區分兩種「知道」,亦即中文裡「知道(某件事)」和「認識(某人/物)」的區別。前一種在英文討論中稱為propositional knowledge(命題知識);後一種稱為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藉由熟悉而認識)。在這篇對話裡的「知識」,兩種都涵蓋。這表示,柏拉圖可能沒有這種區分。但許多討論柏拉圖知識的研究文獻會涉及這議題。中文讀者很容易可以了解「知道」和「認識」的不同:當我說「我知道蔡依林」,只表示我知道有這樣一個人,知道一些關於這個人的訊息,可能是報紙或電視上得來的,但並不認識她本人;可是,當我說「我認識蔡依林」,通常表示我親身見過她本人,並和她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甚至隱含她也認識我的意思。尤其是對一些很有名的人,我們常常只「知道」她的事,但不「認識」她本人。由於人有許多面向,確實也有可能我認識某個人,卻對她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但,無論如何,我至少必須知道「她就是我認識的那個人」這命題,因此「認識」蘊含至少一項命題知識(反之,不論多少相關的命題知識卻都無法保證「認識」)。在當代討論到知識的定義時,所界定的是「命題知識」,也就是「知道(某件事)」的這種知識。Fine認為,對柏拉圖而言,「認識」其實是藉由「知道」有關某人或某物的命題為真而認識,柏拉圖舉例討論知識時,有時似乎也將「認識」與「知道」互換,「認識x」可以改寫成「知道x是如此這般的」。(Fine 1979 98)不過,Fine的解釋雖然可以幫助我們溝通當代知識論與柏拉圖對知識的討論,但這種改寫最多只能是單向的:如果「認識x」,也就「知道x是如此這般的」;但反過來說,如果「知道x是如此這般的」,卻並不就是「認識x」。這點從上面「知道蔡依林」的例子就能了解。再者,「認識」與「知道」也無法互相作量化的比較:「我認識蔡依林」,雖然可以改寫成「我知道蔡依林是……」,但也有可能我雖然認識她,擁有的相關命題知識卻很貧乏;而一個不認識蔡依林本人的歌迷,反而知道很多蔡依林的事情,她所出的每一張專輯、每一首歌曲、她的生日、星座、血型、所唸過的學校等等,但把這許多命題知識集合起來,不論多麼大量,都不能等同於「我認識蔡依林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