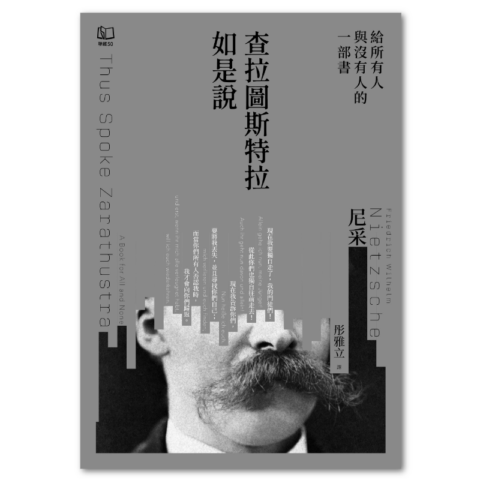論義務
原書名:De Officiis
出版日期:2014-03-20
作者:西塞羅
譯注者:徐學庸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288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3569
系列:聯經經典
尚有庫存
古希臘羅馬文化之父 西塞羅 的最後著作
古今中外未再誕生如西塞羅這般集政治家與哲學家的偉大於一身之人
──美國開國元勳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
西塞羅可謂是「永垂不朽的羅馬人」
──美國古代史權威摩塞司‧哈達斯(Moses Hadas)
西塞羅的《論義務》共分三卷,分別論述「何為德性行為及其源頭」、「有效益的行為是否可與德性分離?」,以及「有效益之事與德行之間的衝突」,充分顯示西塞羅政治保守主義的立場,以及對愛國主義與道德行為的堅持。
《論義務》在不同世代都對哲學家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從西元四世紀安博洛斯(Ambrose)創作的以基督宗教為背景的《論義務》;文藝復興時期馬其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王論》(The Prince);十七世紀葛勞秀斯(Hugo Grotius)的《論戰爭與和平之法》(De Iure Belli ac Pacis);英格蘭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二論》(Two Treatises on the Government);啟蒙運動時期的法國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之《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等,在在可見對《論義務》的諸多引述或取其論證為基礎而成。接下來幾世紀的哲學家,如休謨(David Hume)、康德、穆爾(John Stuart Mill)等,亦多有對西塞羅倫理學觀點的分享。
這部西塞羅生前的最後一部哲學著作,原為寫給兒子的一封信,但其中論述精闢的倫理價值觀與政治學概念,實為西塞羅傳給後世的一份最珍貴的禮物。在今日衝突頻仍的政治社會現象中,這部經典著作中譯本的問世,無疑能帶給我們在行為、道德以及政治上,更多的啟發。
作者:西塞羅
古羅馬政治家、哲學家及修辭學家。
以政治「新人」的身分逐漸躍升至羅馬政治舞台中心,於63 BC獲選為執政官,達到政治生涯頂峰,終其一生護衛羅馬共和制度。
自幼師承當時重要的希臘哲學家們,取各家之長,在知識論上是位新學院的懷疑主義者,倫理學傾向斯多葛學派。受古希臘修辭學的訓練,對羅馬修辭學的發展有諸多貢獻。凱撒遇刺後,西塞羅出言抨擊馬克‧安東尼破壞共和體制,因此遭其殺害。
譯注者:徐學庸
1998年取得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99至2000年任教於東海大學哲學系,2000至2012年任教於輔仁大學哲學系,2005至2006年為牛津大學訪問學人,現任教於臺灣大學哲學系。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洋古代倫理學及政治哲學。除本譯注外,另著有《靈魂的奧迪賽:柏拉圖《費多篇》》、《道德與合理:西洋古代倫理議題研究》和《古希臘正義觀:荷馬至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價值及政治理想》;譯注有《《理想國篇》譯注與詮釋》、《《米諾篇》《費多篇》譯注》及西塞羅《論友誼》、《論老年》、和《論義務》。
導論
西塞羅生平與著作年表
斯多葛學派發展分期
關於譯文
《論義務》章節分析
《論義務》三卷書譯文及注釋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名詞索引
導論(節錄)
■西塞羅的生平
西元前106年1月3日,世居羅馬南方城鎮阿爾皮農(Arpinum)的一位羅馬騎士階級家族裡,誕生了一位男嬰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他日後將成為羅馬著名的政治人物,演說家及哲學家。雖然出身無政治特權的騎士階級,但祖父與羅馬政治上兩大家族,葛拉提迪烏斯家族(the Gratidii)及馬里烏斯家族(the Marii),皆有姻親關係。此外,祖父本人也是極具政治影響力的政治貴族艾米利烏斯‧史考魯斯(Aemilius Scaurus,約155-89 BC)的朋友。西塞羅的雙親亦與當時的權力中人交好。雖然西塞羅以政治「新人」(novus homo)之姿於西元前63年攀登政治權力頂峰,任執政官,但他的家族背景絕對不可說是對其仕途發展,毫無政治資源的供給。
西塞羅以十六歲之齡拜入占卜師史凱渥拉門下,學習法律。除了學習法律,西塞羅年輕時亦接受哲學與修辭學的教育。約西元前88年一位斯多葛學派盲眼哲學家迪歐都圖斯(Diodotus,約卒於60BC)來到羅馬,並寄居於西塞羅家中,西塞羅因此習得斯多葛學派的思想及得到辯證法的訓練;而後又於西元前82年成為羅馬新學院哲學家菲隆(Philon of Larisa,159-83 BC)的弟子,西塞羅《學院思想》即參考他的理論。年輕的西塞羅亦受到來自拿波里的史塔塞阿斯(Staseas)的啟發,此人是位逍遙學派哲學家,強調外在美善事物與幸福生命的關係。另一位影響西塞羅的是,同屬騎士階級的艾利烏斯‧史提婁(Aelius Stilo,約150-75 BC),他自詡為斯多葛學派哲學家,專精文學、語言及歷史,並創作演講詞,不過他並非一位演說者。
西元前81年或許是西塞羅成為執業律師的一年,隔年為羅斯奇烏斯(Roscius)辯護成功,令西塞羅聲名大噪,但也激怒了獨裁者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138-78 BC)的爪牙,惹來殺身之禍。出於這個原因,加上個人健康狀況不佳,西塞羅決定出海至雅典,一方面遠離危險,一方面調養身體。在雅典他從德梅特里烏斯(Demetrius of Magnesia,C 1 BC)學習修辭學;聽費德若斯(Phaedrus,約140-70 BC)及芝諾(Zeno of Sidon,約生於150 BC)講授伊比鳩魯學派的思想;跟隨安提歐庫斯(Antiochus of Ascalon,約卒於68 BC)學習「學院」(The Academy)的思想。安提歐庫斯是菲隆的學生,但不同於後者得懷疑主義立場,前者轉而採取有定見的立場(the dogmatic position)。此外,安提歐庫斯在思想上是位折衷主義者,他融和了學院、逍遙學派及斯多葛學派。根據普路塔荷(Plutarch,約46-121 AD)的記載,西塞羅並不接受安提歐庫斯的思想,因為這與新學院的懷疑主義大異其趣。在羅德島,西塞羅向默隆(Molon of Rhodes,C 1 BC)學習修辭學,且向波希東尼烏斯(Posidonius,約135-51 BC)學習斯多葛學派的思想;再者於小亞細亞的斯邁爾納(Smyrna)向普博利烏斯‧魯提利烏斯‧魯夫斯(Publius Rutilius Rufus,約160-90 BC)學習斯多葛學派的思想。
西塞羅的教育可謂相當廣博,所涉及的學科包括法律、修辭學及哲學,特別是哲學,幾乎涉獵了當時所有主要學派,斯多葛學派、逍遙學派、伊比鳩魯學派及新學院的思想。浸淫於各家各派,西塞羅始終自詡為一忠實的新學院追隨者。《論義務》鼓勵兒子要閱讀哲學著作,因為在其中哲學家「費心完整地討論許多嚴肅有益的議題」。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西塞羅堅守新學院懷疑主義,但他並不認為當時的哲學學派在思想上有實質的歧異,反而不只一次地主張,哲學學派見解的差異其實只是思想表達的不同。此一立場使得西塞羅不僅強調自己是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追隨者,盛讚柏拉圖是哲學家中的哲學家或哲學之神,而且對亞里斯多德也不吝給予溢美之詞,例如他讚美亞里斯多德有近乎神聖的智性,在哲學中除了柏拉圖外,勝過其他哲學家。當然西塞羅最欣賞的還是柏拉圖,他個人的哲學作品大多以模仿柏拉圖對話錄的形式書寫,例如《論共和國》與《論法律》即是模仿《理想國篇》(The Republic)及《法律篇》(The Laws);西塞羅在著作裡亦大量轉譯柏拉圖對話錄的內容,《論老年》及《論義務》皆可見確切的實例。
無法確定西塞羅是在赴雅典前或返回羅馬後成婚,可確定的是他與出身貴族的特倫緹雅(Terentia,約80 BC-23 AD)結婚。妻子的家世對西塞羅的仕途更添助益。西元前77年返回羅馬後,他正式踏出公職之路(cursum honorum),西元前75年,以三十歲之齡當選成為西西里的財務官(quaestor)。隨後的四年專注於律師的工作,並於西元前70年成功起訴維瑞斯(Gaius Verres,卒於43 BC),此人於西元前73至70年任西西里的行政長官(proconsul),但貪贓枉法,使百姓民不聊生。西塞羅的成功獲得西西里人的愛戴,也對他日後在政治上的發展有正面影響。西元前69年,西塞羅競選羅馬市政官(aedile),並成功當選;三年後又成功獲選為法務官(praetor)。至此為止,可謂仕途順遂。他不僅在每一公職競選上都以最低年齡的門檻當選,更重要的是他已為自己累積了競選執政官的資格。法務官任內西塞羅為言支持彭沛烏斯統兵對抗彭圖斯國王米特里達特斯六世(Mithridates VI of Pontus,統治120-63 BC),史稱馬尼利烏斯法案(Manilius’ Law),使得他與彭沛烏斯在政治上逐漸靠攏。西元前63年,西塞羅決定參選執政官,在阿提庫斯全力支援下,與安東尼烏斯(Gaius Antonius,C 1 BC)一同當選,且粉碎了卡特利納(Lucius Sergius Catilina,約109-62 BC)的執政官夢。這也是政治新人在執政官選舉上擊敗貴族的實例,西塞羅攀上政治生涯的頂峯。
結束執政官任期前,西塞羅著手進行處理卡特利納的叛國行徑。儘管後者欲以謀殺西塞羅來阻止他的調查,但西塞羅的先見之明使得自己逃過此劫。獲得元老院議員卡投(Marcus Porcius Cato,95-46 BC)的協助,西塞羅成功說服元老院通過「終極法令」授權執政官以一切的方式阻止卡特利納的行為。卡特利納見事跡敗露,逃至艾特魯里亞(Etruria),但隨即被殺;在羅馬的餘黨共五人,於12月5日在獄中被處以絞刑。然而這是在未經正常審判程序下執行的死刑,西塞羅的政治前途蒙上陰影。成功阻擋卡特利納的判國,西塞羅萬民擁戴,甚至被冠以「國父」(patera patridos)的封號。不過如此歡欣鼓舞的氣氛並未持續,原因有二:第一,卸任執政官職後,彭沛烏斯、凱撒及克拉蘇斯(Marcus Licinius Crassus,約115-53 BC)形成三人執政,大大傷害西塞羅極力維護的共和體制。第二,西元前63年處理卡特利納時的非法行刑,後續效應產生。護民官克婁帝烏斯(Publius Clodius Pulcher,約92-52 BC)在凱撒的支持下,重新恢復對非法執刑者處以放逐懲罰的法令,西塞羅因此被迫於西元前58年離開羅馬,且家產被充公。隔年的9月4日西塞羅獲召重回羅馬,並恢復其家產,但此一放逐對西塞羅往後的政治立場有決定性的影響:他憎恨克婁帝烏斯,對未支持他的貴族感到反感,以及感謝彭沛烏斯在召回他的法案上全力支持。
重返羅馬的西塞羅,投身於法律訴訟,西元前53年獲選為占卜師,且於隔年被指派為奇利奇亞(Cilicia)的行政長官,從西元前51年至50年赴任。西塞羅離開羅馬這段期間,城內政治情勢急轉直下,凱撒率軍從法國邊境渡紅河,直通羅馬。彭沛烏斯見勢不可遏,率眾遠離羅馬,整軍經武,準備與凱撒一戰。西元前49至48年間內戰爆發,西塞羅多所猶豫最後站在日後失敗的彭沛烏斯一方。不過凱撒對此不以為意,西元前47年的9月與西塞羅在布倫迪希恩(Brundisium)前嫌盡釋。西塞羅公私兩面打擊接踵而來,與妻子離異、女兒圖麗雅(Tullia)去世。西元前45至44年間,西塞羅在哲學中尋找慰藉,大量書寫哲學著作。
西元前44年羅馬政治史上的大事是凱撒遇刺身亡,西塞羅多次在書信中稱許刺殺凱撒是英雄的行為。但獨裁者雖已逝,羅馬政體卻未因此而自由解放,因為安東尼的獨裁野心日顯,他不僅握有凱撒的文件與私人財產,且在廣場上為他舉行喪禮,並發表一篇令人不齒的祭悼文。此一作為無異於國葬,行刺者的正當性完全消失殆盡。西塞羅不能接受事態如此,堅定認為凱撒以不正義的方式追求榮耀(gloria),為自己安排帝位,追求個人的貪欲,這不僅對多數人無益,也不會被大眾所認可。眼見當下政治情勢發展不可挽回,西塞羅無奈地決定離開羅馬,在義大利鄉間及南部海岸城鎮遊歷。從這段期間的書信得知,西塞羅欲拉攏屋大維(Gaius Octavius,63 BC-14 AD)對抗安東尼,但事與願違,屋大維與安東尼的密約出賣了西塞羅,西元前43年12月7日他被安東尼的手下逮捕處死,並在安東尼的命令下將其頭顱懸掛在廣場的演說台展示。
■《論義務》的主要議題
西塞羅生前最後一部哲學著作《論義務》,即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完成。根據西塞羅寫給阿提庫斯的信,這部著作是寫給兒子小西塞羅的一封信(XV, 13a, 2及XVI, 11, 4)。書中內容主要是提醒兒子,什麼樣的行為才是適切合宜(officia)。
西塞羅告誡兒子,合宜的行為(kathēkontos)──西塞羅以拉丁文officia(義務)譯之──是哲學家們共同探就的倫理議題(I, ii, 4-5),所以依帕奈提烏斯的論述模式,他提議先討論德性行為的判定,其次處理所做的行為是有利或無益,最後探討德性行為是否會與有利之事衝突的議題(I, iii, 9及III, ii, 7)。這三個主題構成了《論義務》三卷的結構,但西塞羅特別強調,帕奈提烏斯並未論及第三個議題,波希東尼烏斯則有所觸及。
《論義務》卷一關於德性行為的論述,首先以斯多葛學派的oikeiōsis(固有特質)之概念說明,生物皆有自我保存及維繫生命的特質。然而人與其他的動物不同,因為後者僅受當下的感覺影響,但前者具有理性,可知事物的前因後果,能掌握自身的生命歷程,對自己的人生發展有預做準備的能力。此外,理性的力量亦可將人與人匯集群聚,形成社群,並成為人的行為指導,「因為只有這個動物(即人類)感知什麼是秩序,什麼是適切的事,及在行為與言談中什麼是恰如其分」(I, iv, 14)。所有正直的事或德性行為(honesta)皆由秩序與適切合宜產生,且每一個德性行為都源於四個源頭:智慧、正義、雄心(magnitudo animi)及節制(15-17),即所謂四樞德。
卷二及卷三的論述主要是卷一的延伸,卷二的主議題是:有效益的行為是否可與德性分離?西塞羅明確地主張,只要是有德之事一定是有效益之事(II, iii, 10),他提及善意或愛是維持個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追求榮耀應注意的事項,並特別強調應維護正義,因為只有正義存在我們才能擁有真正的榮耀,且將它擴大(II, xi, 39-xii, 42)。慷慨大方的行為可藉由金錢的給予及提供服務來表現,但金錢給予應量己之力,勿用罄家產,且不可劫他人之富,大方給予;此外關於服務應慎選服務的對象,選擇之標準是道德性格,且在為國家服務時切勿為己牟利。更重要的是要保護每個人的私有財產,不可以國家之名,恣意徵收私有財產。卷二尾聲西塞羅提出帕奈提烏斯忽略的兩個議題:保持健康及維護家產,因為這兩件也是有利之事。正確的觀念,生活節制及遵循醫生的建議與指示,是保持身體健康的方式;家族財富之持盈保泰,除了個人要勤奮努力外,亦應懂得正確地使用金錢。
卷三的主題是討論有效益之事與德行之間的衝突。西塞羅指出帕奈提烏斯言及此一問題,但未進行實質的討論。但卷三有一基本原則:有德性的行為只會與看似有效益的行為產生衝突,而不會與真正有效益的行為扞格不入(III, vii, 34)。換言之,有德性之事即為有效益之事,反之亦然。因此任何有效益之事都不可違逆正義,且要避免欺騙,無論是人與人的交往,處理政治事務或進行買賣。此外西塞羅說,在處理戰爭事務時的有效益行為,是符合雄心的行為,他特別以荷馬《伊里亞德》(The Iliad)中的奧狄修斯(Odysseus,其拉丁名為尤里西斯Ulysses)及羅馬執政官雷鼓路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 C3 BC)為例,前者認為不出兵特洛伊是有利之事,實則不是,故是不具德性的行為;後者雖犧牲自己的生命,但對國家是有效益之事,故是有德性的行為。因此追求看似有效益之事是對權力擁有者的傷害,且任何有效益的行為的實踐皆須注意符合環境的變化,否則它不會是德性行為。再者,有效益的行為是否建立在身體慾望的滿足及快樂的追求?西塞羅對合宜行為或節制的論述,以此問題為切入點,並反駁道,快樂的追求定會與德行扞格不入,因為它使得節制無用武之地,「節制對慾望有敵意,但慾望是快樂的追隨者」(III, xxxiii, 117)。這是西塞羅對伊比鳩魯即其學派批判之一;第二個批判是對追求快樂及遠離痛苦的強調,使得伊比鳩魯學派不贊成或不鼓勵參與公共事務,所以它對正義的討論,對西塞羅而言,僅在其倫理學思想中聊備一格罷了,或「處在沉睡的狀態」(III, xxxiii, 118)。失去了正義,一切人倫關係中的善皆無從表現。
《論義務》文末西塞羅告訴兒子,這三卷書是送給他的一份重要禮物,且提醒兒子,雖然他從學於逍遙學派哲學家,但對這部以斯多葛學派思想為藍圖的作品,應認真以對。根據西塞羅的書信,《論義務》前兩卷完成於西元前44年11月5日前,且第三卷完成於12月9日。他於9月2日發表了第一篇《菲利皮凱》(Philippicae),撻伐安東尼的恣意妄為,並在10月底完成第二篇《菲利皮凱》,對安東尼進一步的批判。或許從著述時間的相近,可推斷《論義務》與《菲利皮凱》有某種特殊的體用關係,前者為唯有以正義的方式追逐權力才是合宜的行為,提出理論的論述;後者是對違背此一理論者進行的批判。在隨後幾近一年的時間,西塞羅陸續發表了十二篇反對安東尼的演說詞,被激怒的獨裁者最終以刺殺西塞羅,來回應其對他的批判。西塞羅對兒子說:「我會很快與你親自談話」(III, xxxiii, 121),卻因此不曾實踐。
第一卷
[I](1)雖然,馬庫斯我的兒子,已經在雅典聽了一年克拉提普斯的課,你應該具備充分的哲學原理原則,藉由此位教師與這個城市的最高權威,這兩者之中任何一個都可使你在知識上增長,此外,不同於前人,我自己經常將拉丁文與希臘文結合,為了我的方便,我不僅在哲學上,也在演說練習上做此結合,我認為應該為你做相同的事,所以你在這兩種演說上具有相等的能力。事實上,我們,如我所見,要非常適切地把這重要的協助帶給我們的同胞,使他們會認為,為了學習與判斷,不僅要獲取粗糙的,也要取得大量有智慧的希臘文學作品。
(2)因此,你確實要從學於當代哲學家中的翹楚,且你想學多久就學多久(但你應該希望長期,因為你會後悔沒有長足的進步),然而解讀我們與逍遙學派哲學家並無太大的歧見,因為我們希望成為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追隨者,關於這些事運用你自己的判斷(因為我不阻礙),此外你一定會完成比我們所閱讀的還要豐富的拉丁文演說辭。但我真的不希望這個說法被無禮地評斷,因為從事哲學活動的知識許多人皆可擁有,它是演說家的特質,話要說得適切、清晰及優雅,由於我在此學科上耗費青春,若我認同它,我似乎在某層面上以我的權威保護它。
(3)因此,我非常鼓勵你,我的小西塞羅,不但要勤勉閱讀我的演講,而且要讀哲學相關的書籍,這些書幾乎與我的演講稿一樣多;事實上在演講稿中言說的力量較大,但這平和適中的演講方式也要練習。其實我知道這至今尚未出現在任何希臘人身上,所以在這兩類言說方式上你要努力體悟:公開演說的方式及平和討論的方式。或許法雷倫的德梅特里烏斯可被視為這種人,精確的討論者,不太激烈的演說家,儘管如此是位令人愉悅的演說家,塞歐弗拉斯圖斯的學生可能知道他。此外,我們在這兩件事上會有長足的進步,會有其他人的評斷:
(4)我們確實了解這兩種言說方式。至於我,我看重柏拉圖,若他希望操作公共演說的方式,他有能力以極為嚴肅及流暢的方式發表演說,德莫斯塞內斯有能力說得流暢出色,若他從柏拉圖那兒學到那些事,並記得且希望發表;關於亞里斯多德與伊索克拉提斯我以相同的方式評判,他們兩人對自己的著述感到滿意,却鄙視對方的作品。
[II]然而當我考慮寫些什麼給你,在此時,在漫長的未來,我最希望從最適合你的年紀及我的權威的事開始。因為在哲學中,哲學家費心完整地討論許多嚴肅有益的議題,那些由他們傳承並教授的關於義務的事,似乎廣為人知。事實上生命中沒有一部分,無論是國事或私事,公共事務或家務事,無論是你對自己的行為或與他人的約定,都不能沒有義務,在每一個立基於生命中的部分,應珍惜每一件高尚的事物,忽略每一件有損顏面的事。
(5)其實這是所有哲學家共同的探究。因為有誰敢說自己是哲學家,當沒有任何關於義務的準則被傳授下來?沒有任何主張善與惡的範圍的學問推翻所有的義務,因為以此方式教授至善的人,會使無物與德性結合,他以自身的利益,而非以道德來判斷每一個善,在此,若他言行一致且不會偶爾被人性的道德完整給說服,他不可能珍惜友誼、法律及善意。勇者當然完全不可能斷定痛苦是最大的惡,或節制之人判斷快樂是最大的善。雖然這些議題就在手邊,不需現在討論,但我們會在他處討論。
(6)因此,若這些學問想要與它妥協的話,它們會無法說與義務相關之事,確定、一致及與人性結合的義務準則也無法陳述,除非那些只為了正直,或對正直非常渴求的人自己陳述。那個訓誡是斯多葛學派、學院及逍遙學派的特色,因為亞里斯投,皮若及艾里魯斯的看法早已被駁斥,儘管如此,他們有自己討論義務的正當性,若他們允許某種對事物的選擇,如此會有通往發現義務的入口。因此,我們在當下的探究中是跟隨最重要的斯多葛學派哲學家,不是當翻譯者,而是,如我們所習慣,從他們思想源頭開始,以我們的判斷與決定,我們會體會多少,以什麼方式它會被理解。
(7)那麼這似乎不錯,因為所有的論證都將與義務有關,先定義什麼是義務。我驚訝這被帕奈提烏斯所忽略,因為所有關於某事例的安排被思想接受,應該從定義出發,以了解所討論的相關議題是什麼。
[III]所有關於義務的探討有兩類:一類就善的目的而論;另一類被置於格言訓誡中,生命中每一環節的常規皆可在這些格訓中形塑。這些例子是與前類義務有關的問題,是否所有的義務都完美,某種義務是否比另一種更重要及諸如此類之事。然而關於這些義務的格訓的傳承,雖然它們是就善的目的而論,但這一點都不明顯,因為它們似乎較關注社會生活的組織安排,關於此必須在我們的各卷中處理。
(8)此外,關於義務還有另一種區別;因為我們稱義務是某種中道及完美。我認為我們或可稱完美義務為正當,因為希臘人說的恰到好處,但他們稱共同分擔的義務為〈中庸〉。因此他們以此方式限定了什麼是正當,他們確立這個義務是完美的;然而他們是說,這個義務是中道,因為行為的可能理由可被提出。
(9)因此,帕奈提烏斯認為,關於下判斷的思考有三種。首先,關於行為是道德或卑劣的,人們在他們的思慮中猶豫;在思慮中理性經常對反的意見感到茫然失措。再者,人們探究或諮詢與生活利益及享樂有關的事。關於事物的功能與便利,關於用處,關於效率,藉這些事他們可以使自己感到愉悅,但他們不思考無用之事,所有的思慮都是配合利益用處的理由。第三,有一種懷疑,當行為不符合德性,因為它似乎是為了獲利。因為利益實際上似乎是掠奪自己,反之,正直似乎是重獲自己,在思考中理性出現困惑,且助長思想搖擺的焦慮。
(10)在此分類中有兩件事被略而不談,因為分類的過程中,帕奈提烏斯忽略了某個嚴重的錯誤。事實上不僅行為是道德或卑劣經常被思考,而且所提出的兩種正直是否比較正直,同樣的,所提出的兩種利益是否比較有利也經常被思慮。因此他認為有三種考量必須被分配到五個部分中,且在其中被發現。所以首先是關於德行,但有兩種解釋,再來提出關於利益的說明,之後必須討論關於它們的比較。
[IV](11)從一開始自然賦予一切有生物這些能力:保護生命及身體,避免看來會造成傷害的事,及追求與準備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如食物、藏匿處及其他相同的事物。此外,為了繁衍後代,交媾的自然欲望及對其後代的關心是一切有生物共通的特質。但這在人與動物中有所不同,因為後者只受感覺的影響,只向當下的事物移動,且專注在眼前的事物,對過去與未來之事感覺甚少。然而人,因為分享理性,藉由理性可判知結果,了解事物的原因,且對在事物原因之前的東西,所謂前因,並不是不知道,會比較相似的事物,且在當下的事物上結合與聯繫未來之事,輕易地理解整個生命歷程,並準備必要的東西度日。
(12)同一個自然也藉由理性的力量將人與人結合在一起,為了有理性與生命的同伴,並特別創造某種特殊的愛在那些受造物中,它鼓勵人們的相會與聚集,它希望他們自己能參與其中,由於這些緣故,它熱心準備那些供給衣食的東西,不僅是為了自己,也為了伴侶、小孩及其他他關心且該保護的人,此一關懷也讓人們的精神為之一振,並使他們更熱中於做事。
(13)特別是,探討與研究是人真正的特質。因此當我們免於必要的工作及擔憂時,我們希望看某事、聽某事及多學點事,我們認為關於神祕或令人驚奇的事物的知識,對活的快樂是必要的。從此可知,因為真理簡單明瞭,它最適合人性。與了解這個真理相結合的欲望是領導人的某種自然欲望,所以受過良好教育的靈魂在本質上不願服從任何人,除非他為了益處以正當及合法的方式告誡、教導與命令,從此出現雄心及對世俗事物的鄙視。
(14)事實上自然與理性的影響力不小,因為只有這個動物感知什麼是秩序,什麼是適切的事,及在行為與言談中什麼是恰如其分。因此我們藉視力所感知到那些事物的美麗、魅力及各個部分的和諧,其他動物無法感知到。自然與理性將此相似之物從眼睛傳遞至靈魂,認為這美、恆定與秩序更應該被保存,並提醒不要做有失體面或不具男子氣概的事,而且在所有的意見與行為上都不要做或想情欲之事。從這些事會產生及實現我們所追求的德行,就算它不是最富盛名,却是高尚可敬的;我們正確地說,對自然而言,它是值得讚賞之事,雖然它不被任何人稱讚。
[V](15)其實你,馬庫斯我的兒子,看見那形象,就像看到正直的樣貌,若它被雙眼識出,如柏拉圖所言,會激起對智慧不可思議的愛。然而每一個德行的事都起源於某四種源頭其中一種,因為不是某人忙碌於真理的了解與精微;就是忙碌於維持人群的聯繫,分配給每個人應得的事物,及確保關於約定事務的承諾;還有忙碌於卓越無敵的靈魂的偉大與堅實;不然就是忙碌於一切所做所說的事物的秩序與標準,謙遜與節制在其中。雖然這四部分相互連結糾纏,但從每個單獨的部分產生某種義務,一如從首先描述的那部分,在其中我們放入智慧與慎思明辨,真理的尋找及發現屬於這一部分,這個義務是此一德性的特質。
(16)因為任何人能更精準看見在任何事物中的最真之物,都能以最敏銳快速的方式了解及說明道理,他經常被恰當地認為是最慎思明辨及最有智慧的人。因此從屬於此德性的是,它處理及涉入的事物,真理。
(17)此外,準備及保護那些使生活中的活動得以維持的事物之必要性,是由剩下來的三個德性來表現,所以人的交誼與聯繫可被維持,且靈魂的優越及偉大在增加資源及提供自己與親友利益,更甚者,在看輕這些資源與利益上綻放光芒。另一方面,秩序、綱常、節制及那些與這些類似的德性被認為是那種一個行為必須與之符合的例子,不只是心靈的活動。因為將某種標準及秩序應用於生活中所處理的事務上,我們保持端正的儀節。
[VI](18)再者,從這四個主題,我們曾區分出德行的本質與意義,首先,那存在於真正的思考的事物,對人的本質影響甚深。因為我們都受到思想及知識的欲望的吸引及驅使,在其中我們認為卓越是美的特質,而失誤、犯錯、無知及受騙使我們過得狼狽可恥。此種與生俱來的德行中,我們必須避免兩種錯誤,一個是讓我們不要偏愛未受認定之事甚於已被認定之事,且讓我們不要輕率同意這些未受認定之事,因為想要免於犯錯之人(事實上所有人都該這麼想)會耗時勤勉地思考這些事。
(19)另一個錯誤是,有些人投注相當多的熱忱及時間在模糊困難却非必要的事上。若要避免這些錯誤,將思想的時間與注意力置於道德及有價值的事物上,這會受到妥適的讚美,如在天文學中我們聽過蓋伊烏斯‧蘇爾皮奇烏斯,幾何學中我們知道塞克斯圖斯‧彭沛烏斯,邏輯中我們知道許多人,公民法中我們知道更多人,這一切的知識都與真理的探究有關。從管理政務中被對真理的熱中給吸引是違背義務,因為德性的一切讚美在行為中。然而行動的中斷經常發生,許多人被允許回到研究,此外心靈的活動未曾停歇,它能夠在思想的研究中支持我們,甚至不用我們的活動力。然而所有的思考及靈魂的運動,要從事與德性行為、活得好及快樂相關的決定上,或是知識與思想的研究。
(20)到此,我們實際上已提到關於義務的最初源頭;
[VII]然而關於剩下的三個德性,此議題最廣為人知,人與人之間的聯誼及所謂生命的伙伴皆依此得以維持。它有兩個部分:正義,其中德性的光輝最耀眼,藉由它好人得以名之;與此關係相近的是仁慈,它也可被稱為寬大及慷慨。但正義的首要任務是不要讓任何人傷害他人,除非他受到不當的挑戰,再者,讓任何人使用公共財產是為了公共目的,使用私人財產是為了私人目的。
(21)私人財產不是出於自然,而是長期經營事業的結果,例如之前人們來到荒地,或是在戰爭中獲得勝利,或在法律、契約、規範及運氣中獲利。長期經營的結果是阿爾皮農的土地被認定為屬於阿爾皮農人,圖斯庫倫的土地是屬於圖斯庫倫人的,私人財產的分配也類似如此。由於這個分配的結果,某些原來是公有財產的事物,變成私人財產,因為個人的運氣,任何人擁有它,從此若有人為自己牟利,他將違反高尚社會的法律。
(22)但因為,如柏拉圖清楚所寫的,我們不僅為自己而生,且國家是我們存在的部分原因,朋友也是。此外,如斯多葛學派認可,在大地之上所有受造事物的產生是為人所用,但人的出生是為了人的緣故,所以在人之間可以互蒙其利,這事上我們應跟隨自然的指引:為了公益帶來為眾人所用之事,在人與人之間的交誼以施與受的相互協助,以技藝、工作及能力的互通有無來強化。
(23)此外,正義的基礎是誠信,它是關於承諾與約定的堅持及誠實。因為,雖然這個說法對某人而言是牽強的,但讓我們勇於倣效斯多葛學派哲學家,他們苦心研究語言從何處形成,且讓我們相信所謂的誠信,因為所言之事會發生。然而,不正義有兩種:一種是造成不正義,另外一種是被不正義之事所影響,若可以的話,它們不會避免傷害。因為對某人做不當攻擊的人,不是受憤怒所激,就是受某種其他的情緒的鼓動,就好像他將手置於同伴身上;但此同伴既不避免也不制止傷害,若他能的話,這種錯就如同放棄父母、朋友及國家一樣。
(24)事實上這些傷害,它們有意使人負傷,經常是出於憂心恐懼,因為想要傷害他人的人擔心,除非他傷害他人,否則會遭致某種不利於己的事。然而他們多半出手傷人,所以可獲得他們所欲求的事;在這錯誤中貪婪是顯而易見。
[VIII](25)再者,財富的需求不僅是為了生活必須,也是為了欲望的滿足。然而對財富有較大熱愛的人,從這些金錢他的欲求看到權力與影響力,及予人恩惠的資源,如近來馬庫斯‧克拉蘇斯否認,他會滿足於任何大量的家產,他想成為國家的領導者,若他無法以家產的收入供養一支軍隊的話。甚至可觀的收入及精緻富裕的舒適生活令人愉悅;這些事證明,對金錢的欲望是無盡的。事實上家族財富的增加,不傷害任何人的情況下,不應被責難,但這必須避免不正義。
(26)此外大多數人認為,當他們掉進追求軍事,政治職務及榮耀的欲望中時,他們忘了正義。事實上艾尼烏斯說:「對暴君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交情,也沒有誠信。」這句話可適用於較多的事例。因為任何諸如此類情況的存在,其中大多數人不可能出類拔萃,那情況通常會發生激烈的競爭,以致於很難維繫「神聖不可侵犯的交情」。最近蓋伊烏斯‧凱撒的輕率魯莽顯示了此事,他為了趁民意迷惑替自己安排帝王之位,破壞一切神聖及世俗的律法。其實在這種情況下,令人困擾的事是,極富熱情與卓越才能的人身上,通常存在著對功名、權力、影響力及榮耀的欲望。要更加注意的是,不要在這種事上犯錯。
(27)然而,一切不正義的事例中存在相當的差異性:不正義的發生是在靈魂的某種情緒下,它通常為時不長且是臨時性的,或是發生在擘畫設計及深思熟慮的情況下。這些在某種突發情緒中發生的不正義之事,與那些經過思慮及準備而產生的不正義之事相較,嚴重性較低。其實關於不正義的發生說得夠多了。
[IX](28)關於義務的辯護與放棄的諸多理由通常必須被忽略。因為人們不願樹敵、受苦或犧牲;或無心、緩慢及怠惰,或被他們個人的工作或某些職務給阻擋,所以他們允許該受保護的人被遺棄。因此在柏拉圖的著作中關於哲學家的說法是否令人滿意,必須斟酌思考:因為他們從事真理的探究,且因為他們鄙視大多數人熱烈期盼欲求的事物,人們經常為了這些事互相攻擊,且他們視這些事為無物,因此他們是正義之士。沒錯,他們追求另一種正義,不以從事不正義的行為傷害任何人,他們陷入這另類的正義,因為他們被學習的熱忱所阻礙,放棄他們應該保護之人。因此他們認為自己將不會參與政治,除非受迫。但這依他們的意願發生會較好,因為本質上是正當的行為之所以是正義的,只有當它的發生是出於自願。
(29)此外,有人藉由關切家務的熱忱或某種對人的憎惡,宣告他們從事的是自己的事業,對他人不會產生真正的傷害。他們避免了一種不正義,却涉入另一種不正義;事實上,他們放棄了生命中的聯繫,因為他們個人所追求的是對此聯繫沒有任何貢獻,不做任何努力,也不提供任何資源。
(30)因此我們提出兩種不正義,並分別附上理由,先前我們確立那些標準,藉此可獲得正義,我們將可在每個情況下判斷自己的義務是什麼,除非我們極為自私。因為對他人的事情表現關切是困難的。然而,特倫提烏斯筆下的角色克瑞梅斯「認為關於人的事皆與他有關」;但儘管如此,因為我們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或壞事的感受與知覺,比對發生在他人身上的事的感受與知覺來得強烈,就像是我們在遠距中看著他們,對於他們及對於自己,我們的判斷不同。因此,他們有不錯的建議,避免做任何你不清楚是公平或不公平的事。因為正義會透過其自身散發光芒,懷疑指出不正義的想法。
[X](31)然而經常發生的情況是,被認為極為適合正義的人及我們稱之為好人的行為,改變成為相反的行為,例如退還押金、許下承諾,及真理與誠信的促進,有時候逾越及不遵守這些行為規範是正義的。因為重新回到我一開始所定下適切的正義基礎,首先,勿傷人,再者,為公益服務。行為隨情況改變,義務改變且不會一直維持不變。
(32)因為這可能發生在某個承諾或契約上,履行承諾有害無益,無論是對被承諾人或承諾人而言。如神話中若海神內普圖奴斯沒有做祂承諾塞修斯的事,塞修斯不會失去他的兒子希波呂投斯,因為出於三個願望,如神話所言,這是第三個願望,盛怒的塞修斯希望希波呂投斯死,當心願完成,他陷入極度的哀傷。因此對被承諾之人有害的承諾不須履行,若這些承諾對你的傷害比對你下承諾之人的利益大,也不須履行,違反義務比偏愛較沒價值的事更重要。例如,若你與任何人有約,你將以證人的身分上法庭,且同時你的兒子開始生病,不履行你所言之事並不違反義務,若你下承諾之人抱怨自己被棄之不顧,反而是他違背義務。此外,某人沒有必要依約遵守那些承諾,若他做承諾時不知道自己是受恐懼的脅迫及受悲傷的欺瞞,事實上行政官的敕令免除了許多義務,法律也免除了一些。
(33)不正義也以某種極高明的狡辯存在著,但法律的詮釋上是詭詐的。藉此,那句陳腔濫調「無上的法律是不正義的極致」出現在日常語言中。許多諸如此類的錯誤甚至出現在國與國的交際中,如他,當與敵人訂定三十天的停戰協定,在晚上掠奪土地,因為協定事關白天不關夜晚。若真的是昆圖斯‧法比烏斯‧拉貝歐或其他人(因為我只有聽說此事),我們不應贊許自己的同胞,他被元老院指定為奴拉及拿波里邊境的仲裁者,當他到達該地,他與雙方分別晤談,他們不熱中於做任何事,也不急切,却想要撤退更甚於前進。當雙方皆完成撤退,中間留下一片土地。這片地便劃定了它們之間的界線,如他們所言的邊境,他將此中介地歸給羅馬人。這事實上是欺騙,不是仲裁。結論是,在所有的情況下諸如此類的精明應要避免。
[XI](34)然而對會帶給你傷害的人的某些義務還是須履行。因為報復與懲罰是有底線的;我說得更恰當些,或許這是足夠的:一個為惡之人後悔自己的不正義行為,所以他不會在未來做諸如此類之事,其他人也會較無意於不正義之事。此外在國與國的關係上,戰爭的正義必須特別地確保。例如有兩種決勝負的方式,一種是透過法律的討論協商,另一種是透過武力,由於前者是人的特質,後者是禽獸的特質,有必要依賴武力,若協商討論不被允許使用。
(35)因此為了那個理由一定要開啟戰爭,在和平正義中過活,然而戰勝之後,那些戰爭中沒有殘暴言行的人應被饒恕,他們不是野蠻人,如我們的祖先甚至曾接納圖斯庫倫人、艾奎人、渥斯奇人、莎賓人,以及艾爾尼奇人具有公民身分,但他們徹底摧毀迦太基與奴芒提亞;我拒絕他們完全毀滅柯林斯,但我相信他們有某些理由做此事,特別是柯林斯有利的地理位置,有時候這個位置真的會鼓動開啟戰爭。事實上我的看法是,必須持續地關注和平,不使任何巧詐之事發生。在這個看法上若他們同意我的話,我們或許沒有最好的,但至少是某種現在沒有的政府。對那些你以武力完全征服的人不僅要照顧,且要給那些解除武裝依賴指揮官誠信的人承諾,即使撞槌衝擊城牆。在這件事上,正義經常被我們的祖先執行,他們承諾接納戰爭中被擊垮的國家與氏族,他們成為那些戰敗者的保護主,依據先祖的慣例。
(36)其實羅馬人的菲提亞利斯以最恭謹的態度將戰爭法寫入法律中,從此法可知戰爭無一正義,除非是在要求決戰之後發動,或是先提警告,再宣戰。〔波匹利烏斯將軍是一省之主,他的部隊中,卡投之子是新進士兵。當波匹利烏斯想要解散一個軍團,卡投的兒子在該軍團服役,所以他也會遣散他。然而卡投之子依然保有在軍中戰鬥的熱忱,卡投寫信給波匹利烏斯,若他允許其子待在軍中,他會使他有第二次向部隊宣示效忠的義務,因為之前的宣誓失效,他無法與敵人作戰。所以這是在發動戰爭中最應留意之事。〕
(37)老馬庫斯‧卡投給兒子馬庫斯的信尚存,其中他言及聽到執政官將兒子解職,當他在馬其頓與沛爾塞斯的戰爭中任職士兵。因此他提出警告,注意不要挑起紛爭,因為法律拒絕不是軍人的人與敵人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