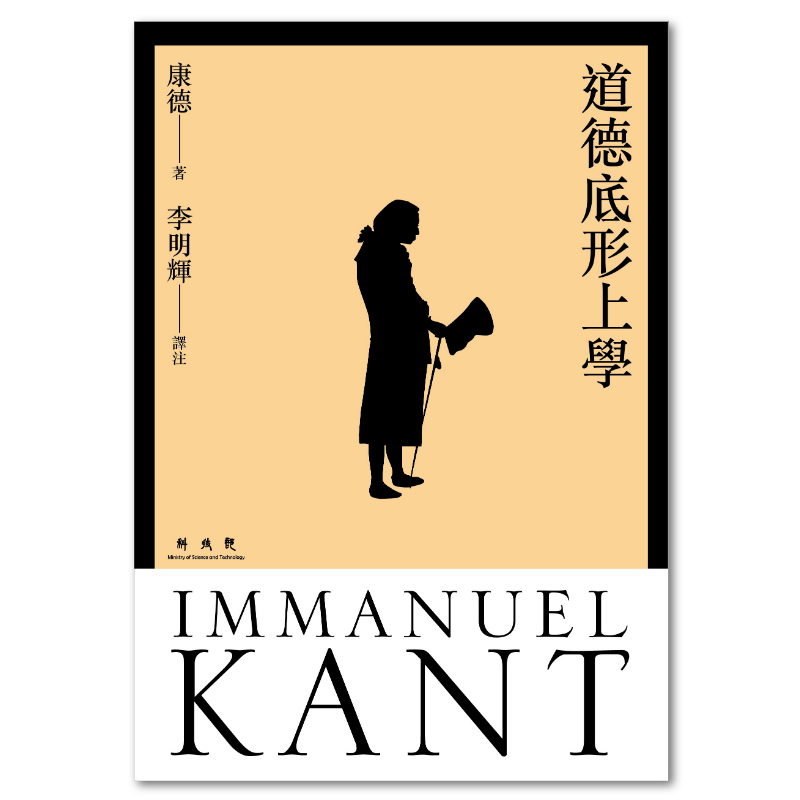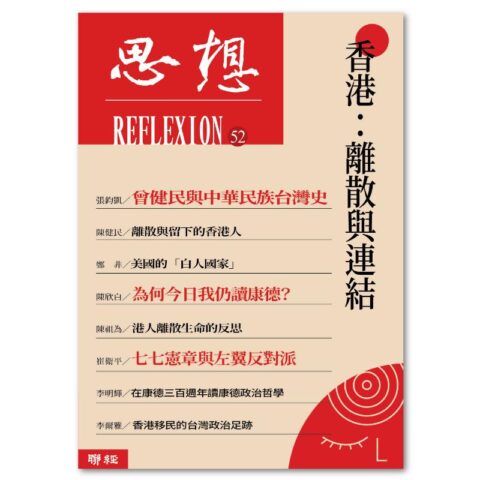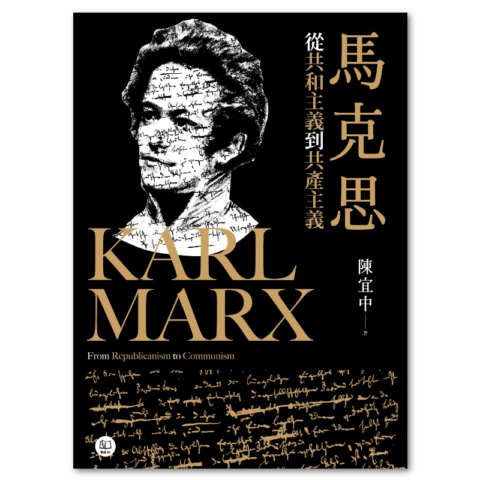道德底形上學(精裝)
原書名:Metaphysik der Sitten
出版日期:2015-03-20
作者:伊曼努埃.康德
譯注者:李明輝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564
開數:25開(高21×寬14.8cm)
EAN:9789570845365
系列:聯經經典
尚有庫存
本書雖名為「形上學」,
其實是探討道德原則與法律原則在具體生活層面中的落實,
因此是康德實踐哲學的完成。
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學》一書包含《法權論之形上學根基》與《德行論之形上學根基》兩部分,在康德生前,這兩部分各分別出版,而未曾合為一書。前者是康德唯一一部完整討論法哲學的著作,探討「法權」的一般概念、公法的三個層面,以及私法的「物權」、「人格權」、「出於物的方式的人格權」等各面。後者有助於我們釐清當代西方「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所引發的爭論,並確定「義務」及「德行」皆是康德倫理學中的重要概念。
康德更早期的《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和《實踐理性批判》兩本著作,突出倫理學之形式主義特徵。在這樣的基礎上,於《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進一步將道德法則應用於人性上,並涉及實踐人類學底層面。在書中康德強調法權論與德行論之根本差異在於:前者可以維持其形式主義底特色,後者卻必須發展出一套「目的學說」。本書探討「法權」及「德行」等核心概念,因此康德在出版《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和《實踐理性批判》後,堅持完成本書,以使其道德哲學更臻完善。
作者:伊曼努埃.康德
1724年生於東普魯士科尼希貝爾格(Konigsberg),1804年逝世於該城。1740年就讀於科尼希貝爾格大學,1746年至1755年迫於生計而終止學業,擔任家庭教師。1755年在科尼希貝爾格大學完成學業後,留校任教,直到1797年因年老力衰,才終止授課。在哲學方面,他繼承啟蒙哲學之傳統,綜合歐陸理性論與英國經驗論,形成其批判哲學,開啟從菲希特到黑格爾的德國理念論;就其原創力及影響力而言,誠為近代西方哲學家第一人。其主要著作有《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道德底形上學》、《單在理性界限內的宗教》、《未來形上學之序論》等。
譯注者:李明輝
原籍臺灣屏東,1953年出生於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及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其後獲得「德國學術交流服務處」(DAAD)獎學金,赴德國波昂大學進修,於1986年獲得該校哲學博士。曾擔任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客座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廣州)中山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目前已退休。主要著作有《儒家與康德》、《儒學與現代意識》、《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康德倫理學發展中的道德情感問題》(德文)、《儒家思想在現代中國》(德文)、《孟子重探》、《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儒家人文主義:跨文化的脈絡》(德文)、《儒學:其根源與全球意義》(英文)、《康德與中國哲學》,譯作有H. M. Baumgartner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康德的《通靈者之夢》、《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未來形上學之序論》及《道德底形上學》。
譯者前言
中譯本導讀:《道德底形上學》之成書始末及其哲學意義
一、《道德底形上學》之成書始末
二、《道德底形上學》之版本問題
三、《道德底形上學》之哲學意義
凡例
康德著作縮寫表
第一部 法權論之形上學根基
前言
法權論之畫分表
道德底形上學之導論
Ⅰ. 論人類心靈底能力與道德法則之關係
Ⅱ. 論道德底形上學之理念與必然性
Ⅲ. 道德底形上學之畫分
Ⅳ. 道德底形上學之預備概念(普遍實踐哲學)
法權論導論
§ A. 何謂法權論?
§ B. 何謂法權?
§ C. 法權底普遍原則
§ D. 法權與強制的權限相結合
§ E. 嚴格的法權也能被表述為一種根據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相協調的全面的相互強制之可能性
附論法權論之畫分
論有歧義的法權(zweideutiges Recht/Ius aequi- vocum)
Ⅰ. 衡平性(Billigkeit/Aequitas)
Ⅱ. 緊急權(Notrecht/Ius necessitatis)
法權論之畫分
A. 法律義務之一般畫分
B. 法權之一般畫分
天賦的權利只有一項
一般而言的道德底形上學之畫分
Ⅰ.
Ⅱ. 根據法則對於義務的客觀關係之畫分
Ⅲ. 根據責以義務者對於承擔義務者的主觀關係之畫分
論對於作為一般而言的義務底系統之道德學的畫分
法權論 第一篇 私法
第一篇 關於一般而言的外在所有物之私法
第一章 論將某外在之物當作所有物而擁有的方式
第二章 論取得某外在之物的方式
第一節 論物權
第二節 論人格權
第三節 論出於物的方式之人格權
家庭社會之權利 第一項:婚姻權
家庭社會之權利 第二項:親權
家庭社會之權利 第三項:家長權
一切可從契約取得的權利之獨斷的畫分
盜印書籍依法律是禁止的
補節 論對於意念底一個外在對象之 理想的取得
Ⅰ. 藉由時效而取得的方式
Ⅱ. 繼承(Acquisitio hereditatis〔遺產之取得〕)
Ⅲ. 身後遺留令名(Bona fama defuncti〔身後的令名〕)
第三章 論藉由一種公開的司法權底判決而來之主觀上有條件的取得
A. 論贈與契約
B. 論借貸契約
C. 論對遺失物的索回(取回)(vindicatio)
D. 論藉由宣誓而取得保證 (Cautio iuratoria〔宣誓的保證〕)
從自然狀態中的所有物到法律狀態中的所有物 之一般而言的過渡
法權論 第二篇 公法
第一章 國家法
論因時效而佔有的權利
論繼承
論國家對於為其臣民而設的永久基金會之權利
結語
第二部 德行論之形上學根基
前言
德行論之導論
I. 關於「德行論」底概念的探討
II. 關於「一項同時是義務的目的」底概念的探討
III. 論設想「一項同時是義務的目的」之根據
IV. 同時是義務的目的為何?
V. 對於這兩個概念的闡釋
VI. 倫理學並不為行為立法(因為這是法權論之事),而是僅為行為底格律立法。
VII. 倫理義務具有寬泛的責任,而法律義務卻具有狹隘的責任。
VIII. 對於作為寬泛義務的德行義務之解說
IX. 何謂德行義務?
X. 法權論底最高原則是分析的;德行論底最高原則是綜合的。
XI. 德行義務之圖表
XII. 心靈對於一般而言的義務概念的感受性之感性的預備概念
XIII. 在關於一套純粹德行論的探討中道德底形上學之普遍原理
XIV. 論德行論與法權論分離之原則
XV. 德行首先要求自我控制
XVI. 德行必然預設不動心(被視為力量)
XVII. 德行論底畫分之預備概念
XVIII.
倫理學底畫分
倫理學的成素論
第一部 論對自己之一般而言的義務
導論
§ 1. 「一項對自己的義務」底概念(乍見之下)包含一項矛盾
§ 2. 但是卻存在人對自己的義務
§ 3. 對這種表面的背反之說明
§ 4. 論對自己的義務之畫分原則
第一卷 論對自己的完全義務
第一章 論人對作為動物性存有者的自己之完全義務 § 5313
第一款 論自戕
第二款 論淫慾的自瀆
第三款 論因無節制地使用享受品或甚至食品而致的自我麻醉
第二章 人對僅作為一個道德性存有者的自己之義務
Ⅰ. 論說謊
Ⅱ. 論吝嗇
Ⅲ. 論阿諛
第一節 論人對作為天生的自我裁判者的自己之義務
第二節 論對自己的一切義務之第一命令
附節 論道德的反省概念之曖昧:將原屬人對自己的義務者當作對他人的義務
第二卷 論人對自己(關乎其目的)的不完全義務
第一節 論人在發展並增益其自然圓滿性時,亦即在實用方面,對自己的義務
第二節 論人在提升其道德圓滿性時,亦即純然在道德方面,對自己的義務
第二部 論對他人的德行義務
第一章 論對僅作為人的他人之義務
第一節 論對其他人的愛底義務
導論
專論愛底義務
愛底義務之畫分
A. 論慈善底義務
B. 論感恩底義務
C. 同情感根本是義務
論與對人的愛正相(相反)對立之對人的恨底罪惡
第二節 論出於對其他人應受到的尊敬而對他們的德行義務
論傷害對其他人的尊敬之義務的罪惡
A. 傲慢
B. 毀謗
C. 嘲笑
第二章 論人與人之間針對其狀態的倫理義務
成素論之結論
論愛與尊敬在友誼中的緊密結合
附錄 論交往底德行(virtutes homileticae)
倫理學的方法論
第一節 倫理學的教學法
附釋 一部道德的問答手冊之片段
第二節 倫理學的修行法
全部倫理學之結論:作為對上帝的義務之學說的宗教學說位於純粹道德哲學底界限之外
結語
倫理學底畫分表
相關文獻
導讀選摘(節錄)/《道德底形上學》之哲學意義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兩個部分當中,《法權論》底哲學價值較易理解,因為這是康德唯一一部完整討論法哲學的著作。上文提到:康德在〈論俗語所謂:這在理論上可能是正確的,中但不適於實踐〉及《論永久和平──一項哲學性規畫》中已討論到法哲學底部分議題。此外,在〈在世界公民底觀點下的普遍歷史之理念〉(1784)、〈評胡菲蘭底《試論自然法底原理》〉(1786)、〈重提的問題:人類是否不斷地趨向於更佳的境地?〉三篇論文中,康德亦論及法哲學底議題。但以上的五種著作,或是泛論法權(Recht)底概念,或是僅討論公法(包括國家法、國際法與世界公民權三個層面)。
對比於上述的著作,《法權論》之重要性就在於:它不但探討「法權」底一般概念與公法底三個層面,還以更大的篇幅完整地探討私法底諸層面。因此,我們要了解康德底私法理論,最主要的憑藉便是《法權論》。在有關私法的探討中,康德先討論「外在的所有物」(das äußere Mein und Dein),再探討私法底三個層面,即「物權」(Sachenrecht)、「人格權」(persönliches Recht)與「出於物的方式的人格權」(das auf dingliche Art persönliche Recht)。所謂「出於物的方式的人格權」係指帶有物權特徵的人格權,包括婚姻權、親權與家長權。以婚姻權為例,康德先界定婚姻關係中的性交合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底性器官與能力的交互使用」 ,再說明其混合特徵如下:
因為一性對另一性底性器官的自然使用是一種享受(Genuß),而為了這種享受,一方委身於另一方。在這個行動中,一個人使自己成為物,而這與他自己人格中的「人」(Menschheit)之權利相牴牾。只有在唯一的一項條件下,這才是可能的,此即:當一個人格如同物一般地被另一個人所取得,而前者又反過來取得後者時,這樣一來,這個人格便重新贏得自己,並且再度恢復其人格性。
大陸學者蔣慶曾如此描述「德國唯心論」:「德國唯心論的特徵就是形而上學佔優勢,不管是康德的道德形上學還是黑格爾的精神形上學,其關注的重點都是遠離現實的概念系統。這些形上學追求的只是自身概念系統的統一與完善,而不關心活生生的現實存在及其要求。」這番評論頗能代表一般人對康德哲學的刻版印象,但是當蔣慶看到康德如此界定婚姻權時,恐怕會瞠目結舌吧!
接著,筆者要討論《德行論》在康德倫理學發展中的意義。筆者底討論集中在以下的三個問題:一、《德行論》與較早出版的兩部倫理學著作《基礎》(1785年)與《實踐理性批判》(1788年)之關聯為何?二、相較於先前出版的兩部倫理學著作,《德行論》有何新的內容?三、對於當前的倫理學研究而言,《德行論》有何特殊意義?以下即分別討論之。對於前兩個問題,德國學者許慕克(Josef Schmucker)在其1955年發表的一篇長文〈康德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與實質的目的原則〉 中作了極詳細的闡述,迄今仍極具參考價值,故筆者以下的相關討論基本上循其思路進行。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康德自己在《基礎》一書底〈前言〉就作了清楚的說明:
我決心有朝一日提出一部道德底形上學,如今先發表本書。誠然,除了純粹實踐理性底批判之外,道德底形上學根本沒有其他的基礎,正如除了我已發表的純粹思辨理性底批判之外,形上學並無其他的基礎一樣。然而,一則,前一種批判不像後一種批判那樣極端必要,因為在道德領域中,人類理性(甚至在最通常的知性中)能輕易地達到最大的正確性和周詳性;反之,它在理論的且純粹的運用中卻是完全辯證的。再則,我要求:純粹實踐理性底批判若要成為完整的,我們就得能同時顯示實踐理性和思辨理性之統一於一項共通原則之下;因為到底只能有同一個理性,而它僅在應用上才須分別開來。但我在此若不引進另外一種考察,而攪亂讀者底心思,就仍然無法使這項工作達到這樣一種完整性。為此緣故,我使用了「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名,以代替「純粹實踐理性底批判」之名。
根據此處所言,《實踐理性批判》是《道德底形上學》(當然包括《德行論》)之基礎,而《基礎》又是《實踐理性批判》之預備工作,以便集中探討倫理學底基本原則(定言令式)及其推證(Deduktion)。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前言〉中,康德也說明:「在實踐理性底批判之後應當有一個系統,即道德底形上學――它分為法權論之形上學根基與德行論之形上學根基。」
此外,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底〈前言〉中也有如下的一段說明:「純粹實踐理性底這樣一種系統(在此係由這種理性之批判發展出來)是否已費了或多或少的辛勞,以便特別不錯失能據以恰當地勾畫這種理性底整體的正確觀點,我必須留待這樣一類工作底行家去評斷。這個系統固然預設《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但僅是就後者使人初步熟悉義務底原則,而且提出並證成義務底一項確定程式而言;在其他其況下,這個系統是獨立存在的。至於一切實踐的學問之畫分並未如思辨理性底批判所做的那樣,為了完整性而被附加上去,其有效的理由也見諸這種實踐的理性能力之特性當中。因為「將諸義務特別規定為人底義務,以便將它們加以畫分」一事,唯有在這種規定底主體(人)事前依其據以現實存在的特性(儘管只是在對於一般而言的義務為必要的範圍之內)而被認識時,才是可能的。但是這種規定不屬於一般而言的實踐理性之批判,而這種批判只該完整地說明這種理性底可能性、其範圍與界限,而不特別針對人性。因此,這種畫分在此屬於學問底系統,而非批判底系統。」
根據這段說明,《基礎》之所以是《實踐理性批判》之預備工作,係由於它「使人初步熟悉義務底原則,而且提出並證成義務底一項確定程式」。至於他所謂「一切實踐的學問之畫分」(包括「將諸義務特別規定為人底義務,以便將它們加以畫分」),顯然是指《道德底形上學》(所謂「學問底系統」)之工作。
康德還特別強調:這種畫分唯有「在這種規定底主體(人)事前依其據以現實存在的特性……而被認識時」,才是可能的。這就涉及《基礎》、《實踐理性批判》二書與《道德底形上學》之不同任務。在《基礎》與《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強調「純粹的道德哲學」(即道德底形上學)必須「完全清除了一切只能是經驗的、且屬於人類學的事物」。因此他問道:「學問底本性難道不要求我們始終謹慎地將經驗的部分與理性的部分分開,並且在依本義而言的﹙經驗的﹚自然學前面預置一門自然底形上學,而在實踐人類學前面預置一門道德底形上學嗎?這兩門形上學必須謹慎地清除一切經驗之物,以了解純粹理性在這兩種情況下能有多少成就,以及它本身從什麼來源取得它這種先天的教導……」
但是在《道德底形上學》中,他卻進一步強調:「如同在一門自然底形上學當中也必須有將那些關於一般而言的自然之普遍的最高原理應用於經驗底對象的原則,一門道德底形上學也不能欠缺這類原則,而且我們將時常必須以人之特殊本性(Natur)──它唯有靠經驗去認識──為對象,以便在這種本性中印證由普遍的道德原則得出的結論,但卻不會因此而對這些道德原則之純粹性有所損害,也不會因此而使其先天來源受到懷疑。這等於是說:一門道德底形上學無法以人類學為根據,但卻能應用於人類學。」
綜而言之,《基礎》與《實踐理性批判》二書僅立足於倫理學的原則論(ethische Prinzipienlehre)底層面,而《道德底形上學》則進一步將道德法則應用於人性上,而涉及實踐人類學底層面。因此,康德在前兩書中討論「義務」概念時,並未特別考慮人底特徵(人性),而在《道德底形上學》中,他特別「將諸義務特別規定為人底義務,以便將它們加以畫分」,故必須涉及實踐人類學底知識。
其次,《基礎》和《實踐理性批判》二書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調亦有所不同:前者突出康德倫理學底形式主義特徵,後者則提出「同時是義務的目的」(Zwecke, die zugleich Pflichten sind)底概念,因而包括一套「目的學說」(Zweck- lehre)。康德在《基礎》中將道德法則(定言令式)界定為一項「形式原則」。他寫道:「欲求底主觀根據是動機﹙Triebfeder﹚,意欲底客觀根據是動因﹙Bewegungsgrund﹚;因此有主觀目的﹙它們基於動機﹚和客觀目的﹙它們取決於對每個有理性者均有效的動因﹚之區別。如果實踐的原則不考慮一切主觀目的,它們便是形式的;但如果它們以主觀目的、因而以某些動機為根據,它們便是實質的。一個有理性者隨意選定為其行為底結果的那些目的﹙實質的目的﹚,均是相對的;因為唯有它們對主體底一種特殊欲求能力的關係能予它們以價值。所以,這項價值無法提供對一切有理性者、而且也對每個意欲均有效且必然的普遍原則,亦即實踐法則。因此,這一切相對的目的只是假言令式底根據。」
在這段文字中,康德主要從反面的角度說明假言令式是一項「實質原則」;若從正面立論,這便意涵:定言令式是一項「形式原則」。所謂「形式原則」即是不預設任何質料或對象(即主觀目的)的原則。至於他在這裡提到的「客觀目的」並非指意志底任何質料或對象,而是指作為「目的自身」(Zweck an sich selbst)的有理性者 ,亦即道德主體本身。
同樣的意思也見諸《實踐理性批判》中的「定理三」:「如果一個有理性者要將其格律設想為普遍的實踐原則,他只能將這些格律設想為這樣的原則,即是:它們不能依質料,而只能依形式包含意志底決定根據。」反之,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卻強調:「法權論僅涉及外在自由之形式條件(根據其格律被當作普遍法則時的自相協調),也就是說,涉及法權。反之,倫理學還提供純粹理性底一項質料(自由意念底一個對象)、一項目的,而這項目的同時被表述為客觀上必然的目的,亦即對人而言,被表述為義務。因為既然感性愛好誘使人去追求可能違反義務的目的(作為意念底質料),則除非再藉一項相反的道德目的(它因此必須無待於愛好、先天地被給與),否則制定法則的理性無法扼止感性愛好之影響。」
在這段文字中,康德強調法權論與德行論之根本差異在於:前者可以維持其形式主義底特色,後者卻必須發展出一套「目的學說」。因為德行論若是無法提出一項基於實踐理性的道德目的,實踐理性便無法對抗基於感性愛好的主觀目的。這種道德目的,康德在《德行論》中即稱為「同時是義務的目的」 ,而它們包括「自己的圓滿性」與「他人底幸福」。因此,康德說:「倫理學也能被界定為純粹實踐理性底目的之系統。」 又說:「在倫理學中,義務概念會導向目的,而且必須根據道德原理,針對我們應當為自己設定的目的來建立格律。」 誠如許慕克所指出,康德在《德行論》中之所以提出「他人底幸福」與「自己的圓滿性」這兩項「同時是義務的目的」,係基於「人底理性本性之不圓滿性、局限性與有需求性」,換言之,「立法的理性只能藉由相反的道德目的來防範感性愛好之影響」。
在提出「同時是義務的目的」之後,康德接著說明倫理學與法權論之區別在於:前者是為行為底格律立法,後者則是為行為立法。由此他進而推斷:倫理義務(德行義務)是寬泛義務(Weite Pflicht),而法律義務是狹隘義務(enge Pflicht)。對於「寬泛義務」,他解釋說:「如果法則只能命令行為底格律,而非行為本身,這便是一個訊息〔,它表示〕:法則為自由的意念在遵循(服從)方面留下一個迴旋餘地(Spielraum/latitudo),也就是說,它無法確切地指出:我們應當如何且在什麼程度上藉由行為去促成同時是義務的目的?但是所謂「寬泛的義務」,並非意謂容許行為底格律之例外,而只是意謂容許一項義務底格律為其他義務底格律所限制(例如,以對父母之愛來限制對鄰人之普遍的愛),而這事實上擴展了德行實踐之領域。、換言之,法律義務直接規範行為本身,而在行為底層面並無迴旋餘地,故稱為「狹隘義務」;反之,德行義務僅規範行為底格律,而在行為底層面留下迴旋餘地,故稱為「寬泛義務」。例如,促進他人底幸福是一項德行義務,但我們該如何去做?該做到什麼程度?義務本身卻無法明確地規定,故為寬泛義務。
其實,「狹隘義務」與「寬泛義務」之區別已出現在《基礎》一書之中,只不過康德在那裡主要稱之為「完全義務」(vollkommene Pflicht)與「不完全義務」(unvollkommene Pflicht),有時稱之為「必然義務」(notwendige Pflicht)與「偶然義務」(zufällige Pflicht),或是「本分的義務」(schuldige Pflicht)與「有功績的義務」(verdienstliche Pflicht)。在提出定言令式之「普遍法則底程式」及其輔助程式「自然法則底程式」之後,康德根據「完全義務」∕「不完全義務」與「對自己的義務」∕「對他人的義務」之兩組區分分別提出四個例子來討論。他在一個註解中表示:「在此大家必得注意:我將義務底區分完全保留給未來的一部《道德底形上學》,因此這裡的區分只是隨便定的(以便安排我的例子)。此外,我在這裡將一項完全義務理解為不容為愛好之利而破例的義務;而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僅有外在的完全義務,也有內在的完全義務。」這裡所謂「外在的完全義務」係指對他人的義務,所謂「內在的完全義務」則是指對自己的義務。
事實上,在《德行論》中,康德也使用「完全義務」與「不完全義務」這組概念。再者,他在〈德行論之導論〉中一方面明白地寫道:「唯有不完全的義務是德行義務。」 另一方面又強調:由於倫理學容許其不完全義務有迴旋餘地,它需要一種「個案鑑別法」(Kasuistik)。所謂「個案鑑別法」係一種以個案為例的指導方法,係由斯多亞學派、猶太法典學者、士林哲學家及耶穌會士逐漸發展出來。其目的在於教人如何將法律或道德法則底規範應用於具體的行為或行為情境中,或者發現在個別情況中有效的規則(尤其是在良心衝突或義務衝突之情況中)。路特維希便發現:康德此處所說的,與他在〈倫理學的成素論〉中所說的,並不一致。因為在〈倫理學的成素論〉中康德將人對自己的完全義務也當作德行義務來討論,並且為每一項這類的義務均提出「個案鑑別的問題」。
現在我們回到《基礎》中關於「完全義務」與「不完全義務」的討論。此書中有一段文字甚具關鍵意義:「我們必須能意願:我們的行為底一項格律成為一項普遍法則;這是一般而言的行為底道德判斷之法規。有些行為具有以下的特質:它們的格律決無法無矛盾地被設想為普遍的自然法則;更不用指望我們還能意願它應當成為這樣一項法則。在其他行為中,我們固然不會見到這種內在的不可能性,但是卻不可能意願它們的格律被提升到具有一項自然法則底普遍性,因為這樣一個意志將自相牴牾。我們不難看出:前一種行為與嚴格的或狹隘的﹙不可寬貸的﹚義務相衝突,後一種行為與寬泛的﹙有功績的﹚義務相衝突。」
這裡所謂「一般而言的行為底道德判斷之法規」便是指定言令式。依康德之意,當我們藉定言令式來檢驗違背完全義務的格律時,我們根本不可能設想它成為普遍的自然法則,而不致陷於邏輯的矛盾(「內在的不可能性」)。但是當我們藉它來檢驗違背完全義務的格律時,我們雖可以設想它成為普遍的自然法則,而不致陷於邏輯的矛盾,但卻會陷於意志本身之自我衝突,故我們無法意願它成為普遍的自然法則。
以康德自己在《基礎》中所舉「不可作假承諾」這項對他人的完全義務為例, 他設想將「為了擺脫財務困境而作假承諾」這項格律當作一項普遍的自然法則之情況如下:「現在我立即看出:我的格律決無法作為一項普遍的自然法則而成立,並且自相協調,而是必然自相牴牾。因為這項法則──每個人一旦認為自己處於急難中,均可對他想到的事作承諾,而有意不信守之──底普遍性將使承諾及我們在作承諾時可能懷有的目的本身成為不可能;因為沒有人會相信他得到任何承諾,他倒會嘲笑所有這種表示為空言。」這就是說:一項假承諾之所以違反義務,是因為它所依據的格律在普遍化之後,會使它陷於邏輯上的矛盾,而取消自己,亦即使承諾本身不可能存在。
但是不完全義務之情況則有所不同。康德自己舉「發揮自己的才能」作為對自己的不完全義務之例,並且如此證成其道德性:「他現在看出:縱使人(就像太平洋中的居民一樣)任其才能荒廢,並且一心只將其生命用於閒蕩、歡娛、繁殖,一言以蔽之,用於享受,一個自然界誠然還是能依據這樣一種普遍法則而存在;然而,他不可能意願:這成為一項普遍的自然法則,或者由於自然本能而被置於我們內部,作為這樣一種法則。因為他身為一個有理性者,必然意願他的所有能力得到發展,因為它們的確是為了各種可能的目的供他使用,且被賦與他。」
「任自己的才能荒廢」這項格律普遍化之後,顯然並不會形成邏輯的矛盾。這項格律之所以被視為不道德的,並非由於它在普遍化之後,會陷於A與-A之邏輯矛盾,而是由於它會使意志陷於自我衝突,如康德在《基礎》中所言:「現在,如果我們在每次違犯一項義務時注意我們自己,我們便發現:我們實際上並不意願我們的格律應當成為一項普遍法則(因為這對我們而言是不可能的)﹚,而不如說這項格律之反面應當始終普遍地作為一項法則;只是我們擁有自由,為我們自己,或者為我們的愛好之利(甚至僅僅這麼一次)破一次例。因此,如果我們從同一個觀點(即理性底觀點)衡量一切,我們會在我們自己的意志中見到一項矛盾,這即是:某一項原則在客觀方面是必然的普遍法則,但在主觀方面可能不是普遍地有效,而容許例外。但是既然我們先從一個完全合乎理性的意志底觀點去看我們的行為,然後卻又從一個受到愛好影響的意志底觀點去看這同一個行為,則實際上在此並無矛盾,但是有一種愛好對理性規範的反抗(antagonismus)。」質言之,康德在此使用「矛盾」一詞,並非就嚴格的邏輯意義而言,而是指兩種觀點(理性觀點與非理性觀點)之間的對抗,它會使意志陷於自我衝突。
筆者在〈獨白的倫理學抑或對話的倫理學?──論哈柏瑪斯對康德倫理學的重建〉一文中曾將以上的討論總結如下:「定言令式之所以可作為道德判斷底法規,主要並非因為它可藉矛盾律排除不道德的行為,而是因為它提供一個理性的觀點,使人在採取不道德的格律時能反省到其意志所涉入的自我衝突。至於我們在完全義務底例子中所見到的邏輯矛盾,也必須就這個觀點來理解,因為一個自相協調的意志也不能容許邏輯的矛盾。一個包含邏輯矛盾的意志不過是自我衝突的意志之一個特例而已。因此,我們在定言令式中據以證成特定義務的,主要是意志底一致,而非邏輯的一貫。」
康德在《基礎》中為「完全義務」與「不完全義務」之區分所提出的理據便止於此,進一步的理據即在於《德行論》中所提出的「同時是義務的目的」底概念。就此而言,《德行論》中的義務學說係繼承《基礎》中的相關學說而有進一步的發展。許慕克又指出:其實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已包含了「同時是義務的目的」底概念。他引述的是《實踐理性批判》中的三段文字:「格律底質料固然能保持不變,但它必然不是格律底條件,因為否則格律就不適於作為法則。因此,一項限制質料的法則之純然形式必須同時是一項根據,將這項質料附加於意志,但非預設這項質料。譬如,假設以我自己的幸福為質料。如果我將這種幸福歸諸每個人(事實上,我可以將它歸諸每個有限的存有者),那麼唯有當我將他人底幸福也包含於其中時,我自己的幸福才能成為一項客觀的實踐法則。」
實踐理性底唯一對象是「善」與「惡」底對象。「善」意指欲求能力底一個必然對象,「惡」意指憎惡能力底一個必然對象,但兩者均是根據理性底一項原則。『善』與『惡』底概念不能先於道德法則(表面看來,道德法則甚至必須以這個概念為依據)而被決定,卻是必須只(就像這裡的情況一樣)後於且藉由道德法則而被決定。許慕克認為:這些文字均符合康德在《德行論》中所言:「在倫理學中,義務概念會導向目的,而且必須根據道德原理,針對我們應當為自己設定的目的來建立格律。」 因為在康德底用語中,意念底對象與目的是一回事。
最後,筆者要回答第三個問題:對於當前的倫理學研究而言,《德行論》有何特殊意義?筆者想從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對康德底「道德形式主義」的批評談起。黑格爾在《法哲學大綱》中寫道:「康德底進一步的形式──即一個行為之能被設想為普遍格律──固然使人更具體地設想一個狀態,但是它本身除了矛盾之免除與形式的同一性以外,並不包含任何其他的原則。──說所有制不存在,就像說這個或那個個別的民族、家庭等等不存在,或者說根本沒有人生存一樣,其本身都不包含任何矛盾。若是我們在其他情況下已確定且假定:所有制和人類底生命均存在,且應受到尊重,那麼竊盜或殺人就是一項矛盾。一項矛盾之發生只能連著某個東西,亦即連著一項事先已作為固定原則而成為基礎的內容。唯有關聯著這樣的東西,一個行為才會與之相協調或相矛盾。但如果我們應當把義務僅當作義務而意願之,而非為了一項內容而意願之,義務便是形式的同一性,正是這種形式的同一性排除一切內容和決定。」
黑格爾顯然將康德底定言令式理解為有如邏輯中的矛盾律與同一律一樣,是空洞而無內容的。筆者在〈獨白的倫理學抑或對話的倫理學?──論哈柏瑪斯對康德倫理學的重建〉一文中曾詳細反駁其說 ,讀者可參看。黑格爾對康德倫理學的批評甚至延續到謝勒(Max Scheler, 1874-1928)在其《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與實質的價值倫理學》(D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一書中對康德倫理學底形式主義的批評。根據以上的討論,此處只消指出:黑格爾與謝勒均忽略了康德對「不完全義務」的說明及其「同時是義務的目的」底概念。在這個意義下,《道德底形上學》中所強調之實質的目的原則足以反駁黑格爾與謝勒之誤解。
此外,《道德底形上學》也有助於我們釐清當代西方「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所引發的爭論。眾所周知,英國哲學家安思孔(G.E.M. Anscombe)於1958年發表的論文〈現代道德哲學〉 引發了復興德行倫理學的思潮。在這篇論文中,安思孔將以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為代表的「古代道德哲學」與以康德倫理學與後果論(主要是功利主義)倫理學為代表的「現代道德哲學」強烈對立起來。暫且撇開後果論不談,流行的觀點認為以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為主要代表的德行倫理學和以康德倫理學為主要代表的「義務論倫理學」(deontological ethics)之一項主要區別在於:前者係以「德行」底概念為首出,而後者則是以「義務」底概念為首出。但近年來,這項觀點在西方哲學界逐漸受到挑戰。因為《道德底形上學》一書顯示:「義務」固然是康德倫理學中的重要概念,但「德行」底概念又何嘗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呢?
近年來已有不少西方學者探討康德底「德行」概念,以顯示這個概念在康德倫理學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勞登(Robert R. Louden) 、歐尼爾(Onora S. O’Neill) 、強森(Robert N. Johnson) 、薛爾曼(Nancy Sherman) 、艾瑟(Andrea Marlen Esser) 等人。近年來,貝茲勒(Monika Betzler)編輯的 Kant’s Ethics of Virtue一書(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8)收錄了一批相關的論文,頗值得參考。貝茲勒在此使用ethics of virtue一詞,而非virtue ethics一詞,有其特殊的用意。她在這部論文集的〈導論〉中表示:「此處的論文表示:康德倫理學的確不可被納入德行倫理學之中。〔……〕但是康德後期的著作有助於我們了解:德行是其倫理學中的一個核心要素,正因為德行有助於我們盡我們的義務。」(頁27)因此,以「義務」與「德行」的對比來區分義務論倫理學與德行倫理學,是無意義的。總而言之,研究《道德底形上學》的確有助於釐清環繞著「德行倫理學」的爭論及其相關問題。然而,由於這個問題牽涉過廣,我們必須就此打住,留待其他的機會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道德底形上學之導論
I. 論人類心靈底能力與道德法則之關係
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ögen)是憑藉我們的表象而作為這些表象底對象之原因的能力。一個存有者依其表象而行為的能力稱為生命(Leben)。
首先,與欲求或厭惡相結合的總是愉快(Lust)或不快(Unlust),而我們將愉快或不快之感受性稱為情感(Gefühl);但反過來並非總是如此。因為可能有一種愉快,它根本不與任何對於對象的欲求相聯結,而是已經與我們對於一個對象所形成的純然表象(不論這些表象之對象存在與否)相聯結。其次,對於欲求底對象的愉快或不快也並非總是先於欲求,並且不可永遠被視為欲求之原因,而是也可以被視為其結果。
但我們之所以將在一個表象上產生愉快或不快的能力稱為情感,係由於這兩者均包含在我們的諸表象之關係中純然主觀之物,而決不包含任何對於一個對象的關係,以形成關於該對象的可能知識 (甚至關於我們的狀態之知識)。而通常連感覺――撇開由於主體之特性而繫屬於這些感覺的性質(例如紅、甜等性質)不論――也都作為知識要素(Erkenntnisstück)而關聯到一個對象,而(對於紅與甜的)愉快或不快卻絕對不表示對象中的任何東西,而是僅表示對於主體的關係。正是基於上述的理由,愉快或不快本身無法得到進一步的解釋,而是我們充其量只能指出它們在某些關係中有什麼後果,以便使它們在運用中可辨識。
我們可以將必然與(對於這樣一個對象,即其表象如此觸動情感的對象之)欲求相結合的愉快稱為實踐的愉快:無論它是欲求之原因還是結果。反之,有一種愉快並不必然與對於對象的欲求相結合,故它根本不是對於表象底對象之存在的一種愉快,而是僅依附於表象;我們可以將這種愉快稱為純然觀照的愉快(bloß kontemplative Lust)或無為的欣悅(untätiges Wohlgefallen)。我們將後一種愉快之情稱為品味(Geschmack)。因此,在一門實踐哲學中,我們並不將品味當作一個內屬的(einheimisch)概念來談論,而是充其量僅附帶地談論它。但論及實踐的愉快,則欲求能力之規定――這種愉快必然作為原因而先於它――便依狹義而稱為欲望(Begierde),而習慣性的欲望便稱為愛好(Neigung);再者,由於愉快與欲求能力之聯結――只要知性根據一項普遍的規則判定這種聯結是有效的(充其量也只是對於主體而言)――稱為興趣(Interesse),則實踐的愉快在這種情況下便稱為愛好底興趣。反之,如果這種愉快只能跟隨於欲求能力之一項居先的規定,它就得稱為一種智性的愉快(intellektuelle Lust),而對於對象的興趣就得稱為一種理性興趣(Vernunftinteresse);因為如果興趣是感性的,而不僅是以純粹的理性原則為依據,則感覺就得與愉快相結合,且因此能決定欲求能力。儘管當我們必須假定一種僅是純粹的理性興趣時,不得將任何愛好底興趣強加於它,但是為了便於語言之運用,我們可以承認一種甚至對於只能作為一種智性的愉快底對象的東西之愛好有一種出於純粹的理性興趣之習慣性的欲求,但這樣一來,這種愛好就不會是理性興趣之原因,而是其結果,而我們可以稱之為非感覺的愛好(sinnenfreie Neigung/ proprnsio intellectualis)。
貪欲(渴望〔Gelüsten〕)――作為決定欲求的刺激――還得與欲求本身加以區別。貪欲始終是一種感性的、但尚未發展成欲求能力底活動的心靈規定。
依乎概念的欲求能力,就其行動之決定根據見諸它自身之中,而非在對象中而言,稱為任意作為或不為的能力。就它與其產生對象的行為能力之意識相結合而言,它稱為意念(Willkür);但若它不與這種意識相結合,其活動便稱為一項願望(Wunsch)。如果欲求能力之內在的決定根據、因而甚至意願都見諸主體底理性之中,它便稱為意志(Wille)。因此,意志之為欲求能力,並非(像意念一樣)著眼於它與行為相關聯,而毋寧著眼於它與意念底行動之決定根據相關聯;而且它本身根本沒有任何決定根據,而是就它能決定意念而言,它就是實踐理性本身。
就理性能決定一般而言的欲求能力而言,不僅是意念,純然的願望也可被包含於意志之中;能為純粹理性所決定的意念稱為自由的意念。只能為愛好(感性衝動、刺激〔stimulus〕)所決定的意念則是動物性的意念(tierische Willkür/arbitrium brutum)。反之,人類的意念是這樣一種意念:它固然為衝動所觸動(affiziert),但不為它所決定(bestimmt);且因此它本身(不論理性之習得的技巧)並非純粹的,但卻能由純粹意志決定其行為。意念底自由是它之無待於感性衝動底決定;這是自由之消極概念。其積極概念則是:純粹理性能夠本身就是實踐的。但這要成為可能,只能藉由使每一行為之格律依從於「這項格律適於作為普遍法則」這個條件。因為當它作為純粹理性而被應用於意念(而不論其對象)時,它作為原則底能力(在此是指實踐原則,因而是作為立法的能力)――在此它欠缺法則底質料――,只能使「意念底格律適於作為普遍法則」這項形式本身成為意念之最高法則與決定根據;再者,既然人底格律由於主觀的原因,並不自然地與那些客觀原則協調一致,則理性只能絕對地將這項法則規定為禁制或命令之令式。
有別於自然法則,這些自由底法則稱為道德的(moralisch)。就它們僅涉及純然的外在行為及其合法則性而言,它們稱為法律的(juridisch);但若它們也要求:它們(法則)本身應當是行為之決定根據,它們便是倫理的(ethisch),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說:與法律的法則協調一致是行為之合法性(Legalität),與倫理的法則協調一致是行為之道德性(Moralität)。前一種法則所涉及的自由只能是在意念之外在運用中的自由,但後一種法則所涉及的自由卻能是不僅在意念之外在運用中而且在其內在運用中的自由――就意念為理性法則所決定而言。因此,我們在理論哲學中說:在空間中只有外感之對象,但在時間中卻有一切對象,既有外感之對象,也有內感之對象;因為兩者底表象均是表象,而且就此而言,均屬於內感。同樣的,無論我們在意念之外在運用還是內在運用中看待自由,其法則作為一般而言的自由意念之純粹實踐的理性法則,必然也是這種意念之內在的決定根據――儘管我們不必總是從這方面來看待這些法則。
II. 論道德底形上學之理念與必然性
對於自然科學(它關乎外感底對象),人們必須擁有先天的原則;再者,在應用於特殊經驗的自然科學(即物理學)之前,以形上的自然科學之名預先提出這些原則之系統,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這已在他處證明過了。然而,物理學能(至少當它意在使其命題免於錯誤時)根據經驗底證據假定若干原則是普遍的――儘管這些原則若要在嚴格的意義下普遍有效,它們就得由先天的根據被推衍出來,如同牛頓假定在物體之相互影響中作用與反作用相等之原則是以經驗為根據,但還是將它延伸到整個物質性自然之外。化學家則走得更遠,而將關於物質藉由其自身的力量結合與分離之最普遍的法則完全建立在經驗之上,但還是信賴其普遍性與必然性,以致他們在以這些法則所進行的試驗中並不擔心發現錯誤。
然而,道德法則之情況則不同。唯有就它們能被理解為有先天根據的且是必然的,它們才被視為法則;甚至如果關於我們自己及我們的行止之概念與判斷包含只能由經驗學得的東西,它們就根本不表示任何道德之物;再者,如果我們比方說受到誘惑,讓出自經驗底來源的某物成為道德原理,我們就陷入最糟糕且最有害的錯誤之危險。
如果道德論(Sittenlehre)無非是幸福論,則為了它而到處尋求先天的原則,便是荒謬的。因為說理性還在經驗之先就能理解,憑藉什麼手段我們能得到對生命之真正快樂的持久享受,不論聽起來是多麼言之成理,但我們在這方面先天地教導的一切,若非同義反覆,就是毫無根據的假定。唯有經驗能教導,什麼東西帶給我們快樂。唯有對於食物、性、休息、運動的自然衝動,以及(在發展我們的自然稟賦時)對於榮譽、我們的知識擴充之衝動等等才能讓人知道,而且讓每個人僅僅以其特殊的方式知道,他該將那些快樂置於何處:也正是經驗才能教導他,他該憑藉什麼手段去尋求那些快樂。在此,所有表面上先天的推理其實無非是藉由歸納而被提升至普遍性的經驗,而這種普遍性(根據一般的、而非普遍的原則〔secundum principia generalia non universalia〕)對此目的而言仍然是不足的,以致我們必須容許每個人有無限多的例外,才能使他對其生活方式的選擇適應其特殊的愛好及他對樂趣的感受性,而最後卻僅僅由於他自己的或他人的損失而變得明智。
然而,道德底學說之情況則不同。這些學說對每個人下命令,而不考慮其愛好,僅因為且鑒於他是自由的,而且擁有實踐理性。在它們的法則中之教導並非取自對每個人自己及其中的動物性之考察,亦非取自對於世事(所發生之事與我們的行為方式)的知覺(儘管Sitten這個德國字,正如mores這個拉丁字一樣,僅意謂儀節與生活方式),而是理性命令我們應當如何行為(儘管尚未出現其事例),而它也不考慮這會為我們帶來的利益(當然唯有經驗能教導我們這種利益)。因為儘管理性允許以一切對我們可能的方式去尋求我們的利益,此外或許也能基於經驗底證據而指望在遵循其命令時(特別是另外考慮到明哲時)比違背其命令時大致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其作為命令的規範之權威卻非以此為根據,而是它僅利用這些規範(作為建議)來平衡反其道而行的誘惑,以便先行在實踐的評斷中調節一個偏欹的天平之錯誤,而且這樣一來,首度保證這個天平因一種純粹實踐理性底先天根據之重量而傾斜。
因此,如果純然來自概念的先天知識之系統稱為形上學,則一套並非以自然為對象、而是以意念(Willkür)底自由為對象的實踐哲學將預設並且需要一門道德底形上學;這就是說,擁有這樣的一門形上學本身便是義務,而且每個人自身也擁有它(儘管通常是以隱晦的方式);因為若無先天的原則,他如何能相信自身擁有一種普遍的立法呢?但如同在一門自然底形上學當中也必須有將那些關於一般而言的自然之普遍的最高原理應用於經驗底對象的原則,一門道德底形上學也不能欠缺這類原則,而且我們將時常必須以人之特殊本性(Natur)──它唯有靠經驗去認識──為對象,以便在這種本性中印證由普遍的道德原則得出的結論,但卻不會因此而對這些道德原則之純粹性有所損害,也不會因此而使其先天來源受到懷疑。這等於是說:一門道德底形上學無法以人類學為根據,但卻能應用於人類學。
一門道德底形上學之對應物──作為一般而言的實踐哲學之畫分中的另一環節──當是道德的人類學。但是道德的人類學當僅包含在人性中有礙及有助於履行道德底形上學之法則的主觀條件,亦包含道德原理之形成、傳播與強化(在教育中,即在學校底教導與對民眾的教導中),以及其他這類以經驗為根據的學說與規範。再者,道德的人類學是不可欠缺的,但千萬不得先於道德底形上學而被提出來,或是與道德底形上學相混雜,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有提出虛假的或至少是可寬容的道德法則之危險──這些道德法則將僅是未達成之事冒稱為無法達成,而此事之所以未達成,正是由於法則之純粹性(法則之優點也在於此)未被理解與闡明,或者甚至不正當的或不純潔的動機被用於本身合乎義務的且善的事情上,而無論是為了引導評斷,還是為了訓練心靈遵從義務(其規範絕對必須單由純粹理性先天地提出),這些動機都不留下任何可靠的道德原理。
但是關於方才提到的畫分所從屬的上一級畫分,即哲學之畫分為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以及「實踐哲學只能是道德哲學」之義,我已在他處(在《判斷力批判》中)解釋過了。一切據稱是依據自然法則而為可能的實踐之物(技藝〔Kunst〕之真正工作),就其規範而言,完全依待於自然底理論;唯有依乎自由法則的實踐之物才能有原則,而這些原則不依待於任何理論;因為在自然底規定之外就無理論存在。因此,哲學之實踐部分(與其理論部分並列)不能意謂任何技術上實踐的學說,而只能意謂道德上實踐的學說;再者,如果依乎自由法則(相對於自然)的意念之技巧在此也該被稱為技藝,則這必須僅意謂這樣一種技藝,即是使自由底系統像自然底系統一樣可能的技藝;如果我們能夠借助於這種技藝,甚至完全履行理性為我們規定的事情,並且將其理念付諸實現,這真是一種神性的技藝。
III. 道德底形上學之畫分
一切立法(不論它規定內在行為還是外在行為,亦不論它先天地藉由純然的理性,還是藉由他人之意念來規定這些行為)都需要兩項要素:首先需要一項法則,它在客觀方面將應當發生的行為表述為必然的,也就是說,使這個行為成為義務;其次需要一項動機,它在主觀方面將對於這個行為的意念之決定根據與法則底表象聯結起來。因此,第二項要素是:法則使義務成為動機。前者將這個行為表述為義務,而這僅是關於意念底可能決定(亦即實踐規則)的一種理論性知識;後者則將如此行動的責任與意念底一項決定根據一般性地在主體中結合起來。
因此,就動機而言,一切立法(即使就由於這項立法而成為義務的行為而言,一項立法可能與另一項立法協調一致,例如,在所有情況下,這些行為可能都是外在的)的確可能不同。使一個行為成為義務,並且使這項義務也成為動機的那種立法是倫理的(ethisch)。但是不將這項動機也包含於法則當中,因而在義務底理念本身之外也還容許另一項動機的那種立法是法律的(juridisch)。就後一種立法而言,我們不難領略:這種與義務底理念不同的動機必須取自意念之感受的(pathologisch)決定根據,即愛好與厭惡 ,而在其中,取自後一種決定根據,因為這應當是一種強制性的立法,而非一種招徠式的引誘。
單是一個行為與法則間的協調或不協調(而不考慮行為之動機),我們稱為合法性(Legalität/Gesetzmäßigkeit);但是使出於法則的義務之理念也成為行動底動機的那種協調或不協調,我們稱為該行為之道德性(Moralität/Sittlichkeit)。
依乎法律的立法之義務只能是外在的義務,因為這種立法並不要求這項義務底理念(它是內在的)本身是行動者底意念之決定根據,而且既然這種立法畢竟需要一項適合於法則的動機,它只能將外在的義務與法則相結合。反之,倫理的立法固然也使內在的行為成為義務,但決不排除外在的行為,而是一般性地涉及一切構成義務的東西。但正因為倫理的立法也將行為之內在動機(義務底理念)包含於其法則之中――這種規定決不會見諸外在的立法――,則儘管倫理的立法將以另一種立法(即外在立法)為依據的義務當作義務而納入其立法中,成為動機,但是它不能是外在的立法(甚至不是一個神性意志之外在立法)。
由此可知:一切義務僅因為它們是義務,便也屬於倫理學;但是它們的立法並不因此就一槪被包含於倫理學之中,而是許多義務之立法係在倫理學之外。故倫理學要求:我必須履行我在一項契約中所作的承諾(儘管對方無法強迫我這麼做);不過,倫理學將來自法權論的法則(pacta sunt servanda〔契約必須遵守〕)及與該法則相對應的義務假定為既成的。因此,「所作的承諾必須遵守」這項立法並不存在於倫理學之中,而是存在於法權論(Ius)之中。於是倫理學所教導的只是:即使去除將法律的立法與上述的義務相結合之動機,即外在的強制,單是義務底理念已足以作為動機了。因為若非如此,而且立法本身並非法律的,因而由這種立法所產生的義務並非依本義而言的法律義務(有別於德行義務),我們就會將忠誠之履行(根據他在一項契約中的承諾)與仁慈(Wohlwollen)底行為及對於這些行為的義務歸於一類,而這完全行不通。遵守承諾並非一項德行義務,而是一項法律義務,我們可以被強制去履行它。但是甚至在不容施加強制的情況下也這麼做,還是一個有德的行為(德行之證明)。因此,法權論與德行論之不同,並非由於它們的不同義務,而毋寧是由於將一項動機或另一項動機與法則相結合的立法之不同。
倫理的立法(縱使義務可能是外在的)不能是外在的立法;法律的立法也能是外在的立法。故遵守合乎契約的承諾是一項外在的義務;但是「不考慮任何其他的動機,只因這是義務而這麼做」的命令卻僅屬於內在的立法。因此,並非作為特殊種類的義務(我們被責成去做的一個特殊種類的行為)――因為不論在倫理學中還是在法律中,它都是一項外在的義務――,而是因為在上述的事例中,立法是一種內在的立法,而且不能有任何外在的立法者,責任才被歸諸倫理學。正因此故,儘管仁慈底義務是外在的義務(對於外在行為的責任),但它們還是被歸諸倫理學,因為它們的立法只能是內在的。倫理學當然也有其特殊的義務(例如對自己的義務),但是它與法律還是有共通的義務,只是責成底方式不同而已。因為只因這是義務而付諸行為,並且使義務本身底原理(不論義務來自何處)成為意念之充分的動機,這是倫理立法之特點。因此,固然有許多直接的倫理義務,但是內在的立法卻也使得其餘的義務全都成為間接的倫理義務。
IV. 道德底形上學之預備概念(普遍實踐哲學)
自由底概念是一個純粹的理性概念,正因此故,它對於理論哲學而言,是超越的(transzendent),也就是說,它是這樣一種概念:在任何一種可能的經驗之中,並無適當的例子能被提供給它,故它並不形成一種對我們來說可能的理論性知識之對象,而且絕對無法被視為思辨理性之一項構造的(konstitutiv)原則,而是僅能被視為其一項規制的(regulativ)、而且只是消極的原則,但在理性之實踐運用中,它卻藉由實踐原理證明其實在性――這些作為法則的實踐原理證明純粹理性無待於一切經驗條件(一般而言的感性之物)而決定意念的一種因果性,並且證明在我們內部的一種純粹意志(道德的概念與法則根源於這種意志)。
無條件的實踐法則――它們稱為道德的――係以自由之這種(在實踐方面)積極的概念為根據。對我們――我們的意念在感性上被觸動,且因此並不自然地合乎純粹意志,而是經常與它相牴牾――而言,這些實踐法則是令式(命令或禁制),而且更確切地說,是定言的(無條件的)令式;這使它們有別於技術的令式(技術底規定)――這些令式始終只是有條件地下命令。根據定言令式,某些行為是容許的(erlaubt)或不容許的(unerlaubt),亦即道德上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但若干行為或是其反面卻是道德上必然的,亦即有約束性的(verbindlich)――由此便為那些行為產生義務(Pflicht)底概念。對義務的遵從或違背固然也與一種特殊種類的愉快或不快(一種道德的情感)相結合,但是在理性之實踐法則中,我們決不考慮這些情感;因為這些情感無關乎實踐法則之根據,而是僅關乎實踐法則決定我們的意念時在心中的主觀作用,並且能隨主體之不同而不同(而在客觀方面,亦即在理性之判斷中,對這些法則之有效性或影響無所增損)。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兩部分當中,以下的概念是共通的。
責任(Verbindlichkeit)是服從理性底定言令式的一個自由行為之必然性。
令式是一項實踐的規則,它使本身偶然的行為成為必然的。它有別於一項實踐法則之處在於:後者固然表明一個行為之必然性,但卻不考慮:這個行為本身是否已必然內在地寓於行動主體(例如對一個神聖的存有者而言)之內,抑或它是偶然的(像是對人類而言)?因為在前一種情況下,沒有任何令式出現。因此,令式是一項規則,其表象使主觀上偶然的行為成為必然的,因而將主體呈顯為這樣一個主體,即它必須被強制(被強迫)與這項規則協調一致。定言的(無條件的)令式是這樣的令式:它決非間接地藉由一項能藉行為達成的目的之表象,而是藉由這個行為本身之純然表象(其形式)、因而直接地將這個行為設想為客觀上必然的,並且使它成為必然的;除了規定責任的學說(道德底學說)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實踐學說能提出這類令式之例證。一切其他的令式均是技術的,而且一概是有條件的。但是定言令式底可能性之根據在於:它們僅涉及意念之自由,而不涉及意念之任何其他的規定(藉由這項規定,一項意圖能被加諸意念)。
一個不違反責任的行為是容許的(erlaubt/licitum);而不受相反的令式所限制之自由稱為權限(Befugnis/facultas moralis〔道德的可能性〕)。由此自然可以理解:什麼是不容許的(unerlaubt/ illicitum)?
義務(Pflicht)是某人被責成去做的行為。因此,它是責任之質料,而且儘管我們能以不同的方式被責成去盡義務,但這可能是同一個義務(就行為而言)。
就定言令式表示對某些行為的一種責任而言,它是一項道德上實踐的法則。但由於責任不僅包含實踐的必然性(一般而言的法則所表示的就是這類東西),而是也包含強制,上述的令式若非一項命令底法則(Gebotgesetz),就是一項禁制底法則(Verbotgesetz)――這視乎是作為還是不作為被表述為義務。一個既不被命令、亦不被禁止的行為只是容許的,因為對這個行為而言,決沒有限制自由(權限)的法則存在,且因此也沒有義務存在。這樣一種行為稱為道德上無所謂的(sittlich-gleichgültig/indifferens〔無所謂之事〕,adiaphoren〔中性之事〕,res merae facultatis〔純屬可能之事〕)。我們可以問:是否有這類的東西?再者,如果有這樣一種行為的話,則為了使某人有依其意願去做或不做某事的自由,除了命令底法則(lex praeceptiva, lex mandati)與禁制底法則(lex prohibitiva, lex vetiti)之外,還需要有一項許可底法則(Er-laubnisgesetz/lex permissiva)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權限就不一定涉及一個無所謂的行為(adiaphoren〔中性之事〕);因為如果我們根據道德法則來看待這樣一種行為,它就不需要有任何特別的法則。
就一個行為受制於責任底法則而言,因而也就該行為中的主體依其意念底自由而被看待而言,這個行為稱為作為(Tat)。由於這樣一種活動,行動者被視為結果之發動者(Urheber),而且這個結果連同該行為本身能被歸責於他――如果我們事先認識使它們產生一項責任的法則。
人格(Person)是其行為能夠歸責的主體。因此,道德的人格性(Persönlichkeit)無非是一個有理性者在道德法則之下的自由(但心理學的人格性只是在其存在之不同狀態中意識到他自己的同一性之能力)。由此便可推知:除了一個人格為自己制定(或是單獨制定,或是至少與其他人格同時制定)的法則之外,他不服從任何其他的法則。
物(Sache)是一個無法歸責的東西。因此,自由意念之每個對象,其自身欠缺自由者,稱為物(res corporalis)。
一般來說,就一個作為合乎義務或違反義務(factum licitum aut illicitum)而言,它是正當或不正當(Recht oder Unrecht/rectum aut minus rectum)――不論義務本身在其內容或根源方面屬於什麼種類。一個違反義務的作為稱為逾矩(Übertretung/reatus)。
一種非故意的逾矩而仍能被歸責者,稱為純然的過失(Verschuldung/culpa)。一種故意的逾矩(亦即與「它是逾矩」的意識相結合之逾矩)稱為犯罪(Verbrechen/dolus)。依外在法則而為正當者,稱為正義的(gerecht/iustum);其不然者,稱為不義的(ungerecht/iniustum)。
義務之衝突(Widerstreit der Pflichten/collision officiorum s. obligationum)便是義務間的關係,它使得其中的一項義務(完全或部分地)取消另一項義務。但義務與責任畢竟均是表達某些行為之客觀的實踐必然性的概念,而且兩項相互對立的規則無法同時為必然的,而是當依其中一項規則而行為是義務時,依相反的規則而行為不但不是義務,反而甚至是違反義務的;既然如此,義務與責任之衝突根本是無法設想的(obligationes non colliduntur)。但極可能是責任底兩項根據(rationes obligandi)之一或是另一項根據不足以使人負有義務(rationes obligandi non obligantes),而兩者在一個主體及他為自己訂定的規則中結合起來;如此一來,其中的一項根據並非義務。當兩項這樣的根據相互衝突時,實踐哲學並非表示:較強的責任占有優勢(fortior obligatio vincit),而是表示:較強的責成根據(Verpflichtungsgrund)占有位子(fortior obligandi ratio vincit)。
一般來說,若對於約束性的法則而言,一種外在的立法是可能的,它們便稱為外在的法則(äußere Gesetze/leges externae)。其中有一些法則,即使沒有外在的立法,對於它們的責任也能先天地藉理性去認識,它們固然是外在的法則,但卻是自然的法則;反之,那些若無實際的外在立法就根本無約束性的法則(因此,若無約束性,它們就不成其為法則),稱為實定的(positiv)法則。因此,我們能設想一種僅包含實定法則的外在立法;但這樣一來,就得先有一種自然的法則來建立立法者之權威(亦即單憑其意念去約束他人的權限)。
使某些行為成為義務的原理是一項實踐法則。行動者基於主觀根據而為自己訂為原則的規則稱為其格律(Maxime);因此,即使法則相同,行動者之格律卻可能極為不同。
根本只是表明「何謂責任」的定言令式是:按照能同時被視為一項普遍法則的格律而行為!因此,你必須先根據你的主觀原理來看待你的行為;但是,這項原理是否在客觀方面也是有效的,你只能從以下這點去認知:由於你的理性藉由這項原理而同時將你設想為普遍法則之制定者,以此來檢驗這項原理,它具有這樣一種普遍立法之資格。
相較於由這項法則所能得出之重大且多樣的結論,這項法則極其簡易;再者,它顯然不帶有一項動機,就具有發號施令的威望――當然,一開始這必然會令人驚訝。但是當我們驚訝於我們的理性底一種能力,即藉由關於「一項格律具有實踐法則底普遍性之資格」的純然理念來決定意念的能力時,我們得悉:正是這些實踐法則(道德法則)首先顯示意念之一項特質,而思辨理性無論是基於先天的根據,還是藉由任何一種經驗,都達不到這項特質,而且如果思辨理性達到它,也無法在理論方面藉由任何東西去證實它,但上述的實踐法則卻無可反駁地證實這項特質,即自由;此時發現這些法則如同數學公設一樣,是無法證明的,但卻是確然無疑的,而同時見到實踐知識之整個領域在眼前開啟(在此,理性憑同樣的自由理念,甚至憑其關於「理論領域中的超感性之物」的理念中的任何其他的理念,必然發現一切都在眼前完全封閉了),就較不令人驚訝了。一個行為與義務法則之協調一致是合法性(Gesetzmäßigkeit/legalitas),一個行為底格律與法則之協調一致是這個行為之道德性(Sittlichkeit/moralitas)。但格律是行動之主觀原則,主體以它作為自己的規則(即他想要如何行動)。反之,義務底原理是理性絕對地、因而客觀地命令於主體之事(他應當如何行動)。
因此,道德論之最高原理是:按照能同時被視為普遍法則的格律而行動!任何不符合這項資格的格律都是違背道德的。
法則出自意志;格律出自意念。在人之中,後者是一種自由的意念;意志所涉及的無非只是法則,既無法被稱為自由的,亦無法被稱為不自由的。因為意志不涉及行為,而是直接涉及對於行為底格律的立法(因而涉及實踐理性本身),所以也是絕對必然的,而且甚至沒辦法受到強制。因此,唯有意念才能被稱為自由的。
但是意念之自由無法如一些人可能嘗試過的,被界定為選擇依乎或悖乎法則而行動的能力(libertas indifferentiae〔無記的自由〕)――儘管作為事相(Phänomen)的意念在經驗中為此提供諸多的事例。因為我們僅知道自由(如同它首先藉由道德法則而為我們所知悉)是我們內部的消極特質,即不受任何感性的決定根據之強制而行動。但若將它當作理體(Noumen)來看,亦即就身為智性體(Intelligenz)的人對感性意念加以強制之能力而觀,因而就其積極特性來說,我們決無法在理論方面呈顯它。但我們的確能理解:儘管身為感性存有者(Sinnenwesen)的人在經驗上顯示一種不僅合乎法則、而是也悖乎法則而抉擇的能力,但這無法界定他身為智思存有者(intelligibeles Wesen)的自由;因為現象無法使任何超感性的對象(自由的意念卻屬於此類)可理解。我們也能理解:自由決不能存在於「理性的主體也能作一項與其(立法的)理性相對抗之抉擇」――縱使經驗極常證明這類事情之發生(但我們無法領會其可能性)。蓋承認一個(經驗底)命題是一回事,而使它成為(自由意念底概念之)解釋原則及普遍的辨別標誌(有別於動物性的或奴性的意念〔arbitrium brutum s. servum〕),是另一回事;因為前者並非主張:這項標誌必然屬於這個概念,但這卻是後者所要求的。其實,唯有關聯於理性之內在立法的自由才是一種能力;偏離於這種立法的可能性是一種無能。而前者如何能由後者得到解釋呢?這是一項定義,它在實踐的概念之外還加上其踐履(如經驗所教導的);這是一項混成的解釋(Bastarderklärung/definitio hybrida) ,它錯誤地呈顯這個概念。
法則(一項道德上實踐的法則)是個包含一項定言令式(命令)的命題。藉一項法則下命令者(imperans)是立法者(Gesetzgeber/legislator)。他是依乎法則的責任之制定者(Ur- heber/autor),但未必是法則之制定者。在後一種情況下,法則便是實定的(偶然的)與任意的。藉由我們自己的理性先天地且無條件地責成我們之法則,也能被表達為來自一個最高立法者之意志,亦即一個只有權利而無義務的立法者之意志(因而是神性的意志);但這僅意謂一個道德存有者――其意志對所有人而言都是法則,但卻毋須將他視為法則之制定者――之理念。
道德意義下的歸責(Zurechnung/imputatio)是藉以將某人視為一個行為之發動者(causa libera〔自由因〕)――這麼一來,這個行為便稱為作為(Tat/faktum),並且受制於法則――的判斷;但如果這項判斷同時具有從這個作為而來的法律後果,它便是一種有法律效力的歸責(imputatio iudiciaria s. valida),否則它便只是一種評斷性的歸責(beurteilende Zurechnung/imputation diiudicatoria)。有權作有法律效力的歸責之人格(自然人格或道德人格)稱為法官或甚至法庭(iudex s. forum)。
若某人依義務所做的,多於他能依法則而被強迫去做的,其所為便是有功績的(vedienstlich/meritum);若他所做的僅剛好符合法則之要求,其所為便是本分(Schuldigkeit/debitum);最後,若他所做的少於本分所要求的,其所為便是道德的過失(Verschuldung/demeritum)。一項過失之法律後果是懲罰(Strafe/poena);一項有功績的作為之法律後果是酬賞(Belohnung/praemium)(假使在法律中所預告的酬賞是動機的話);行事與本分之相稱根本無任何法律後果。善意的回報(gütige Vergeltung/remuneration s. repensio benefica)與作為之間根本無任何法律關係。
一個盡本分的行為之善果或惡果――以及不做一個有功績的行為之後果――無法被歸責於主體(modus imputationis tollens〔否定歸責律〕)。
一個有功績的行為之善果――以及一個不正當的行為之惡果――能被歸責於主體(modus imputationis ponens〔肯定歸責律〕)。
在主觀方面,行為底可歸責性(Zurechnungsfähigkeit/im-putabilitas)之程度可根據在此必須克服的障礙之大小來評估。(感性之)自然障礙越大,(義務之)道德障礙越小,善的作為就越是被算作功績,例如,當我以可觀的犧牲將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人從重大的危難中拯救出來時。
反之,自然障礙越小,出於義務底理由的障礙越大,(作為過失的)逾矩就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因此,在歸責當中,心靈狀態――究竟主體是感情用事,還是以冷靜的思慮行事――形成一項具有後果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