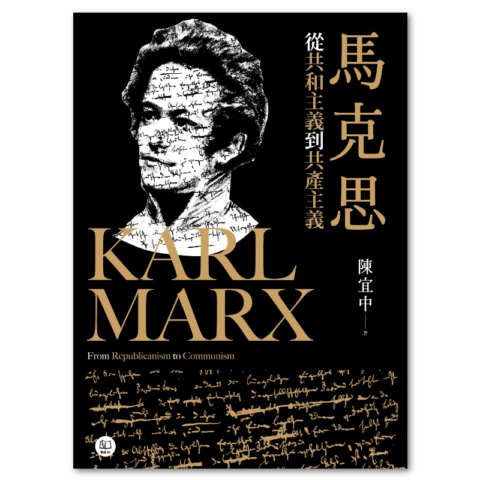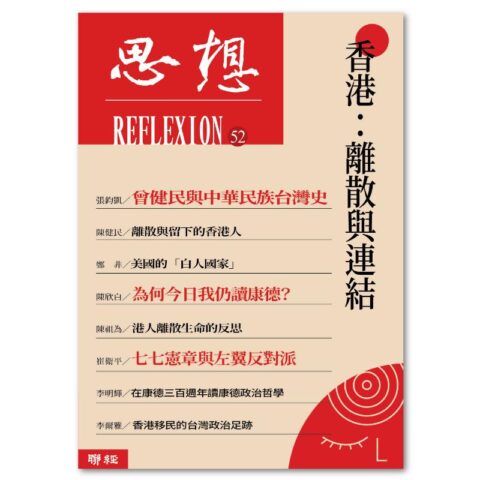歷史與現實(思想2)
出版日期:2006-07-10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328
開數:25開
EAN:9789570830330
系列:思想
尚有庫存
一份以「思想」為名的刊物,不能不強調思想的歷史性格;思想藉著歷史存活、在歷史中生長。純粹的「當下」,只是一堆莫名的事實。將當下放進歷史之中,事實才有來龍去脈、取得面貌和意義,才可能理解,思想才有立足和施展的餘地。所以,思想要生根發枝,首先要喚醒與正視歷史意識。不過,歷史意識談起來不會都這麼從容動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聯邦德國的文化界與史學界,針對納粹階段的德國史,爆發過一場激烈而重要的「史學家論戰」。論戰中間,一位保守派史學家留下一句名言:「在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度裡,誰提供記憶、塑造概念、詮釋過去,誰就贏得了未來。」──歷史具有決定性的政治功能,沒有人會否認。在近年台灣,如何敘述和詮釋近代歷史、如何編纂歷史教科書、如何評價歷史人物,不斷引起爭議和衝突,不正足以說明歷史與政治的緊密關係嗎?面對這種狀況,「歷史意識」與政治的關係,當然值得一探。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吳乃德
當穆罕默德遇上言論自由 陳宜中
追蹤狡猾的非理性 約翰‧唐恩
召喚沈默的亡者:跨越國族歷史的界線 沈松僑
當代台灣歷史論述的雙重挑戰 王晴佳
歷史意識是種思維的方法 周樑楷
也論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兼評李丁讚等所著《公共領域在臺灣:困境與契機》郝志東
期待內在批判的璀璨未來:評《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 湯志傑
百年前的台灣旅客:梁啟超與林獻堂 謝金蓉
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 鄭鴻生
台灣人文寓言:國家哲學院 陳正國
對談 去殖民與認同政治:訪談《成為「日本人」》作者荊子馨 柯裕棻
福山論「新保守主義之後」 鍾大智
施琅連續劇爭論與中國大陸政治文化 成慶
香港《二十一世紀》施密特專輯 李國維
兩位女性主義元老的生死恩怨 李樹山
密爾兩百年紀念 陳毓麟
俄國哲學史新論 彭淮棟
加拿大學者在北京教政治哲學 廖斌洲
美國學院左派的自殘 鍾大智
哈伯瑪斯談知識分子的覺察能力 魏楚陽
追尋一個消逝的年代:《八十年代訪談錄》 楊羽雯
致讀者
一位年輕朋友對《思想》這份刊物的第一個反應是:「名字太老氣了」。的確,今天坐談思想,是有點前朝遺老的氣息,雖然「前一個時代」該如何刻畫界定,也不容易說得清楚。1920年代的前衛、1970年代的反叛,雖然都引領一時之風騷,如今不是得用泛黃褪色的背景呈現,才能出味嗎?每個人都是一己時代的產兒,思想只能把握它的時代。──這是黑格爾的話。不過黑格爾也相信,因為思想有記憶和歷史可言,足以抵禦時間的侵蝕吞噬,所以思想可以跨越時代。
一份以「思想」為名的刊物,不能不強調思想的歷史性格;思想藉著歷史存活、在歷史中生長。純粹的「當下」,只是一堆莫名的事實。將當下放進歷史之中,事實才有來龍去脈、取得面貌和意義,才可能理解,思想才有立足和施展的餘地。所以,思想要生根發枝,首先要喚醒與正視歷史意識。
規劃本期當初,我們就決定要以「歷史意識」為主題做個專輯。可是到了全書編完,我們不禁失笑:哪一篇文章不涉及歷史?即使專輯以外的文章、即使柯裕棻與荊子馨兩位教授的對談,豈不也是在探討此時此地歷史意識的不同面向嗎?在台灣,由於歷史一路至今的轉折總顯得意外而被動,因此歷史意識的扭曲作祟也隨處可見,有深沈者,也有可以欣賞玩味者。感謝我們的作者,讓這些多采多姿的議題在這裡紛雜併陳。
前一期《思想》出刊之後,讀者的批評之一即是少數文章過份艱澀。就這一點來說,本期的《思想》未必有所改善。不過,鄭鴻生、謝金蓉兩位的文章,證明了嚴肅的議題一樣可以用親和的方式娓娓道來,我們盼望刊登更多的這型文章。鄭鴻生先生談自己與岳父的對話、談《小市民的心聲》與《野火集》的時代意義、談水龍頭在東歐、台灣、上海、與以色列的雷同象徵,為的是突出「落後與現代」這個屬於第三世界的典型話題,如何支配著台灣人的歷史意象與自我意識。謝金蓉女士退回百年前的台北與霧峰,描繪海峽兩岸一代人物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相會,其間光景在今昔兩種似異又同的情境對比之下,格外令人低迴含咏。
不過,歷史意識談起來不會都這麼從容動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聯邦德國的文化界與史學界,針對納粹階段的德國史,爆發過一場激烈而重要的「史學家論戰」。論戰中間,一位保守派史學家留下一句名言:「在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度裡,誰提供記憶、塑造概念、詮釋過去,誰就贏得了未來。」──歷史具有決定性的政治功能,沒有人會否認。在近年台灣,如何敘述和詮釋近代歷史、如何編纂歷史教科書、如何評價歷史人物,不斷引起爭議和衝突,不正足以說明歷史與政治的緊密關係嗎?面對這種狀況,「歷史意識」與政治的關係,當然值得一探。
沈松僑、王晴佳、周樑楷三位的文章,組成了本期「歷史與現實」專輯。他們都是歷史學家,卻有著迥異的視野與背景。沈松僑先生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國族意識的產生與成長、傳播,特別探討歷史論述在國族意識中的關鍵貢獻、強調其間的「共生關係」,著作一向帶有批判性格。有懍於史學家面對國族主義試探時,往往缺乏道德資源加以抗拒,他格外強調史學的專業自主性、也呼籲史學家加強本身的倫理自覺。王晴佳先生出身大陸、執教美國,卻對台灣史學五十年的發展軌跡,具有高度的關注。其實,台灣史學界並不是不關心本身的成長歷程;高明士教授主編、國科會出版的《戰後台灣的歷史學研究》八冊,已經提供了最豐富的材料。但是面對材料,台灣史學家的反思還很難見到,只有王晴佳願意提供一個鳥瞰式的回顧與評價。他的觀察有得有失,不過不難猜想,這些觀點最後會無聲地沈入一片緘默之海中。周樑楷先生身為教育部高中歷史綱要編撰小組的召集人,一度捲入有關歷史教科書的爭議,成為新聞人物。不過在本刊上,他寧可退回基本層次的概念釐清工作,以更積極的態度,超越政治對於史學的染指企圖。這些文章或許不好讀,可是您會覺得有必要一讀。
必須強調,所謂用記憶與關於過去的敘事掌握未來,一個意思固然是按照今天的政治需求「建構」過去,但是另一個更積極的用心,卻是吸取歷史教訓,化昨日的暴行與血淚為今人的道德資源與道德能力,讓是非善惡的分辨可以更為清爽。吳乃德先生關於「轉型正義」的文章,直接探討歷史的這一個面向,其倫理─政治的意義特別沈重。這個面向的歷史反思,固然也涉及政治。但是它的政治性格不在於為當朝體制服務,而在於向今昔的有權者提出詰問,也向搖尾其後的犬儒知識份子發出警告。在台灣、在中國大陸,這個問題可能是未來幾個世代的道德思考的源泉、道德教育的首要課題。
當然,這個問題不是沒有它的背面。無論個人的過去或者民族的歷史,是不是都有一些片段是不堪回首的、不忍重提的、只能寬恕甚至遺忘的?無論如何,「面對」與「不面對」之間的倫理張力,倒正足以刺激思考。我們很希望讓這個議題繼續發展下去。不過,下一期《思想》的主要論題,已經逐漸成形,可以在此簡單預告:我們邀請到了敏銳深思的作者,準備討論東亞幾地的「亞洲論」、準備檢討中國大陸新興的一種反普遍主義的文化政治論述、也準備繼續本期的歷史意識議題、以及其他好幾個有趣的話題。
當然,我們竭誠歡迎您來參與,開拓更多的討論。
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轉型正義」是所有從威權獨裁轉型至民主的新興民主國家,所共同面臨的政治和道德難題。對於那段記憶仍然鮮活的歷史──對人權普遍的蹂躪、對人性不移的冷漠、高傲的加害者、無數身心俱殘的受害者──對於這段歷史,我們應如何面對和處置?因為轉型過程不同、道德理念不同,不同的新民主國家對轉型正義經常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台灣的民主轉型至今,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我們對這項民主社會最重要的道德問題之處理,態度仍然是勉強的、不完整的。相較於比台灣更窮、更「落後」的國家在處理轉型正義上所獲得的成就,台灣的表現並不令人驕傲。
本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份以比較的觀點,討論新民主國家處理轉型正義所面臨的諸多難題,以及面對這些難題的不同方式。有些國家採取起訴、並懲罰加害者(甚至包括威權政府的統治者及其同僚)的嚴厲方式,有些國家刻意選擇集體遺忘這段歷史,有些國家則採取類似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的中間路線:只揭露真相、卻赦免加害者。本文第二部分討論台灣特殊的處理方式:賠償受害者、遺忘有加害者的存在、同時讓歷史荒蕪。本文也從台灣特定的轉型過程和威權統治經驗,解釋台灣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處理方式。第三部分則呼籲我們珍惜這段威權統治的歷史,將它化為台灣民主的重要資產,讓它成為民主教育和民主道德重建的重要教材。
轉型正義的難題
民主轉型之後,新的民主政府應如何處理過去威權政府對人權的眾多侵犯,對無辜生命的凌虐、甚至屠殺?具體地說,對威權政府中發號施令的高階層人士,我們應如何加以處置?對主動從事或被動服從指令而侵犯人權的情治、司法人員,我們應該如何對待?甚至,對於許許多多在威權政體中工作、也因此而得利的政府官員、媒體負責人、學術領導人,我們應該用何種道德態度來對待他們:譴責、輕視、或同理心的寬容?這些問題經常成為新民主政府和民主社會的政治和道德難題。而另一方面,對眾多遭受生命、自由和財產損失的人,我們又應當如何補償?這些問題一般稱為「回溯正義」,或「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的難題並非始自現代。對轉型正義的處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雅典。雅典的民主政體中曾經出現兩次短暫的獨裁政權,雅典人在獨裁政權崩潰後,都曾經溫和地處罰了獨裁政權的領導人和附庸者。 轉型正義成為當今學術、文化界熱門的題目,主要是因為第三波民主化的刺激。在1980年代之後的這一波民主化中,亞洲、非洲、南美洲和東歐共產國家的許多威權獨裁政體相繼崩潰。由於這一波的民主化是人類歷史上個案最多、規模最大的民主化浪潮,如何處理威權遺產,也就成為許多國家共有的難題。
轉型正義所面對的第一項難題,同時也是最困難的議題是:如何處理過去威權時期犯下侵犯人權、剝奪生命和自由、凌虐人道等罪行的加害者。加害者包括威權政府的統治核心權力菁英,以及接受其指令的較低階執行者。在某些國家,如南非和阿根廷等,許多對人權的侵害行為,是執行者由於當時政治氣氛和政治慣行、個人偏見和政治信念等,所從事的自發行為。處置威權政府的核心統治成員,和處置為數眾多執行者,面臨不同的法律和道德難題;而兩者都不容易解決。
處置威權政府的統治者和核心成員,在道德及法律層次上比較單純,可是在政治上卻較為複雜。統治階級的核心成員握有至高的權力,他們是獨裁體制的創建者、或維護者,理當為其統治下眾多的侵犯人權、違反人道罪行負責。這在道德層次上沒有太多的爭論。一般而言,在民主化之後,人民也都期待對加害者施以法律的懲罰。如果新生的民主政府不處理獨裁政權所犯的錯誤,不對加害者做某種程度的懲罰,新政府的合法性和支持度經常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尤其在那些對人權的侵犯甚為普及、規模甚為龐大的國家中(如南非、阿根廷、瓜地馬拉、東歐等),民主化之後人民普遍期待「正義」終於可以到來,受害者獲得補償和撫慰,加害者受到應得的懲罰。一般人民對「正義」的重視,其實也是民主社會生存的重要基礎。這種要求如果沒有得到滿足,人民對政治、對民主都會產生嘲諷和疏離。這對民主社會並沒有好處。而更嚴重的是,如果對正義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以前受害的一方經常會用相同的方式來迫害過去的加害者。例如南非由於沒有追究加害者,許多地區出現了黑人用類似過去白人對黑人所為來加諸白人的例子。
然而,新生的民主政體經常是脆弱的。新民主政府經常無法確知軍隊、情治系統是不是接受它、服從它。這些足以影響政局安定的機構,剛好又是威權統治的重要基石,也是最經常侵犯人權的機構。要懲罰威權時期的罪行,很難不追究到這些機構的領導人。擔心法律的追究和制裁,經常是這些威權領導階層抗拒民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某些國家中(如智利、阿根廷、南非等),反對派為了民主轉型得以順利成功,常常必須和威權統治的領導階層妥協,保證民主化之後不追究其過去的罪行。
除此之外,另一個更大的難題是:在這一波民主化中崩潰的威權體制,大多曾經維持相當長的時間。威權政體在漫長的統治過程中,創造了不少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追究政治領導階層的罪行,經常造成社會的緊張和分裂。特別是如果對威權統治的支持和反對,是以族群或種族為分野(如南非),這個問題就更不容易處理。
在這種兩難的政治情境下,不同的國家經常根據自己特定的政治和歷史情境,特別是民主轉型之前、轉型期間、以及轉型之後的政治狀況,而有不同的方式和策略。最嚴厲的方式是以違反人道的理由,處罰威權政府的首腦。此類型的國家包括羅馬尼亞以行刑隊槍斃共黨元首索西斯枯夫妻;保加利亞將元首齊夫科夫及其高級幹部判刑監禁;德國(以謀殺警察、而非政治壓迫之名)起訴東德共黨頭子何內克,雖然後者終因健康理由逃過牢獄之災;玻利維亞將軍人政府首領梅札判刑監禁35年不得假釋(同時將宣判日訂為「國家尊嚴紀念日」); 南韓對盧泰愚、全斗煥遲來的起訴(兩年之後又加以特赦); 以及目前還處於法律拉鋸戰中智利對皮諾契的起訴案。這些起訴、或懲罰最高統治者的案例,都受到國際甚大的矚目。
可是某些國家對轉型正義的追求,目標不只限於最高領袖和統治核心的成員,追訴和懲罰的對象甚至擴及中低階層的人員,包括威權政府的官員、情治系統的人員、以及執政黨的黨工。而懲罰的方式也不限於法律的起訴。德國統一之後,前東德的法官和檢察官將近一半失去先前的工作;另外有四萬兩千個政府官員被革職。 最極端的國家或許是捷克。該國在1991年通過「除垢法」(Lustration Law);名稱來自拉丁文的lustratio,意為「藉由犧牲以完成潔淨」。該法規定:曾經在威權政府中任職於情治系統、或特務機構的情治人員、線民,或前共產黨某個層級之上的黨工,五年之內不得在政府、學術部門、公營企業中擔任某個層級以上的職位。這個除垢法在捷克國內引發甚大的批評。批評者甚至認為此舉無異獵巫行動,本質就是「以道德十字軍來包裝政治權力鬥爭。」 國外的批評者則認為,類似除垢法的措施將使公民失去對新民主政府的信任。
這種爭論反映了追求轉型正義在道德和政治上的難題。相對於發號施令、建立威權體制的最高統治者及其核心成員,那些接受指令、或服從(不義的)法律之執行者,是不是有相同的法律和道德責任?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從心理學的實驗中我們知道,明知權威所下的指令不道德,可是卻加以服從是非常容易、也非常「合乎人性」的行為。我們也知道,下級的執行者有時候為了個人的利益和升遷,主動配合上意和法令侵犯人權。有的時候,則是沒有選擇。可是更多時候,兩者難以清楚分辨。在威權體制中,拒絕服從通常須要付出代價。因為義而承擔其代價固然值得欽佩;這樣的人永遠引發我們的道德嚮往和想像。可是對那些選擇服從的人,我們──有幸無須被迫做這種選擇的我們,有沒有立場對他們做道德的譴責?
另外一個現實的難題是界線的劃定。威權體制並不是獨裁者一個人的功業;他需要各個階層、各行各業的人幫助他。如果我們要追究侵犯人權的政治和道德責任,我們的界線何在?捷克哈維爾總統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發號施令的、服從的、支持的、甚至袖手旁觀的,都直接間接支持了威權統治。可是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有罪,至少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種類、相同程度的罪。哈維爾的論點在道德反省上或許是一個重要的啟發,可是卻無法作為政策的指導原則。如果我們不畫出一個合理的、清楚的責任界線,或許就會如波蘭的米緒尼克 (Adam Michnik) 所說的,報復懲罰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首先是昨日的舊政權中敵人,接著是昨日反對陣營中的戰友,然後就是今天為他們辯護的人。懲罰一但開始,仇恨必然隨之而至。
而對他們求取法律的追訴和制裁,則更具爭論。一方面,我們知道:民主政治建立在某些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之上。這些價值和原則是文明社會的共同規範,法律違反這些核心價值即缺乏正當性。「惡法亦法」的立場是很危險的。畢竟,獨裁者並不是以口令統治,而是依賴完整的法律體系。法律經常是獨裁者手中的利劍。可是另一方面,罪刑法定 (nulla poena sine lege) 卻也是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則:只有違反當時存在的法律之行為,才得加以處罰。放棄這項原則,將對民主社會的法律秩序帶來嚴重的後果。這也是為何匈牙利民主政府的憲法法庭,數次針對追究加害者的法律和國會的決議案,宣判為違憲的理由。 匈牙利憲法法庭的裁決,當然也引起無數的政治緊張和衝突。某些國家因此將法律追訴的對象,僅限定於那些即使在威權體制下也屬犯法的加害行為。
因為接受指令或服從法律而侵犯人權的加害者,我們到底應不應該對他們做道德的譴責,甚至法律的追訴?雖然在轉型正義的追求上經常面臨這個問題,可是至目前為止,它並沒有受到太多的討論。 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從德國一位法官的判決中,獲得若干啟發。1991年年底,德國開始審判兩位執法人員,指控他們於1984年守衛柏林圍牆期間,開槍擊斃試圖翻越圍牆的民眾。相較於前一個起訴圍牆守衛的案件,法庭在這次的審判過程中,從一開始就明顯堅守一個原則:控方只能訴諸東德當時已有的法律。然而法官在判決文中同時也指出:雖然法律賦予衛兵使用強力的方式阻止逃亡者,可是東德法律同時也規定,「必須盡可能不危害生命」。射擊逃亡者的腿部,應該比較符合兩德法律都同樣規定的「適當的措施」。因此,即使根據東德法律,衛兵射殺逃亡者的行為仍然犯了「過度使用權威」的罪行。然而這次判決更重要的是,法官給被訴者緩刑的機會,同時以如下宣示為後來的同類案件設下了重要的範例。首先,法官指出,「上級的命令」不能當作赦免、或合理化犯罪行為的藉口。可是,兩位衛兵在當時的情境下,難以獨立自主行動。「引導他們犯罪行為的因素並非自私自利、或罪惡的動機,而是當時他們所無法影響的環境,包括分裂德國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對抗,以及東德特殊的政治情境。」
這也就是說,一方面,政治壓迫行動的執行者,不能用接受上級指令和遵循法律當犯行免責的藉口。命令的執行仍然有甚大的彈性空間。「逮捕、偵訊」和「刑求」之間有甚大的分野:人性和野蠻的分野。「依法律規定的刑期判決」和「拒絕了解口供如何取得、拒絕求證、甚至拒絕聽取被告的辯護」也有甚大的差別:執行職務和政權幫兇的差別。在很多案例中,上級指令和依循法律,不能成為凌虐人性的的理由。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理解當時的政治氣氛和政治情境,了解人性在組織中、以及特定情境中的脆弱。這種情況下,我們或許可以不追究法律責任,卻不能刻意遺忘。
上述對轉型正義的處理方式,包括對最高統治者及其核心成員、以及壓迫組織中工作人員的追訴,並非每一個國家都有條件這樣做、或有意這樣做。有些國家,如波蘭、智利、和巴西等國,反對派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和統治團體達成協議,承諾在民主轉型之後不對其侵犯人權的罪行提出法律的追訴行動,以減低後者對民主化的抗拒,讓民主轉型可以順利進行。可是有些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雖然沒有經過這樣的妥協,仍然選擇刻意遺忘過去的歷史,放棄對統治團體和其幫手做任何的追究。這些國家包括西班牙、羅德西亞、和烏拉圭等。此種處理方式以西班牙為代表,稱為「祛記憶」(disremembering)策略。
在以上這兩個相反的取向之間,有些國家試圖以中間路線來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最經常被使用的是「真相委員會」的策略。其中最受世界矚目的,是南非師法智利和阿根廷而成立的「真相和解委員會」。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已經有超過二十個國家,成立類似的真相委員會。南非的真相委員會之所以能在成立之後,立即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和道德想像,有幾個主要原因。第一,南非數十年的種族隔離體制,對人權、人性、和生命的凌虐案例太多、太普遍。加害者不只是南非政府和它的軍警特務機構,甚至連黑人反對運動的參與者,也常對同志做出凌虐生命的行為。暴力行為──體制的和非體制的──長久存在而且十分普遍。如何面對這些令人震撼、傷感的普遍暴力,如何創造雙方可以共同生活的新社會,是艱難巨大的挑戰。第二,南非產生不少優秀的小說家,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長久以來,這些小說家透過他們的文學作品,呈現、批判、反省了種族隔離體制和白人暴力體制對人性的壓制、扭曲、和疏離。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早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引起世人對種族隔離體制極度的厭惡。如果種族隔離體制的崩解是從地獄到人間的過渡,世人好奇「真相和解委員會」將如何處置地獄中的邪惡。第三個原因,當然就是真相和解委員會的主席,黑人主教圖屠所具有的世界性的聲望和道德魅力。
真相委員會的特點是,在加害者完整交代其罪行的條件下,給予法律上的豁免。正如委員會的副主席波連所說的,真相和解委員會是一個必要的妥協。當時南非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特赦所有白人種族隔離政權中所有的成員。第二個選擇則是類似紐倫堡大審,起訴應該為大規模的人權侵害事件直接負責的人。如果種族隔離暴力體制的統治菁英堅持特赦,那麼民主化的協商可能破裂。而如果反對派堅持起訴加害者,和平的民主轉型過程可能無法成功。因此,真相和解委員會是舊時代通往新時代唯一的橋樑。
「真相和解委員會」除了是政治上的妥協之外,也經常被賦予更積極的目標。這個追求轉型正義的特殊途徑假定:雖然正義沒有獲得伸張,至少讓歷史真相得以大白、加害者得以懺悔、受害者得以安慰、後代得以記取教訓;同時更重要的,國家社會得以避免分裂。可是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的運作過程和結果顯示:大多時候真相並不能帶來和解。許多其他國家的例子也顯示:不同陣營的人對真相有不同的解釋;加害者的真相和受害者的真相經常是對立的。例如波蘭前共黨的的統治團體就認為,事實上是他們救了國家。他們問:匈牙利反抗蘇聯,造成多少人喪生?因此他們的政治壓迫,只是「衡量之下不得不然」,是「較小的惡」。 歷史記憶,特別是對歷史的解釋,很難避免主觀和對立。在對立沒有受到調和之前,真相不可能帶來和解。在討論歷史真相和歷史正義的下文第三節中,對這個問題會有更仔細的討論。
此種追求轉型正義的第三條路,除了是否能達成其積極目標受到懷疑外,它為了政治現實而放棄公義的追求也受到質疑。在道德上我們有沒有堅強的理由,足以合理化這樣的妥協?有些人認為,即使是善意地為了全社會的政治福祉,放棄對正義原則的追求,仍然須受某些條件的限定。 而在現實政治中,「真相和解委員會」只有真相沒有懲罰的途徑,所成就的似乎只是讓民主轉型較為順利,似乎並沒有為全社會帶來真正的和解。
以上是新民主國家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處置加害者的三個方式和策略。和上述眾多採取不同途徑的例子相較,台灣有一個特色:在台灣至少有一萬多個受害者,可是沒有任何一個加害者。將近二十年了,我們還不知道到底誰應該為這一萬多件侵害人權、凌虐生命的案件負責。因為沒有人需要負責,我們也就沒有討論處置方式的需要。
除了如何處置加害者之外,追求轉型正義的第二項工作和難題是:如何賠償受害者。因為政治壓迫而受害的人,在民主化之後必須給予「正義」:不論是歷史的真相、或物質的賠償和補償。這是毫無疑義的道德理念。可是什麼樣的「正義」?受害者、或其家屬有沒有權利要求真相?當他們要求的時候,社會有沒有義務盡全力滿足他們的要求?即使他們不要求,社會有沒有責任給他們真相?任何人、或全社會有沒有權利要求他們,為了社會的福祉而遺忘真相?
而物質的補償應該多少?補償到什麼程度?除了有形資產的損失,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補償無形的損失?例如:因為政治原因而被剝奪工作、或升遷的機會;妻子在身心上所受的煎熬;子女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因此有完全不同的人生?這些都是難以估計的無形損失。可是在台灣,連有形的、容易估計的損失,我們也吝於補償。全世界的新民主國家,不論其對加害者採取何種處置方式,對受害者總是盡可能地加以補償。除了波蘭之外,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對自由和生命的補償那樣不慷慨,對財產損失的補償又是完全的不理會。
為什麼呢?
缺乏歷史正義的轉型
民主化是台灣政治歷史中最重要的變動。雖然我們對民主化之後的政治狀況不滿意,可是較諸從前的台灣、現在的中國,這項政治變遷仍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不曾在白色恐怖時期生活過的人,以及依附或支持獨裁政權的人,不太能真正理解這樣的成就。可是民主轉型到底是誰的貢獻?台灣社會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共識;不同黨派立場的人仍在爭執之中。而誰又應為過去的政治壓迫、侵害人權的行為負責?台灣社會很少提出這個問題。轉型至今已近二十年,這兩個近代台灣最重要的、也最根本的道德問題,一個沒有確定的答案,另一個沒有被提出來。為什麼?
正如杭廷頓在其討論第三波民主化的書中指出的,新民主政府是不是追訴過去威權體制中的罪行,決定的因素並不是道德或倫理的考慮,而「完全是政治、是民主轉型過程的本質、以及轉型期間和轉型之後權力的平衡。」 如果民主改革是由上所發動,或者是和威權統治者談判的結果,那麼後者在轉型之後將仍保有甚大的政治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對過去罪行的追訴、以及揭露真相的歷史正義,都不可能。除了民主化途徑不同所造成的影響外,一位韓國學者同樣提到另一個和台灣特別相關的因素。菲律賓的民主化過程是威權獨裁政體被推翻,而南韓則是和平的民主化過程。依照上述杭廷頓的說法,菲律賓應該追求轉型正義,而南韓則否。可是歷史事實剛好相反:菲律賓對轉型正義絲毫不以為意,而南韓則起訴了威權時期的兩位最高領導者。這是因為另一個因素的作用:民主轉型之後各政治勢力在權力結構中的比重。